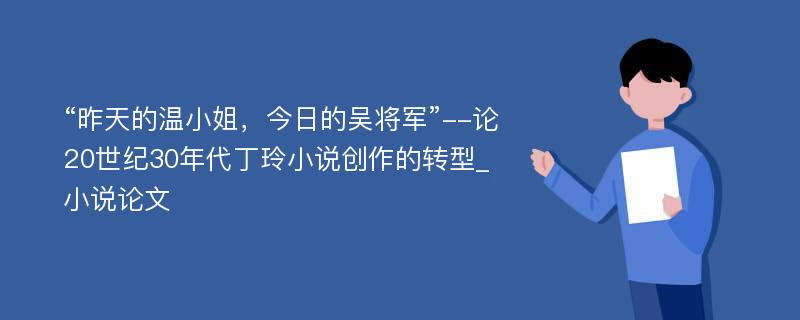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论丁玲1930年代小说创作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将论文,昨天论文,小姐论文,年代论文,今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9)06-0062-05
当文学创作以意识形态的正确与否为标准,而作品只有用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阐释才能获得意义时,那么它正在失去审美性与艺术的多义性而蜕变成一种知识教育;当作家先得到一种主题思想,然后有意识地从生活中寻找证据以创作符合某种先验理念的作品时,他(她)的作品只能是政策的图解;当一个女作家放弃性别意识而变成“政治人”的时候,她也正在失去最基本的个性。——在文学这个最需要艺术个性的领域,失去个体主体意识就失去了生命力,不仅会使文学丧失审美价值,造成伦理价值的高扬与历史价值的缺失,甚至无法为后世提供“以诗证史”的研究材料。
遗憾的是,丁玲的小说创作历程就是这样的。当然,丁玲只不过是革命文学创作队伍中留下以上缺憾的众多作者之一,但基于她在既成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极具悲剧意味的人生,因此,将其1930年代转型前后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仍具有重要的个案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一)
“与蒋光慈不同的是,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在她写作的第一个阶段里(1926-1929),丁玲最感兴趣的是大胆地以女性观点及自传的手法来探索生命的意义。她的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里那几篇,如《梦珂》及《莎菲女士的日记》等,都流露着一个生活在罪恶都市中的热情女郎的性苦闷与无可奈何的烦躁。很明显,由于寂寞及心情混乱,丁玲在她的日记式的小说里,把她的怨愤和绝望的情绪都发泄出来。”[1](P187)让我们由此进入她的小说世界。
《梦珂》[2]是丁玲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也是令她一鸣惊人的小说。“红鼻子老师”欺负女模特,梦珂仗义执言却招致“红鼻子”的寻衅污蔑,梦珂负气离开学校回到寄宿的姑母家。全家人对她呵护备至,二表哥晓淞和他的朋友澹明一起向梦珂发起“爱情攻势”。尤其表哥的热情让梦珂脸红心跳,她全然不知道晓淞这位情场老手时时“得意的称许起自己的智慧,自己审美的方法,并深深的玩味那被自己感动的那颗处女的心。这欣赏,这趣味,都是一种‘时尚’的,细腻的享乐”。梦珂渐渐发现了这个大家庭里的丑恶,比如大表嫂“温柔、蕴藉的心性”无法阻止大表哥的寻花冶游,以致表嫂感到“嫁人就是卖淫”,甚至觉得“一个妓女也比我好!也值得我去羡慕!”作品于此揭示了这个表面一团和气的大家庭“杀人于无形”的丑恶。而直接伤害梦珂的却是晓淞的虚伪:澹明带梦珂去一家宾馆,让她目睹了晓淞与一位太太的鬼混。梦珂伤心不已,晚上独自在花园伤心饮泣,没想到表哥与澹明也来到花园,通过他们的对话才知道,他们都是在玩弄她。绝望的梦珂离开姑母家,在金钱不济时报考了“圆月剧社”并成为女明星……也许是受到沈从文的影响,《梦珂》通过一个纯洁少女的遭际揭示都市的罪恶:梦珂回忆故乡酉阳的生活,充满美好记忆和浪漫温情;与乡村相比,都市充满欺骗、虚伪和假道学,甚至不容梦珂保持一点良心、主持一点点正义。都市使她走向歧路:先在姑母家学会了挥金如土而全然忘了父亲的艰辛,然后感情受亵渎而离家出走并步入乌烟瘴气的演艺界成为艺人。丁玲对梦珂在姑母家生活的描写明显受《红楼梦》影响,梦珂小心处事的样子极像林黛玉。小说的文字与表现手法虽显幼稚,却已显示出丁玲成为优秀作家的潜质。
当时的评论家说:“女作家丁玲的出现于文坛上,乃是一九二八年前后的事,她的第一篇小说《梦珂》一发表就惊骇了世人的耳目,而被许为新人,接着不时地,有新作发表,作风是时常地变换,而每个变换,却像给这个社会投下了一颗炸弹。”[3]她扔出的一颗重磅炸弹无疑是《莎菲女士的日记》,[4]作品透彻地描画了一个女性的恋爱心理,在当时就广受注目,以致“一说起《小说月报》,你会想起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几篇吧。是的,这是值得注意的,作者可是中国第一位女作家。”[5]《莎菲女士的日记》使日记体心理主义小说一时成为流行文体。文学史对此作品评论较多,在此不多述。
随后的《阿毛姑娘》[6]是与《梦珂》相似的城乡对立题材,只不过这次是从乡村写到城市,而不是从城市带着“乡愁”回味乡村生活。阿毛生活在偏远山区,与父亲相依为命。姑姑做媒把阿毛嫁到了西湖边的一户人家。婆家的一切都比父亲家好,因此她很满足。阿毛悲剧命运的转折开始于好奇心促动下的一次进城游历,她看到了城里女人的幸福,也发现婆家的院落只不过是一片豪华别墅包围中的几间破木房,于是她开始想:为什么同样是女人,命运却有天壤之别。不久,左邻的别墅搬来一对“美夫妇”,右邻别墅里的一对更恩爱,这都让她心生羡慕;而“三姐”嫁给一个城里军官作小妾后的变化更激起了阿毛对幸福的热望。她把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但丈夫只不过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可能给她向往的生活。机会来了,城里一所学校招人体模特,阿毛把当模特看作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婆婆不肯,丈夫还动手打了她。于是她陷入绝望并一天天瘦弱下去。直到有一天右邻别墅里的女人因肺病去世,阿毛才明白:幸福会随着死亡而散去。而左邻别墅里的那个“美夫人”的忧郁琴声则证明那个女人其实并不幸福。阿毛顿悟:世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幸福,活着也没有意义。于是她吞火柴头自杀……小说对阿毛向往幸福而最终悟透人生的心理过程进行了细致描写,使这部短篇具有了极大的阐释空间,也表现了丁玲在人物心理刻画方面的天赋。这个城乡对峙的故事如同寓言一般告诉人们:城市,等于欲望;欲望,等于死亡。小说将“城市=欲望=罪恶=死亡”这一串象征意群的隐喻性推到了极致,让人产生一种虚无的恐惧。虽然作者将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姑娘描画成了哲学家般深沉的思想者,似乎与她的身份不符,但是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完全忘记了这一点,反而沉入到对人生荒诞感的思索之中。
短小的《庆云里的一间小房里》[7]通过到城市做妓女的阿英姑娘的道德沦丧,反映了城市的糜烂。阿英最初还想嫁给淳朴的陈阿三,“同他安安静静地在家乡过一生”,可她又知道陈阿三“不是个可以拿得出钱赎她的人”,而且“那是什么生活,一个种田的人,能养得起一个老婆吗?纵是,他愿拼了夜晚当白天,而那寂寞耿耿的长天和黑夜,她一人如何过?”已经没有羞耻感的阿英觉得:
说缺少一个丈夫,然而她夜夜并不虚过呀!而且这只有更觉得有趣的……她什么事都可以不做,除了陪男人睡,但这事并不难,她很惯于这个了。她不会害羞,当她赔着笑脸去拉每位不认识的人时。她现在是怕过她从前曾有过,又曾渴望过的一个安分的妇人的生活。
如果把这篇小说与沈从文的《丈夫》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丁玲绝没有沈从文的脉脉温情,她是一个极端化的小说家,这种个性使她的小说更透辟深入,也注定她不会像沈从文那样优雅从容。
在我看来,丁玲短篇小说中手法最圆熟的要数那篇很少被人提及的《过年》。[8]小说写卜居舅舅家的八岁女孩小菡过年前后的心理变化。就要过小年了,但是带着弟弟在学校教书的妈妈还没回来,小菡为此食不下咽。正在此时,母亲回来了。丁玲将这一场景描写得生动而传神:
一个声音突如其来,这声音救了她。
这声音从腰门边传来,充满了喜悦。柔嫩的音波组成两个可爱的字:
“姊姊!”
于是空气全变更了。……她狂乱地跳下来,从风门边冲到天井里去。在廊上她看见她妈了。穿的黑呢衣,手携着弟弟;她扑拢去,她只叫得一声:“妈!”不知为什么,眼泪却涌出来了,她怕妈骂她又哭,隐忍着,又笑着,便去抱弟弟,弟弟也来抱她。她看见了妈给她的笑容。妈也喊了她一声:“小菡!”她快乐得全身都发痛了。
一连串的动作将一个孩子激动兴奋的心情刻划得恰到好处,读者也会由衷地发出会心的微笑。但小菡很快就感觉到“这年并不属于她”,因为她与弟弟“有服”。小说只轻轻一笔点到为止地写出小菡家庭的变故。快乐的假期很快过去,新学期即将来临,小菡又要与妈妈和弟弟分开了:“她恨不能把日子拉回来,再过一次年!”分别前的晚上,她以肚痛为由得以睡在母亲脚边,“她用手摸着妈的脚”,因幸福而哭泣。《过年》是丁玲小说中最蕴藉的一篇,可谓艺术探索中少有的佳作:无论是父亲的去世,母亲心情的压抑,还是小菡心灵的伤痛,作者均未做正面描写,但孩子体会到的“这年并不属于她”以及妈妈的一句“你再哭时,妈也会哭起来呢”,却是人间最沉痛之语。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的。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丁玲用“心”写作、刻画人物心理、透视人物灵魂的心理主义小说,这是属于她自己的创作,甚至可以说她正在无意中创造一种新型的小说学。从最初完全靠灵感写作到自觉进入手法和文体艺术探索,丁玲的成熟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但是在胡也频、冯雪峰等人影响下,丁玲却走出了自我而走向了普罗文学。
(二)
沈从文后来这样谈起丁玲与胡也频的转向:“革命事业在知识分子的工作中,需要理智的机会似乎比需要感情的机会更多,两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内视听所及以及其他某方面难于置信的报告统计文件中,真使人为他们发愁以外还稍稍觉得可怜可悯。……我把因环境不同,一个信仰一点主张所引起的不同事件告给她,且指明身在租界既不认识历史又不明了空间的作家们,讨论大众文学的效率,与大众文学的形式,以及由文学而运输某种思想于异地青年诸问题,如何昧于事实情形中徒然努力。且在这种昧于事实情形中,作着种种糟蹋青年、妨碍社会自然进步的决定,具有伟大眼光的共产党,尤不可不加纠正。”[9](P190)但是丁玲不仅没听沈从文劝说,反而几乎与之反目成仇。[10](P39-43)在转变期创作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一)》[11]中,丁玲设计了若泉、子彬和美琳这三个人物,似乎代表胡也频、沈从文和丁玲。若泉认为,过去“我们只做了一桩害人的事,我们将这些青年拖到我们的旧路上来了。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只能一天一天更深地掉在自己的愤懑里,认不清社会与各种苦痛的关系,他们纵能将文字训练好,写一点文章和诗词,得几句老作家的赞赏,你说,这于他们有什么益?这于社会有什么益?所以我现在对于文章这东西,我个人是愿意放弃了,而对于我们的一些同行,我希望都能注意一点,变一个方向,虽说眼前难有希望产生成功的作品,不过或许有一点意义,在将来的文学历史上。”因此他“希望能从这知识阶级运动跳到工人运动的区域里去”。而子彬化名“辛”在《流星》上发表《我们文坛上的另一种运动》,似乎也是影射沈从文是追随《新月》的“绅士”。小说最后,美琳给子彬留下一封信“随着大众跑了”。从《一九三○年春上海(一)》开始,丁玲进入了革命文学创作阶段。
在随后的创作中,丁玲日益走向社会大舞台,写作越来越公式化。《一九三○年春上海(二)》[12]开始了典型的“革命+恋爱”式写作:望微以革命为重,他娇艳的情人玛丽因此与他产生了矛盾并投入别人怀抱,而望微则在纪念五卅运动的游行中被警察逮捕。长篇小说《韦护》也是一部“革命+恋爱”的小说,只不过最后丽嘉有所觉悟:“唉,什么爱情,一切都过去了。好,我现在一切都听凭你。我们好好的做点事业出来吧。”
《田家冲》[13]中的“三小姐”已开始走向农村,丁玲从此实现了创作题材的重大转变。《水》[14]以1931年16省水灾为题材,表现了灾民同洪水和饥饿搏斗、与官绅斗争并觉悟的过程。小说一发表就被看作是“新的写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收获:
《水》所以引起读者的赞成,无疑义的是在:第一,作者取用了重要的巨大的现实的题材。……最主要的还在:第二,在现象的分析上,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定的理解。第三,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在《水》里,不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这二点,当然和题材有关系的),它的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的,而是全体中相互影响的,发展的。[15]
茅盾后来也说:“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16]但事实上,《水》的人物形象面目模糊不清,毫无个性,他们变成了符号与传声筒,他们在读者遗忘的逝川中,他们就像雨消失在水中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正如沈从文所说,是由于作者力图去表现她不熟悉的题材。在这种情形下必然会造成一些材料堆积、主观臆想和平面化写作等缺憾。《奔》[17]写张大憨子、王阿三、乔老三、老龙、李祥林、小刘等在乡下无法生存,于是每人借贷两个大洋作盘缠到上海找工作。这两元钱是一斗米的价钱,但放贷的地主孙二疤子要他们春天偿还三石谷。他们到上海后投奔张大憨子的姐夫,然而姐夫早就被每天14小时的劳作拖垮,姐姐则在罢工中摔了一跤而小产,卧在床上奄奄一息,瘦得“像个女巫一样”,穷得连一个夹猪油的烧饼也吃不起,不久死去。他们羡慕着工人,而工人们却受着资本家敲骨吸髓的压榨,有的人只好靠注射吗啡来提精神。于是工人们计划团结来罢工:“坐在这里喊是没有用的,就是杀死几个厂长也还没有用,现在应该要让工人个个都明白,齐心起来站在一块拼命,所以要提条件,还不许开除工人……”小说反映了1930年代城乡经济的破产与凋敝,也力图说明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农民是革命的同盟军。但所用的素材却多是臆想虚构,所以难以生动感人,并且作者有意尝试创作“大众文艺”,因此无论文采还是结构手法都退向浅显易懂和平面化。丁玲此时的小说与初期小说创作已判若两人。季羡林这样表达他对丁玲转型的惋惜:“在这里,很奇怪的,我想到扑火的蛾子。……她所描写的第四阶级只是她自己幻想的结果,……你可以用一个印度人去想象北冰洋来比拟,这个印度人会把棕榈栽在冰山上(当然是在想象中),他会骑着象赤着身子过雪的山……”[18]
(三)
促使丁玲发生创作转向的,除了时代的原因外,还有两个关键人物,即胡也频和冯雪峰。胡也频与丁玲早期都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1929年到1931年间胡也频发生左转,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去。作为胡也频的伴侣,丁玲没有听从好友沈从文的劝告,夫唱妇随地走向了革命。问题是冯雪峰的出现对丁玲起了更重要的促动作用。甚至是胡、丁、沈还在北京的时候,丁玲就已经爱上了冯雪峰。她将这情感告诉过易嘉(瞿秋白)、昭(陈学昭)、冯乃超和姚蓬子。这一点可以从丁玲“失踪”后公开的《不算情话》中得到证实。她在信中说:“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尤其当有着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树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栏上,从叶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远很远,一种完全空空的境界,那里只有你的幻影,‘唉,怎么得再来一个会晤呢,我要见他,只要一分钟就够了。’这种念头常常抓住我,唉,XX!为什么你不来一趟!你是爱我的,你不必赖……”[19]从这信中我们可以相信这爱是真诚的,只是因为冯雪峰已结婚,加之理性的克制,才没有逸出“革命同志”的关系。姚蓬子为《丁玲选集》所做的序也可以证明这一点[20]。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有了冯雪峰的情感支持,丁玲才没有在胡也频去世后倒下去,而是更坚定地走向了革命:一方面是胡也频的遗志,另一方面不排除冯雪峰的鼓励。
丁玲1933至1936年幽居南京期间的创作远没有抒张个性,在艺术上也没有新突破。1936年秋天,这位勇敢的女性、杨开慧烈士的同学,带着宋庆龄赠送的350元钱,冲破重重阻挠于11月到达陕北延安,毛泽东设宴款待并挥毫题词:“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21](P174)丁玲十分感动,她认真调研并试图开始新的创作。写于1937年4月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具有高昂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那个无名的少年红军以及东北军官兵都变成了符号,小说表达的真正主题是:统一抗战乃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而共产党是最主张抗日的政党……至此,丁玲在1930年代的创作转型全面完成。如果她后来没有写出《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那么人们在小说创作中可能再也看不到一个女性主义的、感性的丁玲了。在1949年以后的各种运动中,丁玲受尽磨难,的确令人同情。她也自觉地改造成了“政治人”,从北大荒归来后写作的“小说”《杜晚香》只不过是一篇完全按意识形态要求写成的长篇人物通讯,削平了心灵深度,主人公成为政策的注脚。丁玲以这样一份试卷总结一生的创作,让期待已久的读者大失所望。
从都市到农村,从耽于内心到改造世界,从感性到知性,从个人到集体,从人性到阶级性和党性,从女性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由亭子间、四合院到社会大舞台……这是一条多么正确的路呀,一条“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金光大道。但对于艺术来说,这可能是一条曲折的路:艺术需要开掘人性的深度,广度是不能代替深度的;就像宝藏深藏在大地之下,你纵使走遍千山万水而不向纵深处掘进也不可能得到那宝藏一样。丁玲走上了“广阔的路”以后,由于对人性深度开掘的欠缺,使她的创作步步行至枯竭。
标签:小说论文; 丁玲论文; 沈从文论文; 1930年论文; 梦珂论文; 文学论文; 莎菲女士的日记论文; 胡也频论文; 冯雪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