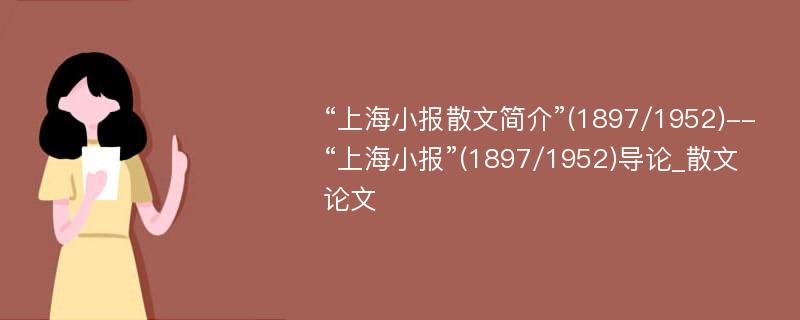
游戏笔调之下的时评杂说和风月小品——上海小报(1897-1952)散文概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说论文,概貌论文,笔调论文,小报论文,时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小报(以下均称“小报”)是流行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休闲性小型报纸。它诞生于1897年,至1952年全部停刊,总计在千种以上。小报散文很长一个时期自外于新文学。它是直接继承明清笔记小品的传统,经由小报文人玩世文化品格的调适,而形成的一种游戏文章。
游戏文章的传统古已有之。近代游戏文章的始作俑者就是刊登在李伯元主办的《游戏报》上的小报散文。《游戏报》1897年初创时期的游戏文章是批评时政的一种手段,而后固定为加强小报娱乐趣味的重要文体样式,渐渐由时评扩及至小报的各类题材散文,并保留和延续下来,直至小报生命结束。游戏文章的特征是:玩世的文化心态,市民的民间价值立场,娱乐休闲的书写主旨,集轻松诙谐、滑稽幽默、插科打诨、噱头打趣于一体的笔调风格,注重读者接受和商业效益。按照体式划分主要有:时评短论、影戏剧评、笔仗墨讼、闲适笔记、风月小品等。小报散文自始至终,就包含这几类文字,从来不曾改变过。改变的是,在不同时期内,每个类别散文的比重此消彼长,散文的内涵被不断地注入新的时代血液。
民国以前的小报散文以时政批评和风花雪月为两大主题,旁及历史掌故、官场笑话、市井嬉谈等。时评论说文每天必有一篇,刊于首条位置,内容关涉政治、社会风尚、道德伦理等大小问题,范围甚广。如《辫子难保说》、《滑头难做说》、《洋烟利害说》、《守贞说》、《崇俭篇》、《开妓院之功德胜于建佛寺说》、《论女界之自治》等。虽然并非都是经国大事的话题,但是,从小报对时评论说文的重视程度看,民初以前的小报散文仍然存有依稀可辨的载道精神,所不同的是,这“道”未必一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高级命题,也包括对世态人心投注的关怀。而风月散文的文野差别悬殊,有雅致的,也有粗俗的。无论是雅,是俗,均重视趣味和广告效果。总的来看,民初以前的小报散文已经奠定了世俗、趣味和商品化的基调,留下了由古代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的痕迹。这时期的主要散文作家有:李伯元、李竽仙、吴趼人、欧阳钜源等。
20年代和30年代早、中期的小报散文沿袭了民初以前小报散文的整体风格,在保持时评论说文的主角位置和风月小品的点缀作用之外,增加了社会新闻报道、影戏剧评、知识小品和历史掌故的分量。20年代初期以揭露军政、社会黑幕秘闻为特色,20年代后期把目光转向市民日常生活,出现了散文副刊或专栏。最早开设散文副刊的是《社会日报》。1929年,《社会日报》开辟“香海”散文副刊,聘请冯若梅、吴农花轮流主持,每天都有短小精悍的小品文面世。较有名气的散文副刊或专栏有《立报》的《言林》,《小日报》的《随便谈谈》,《礼拜六》的《小品文》,《铁报》的《风景线》,《上海报》的《花雨》,《时代日报》的《玫瑰花》等。20、30年代是小报散文作家队伍基本形成的时候。以小报主笔为主的时评散文作家有:《晶报》的张丹斧,《金刚钻》的施济群、陆澹盦、韦兰史、朱大可,《福尔摩斯》的吴微雨,《社会日报》的陈灵犀、冯若梅,《报报》的胡憨珠,《龙报》的蔡钓徒,《大晶报》的冯梦云,《福报》和《大日报》的吴农花,《硬报》的马儿(李焰生),《立报》的萨空了,《小晨报》和《辛报》的姚苏凤,《小日报》的黄转陶、尤半狂,《上海报》和《上海日报》的王雪尘,《金刚日报》的倪高风,《世界晨报》和《时代日报》的来岚声,《铁报》的何二云、谢豹(谢啼红)等。冯叔鸾(马二先生)、朱瘦竹、汤笔花、周世勋、詹禹门、步林屋几位的剧评散文最为出色。鸳蝴作家孙玉声、李涵秋、周瘦鹃、郑逸梅、范烟桥、毕倚虹、胡寄尘、严独鹤、包天笑、袁寒云、江红蕉、张恂子、徐卓呆、王钝根、姚鵷雏等,都是小报散文的高手,时评、剧评、掌故、随笔、趣文,各有侧重,各有专长。20年代后期,随着花国小报和黄色小报的诞生,其他小报上的风月小品数量反而明显减少,且出现分野。风月小品的文学性较以前加强,而花国小报和黄色小报则滑向色情描写,被人称作“花稿”。擅长写“花稿”的小报文人数严芙孙、康不驼、骆无涯(骆大荒)的名气大。
30年代中期新文学作家进入小报,以发表散文为主,小说甚少。曹聚仁先后在《社会日报》上发表过200多篇散文,主编过《社会日报》副刊《学术·思想·文化》和《火线》、《上海报》副刊《文艺周刊》。其他做过小报散文副刊主编的还有茅盾、柯灵、谢六逸、凤子、杨村人、杜衡等。柯灵主编过《社会日报》副刊《社会》和《社会生活》;谢六逸、茅盾先后主编过《立报》副刊《言林》;凤子主编过《上海报》副刊《剧运周刊》等。由于新文学家发表在小报上的散文是新文学作品,数量少,而且与小报散文的风格不同,故在本论文中不作为“小报散文”看待。
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小报散文的特点是:第一,时评论说文章文学化;第二,专栏作家的专栏散文增加;第三,散文风格多样化,文体新旧杂糅;第四,影戏剧评明显减少,几乎被铺天盖地的舞评所取代。这时期的散文作家队伍,老作家以周瘦鹃、郑逸梅、冯梦云、谢啼红、卢溢芳、汤修梅为代表。新崛起的年轻作家有:陈蝶衣、周楞伽、冯蘅、柳絮、唐大郎、龚之方、横云阁主、曾水手、慕尔、傅大可、青子等。另外,作为一种小报文学社会化表现的是,小报为舞女开设散文专栏,《小说日报》、《上海小报》、《海报》、《力报》等都有舞女散文专栏。以往,时评论说文章是小报的重头戏,每天都有一篇,且放在小报中比较显赫的位置上。40年代的小报中,还有时评文章,但身份不再特殊,它与其它类型的散文一样,被置于文学专栏里。而且,执笔者往往是小报作家。由作家来纵论世界风云,自然就带着浓厚的文学气质。冯梦云、周楞伽先后做过《小说日报》时评专栏《葳蕤五记》的主持人。《葳蕤五记》是一个颇受好评的名牌专栏,内容涵盖国内政坛和国际时局,时间跨越民初以来三四十年之久。作者所写融记叙、议论、描写、抒情为一体,增添细节,既生动又有趣,可获得类似于读小说的快感。
小报散文以专栏文章的面目出现,是40年代小报散文的一大特色。散文作家都成了专栏作家。在小报上开设专栏的新老作家和他们的散文专栏有:瘦鹃《霓虹散记》、啼红(谢啼红)《灯边话堕》、华言(周楞伽)《说白》、葳蕤(周楞伽)《葳蕤五记》、婴宁(陈蝶衣)《独处室随笔》、玲珑(冯梦云)《浮生小志》、漫郎(唐大郎)《漫郎杂写》、高唐(唐大郎)《高唐散记》、云裳(唐大郎)《云裳日记》、康公《匡庐赘墨》、轾轩《今人物志》、荒斋《荒斋随笔》、横云阁主《卖文为生》、柳絮《小块文章》等。有的作家同时在不同的小报上开设专栏,冯蘅是一位高产作家,他在许多小报上都开有专栏,现能查到的有10个:《铁报》的《花边小品》,《东方日报》的《珠香集》,《社会日报》的《池上集》(剧评),《小日报》的《纵横小品》,《真报》的《蛇足新篇》,《力报》的《杂乱芜章》,《风报》的《灯尾小记》,《飞报》的《惜力速录》,《诚报》的《扫灰集》,《天报》的《拾穗集》等。专栏散文的体裁,从随笔杂写到美文小品,从率意闲聊到严肃认真,五花八门,随作家的书写风格而别。专栏散文的特色是:快捷、自由、驳杂和世俗。专栏散文是一种“即看即弃”的文学,为适合读者的生活节奏,必须是篇幅短小,反应敏捷。同时,它是一个能让市民畅所欲言的空间。因此,专栏散文的思想、文风、文字可谓自由开放,多姿多彩。专栏散文的内容都是贴近市民生活的软性材料,不需要咀嚼就能消化。舞稿也是以专栏文章的形式刊登在小报上的。较有名气的舞稿专栏有:慕尔《慕尔小志》、大可《啰唣什景》、卜卜跳《卜阁随笔》、严胡英《舞国人物小志》、金星《舞余随感》、韦陀(黄郭人)《神话》、杰西《杰西漫谈》、阿Q《阿Q随笔》、张生《弄火杂记》、哀王孙《王孙小语》等。
小报散文按照文体来看,有特色的是议论性杂文、闲适小品与风月散记等几种。杂文是小报散文的要角,包括时评短论、杂感、影戏剧评和游戏化的笔战等。关涉的主题庞杂而广阔,社会、政治、时事、文化、文学、经济、生活、娱乐、习俗、世情等,凡是都市市井里发生着、存在的人文物象都能成为小报的议题。只是,小报文人写作的议论评说不是追求崇高,更不期求和政治革命产生共振效应,仅仅是为了表达市民的所思所想。多数情况下不是进行判断、推理、论证,往往夹杂着作者对具体事象的描摹叙说,情感散漫不拘,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陈灵犀的《病榻杂感》直书自己生病时的感受:病的折磨,医疗费用的不支,人情世态的冷暖,甚至想到临死前最想做的事就是“将平生所不能说的话、所不敢骂的人,一古脑在报上说个明白,骂个痛快”(注:灵犀:《病榻杂感》,《社会日报》,1933.7.19。)。这种“个人化”特征是与市民的实际利益密切相关的,更多是从市民生活着眼,于是就带来了小报杂文的又一个特点——生活化。生活化的第一个表现是,不管多么伟大的运动或事件,小报杂文都是把它放在市民利益的天平上去称它的“意义”。《国货运动感想录》不取爱国主义的宏旨大义,而是从是否实惠上来谈:“国货运动”提倡国货,但是,国产的丝绸不如日本产的毛呢便宜、耐用,因提倡国货而禁止穿西装,实在是没有道理等等。生活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小报议论性杂文中存有大量的婚姻、家庭、衣食住行的话题。诸如《结婚问题与离婚问题》、《社交与恋爱》、《新女性的健康美》、《批评现代妇女的服装》、《素衣与素食》等等,都可见一斑。
影戏剧评是小报的保留节目大都是专业人士或有造诣的票友撰述。戏剧大师马彦祥曾做过《光报》戏剧版的主编,写过许多有价值的剧评文章。郑正秋、汪优游、陈去病、欧阳玉倩、洪深、舒舍予、翁偶虹、周剑云、周世勋、唐纳这些戏剧、电影界的资深人士,都有过为小报撰写影戏剧评的经历。小报文人中的票友马二先生、袁寒云、朱瘦竹,不仅旧文学底子厚实,而且深谙戏剧艺术规律,是小报剧评的高手。小报中确实存有不少见解独到的影戏剧评文章,如:马二先生《旧戏之精神》、翁偶虹《偶虹谈剧》、欧阳玉倩《个人兴趣与戏剧运动》、翠微《上海之时装剧问题》等。不能否认,有不少剧评戏评是专为捧角而写的,但很少是纯粹的外行。
笔战是最能体现小报散文游戏化特征的。说到笔战,很容易使人想起新文学文坛上的硝烟弥漫和刀光剑影,以及每一次论战所带来的重大文学转向。小报文人的笔战或是相互捉狭,或是意气用事,或是为了发泄一点不大不小的私愤,或是捡一点大报或新文学文坛笔战的唾余,甚至纯粹是为了娱乐消遣而无事生非。所以,小报笔战无论是缘起,还是形式和结果,都是一场游戏而已,不能当真。多数笔战是发生在小报与小报之间,但也有少数是小报和大报、小报和期刊之间的。小报中的笔战很多,各个时期、各种名目的笔战比比皆是,不外有这几点:第一,在无聊的话题上纠缠不休。小报主编挑起笔战的目的是为了把报纸办得热闹一些,以期有更好的销路。《社会日报》针对电影明星胡蝶和摄影师林雪怀离婚诉讼一事,发起“特别征文”说:“雪蝶离缘是件极平凡的事,大家不知为什么如此注意。既然有人注意,我们便也认为有研究的必要,现在虽经法院判决,我们不妨丢开法律,讨论他俩的分离,是林雪怀的幸或不幸呢,还是胡蝶的幸或不幸。好管闲事的朋友,不妨请来谈谈,文稿务请短而清,落笔也请着眼于小的地方,因为这是件极小的事情。”(注:《特别征文》,《社会日报》,1931.7.14。)虽然是件极小的事情,但是,在“特别征文”的号召下,一场围绕着谁幸谁不幸的无聊笔战拉开了战幕,居然持续了几个月,最终也没有争出个青红皂白。小报文人用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挑起笔战的意图,除了商业因素,大概不会是别的。第二,把严正的问题游戏化。新文化运动中,曾经发生过“新旧诗的论争”。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不作古人的诗而唯作我自己的诗”,并率先于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白话诗八首,开创了白话诗的风气,因此受到保守主义者的反对,并产生了论争。小报文人也在小报上与胡适展开了笔战,基本上是站在保守派一边。所不同的是,小报文人把这场新旧文化大论战蜕变为一次笔墨游戏。小报文人用俏皮话嘲讽新文人的新体诗。张丹翁在《为什么新诗都做得不好》中数落胡适提倡新诗的原因是他自己做不好旧诗(注:丹翁:《为什么新诗都做得不好》,《晶报》,1919.11.9。);张恨水把新诗的“没有章法”比作“水牛拉屎噼里啪啦一大堆”(注:恨水:《纯粹新诗决做不好》,《晶报》,1919.11.21。)。显然,这些小报文人所表达的文学观念与正统旧文人如出一辙,但是,采取的话语方式却有天壤之别。第三,小题大做,越扯越远,直至离题万里。关于杨杏佛离婚一事的笔战就是最好的例证。1931年3月30日《社会日报》发表敖溪的文章《杨杏佛又从红袖里求知己》,其中谈到杨杏佛与其夫人离婚后,曾作七律一首,杨诗里有“偶从红袖求知己,应有娥眉打不平”。作者便“步其原韵胡诌一首:“十载江湖载酒行,是杨是赵不分明。又从红袖求知己,定有黄金买爱情”。此文面世后的第二天,即有灵犀《定有黄金买爱情》做回应,并把杨杏佛的事扯到爱情与金钱关系的讨论上去了。接下来参与笔战的作者再由此引出妓院里有没有爱情的话题。然后,再经千回百转,集中到“女子的操守”、“男阀主义”和“伪道学”的争论。继续扯下去,扯到安禄山叛乱和杨贵妃的冤屈,《长恨歌》的艺术性,唐诗宋词孰高孰低等等,无休无止,居然酣战了近一年的时间。这正是小报文人游戏笔墨的最好写照。
小报散文中除议论性杂文之外,就数闲适小品文的数量最大了。小报小品文是明清笔记小品的后裔,与新文学小品文不同。新文学散文是作家“烧着的生命的力成为个性而发挥出来”的结晶(注: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见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34页、第26页。),而小报小品大多是“游荡记录”、“胡闹日记”和“文士生活的票友化”(注: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见鲁迅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34页、第26页。)。写新文学闲适小品的作家往往把未必肤浅的生命意识埋藏在看似平淡、闲散的文字下面。而小报小品文没有真正超越明清笔记小品的规范定位,大多还停留在野狐禅式的书写上。明清两代笔记的内容,“包括了杂史稗乘、乡土风物、琐事遗闻以及‘齐谐志怪’之流。可以说是四部中史部的杂史,子部的杂家和小说家”(注:谢国桢编著:《明清笔记谈丛·前记》,中华书局,1964年,第1页。)。小报小品文的类型基本上与之相对应,大致有:历史掌故、逸闻轶事、都市风习等。小报中的历史掌故比比皆是,只不过这些历史记忆,不是正襟危坐的要还历史以真面目,而是着重于猎奇和趣味的描述。《南社人物小志》在历数南社人物曾经从事的南社活动时,专拣那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事件回忆。《书场琐志》本是梳理海上说书业发展历程的,却没有忘记把女客的听书嗜好和感受惟妙惟肖地白描一番。这种书写习惯显然与明清笔记小品的“杂史稗乘”一脉相承。小报小品文与明清笔记小品割舍不断的历史渊源,还可以从人物小品的风格上得到印证。小报小品文所记述的人物不是举足轻重的社会栋梁,而是能产生名人效应的都市明星和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杂家”。像《史量才壮怀未遂》、《女艺人陆小曼》写的虽然是社会名流,但选取的视角却是能引起市民兴趣的“故事”;《特殊人物——白相人》、《姨太太》、《女相士》记述的则是一些身份暧昧的特殊阶层;至于历史人物多是用皮里阳秋笔法写出来。小报中的人物小品从不去表现人物的存在意义、性格特点或心理世界,而是把笔墨花费在轶闻逸事上。即使注意到人物的行状描写,或者也采用类似于新文学散文的选取横截面的写法,但在选取生活片断时,常常因过于偏重猎奇而忽略情感的表达,以至于丧失了散文的艺术感染力。
闲适是小品文共同的风格特征,小报小品文也不例外,但是,小报小品文的闲适和新文学家的闲适并不同质同构。相同的是都拥有传统文化的资源;区别在于新文学作家还吸收有西方异质文化的丰富营养。新文学小品文和小报小品文都是把明代公安派、竟陵派作为自己的文学之源,这是因为,共同的社会环境使他们殊途同归般地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寄存地。郭预衡认为:明代以来,不同的历史阶段里,产生过不同类型的文章。“开国之初,大乱始平,人心思治”,就会有善歌善颂的文章。待到“大狱屡兴,人不自保”,“法禁日严,言路日窄”,“便产生了台阁之文”。“在这以后,一些文人学者对于现实,日渐不满,对于台阁之文,亦多不满,”于是产生了复古之文。“明代中叶以后,国家衰象日增,社会危机日重。加以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社会风气和社会思潮都有新的变化。”这时,就出现了公安派、竟陵派的“适世之文”(注:郭预衡编选:《明清散文精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可见,闲适小品产生的条件应该是一个国家衰败但政治空气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新文学作家和小报文人生存的晚清、民国时期就具备了这种条件。
新文学家和小报文人在传统上的一致性,还表现在他们都有过“士”的自我定位。不同的是,新文学家的“士”的自我价值判断,参照的是人世的士大夫族。而小报文人则把自己放在“名士”之列。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过后,随着旧的价值体系的崩溃,“士”的权威被毁。曾经有着“士”情结的周作人一类新文学家痛感到自我价值的失落。于是,只好放弃社会改造的努力,在文化改造中寻找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和空间。所以,他们的“闲适”是认真的,经过深思熟虑、潜心钻研过的,穿透着文化意蕴的。新文学家即便远离尘世,追求闲适的生命情调,但决不颓废。而小报文人的闲适多半是由玩世而引起,不但颓废,而且偏于把玩。“名士”角色的自我派定,使他们失去了进取精神,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商业化的报人身份在他们的“名士”气质中又添加了物质因子,于是,他们的闲适不再是纯粹的天高云淡,而是弥散着滚滚红尘。所以,小报小品文的风格是世俗的闲适。诸如《市民趣味》、《谈奶妈》、《命运的研究》、《秋窗谈鬼录》、《阳澄湖蟹》、《溜达上海马路一乐》、《街头科学》、《睡眠》、《谈旅行》、《保健运动》之类的闲适小品都是围绕着作者身边的日常起居、交游酬酢而做,不求高深,但求轻松有趣,迎合潮流,是市民松弛神经的大众化精神食粮。
风月散记是小报小品文特有的品种。小报文人的突出标志是“世俗才子”型的人格特征。“世俗才子”有两大本色,一是词章,一是冶游,前者是才调,后者是风流。表现在小报文人身上,就是永远舍不下“风月”这个文学命题。小报中的风月散记大致包括情景化场所描述和闲谈式记人记事两种类型。因为小品文强调纪实,是作者性情的真实再现,所以,风月散记中少有风月场中种种规矩、门道的揭秘和性描写,都是近于写实的描述。40年代专写舞稿的小报文人傅大可(大可)在《啰唣舞语(三)》中描写“金蕾”舞厅的乐队:“乃乌合之众,溃不成军,拉杂奏来,不堪入耳。”比较“西华士”乐队卖力之情景,“殊亦不无可取”。而“舞场之乐队,与人之灵魂无异,有时音乐奏来死样怪气,使人不打瞌睡者几稀。”文中提到的“金蕾”舞厅、“西华士”乐队以及乐队的演奏,都属于客观描写,没有掺加虚构和想像的成分。小报中属于这类的小品文很多,如《跑马厅之夜》、《茶室风光》、《十里洋场中的现代书场》、《海上歌舞之状况》、《醉艳楼杂写》等。另一类小品是写风月场中的各色人等,这倒是契合小报文学擅长描摹都市众生相的特征。《舞国人物志》描写舞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有舞场老板、拖车、仆欧、舞女大班、揩舞女油的“舞蛀虫”、到处赶场的红舞女、“舞文记者”等。小报文人在写风月场中的人物时,往往直书姓名,不避其真实身份。《望天坍——舞话》写舞稿专栏作家傅大可的形象:“蓬松的头发,黝黑的脸儿,再配上一件半新旧的夹衫,模样的确十分老实”,“所以有了‘老实人’的头衔”。但说他交际舞女的工夫来,却“胜人一筹”(注:《望天坍——舞话》,《上海小报》,1940.10.31。)。在所有的风月小品中,以描写女性的文章居多。这类小品多采用闲谈方式,如数家珍般叙述一个个风尘女子,俨然一副自家人姿态。如《上海小报》的《舞园什景》专栏,每天都要写几个舞女,内容不外衣饰、行踪、性格特征、交际工夫等。文中的妓女、舞女很少是赤裸裸的拜金主义者,也不是理直气壮的性交易者,相反,多数是相貌姣好、举止内敛、身世悲凉的楚楚女子。唐大郎在《漫郎杂写》中美化他所熟识的风尘女子时,不是张扬她们的社交手段如何高明,而是强调她们身上的传统女性美德。常用“白衫白袜白履”来表现“清雅绝俗”,特别指出“曾肄业于某教会学校,孜孜不倦,中英文程度皆臻于中学”的人生经历(注:花郎:《淑兰老八之体格美》,《龙报》,1931.4.15。)。那些虽身陷风月场中,但仍然保持着一颗纯洁之心,重情感而轻物质的妓女或舞女,往往是作者笔下最佳的风尘女子形象,如《一个请客不要钱的妓女》中的蒋老五、以吻筹赈的侠妓花翠玉、把奖金捐助难民协会的“中国小姐”王美梅等,都曾赢得过作者少有的感叹抒情文字。这类书写风尘女子的小品文较前面提到的风月场所的白描,艺术欣赏性稍强一些,也能融入少许情感。但小报作者那一点同情的体验是十分有限的,现代上海的生活节奏与小报文人本身的地位与生存压力,已经让这些小品无法维持一种从容的精神境界了。
倒是小报利用风月人物的自述,如所谓“舞女随笔”之类,消除了部分冷漠,显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关切来。40年代的小报专门设置舞女主持的散文专栏,如《上海小报》的《丁玲闲笔》(米高美舞厅舞女丁玲)、《小说日报》的《紫微小姐信箱》等,让舞女做专栏作家,书写舞女自己的人生体验。舞女自述的问题集中在这样几个向度上:物质对舞女的压迫,和由此引起的舞女社会地位、情感归宿、命运前途的不确定性,以及舞女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担忧等。与小报文人歌颂的那些重感情轻物质的风尘女子不同,舞女阐释的金钱与爱情的关系是:“金钱虽不能买真正的爱情,但是爱情必须要金钱来养活!”(注:《丁玲闲笔》,《上海小报》,1940.12.16。)小报文人在赞美娼门“义举”,而她们自己却说“娼门是最讲金钱的地方”(注:桂花:《娼门中人与自由恋爱》,《小说日报》,1941.3.14。)。舞女为了不被社会轻视而寻找出路,如,组织“舞女联谊社”,学习专业技术,“研究学识”等(注:见《舞女联谊社花絮》,《风报》,1939.7.1。)。而小报文人认为提倡女子职业便是“玩视女性”(注:曾淹:《女子职业与玩视女性》,《铁报》,1930.6.13。)。可见,身受物质压迫的舞女与作为旁观者的小报文人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舞女思考的是自己切身的利益,而小报文人则是站在一个观赏者的立场上进行评说。在小报文人的视野里,舞女是被“看”的对象,是带给舞客快乐的“商品”,因此,他们看重的是:舞女的外貌是否赏心悦目,形体是否适中,举止是否端庄,性情是否温柔,情操是否高尚。事实上,小报文人的心理是一种舞客的买卖心理,因此,他们希望舞女最好能够不计较金钱又提供周到的服务。总之,舞女自述性的随笔是男性小报专栏作家所写舞稿的一个“他者”。这个“他者”照见了小报文人心灵深处那永远也抹擦不去的洋场“世俗才子”的旧文化印痕。
鲁迅曾经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散文进行定位,强调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收入《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页。)。坚信散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77页。)小报散文却正是市民生活中的“小摆设”。上海市民喜欢这种世俗的“小摆设”,喜欢读这种吴侬软语式的小品。它有人情浇薄、世态炎凉的感伤叹息,也蕴涵着矫正时弊、复归人性的思想要求,但都不甚强烈。它不能给人以力量,也不能教人奋进,至多只能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只要市民需要这种文化消遣,就有它存在的理由。因为,人们的需要是多元的。“我们固然欢迎听到震撼天地的狮吼虎啸,感动伟大,但也不妨听听蚊蝇的小唱,因为这都是生命力的表现,有着它们自己的灵魂的独特的声音”(注:李素伯:《“自己的话”》,1934年《文艺茶话》第2卷第6期,署名“所北”。)。
小报的闲适文字多样繁杂,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它属于鸳鸯蝴蝶派散文和通俗海派散文的小型化报章品种。一经问世,即受到市民读者的认可,影响也不断扩大。首先引起大报编辑的注意和仿效,后来成为大报副刊的文笔体式之一。有的文学杂志待需开辟轻松栏目的时候,会想起它来。而众多现代休闲类、家庭类流行读物,通俗文学杂志和画报等也有模仿这种笔调的。这些,便造成小报散文一定的影响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