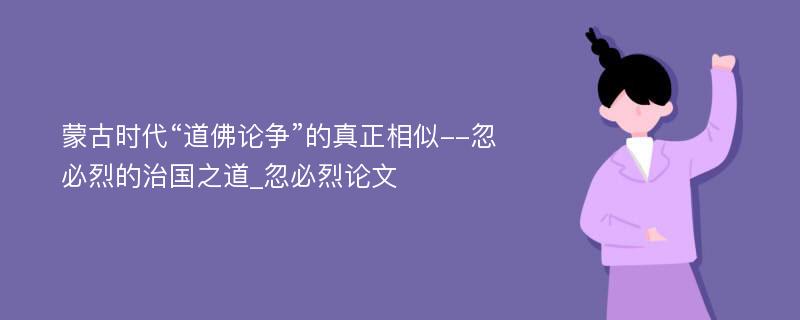
蒙古时代“道佛争论”的真像——忽必烈统治中国之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论文,之道论文,中国论文,真像论文,忽必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续前)
(2)主办者蒙哥眼中的宗教争论
在哈喇和林的包括道佛论战在内的宗教争论始终是蒙哥皇帝主持的。因此,以下将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并以中村、松川1993年介绍的少林寺圣旨碑第一截为线索,从主办者蒙哥的角度出发,对这次宗教争论作一重新评价。本圣旨是在争论前夕的1253年12月7日下达给在道佛争论中通常作为佛教一方的中心而存在的少林寺长老福裕的,它以回鹘字蒙古文与白话体汉文合璧,下旨者为蒙哥。正文及语句解释详见中村、松川文,为回顾其内容,这里仅列书面总译,数字所示为行数:
①秃鲁黑台不花两个,②传奉蒙哥汗的口头的吩咐道与(uguleju ogtugei)少林长老(seulim canglau),③“俺与你都僧省(Tu singsing)名字去也则,不是管汉地(jauqud)的④和尚(toyid)不拣畏兀儿西番河西⑤但是来底和尚每都管底上头换都⑥僧省。不拣那里来底呵,⑦咱每根底来的不合来底都僧省长老识者,⑧合来底都僧省长老与文书者。哈喇⑨和林里有底和尚每俺每根底提名字唤着呵⑩教来者。不唤呵休教来者。(11)依着释迦牟尼(Sagimuni)佛法里和尚每根底管着,管不得呵都(12)僧省名字要做甚么。”(13)圣旨也了。(14)牛儿年,冬腊月(15)初七日开。
前引蒙哥圣旨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③—⑥)再次确认了曾令福裕管辖哈喇和林所有佛僧的事实。如中村、松川文所示,在前引裕公之碑中,前半部分记述的是贵由时代的1248年或1249年以后的情况[(32)]。而以现在形所记的后半部分(⑥—⑩),则叙述了再令福裕任蒙哥时代的都僧省,继续管辖哈喇和林全部佛僧的内容。根据本圣旨,完全可以明确从贵由时代到蒙哥时代居于哈喇和林的所有佛僧,无论其出身与教派,完全被置于曹洞宗福裕管辖之下的事实。
如再次看一下该圣旨的后半部分,可以看到,福裕对应招请者与不应招请者进行了选择,前者给予文书,因而他们可在蒙哥等人面前读其名,招请者与未招请者间的选择即如此进行。但他们究竟被招请到哪里呢?从此后不久即在哈喇和林举行了诸宗教间的教义争论[(33)],以及蒙哥主办道佛论争时福裕仍如前所确认管辖着和林的佛僧诸点来看,我们只能认为这是指教义争论的场所。如果是这样的话,少林寺圣旨碑的第一截即可理解为蒙哥委派福裕选择与管理佛教方面的参加者以进行争论准备的命令文书[(34)]。据鲁布鲁克的《旅行记》,蒙哥对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佛僧同样下达了进行争论准备的命令,其内容与圣旨碑第一截一致,因而应该被看作这是蒙哥对参加争论的各宗教的领袖一视同仁地发出的命令。
在与基督教的争论中“败北”的佛教,在与佛教的争论中“败北”的全真教,而又在与(西藏)佛教的争论中“败北”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事后在哈喇和林遭受冷遇,反之胜者受到优遇之类的事实均难以确认。那么,蒙哥果真是出于想知道各宗教教义孰优孰劣这样的宗教动机才举行争论吗?反观之,鲁布鲁克与对其来说纯属异端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一同参加争论应是毫无意义的。而从少林寺圣旨碑第一截来看,亦可认为噶玛拔希被置于曹洞宗的福裕的管辖之下,也就是说,各宗教内部所存在的教派间教义内容的差别此时已不成其为问题,或许可以说,蒙哥是想通过宗教论战,在各宗教中任命一位超越教派的领袖,进而间接地掌握各种宗教。而争论对于由各宗教的领袖招集起来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让领袖者对自己有深刻认识的场合。
三、第三次道佛争论的政治与宗教的意义
(1)忽必烈与全真教教团
1251年蒙哥即位的同时,忽必烈被委以汉地军政诸事[(35)],遂开府开平,并以此为据点展开活动。有关当时忽必烈地位的确认,如《至元辩伪录》所示,从散见的与其有关的记载中,的确可以窥斑见豹。例如,在第一次争论后全真教方面不履行蒙哥之圣旨之时,佛教方面即首先诉诸忽必烈(卷三,七六九页下)。全真教给佛教造成的实际损害不仅在蒙古,而且在华北也屡屡发生,因而向当地最大的实力人物忽必烈控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换言之,佛教与全真教的争执就发生在其肘腋,因而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切实的问题。这正是忽必烈在开平府主办第三次道佛争论的关键原因。
元代编纂的大都地区的地方志《析津志》虽早已散逸,但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收集其它书籍中所引用的佚文,出版了《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其中学校条收录了四则合刻于1249年所立燕京孔子庙碑中的发令文。其中以蒙文直译体白话汉文所记之1233年6月9日窝阔台的圣旨,由于《析津志辑佚》的刊行才首次得知其存在。该圣旨是为命蒙古必赤(书记官)之子18人于燕京孔子庙学习汉语,而下达给蒙古为统治华北而设置的燕京政府之政要的,同时还命从燕京官人的子弟中选出22名优秀者对其进行蒙语教育。窝阔台认为培养精通两种语言的书记官是非常必要的。高桥文治《太宗窝阔台癸巳年皇帝圣旨译注》(《追手门学院大学文学部纪要》二十五,1991年)一文,主要从汉语中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本圣旨进行了译注,其分析对象涉及到了学校条的全部。为丰富其关联史料,该文还论及了从窝阔台时代至蒙哥时代前后全真教在华北行政中的作用及忽必烈对其的态度。下面将在高桥文的引导下,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第三次道佛争论,并对此加以重新认识。
本圣旨几乎可以说是表明蒙古朝廷对汉语的有组织接触的最早记录,它发令于华北金朝的灭亡已成定局之时。高桥氏以此为着眼点,认为该事件的背后有蒙古对汉地经营的新的展开,窝阔台意欲使汉地的文书行政,均以该圣旨为据。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被作为书记官培养地的燕京孔子庙,从1222年建造之初开始实际上就已为全真教教团所占据。1233年,时为孔子庙道领的冯志亨即全真教道士,而与此同时总括书记官培养的最高负责人则为同教团的领袖李志常,建造孔子庙的王楫是一位从成吉思汗末年到窝阔台时代的重要的政治家,且与全真教关系非浅,向他进言建造孔子庙者正是冯志亨。冯志亨从燕京至陕西设立道观百余所,正如高桥氏所述,其中大多数无疑原为佛教一方的设施。《至元辩伪录》之所以记载全真教占据佛教寺院的暴行在众多地区屡有发生,原因即在于此[(36)]。
窝阔台为何将书记官之培养委诸全真教教团,其原因为1223年丘处机从成吉思汗处所获之全真教道士的差发、赋税的免除特许[(37)]。从撒马尔罕谒见成吉思汗归还的丘处机,同年任长春宫[(38)]住持。窝阔台时期访问蒙古的南宋使节的见闻录《黑鞑事略》(《蒙古史料四种》P495)中,有与此相关的记载:
尔外,有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堕于屠活,去为黄冠,皆尚称旧官,王宣抚(王楫)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赋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
由于金朝的瓦解,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儒者们陷入了科举废行之苦境,而燕京全真教的根据地长春宫,则成了他们的避难之所。丘处机从成吉思汗所获之特许,导致了许多儒士为生存而加入教团的结果。兹举一具体例证:根据窝阔台的圣旨,依冯志亨笔点有秀才二人、通儒道士二名,被培养成书记官。《析津志辑佚》学校条(P199)亦有“(李)志常尝为儒者,因避难而为道家者流”,可见李志常最初亦为儒者。正如高桥氏所言:“1233年前后,华北地区除军队外,在文书行政方面可有组织地利用的具有此种机能与知识的汉人集团,只有宗教教团”(同P421),其中,最早与蒙古接近并与在其庇护下的政治、军事要人保持着非常紧密关系的遍及汉地全域的全真教教团,被委以培养直接参与汉地文书行政的书记官之责,应是再合适不过的了[(39)]。
尽管蒙哥明令归还寺院,但该问题仍迟迟不能解决,这不能不说是原因吧。1258年忽必烈的令旨(第一节②)即针对此前李志常假传蒙哥下令归还寺院之圣旨并将其束之高阁而发的,②意在进一步彻底解决归还寺院问题。祥迈《至元辩伪录》卷三(七六九页下——七七○页上)中将假传之事作为1256年的事件而记载下来。总之在这一期间,全真教教团甚至能够假传皇帝圣旨,可见其对汉地文书行政的干预之深。
《析津志辑佚》学校条有道士冯志亨于1251年将附属于孔子庙的土地送给在京的儒士,委托其进行管理的记载(P199)。这是根据同年成为中国方面的统治者的忽必烈的命令而采取的措施。这一点从同书学校条(P200)所收1254年5月28日忽必烈令旨的内容来看是可以明确的[(40)]。该令旨严令冯志亨不得再度占据孔子庙。也就是说,从《析津志辑佚》中可见忽必烈意将全真教从燕京孔子庙排除出去。此外,高桥文作为相关文献史料而举出的《至正集》卷四十四,上都孔子庙碑中,亦有由全真教教团负责培养书记官“至定宗朝辍”(《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四三页)的记载。反观之,从继贵由而即位的蒙哥令忽必烈进入中国的1251年那一刻起,这一体制便告结束,这与从《析津志辑佚》中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这样,作为蒙古皇族而最先在中国设据点正式君临统治的忽必烈,试图将全真教从华北行政中排除出去,这是可以看到的。若将第三次道佛争论置于这样的前提下来看,可以说忽必烈极大地利用了蒙哥治下的哈喇和林所展开的诸宗教间的宗教论战,一面在表面上装作在教义争论中扶持佛教一方,一面又明确表示出将渗入汉地行政的全真教排除出去的姿态。但此后,忽必烈对全真教进行压制的事实却无法确认,表明忽必烈仅以彻底将全真教从文书行政中排除出去为目的,这一观点应该不为过,而且从争论中的处理中也是可以看到的。正如第一节所示,蒙哥圣旨的内容主要是伪经的废弃与佛像的修复、返还,而忽必烈的令旨、圣旨则着重于全真教非法占据寺院的返还佛教。非法占据的寺院与燕京孔子庙一样,都是全真教干预华北文书行政,并且是人才辈出之际的据点。
(2)八思巴的登场
如岩井所述,在前后三次举行的道佛论战中所见之佛教方面的人物多属禅宗,而野上则指出其中多为以少林长老福裕为首的曹洞宗佛僧[(41)]。有关哈喇和林举行的第一、二次争论,正如少林寺圣旨碑第一节所明示,争论的参加者与其选择权完全委托于曹洞宗的福裕并非毫无关系[(42)]。曹洞宗与全真教的对峙,因而成为道佛争论的基本构图。
然而在第三次争论中,除了作为前两回的中心而存在的华北佛教最大势力禅宗诸僧外,西藏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也作为主要的论战者参加进来。据《至元辩伪录》卷四(七七一页上——七七二页上)及前引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圣旨碑,第三次争论毋宁说是八思巴一人的独角戏。尽管如此,此前的研究对《至元辩伪录》中所见之有关八思巴的事实却评价甚低。一方面起因于将喀什米尔佛僧那摩误解为西藏佛僧,而那摩的被解职则被视为西藏佛教渗透到蒙古中枢的最早的例证[(43)]。但那摩并非西藏佛僧现已明确(参照前注⑩),而完全未顾及西藏文史料也是一大原因。例如,洼德忠文即认为,甚至八思巴的传记也未记载其出席争论之事,而言及此事的仅有《元史》、《新元史》等汉文文献。然而正如今枝由郎《关于八思巴造〈道士伏调偈〉》(《东洋学报》五六,1974年)一文所明确地指出那样,藏文文献明确地记载了八思巴参加道佛争论一事。
今枝氏所介绍的《萨迦派全书》第七卷《八思巴著作集》(东洋文库,1968年)所收小品《道士调伏偈》的跋语中有:
彼(太上老君)之信者称先生(zin shing),其众甚伙,洞察善逝之教已成害,据人主忽必烈( Go pe la)“驳其谬误之宗义”之命,戊午之年(sa pho rta’i lo)仲夏二十三日,八思巴,先生之师,永年修业自至教义之深奥者,以至正之理败十七人,命其为出家人[(44)](据日文译出,未查对原文——译者)。
此处所见之17人,即1258年5月23日被八思巴驳斥而成为僧侣的道士数,与《至元辩伪录》卷四(七七五页下)所谓“持论道士落发者一十七名”相一致。在《至元辩伪录》被活灵活现地大书特书的八思巴是佛教方面的主要论战者,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里不但可见八思巴是应忽必烈之命而参加争论,而且还可以认为,在忽必烈于开平府举行的第三次道佛争论中,由蒙哥委诸福裕的人事权也已消失。
或许忽必烈在举办第三次道佛争论之际,即已在探寻以八思巴为顶点而重组佛教界了。少林寺圣旨碑的第二截即为八思巴被任命为国师的翌1261年忽必烈的圣旨,该圣旨命以少林长老为首的五位汉人佛僧,统领八思巴(Baγisba baγsi拔合思巴八合赤)以下的汉地佛僧,但有关佛僧之事,则必须遵八思巴之命来解决[(45)]。蒙哥时代作为国师而位居蒙古统治下全域的佛教界顶点的那摩的卒年尚无法确定,记载着那摩事迹的前引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碑为1259年4月28日所立,由于此后已不见显示其生存的史料,可以认为他业已于1259年亡故。这样,在忽必烈登极之初即立八思巴为元朝佛教界之首,应是无任何障碍的。除华北佛教界的主流,在前后三次的争论中都作为中心而存在的禅宗以外,新人八思巴在第三次争论中的出现,已隐约可见元初佛教界构图之渊源。
结语
在科举废行的蒙古统治下的华北,确保具有文书行政能力的人才无疑是必要的。为此,窝阔台首先利用的是全真教教团,然而却因此产生了种种(蒙古人亦感觉到了的)弊端。有鉴于此,以正式统治华北为目标的忽必烈,则着眼于受全真教教团压迫的禅宗教团。同时,为了避免重蹈同样拥有众多颇具文书行政能力人才的禅宗教团取代全真教团而过分干预政治之覆辙,忽必烈启用了八思巴。他在自己亲自构筑的开平府召集七百余人演出了一场道佛论战的大仪式,在明确表现出将全真教从行政方面排除出去的姿态的同时,吸取了蒙哥主办的道佛争论并未消除禅宗教团的不满的教训,因而将在华北无任何根基的西藏佛教萨迦派高僧置于当地的汉人佛教教团之上,事先抑制了其势力的膨胀。这样,忽必烈通过1258年的第三次道佛争论而昭示于内外政治与宗教方针,在蒙哥死后的1260年,忽必烈于开平府即位,利用以中国为据点的新的蒙古国家诞生之机,已被明确地具体化。1260年任命八思巴为国师即为该方针的象征。
在13—14世纪的蒙古时代,政治与宗教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历来的宗教史研究都未能较大地超越这一狭小的范围,甚至在蒙古时代史的研究中,宗教史的研究成果也很难说被完全吸取。我们只有在利用汉文史料的同时,积极利用相关多种语言的史料,才能不但完成宗教史的研究,而且还可将其与蒙古时代史更为广泛地联系起来。
注释:
(32)据裕公之碑福裕于1248年应贵由之招请往哈喇和林兴国寺,“未及期月”,即应蒙哥之招,被授总领释教的都僧省之符。
(33)鲁布鲁克作为出使蒙哥的使臣,最初是于西历1254年5月25日即阴历同年五月八日抵达的,与第一截碑文发令的1253年12月7日仅差五个月。
(34)如果笔者的看法是正确的话,与鲁布鲁克对论的华北出身的佛僧,可考虑为福裕(山西出身)其人。
(35)《元史》卷三,宪宗本纪,宪宗元年辛亥六月条,P57。
(36)野上文(P229—231,注(22)、(23))整理了具体例证。
(37)蔡美彪前揭书P1;陈志超前揭书P445—446。
(38)《元文类》卷60,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P667上)虽记有成为书记官培养所的孔子庙即在长春宫,但却没有关于孔子庙特定场所的记载,故无法断定其正确与否(高桥文,P415—418)。
(39)稍错过机遇的禅宗教团也同样拥有众多颇具行政文书能力的人才,这与全真教教团毫无二致。如在少林寺圣旨碑第一截中所见,福裕即根据文书而对佛僧进行管辖。临济宗的子聪(刘秉忠)则于1241年随海云赴忽必烈处之际,也被发现具有这种才能,遂作为书记官而为近侍(《佛祖历代通载》卷32,P704)。其父祖代代出任辽、金为官,而他自己也8岁入学,身具成为儒者的素养(《元史》卷157,刘秉忠传,P3687)。子聪是可被确认的作为唯一的临济宗佛僧而参加道佛争论(第三次)的人物。他在忽必烈登基后也作为旧邸之一参与了新国家体制的筹划。1264年,忽必烈令其还俗,改名为刘秉忠,其宗教色彩已淡薄这一点应予注意(《元史》卷五,世祖本纪,至元元年八月癸丑条,P99)。
(40)关于该令旨及同学校条所收之同年七月一日忽必烈的令旨,高桥氏已预定予以译注。
(41)岩井文,P98—102;野上文,P245—247。有关第一次争论见《至元辩伪录》卷三(七六八页上),第二次争论之实际上未能举行及有关参加者也于卷三(七七○页上)列举出来。关于第三次争论,卷三(七七一页上)与卷四(七七五页中—下)亦分别列举,但如洼德忠文多次指出的那样,卷四中作为“对道士持论师德”而例举的十七个人名中,竟然不见福裕与八思巴之名实在使人不可思议,而且两者人数的差别也很大,地名表记的不统一同样很明显。卷四之“对道士持论师德”究竟是什么意思,笔者也无法说明,应该注意的是,这十七个名字均为汉人僧侣。
(42)《程雪楼集》卷6海云简和尚塔碑(八页表)有“师(海云)历事太祖、太宗、宪宗、世祖,为天下禅门之首”的记载。临济宗高僧海云之名一次也未在道佛争论中出现,是由于他已于1256年正月病倒,翌年4月亡故,因而不可能参加1256年的第二次、1258年的第三次争论(岩井文,P98)。1255年的第一次争论虽不在此限内,但是如果考虑到佛教方面的人事权掌握在曹洞宗福裕之手,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
(43)岩井文,P103—104注⑧②;野上文,P249;高雄文P13—14;洼文,P178。而岩井文(P102—103)中“对道士持论师德一十七名”之最后所列的川蜀讲主元一“为吐蕃系之僧亦即喇嘛僧”其根据不明,故不从。
(44)参照今枝文译出。1283年所著之《八思巴传宝环》(东洋文库藏)也记载了其参加道佛争论的事实,“此时,该大士之名传扬四海”(今枝文,P44—45)。
(45)详见中村、松川文。有关元代西藏佛教与华北佛教之关系,将另稿论述。
陈一鸣 译自《东洋学报》第75卷 1994年
标签:忽必烈论文; 八思巴论文; 全真教论文; 蒙古军队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元史论文; 国学论文; 元太宗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