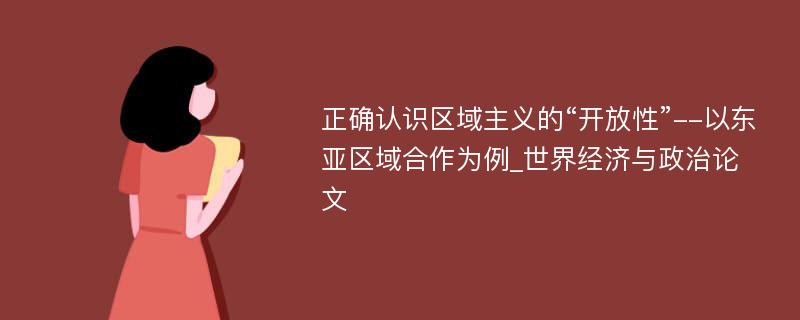
准确理解地区主义的“开放性”——以东亚地区合作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地区论文,开放性论文,为例论文,准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9550(2008)12-0071-06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时代,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成为引领区域合作发展潮流的一面旗帜。“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提出最初是为了解决区域贸易与全球贸易之间的关系而做出的一种努力。时至今日,发轫于亚太地区合作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APEC)的合作模式,还成为世界范围内推进区域合作的一种理想追求以及完善全球多边谈判机制的重要参照。因此,正确认识“开放的地区主义”,对于理解当下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地区主义“开放性”的基本内涵
对于“开放的地区主义”的确切含义及其实践要求,人们的认识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存一定争议。“开放的地区主义”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随着APEC等区域合作组织的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人们对“开放的地区主义”的认识必然会不断深化。鉴于此,人们倾向于对“开放的地区主义”做出较为宽泛的界定。例如,1994年,APEC名人小组(EPG)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衡量“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四条标准①;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坦指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的五种含义。② 同时,人们对“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分散式或者列举式定义也容易出现自相矛盾。例如,伯格斯坦认为,“开放的地区主义”的五种含义既可以独立采用,也可以同时采用。
“开放性”是人们认识“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基础概念。造成“开放的地区主义”出现不同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这种新型地区合作理念的“开放性”存在不同认知。要想正确理解“开放的地区主义”,必须准确认识“开放性”在地区合作中的基本含义。在实践中,APEC等区域合作组织未能就地区合作的“开放性”达成权威共识。这容易造成人们对“开放的地区主义”的认识缺乏相应的学理依据。因此,厘清“开放性”对区域合作的基本要求事关对“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准确把握。
正确认识地区主义的“开放性”需坚持整体和发展的观点。一方面,开放的地区合作空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开放的地区合作空间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会有不尽相同的发展变化,并常常具有一定的地区特色。一般而言,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应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强调自愿合作,不拘泥于形式或者制度。开放地区合作空间一定要立足于相关国家的实际和意愿,不能强制。强行推广区域合作的好处,不符合地区主义“开放性”的本意。在地区合作过程中,自愿让渡主权与强制让渡主权有本质区别。从逻辑的角度看,既然“开放的地区主义”主张地区合作向所有相关国家开放,它就理应尊重国家在主权让渡方面的利益,即国家保留必要时可以不合作的权利。从实践的角度看,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区域组织成员并未被迫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仍旧保持较为完整的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就APEC而言,在成员差异明显的情况下,区域合作只有本着自主自愿、平等协商的精神,才能更好地减少交易成本,提高合作效率。因此,APEC常常被亚洲成员视为咨询性机构,而不是经济共同体。
非制度化、非形式化是开放地区合作空间的独特魅力所在。相对于传统地区主义对制度的重视,“开放的地区主义”主张区域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寻求共识,不断地寻求非正式化、非制度化的灵活的解决方式。“开放的地区主义”提倡不拘一格的合作形式,其原因之一是它发现有些区域组织有时沉迷于制度建设,导致地区合作的运行效率不高,甚至陷入局部僵化的尴尬局面。开放地区合作空间不赞同欧洲区域合作的“介入原则”,③ 并明确反对建立超国家的地区性行政和决策机构。美国学者迈尔斯·卡勒认为,区域制度在设计方面可能非常不同,而且取决于区域伙伴和问题的特殊性。没有理由假定区域一体化的模式一定像欧洲联盟那样。④ 按照地区主义开放性的要求,区域组织对其成员只能通过发表声明、宣言等方式提出建设性意见。例如,东盟+中日韩(“10+3”)各国既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也是亚欧会议、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10+3”机制积极参与、支持并扩展多边规则,并不致力于构建一个封闭的、歧视性的集团(充其量,它仅仅赞同建立具有指导、咨询作用的协调机构)。
第二,倡导多样包容,追求内外开放的互动。尊重多样性是开放地区合作空间的基本前提。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应该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模式的差异。这是世界充满活力的表现,也是世界蓬勃发展的动力。同样,为了更好地推动区域合作,区域内国家需要以平等开放的精神,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地区。只有尊重本地区的多样性,因地制宜,才能探索出一条符合地区特色的区域合作之路。
实现内外互动,是开放地区合作空间的本质要求。传统区域性贸易安排明显具有排他色彩,其自由化措施大多仅限于成员内部,对域外非成员采取歧视性待遇。顾名思义,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在强调区域内合作的同时,也不排斥区域外合作,倡导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达到平衡。正如APEC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贯彻APEC“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是期望区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可以远远延伸至成员的疆界之外。开放地区合作的空间不仅要求区域成员之间相互开放、相互平等、消除歧视、减少区域内障碍,也支持区域成员与非区域成员的交往,力争实现在开放中推动各成员共同进步、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
第三,把握重点和基础,坚持宽领域、深层次的发展。地区合作的开放要做到有的放矢、重点突出。一般来说,地区主义可以从不同层面进行理解。在经济层面上,它提倡一种通过互利合作而达成的理性安排;在文化层面,它体现在人们对地区的信仰(或者价值判断)之中,是一种“想象的”地区共同体;等等。区域合作不应追求“一揽子”式的全方位合作,而应坚持循序渐进的法则,选准推动地区合作的重点、难点,以点带面,产生辐射效应,从而真正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多数情况下,区域合作的重点往往聚焦于经济领域的合作,这是推动区域合作更上一层楼的重要基础。
在抓好重点的基础上,区域合作要向更广泛的领域开放,向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合作逐步向文化领域拓展是深化地区合作的必由之路。换句话说,地区身份的建构也是推动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发展方向。虽然无须建立地区认同,区域一体化也能产生,⑤ 但是如果长期缺乏地区认同的归属感,区域一体化是难以取得长足进展的。事实上,经济一体化向政治、安全领域的扩散和外溢,将会触及地区各成员国国家主权的核心和最敏感的部位,刺激各国内部民族主义的神经,甚至会引起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弹,这时尤为需要共同文化观念的协调作用。鉴于此,地区身份或者认同的形成是检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否深化的基本标准。
二 东亚峰会对地区主义“开放性”的发展
作为亚太地区的次区域,东亚在区域合作方面一直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透过东亚地区合作,人们可以发现东亚地区主义“开放性”的一些基本特征,例如,不拘一格的合作模式(如“10+1”、“10+3”)交相呼应;多种形式的内部经济合作十分活跃;内部开放在观念、进程和体制层面均有所体现;⑥ 等等。特别是首届东亚峰会的召开打破了东亚合作的地域限制,推动东亚合作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丰富了人们对东亚地区主义“开放性”的认识。
首届东亚峰会的与会国不仅包括东盟十国及其三个传统伙伴(中、日、韩),还包括三个新成员(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10+6”模式的逐渐成形意味着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在东亚地区合作的深化过程中有了新的内涵,即开放东亚合作的空间较之以前有了更加宽广的视野。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如开放东亚合作空间的真实动力是什么,东亚地区的开放有无时间或空间的限制等问题。随着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必然会表现出一些不同以往的变化。这样一来,人们应尽量准确地认识“开放性”对东亚地区合作的基本要求,避免出现对东亚地区主义的误解。
当前,正确认识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需要突出强调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开放东亚地区的合作空间并不意味着经济领域的内外互动可以涵盖或者替代其他领域的合作。
东亚地区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启动最早且效果最好。尽管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远未达到欧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水平,但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贸易方面,东亚自由贸易区开始正常运转,东亚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30%上升到2005年的60%左右;在金融领域,亚洲债务市场乃至区域性货币开始启动;等等。按照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要求,地区合作应该是循序渐进而相互协调的,经济领域的合作效应能够“外溢”到其他领域。
然而,纵观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过程,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并未在其他领域引起应有的连锁反应。相对于地区经济一体化而言,东亚国家在安全等其他领域的合作明显滞后。例如,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并没有推动东亚形成一种切实有效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该地区仍存在冷战的政治遗产(如朝鲜半岛仍存在南北对峙局面)。可以这样说,东亚地区合作只是展现了经济合作“一枝独秀”或者“一路绝尘”的景观,并没有实现整体发展的目标,这明显不利于东亚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简言之,经济领域的内外互动只是东亚地区合作的重要内容,而不能涵盖或者替代其他领域的区域合作。
其二,开放东亚地区的合作空间并不意味着“非东亚化”可以成为本地区一体化的主流。
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孤立地实现自我发展。迈尔斯·卡勒认为,开放的区域是指,“区域”不被定义为地理实体,而是被看做一系列在某一特殊经济问题上寻求共同利益的国家。对许多亚洲国家来说,开放地区主义也意味着在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上与非成员国之间分享区域利益。那些同意议事日程并且愿意承担责任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进来,不管它们的版图在哪里。⑦ 要想保持东亚合作健康、可持续发展,东亚国家应适当考虑和照顾区域外国家在本地区的合理利益,增进这些国家对东亚合作的理解与支持。区域外国家参与到东亚合作进程,必然能够为东亚合作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深化同区域外成员(观察员)的务实合作,是近年来东亚国家推进地区合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但是,在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认识地区主义的逻辑起点仍然不能脱离“地区”一词的地理本义。种种迹象表明,名为东亚地区的合作峰会远远超出了地域限制,蕴涵了一股“远离东亚”的发展潮流。作为东亚峰会的主导者,东盟对参会国提出的三条认证条件是比较宽松的:保持与东盟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认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参加东亚峰会,只是东亚地区主义走向“非东亚化”的一个序幕,未来必有更大突破。实际上,上述与会条件为东亚峰会的再次扩展打开了方便之门,不仅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三国能够参加峰会,像美国、俄罗斯、欧盟等都有机会参会。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对整个亚太地区事务的重要影响,一旦美国大力“涉足”东亚合作,那么其影响力是东亚国家所不能相比的,这容易造成东亚地区合作迷失方向。为此,一些学者对“10+6”模式主导下的东亚峰会所体现出的“非东亚化”趋势表示忧虑并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如果开放东亚合作的空间没有明确或者整体的地域限制,甚至默认地区合作逐渐淡化东亚色彩,那么这种类型的“开放的地区主义”所倡导的东亚合作模式将会趋同于APEC模式,“开放的地区主义”在东亚地区将会逐渐失去吸引力。简言之,地区主义的“开放性”不能脱离地理因素的支撑,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也是如此。无限制的“泛东亚化”或者“非东亚化”明显背离开放东亚合作空间的发展潮流。
其三,开放东亚地区的合作空间并不意味着有关国家可以围绕地区合作的主导权展开政治博弈。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首届东亚峰会的召开引发了一场围绕地区合作主导权的斗争。日本拉拢印度等国蓄意夸大中国的“崛起”,力图提高自己在东盟峰会中的影响和地位,借此机会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为了阻止中国成为东亚峰会的主角,日本采取一些针锋相对的措施:在峰会召开前夕,多次抛出“经济绣球”,试图加强与东盟各成员国的关系;鼓吹本次东亚峰会是建立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一次重要机遇,以此回应中国政府提出的“10+3”模式;力邀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会,以此来牵制中国;在吃到美国的闭门羹之后,随即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拉入此次峰会;2005年12月13日,日本与东盟各国签订的共同声明首次正式使用了“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一词,而且日本还设立了总额为一亿美元的“东盟综合支援基金”。日本“制衡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这明显不利于东亚地区合作。欧洲一体化之所以成为区域合作的一个成功样板,与英、法、德“三驾马车”的积极推动密切相关。事实上,无论是封闭的地区合作还是开放的地区合作,都离不开核心国家的共同努力。为此,必须着重强调,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并不提倡权力空间的无限制开放,同样也要求核心国家展开有效合作。
其四,开放东亚地区的合作空间并不意味着适当的制度建设对于东亚合作是无足轻重的。
虽然“开放的地区主义”倡导不拘一格的区域合作方式,但是它并不否认制度对于地区合作的重要性。一种观点认为,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就是要彻底剔除国际制度的外部约束。造成这种褊狭认识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国际制度的基本内涵⑧ 存在误解。实际上,国际制度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法律、经济及政治领域的正式制度,也包括社会领域的惯例以及行为方式,等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在有助于消除封闭性区域经济组织的贸易转移效应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问题。⑨ 其中,最大的弊端在于它容易导致非成员的“搭便车”现象。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开放性的地区合作也需要一定规模的制度建设加以保证。
当前,制度缺失对东亚地区合作的影响日趋明显。具体到经济领域的合作而言,贸易自由化进程要接受普遍规则和强制措施的约束,而东亚地区贸易合作则缺少必要的硬性约束。这自然会引起人们对这样一个核心问题的关注:对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而言,东亚区域贸易是一种促进力量,还是一个绊脚石?区域合作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没有制度的地区一体化”往往充满变数,有时会出现停滞或倒退,明显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例如,南方共同市场的经验表明,“开放的地区主义”有时可以被成员用来证明其自身独特政策的合理性,从而破坏共同贸易政策的统一性。甚至,有学者认为,制度缺失已经成为阻碍南方共同市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⑩ 如果东亚合作始终处于灵活多变之中而不具备相应的稳定性,那么其发展后劲肯定会大打折扣。实际上,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的非制度性一体化组织也可以逐步实现制度化。(11) 因此,开放东亚地区的合作空间需要在“非制度化”与“制度化”之间做出一定区分,而不能一概剔除制度因素的作用。
三 地区开放视角下的东亚合作前景
地区合作空间的开放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有关国家已经深刻意识到,封闭的、排他的和针对任何特定一方的东亚合作并不符合东亚地区主义“开放性”的本意。正如温家宝总理2005年12月14日在《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1)只有开放的合作才能实现不断进步:(2)只有开放的合作才能更好地发挥区域优势;(3)只有开放的合作才能顺应时代潮流。(12) 促进东亚发展和区域合作,必须坚持开放的思维和保持政策的透明,这已经成为事关东亚合作发展前途的时代命题。
同时,地区合作空间的开放也面临许多挑战和难题。历史遗留问题短期内难有实质性进展,冷战思维时而兴风作浪,集体安全机制的建立尚需努力。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历史文化过于多样化,容易凸显政治体制的作用。例如,有些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对中国迅速崛起后的战略走向保持一定的警惕或防范。东亚国家对开放合作空间的认识不尽相同,直接影响到践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效果。因此,开放东亚的合作空间应采取积极措施克服弊端并化解不利因素,做到因势利导。
沿着地区主义的“开放性”提供的思考线索,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东亚地区合作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亚合作的深入发展应得到核心国家的联合推动。大国是推动地区合作的关键。没有大国之间的联合推动,地区合作难以取得长足发展。东亚地区合作始终无法超越的一个尴尬现实是大国未能就推动地区合作形成有效的战略互信。特别是中日关系的发展远未达到预期的水平。虽然“战略互惠”为发展中日关系带来了重要机遇,但是由于两国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如领海争端、国民心理的困惑、美国因素的制约),因此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尚需长期努力。另外,东盟试图担当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的重任,但是有心无力,难以胜任。中日关系的协调远远超出了东盟的能力范围,决定了东盟不可能推动本地区实现更高层次的合作。如果地区大国尤其是中日之间未能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并共同推动东亚合作的发展,那么东亚合作大幅度提升的空间可能是有限的。
第二,东亚合作的深入发展应得到机制建设的适当支持。要想克服东亚地区合作“建设性模糊”或者“过于泛化”带来的弊端,一个切实可行的努力方向是适当加强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总体来看,包含东亚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合作机制发育不足,即使本地区已有的一些制度安排(如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朝核六方会谈等),大多也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在可预见的未来,从功能性一体化的“软地区主义(soft- regionalism)”向制度性一体化的“硬地区主义(hard- regionalism)”过渡,将是东亚地区合作的一个发展方向。东亚各国应积极支持并参加现有的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根据现有组织的不同情况,制定有的放矢、层级分明的区域合作战略,采取措施巩固完善现有机制,使之在区域合作各领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进而形成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格局。例如,在推动地区合作转型的过程中,东亚国家可以积极探索以非国家行为体、非经贸实体为主导的“地区治理”,(13) 以此探寻建设地区合作机制的相关路径。
第三,东亚合作的深入发展应注入地区身份或者地区认同等观念因素。理论上,地区意识、地区认同观念在地区主义的分析中十分重要。(14) 在实践中,地区认同的最终形成对于东亚地区合作的重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东亚是一个文化多样的地区,历来缺乏一些类似“大欧洲”的一体化观念,甚至也没有类似“泛非主义”的整体观念。鉴于文化多样性以及市民社会缺乏的客观现实,东亚地区的归属性地区认同较弱且十分散乱,(15) 东亚国家历来都不奢望地区认同能够在短期内形成。在推动地区合作的过程中,东亚国家常常强调国家层面的“身份认同”,注重国内层面的利益考虑,而很少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社会学习过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东亚国家不仅没有形成一种共同的外部安全观念,而且有些国家还在制造和散布各种“威胁”论调。反观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史,共同观念(包括安全观念)为地区主义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法国和德国不遗余力地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与两国形成的“大欧洲”这种文化默契或者地区身份密切相关。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表明,地区认同的缺失是东亚地区主义异常活跃而略显松散的主要原因所在。尽管地区认同的缺失是目前东亚地区合作的一个明显不足,但也恰恰是东亚地区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不竭动力所在。
[收稿日期:2008-09-12]
[修回日期:2008-11-10]
注释:
① 这四条标准分别是:第一,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扩大成员的单边自由化。第二,在基于最惠国原则实施区内自由化的同时,继续减少对非成员的壁垒。第三,在互惠的基础上,把地区自由化的成果扩大到非成员。第四,允许任何一个APEC成员单边、有条件或无条件地把APEC自由化扩大到非成员。参见周涛:《“开放的地区主义”释义》,载《国际商务研究》,1998年第5期,第32页。
② 它们分别是:(1)实行“开放的成员资格”;(2)坚持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3)坚持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4)推动全球自由化;(5)强调贸易便利化。参见[美]C·弗雷德·伯格斯坦:《开放的地区主义》,载《经济资料译丛》,1999年第2期,第43~47页。
③ 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齐亚曾经专门就介入性地区主义做出论述,并认为围绕介入性地区主义的新形式的地区认同特性的建构可能是21世纪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石。关于介入性地区主义的定义、可能性等内容的详细论述,参见阿米塔夫·阿齐亚:《地区主义和即将出现的世界秩序:主权、自治权、地区特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67~69页。
④ [美]迈尔斯·卡勒:《从比较的角度看亚太的区域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6期,第19页。
⑤ 迈尔斯·卡勒:《从比较的角度看亚太的区域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6期,第16页。
⑥ 苏浩:《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49页。
⑦ 迈尔斯·卡勒:《从比较的角度看亚太的区域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6期,第19页。
⑧ [美]罗伯特·基欧汉:《研究国际制度的两种方法》,载[美]詹姆斯·德·代元著,秦治来译:《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312页。
⑨ Jessie P.H.Poon,“Region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Is Geography Destiny?”Area,Vol.33,No.3,2001,pp.257-258.
⑩ Michael Mecham,“Mercosur:A Failing Development Proj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9,No.2.2003,pp.381-382.
(11) 宋玉华、阮燮富:《论开放的地区主义——APEC的最佳选择》,载《世界经济》,1996年第10期,第15页。
(12) 《首届东亚峰会签署宣言中国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参见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
(13) Nicola Phillips,“The Rise and Fall of Open Regionalism?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on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Southern Cone of Lain America,”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4.No.2,2003,p.218.
(14) Andrew Hurrell,“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eds.,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40.
(15) 刘兴华:《地区认同与东亚地区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5期,第22页。
标签:世界经济与政治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apec论文; apec峰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