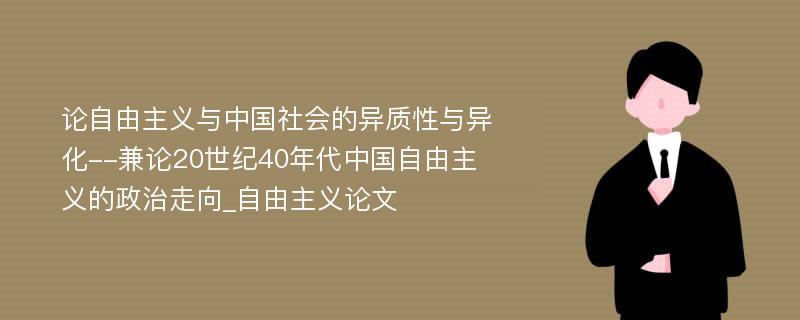
论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异质疏远性——兼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4)02-0114-07
自由主义,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在中国几起几落,对几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思想的一次最集中的展示,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绝唱,虽然声势浩大,盛极一时,但却来去匆匆,昙花一现。虽然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比以往任何时代的自由主义都广泛地卷入了政治漩涡,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至少是潜在的或有关舆论的。但历史的天平并不是真正地站在自由主义一边。作为一种运动,自由主义的失败是不可否认的,但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此作为判断真理与谬误的标准。作为一笔思想遗产,对于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不应该简单地“一否了之”,而是应该深入地分析、借鉴,以便更好地回答:自由主义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中屡遭失败,中国社会究竟需不需要自由主义等一系列问题。
一、自由主义的潮起潮落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是通过维新派尤其是严复和梁启超介绍而来。但作为一个思想流派,自由主义兴起于五四时期,以胡适、张东荪、罗隆基等人为代表。中国自由主义经过了20、30年代不绝如缕的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渐渐兴盛,抗日战争胜利后则蓬勃发展,几成汹涌之势。
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是抗战时期轰轰烈烈民主宪政运动的延续和深入。此时,自由主义的呼声异常地强烈,舆论界一致要求思想言论自由,一些自由主义者更是喊出了:“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1](P603)从而使自由主义在40年代的中国发展成为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
40年代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与20、3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相比,影响更大,其范围遍及整个知识阶层,而且公开打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号。在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公报》,在沪、津、渝、台、港5地设有分版,各地的《大公报》异口同声地说:“大公报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作风,大公报同人信奉自由主义”[2]。在其“社论”和“星期论文”专栏中,有关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教育自由的呼吁和讨论成为其中最突出的内容。这一时期,全国各地自由主义的报刊杂志纷纷出现,影响较大的除了各地的《大公报》以外,有上海的《观察》、《时与文》,南京的《世纪评论》以及北京的《新自由》、昆明的《民主周刊》等,其中《观察》周刊是这些自由主义报刊中的佼佼者,它的前身是在重庆创办的《客观》周刊。《观察》周刊自1946年9月在上海创刊,其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高扬自由主义大旗,以超然的态度,对战后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很快就成为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舆论中心,左右着自由主义思想界的动向,最盛时发行量达到了10.5万份[3](P143)。当时的很多报刊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着自由主义的色彩,一些报刊直接冠以自由之名,如《自由批评》、《新闻自由报》、《自由导报》之类。在争取自由的声浪中,“思想界对于自由主义辩论,曾一度热烈到极点”[4](P1)。
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主张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的色彩”[5]。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主义在文化上意味着“养成个人的责任心与自尊心”[6]。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立场,保持其个人的发言权。”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会加入政党,如果加入,那就牺牲了个人自由”[2],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了。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不须有固定的内容。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只是一个批评的精神与容忍的态度”[6]。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普遍崇尚理性,他们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就是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而且“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7]自由主义者坚信理性的价值,“反对意气、霸气和武器。”[5]
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主张进步,反对倒退,认为“停顿、落后、退步,都是自杀”[7]。但在社会改革的手段上,他们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有和平改良的手段进行社会变革,即:“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要“和平的转移政权”,“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同时他们一再强调宽容的作用,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宽容意味着“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8],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宽容的国家”和“不宽容社会”提倡宽容,更有现实针对性[9]。
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民主至上论者”。在他们的眼里,民主政治简单地说就是民治、民有、民享。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如果少数人的利益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那么他们将坚决反对。“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设施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除此之外,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还把民主的范围由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主张“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须经济民主。”[7]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政治民主(也称之为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也称之为经济民主),“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引导人类和平进步,缺一不可。没有政治自由,经济平等不能良久保持,而人类的精神生活,不能得到解放;没有经济平等,政治自由的根基也不坚实,而人类的物质生活,常有匮乏之虞。”[10]甚至有许多人将自由主义的主张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同起来,认为:三民主义“是彻底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民族主义首先求中国之自由,再求世界之自由……民权主义是求人人在政治上的自由,而民生主义也是一种经济上的自由主义”[11]。
当然,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的信念之上的。他们认为,自由不是指内心的一种境界,而是“不受外界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约束的权利”[8]。在宗教方面不受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可见,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所争取的自由涉及到言论、出版、教育、学术、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但重点是言论出版方面的自由,因为“自由为民主政治的主要观念,言论出版自由则为人民的基本权利。”“任何一国的政府在积极方面自应培养发扬之,消极方面则当维护保障之,此为民主政治的天职”[12]。当然,“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7],但法律首先要保障人民的自由,而且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则,人民就没有守法的义务。
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又是一种人生态度,这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的基本认知。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是近代思想的产物,其功能在指示一种生活态度,尤其是有关政治生活的态度。”[13]“自由主义足以代表一般书生学者对于政治的共同信仰。如注重理性和自由批评,注重个性发展,民主政治,注重缓进改革或不流血的革命等。”[14]而自由主义的“不朽贡献在于反独断主义的批判精神”,“自由主义为求人类意识的解放,因而也必须从两方面同时下手:一方面是争取思想的自由,一方面是唤起自由的思想。”[15]自由主义者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大家有饭吃,各人选路走”的理想社会。
然而,随着国共两党间的军事失衡,自由主义在中国存在的空间越来越狭小,虽然他们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现在留下的只有一条可走的路,让中间派来领导革命,实行新政”。“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主义,领导革命,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只需要三十年时间,这班人必能安定中国,完成革命的最后一步”[16]。
但历史是无情的,国共两党的生死大决战,是代表两个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它逼迫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非此即彼之中做出抉择,夹缝中生长的自由主义遭到了来自国共两党两方面的夹击,其赖以存在的的环境不复存在了。在人民解放军胜利的隆隆炮声中,盛极一时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此在中国大陆的思想界便销声匿迹了。
二、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异质性
当然,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原因非常复杂。毫无疑问,近代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谓先天不足是说自由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而是美雨欧风吹进来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思想资源。
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然而,也是岐义最多、最容易引起人们强烈爱憎的观念。孟德斯鸠说:“没有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的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17](P153)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热烈地赞美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毕生为自由理想而奋斗、为自由事业投身于法国大革命、最后却被送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在临刑前从心底迸发出对自由近乎绝望的感慨:“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亚伯拉罕·林肯说过:“世界上不曾有过对自由一词的精当定义,而美国人民现下正需要一个精确的自由道义。尽管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奋斗,但是在使用同一词语时,我们却并不意指同一事物。……当下有两种不仅不同而且互不相容的物事,都以一名冠之,即自由。”[18](P3)著名学者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指出,“自由”一词有超过二百种以上的意义,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理论对它有不同的看法。用著名学者盖利的话说:“自由这个概念是一个在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19](P3)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也有“自由”一词,但与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是名同而实异,以至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在翻译密尔的《论自由》一书时,对“自由”一词的翻译颇费了一番心血,再三斟酌才最终翻译为“群己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能和自由主义发生亲和作用的是道家思想。老子说过的“道法自然”就含有不受羁绊束缚、追求精神自由的含义。庄子的《逍遥游》更是追求自由精神的形象表述,但《庄子》中只有“自得”、“自适”、“自善”等词汇,却没有“自由”一词。《孟子》中也有“自得”一类的语言,但却没有“自由”一词的明确表述。明确地使用“自由”一词是在唐代的诗歌里。唐代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荒远之地,为了排解苦闷,他寄情山水,写下了不少传世诗文名篇,其中《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一首为千古绝唱,并提出了“自由”一词。诗曰: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杀花不自由。
另外,在杜甫的诗中,“自由”一词曾先后出现过几次。如:
朝光入瓮牖,尸寝惊弊裘。
起行视天宇,春风渐和柔。
兴来不暇懒,今晨梳我头。
出门无所待,徒步觉自由。
又如: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
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自由”,是一种自由自在,心中觉得舒服畅快的感受。这种感受,当然是自由主义所赞许的,但这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所讲的那种自由。所以说,“传统语汇中的‘自由’一词,并不是自由主义所说的观念”[20](P275)。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法治”、“兼爱”、“民主”、“改革”等语汇,但这些语汇的内涵与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自由主义中所讲述的这些词语的意义是不一致的,有些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的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是19世纪西方社会兴起的三大社会思潮,这三种思潮在价值取向上差距很大。其中,民族主义强调国家至上的原则,认为个体从属于群体,个体只有作为国家的一份子而存在才能显示真价值。社会主义强调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并认为真正的社会平等只有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才能实现。自由主义则提倡个体本位和重视个体自由,并认为国家的职能旨在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受侵害。
这三种社会思潮在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如果说从挽救民族危机、追求国家富强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共识的话,中国知识分子首先选择的应该是民族主义。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是先选择了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当成了富民强国的利器。这其中原因很多,在此暂且不谈。本文要强调的是,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虽经过无数的战乱而终不分裂,这与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的传承不无关系。儒家文化的一元论心态和思想上的合模要求,对西方不同类型的社会文化思潮表现出了不同的“亲和力”和“排斥力”,从中国文化的特质上看,中国文化对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吸收较易,而对自由主义思想则较难。例如,中国的家族观念虽不同于民族主义思想,但二者并非是格格不入。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国家是家的放大,个人对家族的忠诚,能够顺理成章地转移到国家上面来。又比如,家族观念中包含有强调家族中利益的一致,提倡父慈子孝、敬老爱幼,以及推己及人的道德伦理思想,这种注重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相契合。此外,传统的一元论心态及思想合模要求虽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有质的区别,但就追求思想的统一及观念一元化方面,彼此之间仍然能够找到交接点,然而,对于提倡思想多元和思想宽容、价值多样化的自由主义思想来说,传统的一元论心态及思想合模要求则似乎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中国,对国家富强的追求远远超过了个体独立人格的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价值取向上的反差如此之大,导致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生根发生了一定的困难,所以,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很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对应的思想资源,汲取自由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养分,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难以引起共鸣与呼应,它们之间实际上是两种不同“质”的文化产物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两种不同质的植物一样,一个嫁接到另一个上,其结果不是嫁接的枝条枯萎,就是被嫁接植物的死亡。
三、自由主义与中国“现实社会”的疏远性
一种思想、学说和观点,如果不能为许多人所接受,或者说如果不能与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相吻合,就不可能动员与号召广大民众投身于变革现实的社会运动之中。任何一种模式的思想都不可能远离某一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而独自大规模地顺利成长,自由主义在适应当时的中国社会与变革社会这两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后天失调是指自由主义思想本身是脆弱的,容易变质的,自由主义思想成长需要很多充分的条件,就如同一粒种子,要有清新的空气,适宜的温度和水才能发芽一样。可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成长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始终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而始终没有成熟,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缺乏自由主义成长、发育的气候和土壤。著名学者托克维尔指出:“再没有其他事情比自由的训练更为艰难,……要在风暴中建立自由通常会发生困难。”一般说来,以社会改良为宗旨的自由主义,总要以法制健全、社会秩序正常化以及社会的稳定为先决条件的。但中国自晚清以来,社会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王权的崩溃,整个社会与政治秩序陷于分崩离析之中,甚至由于连年战乱,连基本的道德秩序与价值系统都无法维持,尤其是在国共两党进行生死大搏斗的历史转折关头,在这样一种社会普遍失范的状态下,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调和国共、兼亲苏美、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学术自由”等社会改良计划与方案,自然无法实现。
另外,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自由主义本身也有它自己的缺陷。在西方,自由主义是与中产阶级的产生而相伴生的一种思想,也就是它以中产阶级为其社会基础。中产阶级面对落花随流水触景生情的伤感和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奔波流浪所产生的痛苦,是根本不同的。中产阶级最关心的是权利的维护和私有财产的保障,而劳苦大众关心的是能够天天吃上饱饭。中产阶级的弱小,使自由主义缺乏它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者的政治主张无法解决劳苦大众关心的、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在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内战问题上,他们不明白内战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斗争的必然结果,而误以为内战是所谓丧失理性造成的。他们认定人是有理性的,会按照理性去认识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且政治应该是理性的产物。所以,他们反复恳求人们诉诸理性:“我们知道一切悲剧的造成,都可能是出于盲目的意志,由于情感抹杀理性。要从悲剧中解脱,从悲剧中升华,只有求救于理性,求救于清明的理性。”[21]
历史并不理会这些呼吁,在短短的3年里,中国社会屡屡翻起轩然大波,终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自由主义者的“和平—改良”的道路撇在了一边。同样,当时人民迫切要求解决的“饥饿问题”、“民主问题”等,说得更远一点,就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问题,对此,自由主义根本提不出任何现实、有效的措施,就连自由主义者胡适所说的“闹中原的五鬼”,自由主义本身也无法解决。虽然自由主义者自认为他们是人民的代言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自由主义者与国共以外的广大人民。这是第三种力量,也是一种民众的力量。这一力量的动向对于中国前途的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2]但事实上,他们与民众有着天生的距离。他们无法动员,也不愿将民众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一股足以影响中国现实政治的强大力量,因此,他们的呼声除了表达出他们对于中国未来前途及政治走向的忧虑和关注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这样,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者关于中国未来政治的种种设计与梦想,终究是纸上谈兵。他们所提出的主张在本质上远离中国的社会实际,是中国政治上的“空头支票”,是“画饼充饥”,所以“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终究只能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却无法成为激励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劳苦大众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旗帜。”[23](P26)这种远离广大人民群众迫切现实需要的思想与主义,在武力与强权面前束手无策,根本无法满足广大民众改变现状的要求,自然得不到广大民众的群起响应。
自由主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层意义上说,美国学者J.格里德讲的是有道理的,他说:“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还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与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24](P368)。
四、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价值
简单的否定意味着对有益思想的排斥,是思想上自我封闭的表现。人类的思想具有继承性。但这种继承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放开眼光,运用脑髓”,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批判地继承,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说的那样:“传统与自由的关系当然极为复杂,但,in the lastanalysis,如果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完全放弃了传统,他们即便高唱自由,这种自由是没有根基的。”只有通过对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批判,使之达到更新与创造性的转化,才能为自由、民主、法治在现代中国的生根,提供文化根基和精神土壤。
毫无疑问,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在对中国社会的总体设计方面,未能充分满足中国现代社会的变革需要,历史的天平不向它倾斜也自有其内在的理由。它表明:20世纪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只能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进行,任何把西方发展模式移植到中国的做法,都不免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历史的冷酷与无情,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我们不能以此判定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便一无是处、一文不值。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人对自由追求的合理性,自由主义为人类贡献的基本理念,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权等,依然是人类不懈的追求目标,有它的合理性、正义性和生命力,关键的是在于我们如何去从中汲取有用的营养。
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者要求在中国实施民主政治,保障个体的自由,他们指出,民主政治并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在中国社会里,民主政治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有说话的自由,并要有容忍别人说话的自由;每一个公民都有选择生活的机会,并获得生活安全的保障;每一个国民都有选举政府决定政策的权力,并保有批评政府及政策的权力。”[25]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无疑是对传统专制制度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他们主张政治改革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而不是激烈的暴力革命,或者说只有在改革行不通时,才能进行革命,因为暴力革命的局限性太大,也就是说:浪费太大,收获太小。革命的收益根本抵不上革命的成本。所以,历史上的革命几乎无一不是牺牲太大而代价不足补偿其十分之一。更为重要的是,革命与改革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革命与改革存在着互变性,即:革命与改革之间存在着互相转化:只有在和平改良行不通的时候,才有革命的发生。如果平和的改良能够行得通,那么,决不会有革命的发生。而且,不能说所有的革命都是成功的,尤其不能以是否夺得政权作为判断革命成败的标准。“所谓成功的革命与失败的革命之区别就在于,一个确是冲开生产力再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或阻碍,而另一个却只是社会关系变化一下,并不能把再进的生产力解放出来。”[26]就是说,只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才是成功的革命。否则,仅仅是使政权发生了转移,或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动,那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中国人过去把改朝换代称之为革命。如果要把改朝换代与革命严格加以区别,就会发现:改朝换代式的革命是失败的革命,失败与成功以什么为标准呢?这就只能看它能不能解除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致使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准有所提高。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就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它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自由主义者要实现经济平等,建立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他们除了在政治领域中强调自由、平等、法治外,还要在经济领域中实现经济正义:“所谓经济正义,简单地说就两点内容:其一是工作权(即人人都有就业的权利)的保证,其二是生存权(即人人都有基本生活的权利)的保证。”[27]自由与平等的完全实现,必有赖于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如果没有经济作基础,自由与民主只能是口头上的或是写在纸面上的。近代历史的发展说明,自由始终没有扩展普及于全民,就是由于贫困的农工阶级在现代国家中,虽然表面上享受自由的法律权利,但是他们自身的经济情况,却阻碍了他们实际上享受这种权利,法律上的规定是“应该”享受自由;而实际的问题是“能”“不能”享受自由。“这种‘能’与‘不能’的背后,实在隐藏着阶级的分野,财富分配的不均。”[28]这种情形正是所谓“不平等”的具体体现,也就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严重地制约着政治权利的实现。有钱的,能享受的,能享受自由的,在现代国家中,都成了特权阶级。他们自由的获得,是建筑在社会的经济不平等上面,因此,少数人经济上不平等的存在,恰好是全民不能普遍获得自由的经济原因。这些政治理想的设计,不管从任何角度讲,都能为人们树立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撇开具体历史条件,仅从抽象的方面,去理解自由主义主张,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政治主张不仅无可厚非,而且也是现代社会所追求的目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者在自由精神、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方面的思想在现在依然有着启发性。殷海光先生说:“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判能力和精神,有不盲从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的主张比殷海光先生的说法更具体,更详尽。他们认为:思想自由应该说是绝对的,任何人也无法干预一个人的思想,而学术自由则是相对的,是需要许多相应条件的。学术自由并不是说政府不管学术事业,就有学术自由了。但这个“管”,不是管制,而是管理。管制是限制学术的自由,而管理是指政府对学术负起了责任,有目的、有计划地发展学术事业。中国的学术事业要想有大的发展,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需要这样的管理。
同时,他们还指出,自由的精神,并不是虚无缥缈、高深莫测的,它只不过是一种批评的精神与一种容忍的态度的结合。从学术探讨的角度上说,没有任何一种学说与思想是不可以批评的。因为真理与谬误往往只是一步之遥,而且真理与谬误也总是相对的,对自由的禁止,无疑是对真理和进步的扼杀。所以,“在自由的精神下,根本不能有‘邪说’,亦不能有‘一尊’,只有研究的所得而无开始的信仰。倘使没有这个自由精神,恐怕不会有实验的科学的产生,也不会有进步的观念的出现。老实说,即马克思亦正是这种文化程度的产物,不先有这个风气,则马克思的思想是不会产生的。”[6]这些话语,至今仍然让人感到掷地有声,发人深醒。
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能是当代史。”它反映了历史与现实间河流与河床般的关系。由此可见,认识历史,无疑有助于加深对现实的认识与理解。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失败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思想遗产是毫无意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要隔相当长的历史时间才能看得清楚。不管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现在看来有多少不足,但他们对自由、民主、法治、平等等思想的不懈追求以及对学术思想的独到见解仍有可取之处,只要我们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其政治主张仍不失为现代社会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收稿日期:2003-12-24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自由主义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大公报论文; 异质性论文; 观察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