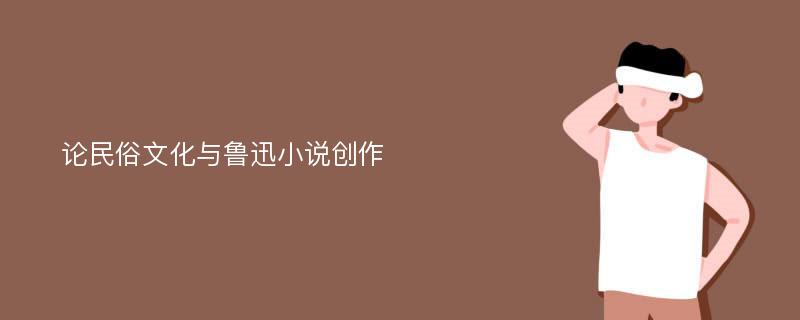
薛文礼[1]2004年在《论民俗文化与鲁迅小说创作》文中提出本文从民俗文化角度论述了鲁迅小说创作及其影响,共分叁篇。上篇,主要从民俗文化、故乡的民俗文化、“胡羊尾巴”的童年记忆和鲁迅小说创作的全新接受视角等四个方面,论述鲁迅之所以成为中国乡土文学第一人的原因及过程。在民俗文化中主要介绍了民俗、民俗文化的概念及其包含的内容,阐述了民俗文化既是形成鲁迅小说创作的传统文化心理定势的土壤,又是表现这种心理定势的最佳物化形态。在故乡的民俗文化中介绍吴越民俗文化以及故乡文化对其气质,人格的形成和创作的影响。在“胡羊尾巴”的童年记忆中旨在谈鲁迅作为“一个民俗库”的成长过程及人格形成的原因。在鲁迅小说创作接受视野中可以看到鲁迅对民俗文化(吴越民俗文化)的接受经过了不同的认识、体验与吸收的过程,进而阐明民俗文化是鲁迅小说创作的全新接受视角。中篇,主要写鲁迅小说的民俗文化情结。鲁迅一方面立足于乡土,另一方面又超越乡土,将笔触伸展到更深远的文化传统上,既有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无情的解剖,又写出封建宗法制度的“吃人”本质。内容涉及家族,祭祀,仪式,服装,称谓,婚俗,葬俗,钱币,求神拜佛等方面。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深邃清新的艺术笔调,通过浙东乡土人生和社会现实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20、 30年代旧中国的社会状况。下篇,主要谈及其对年轻乡土作家的民俗方面的影响。无论是王鲁彦、许钦文、许杰、王任叔和台静农,还是柔石、萧红,他们都自觉地以鲁迅的笔法从历史沉淀的积习和国民愚昧、麻木的情性中,对传统的陋俗进行了沉重的思考和深刻的解剖,发出了震憾人心的力量,吹奏了一曲凄婉低郁的民族生与死的古老的歌谣。
薛淑敏[2]2011年在《鲁迅小说的民俗意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有两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民俗在发展中具有了独特的地方性,也逐渐与文学结合,进入作家的文艺作品中,因此民俗事象也就成为文学作品的艺术道具,从文艺民俗的角度来看,这些进入文学领域的民俗事象具有了意象的功能,我们称之为“民俗意象”。鲁迅小说一个显着的特征就是民俗事象的大量运用,作家在小说中赋予民俗事象独特的文学意义,使其除了具备表层意义之外又具有了文学意义和功能,即意象的功能,从而使民俗意象成为鲁迅小说写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使民俗意象具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取向。本文首先引入了民俗的定义,古今中外对民俗的界定有所差异,但基本观点又十分接近,之后文章从两个方面分别探讨了文学与民俗的密切关系;然后在对“意象”概念阐释的基础上过度到“民俗意象”的含义。以此为理论基础,在下一章节便从民俗学分类的角度,对鲁迅小说中涉及的民俗事象做了详细的梳理,当民俗事象进入文学作品时就具有了意象的功能,转变成民俗意象,进而结合具体的文本,分析民俗意象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的开拓、情节的构成以及环境的渲染所起到的艺术表现的作用。接下来文章从民俗意象的角度,分析了它们独特的文化价值取向,民俗意象中呈现的礼俗观念,以及蕴含的文化反思;我们也看到当代文化的自觉倾向。
李带娣[3]2018年在《民俗学视阈下的台静农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提出皖籍作家台静农曾经在20世纪20—40年代的大陆文坛非常活跃,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散文,成就颇丰。他以诗歌步入文坛,以小说一举成名,其小说大多以故乡的人事为材料,民间性特别强,民俗的穿插、书写更是一大亮点。他通过大量民俗事象的书写构建起了一个羊镇艺术世界,描写了宗法制乡村底层百姓的辛酸血泪,展示了二十世纪初皖西乡村的社会风貌。本文以民俗学为视点,通过文本细读梳理台静农小说所涉及的民俗,深入探讨其小说民俗化创作的成因,发现民俗事象在其小说中的文本价值。本研究共分叁章:第一章依据民俗学的分类梳理了台静农小说中的民俗事象,将其加以归纳分类,并从精神、社会、语言叁个层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小说涉及鬼神论、宿命论、预兆论等精神民俗,展现了冲喜、转房婚、买卖婚等社会婚俗,还表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民俗。第二章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考察了台静农小说民俗化创作的原因。首先,作家生长在民俗文化丰富的乡野,对当地的民俗风情从小就耳濡目染,因而浓郁的地方民俗文化不仅对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其小说创作的源泉。其次,从作者本身而言,他早年亲身参加歌谣搜集活动,回乡搜集了大量民俗素材、积累了理论知识,这为其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在与鲁迅交往的过程中,鲁迅的指导和教诲以及其作品对台静农的影响不言而喻,不容忽视。此外,人情怀于土的乡土情结是作家创作的内在驱动力,促使作家把目光聚焦于故乡百姓,把笔触伸向乡间底层。第叁章主要研究民俗事象在台静农小说中的叙事功能,深入探讨民俗事象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主题揭示方面所起的作用。民俗书写使得人物性格鲜明突出、人物形象鲜活饱满。另外,民俗事象作为小说主线贯穿全篇,使小说情节跌宕起伏,还以细节形式深入小说肌理,丰富了小说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民俗在主题揭示中作用突出,不仅是批判封建陋俗、揭露社会黑暗的最佳例证,还是解剖国民灵魂、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有力工具,使作品主题意蕴深刻。
王辉[4]2016年在《民俗描写: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交汇》文中指出李佩甫是当代河南着名作家。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创作了多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平原叁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金屋》《田园》《乡村蒙太奇》等作品。描写中原大地的山川风物,探索中原村落民众的文化心理,探讨中原村落社会的各种问题,是这些作品一贯的主题。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细致、繁复、精彩的民俗文化描写,使其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历史蕴涵。本文拟立足于民俗学本位,探讨民俗描写对李佩甫作品审美意蕴与历史蕴涵的建构作用。本文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绪论,包括论文的缘起、目的与意义、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主要通过文本细读,对李佩甫作品中的民俗描写进行梳理。本文从宗族文化、人生礼仪、民间信仰、民间文学等四个角度,对李佩甫作品中的民俗描写进行了归纳。这些民俗事象的归纳,为后面我们探讨民俗描写在呈现中原村落社会、探索民众文化心理和内心世界、建构作品历史蕴涵与审美意蕴等方面的作用打下了基础。第叁部分为正文第二章,主要探讨民俗描写对作品深厚文化蕴涵的建构。首先,民俗文化的传承性,让民俗描写有力地增强了作品的历史纵深感,促进了作品炽热而又冷峻、淳朴自然等艺术风格的形成。其次,民俗描写有利于作者对小说氛围的营造。细致、生动的民俗描写营造了作品中的生活氛围,呈现了中原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让作品中的民俗物品具有意味深长的象征意蕴。再次,民俗描写深入民众的精神世界,揭示了体现在民众观念、行动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在探讨民众文化心理的基础上,作者探讨了民族的命运与出路。第四部分为正文第叁章,主要探讨民俗描写对社会变迁、民族文化心理转换的呈现作用。首先,激荡的时代风云冲击着传统的民俗文化与村落社会秩序,同时,民俗文化也一定程度上支撑着民众的生存,维系着村落社会的的秩序。其次,民俗描写呈现了风尚影响下的民众生活。风尚起着为时代生活命名的作用,体现了民众对于权力、面子等世俗价值的追求。再次,民俗描写能呈现社会转型与民众文化心理转换过程中民众的精神世界。通过民俗描写,李佩甫探寻了民众面对转型迷茫而躁动的集体心理,刻画了坚守与挣扎中的传统文化代表者的悲剧形象,更展现了作者对于新人形象的思考与期待。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语。这一部分主要对前述内容作简单的概括和总结。
张昕[5]2009年在《民俗文化与作家作品关系——浅论民俗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作为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民俗文化更是为我们华夏子孙所继承,而这些反映人民大众思想情感的民俗文化也对历代文人学者的思想及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亦可以体会到其中的意蕴。
毕旭玲[6]2008年在《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传说研究史》文中指出本文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20世纪前期现代传说研究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整理,并探索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现代知识者的学术关怀和人文关怀与传说学的学科建设之间有内在的紧密联系:知识者的学术关怀促生了传说研究,导致了传说学的发生。知识者的人文关怀则促使传说文体受到重视,并促进传说学向纵深发展。但现代知识者的学术关怀与人文关怀对传说学学科体系建设也有反面影响。20世纪前期的传说学虽然经过了建设,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本文呼吁尽快建立独立、系统的传说学学科体系。本文的主体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探讨现代传说概念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如何发生并进行初步演进的。传说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1910年。1913年周作人对其进行了初步界定。此后胡愈之、周作人及鲁迅进一步对其进行了界定。到1923年,中国现代传说概念已经比较成熟,现代传说学由此起步;第二章从多角度论述了20世纪前期的传说研究情况,分为文学角度、历史学角度、民俗学角度、社会学一民族学角度。并得出中国传说研究的发展规律:从书斋走向田野,从简单走向纵深;第叁章是对传说专题研究进行的讨论,介绍了以孟姜女传说、祝英台传说和徐文长传说为代表的人物传说专题和地方传说专题的研究情况。并探讨了当时的自由主义社会思潮与传说专题研究发生发展的关系;第四章是以《歌谣》周刊和《民俗》周刊为例,论述了现代报刊的发展对传说研究的促发作用。随着现代报刊的发展,传说研究从单个学者的单一研究成为众多学者的集体研究;第五章是对海外学者中国传说研究情况的论述,分别从欧美学者的研究情况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情况两个角度展开,并穿插论述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中国现代传说研究从诞生开始就被纳入到世界学术体系范围内了;第六章是全文的结论部分,将20世纪前期的中国现代知识者与传说学学科建构联系起来,分析传说研究如何在现代知识者的学术关怀和人文关怀中发生发展,及知识者对传说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田桂丞[7]2016年在《中国神话学百年神话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神话学自1903年起步以来,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发展繁荣,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涌现出一大批驰名中外的神话学家。对中国神话学百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总结和回顾是很有必要的。神话观是神话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命题。神话观是研究者对神话的定义、神话的范畴、神话的起源、神话的分类和神话的功能的认识,集中反映着神话学家的神话思维,是神话学思想的体现、研究成果的结晶。对神话观的发展进行透彻地研究和回顾是神话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神话学界涉及神话观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且不够系统、不够全面,更缺少一部完整的以神话观为主线的研究作品,使得此研究更具有学术意义。本文的主体分为文化人类学神话观、历史学神话观、文学神话观、民俗学神话观、考古学神话观和结语六个部分。文化人类学神话观部分总结了茅盾、谢六逸、林惠祥和叶舒宪的神话观,梳理了四人神话观的联系及传承,总结了文化人类学神话观的总体发展脉络。历史学神话观部分总结了顾颉刚、杨宽、童书业的神话观,重点关注了疑古辨伪思想对神话研究的影响,以及杨、童二人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神话观的发展。文学神话观部分总结了鲁迅、袁珂、潜明兹的神话观,阐述了叁人神话观中神话与文学的关系、神话作为文学的功能性作用等方面。民俗学神话观部分总结了钟敬文、孙作云、刘锡诚、陶思炎的神话观,着重关注了中国民俗学神话研究的诞生与发展,阐释了民俗学发展对神话学的促进作用。考古学神话观部分总结了徐旭生、丁山、张光直的神话观,重点研究了考古学神话观对历史学神话观的论战,点明了徐、丁二人对疑古辨伪思维的批评与改进,廓清了考古学神话观与历史学神话观的界限。结语部分总结全文,认为中国神话学百年神话观的发展历程主要存在文化人类学神话观的一脉相承、历史学与考古学神话观的论争、民俗学神话观的起兴叁个主要的特点,肯定了中国神话学发展历程中的进步和创新。
胡红梅[8]2010年在《浅论民俗风情在小说中的审美价值》文中研究说明民俗风情在小说中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更不是以"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而是小说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部分,在小说题材的构成、氛围的营造、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意蕴的开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
赵倩[9]2013年在《文艺民俗学视野下陕甘地区当代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俗扎根于民间,来源于民间,其含有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与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自古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常涉及民俗生活,从文艺民俗学角度入手对文学进行研究,与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实际是相符的。20世纪末以来,当代文坛上刮起一阵民俗之风,作家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民俗世界。民俗文化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它不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极大的拓展了文学创作主体的想象力,民俗文化对重构中国当代文学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陕甘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人们特有的生活方式使得民俗成为其创作中的重点描写对象之一,陕甘地区的当代文学不仅为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民俗画面而且引发了读者对人文精神的深入思考。本文在文艺民俗学视野下,从陕甘地区当代作家的主要作品入手,试图深入探讨陕甘地区当代文学与民俗之间的密切关系。首先,绪论对民俗的概念、分类以及文艺民俗学、从文艺民俗学角度入手对作家作品的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其次,第一章主要陈述在文艺民俗学视野下的陕甘地区文学中的民俗性,分别从古代、现代、当代叁个方面进行论述陕甘地区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性。第叁,主要是说民文艺民俗学视野下陕甘地区当代文学中涉及到的陕甘地区的主要民俗:比如婚丧习俗、信仰民俗、宗族民俗以及饮食民俗等。但本论文以突出重点民俗为原则,不求面面俱到的阐释其作品中所涉及到的全部风俗习惯或者民俗事象。第四,主要从文艺民俗学视野入手解读陕甘地区当代文学中民俗的审美价值,分别从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强化文学民族特征叁方面来叙述。最后,主要是对陕甘地区当代文学中民俗化追求的反思主要分为积极影响和局限性两个方面。
彭栓红[10]2012年在《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研究》文中指出元朝是我国第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幅员广阔,民族融合,文化多元,时代特色鲜明。元代也是我国民俗文化的重要发展、形成期和转型期。元杂剧是戏剧发展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王国维更称元杂剧为“真戏曲”。民俗文化对元杂剧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元杂剧中也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各族民俗文化,元杂剧演出活动本身也构成了元代一道亮丽的民俗风景线。从民俗的视野研究元杂剧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研究者多重视对元杂剧中的民俗事象的研究,本选题从广义的民俗文化角度把元杂剧中的民间文学也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查漏补缺,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展现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并运用戏剧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文艺学等理论,从文学、戏曲、民族等角度予以整体观照元杂剧。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异彩纷呈,大多是元代前就已存在的民俗,尤以唐宋民俗居多,这应该与元杂剧故事时代多以唐宋为时代背景和民俗的传承性有关。元代民俗在继承前代民俗文化的基础上,也有新发展。本文通过管窥口头文学和信仰民俗的历史变迁,揭示了民俗变迁对元杂剧创作的影响。元杂剧承载着女真、蒙古、回回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中都显得独树一帜。这些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有表现民族融合的,也有折射民族冲突的,其背后潜隐着民族心灵的秘密。元代城乡都有元杂剧演出活动。从演出的角度讲,元杂剧是元代“当代”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杂剧文本对元杂剧演剧行业习俗、化妆、脚色、砌末与戏剧表演的相关记录,不仅让今人对元杂剧演出习俗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可以看到元杂剧部分演出习俗是明清戏曲演出模式的先导。元杂剧中的各族民俗事象具有趋同性特点,这种趋同性与剧中人所处的民俗文化圈有关。蒙古、回回、女真等少数民族民俗表现了北方狩猎游牧文化的共性特点,而中原汉族民俗具有农耕礼乐文化的特点。另外长期的民族融合,也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也具有相似性。元杂剧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民俗,往往是各个民族趋同的民俗事象,这类民俗文化易于被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观众群所接受。在此基础上,进而探讨民俗、民族、国家认同与元杂剧的互动关系。元杂剧承载了丰富的民俗文化信息,这些民俗文化直接影响了元杂剧的情理表达,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剧情结构安排以及曲文、科介、宾白、曲牌也都起着重要作用。元杂剧顺应了俗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体现了大元一统的时代性,或隐或显地传达了底层民众话语,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民间性。总之,民俗文化是孕育元杂剧的文化生态之一,元杂剧也深刻地打上了民俗文化的烙印,折射出中下层民众的审美心理和各民族隐秘的民族心理。
参考文献:
[1]. 论民俗文化与鲁迅小说创作[D]. 薛文礼. 天津师范大学. 2004
[2]. 鲁迅小说的民俗意象研究[D]. 薛淑敏.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1
[3]. 民俗学视阈下的台静农小说创作研究[D]. 李带娣. 东华理工大学. 2018
[4]. 民俗描写: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交汇[D]. 王辉. 温州大学. 2016
[5]. 民俗文化与作家作品关系——浅论民俗文化对鲁迅的影响[J]. 张昕. 学理论. 2009
[6]. 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传说研究史[D]. 毕旭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7]. 中国神话学百年神话观研究[D]. 田桂丞. 淮北师范大学. 2016
[8]. 浅论民俗风情在小说中的审美价值[J]. 胡红梅. 文学教育(中). 2010
[9]. 文艺民俗学视野下陕甘地区当代文学研究[D]. 赵倩. 西北师范大学. 2013
[10]. 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研究[D]. 彭栓红. 山西师范大学. 2012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民俗论文; 神话论文; 鲁迅论文; 小说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民俗学论文; 元杂剧论文; 台静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