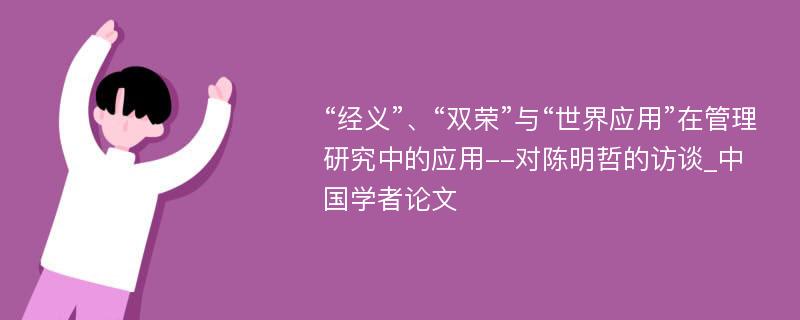
管理学研究的“精一”、“双融”和“经世致用”:对陈明哲的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世致用论文,管理学论文,双融论文,陈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学术思路的跨越与回归 吕力(简称吕):您所提出的动态竞争与文化双融理论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上述理论是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的? 陈明哲(简称陈):我所有的研究可以总结为4个字:跨越、回归。意思是我走到西方去,然后又走回自己老祖宗的东西。最近一期动态竞争国际论坛的主题,我就用了“跨越与同归”,内容包括动态竞争、文化双融,到夏学行践。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说,学问不能算是学问,除非你把它做出来,所以,恐怕我跟大部分中国学者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之根本就在这里:我是两只脚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回到“行”的东西,其实这是中西方学者对于学术很不一样的领悟。你可能听过ANDY,当年我在做管理学会主席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世的学者》,我对ANDY说“人世”这两字是多余的,ANDY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参考文献,我说:我没有办法给你,中国老祖宗已经讲了几千年了,所有的学术都要入世,所以中国的学术和西方所谓象牙塔式的学术是完全不一样的。 吕:您说的“入世”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思吧。 陈: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包括教学与研究的结合、服务奉献等。现在西方学术界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在学术中把“人”拿掉了。尤其是西方大学的考评机制有很大的问题,中国现在慢慢也走上这条路。在西方这种考评制度之下,一个学者只能写文章,而且是非常破碎的一些文章,跟我们传统“经世致用”完全不同,所以我在中国跟企业家交流,他们就说中国目前的管理学研究根本落不了地,而且很多商学院的教授(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他们觉得越来越没有信心,所做的研究都是支离破碎的,这是必然发生的。坦白地讲,如果我们不做一些调整,将来情形还会更严重。台湾地区一样如此。美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体会。在我看来,大学就是“学大”,学做大人之学,西方学术界走的路线其实是我们传统讲的“小学”,非常破碎化。 吕:能具体谈一谈,您的学术思路和西方主流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刚才我讲到,西方主流理论是从象牙塔中出来的,我的理论则来自实践。动态竞争理论的起源,最早只是一个现象:当时西方战略研究的环境,整个学术界是以波特和经济学家这些人为主,而我所观察到的竞争跟他们观察到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就从那里一点一滴地开始。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球员,我年轻的时候一场球最多得44分。所以竞争这个概念,在我18岁之前,一些基本观念就已经形成了。我提出的“动态竞争”和“文化双融”。从一开始就是一件事情,我不把它当做两件事情:一方面是精一,另一方面是双融。一辈子做一件事情,精一就是这个意思。“精一”来自于《尚书》中舜传给禹的16字心法,比佛家心法、心经还早了一千年,原来是16个字,叫做“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16字心经就是说道德心越来越微弱,人心越来越浮躁,这个时候只有用精一的方法。“允”就是真诚,执守中道,这对于当前的管理学术界有很重要的意义。 文化双融其实就是中庸的现代版本,“庸”就是“用”,中庸就是用中。我把这个概念用西方能够理解的说法讲出来,就像是左右手同时开弓。文化双融就是突出“用”。它就是在两个看似矛盾的对立面里,找到好的东西,把不好的东西扔掉。我们碰到的对立现象可能很多,例如,对于某一市场,进入与不进入;对于某一投资项目,投与不投。我上课时经常会挑战那些企业家学生,我问他们:你如果能够活到120岁,整个战略思维会不会调整?然后我又问,如果只有一天呢?你只有一天,怎么办?你要做什么事情?事物都有一个平衡点,找到这个平衡点就是“用中”。换言之,我们需要清楚事物的两端,以及两端之间无数的战略选项,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最大的一个智慧,也就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发明。然而,怎样才能“用中”,这可能需要一个“时”的概念。 吕:“时”意味着环境,周易非常强调“时”。 陈:时间一变,整个战略和思维也要跟着改变。你说得很对,其实像论语里面“时”的出现不太多,但是易经就很多。易经的“易”,第一层意思,就是变易,就是动态。“易”的第二层意思是简易,即你怎样把事情做简单,所以我现在用4个字来讲战略:一二三九。一就是精一;二就是双融;三就是三环链:文化、战略、执行融合在一起;九就是几九归一,生生不息。易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不易,即寻求永恒不变的原则。不管是怎样的战略思维,变易、简易和不易都是一样的。 2 中国式管理及其普适性 吕:管理实践中是否存在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管理是否具有普适性? 陈:这取决于你怎么样定义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管理是指中国的样本,还是中国人做的研究,还是中国的理论,还是中国的实践?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是把中国当做一个思维,当做一个文化,而且我认为它们是普适的。从钱穆的观点来看,学术本来就没有国界。国学的产生完全是五四时受到了西学的大军压阵,所以用国学去抵抗。这样就把中国的学问讲小了,中国的学问有很强的普适性。 然而,中国的学问和观念现在还是非主流。由此,我觉得,包括动态竞争理论,这些中国式思维怎么样去对抗一个主流的、非常强势的学说,以及中国管理和中国管理学者要怎么样把中国的观念介绍到国外去。其实有很深的战略意义。我当初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进行研究的。 吕:中国的观念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有扩散的趋势,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陈:是的,但是坦白地说,我觉得扩散的力道还不够: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对中国自己的了解也不够。我自己很幸运也很幸福,我曾经任教的3个学校,不论是弗吉尼亚、沃顿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其实都是美国传统的核心地区。我现在住在弗吉尼亚,当年美国文明就是从这里开始,一个是南北战争、一个是独立战争,独立战争时英国人的首府就在弗吉尼亚。由此,我就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西方最核心的一些传统。我在哥大时,和企业家交流的时间也很多,这使我了解了很多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我的成长背景跟大部分中国学者可能不太一样:一方面多了一份中国传统的元素;另一方面就是实践,包括美国人的实践。 3 学者与研究 吕:中国人的思维有时候体现为一个很宏大的框架,你要让国外的学者来接受,必须把它变成所谓“中层理论”。就像动态竞争理论,它既有宏观的思维,又有很强的操作性,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可能在“宏观思维与操作性的结合”方面有很大的难度。 陈:确实有难度,但是这取决于:有多少学者愿意一辈子只做一个研究?就我自身而言,到现在为止,我的研究问题仍然没有变。 吕: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竞争”。 陈:对,到现在我还在问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不会问、不敢问的问题我都问了,比方说:到底竞争是客观的事实,还是主观的认知?到底竞争跟合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的机制是什么?其实中国传统是先讲做人,才讲做事,或者是做学问。据此,从我们自己的传统来看,就要问:有多少中国的学者愿意一辈子就问一个问题,把这个问题问到极致。你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核心,很多人问了问题,但是没有问到核心,“学问”二字你拆开来看就是学会怎么问问题,其实就是核心。我可能是误打误撞,因为我自己从小是一个球员,运动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竞争?这个问题绝对是核心,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就是,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再过两百年也依然存在。可见,竞争理论的爆发力会很强,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知道动态竞争以及它的源头在中国的时候,大家会更有兴趣。除此之外,动态竞争理论还有很强的行践性。 我回到你在邮件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像“关系”以及中国的其他观念应该怎么样发展为现代理论?在我看来,不能走西方单一的道路,而是要多面向。你大概也注意到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跟西方不太一样,西方是从本科到MBA到EMBA。然而,至少从过去十几年的时间,整个中国管理教育的重点是在EMBA,EMBA的学员或者中国的企业家有很强的行践经验,但是他们又必须要找理论的基础,至少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管理经验正确与否;然后,还有报社与媒体,最近,你大概也注意到阿里巴巴跟上海报业集团合作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它们很大的一个合作项目是把所有的东西变成大数据。我的意思是,学术是一条路,实践是一条路,媒体是一条路,必须要多元的一种努力。 这种多元的努力实际上就是儒家的思想,我这里说的儒家是传统儒家,不是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原始儒家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所以有不同的道,其实就是多面向的。理论不能从纯学术界出来,理论来自于现象。我们观察问题的路径有很多,但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管理学这么多研究成果接不了地气?因为第一,研究成果是从西方过来的;第二,学者又是在学术象牙塔里面做研究。其实做研究有很多种选择,所以必须用更包容的一种心态,中国管理的发展是多样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份心力。 刚才提到“道必行而不相悖”,就我自己而言,除了从事基础研究之外,我还建立了全球华人管理学者社群、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以及与复旦合作的夏商全球领袖项目。目前,我在中美两国大概各有三四千人的企业家朋友,这对我的研究与实践都大有助益。 4 夏学与中国传统 吕:夏学这个概念是您提出来的吗? 陈:最早是毓鋆老师提出来的。 吕:夏学的主要典籍是《尚书》还是《周易》? 陈:夏学是所有中国人的学问。 吕:中国的学问就叫夏学? 陈:对,“中者天下之大本,夏者中国之人”,所以中国人的学问就叫夏学。中国人实际上是以文化来界定中国的。 吕:华夏夷狄。 陈:对,孔子是集夏学之大成者,孔子拨乱反正就是要返夏学之正。夏学是没有经过世袭、私天下污染的学问,所以夏学就是元儒,就是原始儒学,就是没有经过污染的儒学,所以毓老师的书院叫奉元书院。中国的学问到了舜有一大变,因为从禹开始就是家天下了,所以夏学要回归人性,追本溯源。 吕:但是孔子的时代已经是家天下了。 陈:孔子的思想有3个阶段,他最早的时候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他开始变了,到了第三个阶段,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其实就含有拨乱反正的意思,所以孔子才有春秋三世的观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民国时,孙中山讲军政、训政到宪政,也是“三世”的观念。“吾其为东周乎”意思还是要回到尧舜,“因而不失其心”。中国文化确实有趣,比如,我自己就经常用拆字的方法来解释每个字的意思。 吕:很多研究中国古文字的学者,也是用这种方法的。 陈: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比如,说竞争的“竞”,实际上繁体是两个“竞”,就是两个人放在一起才会竞争,夏学的6句话“学行合一、自觉觉人、有教无类、惟精惟一、执两用中、生生不息”,是我每天行为的准则。人家问孔子,谁是你最好的学生。孔子说是颜回,“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中国的学问一开始就与西方有着不一样的切入点。现在可能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要不要回到这个传统,还是继续走西方这条路,这其实是我们每个学者面临的一个选择。 5 研究方法和学术创业 吕:把西方和东方结合起来,把宏大的思维方式和中层理论结合起来,这应该是最好的研究方法吧。 陈:以我熟悉的战略研究为例,现在大家都在谈战略转型,这是中国最热门的。事实上,企业可以做大,可以做强,可以做久,可以做精,可以做专,也有可能做小。然而,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又回到夏学,我们要同时看到远近、大小,不能只听一家的观点,再进而若能把握人性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例如,我最喜欢用的西方的林肯电气以及中国的海尔的案例,这两个例子都体现了易经中说到的一个“群龙无首”的形象。群龙无首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是CEO,如果每一个人都是CEO,组织就是公平的。人人都一样,这个也就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内涵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信息是公开、开放的,所以交易成本会降到最低”,这也说明中西是互通的。群龙无首的观念用英文讲就是“leaderless leadership”即没有领导人的领导。 吕:从这个方向看下去又可能会找到一大片新的研究领域。我最近对“变通”这个中国式概念很感兴趣,我希望把它结合到管理的研究中,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陈:对,从中两结合的视角来看,机会是无穷的。你谈到的“变通”,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经”和“权”。经,达经;权,权变。两者结合起来最难得。能有什么办法实现执经达权?我认为还是要回到“一”和“无限大”。用怎样的办法一方面抓紧核心,但同时能把这个核心像大海里的浪一样越滚越大?所以最终要回到这个“一”,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一个问题一直问下去,然后就和剥洋葱一样一直问到最核心。 吕:问题要问得准、问到核心,然后还要放得开。问题太小不行,但问题问得太大往往不容易上手。 陈:这很重要。选择问题时你一定要务实,务实的意思就是说刚开始第一步走得很小,然后一块一块地堆上去。我们说不能眼高手低,其实讲的也是这个问题。另外,实与虚也是双融。我记得毓老师上课最常讲的一段话,他说,中国最成功的虚招就是孔明的空城计,但是没有实的东西的话,江山还是别人的,学术界也一样。我完全接受西方的训练,我也百分之百相信,西方这套方法有贡献,但是局限性也很大,所以要怎么样做到东西双融,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率性之渭道”,顺应自己的个性去做研究。我的个性是不喜欢跟人家冲突,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用动态竞争这个词,刻意避免冲撞当时的主流思想,否则可能早就被人家一棒子打死了。以此为鉴,我建议你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可以避实击虚。 吕:去年您在华中科技大学讲学时谈到学术创业,我理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学术研究也要有战略? 陈:一定要有战略。现在学术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为发表文章而发表文章,这个机制创造了很多破碎的知识。当然,这也不是完全不好,但是坦白讲,我觉得对学者自身而言是一种浪费。 吕:研究者可能觉得总是做这种破碎的研究没什么太大的意思,没有系统性。 陈:我虽然研究管理,但我对组织其实抱有很大的问号,所以我才说企业也可以做小,而不只是做大,因为我百分之百相信文化会决定一个企业的发展。企业如果太大,它的文化可能没有办法跟得上去,所以我宁可先把企业做好:因为组织最终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所以我秉持非常传统的思维,就是“君子群而不党”。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个性,或者是我本身的体会。由此,我的动态竞争理论也好,文化双融也好,其实是用不同形式来表现“夏学奥质,寻拯世真文”这个源头的。 我们以前都在吵,是不是要“中学为体、两学为用”,为此一直吵了两百年。在这个问题上,我认可熊十力先生的说法,他说一定要体用合一。我整个的思考,无论从文化还是理念上,都是系统性的。总之,西方有西方的长处,中国有中国的长处,我现在就是用中国理念和西方技术来双融。 6 夏学西渐 吕: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传统可以借鉴,但是这些传统一定要与西方、与现代“相合”,不“合”的话就变成务虚了,同时西方也难以理解。这就是文化双融的涵义吧。 陈:比方说,我如果把中庸的观念直接介绍到西方,完全没有办法,但是使用文化双融思维效果就不一样。2015年1月份,在AMR上有一篇文章讨论如何将文化双融应用在不同的层面。再比方说“精一”,我曾经在华盛顿邮报写的一篇文章介绍精一的观念,我说精一就是“power of one”,一的力量,大家就懂了,懂了之后他们还说这是目前为止最短的一篇讲战略的文章,我用的就是很简单的观念。回到动态竞争,动态竞争里面的中国源,我也给企业界讲,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观念。比方说“破釜沉舟”,我1992年将这个概念解释为“不可逆转性(irreversibility)”;“声东击两”,我解释为“资源转置( resource diversion)”;还有一个“知己知彼”,我称之为“怎么样换位思考”。那之后呢,我也写案例,通常学者不太写案例,我还是回到行践。 吕:为什么用文化双融说给西方人听的时候,他们能接受,用中庸这个概念说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能接受? 陈:因为西方有一个观念叫做“左右开弓( ambidexterity)”,这是西方的名词,我所想要表达的观念,就是怎么样把感觉上是彼此对立的东西整合在一起,然后保留两个的长处,避开两个的短处,这个观点西方觉得没有什么难懂的,但它其实是中国的观念。 吕:2011年AMR上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悖论管理的,它和中庸、文化双融有没有什么关系? 陈:我自己本身每天都在用中庸和文化双融。比方说,我之前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和沃顿都是百分之百研究型的学校,现在的弗吉尼亚大学则是百分之百教学型的学校,这样的学校认为做研究的人没有办法教书,他们真的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自己必须要在研究与教学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人的思维其实是,如何用一个概念来贯穿所有的东西。这个也许是我们中国人或我们的老祖宗给世界最大的贡献,因为现在我们的研究是非常分离和破碎的,如果再不做一些调整,也许还会越来越破碎。 吕:您刚才讲到的例子大部分都集中于战略管理领域,您认为像“关系”这样一些概念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像动态竞争如此体用合一的理论? 陈:绝对有可能,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人愿意集中精力来做。还是回到人,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学者把“关系”重新再梳理一遍,梳理完以后可能要突破两点:①在东西方之间做一个直接的联合,要不然大家觉得这只是中国人的观念,这很重要;②我觉得恐怕更重要的是,要把关系这个概念从理论直接拉到实务,必须要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其实我曾经也试着做过类似的工作,所谓的可操作性实际上是“怎样用不同的方式来‘管理’这个所谓的关系”。总之,要将它变成一个类似动态竞争的可以操作的观念,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类似的这种中国名词还有很多,不只是关系,当然我也觉得只讲“关系”其实是把中国式思维讲小了。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喜怒哀乐还没有发之前就要“中”,必须要达到那个要点、重点或者是关键点,这就是合。以精一的理念来看,我觉得做任何事都要发心,要用心把那个东西做到极致,这样才能成功。我自己本身在乡下长大,一招半式闯天下,就是把一点用到极致、变成绝招。 吕:互联网时代企业家也要这样做:用到极致。 陈:我上周刚给企业家上课讲互联网。马化腾他最近不是在强调互联网+吗?课后,同学要我点评马化腾讲的话,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互联网+是一个境界,“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家”,家庭的家,也就是大家的“家”,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家要怎么样用互联网的思维,把自己的格局提高。 林肯电气是美国的一家做焊接的优秀企业,好几年前哈佛的教授就问,到底林肯电气是走在时代的前列还是走在时代后面。类似的,中国老祖宗的这些东西是已经过时了,可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智慧却没有新旧,很多东西是越久越香,历久弥新,只是看你会不会用。事实上,夏学的很多内容就是互联网思维,只是我们当时没有“互联网思维”这个名词。夏学强调公平、直达人心;就是人心人性;还有透明化,这就是互联网思维。 吕:要真正做到“文化双融”的难度也很大。 陈:对。有两个大的问题我现在都不敢碰:一个是竞争的真旨。“竞争”这个名词中文翻译得不好,把它的意义给抽掉了。中国人说仁者无敌,讲不争、止争,而竞争这个名词最早是日本人翻译的,我觉得那个“争”字不对,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去深思,因为这个问题太大。第二个问题是管理的“管”字,中国人其实是反求诸己,所以才会有严师出高徒。把严师出高徒理解为“严格的老师出高明的徒弟”事实上是不对的,严师出高徒是指“严身之师出高徒”,或者说对自己要求越高,徒弟的水平也越高,这跟企业界也是相通的,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文化双融的发展尚需一段时间,因为在操作性的层面上还不是很完善。 吕:作为一个学者,又要有理论又要有实践,要小又要大,这一点很难。 陈:对。我举孔明的例子,“孔明”这两个字其实就是“又小又要大”,所以才会有远近大小若一。有很多学者是朝“小”的目标做研究,其实应该提升更大,但“大”的理论没有办法落地的话,那也不是一个好的理论。 7 展望 吕:您对于中国大陆管理学界的希望是什么? 陈:我百分之百相信,“人人都可以为尧舜”,但最终能不能成为尧舜,其实还是看个人,“文化双融”这条路不好走,也可能会走得很长,至少我觉得不是不可能,文化双融绝对有可能,只是时问的问题。甚至我想:将来长期的学术走向,中文会不会变成一个主流?我自己说,我对中国的东西有时候是一种“盲目信任”,但“盲信”比“不信”要好 现在大家谈的“中国式管理”实际上是把中国思维谈“小”了。目前,任何中国学者面临的挑战,或者是任何人面临的挑战,第一个是怎么样“知古”,也就是对传统的了解;第二个就是中西的双融,第三个,如果有的话,就是教学与研究的双融、学术与实务的双融。所有这些如果能够融合的话,那么管理学是最好“玩”的一个专业。我是用“玩”的方式来做研究,玩的话就不会让自己有压力,就会感到是为兴趣在做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