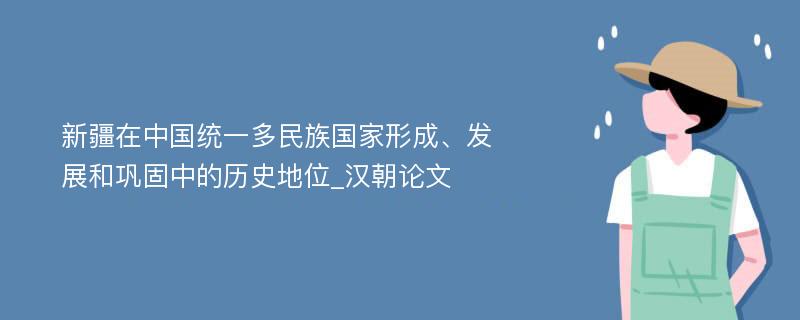
新疆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中国论文,过程中论文,地位论文,多民族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3)10-0001-07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她是以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为基础,先由氏族、部族,局部的或者说某一地区的统一,发展为同一经济区域的统一,进而实现了不同族群、不同经济区域的大统一。其间经历了大约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农业区的统一和游牧区的统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公元前209年匈奴单于冒顿统一蒙古草原,是中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自此,中国开始了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大统一。汉朝、唐朝为实现中国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大统一,取得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元朝终于实现了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大统一,而清朝最后完成和巩固了这个大统一。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和巩固。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农业区和牧业区这两个统一最终又形成混同为一个大统一的过程中,新疆始终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
一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约在距今3000年前后,新疆就以天山为界基本上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即南疆农业区和北疆游牧区。公元前2世纪末,在汉朝开屯垦、置河西四郡之后,中原农业区通过河西走廊便与南疆农业区联系起来了。北疆游牧区则早已与蒙古草原结成一片,成为游牧民族驰骋的地方。当时,西汉政府在与匈奴在北方的争夺中已经取得了主动权。于是,我国历史上农业区与游牧区之间的矛盾在新疆也就集中的反映出来了。
农业区与牧业区的矛盾,是由于二者之间经济结构不同而又相互需要造成的。一般说来,农业区与牧业区都有自己特有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对方所没有或者是缺少的,也是对方在生产、生活上所迫切需要的。农业区需要牧业区的各种牲畜,如马、牛、羊、驴、骆驼等,以及皮革、畜毛和药材等等。牧业区则需要农业区的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如粮食、丝织品、麻织品、金属工具和用具、酒类等等。在一般情况下,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经济交流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中国历史上各个经济区之间开展的“开关”、“互市”就是这种交流的主要形式。但是,当和平的交流方式得不到满足时,便爆发了掠夺性的战争。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原农业区和各牧业区,特别是和北方蒙古草原上的游牧区经常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当然,在古代,战争也是交往的一种方式,暴力掠夺也可以视为互市的继续和补充。其结果,农业区和牧业区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强,并互相促进,进而为农业区和牧业区政治上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3世纪末,中国在实现农业区和牧业区的两个统一之后,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首先表现为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斗争。
匈奴是历史上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民族,兴起于战国,强盛于秦末汉初。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在大漠南北建立匈奴游牧政权。当时,他不仅经常袭扰汉朝北部边境,而且于公元前176年前后驱逐了月氏,控制了西域。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后,为了消除匈奴对北部边境地区的威胁,一面派军队抵御匈奴,一面争取曾经或正在受匈奴政权统治和压迫的民族和地区的支持,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立起了汉朝与西域的政治联系。
公元前121年,驻牧于河西地区的匈奴浑邪王归降汉朝,西汉政府于其地先后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移民屯垦。河西四郡的设置及其农业开发,隔断了匈奴与西羌两个游牧民族和蒙古草原与青藏高原两个游牧区之间的联系,为西域归入汉朝版图创造了条件。公元前107年,游牧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派遣使者朝汉,献良马千匹,求与汉朝和亲。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昆莫,西汉政府与乌孙结成了反对匈奴政权的政治联盟。
公元前101年,西汉政府设立“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在渠犁、轮台一带屯田。此后,汉朝与匈奴在车师(今吐鲁番地区)展开激烈争夺,五进五出,史称“五争车师”。公元前72年,西汉军队与乌孙联合,东西夹击,重创匈奴。翌年冬天,西域各族人民再次打败匈奴,将匈奴势力赶出了天山以南地区。公元前68年,西汉政府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今罗布泊地区西北),以西南道,基本上控制了南疆地区。公元前60年,匈奴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单于位而发生激烈斗争,管理匈奴西部地区的日逐王先贤掸率众归汉。于是,汉宣帝任命郑吉为都护,设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域(今轮台县策大雅),辖西域诸国。自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注:《汉书·郑吉传》。)。这样,新疆就正式列入了汉朝的版图,与其它一些边疆地区相比较早地成为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汉朝统一西域,实现了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势力。此后不久,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分裂,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局面。经过不断火拼,最后剩下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归汉,并娶汉朝宫女王嫱(即王昭君)为妻,在汉朝的帮助下不断发展壮大。郅支单于对汉朝阳奉阴违,杀汉使,攻乌孙,威胁康居、大宛。结果,被西域副校尉陈汤、都护甘延寿消灭。于是,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缔结盟约,表示“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并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与牧业区的第一次大统一。两大经济区域之间,“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注:《汉书·匈奴传》。)
上述情况说明,西域归入汉朝的版图,不仅使新疆成为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为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第一次大统一创造了条件。
二
汉武帝“断匈奴右臂”战略的实现,使西域归入汉朝的版图,并为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第一次大统一创造了条件,突出了新疆在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受到了中国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的重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后,都把统一西域作为全国统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期间也有过争论,有过反复,但这一战略思想始终没有变。
历史上,关于要不要统一西域的问题有过多次争论,其中有三次影响最大:一次发生在东汉中期,一次发生在唐朝初朝,一次就是近代著名的“海、塞防之争”。
东汉时期,东汉政府曾经三绝三通西域。2世纪初,由于北匈奴的袭扰和羌族人民的起义,东汉政府一度放弃对西域的管理。结果,不仅导致北匈奴残余势力卷土重来,“谴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残酷地剥削和压迫西域各族人民,而且挟持西域诸国入寇河西。敦煌太守上表告急,邓太后召集群臣商讨对策。议者多主张关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免的劳师远征,糜费财物。尚书陈忠则认为,若不收复西域,听任北匈奴猖獗,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发展势力,再与南羌联合起来,与汉朝为敌,“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注:《后汉书·西域传》。)班超之子班勇则明确指出,自汉武帝以来,由于“开通西域,离其党与”,“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才使“匈奴远遁,边境得安”。(注:《后汉书·班勇传》。)因此,他也主张尽快收复西域。他们的意见促使东汉政府采取措施,很快恢复了对西域的统治。在这里,陈忠、班勇阐明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即汉武帝“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战略的成功,才使汉朝得以长治久安。反之,如果不守西域,河西则危,河西危机,则陇右不固,陇右不固,必将震动京师长安。所以,守长安,必须守河西,守河西必须镇西域。以后的历代王朝都以此为指导思想,从国家统一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认识和处理新疆问题。
唐朝初期,围绕着要不要平定高昌麴氏王国以及平定以后如何治理该地区的问题,唐朝政府内部展开过一场激烈争论。
高昌即今吐鲁番地区,两汉时期,这里曾是戊己校尉的驻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仍,不少汉人迁居河西,又从河西辗转到新疆,和汉代屯田士卒的后裔汇集在高昌地区,并使该地区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汉人在新疆聚居比较集中的地区。公元327年,前凉政权在这里设置高昌郡,第一次把郡县制推行到了新疆地区。从460年开始,在高昌地区先后建立起阚氏、张氏、马氏、麴氏等以汉人为主的地方政权。特别是高昌麴氏王国存在长达140余年之久,到唐朝初期已传九世。
最初,高昌与唐朝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公元630年,高昌王麴文泰至长安朝见,唐太宗赏赐甚厚,还允许其母宇文氏改姓李,更封常乐公主。但是,高昌与唐朝的良好关系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随末,由于战乱,自玉门经白龙堆至焉耆的“大碛路”闭塞。632年,焉耆王遣使唐朝,请求重开大碛路,以便行旅。但大碛路一开,很多商旅就不必途经高昌了,这就使高昌麴氏王国失去了向商人课税的机会。所以,麴文泰对此极为反感,遂勾结西突厥攻焉耆,焚庐舍,掳掠商贾行人。唐太宗多次派人谴责,麴文泰不但不听,反而相讥说:“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室,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耶!”认为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了他。另外,隋末中原战乱,不少人逃入突厥。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后,有的人又逃往高昌。唐太宗下诏要求把这些人送回内地,麴文泰不但顶着不办,而且与西突厥联兵攻打伊吾。在这种情况下,不解决高昌问题,就不能安定西域。唐太宗决心征伐高昌,但却遭到了朝中许多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兵行万里,难以得志,绝域之地虽得之亦不能守。唐太宗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于639年底派遣兵部尚书侯君集带兵数万,帅师行事。唐朝军队兵临高昌田地城时,麴文泰“惶骇计无所出”(注:《新唐书·西域传》上。),发病而死,其子麴智盛被迫投降。
平定高昌以后,就如何管理该地区的问题,唐朝政府内部又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唐太宗主张于其地置州县,驻军屯垦。魏征、褚遂良等朝廷重臣却认为,“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尝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往交番,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毂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未见其可”(注:《册府元龟·外臣》。),所以建议册立麴氏后裔继续为王。唐太宗又没采纳他们的意见,以高昌为西州,下设交河、天山、柳中、蒲昌、高昌五县,并置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
高昌麴氏王国灭亡以后,西突厥中的反唐势力又挟持焉耆、龟兹与唐朝对立。唐朝又先后讨平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则自动归唐。唐朝在这些地方分别设置都督府。公元648年,唐朝政府将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安西都护府是当时唐朝在西域设置的最高军政管理机构。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唐太宗感慨地说:“顷命将西征,今已克捷,万里清泰,战士咸得回家,此朕为乐之时。”(注:《册府元龟·帝王》。)又说“四海宁一,帝王乐也。联今乐矣。”(注:《新唐书·西域传》上。)
唐太宗为什么坚持讨伐高昌,坚持统一西域?就是认识到了西域在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唐朝统一西域,也促进了农业区和牧业区两大经济区域的统一。唐朝统一西域以后,游牧于蒙古草原上的铁勒诸部酋长纷纷至长安晋见唐太宗。公元647年,唐朝在铁勒诸部牧地置翰海、金微等六都督府,隶燕然都护府管辖。翌年,游牧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结骨部落酋长自动归唐。唐朝于其地置坚昆都督府。
以后,游牧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强大起来了,与唐朝争夺西域。正是从全国统一和安全的整体战略出发,武则天力主恢复安西四镇,不断发展和巩固唐朝对西域的统治。故曾出任过西州刺史的元载说:“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之胫,朝廷可高枕矣。”(注:《旧唐书·元载传》。)
时至近代,就是否收复新疆问题,清朝政府内部又展开了一场大争论。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海、塞防之争。
1864年底,浩罕军官阿古柏乘各族人民举行反清起义之际,侵入南疆。至70年代初,他不仅统治了整个南疆地区,而且侵占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为了与英国争夺势力范围,1871年沙俄悍然出兵伊犁。这样,新疆实际上已被沙俄和阿古柏瓜分了。至此,清朝政府才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面对西北边疆危机,清朝政府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同时,开始调兵遣将,采取措施,以增强哈密、科布多等方面的兵力,以待时机成熟,西征新疆。可是,正当清朝政府关注西北问题之时,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873年悍然发动了侵略福建省台湾府的战争,东南沿海的防务问题同样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在东南沿海防务和西北边疆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究竟还要不要用兵新疆,收复失地?围绕着这个问题,清朝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874年12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借口海防筹饷困难,提出放弃新疆,把准备西征的费用移作东南海防之用。他认为,不收复新疆,“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他还认为,以往每年清朝政府花在新疆的银子达三百万两之多,如今为“徒收数千里之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何况阿古柏有英、俄等国的支持,新疆既便收复了,面对英、俄等国的侵略,也很难守卫。这就是所谓的“海防论”。在李鸿章的鼓动和影响下,山东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等都支持这种观点。甚至连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也认为,李鸿章“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注:《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16页。)。
但是,李鸿章的主张遭到了陕甘总督左宗棠、湖南巡抚王文韶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一)中国的国防是一个整体,海防与塞防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缺一不可。片面地强调海防而忽视塞防,“扶了东边倒了西边”,恐怕“西边又倒东边亦未能扶也”(注:《左文襄公书牍》卷15。)。因此,海防与塞防应当并重。(二)新疆是国家的西北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旦弃守,甘肃、陕西等地难以守卫,蒙古地区也会受到威胁,甚至京师也不得安宁。所以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注:《左文襄公奏稿》卷50。)也。(三)沙俄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略日益严重,加强塞防以抵御沙俄,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俄人得步进步,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虽欲闭关自守,其势不能。”(注:《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一卷。)这就是所谓的塞防论。左宗棠、王文韶的主张得到了朝廷内外多数人士的拥护,特别是军机大臣文祥也认为,新疆作为边疆屏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收复新疆,“借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因此,在清朝政府最高层讨论新疆问题时,他“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注:李云麟《西陲事略》卷上,“故相远谋”。),使清朝政府终于下决心,采纳左宗棠等人的主张,全力西征。
从1876年6月11日刘锦棠进抵吉木萨尔,至1878年1月清军收复和田,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清军就取得了彻底消灭阿古柏侵略势力的胜利,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所有地区。1881年,通过谈判,清朝政府收回了伊犁大部分地区,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新疆建省不仅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中国国家的统一,促进了新疆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而且是中国边疆地区制度的重大变革。以新疆建省为典范,台湾和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相继改设行省,进而推动了中国边疆地区的政权建设。所以,新疆建省被称为“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
通过历史上关于要不要统一西域问题的争论可以看出,主张弃守西域者,多以为新疆是一不毛之地,守之无用,徒增巨额费用,即所谓“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注:《汉书·公孙弘传》。)。显然,他们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问题的。主张统一西域论者,都从中国的统一和安全的整体战略高度出发,认识到了新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的战略地位。综观两千多年来历史的发展,统一论者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这是新疆不能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要原因。
三
新疆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被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了的真理。这里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
历史上,由于弃守西域或者新建王朝还没有来得及统一西域,而造成全国不稳定的事例有多次,其中重要的有两次。一次发生在唐朝中叶以后,一次则是清朝初期同准噶尔的斗争。
公元755年,中原地区爆发了“安史之乱”。为迅速平定叛乱,大批驻守安西、北庭、河西的唐朝军队,以及西域各地少数民族居民组成的军队调往内地,参加平叛,因而削弱了西域及河西地区的防卫力量。“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唐朝的统治虽然维持下来了,但已经大为削弱。藩镇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边疆各少数民族首领各自为政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吐蕃乘机占领了河西地区,截断了西域与内地的正常联系,“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注:《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直至781年,他们才遣使绕道蒙古草原,经回鹘境内到达长安,与唐朝中央政府取得了联系。790年,吐蕃攻陷北庭,808年占领安西。唐朝军队被迫放弃四镇,天山南北大部分地区遂为吐蕃所占据。
吐蕃占领河西与西域,对唐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安史之乱”后不久,吐蕃就一举出兵占领了陇右诸州,并于763年一度攻入长安。是后几十年,吐蕃军常入京畿,抄掠不已。812年,吐蕃寇泾州(今甘肃东部之泾川),“驱掠人畜而去”(注:《资治通鉴》卷239,元和七年。),被唐宪宗视为心腹大患。所幸的是,8世纪末9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地区的大食国“与吐蕃为劲敌,蕃军大半西御大食”(注:《旧唐书·大食传》。),回鹘人也与吐蕃争夺西域,并占领北庭,多少减轻了唐朝面临的压力。848年,张仪潮起事,推翻了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唐朝才解除了来自青藏高原的威胁。不过,这时的唐朝已经衰弱,开始走向灭亡了。
大家都知道,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自此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这首先是中国的两大经济区域,即农业区和牧业区走向统一的结果。中国的中央政府为了管理游牧区的游牧民族,其政治重心不能不向北迁移。在中国的政治重心北移的情况下,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了。所谓的“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就深刻地说明了其中的道理。蒙古人是首先西征,统一西域,征服中亚,然后才返回头来统一全国的。如果说在元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新疆的战略地位还不是十分突出的话,那么明朝的情况就多少说明一些问题了。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弱小的朝代。1406年,明朝政府设置哈密卫,直接管理的地方只是哈密、吐鲁番一带,对西域其它地方只是册封而已。即便是这样,明朝对西域的直接统治也没维持多久。所以有明一代,始终面临着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1449年,瓦剌贵族也先率军攻明,宦官王振挟明英宗率五十万人亲征。结果,明英宗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俘,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重大事件。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是作出过贡献的,今天的中国的版图基本是那时奠定的。清朝时期,新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了。
清朝初期,正当康熙皇帝集中力量统一江南各地时,噶尔丹于1671年夺取了准噶尔部的汗权,控制着今新疆北部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随后肆意扩张自己的势力,“戕害其兄弟,兼并四部,蚕食邻封,其势日张,其志日侈”。1779年,噶尔丹进军南疆,统有维吾尔地区。1690年,他又以追击喀尔喀为名,举兵攻入内蒙古乌珠穆沁地方,距北京仅七百里,对国家安全和统一造成了严重威胁。清朝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夫烈焰弗戢,必将燎原,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圉一日不靖”(注:《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首。)。于是,康熙皇帝决定率军亲征,首先在乌兰布通(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重创噶尔丹军队,清军也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噶尔丹又纠集力量,大举进攻喀尔喀。康熙皇帝再次亲征。清朝政府调集十万大军,三路出击,在昭莫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南之宗莫德),围歼了噶尔丹主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噶尔丹仓猝逃窜。翌年,康熙皇帝又亲临宁夏,指挥两路大军围剿噶尔丹。噶尔丹众叛亲离,势蹙而死。此后,占据新疆的准噶尔与清朝又打过几次大仗,双方互有胜负,出现了几十年的对峙局面。1755年,乾隆皇帝抓住准噶尔上层内乱,政局动荡,经济困窘,以及部分准噶尔上层归附清朝政府的有利时机,两路出兵,直取伊犁,一举平定了准噶尔政权。接着,清朝政府于1757、1759年又先后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和大小和卓叛乱,最终统一了新疆,彻底地解除了来自蒙古草原方面的威胁,从而保障了首都北京的安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上述事实说明,不管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在长安,还是在北京,新疆在维护中国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如前所述,即便是到了近代,也是如此。对新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和巩固过程中地位的深刻认识,是左宗棠主张出兵的主要原因。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两千多年来的事实说明,哪个朝代统一了西域,那个朝代的全国大局就比较稳定,反之就可能出现分裂。因此,我们必须从全国安全的战略全局出发,认识新疆稳定问题。两千多年来,新疆各族人民世代相继,建设、开发、保卫边疆,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新疆各族人民更应该发扬优秀的历史传统,为国家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标签:汉朝论文; 西域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地位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蒙古军队论文; 唐朝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绰罗斯·噶尔丹论文; 高昌论文; 唐太宗论文; 边疆论文; 东汉论文; 秦朝论文; 西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