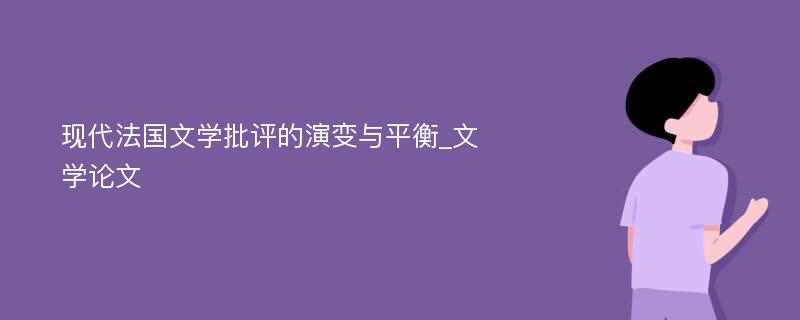
现代法国文学批评的流变与平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法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中,我将借用美国学界惯常的用法,将批评一词宽泛地定义为“有关文学的言论”。这种用法的存在(实为战后文学批评思想的新动向之一)本身就标志着经历了深刻动荡的文学批评,如今终于对自己在诸人文学科大合唱中的角色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而文学批评思想在现代历史中正是以这种认识的发生发展为主线的。
一、描述的兴起
只有将这种认识过程放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潮流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义。这个历史潮流起于18世纪末,以“规范”主义文学批评的式微为开端。在古典主义时期,文学批评遵奉着文学修辞所提出的种种要求,以之为准绳,并用“品味”的名义,指摘文学作品的瑕疵与败笔,评判它的优劣得失。因而,这种以前定规范为尺度的批评始终与对文学作品的结构分析紧密相联。而在浪漫主义的激荡下生成的现代文学批评思想,已不再以指摘作品的缺陷、衡量它的结构是否符合规范为目的,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作品在内容与内在结构上的独特个性。本文必须卓异无双方能称为杰作,这种要求说到底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较为宽泛而已。直到今天,这种新的规范仍然流行于世,无论是报刊上对于新书的评价,各种文学奖项的审定,还是在一如既往地以向学生解释杰作之奥妙为己任的各级学校当中。
尽管存在着这种对独特性的要求(或者不如说恰恰由于有这种要求),描述方法的胜利还是决定了现代文学批评的走向。在19、20世纪之交,文学批评向往达到历史科学的客观水准,将自己的研究分为两部分:历史描述,即对散见于历代的作品的总体作整合的研究;风格描述,即对浓缩于一部作品中的文学效果进行不失客观的个案研究。对于这两种研究方法,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都很得心应手,为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石。然而,描述方法这种追求客观的热情,在其起步之初就遇到了抵触。在《金钱续编》(1913)中,佩吉(Peguy)就以调侃的笔调评价了带着客观主义热情去讲授伟大作家所会带来的结果:朗松在高等师范学校的课程为法国戏剧描绘出一部渊博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一切都可以被“次要原因”(les causes secondes )所解释。佩吉如是评论道:“如果一位作家写出一部《依菲叶尼》,那是因为他是某人的叔父的侄孙,而这个某人曾写过一部《依菲叶尼》的草稿,而碰巧这部草稿又被我们的作家从他姐夫的故纸堆里发现了。”而在谈到高乃依时,次要原因却忽然失去了说服力,因为“谁都知道,那最好地理解了《熙德》的人,正是那一字一句紧贴《熙德》本文的人,那在本文的切磨与横扫之中体会《熙德》的人,特别是那不了解法国戏剧历史的人。”在佩吉看来,朗松的历史诠释无力阐发《熙德》之美,正说明一堆确凿而无用的事实完全无助于领会天才那不可言传的优雅。佩吉这种回响着浪漫主义与柏格森思想的议论,后来被一战后流行的审美主义文学批评(以下简称审美文评)所传承。然而,学界文评与审美文评的深刻对立并不妨碍它们并存于世。在某种意义上,对文学体裁作冷峻的历史考察也好,对杰作进行热情激越的主观观照也好,都是对以指摘文病为要务的传统文学批评的扬弃。20、30年代法国文评的历史虽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毋庸置疑的是,有关文学的各派言论当时大多稳定而繁荣地发展着。
我们研究文学作品,着眼点可以在个性,也可以在共性;可以作历史的考察,也可以不计历史延革而作共时性的分析。这样,我们就不妨按这四个倾向把文学批评分为四类:研究共时特性的批评(风格学和本文解读),研究历史特性的文学批评(语史学和文学史),研究共时共性的文学批评(创作论及文学理论)和研究历史共性的文学批评(将文学放入文化的哲学历史框架下考察)。在1920至1940年之间,这四种研究兴趣都有体现。语文史和文学史在大学界内部极为繁荣。而在“审美文评”的阵营中,阿尔伯·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将历史关注融贯于对文学艺术特性的探索之中,而夏尔·杜波(Charles du Bos)则以其对作品细节的细致分析为二战后新批评的本文解读开了先河。同时, 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的思考与雅克·马里坦(JacquesMaritain)的哲学随笔都指向共时性的文学创作论。最后,探讨文学与思想史之间联系的任务则由马赛尔·雷蒙(Marcel Raymond)与阿尔伯·贝甘(Albert Béguin)所承担。除了这些较为专业的著作,还有面向公众的随笔杂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法兰西文化向来对美文派情有独钟,这些具有文采的随笔大大丰富了文学批评在这种文化中的生命。除了各个文学流派的理论宣言,亨利·布雷蒙(Henri Brémond)的《诗与祈祷》、(注:此书钱钟书《谈艺录》八十八条颇有论述,读者可加以参考。)让·波朗(Jean Paulhan)的《塔尔布之花》、丹尼·德加鲁日蒙(Denis de Rougemont)的《爱与西方》都产生了很大反响。在这个繁荣时期里,各派文学批评之间关注点的分歧,被某种互通的整体性和语言才能所缓和。
这并不是说,
在丹尼尔·莫尔内(DanielMornet)的清新明快、梯也里·莫罗尼埃(Thierry Maulnier)的激昂严肃与让·波朗的简练锐利之间看不出风格的差异,而是说,由于缺乏专门的理论教条与术语体系,文学批评的各个领域彼此开放,并且目标都指向有文化素养的公众。
二、对严谨的向往
二战之后,这种局面被相继而来的两个变化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两个变化,一个是理论上的,另一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一方面,文学批评同那些理论武器比它强的学科,特别是哲学与人文科学,开始对话。这种动向并非全新的现象,早在二战之前,有关文学的思考就曾得助于柏格森主义与托马斯主义(影响较前者小)而在大学的历史主义研究之外另辟蹊径。1945年之后,文学研究的哲学与科学关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文学批评和其它领域一样,都受到了让-保罗·萨特无所不在的重要影响。萨特对文学所持的态度,因为他作家与哲学家的双重身份,而获得了双倍的重视。在他的《文学是什么?》(1948)发表之后,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权,单单是个批评家或者文学史家就很不够了。从此以后,为了不被视为坐井观天的行家,批评家们就必须具有一些额外的才能。各种思想潮流中首先大行其道的是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萨特存在主义与海德格尔诗性哲学之间,正统马克思主义与各立山头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之间论争迭起,壁垒分明。而50年代末,又有人文科学异军突起:先是人类学的崛起,稍后是对精神分析学大规模的再发现,到了60年代,则有语言学建立了自己短暂而又显赫的霸权,文学工作者们像新入校的小学生一般满怀着天真与热情进入了这些学科。萨特、马克思、海德格尔、列维·斯特劳斯、佛洛依德、索绪尔纷至沓来,启发了批评家们的思考,迅速而根本地改变了他们的语汇和方法。
另一方面,这场认识论的大爆炸由于法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而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回声。1940年之前的中学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只面向少数特权者。而在战后的几十年中,随着法国迅速地城市化与市民化,在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中,学生和教员的人数剧增。这种勃兴气候主导着教育部门,又波及至出版业,再至文化生活的整体,鼓励了学术上的大胆创见,孕育出一种面对新鲜事物的宽容心态。这种勃兴使各门新领域的创建势在必行,而在那些已经存在的领域,则允许人们发明新形式以确认自己知识的合理性。
上文提到的四种文学批评,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多学科对话与大学勃兴这两场革命的影响。在这个沸腾的年代,文学批评极力规范自己含糊不定的用语,使自己的研究方法脱离印象主义而有所加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文学批评向自己提出了近乎科学研究的苛刻标准,并且一度竟认为,由于自身的人文主义传统,它已不再获准确定自己的关怀与道路。文学批评被这种不安所困扰,这与世纪之交文学教育将修辞分析和印象主义诠释统统摒弃而采用历史主义方法时所引起的焦虑如出一辙。不过这一次,历史“次要因素”的语汇,当初指责为极端客观主义,如今却由于它的软弱,由于它缺乏理论普遍性而遭到攻击。新一代批评家们爱好坚实的理论和整体的解释,历史研究中的经验主义与审美文评追求的高雅品味同样令他们深恶痛绝。
起初,50年代的批评家们还只是想对历史主义与审美主义做出改善。马克思主义使批评家们得以在历史与理论之间做出新的综合。这种尝试因为吕西安·古德曼(Lucien Goldmann )有关小说社会学与冉森派(注:天主教派别,主张实行严格的道德戒条,认为人不能因自己的善德而获拯救,只有神恩才能救人出苦海。冉森派盛于17世纪,法国著名的保罗-罗雅尔修道院是冉森派的大本营。拉辛、帕斯卡的思想都极受冉森教义的影响。该派被正统天主教派视为异端,屡遭排挤迫害。)作家的论著而得到了很好的样本。与此同时,作品本身的内在力量(与有关作品的轶事趣闻式的史料相对立)激发了与日俱增的兴趣,而战前审美文评的余波与国外类似思想的逐渐引进也使这种兴趣更加浓厚。战前审美文评与50年代新批评之间的渊源,可以从评论家们之间的友谊与集会的一些细节中看出。当初向瑟耶(Seuil )出版社介绍罗兰·巴尔特这位艺术自足论者的人, 正是阿尔伯·贝甘和让·凯罗尔(JeanCayrol)。这种亲缘关系并非杜撰:战前反对审美文评最烈的一个就是萨特;而在《写作的零度》(1950)中,罗兰·巴尔特俨然以审美文评的保卫者自居,极力摒弃萨特的艺术介入政治论。在40、50年代,审美文评的传统体现在一系列讨论共时个性与共时共性的著作中:前者有乔治·布兰(Georges Blin)关于波德莱尔和司汤达的论著,后者有让-皮埃尔·里夏尔(Jean-Pierre Richard)的主题批评、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原型创作论以及让·鲁塞(Jean Rousset)有关文学形式与文学意义的探讨。对相邻学科的兴趣使批评家们从现象学中借用了观察文学本文的新视点,正是这种新视点启发了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和塞尔日·杜勃罗夫斯基(Serge Doubrovsky)等人的著作。借着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流行,黑格尔哲学的概念(世界观、英雄、悲剧)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而一些批评家开始向精神分析学寻求参照,比如在新型的主题批评,夏尔·莫伦(Charles Mauron)的论著,以及巴尔特的某些初作当中,但是应该指出,除了个别情况外,50年代的大多数文学批评向这些思想潮流与相邻学科借用的还只是为数甚少的概念与方法。这种借用,与其说是为了加强自己的理论武器,不如说是为了提高自己在解释本文时的审美敏感度。外部影响对文学批评的更新只起了间接作用:它们激励批评家们关注大学历史主义之外的领域,将本文的解释与文学的哲学史观摆在了文学批评的中心。
这种温和的多学科渗透很快就被对更强有力的认识论范式和国外理论源泉的狂热追求所代替。上文提到的教育与文化传播的勃兴,以及由于制度上的原因50年代法国人文工作者们的落后感,都为这种追求推波助澜。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认为(对错暂且不论),认识论发展的真正范式隐藏于国外的某个角落,其奥秘被那些比较陌生的学科和远在天边的国度保守着。俄国的形式主义,德国的风格学,美国的新批评,都发展于二战之前,与法国战前的审美批评本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也都在相同程度上摒弃了社会历史批评及其对“次要因素”的搜寻,转而集中力量研究文学美的本身,并将研究者假定为一个“不晓得文学史”的人,就如佩吉所言。但是,战前法国文评着重培养审美情趣的自发性,对体系不以为然。而那时的国外各流派却都建立起自身的严整清晰的框架。前者说到底是艺术性的,后者却遵循了大学界对学术研究的要求。列奥·斯毕泽(Leo Spitzer)和爱里克·奥尔巴克(Eric Auerbach)的风格学研究, 稍后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 )和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对美国式“阅读技巧”的描述, 维克多·契克洛夫斯基(Victor Chklovsky)、 罗曼·雅各布逊(RomanJakobson)、符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以及鲍里斯·托马契文斯基(Boris Tomachevsky )的著作(以上学者皆是大学界中人),都提出了确切的批评语汇和精致的描述技巧,甚至为更具普遍性的文学理论构划出一些片断。如果是在1938年,法国人大概会以一种平和的眼光审视这些学派,认为它们只是在外围取得了成绩。但是50、60年代的法国批评家们被强烈的革新热情与落后意识所鼓动,以致于他们准备毫不犹豫地承认国外学派比自己优越。还有一个因素似乎使这种优越更为明显:这些学派都与其本国的教育紧密相联,而法国战前审美文评的推动者则主要是大型文学刊物。法国的大学教育大体上仍忠实于历史主义传统,而文学批评的革新则起步于一些边缘的或是新建的学术机构:高等实用科学院六系(后更名为高等社会科学院)和巴黎第八大学(万森大学)。在这些机构中,研究者们虽然可以撇开在大学界一统天下的历史主义,但也必须极力使自己所用的新方法自成体系,因为系统性本身是任何大学学术研究的标志。当时吸引批评家们的典范是罗曼·雅各布逊和符拉基米尔·普罗普严密科学的著作,而不是夏尔·杜波或者让·波朗的批评作品,这不可不谓是原因之一。
出于类似原因,法国文学批评在向往国外范式之余,又对其它较为严谨的学科的理论威望孜孜以求。结构主义思潮毫不隐螨地声称要为文学批评移风易俗,将其纳入科学的范畴之下。对于结构主义的这种野心,前人早有论述:法国的结构主义在40年代发轫于人类学,它把结构语言学(特别是音位学)奉为圭臬,希望从中学到如何建立概念明确的严整网络,如何进行形式分析,以揭示那些决定人类行为的系统化的普遍规律。在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稍后又加上文学批评家的推动下,60年代初符号研究与符号学在国际上蔚然成风,颇有一统全部人文学科的雄心壮志。结构主义在法国的文学领域得到了双重回响:一方面,对于科学严谨性的向往以及俄美形式主义论著的发现带动了创作论研究的复兴,而新创作论的重点在于叙事学。1964至1972年之间,巴尔特、克罗德·布雷蒙(Claude Bremond)、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 热拉尔·热内特(Gérard Genette)、A.-J.格雷马斯(A.-J.Greimas)以及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等人的著作, 为叙事学这门新兴学科奠定了基石。而叙事学着重强调的正是普遍理论应较对于本文的个案分析占有优先权。另一方面结构主义又激发人们对文学的意义、对文学在象征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广泛的探索。因此,自从修辞学于19世纪末衰落以来,法国的文学批评第一次大规模地转向了对文学现象的共时共性研究。
三、理论的哄价
倘若浮士德看了60年代末的法国批评界,他一定会叹为观止,让时间之神停止他的进程:四种文学批评之间似乎建立起新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所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对文学现象的历史特性研究在大学界内部继续繁荣发展,下文将另有叙述。而历史共性方面的探讨,则体现于结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对西方逻各斯命运的大思辩当中:前者以思想接近吕西安·古德曼或路易·阿尔杜塞的作者克罗德·杜歇(Claude Duchet)和皮埃尔·马契雷(Pierre Macherey)为中坚;后者则由《原本》(Tel Quel)杂志的作者,如雅克·德里达和朱莉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ra)所掀起。共时特性研究成为众多讨论主题与风格的著作的指向(例如在里夏尔、斯塔罗宾斯基、鲁塞的著作中),而共时共性研究则在创作论、叙事学以及文学符号学的视野下长足地发展着。
另外,多学科对话所产生的强大动力也为文学批评打开新的理论缺口,其标志是由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所组成的三重唱。处于认识论大发展中心位置的文学批评,破天荒地跻身于人类知识的前沿。《文学》(注:《文学》杂志的主要编著者即是巴黎八大的教师们,这本杂志在大学文学理论革新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杂志在创刊号(1971年2月)上旗帜鲜明地宣扬了这种前景, 同时也表明了文学批评与多学科联合发展的愿望:“我们希望能够自立于一个破除了稳定边界的多学科领域,以便使文学知识与诸人文科学相联接,使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精神分析学等相关学科有更多的参照。”《文学》第一期讨论文学、意识形态与社会的关系,接下去的几期则探讨文学与精神分析(1971年3号刊)、文学作品的语义学(1971年4号刊)。
60年代末的批评界大体上弥漫着乐观的空气。起初,形势的发展也证明这种乐观不无道理。1968—1969年的学生运动之后,种种新思潮似乎得到了某种制度上的肯定。自然,这次学生运动并非人们所说的那样,是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想家们的煽动:年轻的革命者们追随的其实是境遇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然而从相反的方面讲,68年的动乱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改革深深震动了法国的大学,先前在高等社会科学院和巴黎八大等几所机构中发展起来的文学批评思想,如今一变而为新的标准,逐渐占领了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兰西学院(巴尔特,福柯和布迪厄)以及法国甚至国外的众多大学,例如,巴黎八大对于文学研究的组织方式,就成为加拿大70年代大学教学改革的主要参照。蒙特利尔的魁北克大学在这方面走得最远。在这个时期,新一代的杂志(《创作学》,《文学》,《符号学》,《人文科学》陆续出现,迅速发展起来,另外还有《创作学》(瑟耶出版社)和《L 》(拉鲁斯出版社)等丛书也呐喊助威。
但是,虽然取得了这些无可争议的成功,文学批评的各个新流派在70年代却经历了严重的冲突与逆流。在这一点上,《原本》杂志的改弦更张很能说明问题:从1968年到1976年,这本杂志试图在每一种新的理论和政治潮流中都留下自己的印迹,便以惊人的快速追随各种流派而无视它们之间的根本分歧: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共产主义、毛主义,最后竟向宗教和亲美派敞开了大门。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粉墨登场把许多与杂志有关的作者都套了进去。例如巴尔特,1970年出版的《S/Z》宣告了他对创作学及叙事学构想的放弃,也标志了共时共性文学研究内部致命分歧的开始。同时,由于《S/Z》声称要对巴尔扎克的一部作品进行细节性的分析,它也动摇了共时特性的文学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S/Z》总结了那个时代。这部谜语般的作品在它片断式的表达中有一种隐秘的野心:它要席卷并扰乱文学批评的所有领域,除了历史特性,因为巴尔特向来对它不屑一顾。《S/Z》构造出一套代码理论(阐释法,选择法,文化,符号,象征)建议我们对作品的共时共性做出新的审视。巴尔特所说的代码好比一架庞大的管风琴上不同的键盘与音栓,它们发出一组组回声,正是这些回声的偶然的,非人为的混响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文。在巴尔特看来,作者与读者只不过是混响中偶然的两点,彼此间根本无所谓谁比谁更重要。像作者一样,读者也是在一种自恋的随机过程中随心所欲地利用本文奏响代码,巴尔特将这个过程称为“再写作”。说到本文特性的阅读,风格学的客观追求与现象学的主观关注,都应让位于从精神分析那里借用的浮动注意力法,对显层意义的探求也要让位于对那些几乎无从察辩的“症侯”的寻找,而这些症候所能揭示的只是一些没有答案的谜团。读者享有专断权,他阅读本文是为了愉悦,而本文应该为这个目的服务。巴尔特这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都是为了构划出一种堂皇的历史共性理论:批评行为的指归与文化现代性的要著不谋而合,说到底都不过是要瓦解符号,因为符号从历史之初就一直压迫着人类。
出自新批评、结构主义创作学,以及后结构主义关于西方逻各斯的思辩的各种主题,在《S/Z》中前所未有地杂揉在一起。这种杂揉具体地表现在《S/Z》中的三种批评立场上,而三者之间的自我瓦解是显而易见的。首先,《S/Z》要对文学作品的本文进行细节性分析,却又不考虑到本文是作者有意写成的;它把只有在探讨“创作常规”的共时共性时才适用的方法过滥地推而广之,而这种方法在审视具体的文学信息(messages littéraires)时毫无意义。 其次,《S/Z》将对共时共性的探索简化为一种纯粹语义学上的译码游戏,而游戏的规则简直就是随心所欲;因此,它既忽视了情节的安排,也忽视了作品的表述技巧,换句话说,它把创作学与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揭示的丰富的“叙述格”统统抛在一边;创作学与叙事学确切的普遍性在这里被阅读代码无法操纵的普遍性所取代。最后,由于力图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有关符号历史大思辩的背景之下,《S/Z》的作者无可挽回地既背离了黑格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实体为根本的历史普遍性,又背离了大学界批评所极力保守的历史个别性。
这三种批评立场表明了某种混乱。当然,这种混乱远非由《S/Z》挑起,《S/Z》不过是将它表现出来罢了。产生这种混乱的根源其实是对形式主义文学研究不加思考的哄价。的确,似乎一切都证明,给文学批评安上一套严谨的认识论标尺的企图实现得太快,太热闹,太前卫,以致于不能获得持久的成功。文学批评确信自己借着形式主义的东风,已占据了人类知识的前卫,竟一度觉得自己可以任意伸缩各种新获得的尺度,可以尽享形式主义的名望而不必理会它的严密精确。《S/Z》呈现出的那一派文学批评顾影自怜的景象,确有其不可否认的魅力。有人甚至据此声称,由于巴尔特的这些尝试,文学批评终于摆脱了它对文学作品的附属地位,从而获得了自足的文学本文的身份。谁都承认,说到底巴尔特首先是个引人入胜的作家。但是如此相悖的才能只能在巴尔特一人身上获得成功。因为,既然十余年来如此鼓吹的多学科对话与理论范式勃兴,只是产生出这么一个理论无政府主义与批评的印象主义的堂皇杂揉,就像《S/Z》中随处可见的那样,那么何必不干脆放弃这些劳神的理论建设,转回去捡起那个更易操作的印象主义批评呢?
四、历史主义的力量
直到80年代,理论的危机才见分明。可是前卫派的分裂和不同派别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却早露端倪。一种新的批评形式要生存发展,不光要靠那些追随者们的仿作,更要向公众提出自己之所以应该被接纳的不可回拒的理由。然而,有两个因素不利于60年代的理论革新站稳脚根:一方面,理论界令人咋舌的滚沸翻腾既阻止了任何一种相对稳定的理论的结晶沉淀,也妨碍了一个较为稳定“正常”的研究时期在认识论革命之后出现。60、70年代理论家们过度活跃的创造力没有及时替自己找到立足之地。另一方面,将文学研究改造成严密理论的企图也显得过于冒险,历史主义与审美主义文学批评远比人们想象的更有生命力。
的确,文学史与语史学在战后几十年中成果辉煌,而这些批评领域都与当时的理论大辩论保持着距离。单以对“伟大时代”(注:伟大时代指17世纪路易十三、十四时期。)的研究为例,植根于语史学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就产生了众多佳作,其宏通渊博为人取法,其确凿中肯令人叹服。这其中有安东尼·亚当(Antoine Adam)的《17世纪文学史》和雅克·斯切尔(Jacques Scherer )的《法国古典戏剧》(此书对戏剧技巧深得三昧,结构主义者们当时如能参考,对叙事学研究中常见的平空穿凿的形式主义定会大有裨益)。乔治·库同(Georges Couton)之于高乃依,雷蒙·皮卡尔(Raymond Picard)之于拉辛,菲力蒲·塞里耶(Philippe Seillier)之于帕斯卡,都有力作问世, 诺米·海普(Noémi Hepp )的论文《17 世纪的荷马》、 玛丽一黛雷丝·依普(Marie-Thérèse Hipp )关于小说和回忆录的论文、雷内·高丹纳(René Godenne)、玛德来娜·贝尔托(Madeleine Bertaud)和乔治·莫里尼耶(Georges Molinié)关于巴洛克小说的论述、罗杰·祖贝(Roger Zuber )关于古典时代翻译的著作——类似的例子可以无穷无尽地罗列下去,都证明了传统学术的活力。而传统学术对于它自身,对于它的成果也信心十足。还应指出的是,尽管大学界的著述大都着眼于历史特性的研究,有一些作者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涉及到其他领域:斯切尔的戏剧研究以共时共性为目标; 莫里斯·德拉克洛瓦(MauriceDelacroix )的《拉辛的神圣戏剧》则建议对本文进行灵活而确切的阅读;让·鲁塞的《法国巴洛克时代的文学:西塞和〈孔雀〉》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人类精神的思辨史。保罗·贝尼舒(Paul Bénichou)对这个题目也很感兴趣,在《伟大时代的伦理》(1958)出版之后,他倾心考察作家在现代社会中的象征作用(《作家的加冕礼》(1973),《先知时代》(1979),《浪漫主义的朝圣者》(1988),《幻灭派》(1992))。大学界的论著也越来越多地紧随新出现的兴趣点,并以其博学的功底阐明它们。80年代的一些著作,如马克·弗马罗利( Marc Fumaroli)的《雄辩时代》(1980)、阿兰·米歇尔(Alain Michel)的《言语与美》(1982)、安妮·贝克(Annie Becg)的《法国现代美学的诞生,1680—1814》(1984),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修辞学传统。而如上文所述,新批评中的创作学与叙事学正是希望延续这种传统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那被称为“宏伟理论”的构想没落之后,历史主义研究又焕发出新的吸引力。在最近的10至15年间,很多批评家相继离开了理论思辩,转而研究文学作品的历史个性。这个现象确实耐人寻味。难道30年来为追求严谨而做的种种努力都付之东流,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吗?当然不是。路易·马兰(Louis Marin)、 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chonnic)、安娜·乌布斯菲尔(Anne Ubersfeld )和让-码丽·阿波托利戴(Jean-Marie Apostolidès )等人卓有影响的论著都证明了传统学术与新批评合作所能产生的丰硕成果。还应指出,如果说符号学与“硬”范式已大体退出文学批评,让-克罗德·高盖(Jean-Claude Coquet)关于克罗代尔和瓦莱里的研究, 让·莫里诺(Jean Molino)鞭辟入里的论述,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 例如弗朗索瓦·拉斯提埃(Francois Rastier)和乔治·莫里尼耶(
Georges Molinié)在巴黎四大共同主办的讲座)都使符号学的范式在批评语汇中传播开来。这种传播被大学界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出现的各种理论概念所证明。
仅以莫里哀专家们的近作为例,
帕特里克·丹德雷(Patrick Dandrey)的《莫里哀事件与〈没病找病〉》(1993)、 皮埃尔·弗斯(Pierre Force)的《莫里哀—物之价值》(1994)和马克斯·维尔内(Max Vernet)的《莫里哀—花园与庭院》(1991),都在分别由科学史、文学表现符号学以及象征社会学所开辟的道路上有所前进。如果说近来创作学研究比较贫乏(尽管有米歇尔·夏尔(Michel Charles)等人为这一传统支撑门面), 理论的活力却在文学的美学与哲学讨论中得到恢复,例如让-玛丽·斯卡埃菲(Jean-Marie Schaeffer)的《现代艺术》(1992)和万桑·德孔伯( Vincent Descombes )的《小说的哲学》(1988)。在这方面,热拉尔·热内特很久以来对普通美学的关注(《艺术的作品》,1994)很能说明问题。理论的这种新活力经常被用来说明甚至批评早年的前卫理论,例如在安东尼·孔巴农(Antoine Compagnon)的《现代性的五大悖论》(1992)中。
对当前气候具有揭示性的另一个迹象,便是新生成批评的发明。这种批评受到了历史主义研究与结构主义所珍视的多学科对话的双重浸染。它既是美学的,因为它关注作品,又是历史的,因为它探寻本文与其环境之间的触点。生成批评试图对文学这种文化现象的概念本身进行重新定义。由雷蒙·德布雷-热内特(Raymonde Debray-Genette )与雅克·奈夫(Jacques Neefs)主编的《档案小说》(1987 )和《作品的作品,福楼拜通信研究》(1993)为这个流派做了很好的注脚。近来大学界的文学研究也倾向于多学科和“文化主义”,假如我们不怕滥用这个词的话。 这种倾向起步于宏大的版本工程,比如热拉尔·德福 (Gérard Defaux)主编的拉伯雷集,库同(Couton)主编的高乃依集, 让·麦斯纳(Jean Mesnard)主编的笛卡尔集,皮埃尔-乔治·卡斯代克斯(Pierre-Georges Castex)主编的《人间喜剧》, 让-依夫·塔迪埃(Jean-Yves Tadié)主编的《追忆似水年华》;而后继以作家通信集的大规模出版:巴贝·托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y)、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福楼拜、马拉美、普鲁斯特、乔治·桑、左拉等等。他们的通信揭示了文学史与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最近出版的几部渊博的著作又加强了大学界的这种倾向。我们且举两部有关伟大时代的为例。路易·凡得福(Louis van Delft)的《文学与人类学》在17 世纪道德家们的思考当中看到了现代主义文化质问的前奏;而伊曼努尔·布里(Emanuel Bury)的新作《文学与礼貌》则对文学在现代人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出了真正的再发现。理论时代的回声不但远未消失,反而影响着几乎每一部批评新作,即便是那些挑衅似地要回归印象主义和主观自由的批评作品(例如皮埃尔·巴谢(Pierre Pachet )文笔优美的著作)也概莫能外。
是否可以据此得出结论:在本世纪末,各种有关文学的言论之间正在达成一个新的平衡?这个平衡与文学批评在30年代和60年代的繁荣遥遥相对,仿佛法国文学批评的生命线以三十年为一轮回。这种说法如果正确(尽管要最后证实还为时尚早),那它的得出也要归功于众多评论家们:他们终于懂得,说到底,他们学科的兴旺发达既有赖于对文学的历史文化特性的忠实,也有赖于对理论共性的追求。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结构主义理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法国文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巴尔特论文; 熙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