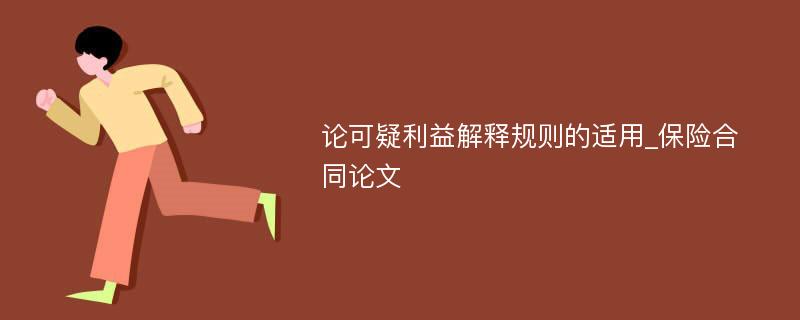
疑义利益解释规则适用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疑义论文,利益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保险合同条款存在疑义时,应作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这就是保险合同中的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目前,世界各国保险立法或司法判例大多都确立或采用此规则。① 我国保险立法吸收借鉴这一立法经验,在《保险法》第31条中作了规定。由于我国立法对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规定过于粗疏,且对该解释规则与合同法其他解释原则的关系未予明确,造成了司法实践中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混乱,保险界对此也颇多异议。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对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具体适用问题作粗浅的探讨,以期对司法同仁有所启发。
一、据以研究的具体案例
[案例一]2001年6月29日,陈某为自己投保了《康宁终身保险》,基本保险金额为10000元,保单受益人为其儿子陈子。2002年2月6日,陈某因肺癌死亡,陈子持相关证明材料向保险公司申请身故保险金。保险公司经调查得知:2001年7月5日,陈某因左骼骨部肿痛至医院就诊而被确诊为“右下肺癌左骼骨转移”,其后一直在间断治疗。保险公司依照《康宁终身保险》第5条第7款有关“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180日内患重大疾病、或因疾病而身故或造成身体高度残疾时,本合同终止”的规定,给予拒付处理。陈子不服,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保险公司《康宁终身保险》条款第5条第7款本身理解上使人产生歧义,针对格式条款应作出有利于受益人的解释。据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败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理解保险合同条款含义,首先应从保险条款整体内容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出发,故主持双方进行了调解。②
[案例二]姜某系某小学学生,于1996年10月在某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学生儿童住院和平安险”一份。姜某投保时,是将保险费交给所在学校,由学校集体办理投保手续。人寿保险公司在1996年10月签发了保险单正面的内容,与学校填写的投保单中的内容一致。其中载明:投保单位为该小学,金额为人均7000元,保险费率为每千元2元;保险期限为1996年10月10日零时至1997年10月24时。保险单背面所附的《××市学生儿童住院医疗和平安保险章程》第5条规定,“平安保险仍按原标准执行,即:保险金额最低为3000元,最高为10000元;保险费率为1‰。”姜某依合同缴纳平安保险费14元、医疗保险费12元。1995年4月20日,学校所在地教委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当地分公司联合下发文件,将××市学生儿童住院医疗和平安保险的费率由1‰上调为2‰。1996年10月14日,姜某与其母亲横过马路时被汽车撞伤。保险公司在理赔时对保险金额为7000元还是14000元发生争议成讼。姜某的监护人认为,保险章程条款规定保险费率为1‰,姜某缴纳了14元保费,由此确定保险金额力14000元。保险公司则认为应按照保险单正面记载的保险金额7000元为基础确定赔偿金额。一审法院依照《保险法》第30条规定的疑义利益解释规则,采纳了被保险人的主张。二审法院则认为双方在填写保单和签发保单时对保险金额达成了一致意见,保险金额应以保单正面记载的7000元为准。③
[案例三]李某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家庭自用车损失保险。保险条款第8条第6款第2项规定:驾驶员无有效驾驶证件驾车造成的车辆损失,保险公司责任免除。在保险责任期间内,李某投保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汽车严重损毁。李某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在审查时发现李某未按照有关要求参加驾驶员资格年审,遂以李某驾驶证未经年检,属于无有效驾驶证驾车为由拒赔。李某认为,其驾驶证虽未年检,但并未作废失效,双方因此成讼。法院依照疑义利益解释规则,采纳了李某主张,判令李某胜诉。
以上三个案例都涉及到疑义解释原则的运用问题。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一)疑义利益解释规则适用的条件是什么?如何理解合同条款的“争议”。(二)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与其他合同解释规则的关系和适用顺序。(三)对于疑义利益解释规则适用的范围,专业术语是否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二、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法理基础以及适用条件
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又称有利于非起草人规则或不利规则,是指当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发生争议时,应作有利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解释。该规则起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原则,其后被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广泛接受,如法国民法典第1162条规定:“契约有疑义之情形,应作不利于订立此种约定的人而利于债务人的解释。”英美法系则有不利于起草人规则(见《合同法重述》第206条)。保险法上的疑义利益解释规则,是伴随保险合同的标准化和格式化发展起来的。由于对交易简便、迅捷的要求,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一般由保险人预先拟定,充分考虑保险人自身利益,而较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意志。投保人投保时只有同意投保或不投保的自由,而没有权利对保险合同的具体条款进行修改。如果确有必要增删或变更内容,通常也只能借助保险人事先准备的附另条款或附属保单,而不能完全遵照投保人的意思来作出改变。④ 因此,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并非处于平等地位。保险合同的格式化,实际上剥夺了投保人对合同具体条款进行协商的自由,是对合同自由原则和民事主体平等原则的背叛。因此,法律有必要对双方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地位进行司法调整而实现公平交易,并体现对保险交易中的弱势群体——被保险人倾斜性保护的价值关怀。此外,保险合同内容复杂,具有较强专业性和技术性,受专业知识和时间的限制,普通投保人一般不可能对保险条款予以细致研究。保险人作为合同起草人有责任让合同的用语准确无误,以便投保人充分了解保险条款的内容和含义。由于保险人的原因,造成歧义,理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以防止其滥用保险专业优势,故意侵害投保人之利益。
保险法上的疑义利益解释规则,最早见于英国的一个著名判例威廉·吉朋诉理查德·马丁一案。⑤ 公历1536年,英国一个名叫理查德·马丁的保险商人为其朋友威廉·吉朋承保人寿险,保额为2000英镑,保险期为12个月,保费为80英镑。吉朋于1937年5月29日死亡,受益人请求依约给付保险金2000英镑,但马丁声称吉朋所保的12个月,系以阴历每月28天计算,因而保单已于公历5月20日到期。受益人主张保期应按公历计算,保险事故发生于合同有效期内,为此成讼。最后法院判决作了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宣判马丁应承担给付保险金之责。此后,该规则逐渐演变成为被广泛采用的保险合同解释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1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对保险条款有“争议”,是适用疑义解释规则的条件。因此,正确理解该条款中的“争议”,对正确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将“争议”等同于“争论”,指各执己见,相互辩论。“争议”一语的解释反映的是对争议双方没有一致认识的表面现象的描述,至于争议双方孰是孰非,“争议”是纯粹由于当事人主观原因还是所争论问题客观上确有疑义引起,在所不问。因此,“争议”与争议涉及条款的实质内容无涉。审判实践中,有的法官根据保险法这一规定,在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对合同条款意见不一致时,不管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提出的问题是否合理,就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显然误解了立法原意,滥用了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笔者认为,滥用疑义解释规则的现象,固有法官理解法律不透彻的原因,也与立法上用语不准确有关。实际上《保险法》第31条规定的“争议”应作限制性解释,仅指由于合同条款存在疑义而引起的争议。合同条款存在疑义,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合同条款模糊不清,即“一个词具有两个以上完全不同的含义,以至于在同一时间,对这一词语的理解既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⑥ 另一情形是不同条款之间内容相互矛盾,无法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如案例二中保险单条款与背面保险章程条款存在矛盾。判断合同条款是否存在疑义,不应该站在当事人任何一方立场上理解,而应从中立的理智的正常人的立场上理解。如果从一个正常人角度理解,合同条款本身内容清晰,被保险人故意曲解合同条款,人为制造争议,不能认定对合同条款存在争议。否则将鼓励投机行为,违背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因此,域外立法多数从合同文本出发,以合同条款有疑义而非以当事人有争议作为该规则适用的条件。
由于知识、文化背景、立场等因素的差异,不同主体对同一合同条款进行解读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法官以什么标准判断合同条款是否存在疑义对疑义利益解释规则有重要影响。总结国内外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应该遵循如下原则。
(一)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存在真实的争议。判断合同条款是否存在疑义,不应拘泥于所使用的文字。即使第三人看来模糊不清的条款,当事人也许并无争议。而争议是合同解释存在的前提,无争议则无解释。只有当事人确实存在争议时,法官才能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而不能越俎代庖,以个人的理解代替保险合同当事人的理解,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替代当事人的价值标准。如果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存在争议,经过协商后对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意见,也应视为无争议。
(二)除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合同条款存在争议外,从一个具有合理理解能力的普通人角度理解合同条款,是否将“诚实地对其含义产生歧义”。只有满足这一条件,才有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余地。
(三)通过其他途径,是否可以将疑义排除。如一个词语有多种含义,但结合合同条款的上下文,可以排除歧义,确定其真实含义,那也不应认为合同条款存在疑义。
(四)对保险合同条款虽有两种解释,但作对投保人有利解释将导致结果明显不合理、违反法律规定,或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情况出现,则不能认为合同条款存在疑义而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如案例三中的李某驾驶证没有年检,依照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26条第5款有关“未按规定审验或审验不合格,不准继续驾驶车辆”之规定,不能驾驶车辆。如对“有效驾驶证件”作有利于李某的解释,无疑认可了李某驾车行为的合法性,违反了法律规定。
根据以上规则,我们再分析上述案例一。该案《康宁终身保险》条款第5条第7款规定:“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180日内患重大疾病、或因疾病而身故或造成身体高度残疾时,本合同终止。”投保人陈某在签订保险合同后不到10天就被确诊为“右下肺癌左骼骨转移”,依照一般正常人的理解,在目前医疗技术水平条件下,该病无疑属于重大疾病,属于保险合同第5条第7款规定的重大疾病,将引起合同终止。该条款约定并无模糊之处,如果保险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履行了格式免则条款的提示义务,应认定为有效,本案应依照保险合同约定作合同终止处理。不能因为被保险人单方对合同条款提出异议而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进行解释。
三、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与合同法其他解释规则之关系
合同法的其他解释规则,同样适用于保险合同。适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将产生不同的法律结果。如案例二,如果用整体解释的方法,姜某的主张无法成立。结合投保书、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当地分公司与当地教委联合下发的文件综合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保险金额为7000元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假定姜某主张成立,应适用保险章程规定,那也与其交费行为产生矛盾。保单背面的保险章程条款的保险费率为1‰,姜某缴纳了14元保费,由此推算保险金额应为14000元。而保背面保险章程规定,保险金额为3000元至10000元。因此,姜某交纳的保费保险费率不可能按照1‰计算,否则超出了保险章程规定的最高保险金额。由此也可推断出背面的保险章程不可能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当保险合同存在疑义时,应优先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抑或适用合同法的基本解释规则,实践中不无争议。有观点认为,与合同法相比,保险法属于特别法,依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保险法的规定应优先适用,因此保险法中规定的保险合同解释规则也应该优先予以适用。
笔者认为,以上意见没有掌握合同法基本解释方法与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性质的区别,有违合同法灵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我国合同法规定了5种合同解释的基本方法,分别为:(一)文义解释。是指通过对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含义的解释,以探求合同所表达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二)整体解释。整体解释又称为体系解释或逻辑解释,是指把全部合同条款和构成部分看作是一个整体,从各个合同条款及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所处的地位和总体联系上阐明当事人系争的合同用语的含义。(三)目的解释。是指解释合同时,如果合同所使用的文字或某个条款可能作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合同目的的解释。(四)习惯解释。是指合同使用的文字词句有疑义时,应当参照当事人的习惯加以解释。(五)诚信解释。是指解释合同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从性质上看,上述五种基本解释方法的立法基础都是根据合同自身的信息以及与其有最紧密相关的因素(如合同目的、交易习惯等),来证实合同条款在整体背景下的真实含义,其着重点在于探究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于合同意义的真实性,属于事实判断。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则是一种价值判断,即不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为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是该规则的生命力之所在。在合同自由法制下,当事人的合意是合同成立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是法律赋予合同法律效力的依据。因此,在解释合同时应该尽量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司法不应对合同自由予以过多的干预。法官对合同进行解释时,首先要确定的是当事人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即依据证据法则进行事实发现之作业,以确定当事人意思表示在事实上的含义。否则,合同如同于一张空白授权书,为法院替当事人订立合同提供依据,从而使合同的效力丧失殆尽,动摇合同法的基石。与事实判断不同,价值判断由法律拟定,无需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具有浓厚的强制干预色彩。其使用必须有正当的基础,即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的理解不能达成共识,而且即使正常的理性人也不能对保险合同条款内容有确定的判断,只有这时,才能进一步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个角度讲,《保险法》第31条规定的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在保险合同解释规则中是一个“第二阶位”条款,只有在保险合同基本解释方法穷尽后仍不能消除对保险合同条款歧义之时,才能适用。
这样,只要依据文义解释等基本解释方法,就可以消除当事人的理解歧义,当然也无需适用《保险法》第31条的规定。这种理解不仅能平衡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还能防止出现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道德滑坡的危险。而且,它首先确定了当事人对合同争议是否真实的事实,然后在此事实基础上构建是否不利于保险人的价值判断,从而能正确地落实该法条的立法意旨。这当然也意味着,法官应严格限定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适用对象,只要基本解释方法能妥当消除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争议,就没有必要适用该规则。在适用顺序上,文义解释等保险合同解释的基本规则要优先于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四、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之限制
保险合同之所以采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就在于保险人的意志在保险合同中占据了主导性,使得保险合同的内容有偏向保险人利益的趋势,法律为了纠正由此可能给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和利益状况带来的偏差,遂有了不利于保险人的价值判断。不过,如果不顾保险合同签订时的具体情况,无条件限制地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也可能会产生矫枉过正的后果,反倒不利于保护保险人的正当利益。
具体而言,对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程度以及对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的决定力量等同于或者大于保险人的相关要素时,就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而作出对保险人不利的判断。这种情形下,投保人与保险人势均力敌甚至拥有强于保险人的能力,它们在保险合同签订过程中,基本上达到了“意思自治”,它们要为出于自己真实意志而做出的行为负担责任,承受相应的后果,包括对各自不利的后果,而不能把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转嫁给对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保险合同的确存在意义不明之处,也表明保险人对该瑕疵具有可归责的事由,它也要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当前审判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再保险合同。再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与保险人同为保险公司,双方地位旗鼓相当,保险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无明显优势,双方同时具备相当的保险专业知识和经验。因此,法律不应对被保险人进行倾斜保护,不存在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空间。
2.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手写的条款。投保人手写的条款基本上是经过双方协商确定,比较真实地反映投保人和保险人意思,且非保险公司拟定,保险人对其内容产生歧义并无责任。基于公平原则,不应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3.银行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关于开展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合作协议。近年来,保险公司开展的个人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多数都事先与银行签订一个总的合作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合作协议虽然不是独立的保险合同,但在很多具体的保证保险合同中,都特别注明合作协议作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因此,合作协议也成为保险合同的条款。由于合作协议为银行与保险公司充分协商订立,在目前保险业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在与银行商谈过程中并不具有优势地位,对于合作协议中的条款,也不应适用疑义解释规则。
(二)对于保险条款出现的疑义保险公司并没有责任。这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1.保险法上专门术语。保险业务专业性强,在数百年的长期经营中,形成了许多为世界各国保险经营者所承认的国际保险市场上的专业术语。这些专门术语具有特定含义,如暴雨专指每小时降雨量在16毫米以上,或者连续12个小时降雨量达30毫米以上,或24小时降雨量达50毫米。这些专门术语对准确界定保险责任,减少争议发挥了积极作用。一般认为,“对保险单文字进行解释时,一般应当首先按普通含义去理解词语,但在词语有‘专门含义’时则不能按照普通含义去理解”。⑦ 如果保险人表明其是在专门含义上使用某一词语的,则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在案例三中,中国人民银行于1995年印发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第5条第12款对“无有效驾驶证”进行了专门解释,其中“虽有驾驶证,但未按规定参加驾驶员年审或年审不合格的”,为无有效驾驶证。而交通管理法规也有驾驶证未按规定审验或审验不合格的,不准继续驾驶车辆之规定。因此,应采用专业术语的定义对持有未经年检合格的驾驶证是否为“无有效驾驶证件”进行解释。
2.保险合同上的基本保险条款和法定保险条款。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是国家保险管理部门为了规范保险市场,维护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从相对中立、公正立场上制定,较好地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的利益关系。因此,这些条款主要是反映了政府主管部门的意志。由于这些条款既没有具体反映保险公司的意志,保险人对于这些条款产生歧义也没有过错,不应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进行解释,而应由国家保险管理部门依照法律、基本保险条款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制定基本条款的目的作出公正的解释。
(三)作为保险人相对方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特定的营业人,就保险合同条款内容涉及其特定营业部分,应按照其职业或者营业特点进行界定,而不能随便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如在董事责任保险、律师执业责任保险等责任保险领域,应按照被保险人具体职业特点确定涉及到与其职业相关的合同条款内容,不应简单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五、结语
总而言之,在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时,应持审慎的态度,综合考虑当事人纠纷的事实情况、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争议能否用基本解释方法予以处理、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实际所处的地位等因素。不能割裂保险合同解释原则之间的联系,只要是保险合同条款争议,就不顾纠纷的实际情况,直接作出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判断。这种对保险合同争议过分简单化、粗梳化的处理,损害了保险人利益,助长了保险合同投保方的道德风险。
注释:
①樊启荣:“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之解释”,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
②刘峰:“论保险合同的‘不利解释’原则”,载《保险研究》2005年第2期。
③于永龙:“保险法律特殊规则优先适用”,载《行政与法》2002年第12期。
④曹菁:“保险合同解释原则及方法探析”,载《内蒙古保险》1999年第3期。
⑤同上注。
⑥SpencreL.Kimball,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surance Law,Little Brown & Campany,1992,p.8,转引自樊启荣:《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之解释》。
⑦[英]约翰·伯茨:《现代保险法》,陈丽洁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标签:保险合同论文; 保险法论文; 法律论文; 保险金额论文; 投保人论文; 合同条款论文; 康宁终身保险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契约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