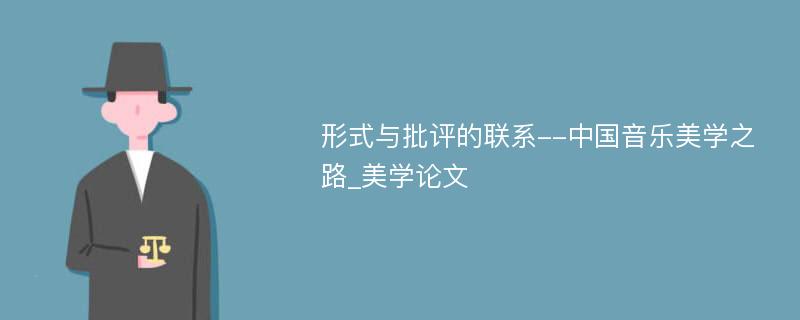
形式与批评的勾连——中国音乐美学的应由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美学论文,应由论文,中国音乐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音乐美学学科体系是从20世纪才开始建立的,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音乐美学在基础理论建设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许多问题的讨论得到了深化。然而,一个学科如果要取得更大的成就,要保持更加旺盛的学术活力,就需要不断地提出新问题,不断地开拓新的学科生长点。在笔者看来,新时期,中国音乐美学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就应该是超拔于纯粹的思辨传统,而尽可能多地关注音乐的活态存在,而这种关注的方式就应该是音乐批评。这既是出于跨学科的要求(批评本身就已经有整合多种学科的可能性),更是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在西方特别是美国,音乐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对实证主义的音乐学传统进行了强烈的反思,美国当代音乐学的领军人物克尔曼(Joseph Kerman,1924—)曾指出:“当前研究19世纪的音乐学家没有全盘接受标准的分析体系,而是一步一步朝着自己更加全面的分析方法前进,即朝着批评的方法论前进。”①几乎与此同时,早在90年代初,于润洋先生就已经在他那篇广为人知的长篇论文《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率先提出“音乐学分析”这个学术概念并做了身体力行的实践。对于音乐学分析的性质,于先生指出:“对一部历史上的或是当代的音乐作品所作的音乐学分析,从性质上讲,它应该是一种广义上的‘音乐批评’,而这种批评应该既是美学的或审美的批评,又是社会—历史的批评。”②很明显,于先生这里说的音乐学分析式的音乐批评,并非通常所指的以个人现场感受为主的所谓乐评,而是具有理论深度的严肃的学术活动,其以深度阐释为旨归,如将音乐学分析的对象从单纯的作品扩展到风格、形态特征等更为广阔的领域。本文所指的音乐批评与于润洋先生所说的音乐学分析几乎具有同样的内涵。除此之外,国内尚有明言等学者已出版、发表的《音乐批评学》等相关著述,对音乐批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面对国内外这些重要的学术指向,我国音乐美学界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而应关注这些趋势。音乐美学作为最具理论品格的学科,有义务也有责任对活生生的音乐的感性内涵、文化内涵、哲学内涵、社会历史内涵做出阐释,而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就本人的感受,在中国音乐美学界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不拟对音乐批评做全面的阐述,仅提几点个人的看法,权当抛砖引玉,希望引起讨论。
音乐形式与审美批评
有人可能会将形式问题看做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笔者则认为这是个常谈常新的问题。于润洋先生的论文《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③、姚亚平教授的论文《错觉图——游走于形式与形式之外的凝思游戏》④以及李晓冬博士的专著《感性智慧的思辨历程——西方音乐思想中的形式理论》⑤,都从美学意义上对音乐的形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我这里仍然要以此为起点讨论音乐批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从实践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在音乐美学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音乐形式,是音乐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基础,形式的特殊和重要,恐怕没有其他艺术像音乐一样体现得如此明显。这一点汉斯立克早在19世纪就异常敏锐地注意到了,正如于润洋先生指出的:“汉斯立克从音乐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殊性质这样一个在当时极为独特的角度提出问题,并以此作为基点探讨音乐的本质,这对音乐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没有这一步,音乐美学就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真正确立下来。”⑥这是汉斯立克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
但与汉斯立克的极端的自律论倾向不同,笔者认为但凡严肃的、有一定价值的音乐作品,通常蕴含有某种内涵,无论是贝尔(Clive Bell,1881—1964)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还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所说的“真理”,抑或茵加尔顿(Roman Ingarden,1893—1970)指谓的艺术作品中某种“形而上”的东西,或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1895—1985)的“内在生命”,无一不将音乐指向某种深层意蕴。既然存在这样一种意蕴,那么去挖掘音乐作品的深层意蕴就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即便是汉斯立克这样的极端形式一自律论者,也不会否认音乐形式蕴含着某种审美感性。而无论是深层内涵,还是形式带来的审美感性,无不蕴含在具体的音乐形式之中。由此,关注音乐形式就成为音乐学家特别是音乐美学家不能忽视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失去了感性形式,再发达的审美能力,也会陷入无美可审的窘境。对于这一点,于润洋先生有过很深刻的论述。他认为,阐释音乐的深层内涵(在笔者看来也就是音乐审美批评),“要深入到音乐文本自身,也即声音层面上的乐音结构体本身,因为任何精神性的内涵只能通过对音乐文本本身的透视才能得以阐释”⑦。于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在音乐这门独特的艺术中,当我们试图深入阐释作品的内在意蕴并揭示它的美时,对风格、技法层面的把握就显得异常重要,这也正是以纯音响为物质材料的音乐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的一个重要特性。”⑧这一点与克尔曼倡导的批评音乐学何其相似:“我力图要达到的是,利用音乐学学科所有的,或尽可能多的成果,去澄清,或确实去发现音乐本体的审美特性。”⑨问题在于,如何将形式分析与感性体验相勾连?苏珊·朗格的理论给了我们重要的启发,在朗格看来,“我们叫做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式——增强或减弱,流动与休止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梦的消失等等形式,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⑩它意味着音乐形式与人的感性生命具有同一性,人们“直接从对艺术作品结构样式的知觉过程中感受到一种运动,一种生命的活力,它与人们内在心理所具有的张力结构模式相互契合,于是产生审美体验”(11)。正是这种具有格式塔性质的异质同构理论给我们讨论音乐形式与审美活动中的感性体验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然,在进行形式分析的时候给予一般性的感性描述,还很难说具有美学的品格,因为描述感性体验并不是批评的最终目的,批评的终极目的应该是阐释,它需要揭示感性何以如此的秘密,由此才能将批评纳入美学的范畴。当前,存在很多将所谓感性体验的描述片面地理解为似是而非的文学想象的情形,特别是在音乐作品与文学作品存在一定关联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如此。于先生就此提出过批评:“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要尽量准确地把握音乐作品与诗歌本身在情感氛围、整体内涵性质上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避免寻求外在的、表层的某种简单对应,通过相关诗歌这个媒介的启示,去直接体验和感悟音乐,最终进入音乐的意义世界,阐释作品的深层内涵。”(12)在这一点上,于润洋先生的专著《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可称得上是一部典范之作。对于阐释对象,他不仅结合形式分析给予感性体验的描述,而且将其纳入悲剧—戏剧性或悲情范畴来加以阐释,从而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美学层面了。
音乐形式与文化批评
一个对象,如果以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会呈现不同的面貌,音乐也不例外。同样一部音乐作品,如果我们不从纯粹审美接受而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它,这时的音乐作品就是一个文化符号,而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自律性的音响符号。从发生学意义而不仅仅从审美知觉上看,一部音乐作品的创作者,必然处于某种环境之中,他是特定文化中的“文化人”,因而其创作的作品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它必然凝聚着某种文化属性。考察音乐作品的文化属性,同样离不开对音乐的形式分析,因为文化内涵必然内化在音乐形式当中,需要通过对形式的分析加以揭示。因此,基于文化视野的音乐批评一端系于音乐形式,另一端则系于文化,而批评的目的则在于实现音乐形式与文化的勾连,打通它们相互通约的渠道。显而易见,纯粹的感性体验已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对具体文化的深入了解甚至深切体认变得尤为重要。文化的外延实在是异常广泛,举凡阶层、族群、习俗、宗教、语言、性情、风土等等皆可入文化之列。这里仅仅列举几个例子以说明这个问题:观察早期奥尔加农,平行四五度进行是其重要特征,从发生学意义上看,难道仅仅能看成是音乐的自律性发生吗?显而易见,这种结构形式与当时的宗教文化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宗教音乐,其目的是力图抑制人的感性冲动,追求内心的宁静和谐,从而洗刷人的罪孽,净化人的灵魂,因此可以说这种宗教文化已经内化进了奥尔加农的结构之中。再如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高度半音化的形式结构,同样不能被视为纯自律性演化的结果,它与19世纪对人的生命中无意识领域的开掘这一文化思潮密切相关,还有这一时期很多民族民间的音乐资源被广泛运用,如肖邦所爱用的波兰民间音乐特有的利第亚增四度、李斯特爱用的吉普赛调式等等,也恰恰与启蒙主义所倡导的“世界主义”理想的破灭,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1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麦克莱瑞(Susan McClary,1946— )等为代表的美国新音乐学对音乐中文化属性的充分挖掘,通过对音乐形式的透视,挖掘出形式本身所承载的诸如性征(Sexuality)、种族(Race)、阶级(Class)等文化属性。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在麦克莱瑞的《卡门》一书中,对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卡门主题中的一个增二度音程,麦克莱瑞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解读出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增二度在西方传统艺术音乐中,通常是一个禁忌,但却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部歌剧最重要的卡门主题中,作为吉普赛音调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在此与西方主流族群中的他者——犹太人、吉普赛人等边缘族群密切相关,麦氏甚至认为这个以增二度为主要特征的卡门动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作为女性的他者对男权社会的威胁和动摇。由此看出,在麦氏的解读中合乎逻辑地将这样一个音程与其代表的文化身份有机地勾连在一起。麦克莱瑞的具体观点也许可以争论,她对音乐中隐含的性征意味的解读有时的确失之牵强而常常遭人诟病,但以她为代表的新音乐学的总体探索方向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中存在许多积极的、有益的因素。
音乐形式与社会批评
在中国,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甚至曲解,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饱受庸俗唯物论、机械反映论的影响,将艺术包括音乐简单地比附于具体的意识形态,强调音乐为政治服务,的确对于音乐创作乃至于音乐理论的建设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然而,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又称“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仍是当下最具活力、最有前景的理论资源之一。强调艺术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路,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前者对艺术形式高度重视,甚至形式问题成为了他们讨论的核心,在他们看来艺术形式“能改变艺术品的封闭状态,使之进入与社会和历史的对话性框架之中”(14)。形式在他们的理论中如此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可视为一种形式美学。当然,西方马克思的形式美学并非“形式主义”,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通常比较辩证,既注意到艺术形式与社会的内在关联,也肯定形式的相对自律。针对艺术哲学中形式与内容长期以来被割裂的情形,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的看法具有积极意义:“一件艺术作品的真诚或真实与否,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容(即是否‘正确地’表现了社会环境),也不取决于它的纯粹形式,而是取决于业已成为形式的内容。”(15)由此,将内容与形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相比,马尔库塞、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等特别是后者更强调艺术对社会的干预、反抗功能,所以阿多诺的美学理论被称之为“否定的美学”。以是否具有批判性作为唯一标杆,他推崇勋伯格的音乐而贬斥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这一点于润洋先生已在其专著《西方现代音乐哲学导论》进行了很深入的解读。那么艺术如何能做到对社会的批判?如何理解他的批判意识?笔者感觉,有一个概念现在尚未得到国内音乐学界的充分重视。这个概念就是艺术形式的中介性。阿多诺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音乐社会学家,但在他看来,审美活动和政治实践是不同的活动,因此他极力反对在艺术作品中直接灌输政治内容,或进行道德说教,也反对在艺术作品中对现实社会进行机械的反映。他认为艺术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关系,这个中介也就是艺术的形式,因此他认为社会现实的潜在要求在艺术中只能通过这一中介以间接的方式加以实现,强调这一中介的意义在于:“它借助艺术自身的矛盾表达了艺术和社会之间的矛盾,间接地同时又是确定无疑地开拓了艺术对现实的批判空间。”(16)阿多诺在谈到现代音乐的反抗性时,正是从音乐形式这个中介出发的,其反抗现实并非像文学作品那样直接在音乐中表现出来,而是间接表现的,具体方式就是通过对传统音乐技法的否定达到对既存现实的否定和抗议。正如阿多诺所说:“反抗以审美的方式而非直接摹仿的方式再生产社会发展过程。激进的现代主义保留了艺术的这种固有本质,它以模糊的形式使社会进入他的辖区,使后者似乎成为一个梦。”(17)
阿多诺以艺术是否具备反抗性作为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显然极端了些,艺术不仅仅只有反抗意识形态的功能,有时也与意识形态形成同谋,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戈德曼(Lucien Goldmann,1913—1970)所说:“艺术作品的结构和作家所属的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具有同构关系;越是伟大的作品,这种同构关系就越是严格和突出。”(18)抛开阿多诺拉一派打一派的合理性不谈,吸取阿多诺和戈德曼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他们以形式为中介来探讨艺术与社会的对话对于克服机械反映论的局限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对于不具有明确语义性与具象性的纯音乐而言,如何实现音乐与现实、观念乃至于与哲学思想之间的对话,形式这个中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为这种沟通开启了一个重要的渠道。可以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形式话语的分析都是“为了建立话语形式与社会的肯定或否定关系”(19)。因为形式本身可以被抽象成某种思维结构,而社会也可以被抽象成某种社会意识的结构,由此,形式与社会就可以在结构层面形成或同一或抵牾的对话。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新潮音乐”对“文革”十年的抗议,不正是通过形式上对传统技法的否定而实现的吗?它以艺术形式为中介,这种反抗当然是间接的。我们也不难理解以形式为中介,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实现了与叔本华的意志哲学的沟通和对话(20),甚或还可以从阿多诺哲学思想中对同一性原则的批判去考察勋伯格无调性音乐的音高关系(21),如此等等。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那么笔者愿意再次重复上面的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仍是当下最具活力、最有前景的理论资源之一。
音乐形式与权力分析
法国20世纪著名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权力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新历史主义,笔者认为它对音乐批评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福柯的权力概念不同于我们一般理解的政治意义上的权力概念,它比政治权力有更为宽泛的意义,它是“存在于具体场所中的局部的、微小的权力,即权力的细微形式……在社会肌体中犹如毛细血管……”(22)它充斥在整个社会网络中,无处不在,“权力不存在于任何人手里,而是通过网络组织被使用和实行。”(23)简单地说,福柯的权力意味着多重的力与力的交织、缠斗,也就是说权力本身是一个关系质。权力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是,他(它)不是一个禁止性、消极的概念,而是生产性的、创造性的、积极的、流动的。权力可以以统治的面目出现,同时从统治里也可以滋生出某种抵抗,于是二者形成某种对抗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权力可以产生知识。福柯在《疯癫史》一书中通过对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对待疯子的不同概念和态度以及不同的处理方式(24),旨在说明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关于疯子的知识,关于疯子的知识是被权力所塑造的,而且是充满变化的,推广开来,其他一切知识、真理也并不都是先验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变化的,充满了权力的干预,是被权力锻造出来的,知识“并非是对世界真相一劳永逸的捕获,知识处在变化中,它在不停地转换自身的视角,它无法独立于权力,独立于偏见,独立于利益,独立于知识的主体。”(25)福柯通过这种关于疯子的权力技术分析,力图揭示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26)
笔者认为福柯的权力理论对于音乐批评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提供了极为广阔的批评空间。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教授的学术研究中已触碰到了这一视角,他的著作《复调的产生》(27)对欧洲早期复调语言机制的文化意蕴进行了富于新意的权力话语分析,比如作为权力主体,在早期复调的演化史中,Tenor声部在权力的角逐中,从最初的霸主到最后让位于Bass声部,终告落败;而四度音程的命运则几经沉浮,从最初的高高在上,到落寞失意,再到后来重获新生,真可谓是跌宕起伏。书中对西方音乐发展过程中的四度音程进行了非常富于新意的权力分析,他将四度音程作为一种权力主体,分析了其跌宕起伏的命运。笔者认为他的分析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除此之外,中西音乐的发展历史,交错着异常复杂的权力关系,很多都可以进行权力的技术分析。比如中世纪早期奥尔加农以平行四、五度进行为主,是不是可以认为是世俗与宗教两种权力的抵牾与冲突所建构起来的一种知识形态——这种权力禁止人内心的感性骚动,而谋求与宗教仪式一起在人的内心建立一种超脱、宁静、平和的宗教情感,后来上述两种力量有了此消彼长的转化——世俗力量越来越强大,宗教力量越来越弱化,这种权力的流动导致平行五、八度的地位越来越式微,到17、18世纪,终于被弃绝、禁用,随之产生了新的知识形态——大小调调性和声。以上假设无疑只是个粗浅的假说,但有助于开拓思路,如需使这个假说更具有说服力,还需要分析这个过程是如何形成的,其中隐含了怎样的权力技术,尚需要我们做更为细致、艰苦的考证、论证。
总而言之,在笔者看来,向批评进发是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应由之路。音乐批评,一方面需要我们走进音乐——关注具体的音乐形式,也就是音乐作品的结构技法,目前国内外音乐分析学的蓬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够合理地借鉴、利用现有的资源是完全可以进入对作品内部结构的深度解析的;另一方面,音乐批评又需要我们走出音乐——关注哲学、美学、文艺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及多元批评思潮的新成果和新动态,夯实批评者自身的人文素养,并寻求内外通约的渠道。内外兼修无疑是困难的,然而惟有面对困难并挑战困难,才有可能实现超越。能力是可以慢慢培养、逐渐提高的,而观念、态度上的拒斥则会使我们永远丧失机会。
音乐批评是个开放性的学术活动,它存在极为丰富的路径和场域,惟其开放和多元,人的主体性才能得以彰显。对于强调“理解”的现代人文学科而言,主体性的彰显本身就充满魅力,本身就呈现出某种价值指向。仅以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为例,如果说仅仅立足于实证的视角,中国学者难以与西方学者比肩的话,那么在音乐批评这个领域,则可以让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进行平起平坐的对话。
音乐美学,请将目光投向音乐批评,那里一定有尽管艰苦却异彩纷呈的学术景观,它一定能让音乐美学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注释:
①[美]约瑟关·克尔曼著、朱丹丹/汤亚汀译《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
②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音乐研究》1993年第2期,第100页,又被收录于《音乐史论问题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③该文发表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第1、2期,后收入于润洋《音乐史论问题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④该文收录于《庆贺于润洋80华诞学术文集》(王次炤、韩锺恩主编),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⑤该书为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⑥于润洋《音乐美学史学论稿》,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⑦于润洋《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导言第9页。
⑧于润洋《音乐史论新稿》,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191页。
⑨同注①,第108页。
⑩[美]苏珊·朗格著、刘大基等译《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11)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
(12)同注⑦,第65页。
(13)参见拙文《浪漫主义和声的文化—美学阐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4)赵宪章主编《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页。
(1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审美之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16)同注(14),第495页。
(17)同注(14),第495—496页。
(18)同注(14),第449页。
(19)同注(14),第417页。
(20)参见拙文《〈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及终曲和声与德彪西印象主义和声的哲学—美学阐释》,《音乐研究》2011年第4期。
(21)参见拙文《弥散的星丛与否定的表现——勋伯格无调性音乐中音高关系的哲学—美学运思》,拟刊于《音乐探索》2013年第1期。
(22)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23)同注(22),第391页。
(24)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疯子尽管被视为异类,但可以和所谓正常人一起进行嬉戏,疯子的言语有时甚至被视为天启的象征。17世纪以后,则将疯子视为懒汉,而懒惰在当时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此疯子与其他罪犯一起被关进了监狱。18世纪末,疯子被人道地加以对待,从监狱里转移到了疗养院,以宗教的方式对疯子的灵魂进行感召和净化。20世纪则将疯子重新视作病人,把他们送入医院进行医治。
(25)汪民安《福柯的界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26)[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页。
(27)姚亚平《复调的产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标签: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阿多诺论文; 音乐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