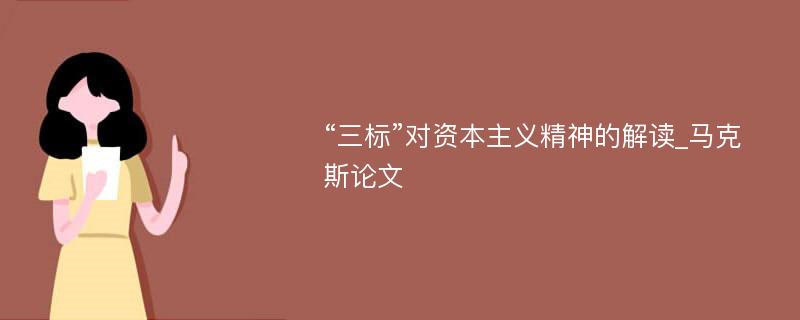
三位“马克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斯论文,资本论文,主义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是现代西方社会学家中对资本主义研究卓有成效而又影响深远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既可互相验证,又可彼此补充。三位“马克斯”对资本主义精神在现代性背景下的解读,对我们今天解读现代性精神气质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界定
韦伯、松巴特、特洛尔奇和舍勒等人共同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一问题,并把它作为现代市民伦理形成的基础。作为他们的思想先驱,马克思虽没有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但在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分析中、在资本家和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对比中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解读。韦伯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术语所适用的任何现象都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就其内容而言它指的是一种由于其独一无二的个体性才具有意味的现象,所以它不能按照‘属加种差’的公式来定义,而必须逐步逐步地把那些从历史实在中抽取出来的个别部分构成整体,从而组成这个概念”[1],而在一开始只能对它作一暂时性的描述。不难看出,韦伯这里所试图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理念型的。舍勒则着重从心理体验结构分析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与韦伯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更多地体现在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资产阶级身上不同,舍勒认为:“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中迈步向前的,……不是‘具有王者气度的商人’和组织者,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他们构成了……新的市民德行和价值体系。”[2] 而怨恨是现代市民道德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总括三位“马克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可以概括如下:
1.以职业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无限制的欲求态度和计算性的认知态度
虽然资本主义精神经常表现为对财富的贪欲,但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3],而是这种赚钱欲望是否被纳入理性化的轨道,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非理性欲望的抑制或理性的缓解,它依靠持续、理性、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把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看作是一项职业”[4],“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5]。舍勒则进一步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类型的欲望结构的鲜明特征是获取精神超出了与身份相符的生计观的界限,这种无限制的获取精神在韦伯看来,尽管在任何时代的任何个人身上都存在,但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它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坏良心”的,由于政治权力决定着财富及其活动范围,这种获取欲被迫不按规则地去进行正常经济生活之外的角逐,而在资本主义类型的欲望结构中,这种获取欲穿上了“好良心”的新装,不仅被认为是正常和正当的,而且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在义务合法性的驱使下,这种欲求态度“恰恰变成了合规律的经济生活起支配性的灵魂”[6]。为了获取超越自己现有身份的地位和财富,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出艰苦劳动精神和积极进取精神。“新的获取精神和劳动精神把中世纪——古代之世界观重视质量的凝思性认识态度变为重视数量的计算性认识态度,从而规定着世界观和科学。”[7]
韦伯认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每个人都应感到、而且确实也感到了这种义务。”[8] 马克思则更深刻地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所造成的这种职业分工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把人固定在特定的生活范围之内,妨碍了人的全面发展。“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9],韦伯的这一论点为舍勒所认同。他们认为,宗教禁欲主义不仅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把赚钱作为天职的商人和资本家,而且提供了视劳动为天职的现代工人。因而,韦伯和舍勒都把自我节制、工作勤勉的劳动者的精神气质看作是资本主义精神结构之内在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显然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也看到了宗教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中的促进作用,但他认为由于工人缺少宗教教育及其他教育,使得工人比资产者更客观,容易摆脱宗教原则的束缚。“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10]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与资产者是截然不同的人,无产阶级在本质上是具有对抗资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的,这种与资产者迥然不同的阶级意识不能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精神体系之中。
2.自我克制与享乐主义并行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韦伯借用富兰克林的自白描述了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典型。“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诚实有用,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守时、勤奋、节俭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11]“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12] 因为这种伦理的思想源头是宗教的禁欲主义。而一旦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稳固的经济地位,不再需要宗教精神的支持,“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13],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享乐主义,“所谓行善的良知只不过成了享受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手段之一”[14]。马克思也深刻指出:“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而实际上它甚至要人们把对新鲜空气或身体运动的需要都节省下来。这门关于惊人的勤劳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禁欲的科学,而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但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和禁欲的但进行生产的奴隶。……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15] 而这种禁欲主义的节俭和克制主要针对工人,它迫使工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16],变成了“文明的阴沟”[17],工人是在一种异化的、敌对的形式下退回到那里去的,“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18]。而那些“实干的、清醒的、平凡的、节俭的、看清财富本质的工业资本家也享受。他决不退回到违反自然的粗陋需要。但是他的享受仅仅是次要的事情,是一种服从于生产的休息;同时,享受是精打细算的,从而它本身是一种经济的享受,因为资本家把自己的享受也算入资本的费用。因此,他为自己的享受所花的钱只限于这笔花费能通过资本再生产而得到会带来利润的补偿。所以,享受服从于资本,享受的个人服从于资本化的个人”[19]。
3.世俗化的利己主义冲动代替了神圣的宗教形而上学动机
马克思认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随着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必然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大获全胜,也就是“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乐欲,公然无节制的、圆滑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必然战胜地方的、世故的、呆头呆脑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的利己主义”[20]。而在韦伯和舍勒看来,这种利己主义之所以获得了合理合法性,乃是因为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尘世的紧张工作原本只是为了获得来自上帝的“获救证明”的一种形式,而这种辛勤工作与禁欲主义的节制消费互相作用的客观结果是资本的积累,随着财富的增长,对尘世之爱不断增强,宗教的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根子反而慢慢枯死,发财致富的利己主义最终代替了上帝的恩宠变成了支配人们不断进取的内在动因。资产阶级“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21]。“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2] 而随着这一脱魅化过程而来的,是形而上学的内在空虚与孤独。舍勒认为,“现代人的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恰是产生向外倾泻精力的无止境活动渴望的根源和发端”[23],正是由于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无助使得人们投身于外部事务的洪流,试图用紧张填补空虚。然而,这种替代性的补偿只能是暂时的,最终人们仍将陷入空虚与无聊。
4.把手段作为目的的拜金主义价值观
韦伯不得不承认,当“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之后[24],“人竟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25]。舍勒认为,“韦伯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无限制的工作意愿和赢利意愿之诸成分的起源,与人世欢乐和享受追求相比,与对财产和财富的追求相比,更有发生性的和时间上的优先”[26]。只是这种最初带有“合义务”特征的工作欲和赢利欲最终抛弃了宗教的面具,“合法挣钱”的观念已从与上帝的关联中彻底清除掉了,挣钱本身原是为了证实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手段,最终却“成了非伦理、非宗教性的物质价值领域,并成为唯一支配生活目标的观念”[27]。马克思则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货币的特性就是货币持有者的特性,资本家的人格也就是人格化了的货币,在他们看来,货币因为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或对象相交换,因而是万能之物,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货币是最高的善”[28]。
二、资本主义起源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形式看作一个独特的具有内在必然性的社会体系,这一思想对其他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产生了根本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式可以被设想为必然对一切人类行为产生影响的统一体,其影响(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通过将人置于‘相互间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早已决定了的必然联系’而发生作用的。将资本主义视为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综合的经济体系的认识,对韦伯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让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将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看作是使纯粹个人的选择相形见绌的威力巨大的理性化力量产生的结果。”[29] 舍勒也不得不承认:“过去,勤奋基于个人的意志行动。今天,企业家被卷入经营速度之中。与此相似,节俭和讲信用成了经营业机构的内部规则……”,所谓“勤奋”、“节俭”、“讲信用”不是个人的意志行动的自主选择,而是个人不得不服从资本主义的生活秩序和游戏规则。资本主义经济好像是“一个可怜的、患偏执狂的巨人”(舍勒语),“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30],“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可谓是一个人生在其中的广漠的宇宙,他对这个人来说,至少对作为个人的他来说,是一种他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他只要涉足于那一系列的市场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31]。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一前提上,三位“马克斯”似乎没有抵牾;而资本主义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而且是生活和文化制度,资本主义的产生这一历史性的社会转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结构上,而且大大改变了人们的体验结构和精神结构,塑造着新的生活秩序和交往方式——甚至在这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三位“马克斯”也基本达到了共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才提出“两个决裂”的要求,不仅要与私有制彻底决裂,而且要与私有制观念进行彻底决裂,因为资本主义“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32],即资本主义不仅生产出物质层面的社会制度,而且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相应的观念形态。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体现在理性化的劳动组织形式、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上,更体现在“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ethos)”上。舍勒则更鲜明地提出:“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的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33] 无疑,资本主义所标志的现代历史转型是一场“总体转变”,三位“马克斯”对此并无疑义(当然,其中对此的认识以舍勒最为自觉),但在这一“总体转变”中,体验结构与经济结构在资本主义的产生中何者更具有因果关系上的优先性,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起源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与韦伯、舍勒的结论迥然不同。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学分析,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认为资本主义产生的最直接的历史前提是商品生产造成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创造剩余价值,从而产生资本。资本主义的根源和本质在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其上层建筑。而韦伯和舍勒则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看作是一种经济的唯物的决定论,认为“经济史观断言具有普遍的历史有效性的一系列历史因果关系之结构法则无疑没有错”[34],但“所有那类规律性丝毫没有如经济史理论以为的那种普遍的历史意义;当且仅当历史的主体即人还受控于典型的、被松巴特称为‘资本主义’的体验结构和欲望结构时,它才是有效的”[35],经济史观“忽视了一点,占据支配地位的观念和愿望之转型比历史现实过程之转型更带本质性”[36]。他们与马克思相反,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资本主义秩序形成之第一原因。韦伯认为,建立在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理性化的劳动组织形式和法律、行政结构,确系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深化,但“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这里的因果关系正好与按唯物主义观点得出的因果关系相反”[37],正是资本主义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所独有的组织形式和总体结构形式。在韦伯看来,“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是违背事实的”[38]。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或中世纪之所以未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三、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未来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尚没有充分发展,还存有早期原始积累的野蛮遗痕,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更多地表现为绝对贫困,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带有强烈的道德激情和意识形态色彩,批判的矛头虽不乏精神层面,但焦点无疑是经济制度,因为经济制度是导致一切精神异化的根源。而韦伯和舍勒则一个从历史社会学入手,一个遵循现象学社会学方法,深入揭示了精神文化气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他们对经济和社会现代性起源的解释,有助于历史学家将关注的焦点从传统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和技术起源,转移到其文化、知识、心理以及社会宗教的起源。”[39] 正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起源的见解不同,所以尽管他们都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表现出某种人文主义的忧虑,但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前景预测却是大不相同的,针对资本主义的精神疾病,他们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疗救药方。
马克思一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解放生产力的伟力,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资本主义也导致了人与人的类本质、人与自然的全面的异化,而这种异化是自我异化。
舍勒提出了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似的陌化概念:认为构成资本主义生活秩序之特色的全部力量,“只能基于对一切精神之本质力量的极度反常之上,只能基于对一切富有意义的价值秩序的癫狂般的颠覆之上,而不能基于属于‘人的’正常‘天性’的精神力量之上”[40],它对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深深的陌化。韦伯虽然执守作为社会学家的价值中立立场,但也不无悲观地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化,作为其精神源头的禁欲主义宗教伦理已被融入功利主义的世俗道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41],人类注定要堕入资本主义的“铁的牢笼”,“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42] 尽管舍勒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批判与马克思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对资本主义未来的设想却与马克思并不一致。
舍勒认为,既然资本主义制度起源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类型的精神气质,那么便已不可能指望资本主义在现存经济财产的私有制、生产—分配制发生某种变化(这是所有社会主义政党所要求和期望的)之后会告消失。而无产阶级的阶级精神由于诞育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活动空间内部,只能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种特定变种,因而不能指望资本主义精神会因无产阶级运动而彻底没落。舍勒认为资本者类型本身的内在法则将导致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那一类型的人逐渐灭种,而独立于培育资本主义精神的官方机构之外的新的文化思想将可望克服作为文化制度的资本主义。为了重建被资本主义精神颠覆了的人心秩序,作为基督教思想家的舍勒,提出建立一种基于“共契主义”的“爱的共同体”。
标签:马克斯论文; 韦伯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