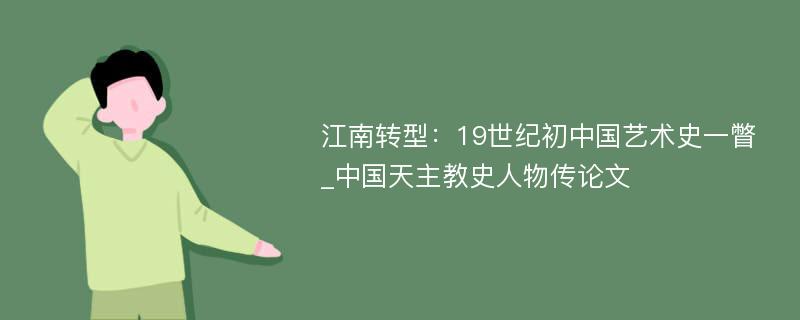
江南蜕变——19至20世纪初中国艺术史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初中论文,艺术史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近世之画衰败极矣”(注:康有为:《万木草堂藏中国画目序》,文史哲出版社,台北,1997。),“清代无画论”(注:陈小蝶《清代无画论》,《国画月刊》,第2期,第18-19页;第3期,第37页,上海,1934。),到“19世纪中国画创造力耗尽”说(注:"From about the year 1800 on,painting in China became rather repetitive;the creative force was spent",sherman E.Lee:A History or Far E-astern Art,P.456,Prentice-Hall,Inc,N.J.& Harry N.Abrams,Inc.New York,1973.),诸多先入为主的结论,曾阻碍了对中国近代绘画史的研究,致使这段最近的历史,变成一座似乎难以辨识的雾中远山。虽然,近30年来,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研究成果,也带动了19世纪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但是时间上大多限于1840年以后(注:19世纪上半叶的个案研究少见,如赵力《京江画派研究》,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通史见拙著,《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台北《雄狮美术》,254期起连载,278期终止。),地域上则仅以上海为热门。或许,这次“江南”研讨会可以推动研究范围有所扩展。
本人认为,在19世纪,甚至18世纪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尚处于十分薄弱、大量的历史空白有待个案研究成果填补的当前,对本世纪中国艺术发展的理解必然受到局限。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若干变革,并非是近百年突然发生,而植根于19世纪,甚至18世纪,是中国社会、经济、观念、文化长期历史转型过程的派生物。本文以江南地区为例,简要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考察,与各位同仁讨论。
一
儒学作为18、19世纪中国的主导思想,自身经历了深刻变革。清初大儒博学不尚空谈,躬行道德气节,倡导经世致用之学;雍正、乾隆时代(1723-1796)文字狱窒酷之下,学者纷纷避祸而转向考古;乾隆、嘉庆(1736-1820)时期以降,则所谓“汉学”(实为“考据学”)盛行(注: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二编第25章及第3编第7章,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1988年第1版。);至清末《春秋》公羊学复兴。成为维新变法的学术依据(注:参见韦政通《中国19世纪思想史》下册第3章,东大图书公司,台北,1991年初版。)。在清代儒学的发展中,清初大儒的明道救世精神,以及乾、嘉之学的考史征实风气,看似矛盾却又相互依存,在19世纪后期国运衰微、内外交困的危机中,融汇为图存求变,接受西学的思想基础。
在这一背景之下,某些直接与艺术相关的观念及文化方面的变革,是值得注意的,这里仅举两例:一是儒家“农本商末”的轻商思想转变为“重商主义”(注:明末黄宗羲即有“工商皆本”的主张;而徽商的“贾而好儒”,“亦贾亦儒”倾向,尤其反映了时代观念的变化;至清末郑观应(1842-1921)则由江南名商而参政,成为近代史上重要思想家,主张“以商为本”是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所著《盛世危言》,影响深远。);二是考据学衍生出的碑学理论及金石学盛行。前者反映了城镇经济及以商贾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的崛起,市民阶层是接受西学,图变求强的社会基础;后者引发了时代审美观念的改变,孕育出不同已往的艺术风貌。
中国虽然号称农业帝国,但是,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却仅占全部领土的不足十分之一。(注:翁之镛《中国经济问题探源》,第36页,正中书局,台北,1965。)清代至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人口已超过四亿,其中四分之三以上集中于东南地区,以江南为最。战乱灾荒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不仅是农民增加补充了城镇工商业劳力,同时也有部分地主转化为商贾。城镇经济每为资本雄厚的巨商富贾所左右,如斥资买下贩盐专利的盐商;掌握金融流通的票商;控制某一行业的行商等,成为市民阶层中的最有势力的核心集团。他们对文教事业的参与,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我认为,以商贾为代表的新兴市民阶层并不仅仅是扮演着艺术赞助人的角色(如盐商对扬州画家;徽商对新安画家等),而是走上前台,直接参与艺术创作,甚至成为开派人物或艺坛领袖。被尊为“西冷八家”之首的丁敬(1675-1764),金石学家,是影响印学200年之久的浙派印章的创始人,被认为是扫尽“工细秀媚”的明人习气,开一代“浑厚醇古”新风的印坛领袖,而他本人则是位酒商。史载丁敬“家杭州候潮门外,邻保皆野人也,酿曲蕖自给,身侧佣贩,未尝自异”。(注:《杭州府志》,光绪版。)金农(1687-1764)曾是丁敬同乡近邻,“相距一鸡飞之舍”,据记载,两人都曾以倒卖古董为生。(注:杭世骏《道古堂集》,乾隆五十七年(1792)版。邓之诚:《骨董琐记》,“金冬心”:“盖当时钝丁、寿门,恃买卖骨董为生”。)除了经济来源及社会阶层的差异之外,如丁敬、金农等人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也与传统(或“笼统”)的文人(仕则食官俸;隐则靠田产)不同。文人的教育以经学为核心,元末到明清两代,程朱理学官方化,科举考试以朱熹注疏为主要内容。理学虽在清初彦元(1635-1704)、李塨(1659-1733)的时代已告尾声,同时“乾嘉学派”渐兴(实渊源于元明宗汉学之非官方学派)但是清廷则死守理学,箝制思想。文网之下,学者转向考据训诂,蔚为风气。同时,尚有部分人专修小学(文字学)等科,其中颇有浸淫书法、篆刻终老而有成者,如程邃(1607-1692)、丁敬、邓石如(1743-1805)等。这些“布衣”的学问,即所谓“金石学”,与科举考试并无直接关系,属朴学思潮派生出的某种“专门知识”,涉及小学(文字学),颇有些类似医药、堪舆、数术、营造之类;所不同者,因举业习经学之仕大夫当时亦多热衷此道,故金石家寄附攀交,混交其间,引为风雅。康熙、乾隆先后两次设博学鸿词科,未仕
者亦可经内外大臣举荐赴内廷应试,实际上是为笼络别有专才的人网开一面。程邃等不就,誉为逸民固有之。而金农等不中(未考上也),恐与其学窄而欠博亦有关。如清代印人中,不少“布衣”,号称金石家,实为高级职业刻工,并不比市井朗郎中、风水先生、刀笔师爷能高出多少,他们应属市民专业阶层,与传统意义的文人是有区别的。即使从文人官僚中擅长治印而有成者,如陈鸿寿(1768-1822)与陶工杨彭年兄妹及邵二泉合作制紫沙壶的事迹中,也可以感受到市民阶层地位的上升,以及文人阶层的观念变化。19世纪初,擅画的镇江殷实布商张自坤(1734-1791),培养其子张崟(1761-1829)别开生面,另辟畦径,以“浑噩苍郁”的独特画风,成为京江画派之首。(注:19世纪上半叶的个案研究少见,如赵力《京江画派研究》,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通史见拙著,《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台北《雄狮美术》,254期起连载,278期终止。)而出于绍兴破产商人之家的赵之谦(1829-1884)则以北碑入画,融诗书画印为一炉,被推崇为“金石画派”第一家。如果文人出身的画家钱东(1752-1817)“弃儒从商”的事例,在18世纪末寓居扬州的画家中尚不多见,那么到了20世纪初的中国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被称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的蔡元培(1868-1940)也曾在巴黎开过豆腐店。(注:冯治、刘永彪《民国名人轶闻录》,第9页,江西古籍出版社,1992。)同样,本世纪山水画大师黄宾虹(1865-1955)先生也曾在青年时代作过字画买卖,而且于1915年在上海正式开办“宙合斋”,经营古董生意。继吴昌硕(1844-1927)之后成为上海画坛领袖的王震(1867-1938),为众所周知的洋行买办。(注:《中国近代画家图录》,条11,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香港,1992。)而王震之后,另一位上海画坛的重要人物,画家兼美术史家郑昶(1894-1952),同时又是首创汉文正楷活字,创办汉文正楷印书局的出版商。(注:《中国近代画家图录》,条25,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香港,1992。)而被称为民国初年北京画坛“教主”的浙江人金城(1878-1926),本人集官僚、买办于一身,还开过古董店。(注:“金拱北先生事略”,《湖社月刊》,1-10合册。)笼统地称上述这些人为“文人”画家或艺术家,似乎是不够恰当的。他们的艺术风格以“古拙”、“沉厚”、“雄强”为共同特征,有意在“娄东”、“虞山”文人画正宗传统之外,另张旗帜,应该说是至少表达了市民阶层中的部分知识分子的审美追求。(注:如张崟
跋《戏法娄东山水轴》:“吾润(镇江别称)画家家自为法,未专一宗娄东。”又如自跋山水:“元人尽弃宋人习气……所谓浑噩苍郁存。白石翁法自梅花道人,而又别出浑噩之气,所以有明一代画家之冠。峭拔如唐子畏,细秀仇十洲,皆不能超其上。可见书画以古朴为最,能为次也。”(以上两件作品均为镇江市博物馆收藏)所谓“市民趣味”有丰富包容,不仅仅是体现在“俗”或“狂怪”等特征之中,不应一概而论。(注:王原祁《麓台画跋》中所谓“广陵、白下,其恶习与浙派无异”,广陵白下指扬州镇江一带,这里所批评的是浙派枯硬刻露的笔墨风格对后世影响,并把扬州镇江一带流行的画风划为同类,却也反映了某种市民所好尚的刚健痛快的视觉效果。)
二
中国的书法艺术在清代取得了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进展,甚至被称为“书学革命”,无论是时代风格或审美标准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对绘画及其他视觉艺术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书法方面的“碑学理论”,绘画方面的“金石”趣味,以及篆刻艺术的流派纷呈,是清代汉学和考据学成就的衍生物,是近代中国艺术史的重要成就之一。这一成就是中国本土自发产生的,并非“西方文化冲击”的产物;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延续到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重要成就,至今并未受到充分的估价。
虽然,明末书法有相当成就,但基本上仍是延续晋唐传统。(注:通史见拙著,《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台北《雄狮美术》,第264期,第113-120页。)清初考据学渐兴,在访古校碑风气之下,不少书家转向铜器铭文(金)及碑刻(石)等,开始古体文字的研习,古籀秦篆,汉隶魏楷成为新的书法范本。对古风的热衷,引发了审美观念的变化。明末清初的傅山(1607-1684),堪称是这一审美观念转化的先驱之一。傅山对金石学有研究,书法亦从篆隶中吸取古意,他的草书有朴拙气息,写篆隶则带草书笔意,正统书家则谓之“怪”。傅山在论书文字中,反复强调学习篆隶的重要,曾谓:“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注:傅山《霜红龛全集》,丁宝全刊本,卷二十五。)又批评明末流行的所谓“南董、北米”(注:董,即董其昌(1555-1637);米,即米万钟(1570-1628)。)书风,是“董则清媚,米又肥靡”。在傅山的审美标准中,“媚”、“肥”是很低下的境界。“熟媚绰约,自是溅态”,“肥字可厌”。从而明确提出了“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的审美原则。(注:傅山《霜红龛全集》,丁宝全刊本,卷四。)“拙”、“丑”、“支离”、“直率”,这些特征在18世纪及其以后的艺术作品中日见明显,而金农、郑燮(1693-1765)、高凤翰(1683-1748)等扬州画家的书法和绘画,则标志着这一“艺术新潮”的开始。康有为(1858-1927)说:“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金农)、板桥(郑燮)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如果说,金农的“漆书”和郑燮的“六分半书”尚带有“安排”做作的痕迹而不够“直率”自然的话,那末金农绘画的“拙”则可以说是天趣与金石学养的自然流露。至19世纪初,“碑学”已渐成优势,又经阮元(1764-1849)、包世臣(1775-1855)、康有为(1858-1927)等人的理论鼓吹,褒碑贬贴,尊魏卑唐,造成时代书风的深刻变革。“书学革命”也带动了绘画的变革,以篆、隶、魏碑书法笔意入画,讲究金石趣味,重视画面布白、平衡对比,成为画家的普遍艺术追求。所谓“金石画派”于是应运而生,以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1864-1957)等为代表,从19世纪中期发展到20世纪。上述三位“金石画派”的大师,诗书画之外,又精于篆刻,而且各自开创印学流派,影响甚著,从而把传统中国画的“三绝”发展到诗、书、画、印“四全”。即使本身不以篆刻著名的画家,亦
同样受到碑学书法的陶冶,如本世纪陈师曾(1876-1923)、吕凤子(1885-1959)、潘天寿(1897-1971)、张大千(1899-1983)等。甚至擅长西画的美术教育家徐悲鸿(1895-1953)和刘海粟(1896-1994),也曾经同是康有为的书学弟子。至于碑派书家更是多不胜数,其中以何绍基(1799-1873)最受推崇,被称为“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注:杨翰《息柯杂著》,苏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甚至与王羲之相提并论,成为划时代的界碑。他的行草作品,可以说是完全实现了傅山所倡导的标准,实现了从以端庄、娟秀、柔媚、娴雅、流宕为主导特征的一千数百年的书法传统,向奇崛、朴茂、雄强、稚拙、沉涩的新时代书风的转化。
在这审美观念转化的背后,是面对清庭腐败,国祚衰微,艺术家奋起追求雄强风格的心理感应。
三
西方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催化了近代中国艺术的蜕变。18世纪传教士供奉清廷的史实已是为人所熟知;然而,可能并不如过去所理解的那样:在当时,西洋画的传播仅仅限于宫墙之内。(注: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通史》,卷,第14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1988;参见《故宫博物院清代宫廷绘画》,文物出版社,北京,1995。)早在17世纪初,圣像及宗教书籍的版画插图已经在宫墙外与平民接触,成为有效传教的工具。(注:中文译本《利玛窦全集》(罗光译)卷四,第405页,光启出版社,上海,1996。)信徒人数迅速扩大,由1596年的百余人,发展到明亡前后(1644)二十几万人,有传教所四十余处,遍布十数省。(注:熊月之《晚清社会与西学东渐》,第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期间,由于传教的需要,已经在中国境内绘制圣像,已知的传教士兼绘圣像的,如生于澳门死于杭州的游文辉(Pereira Yeou,1557-1633),生于日本,1602年来华的中日混血儿倪雅俗(Jacpues Niva,1579-1638)等。(注: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166页,中华书局,北京,1988;另见荣振华《在华耶苏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耶升译),第495页,中华书局,1995。)而18世纪的苏州姚花坞木版画(注:《中国洋风画展——明末至清代的绘画、版画、插图本》(图录),第376页,町田市国际版画美术馆,日本,1995。),流行江南的“西洋镜”画(注:“江宁人造方圆木匣,中点花树鱼禽,怪神秘戏之类,外开圆孔蒙,以五色玳瑁。一目窥之,障小为大,谓之西洋镜。”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北京,1960。)、风俗画等(注:熊月之《晚清社会与西学东渐》,第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已经明显看出西洋画明暗透视法的影响。(注:参见Michael Sullivan,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II.From the Sixteen Centuryto the Present Day),Graphic Society,New York,1973.)而在中国艺术史的文献中,也有擅长西洋画法的画家记载,如张恕(注:“张恕,字近仁,工泰西画法,自近而远,自大而小,毫厘皆准法则;虽泰西人无能出其右。”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166页,中华书局,北京,1988;另见荣振华《在华耶苏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耶升译),第495页,中华书局,1995。卷2,草河录·下。)、丁允泰、丁瑜(注:“丁允泰,钱塘人,工写真,一尊西洋烘染法。其女丁瑜,守其家学,专精人物……”《国朝画征续录》卷下,画史丛书(3),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3。)等。而18世纪时,广东沿海口岸城市的洋画作坊已经相当活跃,其产品远销欧、美。(注:参见拙作《画家与画史·广州外销画简史》,第158-172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杭州,1997。)19世纪中期,天主教在上海设立了生产传教用品的工艺工场,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培养了至少百余名油画、版画、雕塑人才。(注:参见张弘星《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摇篮——上海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艺术事业》,《东南文化》,5,124-130;另见拙作《中国西洋画的摇篮》,“张恕,字近仁,工泰西画法,自近而远,自大而小,毫厘皆准法则;虽泰西人无能出其右。”第148-157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166页,中华书局,北京,1988;另见荣振华《在华耶苏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耶升译),卷2,草河录·下。中华书局,1995。)其中有些成为中国早期商业广告、私立美术教育等行业的先驱,如周湘(1871-1933)、张聿光(1855-1966)、徐咏青(1880-1953)、杭樨英(1900-1947)、张充仁(1907-)等。本世纪初期,西方写实绘画的技术已广泛用于商业广告、月份牌画、市民家中附庸风雅的“八破”画等。(注:Nancy Berliner:"The' Eight Brokens' Chinese Trompe-I' oeil Painting",Ori-entations,(Hong Kong),vol.23,no.2,(February 1992),pp.61-70.)在康有为、蔡元培、陈独秀(1879-1942)等人提倡美术“改良主义”及“融合中西”的同时,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社会实践。而这种源于上海和江南地区的商业西洋画风,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只不过包装技术更为漂亮而已。但是,这些拍卖市场推出的精致行活,内涵却显得贫乏肤浅,与本世纪初的上海商业宣传画相比,明显是缺少当年文学、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等丰富的文化背景。
19世纪“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主要成果,是促成了中国教育制度的根本改革。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学校参西法改制,设小学、中学、高等学府,实用科技知识在总课程中占绝大比重,而以前旧学中占绝大比重的经学则减少到七分之一,标志着旧学的结束。由于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历来以经学为主考内容的科举制度陷入危机,致使清政府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不得不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注:参见《光绪政要》、《光绪朝东华录》。)自隋唐以来延续了一千四百余年的科举制度终于结束了,新式教育体系的确立,知识结构的改变,和文官制度的形成,也标志着存在数千年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从此解体消亡。本世纪初,留学日本、欧、美的美术家成为中国美术教育制度的主要创建者,他们对近代中国艺术蜕变所起的作用是大家所熟知的。江南地区对近代中国美术史的贡献和影响,是尤其值得研究的课题。例如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上海、杭州、苏州等江南城市曾出现过数百个艺术社团,可以说是居全国之冠。1861至1869年之间在北京出现的第一个书画组织“松筠庵画社”,即是由参加过上海“萍花书画会”(1851年成立)的无锡人秦炳文(1803-1873)参与组织的。(注:通史见拙著,《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台北《雄狮美术》,第274期。103页。)1915年江南人汤定之(1878-1946)与余绍宋(1882-1949)在北京发起组织“宣南画社”,广集京城名家。(注:黄萍孙《余绍宋其人其事》,《朵云》第12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20世纪初居北京,在近代中国艺术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中,不少为南方人。其中以江南人为多,如蔡元培、陈汉第(1874-1954)、陈半丁(1876-1969)、汤定之(1878-1946)、金城、周肇祥(1880-1954)、鲁迅(1881-1936)、余绍宋、俞明(1884-1935)、寿石工(1885-1950)、徐悲鸿等,但是其中不少人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其实,有待研究的课题简直是太多了。
不过,以西方的艺术理论套用中国艺术史,发一番聪明的带有结论性的批评,是目前美术史界颇为时髦的学风。我以为,在所知极为有限,大量历史空白有待填补的中国艺术史领域,多作些发掘第一手材料和原创性的个案研究乃是当务之急。有时候,或许暂时离理论远一些,反而会离事实近一些。
(该文系作者应邀在1998年加拿大温哥华“江南”国际研讨会主题发言的中文本,虽较英文本简略,但是更能确切表达作者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