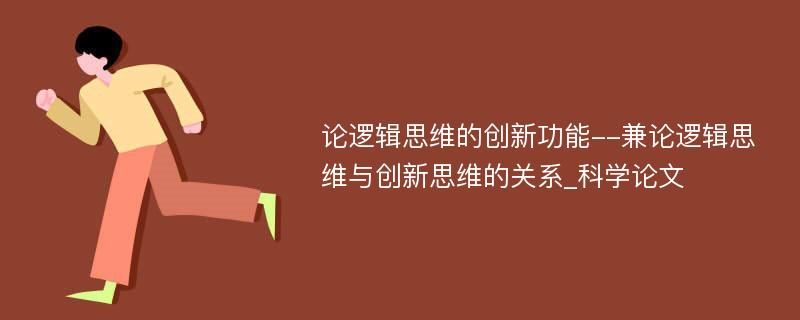
论逻辑思维的创新功能——兼论逻辑思维与创新思维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思维论文,创新思维论文,关系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1)01-0013-04
逻辑思维是否有创新功能?它在科学创造中地位如何?这是逻辑界和思维学界长期讨论的问题。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逻辑思维是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任何科学发明创造都是逻辑思维的结果。如古希腊许多学者就认为任何科学都是按照欧几里得的逻辑思维模式建立起来的;17世纪德国数学家、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莱布尼茨更是认为一切思维活动都按照逻辑进行,他曾设想只要有一套“通用语言”和一套严格的“演算规则”,当人们遇到任何难题时都不必争论,只要坐下来进行逻辑演算,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另一种观点认为逻辑思维没有创新功能,一切科学发现都不是通过逻辑思维,完全是非理性、超逻辑的心理过程,直觉、灵感、联想等便属于超逻辑的思维形式。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就认为科学创新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直觉”,是“超乎人类理智,也超乎客观世界的认识。”(注:刘放桐主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3页。)法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彭加勒更是明确:纯粹逻辑对于科学创新不是“如虎添翼”,而是“仅有牵制之累”,“纯粹逻辑始终只能把我们引向同义反复,它不会创造任何新的东西,本身不能提供任何科学的原理。”(注:《南京社会科学》(经济哲学版),1995年第5期,第32页。)现在,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已经很少了,但同意第二种观点的还大有人在,国内有位学者说:“科学创造性思维是一种以非经验、超逻辑和思维程序与常规思维相倒置为根本特征的反常思维方式。”(注:杨耀坤:《科学创造思维:内涵、形式、机理》,《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6期,第107页。)笔者认为把逻辑思维奉为科学创造中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当然是不对的,但说逻辑思维完全是“同义反复”,没有创新功能则失之偏颇,逻辑思维不但自身有创新功能,而且还是直觉、灵感、联想等创新思维方式的前提和基础。
一、逻辑思维自身有创新功能
什么是逻辑思维?这个问题学术界有着各种不同的回答(美国逻辑学家皮尔士说逻辑有上百个不同定义),不过按传统逻辑的一般观点,所谓逻辑思维是指人脑的一种理性活动,思维主体把感性认识阶段获得的对事物认识的信息材料抽象成概念,运用概念进行判断,用判断按一定逻辑关系进行推理,从而产生新的思想认识,人脑的这种活动过程就是逻辑思维。简单说,概念的形成过程是逻辑思维,对概念进行分析后作出判断是逻辑思维,运用判断进行推理也是逻辑思维。逻辑思维的特点是规范性、严密性、确定性和可重复性,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判断的含义和结构、推理的过程都是规范的、严密的和确定的,而且可重复整个思维过程。有人认为“逻辑思维因为过于规范化、形式化,而限制了人们思维的发散性、想象力,限制了思维建构的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注:黄爱民:《浅论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探求》1994年第3期,第44页。)这是偏颇的,逻辑思维虽具有规范性、形式化等特点,但并不是纯粹抽象的符号和推理游戏,它是人们在实际思维过程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关于思维的模式、规律和规则,是“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33页。),它不但没有限制人的思维的创新性,相反,逻辑思维自身有着很强的创新功能。
第一,从历史来看,逻辑思维方式的变革往往引来科学技术的繁荣。任何科学理论的创立都是对旧理论的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科学都具有创新性。而任何科学都离不开逻辑,黑格尔说:“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16页。)爱因斯坦也说到:科学家必须是“严谨的逻辑推理者。科学家的目的是要得到关于自然界的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摹写。逻辑之对于它,有如比例和透视规律之对于画家一样。”(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99、304、574页。)因此历史上的科学革命运动往往以逻辑思维的发展为先导。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演绎逻辑的诞生,带来了古希腊人文和自然科学空前的繁荣;培根归纳逻辑的创立,掀起了近代科学革命的狂飙;而现代逻辑的出现,则促进了现代科学和哲学全方位的拓展……这些都说明逻辑思维对科学创造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第二,逻辑思维是知识、技术转为科学理论的必经之路。英国已故著名学者李约瑟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科技史,他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中国人在古代取得过许多卓越的科技成就,但近代为什么科学却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发生在中国呢?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和兴趣,爱因斯坦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可能的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99、304、574页。)台湾已故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曾说:“古代中国赢过西方的,大多是技术而不是科学,没有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发展是有限的。”,“科学与技术不能混为一谈,由于对科学与技术的分际认识不清,以致科学思想的扎根工作长期被忽视了,这才是中国长久以来科学发展不及西方的原因。”(注:詹克明·李约琴《难题与吴大猷疑惑》,《杂文报》1996年11月19日第2版。)上海青年学者詹克明也认为:“科学是探索未知世界,揭示大自然客观规律,而技术则主要是利用自己已知的科学知识,解决人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果把科学和技术加以分别考察,就纯科学而言,中国古代科学从来没有真正发达过,而且历来还有注重实际应用,轻视基础科学的倾向,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堪称伟大的技术发明,但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却找不出任何完整的学术体系和重大的科学理论。”(注:詹克明·李约琴《难题与吴大猷疑惑》,《杂文报》1996年11月19日第2版。)总之,一些具体知识也许可以在实际生活和劳动中偶然获得,但要获得对未知世界的规律的认识就必须进行艰苦、复杂的逻辑分析、推论,从而最终形成针对某一问题的知识体系,离开逻辑思维,知识、技术是片面的、离散的,不能整合成科学理论,只有逻辑思维的加入,才能最终完成科学体系。
第三,逻辑思维的具体方式本身就具有创新功能。逻辑思维的具体方式主要是概念、判断和推理,概念作为反映事物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通过对许许多多具体事物进行分析、比较、鉴别之后才能抽象出该事物的特有属性(或本属属性),这种反映不是机械的摹写,而是一种创新,感性认识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但逻辑思维便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没有概念思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片面的、现象的层面上,无法全面把握事物的本质;判断是对事物情况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作为逻辑思维形式的判断不同于直接陈述感官所反映的情况,它是经过逻辑分析加工整理后才对事物情况作出断定,这种断定相对于简单的陈述而言就是一种创新。如一位农学家来到某地考察畜牧业发展情况,当地人向他咨询能否发展养羊业,他说“要养羊先养猫”,这个判断体现了农学家与众不同的眼光,当众人疑惑不解时,他说:“要养羊最好是大量种植三叶草,但三叶草要靠蜜蜂传粉,而本地田鼠太多,蜜蜂巢被破坏严重,影响了三叶草的发展,所以应先养猫灭鼠。”由此可见任何逻辑判断都不是简单重复所见所闻,而是有逻辑分析的一种主观断定,本身具有创新的特征;推理是从已知的经验知识推出未知知识的逻辑思维形式。逻辑推理主要有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三种。
演绎推理以其严密性、精巧性、必然性、确定性奠定了其在逻辑学中的重要地位,它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不但科学探索过程的逻辑分析、论证需要演绎逻辑,就是在新观点提出时也常常依靠演绎逻辑。如关于物体重量与其下降速度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的重量与其下降速度成正比”,即物体重量越大,其下降速度越快。这个观点在一千多年里没有受到丝毫怀疑,到了十六世纪意大利科学家伽俐略对该观点提出挑战,认为物体的重量与其下降速度没有正比关系,物体不论轻重,其下降速度相同。他的逻辑论证是这样:若把重量大小悬殊的两个物体捆绑在一起,设A为重物体,B为轻物体,A与B捆绑丢下,其下降速度是比A物单独丢下时快还是慢呢?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A和B相加重量加大,其速度会加快,但两个物体重量悬殊,其下降速度也悬殊,这样就象一辆快车后面拖着一辆慢车,快车便快不起来,所以A、B两物体捆在一起其下降速度比A物体单独落下要慢,于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出现了不可解的逻辑矛盾,最后被否定了。伽俐略曾感慨地说:在真理面前,一千个权威抵不上一个谦恭的逻辑推理。在科学史上,“氧化说”取代“燃素说”,“摩擦说”取代“热素说”,“日心说”战胜“地心说”等等无不闪耀着演绎逻辑的光辉。
归纳推理是一种极富创新功能的推理方法,其特点是由个别经验知识直接推出一般知识,作为结论的“一般知识”相对于作为前提的“个别知识”来说是全新的知识,如人们发现金能导电、导热,银、铜、铝、铅、铁、锌等亦如此,金、银、铜、铁、铝、铅、锌等是金属的一部分,由此人们断定:所有金属都具有导电、导热的特征。可见归纳推理自身就是一种创新思维方法。
类比推理也属于一种创新思维方法。它的特点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一系列属性上相同(或相异),从而断定这两个(或两类)对象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异)。用来比较的属性是已知知识,是原有知识,而断定其另外的属性也相同则是全新知识,是创新思维。如哈维提出人体血液循环理论时就是根据对一条蛇的解剖观察,发现当蛇的动脉被夹紧后,蛇心由于充血变大、变紫,松开动脉则正常,夹住其静脉,蛇心由于缺血而变瘪、变白,松开则正常,由蛇推及人,于是哈维提出“人体血液循环”的观点,否定了流行了两千多年的“人体血液由心脏生产供全身器官消耗”的“血液单向运动”的说法。哈维的“人体亦如是”是新观点,属创新思维。
二、逻辑思维是直觉、灵感、联想的前提和基础
直觉、灵感、联想通常被称为非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如有些学者认为:“非逻辑思维主要包括幻想、想象、直觉和灵感……如果形式逻辑的功能在于‘发现’,那么,非逻辑思维的功能则在于‘突破’和‘创新’。”(注:刘奎林、杨秀珍:《论非逻辑思维》,《理论探讨》1997年第5期,第59页。)直觉、灵感和联想在创新思维活动中确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不能把它们理解成创新思维的全部,也不能把它们与逻辑思维完全对立起来,不能说逻辑思维不是创新思维,直觉、灵感、联想才是创新思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创新思维、直觉、灵感、联想的含义。
什么是创新思维?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看法,一般认为创新思维是一种敢于打破传统观念,冲破旧的条条框框,大胆提出新见解的思维现象。有人称之为“打破现状思维”,并认为这种思维有独特性、系统性、展开目的性等(注:陈颖健:《打破现状思维的概念引入》,《中国科技信息》1997年第16期。)。
什么是直觉、灵感与联想呢?直觉是哲学和心理学术语,虽然人们对直觉的含义的理解和表述各不相同,但一般认为直觉是指不经过逻辑推理就能直接认识真理的能力,是一种突然对事物达到深入洞察和本质理解的思维活动;灵感原是文学创作用语,指文学家在创作过程中出现的思想高度活跃、敏锐的精神状态。以后把它推广到创新思维活动,当人们对某一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时,由于某种偶然因素的诱导,思维变得极度活跃,注意力高度集中,对所思考的问题出现了“顿悟”。有人就把这种灵感等同于“顿悟”。其实“顿悟”是佛教用语,佛教认为“最高真理”不能分割,对它的觉悟也不能分阶段进行,只能靠“顿悟”实现对“最高真理”的把握。灵感会出现顿悟,但顿悟不等于灵感。联想是由此及彼的思维活动,即由一个现实的刺激(可以是实际的事物也可以是语言、符号等)引起对其它事物的映象或想象。这里的“其他事物”既可以是经验以内的也可以是经验以外的,可以是已知的也可以是未知的。
综上所述,只要人们不受旧观念、旧规则的约束,敢于思考,敢于创造,敢于突破现状都可称为创新思维。逻辑思维由于突破了原有的知识范围,推导出了新知识、新见解,因而其本身就是创新思维;直觉、灵感、联想等“非逻辑思维”由于常常与新思想、新见解、新概念相互联系而被人们称为创新思维。当然这里把直觉、灵感、联想称为“非逻辑思维”并不是说直觉、灵感和联想与逻辑思维是水火不相容、完全对立的矛盾关系,相反,直觉、灵感和联想必须以逻辑思维作为前提和基础,理由是:
第一,直觉、灵感、联想是在艰苦的逻辑思维过程中产生的。在人类发明创造史上,直觉、灵感、联想的作用屡见不鲜,阿基米德泡在浴缸中悟出了浮力定律;牛顿被树上落下的苹果砸了脑袋而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门捷列夫在右脚踏上火车的刹那悟出了元素周期表;凯库勒梦见蛇自咬尾巴悟出苯的分子结构等等。然而这些科学家们真的仅靠直觉、灵感和联想顿悟出科学真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无论他们各自的顿悟过程是多么奇特有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顿悟之前他们都一直在苦苦思索某一问题,曾进行过千万次的逻辑分析、推理、论证,如门捷列夫曾三天三夜未合眼地思考和计算;牛顿在实验室里忘记了自己是否已经进餐;凯库勒在参加舞会时仍在想着他的苯分子结构……可以说若没有逻辑思维作准备,直觉、灵感、联想便不会降临,当然也无法“顿悟”出科学真理。正如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说过那样:“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邦格也说:“没有漫长而且有耐心的演绎推论,就没有丰富的直觉。”(注:《南京社会科学》(经济哲学版),1995年第5期,第35页。)
第二,逻辑思维为直觉、灵感和联想确定目标和方向。直觉、灵感和联想只有指向一定目标和方向,才能称为科学创新中的直觉、灵感和联想。而为直觉、灵感和联想确定目标和方向的,正是逻辑思维。正如葛润林说的那样:“在紧张的创造思维活动中,没有逻辑,思维就会失去方向,失去目标;没有逻辑就没有道路。任何直觉、想象、联想等,如果是有目标的,那只能是在逻辑思维指引和统率下进行的,如果离开逻辑思维,就等于是神经错乱,或者是裂脑人的互相矛盾的杂乱的思维。”(注:葛润林:《论假说的逻辑结构及其在思维形式系统中的地位》,人大复印资料《逻辑》1997年第7期,第23页。)
第三,通过直觉、灵感、联想产生的结论和新概念需要作逻辑的分析、论证。直觉、灵感和联想的特点是没有清晰的逻辑思路,‘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是如果对一个新思想、新概念没有作出(或不能作出)逻辑上的解释和论证,人们就不会接受它,而且它也可能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想象或幻想,因此直觉、灵感和联想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逻辑的分析、加工、整理,只有把直觉、灵感和联想的结论和新概念进行逻辑加工才能使它成为一个论证严密的科学观点,因此凯库勒曾风趣地说:“先生们,假使我们学会做梦,我们也许就会发现真理,不过我们务必要小心,在我们的梦受到清醒头脑证实之前,千万别公开它们。”(注:《南京社会科学》(经济哲学版),1995年第5期,第35页。)
第四,直觉、灵感和联想是逻辑思维的“中断”和“对接”,是逻辑思维过程的高度压缩。直觉、灵感和联想因为常常在极短的瞬间产生新思想,思维者自身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奇妙的巧合,所以常常觉得神奇,疑有神助。其实若能了解直觉、灵感和联想产生的过程,其神秘性就会荡然无存。任何直觉、灵感、联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直觉不过是思维者在无意识状态下调动了记忆库中的知识组块,进行跳跃式的逻辑思维,把逻辑思维逐步进行的逻辑推理程序进行了高度压缩,简化成为对问题的一种直接判断而已。比如一个经验丰富的将军,由于头脑中积累了大量的军事经验和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在大脑中被整理储存,遇到情况这些知识被迅速调动起来,帮助他进行快速的逻辑分析,使他能当机立断,而下级的参谋人员遇到问题则只能按部就班地运用逻辑思维,反复进行分析、推理、思考、论证。同样,经验丰富的商人能迅速捕捉到市场商机,而商学院的学生则要按部就班地进行调查、统计、整理、分析,甚至花了很长时间仍不能准确把握市场态势。由此可见直觉不是“凭空”获得,它是思维者逻辑思维的跳跃和压缩;灵感发生顿悟时总有某种偶然的因素充当媒介,使“中断”了的逻辑思路得以“对接”,如阿基米德的“浴缸”,牛顿的“苹果”,凯库勒的“蛇梦”等,因为灵感的发生总是由于思维者对某一事物或问题苦苦思索,百思不解,逻辑思维的信息材料不充分,不够用,逻辑思路被卡住,出现了“缺环”,于是逻辑思维“中断”了,此时由于某种偶然因素的出现,突然激活了大脑皮层,使潜意识中的信息材料被调出,恰好填充了逻辑思路中的“缺环”,于是逻辑思路得到“对接”,豁然畅通;联想与灵感相类似,也是逻辑过程中陷入困境后由于现实发生某种现象(事物或语言、符号)使思维者突然想到了解答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如关于太阳能源问题,天体物理学家们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核反应理论提出后科学家们马上联想到核聚变恰好能解答太阳能源的问题,于是问题便得到了解决。总之,无论是直觉、灵感还是联想,都不可能离开逻辑思维凭空诞生,正如前苏联学者鲁扎文说的那样:“如果认为没有思维在事先预作精细准备的功效,没有对各种猜想、揣测和假说的评判性参照,新观念就可以产生出来都是难以置信的,而在上面这些活动中,逻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2年第4期,第32页。)
[收稿日期]2000-10-31
标签:科学论文; 联想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逻辑思维论文; 创新论文; 南京社会科学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创造力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