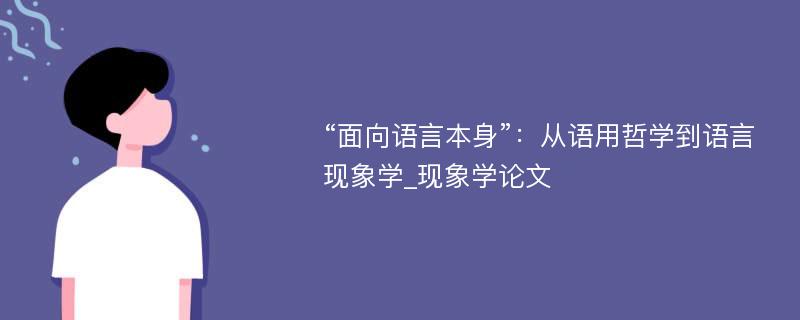
“面向语言本身”:从语用学哲学到语言现象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现象学论文,学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句法学到语义学、由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向。语用学对语言的看法,尤其是晚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以及塞尔等人对语言的看法,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语言观”有着潜在的一致性和融通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实现语言哲学研究的现象学转型,发展为一种语言现象学。语言现象学揭示了分析哲学传统和现象学传统通过语言哲学这一领域进行沟通、对话的理论可能性,这对于超越英美哲学的分析传统和欧陆哲学的现象学传统的简单二元对立,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转向及其语言现象学之谜
早期维特根斯坦是人工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坚持“语言图像论”。受罗素“逻辑原子主义”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将语言理解为一个形式化的“句法结构”和“逻辑结构”,认为语言是世界的图像。世界是由原子事实组成的有结构的整体,原子事实是由客体组成的。语言作为世界的图像描述原子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语言作为世界的图像同样具有结构,这种结构的可能性被维特根斯坦称为语言图像的“描画形式”。语言之所以能够描画世界,正是因为语言与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描画形式”。这种描画形式就是语言与世界共同具有的东西。(参见维特根斯坦,1985年,第27页)语言作为世界的逻辑图像与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和逻辑结构,但是语言自身却不能反映这种逻辑形式和逻辑结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作为一个命题逻辑系统,由无意义的记号组成,它具有一种由符号推演规则组成的逻辑结构。这种逻辑结构本身是不能被语言和命题言说的“逻辑形式”。“为了要能描述逻辑形式,我们应当把自己连同命题一起置于逻辑之外,也就是置于世界之外。”(同上,第45页)换言之,逻辑形式是非逻辑的,是不能用语言和命题来反映的。由此,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语言的界限、逻辑的界限和世界的界限,同时也指出了哲学家的界限:“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同上,第97页)然而,逻辑形式真的不能谈吗?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形式一言不发,认为哲学已经完成了,该说的、能说的都已经说完了。但后来维特根斯坦改变了看法,他开始研究起逻辑形式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其中期作品中。
如果说“逻辑形式”的思想在《逻辑哲学论》中还是一个不能谈的神秘之物,那么在中期作品中,维特根斯坦则将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加以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略论逻辑形式》这篇论文中。有论者认为这篇论文代表了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现象学阶段”。这个阶段揭示了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中的“现象学之谜”。(施皮格伯格,第109-130页)在这个现象学阶段,维特根斯坦主要关注于“感觉予料”的现象学,寻找和物理世界语言相对立的“现象学语言”,但是并没有成功。因此,在后期维特根斯坦转向了“语法综观”研究。有论者认为这是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放弃。(徐英瑾,第270-272页)在这种观点看来,维特根斯坦转向“语法综观”研究,“运用语言分析方法来研究非语言的现象,在实质上就等于否定了我们可以通过‘悬搁’语言而直接朝向现象的可能性——或者说,否认了我们可以合法地以现象自身的绝对性为借口而将语言和世界永远打入冷宫”。(同上,第277-278页)笔者认为这是对现象学的严重误解。维根斯坦并没有放弃现象学和现象学方法;相反,在维特根斯坦的这一阶段以及晚期作品中都贯穿着现象学方法,只不过他所关注的“现象学事实”发生了变化。他的关于“感觉予料”的现象学和关于“语法综观”的现象学,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现象学事实”。这是一次现象学的内部转换,而不是由现象学向非现象学的转换。笔者认为,现象学的纲领性口号“面向事情本身”是现象学的本质,至于事情本身是什么,则造成了各种现象学流派的内部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现象学和非现象学的分野。例如,我们不能因为早期胡塞尔坚持“绝对自我意识”而晚期坚持“生活世界”,就否认他是一个现象学家;也不能因为海德格尔关于现象学的“事情本身”(存在)与胡塞尔的“事情本身”(绝对自我意识)有差异,就否认海德格尔是一个现象学家。各种“事情本身”都是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剩余”,是各种现象学理论的地基和理论前提;它们不能作为理论认识的对象被对象化和表象化,而只能被面对和显示(理论直观)并进而现象学地被描述。
维特根斯坦晚期关于语用哲学的研究并没有放弃其转型期的现象学观点,而是这种观点的继续和深化。他的语用哲学和现象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从他的《哲学研究》的语言观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对早期《逻辑哲学论》中的语言观进行了批判,指出理想语言和形式语言是对语言的形而上学理解,它代表了一幅错误的语言图像。在这幅图像的支配下,“我们有一种幻觉,即以为在我们的研究中,那些独特的、深邃的、本质的东西就在于企图通过这种研究把握语言的无可比拟的本质,也就是存在于命题、词、推论、真理、经验等概念之中的秩序。这种秩序乃是存在于所谓超-概念之间的超-秩序。”(维特根斯坦,2002年,第67页)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这种对语言的理解是将语言的秩序当成了某种理想物和纯粹的水晶体,使语言成了某种“无与伦比”的东西。这是一种对理想语言和形式语言的迷信,这种迷信“产生于语法的幻象”。(同上,第71页)正是为了消除这种“迷信”,晚期维特根斯坦称自己的研究是一种“语法研究”。语法研究需要一种语言观的转换,即从形式化的理想语言转向活生生的日常语言。语法研究在于“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同上,第73页)语法研究认为语言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而是一个多少相互关联的结构所组成的家族”。(同上,第70页)语法研究并不是要为语言的日常使用提供一种先验的规则,而是对各种语言游戏提供具体的语境说明,并对各种不同语境下的语言游戏进行描述。因此,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考察中必须没有任何假设性的东西。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说明,而仅仅代之以描述。”(同上)在笔者看来,这种语法研究与现象学的本真精神是一致的。进行语法研究首先要进行现象学还原,悬置各种关于语言的本质理论,避免对语言的本质进行理论说明,而是进行现象学描述。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晚期维特根斯坦的语法研究称作描述性的“语言现象学”。这种语言现象学主张“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同上,第75页)
二、语用学的现象学内涵
晚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语法研究”是一种语用学研究。究竟什么是语用学?语用学同句法学、语义学相比具有什么理论特点?句法学研究语言的形式逻辑结构,语义学研究语言的命题结构,解决命题体系和世界结构的一致性问题。二者都将语言看作可以对象化的、现成的结构,可以发现这一结构、认识这一结构,并更准确地使用这一结构表达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认识和对世界的认识。总之,在句法学和语义学看来,语言是现成的、可以修改的工具,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而在语用学看来,语言是活生生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语言是在人际交往的使用中才“到场”的;没有对语言的使用、没有人际交往就没有活的语言。语言不是僵死的、自律的“形式体系”和表征客观世界结构和真理的表象体系和命题体系,而是在具体语境下的使用活动,语言是言语行为。语言是正在发生的、情境化的生活和人际交往,没有生活和交往就没有语言。因此,在语用学看来,给语言下定义是不得要领的。语言不是理论而是生活。同样,语用学不是理论,而是对语言在各种语境下的“用法规则”的现象学描述活动。关于语用学,“如果任意给它下个定义,比如‘语用学是关于……的理论(或学问)’,这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这样一来,对‘语用学’的这一界定本身就不再属于语用学的维度,而是属于句法-语义维度的东西了。当语用学强调任何语词的意义取决于它在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时,其中就已经包含‘语用学’的含义了。可见,给语用学做出一种语义学的界定,不仅无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语用学的要义,并且还有悖于语用学的本义。这就决定了语用学维度所特有的含混性,即不可能像在句法-语义维度中那样,只接受一系列意义澄清后的确凿无疑的概念。这不等于说语用学是一种神秘的、不可理喻的东西,而是说,对之只能诉诸描述。当我们揭示了言语在特定情境条件下呈现其意义的用法规则时,也就了解到了什么是语用学。”(盛晓明,第10-11页)
语用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发现语言意义“用法规则”的活动和操作。语言意义是在特定的语境中由语言的使用者构成的,因此,我们必须分析语境由以构成的用法规则。语言的语境、语言在特定情境下的用法规则,就相当于海德格尔现象学(此在生存论的“解释学前见”)的事实本身。对于这一事实本身我们只能进行现象学的描述,采用形式显示的方法来呈现这一事实。这一事实是不能被理论化和概念化的现象学剩余,是语言意义的缘发之域。换句话说,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观点看来,语用学不是关于语言“用法规则”的“某某学”、“某某理论”,而是对“语用”(语言就是生活形式,语言就是语言行为)这一现象学的事实的现象学描述和现象学的形式显现。语言的“用法规则”并不一个先验的、规范的规则,而是“规则就是用法,用法即规则”。这里的“法”并不是现成的,而是在用中生成的、构造的。而所谓的“用”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乱用,而是由特定的生活情境和话语语境(实际在此的解释学情境)决定的。语言是什么呢?语言是此在和存在的家,语言显示此在和存在并使它们“实际在此”。语言具有和“此在与存在”相关联的“生存论结构和存在论结构”,语言通过人向此在的“筹划”和向“存在”本身“去在”而显示自身并“在此存在”。语言决定了人的存在,而不是人在应用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语言具有本体的属性,它不能为人所用。人只能从属于语言,进入作为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被语言所游戏。
笔者认为,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其实就是关于语言的现象学,语用哲学和语言现象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语用哲学的代表奥斯汀将自己的语言哲学称为“语言现象学”(见杨玉成,第20页),就是一个证明。更有论者认为,奥斯汀思想的一些方面和现象学家以及生存主义者的某些先见有密切联系。如塞夫就认为,奥斯汀的语言现象学和欧洲大陆的“世界现象学”相对应,并且以世界现象学为基础。他还指出,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分析到汉普舍尔的《思想和行动》这条道路,与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这条路相似,这两条路都指向生存论分析。(同上,第17页脚注)
塞尔沿着奥斯汀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不仅如此,他还将语言哲学推进到了心灵哲学领域,提出了语言分析的意向性理论,在语言哲学的研究领域实现了他所说的“心灵的再发现”。塞尔认为言语行为是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它不能被还原为符号、语词或语句的代码。言语行为只在特定的语境中、在特定的解释学情境下才有意义。(塞尔,第230页)这里,塞尔的语用学观点又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语言观点不谋而合。按照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观点,言语行为不能被定义和概念化,言语行为就相当于语言现象学的“事实本身”,它是各种语言理论的“意义发生”之域。所以,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奥斯汀还是塞尔对语言的语用学分析,都与现象学的精神内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三、回到语言本身:一种现象学的语言观
在笔者看来,分析哲学内部的语言哲学由人工语言学派的逻辑分析转向日常语言学派的语用分析,和欧陆哲学内部现象学的生活世界转向是一致的。现象学在早期胡塞尔那里主要表现为以绝对自我意识为前提的纯粹先验现象学,在晚期胡塞尔那里主要是以交互主体性为根基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现象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以此在的生活为根基的生存论现象学。总之,现象学发生了由意识世界向生活世界的转变。与这种转变相适应,现象学对语言的观点也发生了从人工语言、形式化语言向诗性语言的转变,主张诗性语言是人工语言、形式化语言的意义基础。这与语言哲学中对“日常语言”进行语用分析的语用学转向是一致的。对现代科学技术所造成的人工语言和形式化语言的批判,导致了对诗性语言的重新发现。据笔者理解,海德格尔将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称作“座架”,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不但“座架”了人的日常生活,而且“座架”了人的语言,使人的语言“形式化”,造成了对“诗性语言”的“遗忘”。在形式化的人工语言(科学语言)看来,即使存在“诗性语言”,也只不过是“尚未形式化”的语言或“形式化语言”的缺乏。海德格尔则认为,诗性语言是不可形式化的语言,它是对存在的显示和道说。“语言本质问题决不可能在形式主义中获得解决和清算”。(海德格尔,1999年,第226页)
海德格尔对逻辑化的、可计算的语言以及作为信息传播工具的语言进行了无情批判。在他看来,对语言的形式化传统和逻辑化理解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自从古希腊的逻辑和语法横空出世以来,人们就把语言的言说囿于确定性的表述这一视域。照此逻辑与语法,一切在语言上超出逻辑函项的东西,都被视为空洞的演讲术,视为添枝加叶的篡改,视为转义(隐喻)。”(同上,2008年,第158页)可见,语言的形式化传统和逻辑化理解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这种传统使语言作为“在者”的确定性表述,而“表述无非是着重强调某种预先设定的东西。把当下正在阐述的东西当作表述的内容”。(同上,第142-143页)这种表象主义的语言观,这种对语言的形式化传统和逻辑化理解,使语言成为可计算的“语言机器”。“语言机器已经在摆布我们对语言的可能用法。”更为严重的是,形式化、逻辑化的“语言机器”使“人对语言的关系正处在一种转变中,我们还没有掂量出此一转变的深远幅度。这种转变的进程也不是可以直接阻挡的。该进程正处在爆发前的至大寂静中”。(同上,第125页)
如上所述,海德格尔对形式化语言、逻辑化的人工语言和作为计算工具、表象化工具的语言造成的可怕后果,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为此他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语言,一种“面向存在”之思的诗性语言和诗性言说。而“存在之思是对语言之用的忧心”。(同上,第28页)海德格尔忧心的是语言在日常世俗生活中作为交流思想和信息的工具使用,忧心语言只是“服务于理解和信息传布的工具”(同上,第124页),认为这只是人对语言的“世俗生活的蕴含关系”。此外,还有人对语言的“另外的蕴含关系”。这种另外的蕴含关系体现为另外一种语言——诗性语言。这种诗性语言才是母语,是语言自身在言说,而不是人在说语言。诗性语言是面向存在的“思的语言”。这种诗性语言是“作为家乡的语言”,语言作为“给予者,语言是家乡的恳切的馈赠,馈赠着的生成”。(同上,第159页)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之思”的诗性语言不同于关于“存在者之表象”的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诗性语言不能被偶然随意地使用,它不是“在者”的表述,而是“存在的家乡”,它给出存在的生成。
总之,海德格尔对语言的看法是与对存在的看法紧密相关的。通过对语言的重新理解,海德格尔要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关于“存在”概念的理解。海德格尔认为关于语言的理解必须摆脱以往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实现语言的转换。传统的语言观“力图获得一种观念,来说明语言普遍的是什么。适合于每个事情的普遍性的东西,人们称之为本质。按流行之见,一般地把普遍有效的东西表象出来,乃是思想的基本特征。据此,运思语言意味着:给出一个关于语言之本质的观念,并且恰如其分得把这一观念与其他观念区别开来。”(海德格尔,1999年,第1页)海德格尔反对关于“语言的本质”的观念性理解和形而上学把握,他要探讨“语言作为语言”的语言本身。“我们并不想对语言施以强暴,并不想把语言逼入既定观念的掌握之中。我们并不想把语言之本质归结为某个概念,以便从这个概念中获得一个普遍有用、满足一切表象活动的语言观点。”(同上,第1-2页)“我们要沉思的是语言本身,而且只是语言本身。语言本身就是语言,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同上,第2页)
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观点将语言本身遗忘了,用各种关于语言的本质的形而上学理论取代了对语言本身的现象学沉思。关于语言本身的沉思不是关于语言的形而上学追问,“而是径直沉思语言,并且把‘语言是语言’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命题当作我们的指导线索”。(同上,第3页)这种直接对语言本身的沉思必须经过现象学还原、使用现象学描述方法才有可能,因此这是关于语言的现象学沉思,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语言现象学”。语言现象学需要关于语言研究的方法上的转换:“如若我们沉思语言之为语言,那么我们就放弃了以往通行的研究方法。我们不再能够寻求普遍性观念,诸如活动、行为、精神力量、世界观、表达等;我们不再能够在这些观念中把语言处置为那种普遍性的一个特殊情形。通向语言的道路要让人们经验作为语言的语言,而不是把语言解释为这个或那个东西,并因此与语言失之交臂。”(同上,第212页)关于语言本身、关于“语言之为语言”,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本身是关于存在的道说和显示。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和真理发生之域,语言透露着存在的消息。语言倾听存在的声音。语言说而不是人在说。语言作为“显示着的道说为语言开辟道路而使语言成为人之说。道说需要发声为词。但人之能够说,只是由于人归属于道说,听从于道说,从而能跟随去道说一个词语。”(同上,第228页)人通过语言(作为道说)归属于道说,倾听存在的声音。可见,作为存在道说的语言即语言本身或作为语言的语言,是人处身其中的存在境域,是人的家园。“为了成为我们人之所是,我们人始终被嵌入语言本质中了,从而决不能出离于语言本质而从别处来寻视语言本质。因此,我们始终只是就我们为语言本身所注视、归本于语言本质这样一种意义上来洞察语言本质。我们不能知道语言本质——这里所谓‘知道’是一个传统的有表象性的认知所决定的概念。我们不能知道语言本质,而这无疑不是什么缺陷,倒是一个优点:由于这个优点,我们便突入一个别具一格的领域之中,突入我们——被用于语言之说的我们——作为终有一死的人的栖居之所中了。”(同上)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本质”不同于“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本质”是形而上学所追求的目标,这种本质是普遍性和共相,是本质主义和表象主义认识论的“残余”。“语言本质”则是语言本身,是“存在的道说”和“存在的显示”领域,是人的“栖居之所”。语言本质是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相互敞开自身的领域和真理发生之域。“作为世界四重整体之道说,语言不再仅仅是我们说话的人与之有某种关系的东西了——这种关系是在人与语言之间存在的联系的意义上的。作为为世界开辟道路的道说,语言乃是一切关系的关系。语言表现、维护、端呈和充实世界诸地带的‘相互面对’,保持和庇护世界诸地带,因为语言本身,即道说,是自行抑制的。”(同上,第182页)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道说本质决定了语言与存在的关联“只有道说才赋予我们用‘存在’这个细微的词而命名的东西以及如此这般跟随道说而说的东西,道说把‘存在’发放到被照亮的自由之境以及它的可思性的庇护之所”。(海德格尔,1999年,第182页)可见,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和存在本身是密切相关的。作为道说的语言本身的自行抑制揭示了存在本身的自行抑制,存在不可能完全显身;同样,语言本身也不可能完全透明,语言本身是不可能完全被说清楚的。
海德格尔对语言本质的探讨,目的是要“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这种经验的取得是要接受、顺从、遭受语言本身的要求。“于是,在语言上取得经验意谓:接受和顺从语言之要求,从而让我们适当地为语言之要求所关涉。如若在语言中真的有此在的本真的居所,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回事情,那么,我们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就将使我们接触到我们的此在的最内在的构造。这种经验就会在一夜之间或者渐渐地改变说着语言的我们。”(同上,第127页)这种对语言本身要求的顺从,对语言作为语言的接受和各种关于语言的形而上学理论是有本质差别的。“但是,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这回事情却大相径庭于人们去获得关于语言的知识。语言科学、不同语言的语言学和语文学、心理学和语言哲学等,为我们提供这种知识,而且为我们不断地输送出这种知识。新近的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研究越来越明显地把目标定在所谓的‘元语言’的制作上了。致力于这种超语言之制作的科学哲学,被认为是‘元语言学’。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了。元语言学它听来犹如形而上学——不光听来如此,其实它就是形而上学。”(同上,第128页)海德格尔的语言现象学要面向语言本身取得关于此在和存在的经验,而不是各种关于语言的形而上学理论。在海德格尔看来,面向语言本身的现象学追问获得的“思的经验”,能够使“语言本身把自身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而在各种关于语言的理论中,语言被当作一种人可以自由地“说”的工具。人们用语言来谈论各种东西,惟独语言本身不能被言说。语言本身被各种“说”抑制了、遗忘了。所以,语言本身作为现象学所面对的事实,正是语言现象学应该研究的。
语言现象学使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看法,由对语言的工具性理解和技术分析转向对语言的诗性理解和现象学沉思;由对象化、可认知的形式语言和人工语言转向不能对象化的、不可计算的语言本身(作为“生活形式”的自然语言和“作为存在家乡”的诗化语言)。语言现象学摆脱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主客二分模式和形而上学的追问方式,面向语言本身这一语言现象学的事实,实现了语言哲学研究的“现象学转型”。
标签:现象学论文; 语用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语言描述论文; 逻辑哲学论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语言哲学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