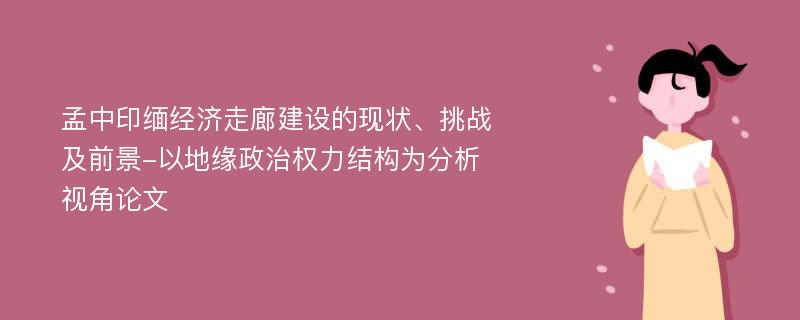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现状、挑战及前景*——以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为分析视角
黄德凯**李博一***朱力轲*
[内容提要]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目前而言仍旧处于议题讨论阶段,尚未进入实质性的启动运转期,而由于内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陷入困境。根据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分析机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逐渐呈现出一种“强—强”模式,其中印度作为地区大国的功能性缺位是主要内因。而陷入发展困境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则逐渐沦为中印之间权力博弈的平台。通过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多维度分析,发现制约与促进其发展的因素共存,但不利因素多于有利因素。妥善化解不利因素,充分发挥有利基础,方可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获得更多早期收获,进而形成稳定良性的孟中印缅区域合作机制。
[关键词]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系统中,存在不同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而且“政治权力的结构决定其政治关系的属性和性质”。[注] 黄美子:“试析政治权力结构与政治关系的属性”,《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34期,第239页。 根据地缘政治的特征来界定一个国家在地缘空间范围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地位,[注] Afshordi, M.H., & Madani, S.M.Regional Power System Structure in the Middle East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superior countries of the region),Modarres Human Sciences ,2009,Volume 13,Number 3,p.113.即权力结构系统中的权力分配。根据权力大小可分为不同的模式,其中“强—强”模式“强—弱”模式和“弱—弱”模式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政治中主要存在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而基于“强—弱”模式下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从其发出倡议之日起,便一直存在着地区内行为体权力间的博弈。从目前的发展及对四国经济走廊建设的研究来看,其既存在着深化发展的有利条件,也面临着深入推进实施的制约因素,而制约因素大于有利因素。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发起倡议至今,也不过几年时间,但以孟中印缅四国为基本单元构成的新的区域性地缘政治权力架构却经历了数年的积累和沉淀。它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偶然的,是现代区域一体化以及大国崛起下对周边地区影响的必然结果。虽然该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构建时间较长,但并没有摆脱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强—强”模式的通病,导致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互动模式逐渐趋于对抗化,即系统内的矛盾大于合作的动力,使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停滞不前,甚至濒临停摆风险。
一、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模式的现状:构成特点与互动特征
孟中印缅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体系有别于其他的地区性国际政治体系。无论是在其构成模式还是运转机制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这也成为该体系不能更好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具体而言,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体系的构成特点及互动特征表现如下。
(一)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模式的构成特点
1.“强—强”模式下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
由孟中印缅四国组建形成的新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体系的内在属性是由中印两个大国主导、孟缅参与的“强—强”模式。中印两国虽都被认为是大国,但大国间也有差别,中国已然是世界性大国,而印度还只是地区性大国。这种大国间的差异并没有转化它们之间权力结构模式,即推动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强—强”模式向以中国为权力顶端的“强—弱”模式转变。这是因为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对中国权力的认知提升仍停留在地区大国的阶段,尤其是印度。不仅如此,印度对大国梦的追求以及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印度作为一个领先大国的权力愿望进一步加强,[注] Takenori Horimoto, “Explain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From Dream to Realization of Major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 Volume 17,Issue 3,1 September 2017, p.463.也助推印度在地区权力体系中拥有更多自信。因此,孟中印缅地缘权力结构是由中印两个大国主导构建的“强—强模式”。从权力结构看,缅甸和孟加拉国作为系统内的弱小国家,位于该模式下的底层位置,是系统内中印两个大国权力争夺的重要战略对象国。也正是由于弱小国家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在大国竞合关系中采取一种“墙头草,两边倒”的策略。
双流机场车站为某城际客运专线中间站,车站总长943 m,有效站台长450 m,标准段宽55.2 m,有效站台中心里程处基坑深20.2 m。有效站台与T2航站楼斜拱桩基承台边缘净距为15 m左右。双流机场站与T2航站楼平面位置如图1所示。
国际地区权力结构系统是全球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体系的子系统,而全球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中拥有无数个地区子系统。这些地区子系统间并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相互交叉且联系紧密的。孟中印缅地区的权力结构系统从2013年建立时,其周边地区便拥有东亚地区的“强—强”模式、东南亚构建的“弱—弱”模式和以印度为中心在南亚形成的“强—弱”模式等地区系统的混合特征。孟中印缅建立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体系位于这三者的中间,并且也是由这三个系统的部分国家行为体重新构建的新的地区权力结构系统。不可否认的是,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系统与这三个地区系统间的关系密切。当然,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以及日本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以及来自域外其他大国的介入,使该系统自建立起就具有较大复杂性,也使孟中印缅地区权力结构系统面临内外权力争夺的挑战。
3.复杂的地区权力系统
2.松散型的地区权力体系
孟中印缅“强—强”模式下松散型的构成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孟中印缅地区权力结构体系建立在无任何相关协议及规则的基础之上。国际体系是由构成单元通过互动的形式并按照一定的规则、原则和秩序等相结合而构成的整体,[注]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Richard Little,The Logic of Anarchy :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p.29.特别强调其构成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或秩序。尤其是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中,只有在相关协议或条约基础上建立的国际政治体系才是长期稳定的。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体系的建立是由中印两个大国的总理在会谈时提出的,除了在两国的联合声明中体现过,以及孟缅两国通过外交形式予以积极回应之外,没有签署任何与体系建立相关的协议或条约。二是在运转过程中,也没有对系统内的任何一方签署或达成普遍或单方面的约束性条件。这种松散化自由式的地区权力结构体系,对系统内的任何一个行为体的非理性行为都无法实施一种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的约束措施,也就意味着体系结构内的任何一个国家行为体都可以随时以维护自我利益诉求为由对体系结构抱有一种消极态度甚至退出,却也不会从该权力结构得到任何惩罚。这就导致该结构是一个松散型的地区权力体系,这也成为地区体系无法有效运转的原因之一。
(二)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互动特点
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体系建立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四国联合工作组会议成为该国际体系运转的主要机制。除此之外,“K2K”经济合作论坛,两两间的双边互动等也成为该地缘政治权力体系的运转机制。这些共同构成了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运转体系。这种运转体系有别于其他地区性的国际政治体系,有较为独特的方面。
在区域合作的推进过程中,安全成为影响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 冷战结束以来,“传统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极度优先地位相对下降,非传统安全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对国际社会带来的危害日益突显”。[注] 王学军:“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辨析”,《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第108页。 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成为区域合作的拦路虎和绊脚石。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原本“是世界上安全问题较为复杂的地区之一”,[注] 黄德凯:“中国新安全观下BCIM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1期,第83页。 当前更是面临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变化和新动向,导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严峻。从原有问题来看,地区内的毒品贩卖猖獗,还与恐怖主义有密切联系;[注] Sahoo P, Bhunia A, Dhankar S,“BCIM Economic Corridor: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Working Papers,http:∥www.esocialsciences.org/Download/repecDownload.aspx?fname=A201471592925_20.docx&fcategory=Articles&AId=5961&fref=repec. 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合流趋势明显;走私、人口贩卖、贫穷、疾病、难民、自然灾害等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且形势严峻。与此同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还出现了与国际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错、地区“外溢”、影响范围扩大、危害加深等新动向。无论是原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还是新形势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客观上对“对经济走廊建设造成一种非常不利的氛围,将难以避免地对经济走廊的推进产生负面影响”。[注] 杨思灵、高会平:“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问题探析”,《亚非纵横》,2014年第3期,第53页。 例如,发生在2017年8月的缅甸若开邦的冲突,导致超过64.6万罗兴亚人沦为难民,逃亡孟加拉国,[注] “Rohingya Refugee Crisis,”https:∥www.unocha.org/rohingya-refugee-crisis,27/12/2017. 这不仅影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进程,还影响地区内的双边关系。
1.参与运转的层级仍较低
综上所述,以中印两国为主导的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陷入相互竞争和相互猜疑的“大国困境”是其本身缺陷所致。在此基础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凸出的功能性问题、替代性建设方案的重叠与竞争以及中印边境问题持续发酵等共同制约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深入。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本身缺陷才能得到有效控制,功能性问题才会得到妥善解决,替代性建设方案也会减少,其他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才会焕发新生。
第二、后续计量环节。商业银行抵债资产后续计量环节的会计与税务处理差异主要来源于抵债资产减值的计量。会计准则规定,商业银行需要对抵债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这会对商业银行整体利润会带来影响;税法则要求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减值准备,这就形成会计利润与税法利润不一致,需要对企业所得税进行适当调整。
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体系运转的层级既决定了地区权力结构体系的作用与地位,也代表了系统内国家行为体愿意让渡出的权力。虽然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体系的建立与运转得到了中印两国总理的同意,也得到了孟缅两国的积极响应,但实际参与互动的层级仍旧较低。从该体系的主要运转机制来看,孟中印缅四国联合工作组会议机制参与的层级仅到部级。其中中国和缅甸分别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计划和经济发展部副部长为首组建代表团参加,而印度和孟加拉国多次以外交部秘书为首组建代表团参会。由于各国中央政府参会的级别与层次较低,导致该会议机制所商讨的范围有限,不可能发挥更大作用。与此同时,K2K和双边互动作为该体系运转的机制之一,也因为其层级较低、涵盖范围较小,因而决定了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体系较低的运转效率。
2.互动波折:从孟中印缅四国联合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到第三次会议
肯尼斯·华尔兹认为,“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取向的,都将他们的系统还原为互动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其系统具体化”。[注] [美]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孟中印缅四国联合工作组会议作为该地区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系统的具体互动形式,联合工作组会议的举行就是孟中印缅地区权力体系的互动过程。前两次四国联合工作组会议顺利召开,但第三次会议不仅没有如期召开,反而拖延了原有的工作计划和安排。原计划于2015年完成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研究报告,则拖到了2017年4月,年内修改完善并完成联合研究报告的计划也延期到了2018年。在此期间,印度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兴趣逐渐降低,甚至在第三次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会议前,出现抵制该走廊建设的言论,并且出台多个替代性的地区建设方案,包括孟—不—印—尼经济走廊、印缅泰经济走廊等一批新的区域合作等。因此,孟中印缅地区体系的运转机制在受到该地区其他合作形式的冲击下,动力不足,地区体系濒临停摆或散架的窘境。但2017年4月第三次联合工作组会议的召开,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孟中印缅地区秩序停摆的危机,而经过此次冲击,孟中印缅地区的合作前景仍不明朗。
3.大国主导下的互动关系
在“强—强”模式中,大国间的关系是决定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体系运转的关键所在,即中印作为大国既是孟中印缅地区权力体系运转的主导者,同时也是影响该体系运转的决定性因素。系统内两个大国合作推动地区机制的运转,将会使得地区内的互动向良性方向发展;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大国失去兴趣或者退出,都会导致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体系的停摆,使地区合作机制面临危机。中国和印度是孟中印缅地区权力结构“强—强”模式下的两个大国。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初期,中印两国有意推动地区内的国际合作,不仅四国联合工作组会议顺利召开,合作工作稳步推进,而且在2015年11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表示,“中方愿同印度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取得早期收获”。[注] “李克强会见印度总理莫迪”,2015-11-21,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11/21/content_5015014.htm。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系统内的对抗不断加强,中印间的博弈逐渐占据主流,孟中印缅地区的权力结构体系在内外因素的夹击下面临“停摆”风险。其中印度的大国作用尤为明显,成为“强—强”模式下阻碍地区权力结构系统正常运转的障碍。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挑战
虽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相比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效率和自身的建设预期,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规划与建设的“二元”分离
在现代区域合作中,规划设计是必不可少的阶段,它不仅为区域合作描绘蓝图,成为具体实施的基石,还可吸引市场的注意,形成聚集效应。例如,《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既对该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助推作用,还“成为拉动双边贸易额提升的有力引擎”。[注] 曹志宏:“论‘规划纲要’对中俄贸易和投资的引擎与拉动效应”,《学术交流》,2011年第7期,第123页。 但如果区域合作规划仅停留在图纸上,未得到具体实施,规划则永远是规划,无法转化成为实际的建设行动,出现规划与建设的“二元”分离。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2013年开始建设以来,始终处于规划建设的讨论、编制和修改完善中,虽然在2015年中印两国达成早期收获计划,但仍没有对具体的合作项目加以规定和明确。这种仍停留在口头和图纸上的建设规划,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实际进展完全脱离。有学者在研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时指出,目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正处于“地区性合作新规划的表层性”,[注] 张立、王学人:“从地区主义视角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南亚研究》,2017年第3期,第40页。 只是构建起了抽象的区域合作轮廓,并没有真正步入到走廊建设的实质性推动阶段。
(二)双边建设火热,区域整体合作乏力
双边合作是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然而双边合作毕竟是区域合作的“低阶”,区域整体合作才是最终目的。当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进展不力的表现之一,便是双边建设火热,区域整体合作乏力。中缅、中印、中孟、印缅和印孟之间的双边合作一步步提升,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整体合作尚未完全开展,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合作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不仅如此,这种碎片化的双边合作并不是以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为目标,而是以实现其他区域性合作框架为主。印度推进与孟加拉国、缅甸间的双边合作,主要以实现孟不印尼经济走廊、湄公河—印度经济走廊、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组织等其他区域性合作为主。此外,两国促进双边合作的计划也没有纳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计划中,仅仅是双边合作不断提升的结果。2017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缅甸时提出“人字型”中缅经济走廊,目的是“巩固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化务实合作”。[注] 王毅:“中方提出建设中缅经济走廊设想”,2017-11-20,http:∥www.fmprc.gov.cn/web/wjbzhd/t1512003.shtml。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双边合作仍“有助于加快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步伐”,[注] 姚勤华:“中缅交通互联互通现状与前景分析——以云南基础设施建设为视角”,《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25页。 有利于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整体合作。
(三)国家单方面战略尚未与区域整体建设接轨
区域内的中国和印度都拥有各自的区域合作战略,但这些战略几乎没有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实现对接,反而是相互独立的。近年来,中国和印度都在推行各自的区域合作倡议,2013年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际,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是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纳入到“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个内容的合作。[注]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交通财会》,2015年第4期,第20页。 而与此同时,印度自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推出“东向行动”政策,打造“向东看”政策的升级版,不仅在原有的区域合作上扩大合作范围,还把经贸与投资领域放在第一位,改变过去“喊口号”“不作为”的施政方针,把“行动”摆在首要位置。[注] 赵干城:“从‘东向’到‘东向行动’——印度莫迪政府的外交抱负及其限度”,《当代世界》,2016年第1期,第56-59页。 时至今日,无论是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五个具体内容建设方面,还是在印度“东向行动政策”中,国家单方面的区域合作倡议仍未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接轨。
(四)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形势
——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市管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防止领导人员利益冲突的办法(试行)》,从经营业务往来、投资融资合作、企业改革改制、人员使用安排、个人经济往来等方面,对企业领导人员在履行经营管理职责中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提出了“七个不得”的具体规定。对此,上海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廖国勋说。(《人民日报》11月6日)
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进程中多重挑战产生的根源
如上所述,当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究其原因是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大国困境”决定了中印两个大国间的矛盾长期存在,由此导致资金、技术、互联互通、政府参与有限等功能性问题不断爆发。此外,中印两个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催生多个替代性建设方案。因此,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陷入停滞不前、困难重重、前景不明。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大国困境”
“政治现实主义认为,两大缺少战略缓冲空间的地缘力量中心必将在‘安全困境’的作用下重复过去法德争雄的梦魇”。[注] 李小华:“走向经济大国的中国与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地缘政治与相互依存的双重分析”,《世界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第70页。 这就意味着在同一地理格局中,新兴大国意识不到自身的战略选择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某种威胁感,[注] 姜鹏:“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崛起的‘威廉困境’与战略选择”,《当代亚太》,2016年第5期,第66页。 当两个国家都是崛起国时,这种威胁便是相互的,即双方都能感觉到来自对方的威胁,丝毫感觉不到自身会给他国带来安全影响,陷入“威廉困境”。大国安全感的缺失将进一步助推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潜移默化地把他国的战略视为对本国的威胁。相反,自身的战略却又在极力宣扬合法性与合理性,引发邻国间的“战略猜疑”,使得大国间的战略猜疑和竞争成为常态。中国和印度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两个大国,不可避免地也陷入到地缘空间内的“大国困境”。2013年中印共同倡导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时,两国并没有意识到会陷入无休止的猜疑和竞争中。虽然中印也在多双边场合频繁互动,可两个大国间的政治不信任却持续提升,两国间的冲突与对立大于合作,猜疑多于信任。原有合作停滞不前,即将开启的合作胎死腹中。使得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本身以一个区域经济合作为主的地区框架,转变成中印两个大国陷入困境后相互进行权力博弈的平台。
(二)凸出的功能性问题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凸出的功能性问题,成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停滞不前,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之一。功能性问题尽管不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向前推进建设的根本原因,但却严重制约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发展。尤其是一些关键性的功能缺失,使合作难以持续开展。首先,资金问题是阻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首要功能性问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2013年5月倡导建设以来,很多项目尚未开展,其中最大的技术性问题就是区域内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制定了全面有序的公共财政管理改革计划”,[注] Islam N I, Matin S, Hossan M M, “Bangladesh, China, India and 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BCIM-EC): Next Window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sia,”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 Volume 9, No 1, June, 2015,p.131.但这些计划仍停留在纸上,以至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推动和维持项目的开展。其次,技术变革和新技术使用有限限制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所涉及的范围是世界上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这里不仅现代科技变革缓慢,而且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更是低下,许多具有前瞻性、引导性的建设规划迟迟不能付诸实施。再次,连通性成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滞后的关键所在。目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尚未实现互联互通,这就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互联互通带来的效益和红利没有显现;二是在互联互通基础上实现其他功能性合作就不能得以实现。例如,通过互联互通实现四国地区间的货物、人员往来就无从谈起。最后,四国政府参与度有限既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问题也是原因。政府参与度有限直接导致合作项目难以开展。这不但导致四国参与建设的意愿下降,而且催生其他功能性问题,如货物跨境运输、人员跨境流通、金融货币跨境结算等领域的问题层出不穷。这些功能性问题不是单凭其中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就可以解决的,需要四国共同协力合作完成。
(三)替代性建设方案削弱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作用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大国竞争就是提出具有竞争性的替代性区域建设方案。替代性建设方案的增多对某一个建设区域合作而言无疑是好事,因为这个区域会越来越被重视,越来越多的资源也会在这里汇集,也是对区域建设路径多元化的探讨,所以在众多建设性方案共同作用下的区域建设将会欣欣向荣。但这也会降低其他方案的地位和作用,甚至会出现不同方案之间的竞争,使得该建设性方案的优势不能完全发挥。自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启动以来,印度先后在这一地区出台和推动过多个区域性建设方案,其中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加大对原有区域合作框架的推动力度。例如,重启印缅泰公路项目,打造印度-湄公河走廊。二是推出新的区域合作项目。2015年1月,在尼泊尔举行的联合工作组会议上,宣告“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机制正式形成。[注] 吴兆礼:“印度推进‘孟不印尼’合作:诉求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第72页。 印度出台这些替代性方案,一方面是意图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逐渐推向边缘化,降低中国通过该方案参与该地区建设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利用这些区域性建设方案加强对这一区域的影响,提高自身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进而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赚取更多中印“大国困境”的战略资本。
(四)其他影响因素
除上述因素之外,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困境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虽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仍不可忽视。具体来看,中印边境问题的持续发酵和中巴经济走廊给印度带来猜疑的“外溢”,导致印度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热情持续消减,进而波及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外界宣扬“龙象之争”的“墨菲定律”,致使中印两国间关系陷入竞争,也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区域建设框架视为竞争的平台。印度独立以来所依据的地缘政治传统历史经验与外交思想同新时代下区域合作共有观念思想不一致,使得中印双方之间在推动区域合作的“双中心”模式下难以取得共识。而域外大国介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使其变得复杂和艰难。近年来,日本积极参与缅甸、孟加拉国、印度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经济建设,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并取得一定成效,这给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区域合作建设增添了复杂性。
立春的那天,我在电视中看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开了。粉红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里就是一颗颗爆竹,噼噼啪啪地引爆了春天。我想这时节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没有星星可看了,因为老天把最美的那条银河,送到人间天堂了。
(1)黄铁矿化:是区内广泛分布的蚀变,早期阶段生成的黄铁矿大都为不规则状和立方体状,部分具裂纹构造,导致金初始矿化;成矿阶段生成的黄铁矿为菱形十二面体、八面体聚晶和五角十二面体,粒度一般为0.1~0.5mm,呈浸染状产于蚀变岩中,与金矿化关系密切。
四、孟中印缅地区权力结构体系的前景
孟中印缅地区权力结构体系当前处于内部权力构成不断变化,外部局势风云莫测的环境下,该权力结构系统的前景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尤其是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和实施,更增添了该地区权力体系与区域合作的不稳定性。印度洋-太平洋各地区权力结构子系统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具体来看,地区权力结构系统的前景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b)51单片机汇编语言编程部分。电子13级之前选用的是传统的单片机教材,在安排软件编程语言时,一般都是汇编语言。这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极不合理。主要原因有:第一,汇编语言本身晦涩难懂,可读性差,指令系统,寻址方式学生记不住。第二,单片机种类比较多,每种单片机都有自己的汇编语言,不同类型的单片机汇编语言不能移植。学生上课犹如听天书,睡到一大片,学完之后,唯一的收获就是感觉太难。
(一)孟中印缅地区的权力结构模式面临转换风险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系统拥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因此,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会处于两种变化形态:一是系统特征的变化,但并没有引起权力结构系统的整个变化,即权力结构系统的某些特征发生变化,而另一些则相对稳定,[注]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郭方、吴必康、钟伟云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0页。 仅仅是系统结构上的强弱变化。二是地区权力结构系统发生质的变化,既可以改变系统的原有模式,也可以消除旧的系统、产生新的系统。由于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下中国的国力不断上升,印度同中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虽然这种实力差距是权力结构内的特征变化,也尚未达到瓦解“强—强”模式的程度,但这种模式下的权力结构逐渐减弱。一待中印间的权力差距达到某种“临界点”,原有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强—强”模式即会出现向以中国为主导的“强—弱”模式变化迹象。
(二)对抗逐渐多于合作
国际体系的互动形态是由该体系的内在属性决定的。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系统中,权力是互动的基础,尤其是“强—强”模式下,米尔斯海默“通过对大国行为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所有大国对于彼此都是潜在的敌人”。[注] Mearsheimer J J,“Anarchy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Journa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Edinburgh , 2001, 40(40),p.362.因此,这种大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强—强”模式下互动的主要形态,即大国间的对抗性。不论其中一个大国如何竭力消除相互间的隔阂,推动利益相互交汇,采取何种友好措施,结构性矛盾始终主导着地区权力结构的互动进程。在孟中印缅地区权力结构的“强—强”模式中,中印两国间存在权力的结构性矛盾,其实质是权力争夺,由此带来的地区冲突与对抗,也成为孟中印缅地区权力结构系统互动的主要形态。这种非正常化的互动形态非但不会消减,反而会在系统的持续运转过程中持续加强。
(三)孟中印缅四国联合工作组会议机制面临沦为中印间博弈场的风险
任何国际体系的互动都依赖于一个或多个平台,这些平台一方面是体系内各个国家行为体构建政治互信、消除隔阂、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大国间权力的博弈场。孟中印缅地区权力结构体系构建起以四国联合工作组会议为主的运转机制。起初该会议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四国参与地区合作,加强系统内各国的政策对接,提升地区内的资本、技术与人员的流动性等;如今它却沦为中印两个大国权力的博弈场,印度对中国的政治不信任、安全顾虑以及战略考量都集中在四国联合工作组会议上,导致该会议机制进展缓慢、收效甚微。
从表2内风路温差异常情况来看,电机内风路的热量没有通过冷却器带走。分析存在有两种可能:一是翅片表面油污等垃圾集结严重,影响热交换;二是换热面积不够,造成热量带不出,仅带出5 K左右的热量。
综上所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间存在“二元性”,即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作为国际政治的内嵌形式,是一切国际互动产生的根源;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推进区域合作的外在形式。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属于“强—强”模式,不可避免的会引发域内大国之间的竞争。由于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强—强”模式下,区域内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并不是最为紧迫的,加之缺乏域外力量对该区域内的有效介入,进而导致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停滞不前,动力不足,前景堪忧。
2)优质的客户资源。公司下游覆盖包括通讯、工控医疗、航天航空、汽车电子和计算机等多个细分行业,客户覆盖面广,质量优质。通讯业务2017年占比为60%,核心大客户华为贡献了约三分之一的营收,其他大客户还包括中兴通讯、诺基亚等。在移动终端领域,公司的客户主要为苹果和三星,主要为其提供HDI;工控医疗主要客户为西门子医疗、迈瑞医疗、艾默生等,主要提供低层数PCB;而在汽车电子、计算机和航空航天,主要客户有霍尼韦尔、博世、比亚迪、长城汽车、希捷和联想等。从未来五年产值增速看,汽车电子和通讯会明显高于PCB行业整体增速,公司背靠优质大客户,通信和汽车电子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机会。
五、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多重挑战使其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为了顺利推进这一经济走廊建设,四个相关国家行为体需要增强合作意识,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坚持以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推动相互之间的合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不同的区域合作虽在整体上有共同的应对战略,但从实践来看,也存在各自的差异。具体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应在打造共生型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处理好大国竞合关系、引入适当的域外力量参与、早期收获增强信心等方面协调推进。
墨西哥与美国接壤,美国是墨西哥的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80%以上,而美国是全球竹制品的主要进口国[5]。因此,墨西哥开展竹子种植、发展竹产业,对于满足美国的市场需求具有很大优势。墨西哥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非常有利于发展竹产业。新当选的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提出的主张之一即是将墨西哥从现在的廉价制造国转变为技术应用国,这为从中国引进竹子技术带来了可能。墨西哥国内还有一些十分热衷竹子的学者,他们了解竹子,认识到竹子的重要性,致力于普及竹子的知识,作为主办方曾多次组织“世界竹子大会”,成立了“竹子技术发展中心”,为今后发展竹产业奠定了学术基础。
(2)由题意可知当x∈[0,+∞),f(x)≤ax+b,即x∈[0,+∞),f(x)-ax≤b成立,所以当0≤x<1时,可得(1-a)x+2<b恒成立,即当0<a<1时,(1-a)x+2无最大值,所以a≥1,此时(1-a)x+2的最大值为2,所以b≥2,当x≥1时,可得(3-a)x+2<b,所以当a≥3时,(3-a)x+2的最大值为2,所以b≥2。
(一)打造共生型地区国际关系体系
传统上的国际体系是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温特(Winter)把国际体系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相结合,产生出一种新的国际体系解释理论,即国际体系的社会—文化解释模式,并认为国际体系的未来发展趋向于康德文化模式,这种文化体系“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核心内容是友谊”,[注] 秦亚青:“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读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第142页。 这就为共生型国际体系的理论奠定了基础。所谓“共生型国际体系”,强调“共生体系”“本质是发展问题,着力点是如何实现均衡、平衡、和谐发展,目标是建立‘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注] 蔡亮:“共生性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的道、术、势”,《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第52页。 共生型国际体系既消除了现实主义理论关于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弊端,也充分发挥了建构主义理论的优势,是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向,在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学界对如何实现共生型国际体系进行了路径研究,认为它是在“新的文化启蒙”的基础上,铸造“包容式改进的共识”,实行“结伴而不结盟”的“跨国合作”,[注] 袁胜育:“共生型国际体系:理论与挑战”,《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5页。 从而建立共生型国际体系。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地区是东亚文化、印度文化、土著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相互融合交汇的地方,具备打造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基本条件。目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需走出第一步,即如何促成各国形成“包容式改进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孟中印缅四国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国际合作。唯有如此,孟中印缅才将会涅槃重生,展现出走廊建设的应有风采。
(二)妥善处理好大国竞合关系
在推动建立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同时,也要处理好中印两个大国间的竞合关系。因为大国竞合关系不仅是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组关系,也是影响国际体系转型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国竞合关系是该国际体系稳定与否的关键所在。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大国间的竞争与合作都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是国家行为体谋求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注] Jervis Robert, “Realism, game theory, 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 Volume 40, Issue 3 April 1988,p.317.建立在现实主义理论上的大国竞合关系容易引发国家安全的顾虑,导致大国间形成对立和冲突的局面。中印两国的竞合关系失败,导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化解其中的危机,转对抗为合作,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面临的困境之一。因此,改变利用现实主义的理论观念来指导大国关系的传统零和思维,采取一种较为良性互动的发展进路,才能有效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深入实施。近年来,中国根据“国际秩序深刻演变的历史背景”,[注] 阮宗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求是》,2016年第9期,第61页。 率先提出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型国际关系弥补了现实主义理论关于大国竞合关系的理论缺陷,也为大国竞合关系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落实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上,中印两个大国应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开展竞争与合作,既消除了中印两个大国间的对立与冲突,也将有力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
(三)引入适当的域外力量参与
就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本身而言,在同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体系和区域内问题极为严重的背景下,两个大国之间发生对抗与冲突的几率远远大于合作。为此,如何降低大国间的冲突风险,并将此转化为合作的动力,成为各国政府及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引入域外力量参与成为实现地缘政治权力平衡有效且可行的方式之一。特别是加强对域外力量参与的限度进行管理,降低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大国冲突和对抗,推进国际合作收获明显效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是因为区域内主导力量“缺位”。引入其他大国或国际组织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是实现区域内权力结构系统平衡的重要方式。形成以孟中印缅四国加域外大国或组织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4+1”模式,可有效缓解域内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实现区域内的三边或多边制衡的共建模式,如东盟。作为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相邻的一个重要的地区力量,鉴于其“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注] 张振江:“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页。 可首先引入东盟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一方面,平衡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权力关系,中国和印度都是东盟“10+1”的重要合作伙伴,东盟可在中印之间可充当协调者的角色,实现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平衡;另一方面,可以发挥东盟的建设性作用,中印两国对东盟的经济吸引力以及与东盟的经济依存度作为发挥作用的基础,打造中—印—东盟之间的三边参与与三方推进的合作机制,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推向更高层次。
(四)增强早期收获的信心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早期收获都是建立在某一个或多个合作框架协议之上,并且是按照既定计划在开展合作初期取得的建设成绩。早期收获作为合作的前期试验田,关乎着合作框架的前景。一般来讲,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合作的信心,也为其他合作项目提供示范,形成早期收获效应。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规定第一阶段是以农产品为主的600余种产品实施减税”,[注] 潘金娥:“‘早期收获’方案对中越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当代亚太》,2004年第7期,第37页。 “到2006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规定的第一阶段关税消减为零,贸易自由化效应开始出现”。[注] 徐婧:“CAFTA早期收获产品的贸易效应评估”,《国际经贸探索》,2009年第3期,第76页。 这为迈入第二阶段即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打下基础。同样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方面,早期收获效应的作用是全面深入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第一步。由于孟中印缅四国尚未就经济走廊建设达成任何愿景性文件,目前关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早期收获仅在2016年的第四届中国—南亚智库论坛上,由参会学者专家在口头上达成“早期收获喜人”的共识,并没有以任何相关愿景性文件的规定为评判标准。因此,在尽快制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愿景性文件的同时,能否加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早期收获建设,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能否继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以权力界定国家行为体利益的国际关系中,合作与竞争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出于维护自我利益诉求的目的,单一理性的国家行为体在同其他国家行为体进行互动往来的进程中,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随时调整自身的对外战略,以达到最大化实现本国利益的目的。基于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分析模式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进行理论化、多维度的分析后发现,孟中印缅四国间的合作模式处于一种中印两大力量共治的“强—强”模式之下。虽然中印之间存在着权力差距,但这并没有对四国经济走廊建设的权力分配模式造成颠覆性的影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提出及其发展过程所凸显的正是中印两大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博弈,即对四国间区域合作架构中主导权的争夺,这不仅是四国间经济走廊建设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之一,也是造成这种发展困境的关键性根源所在。有鉴于此,为了能够将这一经济走廊建设切实从规划中的蓝图转化成实际的合作实践,需要作为主导性影响力量的中印两国之间增强互信,加强政策对话,尽快破除两国间的“信任困境”与战略疑惧心理,加强两国政府层面的互动对话;与此同时,在充分尊重孟缅这两个中小国家意愿及合法合理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可以考虑适当适度引入域外大国力量对地区体系内的力量进行一种平衡,形成一种行为体间的“充分互信”,而作为主推力量之一的中国,则需要以一种“共生”的国家间关系理念,积极发挥四国间合作的“外溢”效应,增强各国对经济走廊建设早期收获的信心,进而为这一地区性合作机制与权力体系奠定良好的经济技术与文化心理基础。
*博士,四川警察学院讲师。
**江西萍乡学院政法系讲师。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是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印日自由走廊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AGJ009)》阶段性成果;受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周边国家安全形势研究创新团队”资助。
[中图分类号] D8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508(2019)02-0099-09
[DOI] 10.13252/j.cnki.sasq.2019.02.13
标签:地缘政治论文; 权力结构论文;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论文; 四川警察学院论文; 江西萍乡学院政法系论文;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