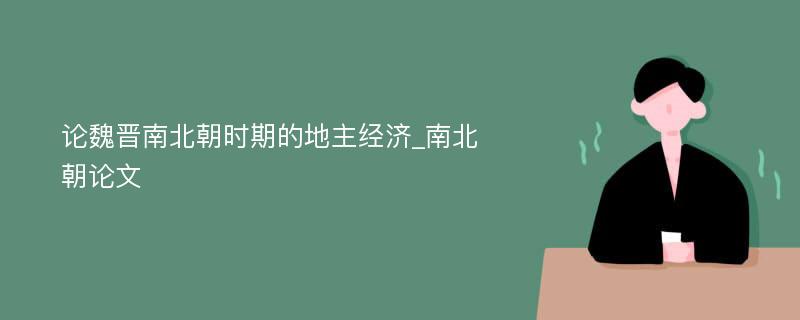
论魏晋南北朝北方坞壁地主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主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乱,江南偏安的社会环境不仅决定了南北地区有着不同的土地制度,而且也塑造了南北地区不同的地主经济特色,即北方坞壁式地主经济和南方庄园式地主经济。探讨这一时期北方坞壁地主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特点及作用则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一
坞壁地主经济产生于两汉时代。伴随着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社会动荡不安。豪强地主为抵御农民军的进攻,保其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遂组织私人武装,构筑工事,把原来为国家军队用于防御设施的坞壁移植到民间,产生了豪强地主武装的同时,也使地主坞壁经济问世。关于豪强地主坞壁的最早记载见于《后汉书·酷吏传》:“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所在害。”赵纲为两汉之际人。此时,正值农民大起义爆发,社会动荡,为坞壁地主经济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西汉末年,长安周围的三辅地区、洛阳周围的中原地区及河北地区是坞壁地主较多的地方。据有坞壁的豪强地主或“作营堑,以待所归”,或联合以抗刘秀,或进行小规模的封建割据。至刘秀一统天下,豪强地主的坞壁“皆平之”[①],“营堡降者遣其渠帅谒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②]。坞壁地主受到了沉重打击。
东汉末年,战乱为坞壁地主的迅速发展注入了强心剂。正如王仲荦先生所说:“由于中国国家形态的比较早熟,在社会制度上,氏族残余也长期严重遗留。因此秦汉以来的小农农村,他们的大众,……依然以氏族为纽带而巩固结合起来,他们是聚族以居的……通过血缘的结合关系,在坞垒堡壁之间,部勒宗姓,加以武装,或举宗而避难。”[③]这就是说,原始社会所残留的血缘氏族的凝聚力是地主坞壁经济赖以产生的基础,而社会的动荡仅是这种经济问世的助产婆。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继以董卓之乱,又继以各种封建军阀的混战,社会秩序大乱,在动乱的岁月中,那些据坞壁不能自卫的大姓便举宗而流移南渡,能自立的豪强地主便各自为政,修坞壁,筑垒壁,割地以为退守之计。在关中,董卓筑“万岁坞”于郿县,“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④]在河南,袁绍“门生宾客布于诸县,拥兵据守,(满)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⑤]许褚于“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⑥]袁术在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筑“袁公坞”,曹操在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建有“曹公垒”[⑦]。杜恕“营宜阳——泉坞,因其堡垒之固大小家焉”[⑧]。在山西,常林“避地上党,依故河间太守陈延壁。陈、冯二姓,旧族冠冕。张杨利其妇女,贪其赀货,林率其宗族,为之策谋。见围六十余日,卒全壁垒。”[⑨]在河北,豪强田畴“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⑩]“少室山西有袁木固,可容十万众,一夫守隘,万夫莫当。”[(11)]在辽东,管宁避乱处,往归者“皆来就之,旬日而成邑。”[(12)]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13)]这些世家大族,皆聚族而居,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足以与战乱相抗衡的坞壁地主经济,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主经济的特有形式。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一发而不可收。中原地区的豪强坞壁经济在战乱的刺激之下发展到了最强盛时期。一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地主坞壁遍布。如李矩“素为(平阳)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矩招还离散,远近多附之。”[(14)]永嘉之乱时,郭默率河内怀人,“自为坞主,……流民依附者渐众。”[(15)]洛阳城陷,魏浚“屯于洛北石梁坞,……归之者甚众。”[(16)]刘遐为坞主,“遂壁于河、济之间,贼不敢逼。”[(17)]郗鉴归乡里,“举千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18)]苏峻亦“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山东掖县)。”[(19)]这些坞主,多为“乡人”所拥戴,实际上也是以氏族血缘纽带为基础的以地主经济为实质的拥有武装力量的豪强地主。
当然,作为统治者是绝不希望坞壁地主大量存在的。刘、石时期,已有能力君临中原的少数民族权贵,采取了攻战和诱降等办法,分化瓦解坞壁豪强。八王之乱时,匈奴贵族刘渊乘机起兵,建国号汉。随刘渊而起兵的石勒率众3万余,转战魏郡、汲郡、顿丘一带,攻下堡垒50余处,“假垒主将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永嘉三年,石勒又攻下河北郡县堡垒百余处,部众发展到10余万,河北诸坞壁皆请降,送“质子”。两年后,洛阳饥困,石勒南出襄阳,攻拔长江以西坞壁30余处,屯于葛陂,“徐、兖间垒壁多送任请降,皆就拜守宰。”与此同时,刘曜“卒众四万,长驱入洛州,遂出辕并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百余……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20)]洛阳城破后,愍帝西入长安,为取得关中武装地主的支持,他不得不“以爵位悦人”,“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21)]刘聪继刘渊为主后,石勒曾上表建议:“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垒壁率多降附,运粮以输勒。”[(22)]
东晋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割据区的地主坞壁,为保持其本身势力,不得不采取南北奉迎策略。对于“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南北政权“皆听两属”[(23)]。可见,当时大量存在的豪强坞壁,既有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矛盾的一面,又有与其相统一的一面。
整个十六国时期,北方地区战乱不止,豪强坞壁也相应而根深蒂固,灭而复生,绵延不断。前燕时,“幽、冀之人,……所在屯结”,司徒慕容评讨张平,“并州垒壁降者百余所,……皆复其官爵。”[(24)]关中地区,后赵时,“三辅豪杰多杀守令以应(司马)勋,凡三十余壁,众五万人。”[(25)]到前秦时,“关中堡壁三千余所,……相率结盟遣兵粮助坚”[(26)],“三辅郡县堡壁及四山氐、羌归坚者四万余人。”直至后秦时,“西州豪族尹祥、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五万余家,咸推苌为盟主。”[(23)]可见,当时关中地区坞堡的众多,分布的普遍。
北方其他地区较之关中,战事尤繁,因而豪强坞堡当会更多,势力更大。如河东汾阴薛氏,“有部曲数千家。永嘉之乱,保河汾以自固,历刘、石、苻氏,莫能屈。”[(29)]直至北魏,仍“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30)]北魏拓跋嗣时,娥清率军渡河略地,“高平民屯聚林薮,拒射官军,清等因诛数千家,虏获万余口”[(31)]。
汉末军阀混战,使乡亭里地方政权机构失去作用之后,以血缘氏族为纽带的坞壁就一直成为维系北方基层民众的唯一组织。北魏初期的宗主督护制便是在坞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典·乡党》说:“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赵郡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32)],便是极典型的例子。魏孝文帝太和十年依给事中李冲建议,推行三长制,设邻长、里长、党长,表面上看来已打破了以血缘为纽带而建立的宗主督护制,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豪强坞壁时的从属关系。北齐时,“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33)],便是豪强坞壁的改头换面和进一步发展。
直至北周时代,豪强坞壁仍有存在的迹象。北周在府兵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曾于大统九年“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34)]。这说明,当时北方豪强地主仍有强大的私人武装。在这种情况下,诸如斐文举、韩雄、陈忻、魏玄、卢光等人,皆率乡兵义从,起家而为府兵将军。三辅著姓韦瑱,“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迁大都督。”[(35)]敦煌人令孤整,“世为西土冠冕”,“常愿举宗效力,遂率乡亲……随军征讨。”[(36)]这些“乡兵”和“乡亲”、“义从”等,实质是坞壁豪强地主的私人武装。府兵制的出现和不断完善,使坞壁地主有了“举宗效力”的机会,标志着坞壁豪强私有武装逐渐与封建国有武装走向合流,至此,坞壁豪强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坞壁地主经济也随之而告以结束。
二
虽然坞壁地主的出现与中国国家形态的早熟、氏族制度长期残留、血缘纽带仍然维护着当时我国村落居住有关,但是这绝不是说,坞壁是一种氏族结构、坞壁地主经济是一种氏族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因战乱而扭变了的畸形地主经济。
坞壁地主经济的特点,首先是既具有军事防御性,又具有生产自给性,是耕战结合型农业经济。魏浚屯于石梁坞时,“抚养遗众,渐修军器。”[(37)]“(刘)遐为坞主,每击贼,率壮士陷坚摧锋,……遂避于河洛之间,贼不敢逼。”[(38)]郗鉴“率乡曲千余家保聚峄山,随宜抗贼”[(39)]等等,无一不说明坞壁豪强首先是以拥有强大的私人武装而出现的。这种坞壁的出现,是战乱破坏了农业生产所必须的正常安定政治局面的结果。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的原因就在于“张弘等肆掠于阳翟”[(40)]。苏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的原因则在于“永嘉之乱”[(41)]。其他豪强所建坞壁也无一例外地都因战乱所逼。
战乱破坏了农业生产赖以进行的安定社会环境,而坞壁的建立则在于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小范围的安定的社会环境,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田畴“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家”[(42)],庾衮“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建坞壁于有“九州之绝险”之称的大头山,“而田于其下”[(43)]。十六国初期,坞主李矩“阻水筑垒,且耕且守”[(44)]。祖逖北伐以宗族部曲为骨干,他在谯时,“佃于城北界……谷将熟,胡果至,丁夫战于外,老弱获于内。”[(45)]十六国后期,王康“纠合关中徙民,得百许人,驱帅侨户七百余家,共保金墉城。……康劝课农桑,百姓甚亲赖之。”[(46)]可以说,如此“且耕且战”的坞壁地主经济不仅是战乱北方的主要农业经济形式,而且也为北周时代府兵制的兴起,为隋唐时期寓兵于农的府兵制的完备奠定了基础。
其次,坞壁地主经济有一套带有宗族色彩的管理体系,负责指挥防御性军事行动,组织自足性农业生产。坞壁组织,首先是坞主。坞主的产生则带有着氏族民主选举制度遗风。如李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47)]。再如庾衮,在推选坞主时,他就说:“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何?”在坞主之下,又“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48)]郗鉴归故里,“恤宗族及乡曲孤老,……遂推鉴为主。”[(49)]祖逖避乱淮泗,也被“推”为“行主”[(50)]。可见,在坞壁组织中,是有自下而上以“推”选形式产生的管理体系的。
而且,坞壁组织的维系表现为一种强大的聚合力。这种聚合力除由“宗族”、“部族”所产生的血缘凝聚力外,还有类似乡规民约性的不成文法规所造成的向心力。田畴结垒于徐无山中,“轻薄之徒自相侵侮”,田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51),以坞壁法律和封建礼教来规范坞民的言行。庾衮被推为坞主后,曾说:“古人急病攘夷,不敢逃难。然人之立主贵从其命也。”于是订立规约说:“毋持险,毋怙乱,毋暴邻,毋抽屋,毋樵采人所植,毋谋非德,毋犯非心,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以达到维持坞壁内部“分数既明,号令不二,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着,匡救其恶” (52)的社会秩序的目的。这种不成文的乡规民约,既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又带有氏族社会的原始色彩,成为维系坞壁组织的一种约束力。
但是,必须指出,无论是坞壁组织具有原始民主色彩的“推”选式制度,还是具有乡规民约性的不成文法规,都是建筑在豪强地主与部曲佃客的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是以阶级统治为其根本特征的。北魏李元忠,“家素富,在乡多有出贷求利,元忠焚契免责,乡人甚敬。……后葛荣起,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坐于大槲树下,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53)这一方面说明宗主的权力之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坞壁组织中,“里推其贤”、“邑推其长”,以及“坞推其主”,实质上都是以其财力大小为根据的。因此,一个坞壁之中,实际是大小地主对于坞壁领导权按其财力的大小进行的相应权力的分配,是大小地主所组成的坞壁领导权的金字塔。而在坞壁与坞壁之间,则推选更强有力者为“统主”、“盟主”。“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 (54);“西州豪族尹祥、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五万余家,咸推(姚)苌为盟主。”(55)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坞壁组织,实际上是最典型的既拥有武装力量,又占有经济地盘的封建军阀。
表面上看来,这种封建军阀既“屯聚林薮,拒射官军” (56),又“每击贼,率壮士陷坚摧锋” (57),似乎对一切影响其生存的武装力量都进行反抗。但是,这仅是特殊环境中豪强地主求取生存的一种形式。当形势改变,代表豪强地主的政权出现之后,那些大大小小的坞壁豪强或则“皆为晋士” (58),或则“运粮以输(石)勒” (59),或“遣兵粮助(苻)坚” (60),变成了在北方地区相继出现的地方政权的阶级基础了。
在坞壁组织中,豪强地主与部曲之间的关系也是宗族色彩掩盖下的阶级对抗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豪强地主的依附人口极多,称谓也相当繁杂,有“僮隶”、“私附”、“佃客”、“宾客”、“家兵”、“部曲”等。前秦时,关中水旱不年,苻坚“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原,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61)北魏高崇“家资富厚,僮仆千人。”(62)咸阳王元禧“奴婢千数,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63)这种“僮隶”,是豪门权贵所蓄养的生产奴隶。而“佃客”、“部曲”等则是豪强地主所奴役的农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佃客”很大一部分并不类同汉代佃客那样租种豪强地主的土地,而是身系原编户齐民耕种自家原有土地的农民。鉴于当时各种徭役的繁重,“小人惮役” (64),自动荫附到贵势门下而成为佃客。因此,“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而豪强征敛倍于公赋。”(65)可见,这时佃客所耕种的土地应是自家原有的,只不过把原应交国家的赋税在量上增加之后交给豪强而已。
东汉末年,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和延续,困于战乱纷扰的农民,投身于豪门以获得庇护,世家大族屯坞自守,筑堡求全,把这些投靠的农民按军事建制编制起来,于是,佃客便成为武装起来的部曲。三国时代的李典,“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官渡之战时,李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66)在这里,宾客与宗族部曲实为一类人,不仅看到了部曲由佃客、宾客转化而来的痕迹,也看到了宗族色彩掩盖之下豪强地主部勒佃客,使其成为武装部曲的实质。实际上,此期的部曲即豪强驱使下的武装佃客,而佃客又是交租纳税的耕种部曲。战时,部曲要荷戈作战,平时则要操耒耕作。部曲作为豪强地主的依附人口,不仅要“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从事修堡固坞的军事活动,而且要被“考功庸,计丈尺,均劳役,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 (67),担负坞壁豪强所征收的租税和摊派的劳役。尽管,此时租税的计征和劳役的摊派主要并不是以佃耕豪强地主的土地多少为标准,而是以豪强在战争环境中庇护小农得以正常进行农业生产为前提,带有“量力任能”特色,但其榨取却“倍于公赋”。刘曜攻坞主郭默于怀城,“收其米粟八十万斛” (68)。石勒军中大饥,击败汲郡枋头数千众组成的坞壁,“因其资,军遂丰振” (69)等史实,不仅说明当时坞壁内农业生产成绩不错,而且说明坞主对于部曲的榨取是相当苛刻的。而这种苛刻盘剥,正是豪强地主与部曲阶级对抗实质的反映,是对宗族面纱的无情揭露。
再次,尽管坞壁组织是一种耕战结合式的组织,但是,这种组织又是一种可以移动性的耕战结合组织。耕地的特征之一即在于不可移动性。作为以土地为生产场所的农业经济活动以及相应的生产组织,一般说来具有固著性,是较少移动的。但是,在武装力量保护之下的坞壁组织,却是可以移动的生产单位。李特率领的“流移就谷”集团,实际上也是一种坞壁组织。这些“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又分人散众在诸村堡”,进行农业生产和求取生计,以致引起土著坞壁和流人坞壁之间的矛盾纠纷(70)。这是在人口密集区的客民坞壁与土著坞壁间冲突的现象。管宁避乱辽东,“避乱者皆来就之,旬日而成邑” (71),杜恕去京师洛阳,“营宜阳一泉坞,因其堡垒之固大小家焉” (72),则是避开了军事要冲、动乱之地而寻找偏僻之乡结坞自守。更有甚者,田畴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五千家依附农民在田畴的督导下大规模开展农业生产,竟一直与外隔绝达十几年之久(73)。肯定,这些避乱荒远者是绝不会躬耕他们自己原有土地的,但由于在地荒人稀之处屯坞结垒,因而并没有爆发李特遇到的流人与土著矛盾的冲突。
至于在军事活动频繁地区,那些武装力量强大的坞壁可以固垒而自守,保证其农业生产在一个固定地区照常进行下去,那些势力弱小者则不得不使自己的生产点实行游动式了。李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矩招还离散,远近多附之。”(74)庾衮率其同族和庶族部曲,初堡于禹山,后又堡于林虑山,及石勒攻林虑,乃“登于大头山,而田于其下” (75)。但是,刘遐为坞主,“壁于河济之间,贼不敢逼” (76)。这种现象说明,坞壁农业生产点的固定与否,其决定因素在于军事力量的强盛与否,强则可据坞而自守,排除外界干扰,在一地坚持生产下去;弱则东游而西窜,造成军事保护之下的农业生产点处于经常变换之中。
三
关于坞壁地主经济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坞壁组织维护了局部地区的农业生产秩序,保证了农业生产在战乱烽火中能在这些地区得以正常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持续不断的战争给北方地区所带来的是一个大破坏的局面。尽管西晋初年和北魏中期,北方地区曾一度出现过稍微安定繁荣的景象,但那只不过比流星划过天空还短暂的瞬息祥瑞,实在太可怜了,而充斥于史书的却是“诸夏纷乱,无复农者” (77),“中原萧条,千里无烟” (78),“海内沸腾,郡国荒残,农商废业” (79)等等血腥记载。在这种大乱中,与“中原萧条,千里无烟”相对照的是,坞壁地主农业经济却“丁夫战于外,老弱获于内” (80),仍然有一种“劝课农桑,百姓甚亲赖之” (81)的局面。这就是说,在军事力量的保护之下,农业生产在坞壁组织内并没有停止,平头百姓还有可能生存下去。尽管坞壁地主的盘剥“倍于公赋”,但能在战乱中生存下去,则也是百姓求之不得的事情了。大概正是基于生存的欲望,才使“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 (82),“三年间众至数万” (83)现象的发生,也才导致了北魏中期之前“或百室合家,或千丁共籍” (84)局面的形成。对此,史学家们往往指责豪强地主荫附国家人口的一面,而忽略了坞壁组织维护了局部的社会生产环境,使小农首先有立身之地的一面。
不错,坞壁地主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国家控制人口的减少和财政收入的降低。汉献帝初平年间,“胶东人公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85)建安年间,司马芝为菅县长,“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前后未尝给徭……而宾客每不与役。”(86)至魏晋南北朝时,丧乱分据,“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小农不得不“多依豪室” (87)。这些“荫附者,皆无官役” (88),“皆无课役” (89)。在地主豪强与封建政权对农民剩余劳动成果的榨取分割上,自封建政权诞生那时起就有着既统一又矛盾的两个方面。封建政权既要给予地主豪强一定的特权,以有利于其阶级基础的塑造和强化,又要限制地主豪强经济势力的无边际膨胀,以防止地主势力对于中央政权的威胁。当封建中央政权较为强化时,对于地主豪强既支持又限制的措施便显得有力。但是,当中央政权处于瘫痪或四分五裂状况时,封建政权不仅对于地主豪强的限制会处于失控状态,而且对国家财政来源的主要对象编户齐民也将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小农为了使自己不至于抛尸于沟壑之间,避开战争灾难,不得不求取地主坞壁的保护,变成了依附人口。于是,遵守国规国法的编户齐民成为服从坞壁纲纪的部曲家兵,缴纳国家赋税的小农变成坞壁豪强征敛的对象。这种状况,对于封建国家来说,无疑是十分不利的。但是,对于小农来说,只不过是改变了缴纳赋税予谁的问题,而且通过这种改变得到了继续维持农业生产的条件和环境,实现了能够生存下去的最起码要求。因而,在当时烽火连天的环境中,坞壁农业经济的出现对于势单力薄的小农来说,不能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坞壁林立于北方地区,防止了战争对坞壁内农业经济的破坏,使坞壁经济与当时“千里无烟”的社会经济的衰退和破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坞壁,不仅成为刘曜、石勒、苻坚等人的重要军事物资补给基地,而且为北方农业生产在短暂统一时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北方旱作农业技术的定型奠定了基础。战争年代,石勒“攻冀州郡县垒壁,率多降附,运粮以输勒。”(90)淝水之战后,慕容冲围攻长安,关中堡壁三千余所,“遣兵粮助(苻)坚。”(91)这些都说明,在新的封建政权建立过程中,坞壁组织虽与那些新兴起的强权人物有过冲突,但他们终归要成为新兴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北魏孝文帝时期,国势达到了鼎盛,北方农业经济曾一度出现过“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 (92)的局面。这种社会经济繁荣现象的出现实在与“宗主督护”有一定的联系。宗主督护实际是坞壁组织的一种延续和发展。宗主督护保证了北魏三长制确立之前基层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北魏的立国,对于北魏的强盛是很有关系的。只是当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时,这种社会基层组织才日益不能适应于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至魏孝文帝时便才由三长制替代了。但是,这却说明坞壁农业经济对于短暂统一时期强盛局面的出现是有一定的基础作用的。
第二,坞壁农业经济有利于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封建军阀的形成。东汉末年,因战乱而兴起的豪强坞壁首先是以镇压黄巾起义军的面貌而出现的,诸如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93)再如白超,“汉末,黄巾贼起,白超筑此垒以自固。”(94)黄巾大起义本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准备的农民风暴,但是,这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很快被分割包围而遭各个击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是豪强坞壁武装力量的众多和强大。而当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豪强坞壁武装力量防范农民起义的主要作用转为防御各种封建军阀势力和农民势力,即具有所谓“拒官军”和“御贼寇”两种功能。在长期的防御作战中,那些势力弱小的坞壁地主大都被吃掉或被吞并,而那些拥有强大武装的豪强则逐渐发达起来,有的甚至历几个政权而不败。如河东汾阴薛氏,“有部曲数千家。永嘉之乱,保河汾以自固,历刘、石、苻氏,莫能屈。”(95)北魏前期,实行宗主督护制下的各地宗主,以及那些拥有众多荫附人口的豪强地主,实际上大都从坞壁脱胎而来。北周时期,那些率乡兵义从,起家而为府兵将军的地方豪强,也该是为坞壁豪强的进一步演化。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坞壁组织的武装力量维持了豪族地主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使豪强地主有了赖以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经济势力,同时也具有了一定的防止被吞并的武装自卫能力。
但是,也必须看到,正是因为坞壁豪族拥有足以立命的武装力量,因而往往加剧了此期的军阀混战,导致战争的长期性、剧烈性和普遍性。无论是十六国,还是北魏,各个封建政权的建立,无不都对坞壁豪强的地方武装进行过残酷扫荡和分化瓦解。这些林立于北方地区的坞壁组织无疑于一个个封建山头,阻碍着黄河流域的统一。石赵时,石勒等“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寇襄阳,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徐、兖间垒壁多送任请降,皆就拜守宰。”(96)为攻伐坞壁,石勒可谓不遗余力。而前秦、前燕直至北魏政权也无不在摧毁坞壁组织上费掉很大气力。北魏拓跋嗣时,娥清率军渡河略地,“至湖陆、高平民屯聚林薮,拒射官军,清等因诛数千家,虏获万余口。”(97)魏晋南北朝之际,我国北方地区政局动荡,王朝迭起,河山分割,战事不已,一个重要因素即在于豪强坞壁这种分裂因素的存在。在豪强坞壁中,那些强有力者被推为盟主,坞壁武装力量便成为其独霸一方的基础。羌族姚氏占领关中,建立后秦,其源便为“西州豪族尹祥、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五万余家,咸推苌为盟主。”(98)北周时代,关陇地区成为统一我国南北的发源地,其原因也在于宇文泰“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 (99),利用府兵制形式,妥善地解决了坞壁豪强所拥有的私人地主武装,使关陇统治集团形成为被中央政权所驾驭的强大政治力量。为隋唐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后汉书·耿弇传》。
②《资治通鉴》卷40。
③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
④《后汉书·董卓传》。
⑤《三国志·满宠传》。
⑥ (93)《三国志·许褚传》。
⑦ (11) (94)《元和郡县图志》卷5。
⑧ (72) (92)《三国志·杜畿传》。
⑨《三国志·常林传》。
⑩ (42) (51) (73) (82)《三国志·田畴传》。
(12) (71)《三国志·管宁传》。
(13)《三国志·邴原传》。
(14) (44) (47) (74)《晋书·李矩传》。
(15)《晋书·郭默传》。
(16) (37)《晋书·魏浚传》。
(17) (38) (57) (70)《晋书·刘遐传》。
(18) (39) (49) (83)《晋书·郗鉴传》。
(19) (41)《晋书·苏峻传》。
(20) (22) (59) (69) (90) (96)《晋书·石勒载记》。
(21)《资治通鉴》卷89。
(23) (58)《晋书·祖逖传》。
(24)《晋书·慕容俊载记》。
(25)《资治通鉴》卷98。
(26) (54) (60) (61) (91)《晋书·苻坚载记》。
(27)《资治通鉴》卷108。
(23) (55) (98)《晋书·姚苌载记》。
(29) (95)《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77《薛府君墓志铭》。
(30)《宋书·薛安都传》。
(31) (56) (97)《魏书·娥清传》。
(32) (53)《北史·李灵传》。
(33)《通典·食货典·田制》。
(34) (99)《周书·文帝纪》。
(35)《周书·韦瑱传》。
(36)《周书·令孤整传》。
(40) (43) (48) (52) (61) (75)《晋书·庾衮传》。
(45) (80)《资治通鉴》卷96。
(46) (81)《资治通鉴》卷118。
(62)《魏书·高崇传》。
(63)《魏书·咸阳王元禧传》。
(64)《晋书·王恂传》。
(65)《资治通鉴》卷136。
(66)《三国志·李典传》。
(68)《晋书·刘聪载记》。
(70)《晋书·李特载记》。
(77)《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载记》。
(78) (84)《晋书·慕容皇光载记》。
(79)《周书·于谨传》。
(85)《三国志·王修传》。
(86)《三国志·司马芝传》。
(87)《通典·食货典·丁中》。
(88)《魏书·食货志》。
(89)《隋书·食货志》。
(92)《洛阳伽蓝记》卷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