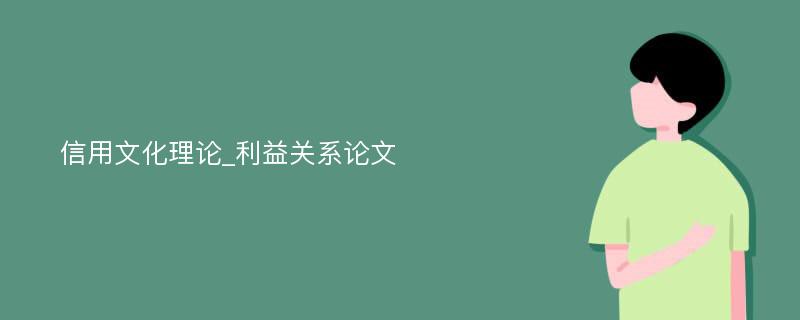
信用文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用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信用是人类文明的基石
人类能超脱于动物界,以“万物之灵”而树立起自己的文明大厦,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分工合作。而合作的基础在于信用,即信任。所谓“信任一个人”指的是愿意同他一道做事,相信他会全力以赴地去履行义务,相信他的话,愿意与他订协议,更一般地说是愿意与他合作;说一个人不值得信任,是指人们应谨慎地同他打交道的人,至少要尽可能少地与他往来。总之,人们由于对某种利益的预期,基于信任的基础上选择与他人合作;若你不信任任何人、或不被他人所信任,就会丧失掉许多选择的机会而享受不到合作的好处。
正因如此,各民族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强化信用需求与信用结构。比如“诚实信用”几乎被各民族视作美德而予以提倡和鼓励;对背信行为及无信之人予以遣责乃至惩罚。
比如,在中国古代,孔子强调“民无信不立”,孟子把“朋友有信”作为五伦之一,荀子视“言无常信”为小人。民间“人无信不可交”的训诫以及“然诺则千金不易”的准则不绝于史。“诚信”也构成近现代民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恪守信用的要求被如此高扬,就在于信用是人类社会文明赖以成立的重要基石。
在当今社会中,信用作为一种文化要素主要以伦理道德意识以及众多的制度安排的形式存在,并落实在人的一系列活动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所谓“信用文化”。我们每天在享受着这个文化传统的好处而较少去认真深究其中的奥秘,正如同我们每日每时都在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空气而较少意识到这一点一样。
当然,人类社会各地区,各民族国家的信用水准、程度和类型是不平衡而又参差不齐的。国外学者福山就曾区分了“低信任”文化与“高信任”文化。前者指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的社会文化,这种文化不利于私营大企业的产生或持久生存,因而小的家庭企业与国有大企业较为普遍;后者指信任超越了血亲关系的社会,那里有利于造就大规模的经济组织(主要指私营大企业)以及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如美国、日本、德国等。此论注意到了信用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
2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现代社会广泛而高度的相互依存性,对信用有着更多更高的诉求。
近代以来,社会分工日趋细密。高度的社会分工必然伴随着广泛而频繁的交换,市场秩序得到深化和扩展。绝大多数经济活动不得不采取“商业”的形式得以运作和展开,以至有“无业不商”之感。人们的绝大多数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要素都要从市场那里取得。不仅交换物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而且交换的复杂程度更趋增强,无论是商品交换、劳务交换,还是信息、服务交换,其交换的完成或实现,都存在着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差距,这个差距导向要靠信用来保障。否则,交换无法稳健进行。
与这种广泛的社会依存性以及强烈信用需求相适应的,必是信用关系的普遍化和形式多样化。如借贷形式的银行信用、赊销预付形式的商业信用、分期付款形式的消费信用、信用社形式的合作信用、以政府为债务债权人的国家信用、各种国际信用、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保险、信托、租赁、信用支付手段(信用单、信用支票、信用卡等)都属某种信用形式。对广泛的市场交换来说,信用构成经济运转的润滑剂,不仅提高了交换的稳定性、安全性,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进交易效率。
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既是企业的生命又是一种资源。首先,信用不仅存在于制度安排之中,而且表现在企业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一是质量信用,只有产品质量过硬,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二是广告信用,就是做广告要实事求是,不搞欺骗;三是服务信用,即经营中做到“秤平斗满尺码足”、童叟无欺(即计量信用);切实履行售后服务的承诺;四是合同信用,遵章履约,恪守合同,维护合同的严肃性,等等。缺乏起码信用,企业就无法生存,所以信用就是企业的生命。其次,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里,每一个企业家及其企业都十分着重和保持自己的信用形象。因为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个企业如果在大众心目中有良好的信用形象即信誉,就能给它带来超常的利润。所以信用能转化为资源,或者说信用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和无形资产。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家们争创名牌的原因。名牌产品、名牌企业乃至名牌企业家确实包含了人们更多的信任。
从历史上看,那些有着良好的商业信用的民族或企业常常占尽天时地利。比如产生了不少世界商界巨子的犹太人,就有着重信守约的商业传统。一方面,长期的商业实践就是铸造其商业意识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这个民族的契约精神构成其商业信用意识的文化资源。在他们的观念中,契约是神圣不可毁坏的。这种契约精神得益于宗教传统,因为作为犹太人信仰源泉的《旧约全书》中的“约”即上帝同人类之间所订立的“古老契约”。就是说,通过《圣经》向所有的人(包括商人)灌输“约”的神圣性、履约的强制性和义务性,这使他们受益非浅。
正是基于上述几个方面,所以我们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这既是一个价值判断,又是一个事实判断。作为价值判断,是指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建立在高度分工合作基础上的经济形态,有较高的信用要求;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市场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善意和较高的信用水准。作为事实判断,是指在健全的市场环境中人们一般都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各式信用准则(这既有信用伦理之功,而更取决于制度约束之效)。常有人说,市场社会里到处经常发生欺诈现象,故信用水准较之前市场社会更低,这乃是片面之辞。市场社会的确存在大量欺诈,新兴市场尤其如此,但欺诈还是以普遍的信用为前提条件的。一些人正是利用了别人合作和信任的姿态以及信息的不对称而欺骗得逞,这种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信誉的极端投机行为终是要被淘汰的。
3 信用模型分析与信用制度化
从人类交换合作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关系中,我们不难抽出最基本的信用关系模型:最简单的信用关系包括两个行动者——委托人与受托人。此处的前提是两人都是有目的的理性行动者,其目的是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
在这个关系模型中,双方都面临着一定的理性选择与考虑。委托人考虑是否信任受托人,也就是为了在风险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获得个人利益,在拒绝信任或给予信任之间作出选择,即对预期所得与可能所失进行理性权衡。受托人亦面临着守信用还是不守信用的选择(当然有时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委托人是否信任受托人,常常不是根据受托人愿望或允诺,而是根据他是否有能力恪守诺言)。在某些情况下,受托人违背诺言可以获利(如卷款潜逃等),无疑这是一种短期利益与短期行为,从长远看,受托人的利益会因委托人永远丧失对他的信任而蒙受损失,或付出其他代价(如抓获归案、声名扫地等等)。无论委托人的给予信任还是受托人的不守信用,都伴随某种程度的风险因素。可见,长期以来被视为重要的,甚至先验的道德品质的信任或守信,其成因之一是建立在利益的长期的博弈之上。虽然这种解释,也许并非是其唯一的和完善的解释,但它至少足以让我们看清人类“信用”现象并不神秘。
信用制度本身就是长期博弈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信用规则,反过来又帮助强化了人们的信用意识,提高人们预期的可靠性与稳定性。它内在地包含信用伦理与契约制度,二者分别适应了不同形式的人际关系之间,以及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交换合作的信用需要。常常是在重复式、人情化的交易中,借助非正式的信用约束,而在交易的非重复性、非人情化而且涉及当事人重大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多诉诸契约形态——这是信用关系、信用制度的法律操作系统。
信用制度的完善,有赖于人类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进步。现代西方社会如美国,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出现了信用制度的商业化运作机制。具体来说,就是设立信用记录公司,对金融市场参加者们的信用状况进行调查登记,将记录资料输入电脑数据库,数据库一直连续跟踪客户的信用变化情况。当金融机构需要调查某一位客户的信用时就要向信用记录公司购买该客户的信用记录资料。信用记录公司提供有偿的信用服务,就变成了信用信息公司。目前美国的三家信用记录公司几乎将所有参加金融市场活动的美国人的信用都给记录了,并通过互联网络通讯技术,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在线服务。
通过这种机制,把信用好的人与信用不好的人区别了开来,并诉诸于社会进行评判和选择,若是有不良信用记录而被置于“另册”或“黑名单”上,就会被社会视为“艾滋病人”或其他“危险病毒”携带者那样加以对待,这对其自身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可见这种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信用制度创新,其警示作用与威慑力量是可想而知的,它对营造一个更为健全的市场环境有着重大帮助。
4 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信用文化建设的方向
在传统社会,信用主要表现为一种人伦信用关系,就是说人们之间发生经济往来时,主要依靠双方之间的道德信任、道德默契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依靠无字无据的“君子协定”来使双方自觉地履行经济义务或其他义务。这种信用关系的特点是:第一,较为模糊。一般性地要求诚实信用,但应达到何种程度,却没有任何量化指标;第二,约束机制方面侧重软约束,即主要依靠社会舆论来保证。背信之人、之行受到的是社会舆论谴责,仅此而已,难有进一步的惩罚;第三,从作用范围看,常常是很狭窄的。由于约束机制较为软弱,人伦信用关系很难在较广的范围内,或在素不相识的人之间实际发生作用,多是限于朋友、亲戚、邻里之间或较为熟悉的人之间,带有较浓的人情人伦色彩,所以是一种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特殊主义信用;第四,从价值取向看,在义利关系问题上,人伦信用关系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强调信用关系是道德义务,应自觉履行,否则便是不义之人。
我们认为,人伦信用固然有它的优点,如充满人情味等(传统社会的信用状况因此而常被一些人美化为“淳风美俗”,也流传着不少“一诺千金”的故事),并且仍为现代人所必需。但我们应看到,人伦信用是从传统社会里相对封闭的各式共同体吸收信用资源的(如亲缘、血缘、地缘等),这显然适应不了新时代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普遍化,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和复杂,交换常常是跨地域、跨国度、跨文化进行的,人员流动性较大,传统的重复式、人情式交易愈来愈被非重复式、非人情化交易所取代,这时仅仅依靠人伦信用关系无法满足流动的、分化的、异质的个体之间的经济秩序需要。于是必须借助于以法律为保障和后盾的契约信用关系。
契约信用关系是人们之间发生经济交往时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其特点是:第一,其要求具体而明确,往往伴有量化的指标来衡量信用关系的实现程度和可靠程度。信用评估是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不仅对企业进行信用评估,而且也对国家进行信用评估;不仅有定性分析,更有定量分析。第二,约束机制硬化。主要是借助法律权威监督和保护;信用遭到破坏时,对责任者要实施惩罚和赔偿。第三,作用范围广泛,突破了血缘性和地缘性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起来。不仅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们中起作用,而且突破了国界,成为国与国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纽带。第四,在价值取向上,虽然也强调义,但更强调的是经济利益,强调信用双方或各方独立的经济利益。
契约信用的根本在于法制。契约是市场交换关系的法律形式,或者说是法律的延伸,契约信用关系的建立和正常运行,必仰仗于强有力并且公正的法律权威。前市场时代之所以不得不主要借助人伦信用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制不健全,经济交往常常得不到法制保障,即使形成了文字契约关系,也会受到强权和暴力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市场经济既是信用经济,又是法制经济。所以对处于转型社会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来说,加强法制建设刻不容缓。
契约信用建设是一个关乎着“法治”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对此,我们必须从认识上廓清两点:
第一,信用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一般道德伦理层面,也不仅仅局限于商业或经济的层面,而且也应上升到政治层面。现代西方民主法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信用制度。在这个制度架构中,具有契约性质的法律对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进行了界定,这既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建立了一道屏障,以防止前者对后者的任意干预,同时又明确了双方是一种权利义务对等的关系。在这种社会政治秩序中,所谓“权利”与“守法”就是靠法律权威机制在各主体间建立起的一种“信用关系”。封建时代由于没有法所设定的权利界限与屏障,所以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臣民们的人身权利很容易随时受到侵犯,对统治者而言,又有何“信用”可言?若有,恐怕也只能依靠“君”们的良心未泯。可见在人伦信用主导的时代,信用约束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十分苍白而无力的。
第二,守信履约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觉悟问题,又不单纯是个履约能力问题,而是关系到更为复杂的制度因素与文化背景,这只需要看看当代中国社会国有企业之间“三角债”的大量存在就可发现,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现代信用制度的作用效力不够灵验;而法院虽对一些合同债务案作出了判决,但强制执行又会引起某些社会后果(比如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加之地方保护主义,等等这些非法律因素又使契约(合同)信用制度的严肃性大打折扣。可见,完善产权制度是信用建设中不可绕过的重要环节。
收稿日期:1999—0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