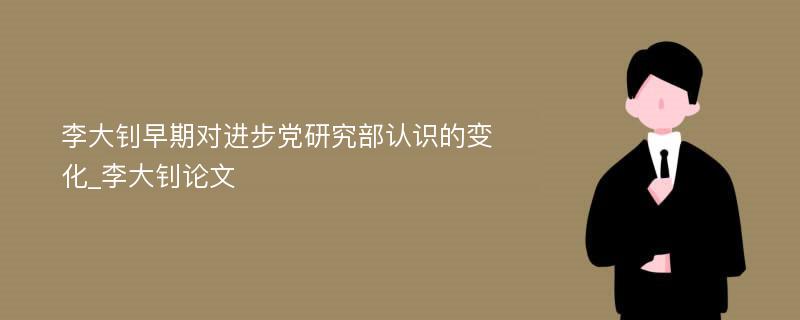
早期李大钊对进步党研究系认识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步党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早期李大钊不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过程的。早期李大钊同进步党研究系存在着较密切的关系,只是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步党研究系保守反动的面目逐渐显现时,李大钊才逐渐转向研究系的反面,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李大钊的思想转变的内在动力在于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早期李大钊是民主主义者,他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如何得以形成的呢?早期李大钊是不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呢?要认识这些问题并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回答,就不能不考察早期李大钊思想的演变和发展。研究早期李大钊对进步党——研究系认识的变迁,可以窥见李大钊早期思想发展的线索,从中发现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复杂性及其所具有的特质。本文试图以民国后政局演变为总体背景,以进步党——研究系政治意向的变化及其活动的逐步展开为脉络,以李大钊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考察为基点,全方位研究早期李大钊对进步党——研究系的认识过程,力图勾勒出李大钊早期思想演变的轨迹。
一、民国初年,李大钊受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其政治主张与进步党相近。
民国建立后,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资产阶级改良派幻想在袁世凯政府内进行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3年5月29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在北京召开合并大会,正式组成进步党。黎元洪是名义上的领袖,党内实权操纵在梁启超和汤化龙等立宪派人物手中。进步党标举的政纲是“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①它明确表示要以“国家主义”对抗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以“建设强善政府”为袁世凯反动统治效力,反映了进步党的反动性。
民国前后,李大钊所接受的是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受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李大钊1907年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读书,1913年暑假从该校毕业。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是随着君主立宪活动的展开而创办的,李大钊从这所学校所受到的影响基本上得自君主立宪派,表现出拥护政府赞同改良的政治意向。第一,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李大钊站在进步党一边,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分权。李大钊在1914年3月发表文章主张中央集权,认为由革命时期的各省纷纷独立所造成的都督权重现象会导致“暴君歇而暴民兴”的结果。②他认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裁督”,实际上主张裁撤掌握地方实权与袁世凯对抗的国民党都督。他甚至说:“今人不察,徒龂龂于中央之是防,而不知跳梁违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不在中央而在地方也。”③这与进步党拥袁主张是一致的。第二,在对待国民党问题上,李大钊与进步党一样采取了反对的立场。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国民党人奋斗的结果,国民党革命派对推翻帝制实行共和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大钊受君主立宪派的影响,对国民党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早在1913年4月他发表《大哀篇》明显地把矛头指向国民党人。他说当时政象是:“骄横豪暴者流,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众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流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于吾民何有也!”④李大钊对政象混乱的深切忧虑和对人民痛苦的同情,表现了进步的思想。但他所指的“骄横豪暴者”,从他用的词语“傲岸自雄”、“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以及借“豪暴者”之口所说的“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一语来看,显然是指为辛亥革命立下功绩的国民党革命派,也就是说李大钊把国民党革命派作为政治批评的主要对象。如果说这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宋案发生后,李大钊继续发表文章强调“宪典昭示之日”就应废除都督、完成中央集权的国家建设,那就公开地把矛头指向国民党革命派了。他说“皖赣湘粤,傲岸自雄,不待宋案发生、借款事起,始有离异之迹也。”⑤以上两点,足见李大钊受进步党影响之深。
李大钊在民国初年受进步党偏见影响之深,章士钊的回忆也说明这一点。章士钊说:“据吾所知守常(李大钊)初从汤济武(化龙)孙伯兰(洪伊)游,谈政臭味,与进步党相近。”⑥事实正是这样。1913年夏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即去北京,接交进步党人汤化龙,并办《法言报》,后又受进步党的资助留学日本。据李大钊被害时的报纸所载:“李(大钊)在该校(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结识孙洪伊,复由孙介见汤化龙,二氏皆器重之,即共同出资送往日本留学,此为李立世之始。”⑦当为可信。可见李大钊此时与进步党的关系非同一般。⑧。
民国初年,李大钊的政治主张与进步党相近,是有深刻的原因的。第一,李大钊所接受的教育深受立宪派的影响。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六年,所接受的是改良主义思想的熏陶,而且在北方,君主立宪有很大的声势,相比较而言,国民党革命派的影响则不大。由此,当时李大钊从自己思想实际出发,拥护现行政府,主张改良,其主张与进步党相近并不为怪。第二,民国初年,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状况,也使李大钊更倾向于进步党。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国,国民党革命派以为帝制推翻革命告成,大都揠旗息鼓,声势不大,即使是孙中山也想不过问政治而致力于经济建设。而君主立宪派则极其活跃,以在议会中多占席位,左右政局。客观形势也使得李大钊倾向于立宪派。第三,李大钊的认识也处在一个急待发展的阶段。1913年李大钊24岁,世界观正在形成之中,而此时他的思想基本上是改良主义,因此对政局的分析必然失之偏颇;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政党在政治活动中可以说才初步展开,其本来面目需要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因此李大钊对进步党的认识需要不断地加深。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李大钊此时的政治主张更接近于进步党,这就不足为奇了。
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此时政治主张虽然与进步党相近,但他与梁启超、汤化龙之流却有很大的不同。一者,他不是要依附袁世凯找官做,进行政治投机,而是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深挚的感情;二者他敢于揭露弊政,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表示极大的不满,力图以改造社会为己任。这是与进步党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以后李大钊思想不断发展,最终与进步党彻底决裂的内在思想原因。
二、袁世凯复辟时期,李大钊逐步偏离进步党的政见,奉劝进步党与国民党合作在“政治正轨”内与袁世凯专制作斗争,对进步党参预的护国战争表示拥护。
李大钊对进步党的认识,是随着进步党活动的展开而逐步加深的。进步党执行依附袁世凯排斥国民党革命派的政策,1913年7月,当袁世凯提出要熊希龄组阁时,进步党积极支持。几经讨价还价后,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汤化龙也出任众议院议长。这表明进步党在政府和国会中的地位有所提高,立宪派加紧了与封建军阀的勾结。进步党实行排斥国民党人的政策,汤化龙居然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⑨对进步党这种排斥国民党的政策,李大钊表示了明显的反感。1913年9月1日发表《是非篇》指出:“一年以来,由党见之故,诬蔑轧倾,不遗余力。”⑩这之中也包含对进步党的批评。1913年8月进步党人梁启超为支持袁世凯当选正式总统向袁世凯建议:“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进步党附和“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怪论,以便使总统凌驾于宪法之上,助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一时舆论为袁当总统摇旗呐喊,浊浪声起。对此,李大钊著文指出:“前参议院之权能,议决者法律也,非宪法也。大总统之权能公布者,法律也,非宪法也。”(12)李大钊旨在从学理上说明总统与宪法的关系,不满当时拥袁为总统而不先制定宪法的舆论,反对总统凌驾于宪法之上的行为,实际上婉转地批评进步党依附权势、违背民意和政理的做法。
当时国内政局的变动,袁世凯野心的膨胀,也引起李大钊对进步党政策的思考。袁世凯的目的并不是当正式大总统就止步,他帝制自为独断专行的野心日益暴露。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于1913年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资格。1914年初袁世凯开始遗弃进步党。对袁世凯的野心,李大钊有了初步认识。这时李大钊希望进步党改变态度与国民党联合,组成“政治对抗力”在法律的范围内同袁世凯专制抗衡,遏制袁世凯专制主义的发展。李大钊回顾了辛亥革命中革命派与立宪派合作的历史,指出进步党与国民党合作的重要性。他说:“武汉义声,江湖震动,举国人士,鉴于满清之不克与图存,温和政社,相率奔驰运动,而亦同情于激进派之主张,并力以赞改革之新运,共和遂以告成。设非二派同心协力,仍相背驰,则革命之成否,未可知也。”(13)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李大钊奉劝进步党:“党派分流,势力削弱,所谋遂亘数年而各无所成”,特别是政党之间更“不可互相水火,与人以渔夫之利。”寄希望进步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抵袁。李大钊的这些言论是在进步党的机关刊物《中华》上发表的,“对于进步党(改良派)的批评,更为精到而切中要害。”(14)1914年8月李大钊发表《风俗》的文章告诫进步党人放弃拥袁的方针,“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不要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助桀为虐。李大钊对进步党依附袁世凯寻官做的政客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势在一党,则蝇附一党,势在一个,则狐媚一人,既以贿而猎官,更以官而害民,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各择其地位之便,从而发挥其才智聪明,尽量以行于恶。”(15)这表明,李大钊在思想上开始背离进步党。
进步党在护国运动中的表现,使李大钊在实际行动中又表示支持。1915年8月,袁世凯指使党徒组织筹安会,公演帝制丑剧。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大为不满,由拥袁立场转变为反袁立场。8月末,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说袁世凯就任总统时“宣誓之说”,“历历在目”,现在称帝是“食言自肥,匹夫贱之”,“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16)汤化龙也在《顺天日报》上发表通电,斥责袁世凯复辟帝制“非时代所能容,倘不立即下野以谢国人,千夫所指”,必至无病而死。(17)与此同时,在政府中供职的进步党人大部离职,转到反袁的阵营,掌握了护国运动的领导权。此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对进步党的反袁行为表示赞同,积极参加反袁的留日学生总会,主张进步党与国民党共同合作起兵反袁,并为护国军积极捐款。1916年初,李大钊弃学回国,并准备参加讨袁的护国战争。由于护国战争主要是进步党发动和领导的,同时也由于进步党此时对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所以此时李大钊对进步党表现一定的好感。
在这一阶段,李大钊的政见与进步党有明显的不同。既然李大钊是在进步党的资助下留学日本的,此时李大钊为什么在思想上开始背离进步党呢?这是因为李大钊留学日本,视野开阔,思想发展的缘故,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加深。李大钊在日本接受的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对李大钊民主主义思想意识的生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李大钊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当是章士钊及其所创办的《甲寅》杂志。《甲寅》杂志出版后,李大钊投书章士钊并投寄《风俗》一文,一起发表在1914年8月出版的一卷三号上,这是李大钊在文字上与《甲寅》合作的开始,在此后的一个时期中,李大钊深受章士钊影响,政治上与章士钊相当接近,甚至也被时人当成是“甲寅派”,从而与进步党关系更为淡薄。章士利的回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问题。章士钊回忆:“1914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识其人,朋友中亦无知者,不获已,巽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至,于是在小石林町一斗室中,吾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及与余交,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当时高李齐名,海内号甲寅派,胡适之曾屡之道,高谓皖士高一涵也。”(18)李大钊作为受进步党着力培养的人,这时转而接近曾参加辛亥革命并且正在积极进行反袁斗争的章士钊,这不能不说李大钊开始摆脱进步党的表现。(19)与章士钊相识后,李大钊经常到章士钊的住所讨论各种问题。章士钊学识渊博,他的调和论、养成政治对抗力主张以及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大钊,这是李大钊对进步党看法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从李大钊这一时期的著作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三、段祺瑞控制北京政权后,李大钊加深了对进步党本来面目的认识,最终与研究系彻底决裂。
袁世凯复辟败亡后,北京政权实际上为段祺瑞所控制。这时进步党分成两会,一是以汤化龙、刘崇佑、梁善济为首的“宪法讨论会”;一是以梁启超、王家襄、林长民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1916年11月下旬,他们又合组为“宪法研究会”,被称为“研究系”。“研究系”是进步党的继续,执行拥护段祺瑞的政策。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迅即被进步党拉了进去,担任了研究系筹办的机关报《晨钟报》的编辑主任(即总编辑)。如前所述,李大钊留学日本后政治上已与进步党分手,那么此时李大钊又为何进入研究系(先前的进步党)的阵营呢?依笔者之见,主要有三点原因:其一,李大钊为进步党所资助而留学日本,留学期间使用过进步党的经费,而且汤化龙与李大钊的私交不同一般,所以李大钊回国后碍于私人情面只得答应为研究系办报纸。其二,李大钊留学日本后与进步党在政治上虽已渐渐分手,但进步党在讨袁的护国战争中表现出积极态度,李大钊对此抱有好感。李大钊这时思想体系还从属于改良主义,希望通过改革的途径实行国内宪政,因此他此时对研究系还抱有幻想,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研究系,从而影响国内政治。其三,李大钊在留学日本期间思想有新的发展,民主主义思想得以生成,如他说:“群枢倾子朝,未必不能兴于野,风俗坏于政,未必不可正于学”,“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20)认识到思想启蒙的迫切性。因此他希望能通过《晨钟报》这块阵地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李大钊以后在《晨钟报》的言论也说明这一点。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李大钊接受了研究系的邀请,出任《晨钟报》的总编辑工作。很快,李大钊与研究系的矛盾公开化。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李大钊发表创刊辞——《<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提出了改造中国的希望,认为社会改造“不在白首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逐渐地抛弃思想中的改良成份。李大钊把“再造”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宣告“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国家丧其青年,则其国无生机”;“青年者,国家之魂”。声明《晨钟报》为“青年之舌”,“青年之友”,担负起“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21)李大钊的言论不能为研究系所容忍,他所声明的办刊方针当然也不能为研究系所接受。终于仅22天(8月15日——9月5日)时间,李大钊就发表声明脱离《晨钟报》,对“所有编辑事项,概不负责”。(22)李大钊又为何迅速脱离《晨钟报》与研究系分离呢?主要是李大钊在《晨钟报》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对研究系依附段祺瑞的政策表示反感的缘故。他在1916年9月4日《晨钟报》发表《别泪》隐含地表明自己当时的心态及其对研究系的态度。他说当时中国有三支政治力量,“甲支”是“专好交结官僚豪暴之弟,因之浸染恶习甚深”。这是暗喻北洋军阀。“乙支习与游侠者游,好问人间不平事,间有流于躁暴者,但其奋斗勇往之精神,盖百折而不挠。”这是暗指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现较多的肯定态度。“丙支”是“势力为最微,于是群相为谋,咸谓非亲近甲支不足以自存”。这是暗指资产阶级改良派研究系,揭露了研究系依附北洋军阀的行为。李大钊借喻自己为“丙支中一少年迪穆者之未婚妻”,写信给“迪穆”,(23)和他“绝别”,奉劝他“此后之行动勿过于随波逐流,于断岩绝壁之前,稍一自持;天不绝人,沈沈堕落之深渊,或能自岩而返。妾纵漂泊天涯,得闻君子忏悔之音讯,转穷途之身,仍当求所以效命于君子之前矣”。(24)反映李大钊“绝别”时还带有依恋之情。《别泪》总体格调是奉劝研究系悬崖勒马,好自为之,希望研究系“珍重珍重”,能够回心转意,言下之意颇带依恋和婉惜之情,并未要与研究系割断一切关系。李大钊稍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谈到:“方愚去某报时,临别赠言,尚托辞寓意以为调劝。”(26)这正反映李大钊当时的心情。
张勋复辟,研究系依附反动势力的丑恶行迳暴露无遗,促使李大钊与研究系进行彻底的决裂。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戴宣统复辟。梁启超亲赞戒机,成了段祺瑞的首席幕僚,军中所发重要文告多出其手中。其他研究系分子汤化龙、林长民等也通电声讨张勋,对段拥护备至。段祺瑞重新掌握政权之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入阁者五人,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汤化龙为内务总长。鉴于研究系依附段祺瑞的所作所为,李大钊发表《辟伪调和》文章,公开地、毫不留情地声明与研究系决裂,其言论之激烈、揭露之深刻、态度之坚决,超出以往。具体表现为:
其一,李大钊回顾民国以来的政治,揭露进步党、研究系代表的“缓进派”依附军阀排斥国民党革命派的反动实质。李大钊指出,民国建立后“缓进派则以为袁氏之势力大足倚为抗制急进派之资,于是相率而趋承之缘附之。政客之运动,论士之言谈,乃如万派奔流,众矢一的,悉注重于拥护强力排斥激进之一途。于是有最流行之语,不曰中央集权,则曰强固政府;不曰临时约法之束缚太甚,则曰总统制之适于国情。酿酝之日未久,鼓吹之效大张。未几,而袁氏以兵力铲除民党矣。未几,而袁氏以武力劫夺总统,随即解散国会矣,而癸丑之局以成。又未几,而约法毁废、参政院成矣。又未几,而神武建号、洪宪改元,而帝制之以起。急进派既归失败,缓进派亦遭屏绝。缓进派诸公乃翻然变计,反其向之所为,护国军兴,或则驰入军府,躬参密勿,或则洁身海上,遥为声援,倒袁之役,厥功亦不可没。”然而袁世凯败亡后,进步党研究系又重蹈覆辙,对国民党革命派采取“援引轨道以外之暴力以为抵制”。李大钊感慨道:“诚不断缓进派诸公,竞一再援引特殊势力之嫌,而终不觉悟。观其党魁致辞,报章著论,不曰特殊势力为今国家所托命,则曰破坏旧势力无异破坏国家。”(26)通过对民国后政治斗争的回顾,揭露了进步党研究系一贯依附反动军阀的政治立场。
其二,李大钊通过对进步党——研究系历史的考察,指出缓进派虽以中间人自居“调和”矛盾,其实与北洋军阀一样都是“旧势力”的代表。李大钊指出,缓进派与北洋军阀紧紧勾结在一起本质上已毫无区别:“环顾北京政治之舞台,兴高采烈之政客,则半为缓进派之魁俊。某也长财政矣,某也长内务矣,一堂济济,相与庆再造之丰功,赞光复之盛兴矣。”(27)“而缓进派与官僚武人相结,附敌同攻,助纣为虐,而一而再,不自悛悔,咎固亦居其强半,虽百喙而莫可辞也。”(28)研究系明明是站在北洋军阀一边为统治者效力,可是往往又以“调和者”的面目出现。对此,李大钊反问道:“缓进派诸公既以调和自任,胡以与特殊势力相周旋晋接之际,不闻建一言陈一义焉以促旧势力之觉悟,使之稍与新势力以自存之余地,而日惟奔走相告,以戒急进派。”(29)通过分析,李大钊指出:“缓进派当然亦在旧势力之列”,“缓进派时时在特殊势力卵翼之中,即特殊势时时在缓进派指导之下。”李大钊认为,缓进派与旧势力举的是同一旗帜,政治信念“相近而可一类视之”。(30)这表明李大钊此时与研究系已彻底决裂。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与研究系决裂的过程中对自己过去与进步党“过从颇稔”进行了自我反省,认为对进步党研究系已不敢作任何“奢望”。(31)
李大钊与研究系彻底决裂后,就勇敢地批驳研究系的反动谬论,毫不掩饰地阐明自己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1917年10月李大钊发表《暴力与政治》文章,批判梁启超所谓政治高于法律的观点。梁启超主张让法律上的主权屈服于事实上的强力的观点,实际上是屈服于反动军阀的统治。对此,李大钊指出:“事实上之强力,苟其与法律之主权不属于一体,则必当依法律上之主权以行动,不当反法律上之主权以为行动”,否则,就是“非法之暴力”。而对于非法之暴力,“则社会督责,公民逆命,自有制裁之道矣。”对于梁启超反对革命、宣传“革命不能产出良政治”的观点,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梁先生既反对革命,而独不反对暴力,有时且与暴力相依为命”,揭露了研究系依靠军阀“强力”的本质。针对梁启超反对革命的论调,李大钊指出:“故反对革命者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32)对研究系反动观点的有力清算,表明了李大钊鲜明的政治立场。
当然,李大钊在与研究系公开决裂的过程中,在理论上也是有不足之处的,突出地表现为受章士钊思想的影响。虽然此时李大钊与章士钊在政治上的合作关系已结束,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受章士钊思想的影响。李大钊“辟伪调和”是为了希望出现“真调和”,实际上是要求以梁启超、汤化龙为代表的研究系与章士钊为代表的政学会合作来共同对付北洋军阀。他在批判研究系时力图说明梁、汤与章之间在过去的政争中是有“调和”之处的。他写道:“历次政争之起,究因急进派欲破坏旧势力乎,抑因旧势力不容纳新势力乎?以愚所知,急进派多数之纯正思想,固未尝有破坏旧势力之迹,且与之调剂、与之融蛤,不遗余力。此即观于辛亥之取消南京留守府,而举袁世凯为总统,丙辰之取消肇庆军务院,而认段祺瑞为总理,足以证之”。(33)以此说明研究系与政学会有调和的可能,能出现所谓“真调和”,进而与封建势力对抗。可见,李大钊在与研究系进行彻底决裂的过程中还受章士钊政见特别是“调和”论的影响。
民国后中国政治变化复杂,险象环生。进步党及以后的研究系也以不同的面目活跃在政治舞台。随着李大钊自身思想的变化和对社会政局的不断考察,他对进步党研究系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研究早期李大钊对进步党——研究系的认识过程,可以发现早期李大钊是从改良主义立场出发的,而逐步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在李大钊早期思想中,民主主义因素逐渐增多并超过改良主义因素,最终完成由改良主义到民主主义的思想转变。就总体而言,早期李大钊确是民主主义者,但不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注释:
①谢彬:《民国政党史》,第54页。
②《更名龟年小启》,《李大钊文集》(上)第21页。
③⑤《裁都督横议》,《李大钊文集》(上)第32页,35页。
④《大哀篇》,《李大钊文集》(上)第4页。
⑥(18)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
⑦《晨报》,1927年4月30日。
⑧目前有些论文或专著说李大钊在1913年加入进步党,据笔者查考,尚无史料充分说明这一观点。
⑨《时报》,1913年7月24日。
⑩《是非篇》,《李大钊文集》(上)第60页。
(11)《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转引自《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上)第4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李大钊文集》(上)第62页。
(13)《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李大钊文集》(上)第102页。
(14)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第26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20)《风俗》,《李大钊文集》(上)第93页,92-93页。
(16)《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第96页。
(17)华觉明:《进步党与研究系》,《文史资料选辑》第13集,第118页。
(19)李龙牧:《五四时期思想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21)《<晨钟>之使命》,《李大钊文集》(上)第177-182页。
(22)《李守常启事》,《李大钊文集》(上)第217页。
(23)“迪穆”是德谟克拉西(Democrac--民主)的谐音。李大钊以“迪穆”的未婚妻身份讲话,其寓意是深刻的,表明要做一个民主派。
(24)《别泪》,《李大钊文集》(上)第213-214页。
(25)(26)(27)(28)(29)(30)(31)(33)《辟伪调》,《李大钊文集》(上)第511页,506-507页,508页,509赠,507页,505-506页,511页,507页。
(32)《暴力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第524-525页。
标签:李大钊论文; 进步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历史论文; 梁启超论文; 袁世凯论文; 章士钊论文; 甲寅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