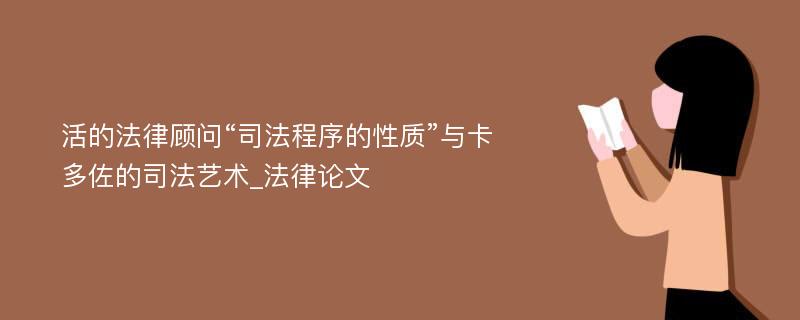
活着的法律宣谕者——《司法过程的性质》与卡多佐的司法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法论文,性质论文,过程论文,法律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卡多佐的思路直截了当,清晰而富于逻辑;身为法官,每天都要与法律打交道,处理永远也不可能有个尽头的案件,日常工作其实十分单调而刻板,冗繁却又不可掉以轻心 。总体而言,绝大多数案件事实清晰,规则明确,法官的职责只是将规则与事实两相连接,藉司法之具,凭法官之口,代言法律之声,而落实公正之实。但是,还有一部分案 件,为数甚少,却属于所谓的“疑难案件”,一时间难以下判,需要法官慎思明辨,基 于“理性和正义”,在先例与成规中,于考量社会与文化背景之后,寻找、提炼出正确 答案,从而发现或者标立新法。此一过程亦即所谓的“法官造法”——一个经由司法来 实现的有限度的立法过程。正是这一职责,催生出司法过程的立法性质,展示了“法律 的成长”的内在机制,揭示了法律的功能与目的。而法官在此过程中究竟可能、已经和 应当担负起什么职责?在践履这一职责过程中,法官不可避免要面对的法官立法及其边 界又是什么?如何发现和解释立法旨意,特别是力保法律对于人类情感作出真切的呼应? 凡此种种,均连带而出,同样既是司法本身,又是司法的真切语境。卡多佐正是通过对 于这些问题的描述和阐释——常常是饱含感情的描述和阐释,向世人展示了究竟“司法 ”为何与如何,其然与所以然。
本文顺延卡多佐的思路,借助大法官之眼,在理叙卡翁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过程中,省视经由司法的法律成长这一普通法主题,并衍展开来,旁及其所透显的普通法世界事实与规则、法制与法意和人生与人心间的诸般纠缠。全文共分五个部分,自卡翁所揭示的司法过程的起点,追论至立法旨意的发现和阐释、影响判决的因素和方法,而以对于上述诸般纠缠的重新分析作结。
一 三类案件与三项职责
《司法过程的性质》(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将普通法传统下法官日常处理的案件简要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案件的事实与规则均甚简明,所要思考的只是“对事实如何适用法律规则”。(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2—3页。 )这些案件构成了法院的大部分事务,甚至于“堆积成山,令人乏味”。(注:[美]本杰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页。)不过,相对于后述案件,其答案通常是确切不移的,甚至是惟一的,“只有一条路、一种选择”,(注:[美]本杰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因而,大部分法官在自己大部分的时光里,历练既久,阅世多矣,如何处理,多半早已成竹在胸。
在第二类案件中,事实是明晰的,规则也是确定的,但是规则的适用却成问题,答案 常常也并非惟一的,因而需要法官斟酌诸端,综合为判。
第三类案件的数量较少,甚至很少,但却属于通常所谓的“疑难”案件。当然,“疑难”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重大”案件。在这些并非习常的案件中,相关规则尚付阙如,或者呈现出诡谲的不确定性,法庭因而具有作出多种判决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面对同样的事实,法官“可以找到言之成理的或者相当有说服力的理由来支持这一种结论或者另一种结论”。(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4页。)在卡多佐看来,如果说前两类案件不论如何判决都还尚未“触动法理”的话,那么,此种案件的判决之最后达成,却必然会“触动法理”,对于既有的规则体系和意义体系来说,甚至会伤筋动骨;(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4页。)如果说法官对于前两类案件的处理不过是在“适用法律”的话,那么,正是在这里,法官经过周密权衡,审慎揆度,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中最终作出自己的选择,从而“承担起了立法者的职能”。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并非只是发现法律,“而是创造法律。”——虽然只有极少数的法官在极少数的时候享有这一禀赋、才干和幸运。(注:以上详[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 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5页。)
基此,卡翁喟言:
所有的怀疑和担忧,希望和畏惧都是心灵努力的组成部分,是死亡的折磨和诞生的煎熬的组成部分,其间,一些曾经为自己的时代服务过的原则死亡了,而一些新的原则诞生了。(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5页。)
换言之,这类案件的判决一经宣告,即意味着一种关于对与错、合法与非法的新的标准问世了。(注:[美]本杰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作为一种新的先例,它为后续同类案件敷设规则,为同一领域内的人世生活烛照未来。有时候,个案的判决所蕴涵的伦理与法理,甚至会发散开来,持久地影响广大的公共生活,乃至于对于公众的精神生活产生重大冲击。
这里,卡翁经由归纳三类案件向我们展示了普通法传统中规则世界的复杂情景。首先,法律,包括凯尔森意义上作为“个别规范”的契约和判例,它们本身就存在着“隐含之义”;其次,规则之间存在着“空白”,甚至是相当程度的空白——它让我们想起此前布莱克斯通的“法律空白”这一意境,霍姆斯大法官的“法官即空隙立法者”的著名论断和此后哈特的“法律的空缺结构”这一指谓——当然二者并非一回事;(注:详Southern Pacific Co.v.Jensen,244 U.S.,205,201(1917)(法官异见);[英]哈特:《 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以下。)再次, 法律理性的逻辑连贯性、匀称性可能断裂或者扭曲,而表现为“疑问”与“含混”,因 而出现需要淡化——如果不是回避——的错误。(注:以上均详[美]本杰明·卡多佐: 《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页。)凡此规则的三种情形, 主要表现在第三类案件中,而赋予普通法体系中的法官以三项任务,三项不可回避的职 责,即发现“隐含之义”,填补“空白”之处,衔接、修补法律理性的逻辑连贯性或者 一致性。(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第60—1页。)用卡翁在稍后的另一部作品中的优美语句来表达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理论:期望法官透过瞬息万变的波动,发现更为深层的原理原则,将它从正在流逝的特定潜流中拯救出来。(注:[美]本杰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译文略有修订。)
正是在履行这三项任务的过程中,法官依据“理性和正义”,经由阐释判决理据,发现并宣告事实所隐含的规则,规则背后的原理和原则,从而宣示法律。在卡多佐看来,这是法官的日常作业,更是法官不可推卸的义务,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的职责。(注:以上分别详[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6,65页。)——或许,这也就是一种在“法律帝国”里找寻德沃金意义上的“ 惟一正确答案”的作业。为此,才需要法官立法,司法也才真正获得了立法的合法性。
现实生活本身恒定而恒变,但却要求另有一个虽然恒变但却恒定的规则世界以为凭恃,为人间世营造秩序感和规则性,所以要有一个“惟一正确答案”来加以安顿,虽然从非法学的终极意义上来说,此亦水中捞月,沙上之塔。但就法学意义而言,总括上述三项职责,大而言之,则法官和法庭的职责正在于调理事实与规则之间的积极互动,力保 法意与人情之间流转顺畅,从而营造出一个有序、和谐的规则世界,给实存的人世生活 一个至少看上去坚实的凭依,“好歹有个讲理的地方”,并且提供道理让大家公开地讲 ,从而安顿一方水土的人生与人心。正是在这里,极少数伟大的法官,一如维科的“第 一立法者们”,(注:Donald R.Kelly,The Human Measure:Social Thought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38.)明知终极意义上 的规则世界的无序,却又务须为俗世人生维系乃至凭空造出一个人间秩序来,而信誓旦 旦规则体系之确凿不谬。身处此豁,充溢心灵而常常压抑心底的,便是一腔悲悯,乃至 于略经化解而后得的尽万一以救世的“悲凉的美感”了,一种充满同情的就事论事、将 心比心了。“大法官”霍姆斯们和卡多佐们,平生志业,惟物事与人事、法理与情理, 洞悉既博,感慨必厚,而一恭敬践履,漫长从业岁月里赋信于上帝,一终生独处,将自 尊换形为谦恭与幽居,岂偶然哉,岂偶然哉!——三类案件与三项职责,其不易乎!?
二 立法旨意的发现与填补
职是之故,对于“隐含之义”的查索,“空白”之处的填补,乃至对于法律理性逻辑连贯性和一致性的衔接或者修补,某种意义上,首先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立法旨意”的查找过程,或者说对于法律原意的发现过程,如果这一旨意或者原意的存在本身乃是不言自明的话。
那么,所谓的立法旨意或者法律原意,包括宪法条文所隐含的立宪者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卡多佐通过征引德国法学家布鲁特的话,指它不仅意味着“实在法的深层含义”,(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页。)而且,它意味着——再一次地,卡多佐借用同时代学人约翰·齐普曼·格雷教授的话说——是当初的立法者面对今天的情形,他当时不曾想到,而此刻“可能会有 什么样的意图”,(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 书馆2001年版,第5,51页。)进而,它意味着是对于“法律精神”的发现。(注:[美] 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1,6页。) ——一个似乎是从现象世界往形上世界层层深入、逐次上攀的运思。如果当初的立法者 之所以如此立法是为了因应当初的情境,满足当时的优位需求,那么,很多时候,今天 的法官对于法律的“原意”的解析,事实上便是对于当下时代“需求”的宣示了。经由 诉诸判决理据所实现的法律解释,司法者移花接木,暗渡陈仓,为自己的时代“需求” 张本。原来,所谓原意者,自文本的逻辑一致性连带递生、推演而来之当下心意也。这 就如“法不禁止即自由”,因而,公民的权利不仅载述于法律文本,而且包括尚未得到 承认,但是根据逻辑一致性,从已然获得认可的权利所彰显的正当性理据中,也可以推 导出来的那些权利。此一情形,就如德沃金在谈到“埃尔默案”时指出的那样,“纽约 州的立法者那时不可能考虑到人们会把电子计算机遗留给后代,但是,由此便得出结论 说,纽约州的遗嘱法不包括此类遗产,就不合情理了。”(注:[美]罗纳德·德沃金: 《法律帝国》,李常青等译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而法官之所以能够如此这般,本质上还是因为司法恰恰具有一种回应当下需求,而经由解释,将新意义引入旧规则的功能。很多情形下,普通法的司法技艺就表现在,如果说规则是一只人见人爱的老旧瓶子的话,那么,当下生活中凸显的正当需求便是新酿。卓越的法官何许人也?旧瓶装新酒的老辣饮者也,经验丰富的职业酿酒师也!而一句话归总说到底,是法律本身具有或者应当具有因应当下生活事实的秉性。这是法律总体上之 能存续的前提,也是诸多具体法律规则之能逐渐换形或者消亡的原因。——套用一句名 人名言,则生活(事实)之树常青,而规则总是灰色的,因而,章回小说及其作者,同样 恰如罗纳德·德沃金所言,是一本本难唱的戏呀!
在卡翁眼中,此非惟适合一般的法律,对于宪法的解释亦然。因为宪法所具有的高度概括性赋予自己以循时代变化而理性更张的内容和能量,愈是成熟的公共理性,愈能孕育出如此宪法,而愈是如此宪法,愈是具有如此“内容和能量”。因此,宪法“所宣告或者应当宣告的规则并不是为了正在消逝的片刻,而是为了不断延展的未来。”(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1页。)正因为此,称职的解释者掠过“过渡性的具体问题”,可望达臻“其背后的永恒”。(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 —7页。)在此语境中,对于法律“原意”的解释不仅旨在发现“隐含之义”,而且在于 “填补”其未曾虑及,也不可能虑及,但却应当虑及,倘若可能必会虑及之处。也就因 此,对于既有的法典、制定法和一切判例的评论或者“疏议”,包括否定性的评论,乃 是司法回应当下时代的“人的需求”,从而实现司法职能的必然,更是司法之所以能够 存续甚至“繁荣”的理据。当年,查士丁尼大皇帝禁止后世之人评说《查士丁尼法典》 编纂者的任何作品,卡翁论及于此,小露机锋,调侃人们之所以还记得该项禁令,仅仅 是由于这一禁令毫无结果,可谓入木三分。(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 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页。)
对于立法旨意或者法律原意的揭示总是要委诸具体个人来进行的,虽然这里的个人多半消隐于立法或者司法机构的形象背后,个人的意志也几经辗转而变成公共权力甚至公众意志的声音。如果说立法机构对于“立法旨意”的解释通常总是以“立法机构”这一无名或者匿名的集体形象出现的话,那么,普通法传统下经由判决理据的阐释而进行的立法旨意的“发现与填补”,就总是表现为具体法官的个人性作业了。但是,问题在于 ,既然人总是人,也不过是人,那么,不管他或她被称作法官、议员还是别的什么,毛 病不免,缺陷多多,甚至私心甚重,也就在所难免。一句话,他们、我们和你们,大家 都具备平均数意义上的人性的一切弱点。因而,对于诸如后来发生的“隔离即平等”与 “隔离即不平等”的反复,或者类如“无主土地”(terra nullius)之否定,乃至于大 不列颠联合王国关于黑老头曼德拉及其南非国民大会是否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之出尔反 尔,其情形岂不就是此一是非,彼一是非了吗!?当事人置此是非之下,以一身而敌一国 ——任何法律总是“国法”,任何司法也总是“国家的”,——未待反复早已撒手,对 于他们的“旨意”,司法究竟如何来打理?这样的打理又究竟有何意义呢?总不能耗财伤 神甚至是流血送命之后,换来的只是事后甚至是身后的“平反昭雪”吧!?而且,进一步 说,法官与立法者只能宣示是非,而不能垄断是非,也不可能垄断是非,所谓的当下社 会的“需求”不一,则是非不一,判决泾渭,最后只得如“戈尔诉布什”,看投票比数 ,将司法的理性的、最终的判断权,一骨碌委屈成“大民主”,是非问题陡然间突变为 势力问题,则司法昭昭,赖何安身立命?司法不能安顿自己,所谓的正义等等往哪里安 放?放得了吗?这就正如卡氏之后又半个多世纪的一位美国法官所言,司法“权威”的过 度膨胀,同样可能造成法官并非秉持宪法权威下判,而是“将自己的权威推展到对于国 家的统治”这种未必具有宪政的正当性的结果。(注:Bowes v.Hardwick,478 U.S.186( 1986).)凡此种种,是司法的痼疾,或许无法幸免。卡翁当然明白这些——笔者姑为君 子度,但通观卡翁全部著作,他对相关原理却并未深究,则正暴露了司法和司法者的局 限性,在某些情形下,经由司法主张社会正义的不可能性,同时,也说明了卡氏法律理 论缺乏深层次哲学思考的软弱。
三 四种力量与四种方法
行文至此,我们不由想问,法官究竟凭借什么来发现“原意”或者填补“空白”呢?换言之,法官在对“疑难案件”下判时所需虑及的主要因素为何?哪些因素真实地影响法官的判决?实际循依的具体方法又有哪些?毕竟,“理性和正义”只是原则性的指导,当 下时代“人的需求”也仅为一种目的论诉求,要实现司法过程的上述职责,很显然,需 要循随更为具体的原则,借助切实有效的方法。在《司法过程的性质》以及一年后发表 的《法律的成长》中,卡多佐“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揭示了必须虑及的四种 因素与四种方法。这四种因素即逻辑、历史、习惯和价值,这四种方法即哲学、历史、 传统和“社会学的方法”。当其时,卡翁已过半百之年,由庭下的律师而庭上的“尊敬 的大人”,三十年的法曹历练,过案无数,“老法官了”,面对年轻学子,将此和盘托 出,可谓经验之谈,夫子自道。
第一种因素是逻辑,即事实与规则本身特别是后者的固有的内在理路,构成它们之所以为其自身的一致与连贯。作为案件中先验的存在,它们当然首先而直接地影响到法官对于案件的认识,因而成为一种“力量”或者“势力”。探查其间的脉络,屡述双方的恩怨,这一任务常常落在标名叫哲学的人类认知理性身上,因而,法官运用的第一种方法即哲学方法,当然哲学不仅是逻辑。哲学方法赋予法官经由逻辑推演阐明判决理由,宣示原则的能力。虽有“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的名人名言在,但是,作为一种规则体系,法律必得首先自恰而后自治,始成为规则;作为一种意义体系,法律也必得自恰而圆融,“说法”通达,慰贴心肠,始得被芸芸众生奉为意义,产生信仰,而恰成 意义。而无论是作为规则体系还是意义体系,法律都必须秉有逻辑的一致与连贯,具有 理性化的匀称之善与美,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生活本身如此,应当如此,终极而言,也不 得不如此。因此,上述“名人名言”讲述的乃是法律在发生论意义上的图景,仅仅略涉 其本体论意义,但却绝非统概其认识论意义。所以卡氏才会说除非有足够的历史、习惯 、政策或者正义的因素需予考量,否则,的的确确,“霍姆斯并没有告诉我们当经验沉 默无语时应当忽视逻辑。”(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 ,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8页。)
的确,哲学方法并非最为重要的方法,而“逻辑一致”也“并非至善”,但却是将事实与规则之间的纷纭互动予以理性化梳理的一种无可替代的方法。它也具有这样的能力。从而,它是形成判决理据,乃至于发现“原意”或者填补“空白”的首选。毕竟,任何判决首先必须符合逻辑,逻辑的一致同样是法律的生命。而且,透过冷冰冰的逻辑之幕,法官对于法律的形式和实质的对称性的“智识性渴望”的知性背后,潜藏着的是力保法律对于人类情感作出真切回应的法律本身及其法律从业者的德性。(注:[美]本杰 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9页。)而任 何此种德性,都是下述卡翁揭示的“历史”的产物。正是在这里,卡多佐的论述不仅没 有什么“令人无法忍受的含混”,(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页。)而且,在笔者看来,它们将法律的知性、理 性与德性三维有机统一。也正是在这里,如同后面对于卡氏有关法律的目的旨在促进社 会福利的揭示所展示的,将卡氏的全部法律主张冠以“实用主义”名头实在不恰,尽管 “实用主义”并非贬义。(注:例如,波斯纳法官即认为卡多佐的“《司法过程的性质 》一书的某些引文会使你品尝到一点实用主义法理学的味道”,该书“清楚地阐述了一 种成熟的实用主义法理学”。并进而指证“霍姆斯、卡多佐以及现实主义法学家都是实 用主义者。”正是卡多佐和霍姆斯、约翰·奇普曼·格雷和罗斯科·庞德,特别是霍姆 斯,为后来的现实主义法学奠定了基础。详[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 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28—9,35页。)
第二种影响判决的因素是历史本身。既然任何规则都是历史的产物,演化的结果,历史方法因而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历史方法启示法官在历史语境中考察规则,寻找和发现原则。在笔者解读,也就是使法官置身于事实与规则“之所以来,往哪里去”的故事中,在德沃金“章回小说”的连续性意境中,做一回事实与规则本身,从而一定程度上消解逻辑以及自认为掌握了逻辑之刃的法官有可能任意曲解事实与规则的嚣张。毕竟,对于“逻辑”的探查可能会是逻辑的探查,行为者本人的先见让一切努力变成“庄子注郭象”式的理性的僭越。常人如此,文艺如此,法律理性和理性的承载者的法官也如此。正是出于对此僭越的怵惕,如果说有什么力量足以阻止逻辑推演的无限扩张,则规则之所以由来的历史本身恰恰具有这样的功能。一个法律原理原则常常具有将自身扩张到极限的倾向,导向荒谬,而正是在这里,该原理原则“本身的历史限度会限定其自身。”——正如后面将要述介的“正义和效用”这一因素为司法“发现和揭露逻辑中虚假的成分”提供了利器一样。(注:卡多佐1925年5月1日在美国法律研究协会第三届年会上的 讲话,详[美]本杰明·卡多佐:《法律的生长》,刘培峰等译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37页。)前者作为纯粹理性,受制于历史理性,相互关照相互为用的结果是可 能避免这一荒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实践者的法官对于逻辑的运用,总是在历史 语境中的运用,从而,秉具实践理性和人为理性特性的法律理性将自己与逻辑实证式的 经院哲学区别开来。(注:关于法律理性,详拙文“以法律为业——关于近代中国语境 下的法律公民与法律理性的思考”,载《金陵法律评论》(南京),2003年春季号;“论 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载《中国社会科学》(北京),2003 年第1期。)关于“历史方法”,本文第四部分还将论及。
第三种因素是习惯。习惯不仅具有创制法律的功能,而且制约着法律的运行,特别是对于制定法的功能的实现,其制约性尤为显明。即便是在所谓的现代社会,习惯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现代社会中的许多规则恰恰不过是获得规则效力的新型习惯。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角度来看,则习惯多是传统的产物,也是传统本身,因而,法官判决时考量习惯这一因素,便也就是在考量传统。与逻辑和历史相比,习惯就是习惯,大家一贯就这么着,奉守无违,习而不察,真要讲出什么道道来,有时还真不好讲,可要违逆,它便制你,别人也不答应。职是之故,当逻辑和历史都无所用力之时,为了确知规则或原则的可能成长方向,卡翁体认,法官于是乎不得不转而考量习惯。在涉及基于习惯而发展出来的规则时,情形尤其如此。现代工商社会的许多商事规则,卡 翁回答,也就是演自昨日的习惯而已;而新的生活实践,又会催生出新的习惯。在卡翁 生活的当时,代表着“新”,体现了“蒸汽”和“电的力量”的伟大发明,如铁路和汽 船,电报和电话,已然渐次形成了一些新的习惯,并导致了基于这些新的习惯而来的新 的法律。对于这第三种因素的考量,形成了卡翁所谓的“传统的方法”——不是自过往 一脉传承而来、不绝如缕的老套路意义上的“传统”,而是对于作为既定事实的老套路 本身的考量意义上的“传统”。正是在对于传统,特别是作为当下的活的传统的“生活 ”本身的考量中,法官为疑难案件找寻规则与原则,从而为人世生活阐明规则与原则。 如果说“逻辑”提供的是一个批判的武器的话,那么,“历史”和“习惯”所牵扯到的 则是“事实与规则”这一更为根本的法律问题——一种武器的批判了。只不过习惯将历 史具体化、世俗化,使逻辑更加语境化,甚至彰显出逻辑的非理性。也就因此,进入司 法视野的习惯其实不仅仅只是习惯了:
我们寻求习惯,至少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创造新规则,而是为了找到一些检验标准,以便确定应如何适用某些既定的规则。(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6页。)
正是在这里,整个近世西方法律都在遵循着同一个命题——“一个恒定的假设”:人的习性的自然且自发的演化确定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而与惯常的道德、一般性的关于 “正确行为的标准”和“时代风气”等等异曲同工。卡翁以一个“法律实践者”的身份 讲明,这就是为什么适用规则同样要因应习惯,习惯可能会比“正规的”规则更有“地 位”;而“观俗立法”,是不二准绳。卡翁并举“贸易商号”的成员具有制作或者背书 流通票据的权力为例加以说明,而将论述引导到“事实与规则”层面。(注:[美]本杰 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8页。卡氏用来 说明的案例是:Lewy v.Johnson、First National Bank v.Farson和Irwin v.Williar 、Walls v.Bailey。关于卡氏对于三起案件的著名判决,详见[美]卡尔·N.卢埃林:《 普通法传统》,陈绪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7页以下“卡多佐的 三个阶段”一节。)这一点,本文后面还将论及。
第四种应予考量的因素是正义、道德和社会福利,而表现为“社会学的方法”。——将法律置于广博的社会背景之下,充分考量其涉关人生与人心深处的价值诉求的思路。揆诸卡氏的前后文,可知此处实际讲述的乃是对于事实和规则的价值考问,尤其是对于规则的价值背景的阐释。藉由价值追问揭示规则,阐明规则背后的原理原则,必然牵扯到并必须落实为若干具体价值因素,以对于这些具体价值指标的考量来说明规则的意义之维。这是卡翁心目中的法律不仅是一个规则体系,同时并为一个意义体系这一理路的必然要求。卡翁于此主要列举了彼此关联的“正义、道德和社会福利”三大因素,而分别指涉法的目的、法的目的的伦理指标与功能指标。(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9页以下;[美]本杰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以 下。)是的,正义是法律的目的——一切法或法律的最高目的,而法的目的决定了法律 的成长方向。(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 001年版,第62页。)如何衡量是否正义,“谁之正义”——借用一句套话,则需诉诸“ 社会福利”,也就是整体而言的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利益这一大词。因而,卡多佐氏的法 律理性向我们展现出一幅吊诡兮兮的景象:作为“人民的自由和福利的最终卫士”的法 庭与法官,在对于正义这一价值进行考量时却需要进行社会福利和公共之善等等的功能 分析,讲求法律运行的实际效用,不得不以对于实际效用的功能分析反过来推论价值判 断。(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第43,44,55页。)换言之,所谓正义就在于能够增进社会利益或者社会福利。而究 竟应优先护持或者增进何种社会福利,则又需要反过来秉持正义和效用这两个指标。( 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4 ,45页。)看起来像是循环论证,事实上却是以“将事情办成”,具有实践理性特色的 法律理性的圆融所在。正是在这里,价值判断常常最后超越其他一切因素,在形成案件 判决过程中具有最为重要的“力量”。
在此情形下,卡翁以非常决断的语句写道:
当社会的需要要求这种解决办法而非另一种的时候,这时,为了追求其他更大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扭曲对称,忽略历史和牺牲习惯。(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 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9页。)
这里说的不是别的,正是卡氏申说的法官对于涉案的社会利益或者社会福利的重要性的价值考量。(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9页。)因为上述四种进路都会独立或者共同地作用于经由司法过程而影响法律成长的过程,所以,在具体个案审判中,法官究竟最终会受到哪一种或哪几种因素的影响,大法官认为,这取决于他对于利益的考量,而以保护他所认定的优位价值为己任。非他,正如霍姆斯所言,“掂量社会利益”这一义务是法官不可逃避也“无法逃避的”。——好一个“掂量”二字。(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3页。)进而言之,“掂量”社会利益成为法官正义天平上最有分量的称盘,不正反映了20世纪初年,天下熙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虽自古已然,而在当时的美利坚却于今为烈的合众国“社会背景”吗?由此可以看出,正是此种20世纪初年的美国社会生活,催生出所谓社会法学和利益法学的种种命题,也孕 育了卡氏的法律理性取向。
因此,在进行这一价值—功能的互换分析时,依笔者理解,卡翁进一步引入了一个更具有操作性,也更加不具有操作性的指标,即道德之善这一最高的超越源头。说它更具 操作性,是因为何为正义并非或者不仅仅取决于法庭与法官的个人标准,“而是那些我 有理由认为其他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都可能会合乎情理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注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4页 。)这里说必须诉诸“正常的智力”、“良心”和“合乎情理”诸端,用笔者的用语来 解读,亦即当下社会的“常识、常理与常情”。正是借助人人心中本有、较易衡估的“ 常识、常理与常情”,法律理性通达的是那个被习称为道德的东西,一种指引我们懂得 什么才是最应予以珍视,因而是法律和法庭应予竭力护持的最大价值的慈悲。毕竟,诉 诸“常识、常理与常情”这一行为仍然是法官本人的个体性活动,一旦出现“此一是非 ,彼一是非”的情形——这种现象并非绝无仅有,则法官诉诸的人情之常也不顶事时, 法官又该当何为呢?卡翁提示,正是在这里,“法律应当统一并且公正无私”本身,就 是一项最为基本的社会利益,从而为判断其他社会利益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基本坐标。 法官正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从生活本身获取”作为“立法者的智慧”,从而在“空白 处”立法。(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 1年版,第70—1页。)可是,这不又回到了“正义”这一出发点了吗?因而,也就更加不 具有操作性了吗?虽然上文笔者曾谓此举彰显了法律理性的特有的圆融,可是,在将天 下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这一活剧演到法庭的人们手中,谁能保证它不会变成一种无尽的循 环论证,乃至于险恶的狡辩呢?!而公正明辨如法官者——姑且从应然立论,如下述卡翁 所言,也是常人,那么,谁又能保证他们个个都像卡翁本人在“迈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 案”和“帕尔斯格拉夫案”中那样,将此圆融之术运用得如此圆融呢?!——的确,只有 极少数才智卓越、秉性公正而又天赋良机的“大法官”,才能获赋此任,配当此任。况 且,就像有时候爱国主义可能会成为一顶把人压死的大帽子,而所谓的保守主义的指控 常常等于宣判被指控者的理性和道德破产一样,“社会利益”或者说“社会福利”会不 会变成这样一顶大帽子,这样一种宣判呢?是的,卡翁提供了一个“四维合一”的诠释 框架,在此框架中,逻辑与历史两相释证,习惯与价值彼此印证,最后统归于在正义、 理性与效用的照引下——“法律应当统一并且公正无私”,实现对于社会福利的最大限 度的护持。(注:“四维合一”的诠释框架贯穿卡氏的全部法律思维。一个令人感动的 例子是,1925年6月10日,在奥尔巴尼法学院第74届学位授予典礼上的演讲中,卡翁于 演讲结束时向即将踏上职业生涯的法科学子们提供了下述“金言”,同样体现了这一诠 释用意。题为“法律游戏及其奖赏”的演讲的结尾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学习历史的智慧 ,因为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告诫的旷野之上,它为你照亮一条小路。你们要学习人类的生 活,因为这是你们必须应付的生活,必须用智慧去应付的生活,你必须懂得它。你们要 学习正义的训令,因为它是惟有通过你们才能获胜的真理。以上详[美]本杰明·卡多佐 :《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 页。)实际上,卡翁反对片面强调其中一端,警示必须根据具体情境,综合考虑,酌情 下判。可是,经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框架不仅一定意义上解决了问题,同时不也 留下了更多的疑问吗!
四 历史、事实与人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以下饶有意义的诸端,围绕着这些论题,卡翁铺陈出自己的思绪,也是他留给普通法世界的精神遗产。
第一,法律与历史。如上所述,历史是卡氏“四维合一”诠释框架中的重要一维,而在《司法过程的性质》中,卡氏对于法律的历史维度也确乎多所着墨。身为高位的法官,乃至后来位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与其前任霍姆斯大法官一样,卡氏在反对历史法学的诸多言说的同时重述着历史法学的命题。二人有关法的历史之维的观点是如此如出一辙,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将他们“定性”为实证主义或者实用主义的法律学说谱系之外,另需编织一幅“历史主义”法学谱系图景。这里,试将二人的代表性论点综合如下:
首先,关于法的发生论:
霍姆斯:
目前,在大量案件中,如果我们欲知为什么一个法律规则表现为此种独特的形式,或 者,我们对其存在本身多少心存疑惑,则我们必得转而追问于传统。
理性地研究法律,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历史。因为没有历史,我们即无以知晓规则 的精确范围,而对此了然于心,乃吾人职责之所在,因而,历史必得成为法律研究的一 部分。
法律之治乃是在历史的渐次演生中,而非有意识地根据可得预见的社会目的所为之全盘人为重新改造中,逐渐形成的。(注:以上均详霍姆斯:《法律之道》,第327页。)
卡多佐:
某些法律的概念之所以有它们现在的形式,这几乎完全归功于历史。除了将它们视为历史的产物外,我们便无法理解它们。(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2页。)
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看,某些法律的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在这样一些部门中,历史会趋向于对法律的发展给予指导。(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9页。)
法律确实是一种历史的衍生物,因为它是习惯性道德的表现,而习惯性道德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发展是悄无声息的,且无人意识到的。(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4页。)
其次,关于探查法的历史之维的宗旨与功用:
霍姆斯:
对于历史之深怀兴味,原旨在接引历史之光以烛照当下现实。
卡多佐:
历史在照亮昔日的同时也照亮了今天,而在照亮了今天之际又照亮了未来。(注:在此,卡多佐并引用梅特兰爵士的话说:“今天我们研究前天,为的是昨天也许不会使今天无所作为,以及今天又不会使明天无所作为。”)
再次,关于法的历史之维的意义:
霍姆斯:
我们之做大部分事情,其理由无非是吾侪之父辈或者吾侪之邻人亦且如此行事,推而广之,其理亦然,其范围甚至超出吾人之所思。
我们并未意识到,吾人法律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乃是根据公共心意的潜移默化而重予审议的。
法律的最大正当性,在于其与人类最为深沉之天性契合无间。(注:霍姆斯:《法律之道》,第326,327,331页。)
卡多佐:
所有这些法律的名目都只有在历史之光的照耀下才能理解,它们都是从历史中获得促进力且必定会影响它们此后的发展。……因此,为了真正合乎逻辑,它们的发展就一定要充分注意到它们的起源。(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2,33页。)
上述这些代表性的论述表明,两位大法官其实都深受历史法学的影响,而将当下规则放诸历史之维慎予纵深观瞰,相信“一页历史抵得上一卷逻辑”。(注:如前所述,波斯纳指证霍姆斯大法官为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但同时承认其法律思想中的深重的历史法学渊源。详见[美]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武欣、凌斌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以下。)不过,虽然都强调法律自历史演来,因而理解法律必须以对历史的理解为前提,但是,卡氏同时认为法律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时并为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生成物。因而,他指认萨维尼将法律理解为某种无须斗争、其目标或目的就能实现的东西,理解为一个沉寂的生长过程,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及其天才的生活和习惯的结果这一描述,所提供给世人的乃是一幅不完整的并且有偏颇的图画。(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4页。)暂且不论究竟萨维尼的法的历史图景如何,就卡翁的论述来看,很显然,20世纪初年美国司法力量对于社会生活的积极介入讲述了另一幅法律图景,也确乎给予大法官们甚深的自信,则毋庸讳言。
卡多佐说在任何法律场景的审视下,霍姆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地位都是颠扑不破的。(注:详[美]本杰明·卡多佐:“霍姆斯大法官先生”,原载《哈佛法律评论》(1931 )第44卷,第682—92页,详见《本杰明·N.卡多佐选集》(纽约:Fallon Law Book Company,1947),第79页。参阅拙文:“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载《环球法律评论》 (北京)2001年第1期,第123页以下。)以此反观卡翁本人,亦正彰显了其对历史作为一 种“力量”的重视。正是基于对于历史因素的深切体察,深谙整个司法过程本身,包括 当下的判决在内,同样是而且必将是一种历史过程,才使得他对于将历史法学与社会法 学两相对立之举深不以为然。“实际上”,卡翁调侃,“许多为某一学派摇旗呐喊的法 律从业者,无意中却援助、鼓舞了另一学派,……那些公然宣称在宣判案件时使用历史 方法的人,并不比那些宣称使用社会学方法的人更忠于历史学派的价值。”(注:[美] 本杰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 02年版,第58页。)
第二,事实与规则。如前所述,无论是“三类案件三项职责”,还是“四种力量四种方法”,都是“事实与规则”(Physis v Norms)的互动这一永恒法律主题的具体展开。具体而言,卡多佐对于“事实与规则”关系的论述是以生活本身为出发点,而以法官朝夕实际接触的规则为核心的。因为日常生活源于历史和传统,从来就这么着,日子就那么过。常态、常规和常例是亿万普通人维持就“这么着”与“那么过”的洒扫应对之必备,更何况它们的背后还有相配套的常识、常理和常情呢!这些在打理日子的悠悠岁月中逐渐形成的常态、常规与常例,就是规则,甚至是比制定法更为根本的规则;也就是事实,至少是重要的事实。卡氏不是基于“逻辑”而是根据“经验”指称,在无数的案件中,特殊的贸易、市场和职业的习惯,其间的常例,决定着纠纷解决的进程,也是法庭应当循依的“规则”。其间的关系,卡翁从“行为与秩序”、“生活与法律”之间的互动角度作结:
生活塑造了行为的模子,而后者在某一天又会变得如同法律那样固定起来。法律维护的就是这些从生活中获得其形式和形状的模子。(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8页。)
换言之,不管是经由立法还是司法,如前所述,“观俗立法”是法律成长的重要机制。生活本身塑育了自己的行为方式,法律规则即为对此行为方式的摹本,而赋予其规则形式,以维护这一行为方式,也就是维护这一生活方式。用笔者的理解来说,立法反映了一种活法,并给予一种说法,而最终安顿这一活法。(注:详拙文“说法活法立法”,原载《读书》1997年第11期,详见拙集《说法活法立法》(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也就因此,卡氏在其后的《法律科学的悖论》中喟言,“我们 在判断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管制将增加还是减少自由之前,必须知道人们如何工作,又 如何生活。”(注:[美]本杰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 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就此而言,普通法传统中的法官之所以能在“空白处”立法,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法律本身蕴涵有一种“自然的力量”,即法律源于事实——源于日常生活本身;事实及其关系恒定而恒变,法律因而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品格,同时并处在永恒的不断新生之中。因而,法官不是根据对于法律的文本的纯粹逻辑推演,而是根据对于逻辑、历史、传统和社会“正义”与社会“效用”进行的综合考察,来厘定规则,阐明原则,寻找出法律渊源。其中,就卡多佐的“当下”来说,法官立法的诉求对象不是或者不仅仅是“逻辑演绎”,而是“社会需求”——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迫切需求;最终而言,是根据理性和正义判知,符合正义的“人的需求”。(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5—6,59,7页。)——这才是一切规则赖以 立基的最为根本的事实。
第三,法律理性与法官立法的限度。我们知道,法官立法多半只是普通法的传统,是该传统中法官的“一种”行为方式,因而是一种有限度的司法活动。作为局内中人的卡翁虽然畅言司法的最高境界在于藉由司法而立法,但是,他在进行如此这般的演示之后也不忘提醒听众,“这一种”行为方式的展现却是极其语境化的。即法官仅仅是在规则的“空白处”这一“荒芜地带”立法,而与法律大地上“早已播种且硕果累累”的沃土相比,这样的“空白处”极少。实际上,随着普通法世界制定法功能的强化,这样的“空白处”可能益且狭小。而且,卡翁警言,这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法官还会犯错误,并非具有“无限的预见力”。(注:以上分别详[美]本杰明·卡多佐:《 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0,86,12和91页。)卡翁引述 发生于20世纪初期的法国,作为司法对于立法的反动的“马格劳德”现象,说明“法官 立法”的有限性——极其有限性。
尤有甚者,当案件涉关重大社会价值的分歧时,例如堕胎问题,法官为了明哲保身,常常不愿得罪公众,而选择优位势力作为价值坐标,尽管自己内心可能另有判断。(注: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判例莫过于“罗伊诉韦德案”。详见“俄勒冈州诉巴尼特案”(State of Oregon v.Ruth Barnett[1966]# 15955.,the Transcript in Oregon State
Archives,Salem);[美]杰克·弗罗斯特:“堕胎——需要予以合法化的堕胎”,载《刑法与犯罪学杂志》1938年第29卷,第596页以下(Jack Frost,“Abortion-Need for Legalized Abortion”,i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29 [November ,1938]:596);[美]瑞科雅·索琳歌尔:《妇女对法律的反抗——美国“罗伊”案判决 前堕胎法的理论与实践》,徐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任何法律体系 中,法官的这种“耍滑头”现象都不是不可能的。或者,情形恰恰相反,法官得风气之 先,遽然下判,而站在时代前列,摧折了秩序与秩序感赖以立基的规则的确定与确定性 。——在此,可能,他或她是“为了社会大众的好”,但却不免行“仁爱的专制”之实 。一如“政府可能在父爱关怀的伪装下,根据自己的意志隐秘和渐进地塑造其成员。” (注:[美]本杰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 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毕竟,二者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均为一种权力。可 能正是出于此种怵惕,卡翁提醒自己的听众,法官并没有获得授权可以随意按照变化着 的关于“便利”或者“明智”的看法来制作或者废除规则,相反,卡氏借助英国的詹姆 斯·帕克爵士的话说,为了法律的统一性、一贯性和确定性,普通法的路数是将从法律 原则和前例中推导出来的规则适用于新的情境,而且,只要这些规则对于所发生的案件 并非明显不合情理和不便,法官就必须运用这些规则,“在尚未慎重地适用这些规则的 时候,我们没有自由因为我们认为这些规则不像我们本来可能设计的那样便利和合乎情 理而拒绝这些规则”。(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 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1页。)在谈到人们关于法官可能会借助司法来立法而实行专制 ,哪怕是“仁爱的专制”这一担忧时,卡翁坦言,“与来自各方的限制法官的规则之数 量和压力相比,任何法官创新的权力都无足轻重。”(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 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5页。)但是卡翁可能没有预料到 或者没有说出口的是,司法权的极度扩张难道不是同样会造成权力平衡架构的倾覆,导 致对于自身的背叛吗?卡氏倘若在世,目睹司法介入民主,而最终打着公正的旗帜屈服 于党派的利益,是否深悲于“仁爱的专制”的现实呢?的确,毕竟司法同样是一种应当 受到制约的权力,而司法者们对于法律之外的人间万物的敬畏,就是一种必要的内在制 约。其中,最应在它面前保持谦卑的,乃是人类最为深切的情感。由此,它牵涉到下面 这一论题。
第四,法意与人心。一定意义上,卡多佐的整个讲座都是在讲述这一主题,而从另一人文类型传统、非普通法心智的读者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全书所展现的亦正是讲述 者所体认的美国普通法的法意与人心。具体而言,首先,大法官主张,法官应力保法律 对于人类深层而迫切的情感作出真切的回应,这是“诚实的法官”的义务,亦即司法的 职责所在。(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 1年版,第19,83,84页。)如果说没有道德支撑的法律是危乎殆哉的法,那么,失却对 于人类情感的护持之责的司法,在最好的意义上充其量不过纯粹是法律的工具,而不论 这是什么法律;在最坏的情形下,只能是暴虐的走卒。在人类的情感中,不分人文类型 、历史差异,对于公平、正义的热爱始终是奔腾不息的一脉主线,因而,司法对于人类 情感的回应主要就表现为满足人们经由司法追求正义的需求,即通过判决理据的阐释, 揭示法理背后的伦理,从而护持人们心中关于公正的平衡感觉。这样,正义不仅是司法 的目的,更是全部法的目的所在。(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0,83,25页。)这也就是法律的理想主义,而法律 的理想主义是法律发展的精神动力。尽管实用主义风樯阵马,卡翁却指认,理想主义乃 是正义之法潜藏于内、默然无声的灵魂所在。(注:[美]本杰明·卡多佐:《法律的成 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页。)
那么,司法如何保证法律作出这种呼应呢?法律能否作出这种呼应呢?在卡翁眼中,法官通过判决尽力使法律判断与道德和习俗的判断一致,是司法力保法律作出这种回应的手段,或者说,手段之一。(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4页。)换言之,可以推断,在卡翁心中,所谓的人类情感通常寄寓于道德和习俗之中,因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事实”里面,自当包含道德与习俗在内,也就是自当包含人类的情感在内。——情感是一种“事实”。这也就是“社会学的方法”之所以必要与可能的原因所在。
而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之所以应当如此,不得不如此,也只能如此,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法律与道德之类的超越价值之间具有“更深层面上的和谐”。事实上,整个普通法都建立在“法律是道德的一种表现”这一假设之上,法律本身就蕴涵了丰富的人类情感,载述着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展现出人类情感的理性的凝练形式。的确,不能说什么道德和正义不是法律,从而驱使人们对法律滋生怀疑和蔑视,相反,法官应当在法律与道德、在法律的戒律与理性和良知的戒律之间保持必要的关系。即便是所谓的“实在法”,其本身也蕴涵着“理想”即“意义”因素。实际上,大法官举例说,“伟大的衡平法官”经由不断诉诸理性与良知,不仅救济了普通法的不足,建立起衡平法体系,从而将规则与它所要调节的人心两相联结,而且,它同时并保持了法律的一致性和确定性。卡翁重申,这是普通法的传统,它体现在曼斯菲尔德和马歇尔大法官的手中,也传承到肯特和霍姆斯的法庭上。(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3,86页;[美]本杰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换言之,时移势易,前仆后继,它同样是他的法律理性的灵魂。
而一言以蔽之,保持法律与道德的密切联结,某些情形下,甚至不惜有损法律的所谓“自治”,卡翁并未明说,但在笔者体认,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下面一段话所揭示的深刻悖论之中。并非“以法律为业”的中国学者殷海光先生,一生为“自由、民主”而呐喊,撒手人世前,面对纷纭世像,却不由感慨:
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注:殷海光:“《海光文选》自叙”,载林正弘主编《殷海光全集》第17卷《书评与书序》(下册),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第652—653页。)
这正是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回到卡多佐,往深里说,法官在履行“宣告”法律的义务时必须虑及法律的道德基础,法律推理不能违反普遍共谕共守的“公理” ,亦即对于深蕴于特定社会及其人文类型的常态、常规和常例,涉案的常识、常理和常情,法官务予周罗密致,理性彰显。(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4,67,110页。)——毕竟,法律是制定来供大家 讲道理用的,因此,必须符合情与理,一碗水端平了;也就因此,推思一步,法官应当 是通情达理、明白过日子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明理之士。
话说回头,凡此种种,当然是法官基于自己的道德体认而提炼、归纳出来的。即是一 种个人性的作业,那么,如果出现社会道德与法官个人道德信念之间捍格不凿甚至根本 对立的情形的话,却又当如何?在卡多佐看来,这种情形很少见,也“很少具有什么决 定性的意义”,如果说它依然具有“玄思之旨趣”的话。但是,既然说是“很少见”, 就意味着总是会出现的,在此关节处,卡翁警言,一旦出现,法官的大忌是欲将自己的 “行为癖好或信仰癖好”作为一个生活规则强加于社会,以个人的正义感来评断一切个 案。但是,这并非是说法官在此完全无所作为。实际上,法官通过揭示规则,阐释原则 ,并不断赋予其新意,而使法律与道德保持一致——二者深层次的和谐,从而,卡翁断 论,也可说是憧憬,法官“在提升通行的道德水准上”,倒也并非“无能为力”。(注 :以上分别详[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版,第67—68,84—85页。)——或许,也是一种法律经由司法而对人类情感的呼应方 式吧!只是,切莫走过头了。
五 回荡心中的主题
通观考察卡翁对于上述诸端的考问,可以看出,大法官心中进而有四个主题始终徘徊不已。
第一,藉由事实与规则的互动图景,不仅展现法的世界的确定性,而且揭示其非确定性,从而,努力寻求规则和规则性、秩序与秩序感,最终揭示法律世界和人间秩序的确定性。而如此穿梭奔波,劳心费神,根本动因还是因为秉持常识、常理与常情,为大家过日子提供可得循依的常态、常规与常例,是司法及其从业者的职业本分与志业追求,更是其天职之所在。而所谓“最终揭示法律世界和人间秩序的确定性”,我们后人今天不妨说,某种意义上其实也就是人为地铺设或者提供、赋予人间世的确定性,纷乱的人间世由此获得清晰的画面,日常行为的进退出处才有了凭依和预测性,大家心中也才有了安全感——一种基于秩序的坦然。就此观之,司法及其从业者才是真正的立法者这一说,实在非为虚言。此不惟普通法世界,制定法传统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域,情形亦多类似。正因为像霍姆斯、卡多佐这一层次的伟大执法者们对于人间世的规则性和秩序格局的虚幻性多所体认,而职业与志业所系又不得不勉力为之,故尔,才会一腔悲悯涌心头 ,“铁面无私”的两位“大法官”的精神世界均充溢着救世情怀。(注:在自传《超越 东西方》中,吴经熊即说过这样的话:“事实上,霍姆斯是一个无意识的哲学家。要公 平地对待他,就不要智性地判定他是哲学家,而要审美地把他当作一个人格来看。在深 处,他是一个变成了法官的诗人。”详周伟驰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2 年版,第104页。)
第二,藉由现身说法揭示司法过程的理性与直觉、理性与非理性,阐释法的知性,展现法律世界,特别是法律运作过程中的种种诡谲而细微难以捉摸的特性,在坚守信誓旦旦的法律理性的同时明白其无理性乃至反理性的一面。而对法律和司法过程中此一暗点之洞若观火,却正在于“信守”法律理性之确凿不易。另一方面言,则此种信守——惟有信守,始有存在——亦正说明了法律理性一脉流连,不绝如缕,危乎殆哉!正是在这里,夜阑人静,扪心辗转,有良心的“大法官们”可能常常不由不长叹:理性,法律理性,乃至人类理性,何由来?!安在哉!?因而,为了实现司法的目的,理性才不得不受正义的督视,而正义应为慈悲所支配。基此,秉持理性与正义,在通盘考虑社会福利和实际效用的同时,谨慎下判,将人间纠纷摆平了,大家感到事情平顺而慰贴,才是司法之道,也才是司法之道所昭显的法律之道,法律之道所凸显的生存之道。这里,就如其他人间事业一样,可能,“信守”的愿力比智力更重要。所以,卡翁才会在引述了一段关于信仰的论述后说道:
法律的发展经历了许多世纪,总是处于锻制之中的就是这种新的信仰,它默默无言但会坚定地抹去我们的错误和偏执。(注:[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3页。)
第三,通过揭示司法过程调剂法的功能追求与价值关怀的努力,尤其是藉由对于法律 与人类情感关系的阐释,作者表述出对于法的合理性之孜孜以求,对于人间世的合理性 的深思与苦恼。法律与人类情感的复杂互动,法意与人心的纠缠,恰是纯粹理性意义上 的法律理性所无法解决的,更是片面的效用主义法律观难以应对也应对不好的。我们拜 读卡氏的遗作,深感作者恰恰在此是悲悯多于苦恼,苦恼甚于自信,而自信不敌惶惑。 卡翁之所以说“贪婪的官职有可能吞没人性……我没有让官职吞没人性……感谢我有着 做人的能力”,(注:这是卡多佐1927年12月20日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校友午餐会演讲中 的话,演讲题为“法律共同体的友谊”。详[美]本杰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 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可能正是有鉴于此 ,而自勉并勉人吧!
第四,藉由司法来运作法律以调节利益——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旨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通过追求法的世界的和谐,进求人世生活的和谐与安宁,包括正义昭彰赋予人们心灵的和谐与安宁。在此,法律成为编织人世意义之网的手段,而对一个法律在其中担负了极为重要的组织生活的职责的社会来说,法律由此成为信仰的对象,特别是其中的宪法,更是成为公民的政治忠诚和大众的世俗信仰的直接对象。
可是,面对现实的人间世,法律实际上已经做了什么?又能够做些什么呢?!对此,恐怕越是老辣的法曹,越是三缄其口吧!辗转于这重重帷幕之中,恐怕这也恰恰是卡翁的心思所在。
相比而言,卡多佐一生著述不多,主要作品基本备见于死后印行的《本杰明·N.卡多佐选集》。其后的著述,如本文征引的诸篇,大致是对《司法过程的性质》的基本主题的发挥和深化。而《司法过程的性质》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作为大学讲演稿,几经润 饰而后刊行。虽然作者事后谦称出语“轻率”,实则“煞费苦心”,(注:[美]本杰明 ·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第36页。)堪谓殚精竭虑之作,无怪乎风雨无阻,一纸风行。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 这部小书经受住了时间的淘洗,蔚为经典,影响超出英语法律文明。早春时月,清华园 的夜晚,笔者与学生一起研读,曾谓“袖珍型”的经典,因为可得挖掘的意义含量丰硕 ,读起来可能较一般的大部头更难。而因为意义含量丰硕,著者却惜墨如金,微言大义 ,点到即止,因而,读起来甚至难得多。从而,这类经典著作遂为一个所谓的“开放文 本”,每一代人均可将自身的生活经验熔铸其间,在阐发文本涵义的同时,接引意义之 源,而丰富现世人生,为当下生活采撷、编织意义之网。大凡文明的传承,此为一招。 法律文明的传承,此亦一招。而就不同人文类型的交流可能性而言,汉语文明的法律从 业者隔洋隔代奉读,既为纵向传承,更为横向的“借鉴”了。而目的,不外乎还是接引 法意,丰富汉语文明的意义含量,服务于当下吾族吾民的人世生活。
人世生活离不开法律,因而每一人文类型都有自己的“以法律为业”者。其言在于表述人世生活的规则,其行则为同胞标立取舍标准。如此持之以恒,历经数代践履,其集大成者,涵养于民族生活,而屡叙民族生活的规则,如用西人话语,则适成该人文类型“活着的法律宣谕者”(living oracle of law),该民族法律生活的精神导师。卡多佐 借布莱克斯通此语以状喻伟大的前辈同行,其实,后人以此回馈卡氏,表彰其对美国人 民法律生活的贡献,亦最恰切不过。——就如传记作者所言,他为法律而生,法律也使 他成名。(注:[美]A.L.考夫曼:《卡多佐》,张守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或者说,法律令他不朽。而今日作者在此表彰卡翁,亦正在呼唤足以表彰汉语 文明法律智慧的“活着的法律宣谕者”,伟大的法律公民法学公民,如沛然春水拍岸, 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而涓滴汇流,势成汹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