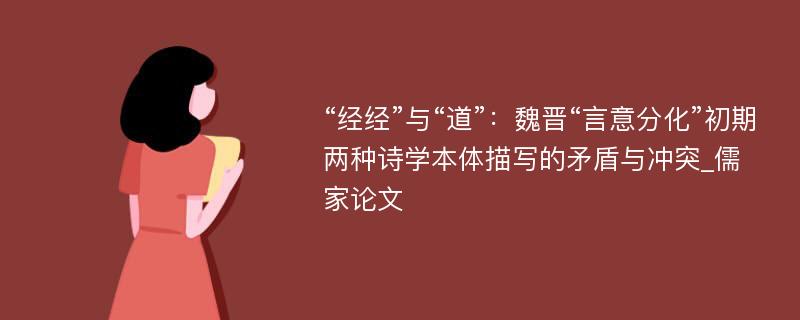
“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悖立与冲突——魏晋“言意之辨”前期学术语境的描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诗学论文,两种论文,语境论文,魏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言意之辨”的前期学术语境即是“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悖立与冲突。本文把“言”与“意”的冲突归属到两种本体论范畴“经”与“道”的悖立上,认为“言”就是“立言”,即崇尚在儒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经”的范畴上“立言”,“意”就是“立意”,即崇尚在道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道”的范畴上“立意”。在修辞学意义上,“经”与“道”均是超感性的抽象能指,是生命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设定的两个外延最大而内涵最小且具有恒定意义的本体范畴。“经”是一个遮蔽的本体范畴,而“道”是一个敞开的本体范畴。西方古典诗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理论和思维形式上对应于儒家诗学的经学中心主义,而不是道家诗学的体“道”本体论。道家诗学的本体在敞开中没构筑起一个中心主义,因此道家诗学理论的直觉体验没有形成一种封闭而剥夺他者思想自由的权力话语。而儒家诗学的本体论建构者以语言游戏在本体——“经”的范畴上遮蔽了这个世界,在剥夺芸芸众生的意志自由中把思想统治者个人的“唯我自由”写真在本体论的语境表象上。
“言意之辨”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场重要的理论持久论战。诗学界、哲学界、美学界、古典文论界的学者们,只要把自己的思考投放在魏晋,几乎没有人愿意放过对“言意之辨”的插足;他们大都以对“言意之辨”的“再思辨”来呈现自身的思辨素质与理论素养,尤其20世纪西方哲学在转向语言的思考后,其对当下大陆诗学界有着不可低估的深度性侵蚀,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回过头来反思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往往会有更为深刻的启示。
在这里,笔者主要通过反思,简略地描述一下“言意之辨”在魏晋崛起的前期学术语境,以及在华夏大学术语境下这场理论交锋的逻辑承递。
一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这场关于“言意之辨”的公开论战,最初肇事于曹魏玄学家荀粲与其兄荀彧之间关于在经典文本上能否“立言”的争执;而后,在魏晋那位短命天才、玄学大师王弼“得意忘言”命题的推波助澜下,又于曹魏的拒儒偏执狂嵇康的《言不尽意论》和西晋名士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之间的论战中走向白热化;最后,又引入了东晋殷融的《象不尽意论》。我们认为,这些思者对“言意之辨”的卷入,在骨子里都是出于对话语权力争夺的极端功利性。因为,他们是把《周易·系辞上》假托孔子所言的三个范畴:“言”、“意”、“象”、统摄于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对话语权力的争执下,从而肆意挑起这场公开的理论论战的。关于“言”、“意”、“象”这三个范畴的设立,原典见于《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由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①]其实,在这场理论论战的表象下及在参与这场理论较量的思者人格中,掩盖着参与者控制话语权力的野心和征服他者的欲望。
笔者以为,倘若我们把对“言意之辨”的关注与思考,仅仅局限于魏晋,局限于这几位肇事者——荀粲、荀彧、嵇康、欧阳建、殷融,或局限于“言意之辨”这个命题的本身,这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种理论思考上的短视。而恰恰理论界以往关于“言意之辨”的讨论也正是囿于这个命题本身和魏晋这个文化景观之下而展开的。如果对“言意之辨”的思考,不跨过这一命题本身,不超越魏晋进入这一命题争论的前期学术语境,即原始儒家诗学与原始道家诗学在建构本体论上的悖立与冲突,就无法有效地理解这一命题与这争执的基本意义。
我们想在这里设问:魏晋“言意之辨”的前期学术语境缘起何时,又究竟是谁对着谁来的?这一命题的内部冲突对后世的一些思想大师又为什么有着如此难以割舍的诱惑力?让我们回原典去。
魏晋“言意之辨”的经典性言论见于《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荀粲传》曰:“……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荀)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荀彧)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②]学术界诸多学者在讨论“言意之辨”时,往往癖好般地引用这一条史证来启开自己的思路。在这里,如果我们用抽取主题句的方法来读解原典的潜在理论,至少我们可获得这样几个命题:“以儒术论议”、“独好言道”、“夫子之言不可得而闻”、“‘六籍’(‘六经’)虽存,固圣人之糠秕”。那么,我们把这几个命题组合成一个背景理论来进行描述,即是:荀粲和其兄荀彧在议论儒术时,荀粲安身立命于老庄的宇宙本体论——“道”,以为孔子之言不可得闻,进而在思考的逻辑上推导出儒家的“六经”文本虽然还在,其只不过是圣人的糠秕而已。实际上,在荀粲言说的表象下潜在着这样一个阐释学的理论组合,即儒家的经典文本——“六经”无法有效地负载、承传和表达圣人赋予它的原初意义,从而拒斥了儒家主体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说到底,荀粲就是崇尚“言不尽意”论,也就是拒斥“立言”而崇尚“立意”。然后,其兄荀彧援引《周易》的原典对荀粲拒斥“立言”的理论表达进行了反驳,即以“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来阐明圣人以“卦象”和“爻辞”来“尽言”的方法论。这实际上也就是背靠儒家诗学安身立命的终极本体——“经”,崇尚“言尽意”论,而拒斥“言不尽意”论。也就是这样,从而引发出了后者(即王弼、嵇康、欧阳建、殷融)对“立言”与“立意”的崇尚与拒斥的讨论。
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言意之辨”的冲突绝对不是某一两位思者出于思辨的癖好和才气的炫耀而无事生非,这一冲突实际上是昭示着儒家与道家这两脉浸润中国文化的本土学派及其学人,围绕着书写的文本能否“立言”,来争夺控制文化主潮和诗学批评主潮的话语权力。在一个学术命题的表象下遮蔽的往往不纯粹是本命题自身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不难看到,“言意之辨”实质上“辨”的就是中国古典阐释学的问题,并且一直“辨”到了生命主体安身立命的本体论上来了。笔者在思考“言意之辨”的理论冲突时,总是无法拒绝感受到冲突者之间以一种极端的占有欲来满足话语权力争夺的野心及争夺之间的张力。一言以蔽之,“言意之辨”就是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两者之间的冲突,也更是儒家学派与道家学派两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宿怨我们一直可以从玄风狂起的魏晋跨越两汉经学,一直追寻到诸子蜂起的先秦,即原始儒家诗学与原始道家诗学为安身立命而以思想、精神和信仰把对方置于死地的两种本体论之间的冲突。可以说,这是两种生存方式和两种生存信条之间的冲突,也是两种终极关怀方式之间的冲突。
为了使我们的描述简略化,在这里我们作一次对应范畴的组合。上述我们把“言”与“意”的冲突归属到两种本体论终极范畴的悖立上。倘若说,“言”就是“立言”,“意”就是“立意”;那么,“立言”就是在儒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经”上的“立言”,“立意”也就是在道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道”上的“立意”。因此,“言意之辨”的冲突,也就是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在本体论之间的冲突,也更是两个本体范畴“经”与“道”之间的冲突。“道”即是道家学派及其后学安身立命的终极本体范畴,在学术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老子以为“道”是在“无”中创生了整个宇宙大全,即“道”就是“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③],“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④]在道家诗学那里,庄子及其学派认为“道”作为一个本体范畴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庄子·知北游》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⑤],并且《庄子·则阳》告诫芸芸众生,面对不可言说的宇宙本体——“道”,主体便失落于“言默”的状态:“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⑥]道家诗学理论认为,主体对“道”的把握只有带着直觉的悟性体验,在“立意”中完成,这就是《庄子·秋水》所称言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⑦]多少年来,学术界往往对道家诗学及其本体范畴的思考是非常痴迷的、用心的,这种痴迷与用心最终导致了道家诗学从神秘化走向了通俗化与大众化,搞得学术界妇孺皆知。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看儒家诗学。从李贽到蔡尚思、到“文化大革命”、再到刘小波,一路被骂臭了的儒家学派、儒家诗学、儒家诗教和儒家诗论都被置于批判的一知半解中;谁又真正地立足于本体论上触摸到了一统儒家学派与一统儒家诗学的那位黑衣主教——孔子的亡灵?谁又在本体论上真正地读懂了儒家诗教与儒家诗论?我们想在此设问一下,支撑儒家诗学体系得以建构的阿基米德点在哪?为什么儒家诗学在一个学术宗教般的祭拜历程中能够折服两千年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如此众多的文学大师?司马迁、王充、班固、刘勰、陈子昂、杜甫、韩愈、柳宗元、王安石……。为什么?西方中世纪的美学思想是在上帝的本体格位上踏平了尘间的美,动摇了古希腊艺术摹仿自然的古老神律,使西方中世纪的诗学笼罩上一层浓厚的宗教色彩,那么儒家诗学的学术宗教色彩又是踞守在一个怎样的本体上涂抹于尘世的文学创作?简言之,儒家诗学“立论”、“立教”、“立言”的本体又在哪里?这,才是遮掩在“言意之辨”冲突表象下的深层问题。让我们的思考再回到魏晋“言意之辨”的经典性表达,即《三国·魏志·荀彧传注》引《荀粲传》曰:“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对这一句表述的意义读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遵循西方古典阐释学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追寻经典文本的原初踪迹,我们可以把荀粲的这句表达,在意义的逻辑上追寻到《庄子·天道》:“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⑧]魏晋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型期,中国古典诗学、中国古典文学就是在这一时期走向理论与形态的自觉。那么,用规范的学术话语来表达,这一时期在学术理论思潮上的张显,就是经学的衰落与玄学的崛起。在玄学大师们——何晏、王弼用老庄文本的话语对儒家的经典文本进行自觉地破坏性误读下,一统两汉的儒家思想及两汉经学从文化中心的踞守向文化的边缘退却,而两汉期间被经学逼压于文化边缘踞守孤独的道家思想向文化中心回归,道家诗学成为批评这个时代文学的主流话语和权力话语。因此,荀粲的反“立言”理论表达,就是在这样一方学术景观下言说着《庄子·天道》的话语。其实,荀粲仅仅是在回归文化中心的道家话语推动下的一介被动的言说者而已。实质上,在荀粲的反“立言”理论表达中,回响着先秦时期老庄及原始道家诗学背靠着宇宙本体——“道”,对原始儒家诗学崇尚在道德本体——“经”及经典文本上“立言”的挑战。
上述我们曾设问,儒家诗家踞守一个怎样的本体安身立命?其实我们已经提及,那就是“经”。“言意之辨”的理论深度就是道家诗学以崇尚在“道”的终极本体上“立意”,以拒斥儒家诗学崇尚在“经”的终极本体上“立言”。至于在“言意之辨”的冲突下再度讨论的“意”与“意境”的问题、“言”与“意”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义漂移问题、“象”是由“言”达向“意”的中介问题,“言意”之下的形式与内容等问题,都是这一冲突下的副产品。
二
我们都知道,老庄的生存信条是逍遥于无为的高蹈之中的,它恰恰是栖居众妙之门,吁求一种非语言悟解的宁静与高旷而摄人心魄。那么,老庄为什么又这样极端功利性地以崇尚“立意”来拒斥在“经”的本体上“立言”呢?在老子与庄子的文本中,反“立言”的言论是非常多的。《老子·第二章》:“圣人行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⑨],《老子·第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⑩],《老子·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11)],《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12)],《庄子·知北游》:“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13)]值得提及的是,老庄拒斥“立言”是反对同期原始儒家学派在本体范畴——“经”与经典文本上的“立言”,因为《庄子·天道》两次提及“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那么,为什么儒家诗学崇尚在“经”的本体上“立言”呢?其关键就在于“经”这个范畴的本体地位。
在这里,让我们从“语言作为阐释学本体论的视域”,对“经”作一次终极意义上的界定和描述。“经”作为一个“能指”的使用,最早见于周代的铜器铭文,其原初意义为“织物的经纬线”。南朝文字学家顾野王在《玉篇》中是这样释义的:“经纬以机织缯布也”[(14)],清代语言学大师段玉裁于《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释义为:“经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天地之常经。”[(15)]注意,在“经”使用的原初语境下,“经”是作为一个实物名词来使用的,它的原初意义是指“经线”和“经纬线”。“经”在后来的语境使用中,又有一个从实物名词向动词和抽象名词转型的过程,“经”也正是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裸露出儒家主体在理论思维上控制话语权力的霸权主义精神。“经”的原初意义作为动词使用,这样,“经”作为一个能指,在涵义上就被使用主体赋予对时空的“涵盖”、“统摄”、“包容”、“囊括”、“占有”这些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及“统治”、“占有”的野心。这些表达在先秦典籍中也是最为常见的,《周易》中的“君子以经伦”[(16)],《左传》中的“经国家、定社稷”[(17)]、“经纬天地曰文”[(18)]、“以经纬其民”[(19)],《吕氏春秋·求人》的“终身无经天下之色”[(20)],在这些话语的表达中所运用的“经”,就是在上述语境意义层面上完成的。但是,理论思维形式的发展使主体并不满足于把“经”仅仅作为一个动词来使用,并不满足用“经”来表述主体在运思的瞬间显露出的终极关怀。因为,动词在语境中的品质决定动词本身只能生动地表现运思的瞬间,而不能把这个“运思”本身含有的意义转型为一种理论形态,再作为一种终极关怀恒定下来。而主体希冀把在运思瞬间所显露出的极终关怀恒定下来,以满足他们对话语权力的永久性控制。在这样的理论思维导向下,“经”也必然在话语的表达中从动词向抽象名词转型。因为,动词所表示的生命主体对时空的“涵盖”、“统治”、“包容”、“囊括”、“占有”和“治理”这些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也只有借助于抽象名词才能凝固下来走向恒定。《周礼》的“以经邦国”[(21)],《左传》的“天也之经”[(22)]、“天地之经纬也”[(23)],也就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完成的。伽达默尔在讨论语言作为阐释学本体论的视域时,曾言称:“如果,依据人拥有整个世界这一事实来说,语言不仅仅是人在这个世界中所拥有的唯一。这个世界作为人所存在的世界而不是作为其它动物存在的世界,即因为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语言的。”[(24)]的确,人所生存的世界及人的思维形式首先呈现和记载于人所使用的语言中,是语言使这个世界本质化了。儒家诗学主体也正是这样在他们的语言操作中构筑起自身生存的世界,并使他们生存的世界在他们言说的话语中意义化和本质化了。语言的征服是最彻底的,也是最可怕的。在智者哲人的思想体系建构那里,语言首先占据宇宙本体,然后再从本体的高度切入芸芸众生之主体灵魂对其进行精神的屠戮。
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出“经”作为动词向名词的转型,这标志着“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的形成。“天也之经”的“经”和“天地之经纬也”的经,在语言表达式中就是作为一个本体范畴概念被生命主体所使用的。可以说,生命主体在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只要以思想与精神抓住一个“经”字,就可以“拎”起一方博大的天地。在本体论的理论形态上,这方博大的天地就是生命主体在“经”的本体格位上建构起来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家园,而这个思想空间和语言家园正是以“经”作为逻辑序列的倒溯终极,从而“涵盖”、“统摄”、“包容”、“囊括”和“占有”了整个“彼在宇宙”和“此在世界”所构成的“大全”。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经”曾作过一次精湛的本体论阐释,其给人的启示是最为深刻的:“(经)覆而无外,高而在上,运行不息,日月星辰,温凉寒暑皆是天之道也;训经为常,故言道之常也。(经)载而无弃物,无不殖山川,原阳刚(阴)柔、高下,皆是地之利也。”[(25)]孔颖达在这里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怎样恐怖而博大的本体论意识啊!“(经)覆而无外,高而在上,运行不息,日月星辰,温凉寒暑皆是天之道也”,那是言指“彼在”;“(经)载而无弃物,无不殖山川,原阳刚(阴)柔、高下,皆是地之利也”,这是言指“此在”;也正是“彼在”和“此在”这两者构成了亚斯贝尔斯在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所言指的那个宇宙“大全”,而“涵盖”、“统摄”、“包容”、“囊括”和“占有”这个宇宙“大全”的终极本体就是“经”。
罗素在思考为什么智者哲人于思想的运作中无法逃避对本体论的建构时,他曾把这一疑惑归结为生命主体对“永恒”的追示,认为追示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入研究哲学(本体论)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在修辞学意义上,“经”作为一个超感性的抽象能指,是生命主体在本体论上设定的一个外延最大而内涵最小的具有恒定意义的本体范畴。倘若我们把东西方哲人的运思在本体意义上做一次对比,“经”相当于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圣·奥古斯丁的“上帝”、康德的“物自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因此,当儒家诗学立足于“经”的本体格位上建立起自我栖居和生存的语言家园,并把自己庞大的诗学理论体系建构于这个语言家园中时,他们必然把“经”认同为是一个恒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本体的铸造者总是企图在思想与精神的逻辑序列倒溯终极上以语言来封闭与剥夺此在芸芸众生的思想自由,而最终又把剥夺的这一切为自身所独占。这是本体论建构者在语言游戏中裸露出的最狂妄的野心。伽达默尔在思考语言与阐释的关系时曾有过这样一句启人至深的理论表达:“真谛在于因为人总是能够超越他发现他自身的特定语境之上,因此他的言说能够把这个世界带入语言之中,从一开始,他就在多变的语言能力操作中获取了自由。”[(26)]的确,儒家诗学的本体论建构者,就是这样以语言游戏在本体——“经”上遮蔽了这个世界,在剥夺芸芸众生的意志自由中,把思想统治者个人的“唯我自由”写真在本体论的语境表象上。
三
让我们回过头来反思一下中国古代文化史,看看历代的哲学家、文学家、诗学理论家、史学家、文字学家和经学家是怎样屈服于“经”的奴役下,以阐释对“经”这一个本体范畴进行意义的承诺的。班固的“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27)],刘熙的“经,径也,常典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28)],刘勰的“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29)],其阐释都是在本体的格位上屈服于“经”的终极真理意义。《孝经序疏》引南朝梁代经学家皇侃言,“经”是在本体上恒定天下的大法:“经者,常也,法也”[(30)]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一》引郑玄《孝经序》认为“经”是不变的终极真理:“经者,不易之称”[(31)],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把“经”承揽为一个恒常的本体:“经者,道之常义者利之宜”[(32)],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把“经”默认为统摄宇宙大全的“常道”:“经,常也,……天地之有常道,人民实法则之,……天地之经明天地皆有常也”,“训经为常,故言道之常也”[(33)],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三十七》中认同了“经”是一个万世恒定的终极;“经是万世常行之道。……经者,道之常也”[(34)],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更是把“经”承纳为主体命定于天之本体的常道:“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35)]所谓“五常之道”、“常道”、“常典”、“恒久之至道”、“不易之称”和“道之常义者”都是言指“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的恒定性。“如路径无所不通”、“不刊之鸿教”即言指称“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和垂教万世的大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清代经学大师皮锡瑞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慨叹把“经”崇奉为“圣经”,认定“经”就是“实圣经通行万世之公理。”[(36)]
在《道与逻格斯》一书中,张隆溪在本体论意义上曾把西方古典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进行比较,以道家诗学安身立命之“道”对应于西方古典诗学的“逻格斯”:“换言之,逻格斯融含着‘思’与‘言说’两个层面的意义。此外,伽达默尔也揭示我们,虽然逻格斯常常被翻译为‘理性’或者‘思’,但它的原初意义和主要意义是‘语言’,而人类作为理性动物则是拥有语言的动物。正是在这样一个精彩的表述中,‘思’与‘言说’融合为一体了。在这样一方特定的意义下,可以说,中国文字的‘道’,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国哲学概念,在这个文字中同样蕴涵了‘思’与‘言说’的二重性。”[(37)]在这里,张隆溪把道家诗学的“道”认同为西方古典诗学的“逻格斯”。非常遗憾,张隆溪作为一位栖息于外域文化的国际汉学家,他在东西方诗学的比较中对“道”与“逻格斯”的估价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仅从本体的倒溯终极上去判断“道”的格位,“道”的确是一个本体范畴;但是,在本体范畴“道”和本体概念“逻格斯”接受和承纳世界的理论价值取向上,“道”是敞开的,它可以给予芸芸众生最宽泛的“思”之自由,但“道”又是不可以为“言”所表达的,因此体道者必须拒斥“立言”而走向直觉体验的沉默:“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可以说,“道”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其不是“思”与“言说”的整合体,而是“思”与“立意”的整合体。因为“道”是主体在沉默中以“玄览”、“坐忘”和“心斋”的直觉而触摸宇宙的本体,道家诗学的“思”也正是在“立意”的沉默中走向了博大精深。在西方古典诗学那里,“逻格斯”是“思”与“言说”的整合体,但“逻格斯”是遮蔽的。以“逻格斯”为逻辑的倒序终极,主体可以建构一个思想的金字塔而封闭这个世界。
笔者以为,如果以西方古典诗学的“逻格斯”为本体的参照系,在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历程上追寻生命主体崇奉的最高存在,那就是儒家诗学的本体范畴——“经”。“经”才是“思”与“立言”的整合体,在“经”的本体终极上“立言”,是儒家诗学展开“思”的理论前奏。“经”是张扬语言的,而“道”是拒斥语言的。老庄在沉默中以“立意”的直觉触摸着沉默的彼在宇宙,从而命定于宇宙的本体——“道”;儒家诗学似乎认为宇宙太遥远、太沉默,更着重在中国古代学术宗教的本体——“经”的终极上建构一个用“思”与“立言”凝固成的文本形式,这个文体形式即是以“立言”所构成的思想金字塔。这个思想的金字塔出就是儒家诗学、儒家诗教与儒家诗论栖居的语言家园——儒家经典文本。儒家诗学主体也就是崇尚在这个语言家园中来“立德”、“立功”和“立言”,以此追寻精神、思想的不朽及对文学进行批评的话语权力。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诗学主体在对本体的追寻中,其张扬一种“三不朽”精神:即“立德”、“立功”和“立言”,这一精神必须落实在“立言”上,这样才能转化为以语言文字凝固成的文本形式。因此,可以说,在“经”的本体上“立言”以语言的喧哗而遮蔽这个世界,展览了儒家诗学内心的极端功利性。
儒家诗学为什么崇尚在“经”的本体终极上“立言”,就是要超越肉体的死亡在追寻精神的不朽中控制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力。因此,儒家学派、儒家诗学、儒家诗教和儒家诗论总是把自身“立言”的文本形式尊称为“经”,如“六经”、“十三经”。笔者在《经学与儒家诗学》一文中曾指出:“经”作为一个能指,其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经纬线”;第二,作为书写的文本形式的“经”,即“‘六经’文本”;第三,具有统摄性的,作为本体范畴的“经”[(38)]。我们想;倘若把一部“立言”的文本称之为“经”,这实质上是赋予这部文本一个非常神圣而崇高的地位。孔子删定的“六经”就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程上的六部圣典,就是圣经。我们把西方的“Bible ”翻译为“圣经”,就是借取此意。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份量是极为沉重的。经学就是一统两千年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学术宗教,孔子就是黑衣主教。在这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先秦诸子学到两汉谶纬,到魏晋玄学、到隋唐代的诗学思潮与古文运动、到宋明理学与心学、再到清代的乾嘉学派,这些学派与思潮的崛起都是遮蔽在经学的阴影下选择自身的价值取向的。如果我们把东西方诗学作一次双向的参照,经学从崛起到终结,就是从孔子删“六经”(即:原始经学的崛起)到最后一位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和最后一位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的寿终正寝。这就如同从巴门尼德的“Being”到黑格尔的绝对理论——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崛起与终结历程。如果说,从叔本华、尼采、伯格森到伽达默尔、德里达和哈贝马斯,西方的现代主义诗学与后现代主义诗学都是从不同的方法论对着西方古典形而上学来的,那么,从诸子学、谶纬、玄学、古文运动、理学、心学到乾嘉学派,都是在经学的阴影下成立自己而拒斥它者的,无论他们是拒斥经学还是崇尚经学。西方古典诗学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在理论和思维形式上对应于儒家诗学的经学中心主义,而不是道家诗学的体“道”本体论;因为道家诗学崇尚的本体——“道”是敞开的,其在直觉的理论体验中最终没有构筑起一个封闭而剥夺他者思想自由的关于权力话语的中心主义。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张隆溪的“道与逻格斯”的命题设立值得质疑与值得商榷。但需要进一步追究的是,这一命题的设立究竟是张隆溪本人的思考,还是他者的启示?毫无疑问,是他者的启示。张隆溪在《道与逻格斯》一书中把这一思考的启示归结于钱钟书的《管锥篇》:“在对《老子》敞开的文本具有极为洞察力的详细阐释中,钱钟书曾经指出道与逻格斯值得相提并论的。”[(39)]那么,我们的思考不得不再追溯到钱钟书的《管锥篇》。钱钟书在《管锥篇》第二册《老子王弼注一九则·二·一章·“道”与“名”》下有这样的论述:“‘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三两‘道’字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为道白之‘道’,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语言。古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可以相参……”[(40)]实际上,此句是钱钟书对S·艾尔曼《语义学》一书中的理论表述的翻译,钱钟书在这里把“Logos”翻译为“道”。不错,仅在本体的格位上“道”等同于“Logos”,两者都是本体范畴。但是,正如我们上述所论述的,这两个本体范畴的内质不尽相同,一个是敞开的,一个是遮蔽的。其实,钱钟书关于“道”与“逻格斯”的相提并论也只有这样的一句表述,并没有其他深入下去的讨论。
无论如何,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国古典美学、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空间中,不管是哪一脉学派、哪一脉思潮与哪一位学人怎样地拒斥和崇尚经学,它(他)们都无法逃避在经学中心主义的阴影下生存。仅从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这两个时期来看,可以说,经学的鼎盛就意味着文学的贫困,而玄学的崛起则意味着文学的自觉。
最后,让我们的思考切入我们讨论的主题上来。
在汉魏转型期,经学的衰落与玄学的崛起呈现在中国古典阐释学理论的意义上也就是经学的玄学化,其张显在诗学理论的一个层面上,即表现为儒家诗学的“立言”与道家诗学的“立意”之间的悖立与冲突。因此也可以说,在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历程中,“言”与“意”的方法论悖立与冲突也就是“经”与“道”的本体论的悖立与冲突。倘若我们把这一现象浓缩为一个诗学命题来涵盖,那就是“言意之辨”。
注释:
①(16)《周易正义》见于《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影印世界书局阮元校刻本,第82、19页。
②《三国志》见于《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乾隆四年武英殿本,第1105页。
③④⑨⑩(11)《老子》见于《二十二子》,上海古籍书店1985年缩印浙江书局光绪初年汇刻本,第5、5、1、6、9页。
⑤⑥⑦⑧(13)《庄子》见于《二十二子》,同上,第61、73、50、45、61页。
(12)《庄子集解》见于《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0年影印世界书局编印版,第三卷,第181页。
(14)顾野王撰《玉篇零本》,明治十六年十二月日本影刻高山寺本,第4页。
(15)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44页。
(17)(18)(19)(22)(23)(25)《春秋左传正义》见于《十三经注疏》,同上,第1736、2119、2124、2107、2108、2107页。
(20)吕不韦撰《吕氏春秋》见于《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0年影印世界书局版,第六卷,第293页。
(21)《周礼注疏》见于《十三经注疏》,同上,第645页。
(24)(26)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Hans-George Gadamer.Truth and Metbod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Press.New York.1989,P443/P.444)。
(27)班固著《白虎通》,见于《广汉魏丛书》,何元中辑,第17册,第8页。
(28)刘熙撰、毕效钦校刻《释名》,日本明历二年丙申九月,室町通鲤山町,小鸠弥尢卫开板,第6页。
(29)刘勰撰、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拾遗《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1959所版,第13页。
(30)《孝经注疏》见于《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593页。
(31)王应麟撰《玉海》,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书库,高氏藏书八四四种,第27页。
(32)杜预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见于《十三经注疏》,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同上,第2107页。
(33)《春秋左传正义》见于《十三经注疏》,同上,第2107页。
(34)朱熹撰、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89页。
(35)王守仁撰《尊经阁记》见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36)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2页。
(37)(39)张隆溪:《道与逻格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Zhang longxi.The Tao and The logos:Literary Hermeneutics,East and West.Duke University Press,Durha& London.1992,P.26/p.27)。
(38)关于“经”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三个层面界分,详细论述请参见拙作《经学与儒家诗学》见于《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第142页。
(40)钱钟书著《管锥篇》,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册,第408页。
标签:儒家论文; 本体论论文; 国学论文; 魏晋论文; 语言表达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语言描述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荀粲论文; 道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