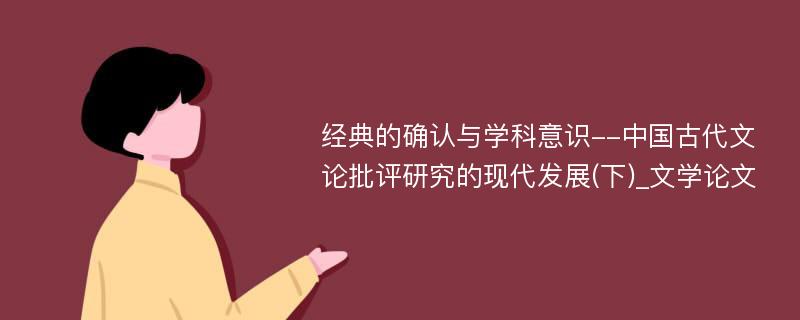
经典的确认与学科的自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现代展开(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之二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学科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文心雕龙札记》:“依傍旧文,聊资启发”
黄侃在其《文心雕龙札记·题词及略例》中写道:“文气、文格、文德诸端,盖皆老生之常谈,……世人忽远而崇近,遗实而取名,则夫阳刚阴柔之说,起承转合之谈,吾侪所以为难循,而或者方矜为胜义。”他所取的姿态,分明是对桐城文章理论的批判姿态。此其一。其二,又曰:“今为讲说计,自宜依用刘氏成书,加之诠释;引申触类,既任学者之自为,曲畅旁通,亦缘版业而散见。……自愧迂谨,不敢肆为论文之言,用是依傍旧文,聊资启发,虽无卓尔之美,庶几以弗畔为贤。”尽管在强调“弗畔”之旨,但其引申而旁通的意向,仍是十分鲜明的,借旧文以资启发,恰恰是其讨论文学问题的独特方式。凡此,都说明,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有着与姚永朴《文学研究法》一样的性质:借清理传统理论,阐发自己的文学思想。
首先,黄侃在讲说《文心雕龙》一书时,对原书章节是有选择地进行讲疏。这就与完整全面的专书研究不尽相同。
黄侃后人黄念田一九五九年为《札记》所作《后记》云:
或疑《文心雕龙》全书为五十篇,而《札记》篇第止三十有一,意先君当日所撰,或有逸篇未经刊布者。惟文化学社所刊之二十篇,为先君手自编校,《时序》至《程器》五篇如原有《札记》成稿,当不应删去。且骆君绍宾所补《物色》篇,《札记》即附刊二十篇之后,此可证知先君原未撰此五篇。至《祝盟》讫《奏启》十四篇是否撰有《札记》,尚疑莫能明。顷询之刘君博平,刘君固肄业北大时亲聆先君之讲授者,亦谓先君授《文心》时,原未逐篇撰写《札记》,……
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黄侃当年为什么要有所取舍呢?
关于这个问题,似乎没有怎么引起人们的注意。
殊不知,在此取舍之间,恰恰体现着黄侃的学术理路。按今见黄侃《札记》三十一篇篇目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议对》,《书记》,《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术》,《序志》。与刘勰原作相比照就可以发现,黄侃所舍去而不讲的《祝盟》以下十四篇,与这里所选讲的诗、骚、赋、颂、乐府、书记、议对相比,明显不属于文学的范围。于是,问题的实质已很清楚,黄侃讲的是“文学”的《文心》,而不再是“文章”的《文心》了。这当然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张少康等所著《文心雕龙研究史》(注:张少康、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本书引用此著之际,不再一一罗列注释,该著有鲜明标题,请对应参看即可。),尝引述台湾李曰刚之评曰:
民国鼎革以前,清华学士大夫多以读经之法读《文心》,大则不外校勘、评解二途,于彦和之文论思想甚少阐发。黄氏《札记》适完稿于人文荟萃之北大,复于中西文化剧烈交绥之时,因此《札记》初出,即震惊文坛,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故季刚不仅是彦和之功臣,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
其实,黄侃着重阐发刘勰文学思想的意图,首先就体现在略于文体分辨的选择取舍上。尽管我们都知道黄侃在学术思想上多有继承乃师章太炎之处,而且我们也知道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实际上是一种泛化的定义,具有视一切文字著述为文学的意向。然而,不仅在黄侃这里,就是在姚永朴那里,不也照样有着文学家“异于性理家”“异于考据家”“异于政治家”的朦胧意识吗?不也在相关的论述中透露出以说理、抒情、叙事三大类别划定文学范围的观念吗?这就是说,毕竟时代已到了二十世纪,再保守的学者,也不能不应对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在黄侃,不仅通过略文体分辨而详理论思考来展现自己的学术态度,而且就像他在讲疏《章句》时引入《马氏文通》一样,当其阐发《文心》之文学思想时,每每“依傍旧文,聊资启发”而展开新的理论思考。
这里所谓“新的理论思考”,首先是具体针对桐城后学之旧说而展开新论。这一层面上的内容,张少康等所著《文心雕龙研究史》,以及周勋初为黄侃《札记》所作导读文章,都有深入的论述。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第二章为《根本》,其中写道:
是故为文章者,苟欲根本盛大,枝叶扶疏,首在于明道。
其次在于经世。……昆山顾亭林(炎武)《日知录》云:“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
要之,其所阐发者是从曹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来所形成的具有典型性的“明道”“经世”文章观出发的。如果再考虑到他是以《中庸》为“明道”观念之本,那么,其所谓“道”者乃属于儒家文化思想体系将不会有什么疑问。针对桐城后学的这种观念,黄侃《札记》在首先阐发刘勰原著《原道》之义时,便从老庄道家系统入手而作阐发。这一点,当然是很可注意的了。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
黄侃接着引《韩非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战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文下有注曰:“道,公相。理,私相。”又引《庄子·天下》:“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所不在。”黄侃于是论到:“庄、韩之言道,犹言万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韩子之言,正彦和所祖也。”
众所周知,庄子在论说“道”无所不在时,尝有“道在屎溺”的话语,这种直通禅机的话头,具有将“道”泛化的意味。既然“道”无所不在,是“万物之所由然”,那么,文章本身的规律,也就自然具有“道”的价值了。无所不在者,处处在,道法自然者,法自身,在这样的理解和阐释意义上,以“自然”论文学文章,便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文学文章的独立意识。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要想破除古文家所谓“文以载道”之说对“道”的具体规定,最有效的理论方法又莫过于以无法为法。桐城派所阐发的古文家“文以载道”的“道”,由于有着自唐宋古文复兴以来的文论背景和与此相关的复性明道之心性哲学的思想背景,其指称是比较明确的。其实,在古文家和道学家有关“文”与“道”的多次讨论中,已经涉及到了其为两物还是一体的问题,而在为人与作文相统一的意义上,“道”与“文”既然是一回事,便不存在从外面拿一个“道”来放进“文”中的问题。所以,“文以载道”之说,尽管确实存在着妨碍文学自足性自觉的问题,但其自成系统的内在逻辑,未可轻易否定。至于老庄所谓“道无所不在”,以及进一层可说“道法自然”,并因此而以“自然”为“道”之内在规定,这却是一个带有玄学色彩的理论课题。若从“理,私相”“道,公相”的前提出发,则“文理自然”之“理”,就是所谓“行文之道”(注:张少康等《文心雕龙研究史》第244页。),换用现代文学批评的语言,不就是文学创作规律吗?但这样的推定有着明显的逻辑环节上的欠缺。一方面,作为特殊规律的文学(文章)原理不可能通用于其他事物,如同其他事物的规律不一定适用于文学创作一样,特殊和一般的矛盾将使“道无所不在”的命题发生裂变:或者,此所谓“道”者并不指任何一个具体的“道”,而只是泛指各个具体的“道”都各自存在着这样一种现实;或者,将不能不承认“道”之存在状态的多样性,这里将有“道呈万象”,而且不能不是在以“道”这个概念去表述“象”的内涵。无论如何,当黄侃因批判“文以载道”之说而突出自己以老庄之“道”阐发《原道》本旨之际,并没有就以上问题进行必要的论证。这一论证本来是应该有的。
虽则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黄侃对“载道”文学的反对。他因此而以“自然”为《文心》作者《原道》之旨,从而有着凸显文学自身独立价值的意向。如其曰:“即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这里的“泛论”与“非泛”之说,“无所不包”与“实有专美”之说,具有浓厚的辨证思维色彩。而正是这种辨证性的论述,为阐释刘勰原著和阐发自我思想提供了相对的空间。
那么,在此含纳古今、涵盖广狭、兼容骈散、并包雅俗的空间里,黄侃的学术姿态是什么呢?他在介绍阮元《文言》等说及乃师章太炎所评之后,曾明确表述自家看法:“又况文辞之事,章采为要,尽去既不可法,太过亦足召讥,必也酌文质之宜而不偏,尽奇偶之变而不滞,复占以定则,裕学以立言,文章之宗,其在此乎?”在不古不今、亦文亦笔而文质彬彬的辨证思维中,毕竟有一个主线——章采为要。
他毕竟是被誉为近代骈文高手的人,而《文心雕龙》一书原就是六朝骈文的代表作品!
至于刘勰《原道》是否以韩非之说为本,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了。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的主导思想问题了。
关于刘勰《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究竟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佛家,学术界有过热烈的讨论,各家俱有论有据,未可轻易作截断众流之判语。而在黄侃这里,于《原道》一篇,阐明刘勰所本实为韩非,而韩非所解又在老子,那么,显而易见,这是以老子所创道家学说为刘勰《文心》明道之本了。其于《征圣》一篇,则又道:
近代唯阮君伯元知尊奉文言,以为万世文章之祖,犹不悟经史子集一概皆名为文,无一不本于圣,徒欲援引孔父,以自宠光,求为隆高,先自减削,此固千虑之一失。然持较空言理气,忆论典礼,以为明道,实殊圣心者,贯三光而洞九泉,曾何足以语其高下也!
其中所谓“空言理气”,自然是指与古文家之文统相依存的道学家之道统。就像其批评“文以载道”之论而不遗余力一样,对心性理气之学,似也是深恶痛绝的。但平心而论,如姚永朴者,其论文学范围,也已经朦胧意识到其与性理之学的区别,就说明对“空言理气”者的批评,虽“桐城”后学也已经有所自觉了。既然如此,黄侃此地所说,难免带有一点意气议论的痕迹。相比之下,倒是对援引孔父以自宠光者的批判,实在具有价值,因为这乃是中国传统文学文章理论批评的致命特征,包括刘勰《文心雕龙》在内。正因为能意识到这致命特征之所在,所以,最终才能指出“衔华佩实”为“彦和《征圣》篇之本意。”其说云:“审是,则文多固孔子所讥,鄙略更非圣人所许,奈之何后人欲去华辞而专崇朴陋哉?如舍人者,可谓得尚于中行者矣。”在这个意义上,黄侃其实相对淡化了《原道》论的思想归属问题,而是把人们的思路导向文学文章的“中行”之路。
不过,至少在理论上,以“自然”为“文心”之本的观念,与“中行”观念之间,是有一定矛盾的。这一点,在《札记·乐府》中即有所表现。黄侃道:
彦和此篇大旨,在于止节淫滥。盖自秦以来,雅音沦丧,汉代常用,皆非雅声。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缪。彦和闵正声之难复,伤郑曲之盛行,故欲归本于正文。以为诗文果正,则郑声无所附丽,古之雅声虽不可复,古之雅咏固可仿依。盖欲去郑声,必先为雅曲。……彦和生于齐世,独能抒此正论,以挽浇风,洵可谓卓尔之才矣。然正声之生,亦本自然,而厌雅喜俗,古今不异,故正论虽陈,听者藐藐,夫惟道古之君子,乃能去奇响以归中和矣。……至于今日,乐器俗,乐声亦俗,而独欲为雅辞,归于正文,此必不可得之数也。
凡读过以上文字的人,都会强烈感受到黄侃所具有的复古意识和雅正观念。他当然和那种迂腐守旧者有别,因为他是主张“郑声之生,亦本自然”的。但是,在具体讨论到文学音乐和音乐文学时,他的“自然”观却受到了“中和”“雅正”规范的挑战。不仅如此,这里的雅郑之辨,实际上又与雅俗之辨纠缠在一起,所谓“厌雅喜俗,不仅不异”。而在作出这样的论断时,黄侃可能并没有考虑到,既然自古以来人们就“厌雅喜俗”,则所谓俗情郑声,不就成了“自然”之物了吗?为什么还要去俗情、去郑声而归于雅正呢?是否所谓“自然”者,本来就是指“中和”“雅正”之为自然呢?总之,对这些本来应该给予深入论证的问题,黄侃《札记》并没有给出自己的说明。而就其阐说所客观体现出来的倾向而言,这里对“中和”“雅正”的强调,多少与其鲜明反对文以载道之论的立场不相协调。
在这里,比较一下黄侃与姚永朴在雅俗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是很有意思的。
姚氏《文学研究法》专有《雅俗》一章,其论述以引述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开端,足见立场与黄侃相一致。但在具体的论述中,却沿着“雅俗全在人品上分别,人品全在心源上分别”的理路发挥,尽管现在看来太偏重于心性问题,但从文学就是人学的角度去看,其议论反倒显出了深刻。其引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语云:
夫所谓雅者,非第词之雅驯而已,其作诗之由,必脱弃势利,而后谓之雅也。今种种斗靡骋妍之诗,皆趋势弋利之心所流露也。词纵雅而心不雅矣,心不雅则词不能掩矣。
的确,真正的文学的独立意识,并非是指文学作品脱离现实生活,并非是指作家对现实漠不关心,而是指作家创作之际具有真正非功利性的意识。这可以说是一种创作主体精神。有此精神则雅,无此精神则俗。雅俗在神不在形。姚氏这种带有道学色彩的议论,未必不切中当今的现实!如果姚氏所论与黄侃所见彼此合一,则不失为更有深度的见解。
就黄侃而言,尽管与姚永朴这样的桐城后学相比属于《文选》派,并因此而具有颇重文采的文学文章思想,但与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相比,他显然又属于复古派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心目中的“自然”,大体上不具备与时俱进的发展求新意义上的“自然”性质。这一点,在《通变》一篇的讲疏中有着清晰的表现。其解释“通变”而开宗明义道:
此篇大指,示人勿为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
中间又道:
彦和此篇,既以通变为旨,而章内乃历举古人转相因袭之文,可知通变之道,惟在师古,所谓变者,变世俗之文,非变古昔之法也。
这样来阐释“通变”,的确与现今人们的理解有距离。当然,这要看其所谓“世俗之文”者,究竟指什么而言。如果是指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学,那就难怪当时的新文化人要以“选学妖孽”相对待了。或者,“世俗之文”另有所指。黄侃讲疏刘勰《通变》,于篇末附《钱晓徵与友人书》,其中有道:
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
黄侃实际上已经藉此而说明,他所谓的“世俗之文”,在一定程度上指的是“桐城”派的文章作风和理论讲求。既然“桐城”讲求是为“世俗之文”,则反对“桐城”者如“文选”派之所讲求者就是“雅正之文”。完全站在派别立场上议论,无论如何也是偏狭的。事过境迁,这种议论的意义和价值就会消失。不过,对当今的一般的古代文学接受者(注:这里用“一般的接受者”这样的说法,用意是这样的:凡是能够以学术的冷静来独立思考的人,不管他是专门的研究者,还是一般的古代文学爱好者,都会有自己经过思考的看法;而此外的人群,不管是大学的教授还是中学的学生,大体是满足于现成地接受书本上的结论的——而写作教科书的教授,又未必一定能超越时代的制约而真正运用历史的辨证的学术分析法。所以,对古代骈文的历史偏见,实在是一个沿袭多年而未必已经完全克服了的学术现象。)来说,黄侃的理论至少具有以下的意义:多种文学史在叙述散文发展历史时,将当时人们称为“时文”的骈文视之为形式主义和技巧主义,在与所谓占文相比的时候,大多站在古文的立场上批评骈文,久而久之,难免会形成一种误解,以为骈文就是“时文”就是“世俗之文”。殊不知,当反对骈文的古文家长期提倡古文,从而使古文成为流行文体以后,古文就成为“世俗之文”了。如果我们的雅俗之辨,总是在古代经典和当今流行相对立的思维框架里运作,那就必然会有这种交替轮换式的雅俗易位现象。天下大势,雅者亦俗,俗者亦雅,一切只在历史的轮回之中。是啊,自唐宋古文家提倡古文以来,到社会上普遍接受“唐宋八大家”这样的说法,并以他们的文章成就和创作经验为文学——文章学的理论基础,古文实际上就已经成了时尚。在这样的背景前来谈论“复古”改革,不提倡骈文又提倡什么呢?
而这样一来,关于“通变”的问题,便可以部分转化为“新旧”的问题。黄侃道:
新旧之名无定,新法使人厌观,则亦旧矣。旧法久废,一旦出之尘霾之中,加以拂拭之事,则亦新矣。变古乱常而欲求新,吾未见其果能新也。
很清楚,关于新与旧的判断,不能简单地只凭借一个后来者必新的标准。这种观念,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其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不妨看作是对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人斥其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回应。按照“冲击——回应”的原理,这正是旧学圈子里的人对“新人”挑战的一种回应。所谓“变古乱常而欲求新”,其所指还不明白吗!然而,黄侃不知可否想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新法是否已经“使人厌观”了呢?此其一。另外,如果完全以人心之喜厌为标准,那还有什么永恒的追求呢?再说,人心之所以喜此而厌彼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或者,就只一条——日久生厌?凡此,都是需要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相对于问题本身对学者思想的吁求,当时已有的思考是不够的。
但这并不会影响到人们对黄侃《札记》的充分肯定。
黄侃在解释刘勰《通变》“龌龊于偏解,矜激于一致”之句时,又一次抒写了对“高谈宗派,垄断文林,据其私心以为文章之要止此,合之则是,不合则非”的深恶痛绝。这显然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但是,以此而批评别人者,自己千万不要如此。不管是在对待新文学问题上,还是在对待“桐城”派问题上。即使到了我们今天来作二十世纪学术回顾的时候,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者,就以“私心”而评价他者,甚至对新文学新文化产生误解。当年新文学新文化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没有过时。同样,黄侃关于“高谈宗派”的议论,至今也还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黄侃在着重阐发刘勰《文心雕龙》之文学思想的时候,一面针对由来已久的古文、骈文之争,一面又针对当时新文学新文化对传统学术和古代文学的挑战,本着于复古中求通变的思路,借助于道家“自然”观念的理论潜力,作出了自己的积极回应。这种回应,在理论上远非完备。但是,其中一些充满现实感,也充满辨证性的思考,至今都有启示作用于我们。
黄侃《札记》,尚有一些问题需要再作专门讨论。
关于《神思》。
《神思》一篇,是《文心雕龙》有关于创作论的首要论述,历来受到学人的重视。如果仅从《札记》的篇幅上看,黄侃对此并没有投入太大的心力。但是,其诠释原著之际,却有一些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对“神与物游”一句,黄侃的解释是:“以心求境,境足以役心;取境赴心,心难于照境。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斯则成连所以移情,庖丁所以满志也。”显然,他是在运用唐宋以来诗学理论中情景交融的观念,以及相关的意境与境界理论。这一点颇可注意。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当与黄侃颇为独到的诗歌美学思想有关。其于《文心雕龙讲疏》中多次提到,自己又有《诗品讲疏》之著,并多次加以引述。如在《明诗》篇讲疏之际,其转录《诗品讲疏》有云:
按孙许玄言,其势易尽,故殷谢振以景物,渊明杂以风华,浸欲琼规洛京,上继邺下。康乐以奇才博学,大变诗体,一篇既出,都邑竞传,所以弁冕当时,扢扬雅道。于时俊彦,尚有颜鲍二谢之伦。要皆取法中朝,力辞轻浅,虽偶伤刻饰,亦矫枉之理也。夫极貌写物,有赖于深思,穷力追新,亦资于博学,加工欲排除肤语,洗荡庸音,于此假涂,庶无迷路。世人好称汉魏,而以颜谢为繁巧,不悟规摩古调,必须振以新词,若虚响盈篇,徒生厌倦,其为蔽害,与剿绝玄语者政复不殊。以此知颜谢之术,乃五言之正轨矣。
看来,黄侃当年是打通《文心》与《诗品》两书来作讲疏的。众所周知,钟嵘《诗品》在评品谢灵运时,就曾一反世人繁富之讥而作出“其繁富宜哉”的评价,而其关于谢诗“外无遗物,内无乏思”的概括,便体现出对写物与穷理的双向理论认可。谢灵运是中国古代山水诗传统的开创者,“大谢模式”甚至成为后来者用五言诗体写照自然的习惯手法,也因此,对“颜谢之术”的肯定,以及因此而必然具有的对刘勰所谓“近世之所竞”的肯定,实际上不能不是对诗人风景审美心理的肯定。肯定了诗人写物之志,也就肯定了诗意风景之美,这样,历来所谓情景交融以及意境、境界的议论,自然成为题内应有之义。这当然与其不去辞华的《文选》派立场有关。不过,其于汉魏之外,特意凸显颜谢地位,并因此而推崇“钻貌草木之中,窥情风景之上”的艺术创作世界,确实具有启示意义。
对于中国古典诗学来说,以情景交融为理想境界,乃是—个历史的共识。尤其是唐宋以后,论诗之言,十九涉及到“情”与“景”两个概念,并且无不以两者的水乳交融为理想所在。这一诗学史现象的形成,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原因。就实践方面而言,晋宋以降诗人作家热情描写自然风景的创作成就,以及在此基础卜形成的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发达,乃至于与山水诗发展相协调的宋代山水画的繁荣,共同促成了表现东方诗情画意的艺术理想。而就理论方面而言,刘勰《文心雕龙》专设《物色》一篇来讨论相关问题,钟嵘《诗品》充分肯定“巧构形似之言”的诗歌作品,入唐以后,王昌龄《诗格·诗有三境》第一就讲到“物境”,而且明确说它专指“山水诗”,同时又在其他论述中提出“景入理”“理入景”等具体的艺术方法。凡此,足见体物写景一事,已进入人们的艺术思维,成为诗学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了。刘勰《神思》一篇,关系到对创作原理的阐释,这种阐释,既需要从一般原理上展开,也需要结合历史背景来展开,黄侃解“神与物游”而运用“心境相合”的理论话语,显然具有释“物”以“境”的倾向,而其所以如此者,又显然同对“物境”的诗学认识相关了。应该看到,如此一种理解和阐释,是体现出了黄侃对古代文学发展史脉络的准确把握的。
关于《风骨》。
若从对后人之影响巨大这一角度而言,黄侃《札记》之说《风骨》,当推第一。黄侃道:“二者皆假于物以为喻。文之有意,所以宣达思理,纲维全篇,譬之于物,则犹风也。文之有辞,所以抒写中怀,显明条贯,譬之于物,则犹骨也。必知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然后不蹈空虚之弊。或者舍辞意而别求风骨,言之愈高,即之愈渺,彦和本意不如此也。”在下文中,他又说道:“综览刘氏之论,风骨与意辞,初非有二。……自为文着,不能无注意于命意与修辞也。”他同时还指出:“《风骨》篇之说,易于凌虚”。另外,在解释《熔裁》一篇时,又一次指出:“作文之术,诚非一二言能尽,然挈其纲维,不外命意修辞二者而已。”可见,在黄侃看来,命意构思,修辞写作,是文学文章最基本的要素。若本着其务实而不凌虚的精神,这样的阐释思路是很有意义的。这一阐释思路的最大好处,自然就是简明而平实。多年来,许多人接受黄侃的思路,原因之一也就在于简明平实。
当然,每逢此时,又要引发一种未必多余的思考:对某一前人专著的研究,是以阐明原意为上呢,还是以启示新思为上?
若就阐明原意而言,则黄侃所讲,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刘勰原著有云:
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又云:
相如赋仙,气好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
不知道黄侃所谓“易于凌虚”者,是否也包括刘勰原说在内。如果不包括刘勰原说,那么,我们则要指出,刘勰《风骨》之原意中,其实是包括“凌虚”之意的。不然,司马相如之《大人赋》,杨雄批评其以此为“风”而“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注:《汉书·杨雄传》引杨雄语。)者,刘勰何以举为例证呢?可见刘勰“风骨”论原是带有一些“凌虚”色彩的。为什么会这样?请注意刘勰的具体论述。其一,刘勰论“风骨”之际,曾特意提到曾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观念。这一观念,与刘勰最后将“风骨”概括为“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是有一定联系的。唐代陈子昂《修竹篇序》是刘勰之后第一位明确复兴“风骨”理念的人,而他对“风骨”之作的形容是:
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
其中,所谓“骨气端翔”,就分明含有“凌虚”“凌云”的意味。如果说“骨气端翔”的“翔”可以体会作凌云飞翔之意气,那么,“端翔”的“端”字,应该就是端庄的意思了。这样一来,“风骨”就不仅是一种关系到文学文章一般创作原理的范畴,同时也是一种与文学文章风格相联系的范畴。作为对创作原理的揭示,黄侃的“命意修辞”之说,可谓切中要领。而作为对风格理想的确认,黄侃所解就有些隔膜了。黄侃在自己的解释里,没有注意到“风骨”这一范畴与“风清骨峻”这一命题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就难免会忽略一般原理与特定追求之间的理论统一。
此外,黄侃《札记》和大多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一样,缺乏严密的推理逻辑和话语逻辑,“自相抵牾处就不能强加掩饰了”(注:张少康等著《文心雕龙研究史》第1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比如,一面说刘勰不过是以“风”“骨”为喻而已,一面却又在说“风缘情显,辞缘骨立”,实际上已经将“风骨”看作实实在在的批评范畴了。由此亦可见,刘勰所谓“风骨”,并非比喻之辞。不过,在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以及关于这种理论批评的阐释研究时,也不能太注重于表述话语的逻辑性。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去迁就中国古人在理论思维上的感悟习惯和点评兴趣,而只是说,透过前人那看似不很严密的论述,把握其真正富有启示意义的见解,才是需要努力的方向。在这里,我们何尝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和阐发:“风骨”话语,既是一种比喻性的批评,也是一种论证性的批评,其合理之处,或许正在此似喻非喻之间!
当然,无论如何,黄侃未及充分阐释刘勰《风骨》论所含有的理想风格论的意蕴,这是应该指出的。
关于《隐秀》。
黄侃《札记》于此篇,在明确表示原“补亡之文,出辞肤浅,无所甄明”以后,遂又表明“仰窥刘旨,旁缉旧闻,作此一篇,以备搴采”的意向。我认为,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值得关注的,它所体现出来的学术精神,实质上是述而有作,分明区别于传统的“述而不作”。正是在此“有作”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对原著的创造性的阐释。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注: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在《隐秀》一篇的《说明》中写道:“黄侃《札记》又拟了一篇《隐秀》,其中颇有胜义。”至于具体是那些地方具有“胜义”,周振甫主要引述并分析了“燃隐秀之原,存乎神思”以下至“故知妙合自然,则隐秀之美易致,假于润色,则隐秀之实已乖。”周振甫的分析论述,主要集中在用景物、通过境界来表现精辟思想和深厚感情这一点上。他的阐释理路显然综合了古代诗学情景交融的理念和王国维“境界”说的意向,应该说是契合于黄侃原来思路的。黄侃本来有言:
按此纸亡于元时,则宋时尚得见之,惜少征引者,惟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真《隐秀》篇之文。
张戒的这两句话,分明与前此梅尧臣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一脉相承,反映着唐宋以来诗学思想对审美风景的特殊关注,以及因此而使传统的比兴模式发生重大变革的理论发展趋势。后来王国维探讨“境界”之美,也是以唐宋以来诗人词家的佳篇名句为经验基础,其论述显然具有对诗意世界之景象化的讲求。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黄侃的补文,可能采撷了这些合理的理论成果。就像王国维论“境界”而并称“真景物,真感情”一样,黄侃一面说“至若云横广阶,月照积雪,吴江枫落,池塘草生,并自昔胜言,至今莫及。”一面又道:“故知叙事叙情,皆有秀语,岂必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争奇一字,竞巧一韵,然后为秀哉?”注重融情思于景象,但又不拘束于物色形似,而将视野放展到叙事与抒情领域,其思路既清晰,其见解亦精确。而这种清晰与精确,不能不考虑到黄侃毕竟已身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一历史的真实。
不仅如此,黄侃补作《隐秀》一篇,显然是出于一种系统的理论思考的。在此系统的思考中,确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值得现在提出来重新加以讨论。
其一,其说先云:“盖言不尽意,必含余意以成巧,意不称物,宜资要言以助明。”后面又道:“目送归鸿易,手挥五弦难,隐之喻也;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秀之喻也。”就前者言,黄侃已然是在联系魏晋“言意之辨”的背景来作思考,并且将“言意之辨”的背景与陆机《文赋》对“恒患文不逮意,意不称物”之创作难题的思考结合起来了。这样,自然就使这里对《隐秀》意蕴的阐发拥有了一种思想史与文学批评史相通观的深度。尤其是当他将“言不尽意”的哲学思考和“目送归鸿易,手挥五弦难”(注:黄侃此处不知是否有意将原来的“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改为其补文之所表述。好在其精神所在,不难理解,故引文之确否,另当别论,此处不作讨论。)的美学论题联系起来时,关于“隐秀”的探讨,就富于艺术哲学的意味了。不过,问题也恰恰在于,黄侃在接触到这样一种艺术哲学的问题时,其思考却是不完整也不严密的。须知,由于言不尽意而不得已留下深思妙意在言外,与言有余地而故留情思在言外,明明是两回事。有话不说,与说不明白,当然是两回事了。黄侃于此,未见阐发。另外,当年陆机所谓“恒患文不逮意,意不称物。”所表现的理论自觉,其实是期望着“文逮意”“意称物”,从而才有了“巧构形似之言”的一代潮流。黄侃于此,应有必要的说明。其实,从下文有关论述可以领会到,黄侃之意与陆机之所期许,本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阐发上,却显得薄弱了。
魏晋“言意之辨”,本来是由“言尽意”与“言不尽意”两种观点的争辩构成的。如果只有一种观点,那又怎么可能形成“言意之辨”呢?“言意之辨”是所谓魏晋玄学的重要课题。而所谓“玄学”之“玄”,用《老子》首章的意思来解释,应该就是先承认“言尽意”与“言不尽意”两者,然后认识到:“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这里的“同”,自然有“同根”“同生”“同存”诸义,就其“同生”“同存”者言,正因为同时存在着“言尽意”与“言不尽意”,所以,才有可能于可尽与不可尽之间寻找创造性的空间,才有可能设计出一种可尽而不必尽的特殊模式。如果只有“言不尽意”观,那就只能是穷其言语之能而不逮其意,还谈什么留有余意在言外呢?若因言不尽意而留其未尽之意于言外,则其意本属未明之意,作者本就不明,以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这是知难而退,又岂可视为理想境界!即使从文学史实的角度看,魏晋以来,一方面是“清谈”背景下的玄言文学的流行,它代表着人们对思辩性理性语言的运用热情;另一方面,则是“钻貌草木之中,窥情风景之上”的巧构形似之言,它代表着人们对描写性艺术语言的运用热情。不管是思辩性语言还是描写性语言,都体现出人们对语言表达能力的追求。正因为有如许这般的追求,所以才有苦于表达不出来的困惑和无奈,并同时产生广“言不尽意”的意识。显然,穷尽语言能力与苦于语言无力,是彼此依存的两个方面,如人手之有手心手背,这中间的细微深奥之处,以及矛盾辨证之思,古人其实已有展开,而今人尤须深入探询才是。黄侃毕竟是旧式学者,其论述辨析之未见透彻,尚有可以体谅处。如果我们在进一步研究其论述辨析时,仍然不能发现问题并作出必要说明,那就太不应该了。
其二,黄侃《札记》之自阐《隐秀》意蕴,有云:
《易传》有言中事隐之文,《左氏》明微显志晦之例,《礼》有举轻以包重,《诗》有陈古以刺今,是则文外重旨,唯经独多,……
刘勰原著,本来就有《宗经》的倾向。黄侃此处说“唯经独多”,乃是情理中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春秋左氏传》的微言显晦,与《诗经》的陈古刺今,共同看作是“文外重旨”的经典,视之为“隐秀”之美的典型,这是意味深长的。要知道,《春秋》笔法所体现的微言大义,与诗人比兴所体现的美刺讽喻,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彼此依存的两大文化批评系统。讲“隐秀”而联系到这两大文化批评系统,自然就赋予“隐秀”以文化批评的色彩。这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黄侃列举了屈原《离骚》、宋玉《九辨》、贾谊《吊屈》、杨雄《剧新》、王粲《登楼》、以及《古诗》十九首、阮籍《咏怀》等等,凡此,无一不是抒愤感慨之作,大都被文学史认为是具有兴寄的作品。而这样一来,“隐秀”作为一种理想的文学文章境界,就具备了丰富的内涵。仅就《札记》所明确表述者而言,不仪有“依《诗》以取兴”从而“假喻”“托情”的艺术特征,而且有悲思自伤、寓讽谏君的精神趋向。最终,说明“隐秀”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文章的修辞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情余言外”“状溢目前”的形象含蓄问题,而是有着与精神内容直接相关的特定追求。黄侃的这一理解和阐释,确实具有启示意义。
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时代的局限。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一书,作为二十世纪里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中专书研究的奠基之作,其阐释之合理合情与否,人们很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总体来说,其于“文选派”文章讲求之外,更能含纳传统人文情怀于其中,这是十分可贵的。也许,正因为其有阐发传统人文情怀之意,所以,每能超越“桐城”与“文选”之争而在更高层次上与现代思维达成共识。当然,另一方面则是学界已经认识到的循本务实的学术态度,以及因此而表现出来的对文学史实的尊重,比如对六朝美文,包括巧构形似之言,他都给予较为充分的肯定。一般说来,作为研究传统学问的人,往往会与新的现实比较隔膜,而黄侃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含新容古式的“通变”意识,实在耐人寻味。二十世纪初的学术界,没有人不感受到古今中西文化冲突的巨大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