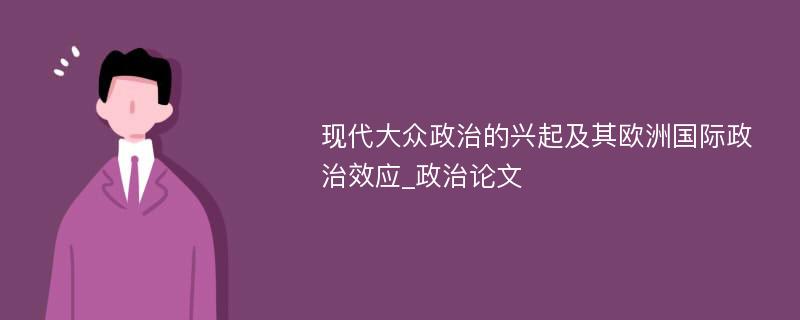
现代大众政治的兴起与其欧洲国际政治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欧洲论文,大众论文,效应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04:D509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 —0214(2000)02—0090—06
一
国家是近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而其对外政策的性质和内容、为贯彻这些政策动员和运用国家资源的方式,以及可用于对外行动的资源的规模,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同国内社会的基本政治关系,或者说取决于参与国家政治(包括参与对外政策在广义甚至狭义上的形成)的社会成员的范围,还有这参与的程度和方式。被相当大一部分国际体系理论家所漠视(注:“自相矛盾的是,关于国际秩序的种种理论既有过多地集中于国家的毛病,又有对国家演化着的性质阐析过少的弊端。”Ian Clark,The Hierarchy of States: Reform
andRes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Cambridge,1989,p.212。)的这一类因素,实际上在国际政治总体面貌的塑造方面有巨大的意义。在18世纪的欧洲(除英国、荷兰等极少数国家有所不同外),国家同国内社会的基本政治关系是王朝政治,即平民极少参与国家政务,国家利益大致或完全由君主利益来定义,而自19世纪最后30年起,经过欧美国家一般都有过的上层有产者代议政治这一过渡阶段,现代大众政治——“一般公民或臣民广泛参与政治事务”(注:K.J. 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3r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N.J.,1977,p.218.)——成为越益广泛乃至近乎普遍的国家政治形态。因此,如同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其他一些基本要素(包括其基本环境、界限、结构等)经历的变更一样,现代大众政治及其国际效应的兴起是19世纪开始出现的世界政治重大趋势。
二
现代大众政治出现并流行以前的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有其首要特征,那就是不受公众舆论影响,不管这影响是推动、襄助还是制约,也不管它们是通过较为明确具体的政治活动还是通过含糊笼统的所谓“对外政策情绪”(注:指一定时间内流行于一国国民中间的非常笼统的对外态度或倾向,例如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国民中占主流的对欧孤立主义。详见Ibid.,pp.394-395。)起作用。甚至可以说,在此之前一般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公众和公众舆论,王朝政治时代尤其如此。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曾称希望在他打仗的同时,农夫和工匠照旧劳作而对之一无所知——实际上这夸大的愿语离那个时代一般平民无闻于政事的实况相去并不很远,奥地利的梅特涅则干脆说“对外事务与老百姓无关”(注:Gordon A.Craig and Alexander L.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3rd Edition,Oxford,1995,pp.20,29.)。同样,在现代大众政治出现并流行以前,大体上不存在对国家对外政策制订积极地施加影响的政府外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例如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事情还远“未发展到工商企业组成游说集团和谋求影响政治决定的地步;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工商业家相信政府能做的最好事情是不干预他们。将值得想望的对外政策举措同强有力的私人利益调和起来这一难题……还没有来折磨各国外交部”(注:Ibid.,p.29.)。 即使在那些已有独立或半独立的立法部门的国家,支配对外政策制订和实行的也是这么两条广泛的信念:对外政策控制权应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不让立法机构横加干预,外交谈判(往往连同其结果)则须保密,不能成为公开辩论的话题,否则国务家就无法在国际政治中足够有力、足够灵活地追求国家利益。所有这些状况导致和加固了所谓经典外交,直至当今许多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实践家仍对之赞叹不已。这种外交的实行者是一个有着跨国的共同行为标准和共同情趣风格的职业外交官共同体,或用大历史学家、法国七月王朝的外交大臣和首相基佐的话说,他们“在欧洲大社会里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它按照自己的原则、习惯、眼光和抱负而生活,在国与国之间的分歧甚至冲突中保持它自己平稳和持久的团结”(注:David 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1993,p.248.)。他们的基本准则是外交谈判必须始终机密(甚或连同外交承诺),必须非常耐心(哪怕有时流于无所事事),还必须完全依靠与普通人的情感冲突和浅薄无知截然相反的心理平静和专门知识(尽管这种信念时常反映了麻木、 偏狭和自大)(注: Harold Nicolson,The Evolution of Diplomacy.New York,1962,pp.102—107.“经典外交”问世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而其最后的系统的遗存可以说也在法国,亦即以德尔卡塞为主要执掌者的19、20世纪之交的法国外交。详见Ibid.,chapter 3;Felix Gilbert,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1890 to the Present.2nd Edition,New York,1979,pp.67,107.)。
三
现代大众政治将改变所有上述状况,不管这变化对外交素质和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好是坏,也不管它们在多大程度如此。这种国家政治形态的兴起有其根本性的社会历史进化原因:工业革命的广泛展开导致传统依附关系的瓦解和人口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由此而来的“大众社会”既产生了传统的政府机器所无法应付的种种新社会问题,也产生了倾向于要求按各自利益予以解决、并以自身的政治参与主动追求这样的解决的种种新社会力量。在此情况下,政府的产生和运行体制总会发生更动(注:Geoffrey Barraclough,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Harmondsworth,Middlesex,1967,pp.124—126.参见Mark R.Brawley,Liberal Leadership: Great
Powers
and
Their Challengers in Peace and War.Ithaca,N.Y.,1993,p.38.)。它像19世纪欧洲的其他许多重大事态那样,就发生时间而言异常集中:大约从1870年起不足30载,中欧、西欧原先的中上层有产者代议制因选举制度的改革,几乎普遍成了全体(或绝大多数)成年男性代议制,亦即初始的自由民主制(注:它将由于全体成年女性逐渐取得参政权利而进一步发展为较完全的自由民主制。当然,它就19至20世纪初的德国来说,多半只是形式的,而且是在残缺不全的形式上。)(德国和法国在1871年,瑞士在1874年,英国在1884年,西班牙在1890年,比利时、荷兰和挪威分别在1893、1896和1898年,意大利迟至1912年)。
选民范围急剧扩大导致了国家政治运作方式的一系列近乎革命性的变化。首先,获得政治权力或参政影响的根本途径变成了从千百万社会大众获取尽可能多的选票,而要进行为此所必需的争取和动员,就只能靠现代政党这一政治机器,其主要特征在于其大众基础或大众构成(即所谓“大众政党”),还有自下而上、统一经久的组织结构和大众化的政治宣传纲领。由此,现代政治差不多可以说就是政党政治,现代政府也相应的就是政党政府(注:参见Barraclough,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pp.128—129,138—139.)。其次,从“大众社会”内部各种各样较为具体、狭窄和多变的利益群体当中,必然随代议政治的扩展而产生出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它们主要利用政治家希望获得或保持公选职位这一几乎压倒一切的心理进行政治活动,以便为本集团的特殊利益影响国家政策。最后,由于政治机制的所有上述变化,加上随工业化而来的教育普及和信息加快传播,出现了现当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虽然外延含糊和内涵复杂使之至今仍为政治学上的一个辩题,但无论如何它确实通过越来越多的渠道直接间接地表达出来,并且以不同情况下有所不同的方式和程度,作用于总的来说越来越依赖于公众支持或许可的政府,从而影响国家政策的形成(注:关于自由民主制下公众舆论的定义、 内涵分析、 作用方式和程度等, 参见
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pp.392—398.)。由于这一切原因,进入20世纪时绝大多数中欧、西欧国家的政治已经是大众政治。不仅如此,即使在以后出现的与自由民主制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政治体制(包括纳粹和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之下,国家政治说到底一样是大众政治,因为它们都是对旧体制“在大众社会压力下崩解所作的不同反应”(注:Ibid.,p.129. 参见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Totalitarianism.Cleveland,1958,Chapters 10—12.),尽管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和利益集团在这些体制下的表现形态和作用方式还未得到足够充实的说明。
四
19世纪后半叶,随现代大众政治逐渐形成,公众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开始变得相当显著和频繁。较早的突出表现首推拿破仑三世的对外政策。虽然大众政治在当时的法国还未过完酝酿阶段,但这位既缺乏合法根基又极爱虚荣的皇帝始终非常惦虑公众舆论,无论是实在的还是他自己想象的,以致深知内情的奥地利驻法大使向国内报告说,在他那里对外政策只是用来取悦民心以求皇位合法化的一个工具(注:Henry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1994,p.107.“拿破仑操作对外政策的风格如同现今时代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根据电视晚间新闻的反应来衡量自己有多成功。”Ibid.,p.136.)。大半出于这个原因,拿破仑三世外交以急切近利、哗众取宠和摇摆不定为特征。在大致同时期的英国,固然找不到拿破仑三世这样的领导,但发展中的大众政治使得政府首脑在制订对外政策时几乎一样看重公众舆论:例如首相狄斯累里(保守党人)1877年因国内声讨奥斯曼土耳其暴政的舆论,不得不停止鼓励苏丹拒绝俄国放手干涉以便扩张的要求,从而导致俄国无所忌惮地发动又一次俄土战争;继任首相格莱斯顿(自由党人)更是主动迎合和积极助长此类强烈倾向于废除传统外交的公众舆论,而且正是靠此在1880年大选中击败了狄斯累里(注:基辛格将这次选举结果称为“公众舆论至关重要的新作用的最显著例子”。见Ibid.,p.161.)。约20年后,在英国大众政治已完全形成的情况下,厌德反德的公众舆论成了英德结盟尝试夭折的一大原因, 并且严重加剧了那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德敌意(注:G.P.Gooch,Studies in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NewYork,1942,p.66; Paul 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Antagonism.London,1980。还有一个尤其重要的例子,那就是俄国民族主义舆论在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由来的关键性事态之一——德俄关系恶化和俄法同盟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见Geor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k's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Relations,1875—1890.Princeton,N.J.,1979.)。在表明公众舆论开始严重影响国家外交的实例中间,所有这些只占很小部分,而国际政治学家对传统外交政策的一项核心内容所作的如下理论批评,则概括了远为更多的有关历史事件,那就是经典均势操作的一大前提——国家有依照制衡的需要随时从一个联盟组合转入另一个联盟组合的行动自由——大致只适合19世纪以前以王朝政治为普遍准则的旧欧洲,而不适合大众政治兴起并流行的现时代。“16世纪的君主们能够通过王室婚姻和随圣上一时喜怒而结盟或废盟,现代统治者却不能。在国民大众相信昔敌为友或昔友为敌以前,需要有经年累月的宣传。”(注:A. F. K.Organski,World Politics,2nd Edition,New York,1968,p.290.)
五
大众政治带来的另一新事态,是利益集团积极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它同样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变得越益频繁,而且往往后果重大。其中,殖民、经济和军事三类利益集团最为引人注目,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或者盘根错节地结为一体,或者互相协调共兴波澜。作为殖民活动的最积极力量和开拓先锋,许多冒险家、传教士、商人、驻外军人和为他们提供物质后援和精神支持的殖民主义社团,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现代帝国主义扩张狂潮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致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强调这狂潮“与其说是政府有意组织策划的结果,不如说是坚执之士群体的活动的结果”(注:René Albrecht-Carrié,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Vienna.Revised Edition,New York,1973,p.191.)。按照另一位历史学家的描述,例如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军人在海外扩张方面肆意妄为,以“取悦(母国的)殖民宗派”,并且为此同报界串通一气来制造公众舆论。殖民利益集团的构成范围如此广大,甚至一定程度上包括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注:V.G.Kiernan,European Empires from Conquest to Collapse,1815—1960.Bungay,Suffolk,1982,pp.176—177.“王家很高兴(同殖民军人一起)分享出风头机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维多利亚女王像(法国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力普一样,需要使王位解脱不得人心的状况,而且她是个全心全意的帝国主义者。在占领埃及过程中,她一天里就向陆军部连发18封信函,确实以一种格莱斯顿认为违宪的方式干扰政务。”见Ibid.,p.177.)。就当时这类利益集团明显左右国家对外政策的例子而言,最受后人广泛注意的是有大工商利益背景的“德意志殖民协会”等团体,它们经过愈演愈烈的鼓噪,促使俾斯麦恝置专注于欧洲而不搞海外扩张的政策,德国由此开始掠取殖民地。
同殖民利益集团相比,经济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无孔不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它们造成的国际关系后果也同样重大。例如,容克地主势力集团为占据国内市场和抬高粮食价格,依靠各种政治活动使德国帝国议会于1902年通过新关税法案,以德国为重要市场的俄国谷物自此实际上被挡在德国门外。“这项关税打击了俄国国内一向对德国最友好的那个阶级的经济利益,一旦如此德俄和解的任何希望即告破灭”(注:Craig and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p.36.), 欧洲由此朝未来大战灾祸又迈出了一大步。至于军事利益集团,在许多场合同经济利益集团难分难解,它们一起造成的后果甚至更为严重,特别是因为它们作为重要角色帮助煽起了英德海军竞赛。大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揭示了这两者的结合体——用大半个世纪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创造的著名术语来说是“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如何在英国形成,又如何提供了海军竞赛来自英国方面的很大部分原动力。80年代初,以未来的英国海军大臣(1904—1910)约翰·费谢尔勋爵为中心,一批精通技术的海军军官开始同英国私营军火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几年后,这些企业因费谢尔出任海军装备主管而得以垄断海上重武器生产,它们同海军有关系统的中上层要人之间的个人关系网络也随之大为发展,而这两者的共同欲望及其政治活动目标便是多多益善地增加和更新英国海军军备。与此同时,选举制度改革使得选民范围急剧扩展,这同经济萧条结合起来,一反旧例地导致“追加开支比在繁荣时节更为紧迫和诱人,而不是使耗资巨大的海军法案更难得到议会通过”。在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自80和90年代之交开始,英国海军节节扩充,自90年代末往后的德国造舰大冲动更如同火上浇油(注:William
H. 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 Armed Force,and Society since A.D.1000.Chicago,1982,pp.269—277.麦克尼尔总结道:“这无一例外地倾向于使海军开支越来越大的一长系列政治决定,既是由快得无法控制的技术革命、也是由国际争斗和英国改变了的国内政治结构刺激而成。”(见第277页))。 事实上,德国方面同样有海军统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为首的海军—工业利益集团,它同样提供了海军竞赛的一大原动力。
六
在一定意义上,大众政治同民族主义是一对历史孪生物,而现代大众政治的勃发同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泛滥有密切联系。法国大革命既首创了大众政治(尽管是在大革命这一非凡情况下),也宣告了民族主义的真正兴起。在革命爆发阶段,国民议会大致同时颁布了两项分别象征人民主权和“民族统一首次实现”(注:Hans Kohn,Nationalism:Its Meaning and History.Malabar,Florida.1982,p.24.)的宪法性文件,即《人和公民权利宣言》与废除地域、 等级和其他传统封建特权的法令,它们明白无误地表明民族主义就是“在传统的地方性忠诚之外对中央国家的强烈感情依恋和普通公民或臣民之介入其政府的政治生活”(注: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p.66.着重号系引者所加。)。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之间的联系具有一种逻辑必然性:作为一种超越地方和社会阶层的文化心理现象和政治现象,民族主义说到底是民族大众性质的;民族主义思想除非转移到民族大众,变为激励他们行动的情绪、心态和感情,就不可能有任何重要作用(注:时殷弘:《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及伦理道德思考》,载于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9页。)。另一方面,随工业革命及其导致的社会大转型的来临,大众心理严重不适甚而强烈动荡,而原先起社会维系作用的传统道德观念、习俗和组织体制却已无可挽回地削弱或毁坏,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凭其提供的广泛认同感,给新生的“大众社会”增添了相当大一部分凝聚力(注:时殷弘:《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及伦理道德思考》,载于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6页;Kohn,Nationalism.p.24.)。
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在那些已不存在境内民族统一或民族解放任务的欧洲国家(除其中公认的弱小国家外),支配社会大众并主要通过大众非理性情感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大都构成导致或加剧国际紧张、威胁国际稳定与和平的恶性力量,而且这力量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急速大众化而异常强大。正如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所言:“民族主义之兴起意味着更广大人口的政治参与。大众不仅希望自己的意愿被听取,而且希望自己的国家无可匹敌。他们将国际政治视为他们本国应当在其中夺魁的竞争。由‘jingoism’这个词描述的民族傲慢横行于整个欧洲。”(注:Gilbert,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p.108.Jingoism意为极端爱国主义、侵略好战主义。)随教育普及而勃兴的大众传媒(特别是廉价报刊、小册子和通俗图书)在传播和鼓动极端民族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多半由其表述、助长甚或塑造的公众舆论,连同利用这舆论的利益集团活动,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几乎总是非同小可,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在1887年初的一次演说中,俾斯麦道出了得力于大众政治的极端民族主义在各国造成的严重压力:“人人都在问,战争是否行将来临?我不相信任何国务家会蓄意点燃越积越高的火药堆。然而群氓的激情、政党领导人的野心和被误导的公众舆论——这些因素比统治者的意志潜在地更为有力。”(注:Gooch, Studies in Diplomacyand Statecraft,p.42.)虽然俾斯麦本人一般来说讨厌并抗拒这类压力,而且这次演说针对的首先是当时在法国泛滥的大众化民族复仇主义,但如基辛格所指出:“前此作为保守主义堡垒的东欧宫廷(注:Eastern Courts:德、俄、奥三大君主国政府的惯用合称。)证明甚至比代议政府更易受民族主义公众舆论影响。
”(注:Kissinger,Diplomacy.pp.163—164.)至于现代大众政治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在作了上面这些说明之后只需强调一点,那就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猖獗于欧洲各大国的所有各类帝国主义思想,特别是种族主义形式的、宗教或救世形式的以及民族归并形式的帝国主义思想,都以更为非理性的形态广泛流行于大众之中,并通过种种大众化的渠道反作用于各大国政府,否则那个时期的帝国主义扩张大潮决不会那么凶猛,甚至它是否会出现也可以怀疑(注:参见Gilbert,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pp. 108—109.)。
【收稿日期】 1999—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