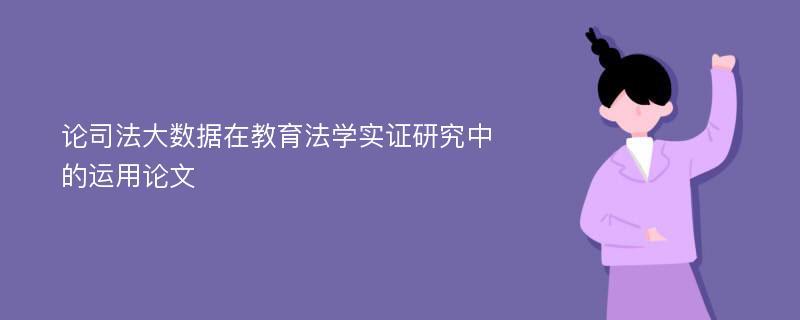
论司法大数据在教育法学实证研究中的运用
王工厂
(郑州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 长期单一的规范研究范式下,教育法学的学科交叉属性没有展现出来,在法学、教育学的双向误读中,教育法学的独立性被消弭。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法治实践中教育法学固有的、为规范研究所隐匿的独立特质,在基于数据的教育法学实证研究中逐渐显现出来。从法治实践中追寻自身的独立存在是新时代教育法学的历史使命和机遇;尽管现有数据库存在数据不够全面、相关性预测有限的限制,但大数据思维下的逻辑进路,巨量、权威、客观、迅捷的数据,更具操作性和可接受性的分析方法,还是让正在建设与完善的司法大数据为尚未真正起步的教育法学实证研究提供了现实路径。
关键词: 教育法学;实证研究;研究范式;司法大数据
一、教育法学研究范式的反思
考察30多年我国教育法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自发端就带有浓厚的实在法附庸烙印,基础理论及学科知识体系带有概念借用甚至生搬硬套式的“拼装”味道。20世纪90年代后,教育法制逐步完善,教育法治继续深入,在以劳凯声、湛中乐、秦惠民等为代表的学者努力下,教育法学研究渐次繁荣。进入新时代,高校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教育法学科理论从自发走向自觉。[1]学界开始反思和追问学科视阈下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路径;有学者对1985—2015这30年的教育法学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千篇一律的是基于定性分析的规范研究;[2]79-90基于逻辑演绎和价值推演的规范研究固有立场既定、结论预设的特质,难免会形成过分注重实然“文本法律”规范,忽视“活法”的思维定式。长期单一的研究范式使得作为交叉学科的教育法学,研究内容的交叉性却被虚化;由于规范研究的学术进路和概念体系的差别,法学视阈内的教育法学研究主要体现其法学的一般属性,基本局限在教育特别行政法的范畴,但教育法不仅涉及教育的法律问题,而且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行为密切相关,教育的特殊性被忽略;[3]教育学视阈内的教育法学则更多呈现了教育学话语特质,其对法学属性的规范推演则带有很强的套用其他部门法理论的色彩,缺乏自有灵魂。不同视阈内的教育法学理论建构各言其是,较少相互参考,教育法固有的独立性被隐匿,研究结论认同感较差。
以部分抑菌浓度(FIC)指数为联合药敏试验的判断依据,判断标准:FIC≤0.5为协同作用,0.5
进一步来看,研究范式多样化的缺乏甚或形成教育法学理论建构中法学、教育学的双向误读。任何理论背后其实都有它的经验基础,但抽象的理论会隐藏和消除经验的痕迹;尤其是实践性强的学科其诸多理论来源于实践,它隐藏或暗示了经验的前提。忽略甚或对这种前提的无知会误解、误用理论。一方面,用其他部门法的理论或者西方教育法理论推演教育法学,其经验前提在本土教育法治实践和学术氛围中并非显而易见,表面相同的概念和理论指称其经验性前提可能大相径庭;缺乏足够的经验内涵,曲解理论可能发生“指称错位”问题,也就是仅从概念字面意义上看,凭自己的片面理解、个体经验甚至去臆测,概念的本来含义被误读。例如,以民事契约理论解构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是对教育行为和民事行为的误读,教育除传授技能,还肩负人格养成、情操塑造等不能商品化的义务,合意行为不能涵盖;品格、情操不能复原和估值,违约责任不能适用。另一方面,以其他部门法理论来分析教育法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时,有可能对现有的教育经验进行割裂。理论自然具有建构性,可能会对现有经验加以重构,以自身的逻辑来建构性地铺陈经验,进而隐藏经验的逻辑,缺乏理论背后经验基础的足够认知,既有经验就可能会被碎片化地随意建构,就不能有助于全面认识法律现象。同样,在其他部门法理论视角下,其自身的一些理论内容均可以从既有教育法治经验中找到符合或不符合之处,该部门法理论也因此得以证成或证伪。“这种情况下,理论的认识功能,及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无法实现,既有经验也就无法得到提升,无法发挥出认识教育法律实践现象的有效中介作用。”[4]例如教育法问题可纯以行政法视阈内证成或证伪,但教育却绝非行政行为,教育过程尽管存在教学团队、科研团队和合作机制,可能包含行政行为,教育实践中的教师与从事教育的学者并非任何意义上的行政主体。总之,无论教育法学的其他部门法解读或者是借用、移植其他部门法概念肢解教育法,其根本问题都是单一研究范式下对本土教育法治实践的忽视,由此造成的误读或曲解,可能会消弭教育法自身。“研究方法的匮乏乃至缺失是教育法学的致命伤,没有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与多样化,教育法学根本不会被学术界认为是‘学’,教育法学就没有学术地位。”[5]
长期单一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教育法学封闭、静态的研究氛围;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静态和动态时认为,静止状态是生产与消费、分配与交换这些方面所依赖的各种一般条件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换句话说,在静态问题中某种特定类型的变化后果也被考虑,但一般的社会经济条件被假定是不变的。[6]89-94如果说法学整体的研究已有早期单一的政法法学发展到了诠释法学、社会法学以及新型的实证法学并存的阶段,而教育法学整体上仍处于诠释法学的阶段,尽管有学者在十余年前就提出教育法学研究已经出现了诠释法学(中国的诠释法学功能本质上均是以文本为中心来解释法律问题)向法社会学转变的趋向,但就研究文献梳理来看,这种转变显然没有完成。法学研究整体发展趋势和教育法治实践的变迁,并未引起大部分教育法学研究者的关注和回应,教育法学研究落后于其他部门法的发展。[7]劳凯声认为,“有些研究,仅从学科体系所提供的一套概念范畴、公式原理、理论观点出发,在自己设定的领地里自说自话,使问题演变成研究者头脑中的思辨之物,最终隐匿了问题”[8]。教育法学对教育法发展、进步的影响和引导是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教育法学应能从现实出发,直面现实问题,理解和解释‘实然’,通过科学的理性运动创造‘应然’,从而超越‘实然’,这就是教育法学的功能”[9]。如果教育法学的成长没有根植于本土教育法治资源,则教育法学规范诠释研究的工作越成熟、技巧越精湛,其和中国教育法治实践的距离就越遥远,研究结论就越荒谬,与社会期待的距离落差也就越大。教育法学除了“在法规范解释学的范畴内追寻外,应当从司法实践中获取相应信息,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观察教育诉讼呈现的实然状态的特殊性”[10]。
二、实证研究是法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实证研究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
实证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括所有基于经验对所得的一手资料进行的研究;狭义实证研究是与规范研究相对应的研究范式,利用数理统计和计量技术,分析和确定相关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数量关系,具有研究程序特定、明确,方法固定的特点。实证研究范式的出现和规范研究在科学研究中遭遇的瓶颈密切关联,具有历史必然性;在18世纪以前,科学研究在物理学、天文学、化学领域取得重要成果,人们更关注重复性运动规律的研究客体,进而举一反三,以演绎推理为主要逻辑进路的规范研究优势明显;随着经济学、管理学等复杂的研究领域兴起,规范研究对不符合单一运动规律的研究客体,采用确定、决定和普适的概念来描述时,也隐匿了研究客体的本质特征,获得的成果不能让人满意,规范研究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9—20世纪以来,哲学、数学和经济学的成果,特别是概率统计的发展,为复杂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技术工具,也奠定了实证研究的坚实基础。“经济学的更高阶段,对我们分析经济的增长与进步问题时,适宜的做法是少做演绎多做归纳。这正如产生推理结论的过程影响结论的性质和价值,如果结论完全是经验性的,那么它总在某种程度上有存在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如果结论来自演绎推理,那么,在结论赖以成立的假说被证实以及推理条件被肯定之前,结论就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存在。”[11]1-15所以,“合理的方法即是抽象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演绎的,也是归纳的;既是数学的,也是统计的;既是假说的,也是历史的”[11]89-94。事实上,实证研究的兴起是人们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研究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
(二)作为研究范式,实证研究在法学研究中正在兴起
较之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可以说是“新生事物”。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2000年之前,在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上发表的以“实证”为标题的文章,数量仅为18篇;自2000年白建军教授在《中国法学》发表《论法律的实证分析》一文以来,截止2018年10月,以“实证”为标题的文章已计1610篇,尤其是2012年至今更是呈高位震荡态势,总量就达1098篇,平均每年发文量都在156篇左右。尽管各部门法实证研究成果分布并不平衡,但总体均呈大幅上升趋势。[12]学者认为,法实证研究是中国法学研究范式转型升级、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内在要求,是一场“新的范式革命”[13]。尽管存在些许争议,例如,个案或同质几个案例的研究是否属于法实证研究,认识就有所不同,但学界基本上都认同法实证研究应当包含经验(明确、确定的过程或程序)、数据、量化统计以及以归纳为主的逻辑进路等基本要素。[14]30-40
基于各种原因所造成的教育司法案件数据稀少,随着司法大数据越来越完善,已经不再是教育法实证研究展开的主要问题;较之其他渠道,例如新闻报道案例、教学案例以及部分典型指标案例,司法大数据提供的官方记录更为权威客观,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的高度普及使得数据获取高效便捷。尽管较之其他部门法案例数据,教育法数据要稀缺很多,但并不妨碍以全样本或大样本思维进行实证分析;全(大)样本案例数据,很少有完全符合预先设定的数据种类。研究者只有在收集和处理案例数据的过程中才会发现,小数据的抽样调查需要问题预设,难免存在少量假设基础之上的立场既定;结论缺乏延展性,即调查得出的数据不可以重新分析以实现计划之外的目的。当然司法大数据中的“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大而全,笔者的数据收集过程发现,就裁判文书上网工程发布的数据文书而言,尤其是教育行政管理诉讼文书数量还是偏少,距离完全意义上的大数据尚有距离,最多是大样本数据,同时也需要说明,当数据大到一定程度时,结论的可靠性并不随着数据的增加而增加,存在类似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形,我们在一个案例数据上获取的有价值信息越来越少。因此,基于司法大数据的教育法实证研究,不用随机抽样的分析进路,而采用大数据的分析进路,也就是全样本思维。这样,基于司法大数据实证结论的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较之以抽样调查为进路的小数据时大幅提高。
2.1.2.2 健康教育方法的培训 在进行健康教育前护士应先了解患者的基本背景资料,如患者年龄、文化程度、生活习惯、家庭状况、职业、社会经历等,同时还必须清楚地了解患者的病情、对哪些指导内容比较感兴趣。交谈时,护士应掌握一定的沟通技巧,从最熟悉的人或事物谈起,并根据疾病的相关知识,结合患者的需要开展健康教育,从而提高患者对护士的信任感和对学习的兴趣,使健康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
四是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服务能级。2018年,成立上海市能源互联网创新联盟,推动全市能源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进一步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并顺利通过5A级社会组织复评工作。
3.可以避免规范研究学术进路差异形成的“误读”
(三)教育法学实证研究尚未真正展开
文献梳理后,可以发现,与其他部门法相比,教育法学实证研究显然已经落后。
首先,作为研究范式,实证研究尚未进入教育法学研究者的视野。教育法学语境中,鲜有对法实证研究范式探讨的成果。 截止2018年10月22日,笔者以部门法为搜索词并“实证研究”关键词对中国知网的文献进行精确搜索,得到文献分别为“民法”20篇,“刑法”为54篇,“宪法”23篇,“诉讼法”为52篇。可见,法实证研究在各部门法尽管存在较大差异,但均呈现发展上升的态势,文献数量逐年增加;前述搜索方式得到教育法文献仅1篇。可以说,教育法学研究中对实证研究范式的探讨尚未全面展开。[16]其次,对法实证研究范式的内涵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存在将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等同起来的认识,认为“教育法案学的研究可以繁荣教育法学的研究领域,从而提高教育法指导现实教育问题的能力”;[2]121指标式个案(以最高法院公报案例为代表)或是其他渠道得来的典型案例研究,主要是为了探讨案例中蕴含的法律规则,或者是作为问题提出验证某种理论预设,或是为了展示修改立法的必要等。尽管案例研究具有凸显争议增加问题意识的价值,但显然不同于以大范围数据收集、量化统计、经验发现为要素的实证研究,就其逻辑进路而言,仍是将案例几经剪裁、切割纳入既有理论框架,案例的内部结构和实践的联系被肢解。教育法学视阈内的案例研究,无论是个案研究或是部分典型案例研究,基本上是在诠释法学范畴内的规范研究。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自称为实证研究,但在整个研究方法中并没有体现数据分析,只能是有一定实证色彩的研究。[17]
1.研究现状表明,法实证研究尚未完全进入教育法学的研究视野
总体而言,对教育法治实然状态关注与回应的缺乏,不能满足教育法学发展和我国教育大国的教育法治实践内在需求,教育法实证研究落后于其他部门法,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教育法学整体研究的发展,使之与社会期待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2.教育法学实证研究现状原因分析
教育法实证研究尚未展开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方面:一是,教育法治实践数据稀少,存在开展实证研究的客观困难。教育法律刚性不足,柔性有余,立法质量有待提高,同时传统特别是权力关系理论对高校治理及司法机关的影响依旧存在,进入司法审查的高校治理纠纷受到限制,司法实践现状与教育法治发展需求深度割裂;数据采集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教育法研究者对基于主观逻辑及价值推演的规范研究偏好。二是,教育法学研究氛围相对封闭,缺乏法学、教育学的深度“科际对话”,没有实现与其他部门法在实证研究上的同向同行。我国的教育事业覆盖了十多亿人,一大批公民需要接受不止十年的教育,教育过程中产生涉及侵犯合法权益的纠纷数以万计,而现行的权益保护机制与教育法治实践现状相比较已经错位,解决问题通道的建设远远跟不上教育事业的进度。
确保建造工程的质量合格第一步就是保证所使用的施工材料质量达标。保证施工材料的质量就必须加强质量检测部门的专业技能,要不断完善检测流程,提高检测效率,提高检测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与职业素养,利用先进设备仪器去操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升建筑工程材料的检测过程的工作水平和检测水平,使检测结果更为准确,为建筑工程整体质量提供保障。
其次,实证研究应当以数据为中心。实证研究就是收集、分析数据并以此为中心展开阐述,在规范研究中,数据不是理论推演的关键,要么没要数据,要么将数据作为理论建构的论据。法律实证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数据而为的法学研究,当然不同于诠释法学以法条或教义为关注点、阐释点的研究,也显著不同于以个案关注为主的经验研究,包括社科法学研究。
三、司法大数据的建设和完善,为教育法学 实证研究提供了现实路径
(一)大数据与司法大数据
一般认为大数据具有Volume(海量数据)、Velocity(处理速度快)、Variety(数据多样态)、Value(价值)四个特点。我国最高法院主导的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工程,把作为法治要素官方记录重要载体的裁判文书,以官方机构平台发布电子文本形式向社会公开,发布平台包括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各省市裁判文书网,截止2018年10月23日,文书总量近5500万篇,访问人次近200亿。作为世界最大裁判文书数据库其巨量、多样态的案例数据蕴含巨大价值,长期从事法实证研究的白建军教授认为,由此我国(至少在理论上)建设了全国性的司法全样本,这是一座法实证研究的免费金矿。[18]30-32左卫民教授认为,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工程是中国司法乃至整个法律大数据的最新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关注和运用大数据的法律与法学研究方式会是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法律与法学界的普遍趋势”[19]。但也有学者认为,司法大数据的数据分析本质,仍为通过传统方法收集和分析的数据,与大数据思维与分析方法相距甚远。[20]笔者认为,关键是研究者思维的转变,以传统思维看到的是数据案例传统的内容和形式,以创新大数据思维看到的则是裁判文书上网工程的大数据基本特质,或许其有诸多不完善,但不能据此否定其大数据的性质。就法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方式而言,首要的就是法院公布的生效裁判文书,每一份文书都是鲜活的微缩的法治,是法治的细胞;蕴含着立法要素、司法要素;体现了实体规则和程序性规范;是字面法律转化“活法”的生动诠释,几乎囊括了与法有关的所有信息。[21]生效裁判文书是观察应然法实然表现的最佳途径,是法实证研究的最佳数据;基于司法大数据实证研究是对法实证研究的拓展与延伸,是互联网时代法实证研究的新形式。
(二)司法大数据作为教育法学实证研究现实路径的可能性
1.数据来源与结论更加权威、客观、高效、简便
你是了解我的小兰,我真的被李老黑暗算了,要不我怎么会办那样不要脸的事。我还怀疑,那天是李老黑把我灌醉后给拖过去的。再说,我已经醉成了一摊烂泥,就是真的跟李金枝钻了一个被窝,我也不敢对她怎么样啊。小兰,我可是清白的,你要相信我。你要不相信,我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首先,经验应当是实证研究的基本内涵。广义而言,实证研究也就是经验分析,作为“是什么”或“怎么样”的知识体系,强调“发现”而非“认为”;法实证研究关注现实中法律规范运作的实际过程,迥异于诠释法学关注实然法律规则而忽略法律运行实然状态的做派。这也决定了实证研究的“经验”分析过程是清晰可见的、可重复的,对某个事实的描述和解释才是可信的;研究结论不是价值评判,应当可验证,毕竟假设不能仅偶然地被支持,而是对研究对象总体真实状态的反映;同时研究结论也是客观的,是基于数据推导而非主观判断得出的;实证研究是经验的同时也是对研究过程的展现。
2.大数据思维下,教育法学实证研究进路更具有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
4总而言之,为了促进土地整治项目地顺利开展,如今,人们积极使用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技术,基于此技术的使用取得显著的效果,比如,能够及时获取数据信息,同时更加清晰地获得图像资料等,这种技术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每一个阶段,基于此,项目工程的每一个环节的工作能够更加有效地完成,提高土地整治的效率。如今,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技术也积极使用在其他领域之中。
法实证研究的要素之一就是基于数理统计的案例数据量化分析,在数据少的时代,传统的样本分析很难容忍误差数据的存在。如何防止和避免在采集样本和分析时出现错误,统计学使用了一套策略来减少出错的概率和可能的系统性偏差。然而,即使只有少量的数据,这些错误规避策略仍然存在昂贵的成本。许多法学研究者,在认识法实证研究这个新生概念的最初阶段,往往就因为接触到复杂的统计学论述(或其他非量化的复杂研究方法),失去了对于法实证研究的兴趣。这种“成也统计、败也统计”的法实证研究发展,不仅在我国,在其他法实证研究有更长历史、更多研究者投入的国家,也深受其累;关于此种对研究方法的陌生和抗拒,学者Methodological Anxiety Syndrome称之为“研究方法焦虑症候群”[22]。大数据思维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精确性的优缺点,追求精确性是信息匮乏时代的产物。数据匮乏时,任何数据点的测量都是结果的关键,每个数据的精确性都需要得到保证,才可能预防偏差。大数据时代要接受纷繁数据不精确的存在并从中受益,而不是以高昂的代价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大数据的容错思维下,门槛较低的描述性统计方法,有助于更多研究者接触法实证、了解法实证,进而从事法实证研究。
再者,实证研究是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逻辑推演。实证研究是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经验研究,实证分析中的定量分析既有研究客体范围、规模、内部结构的量化描述,又有客体与外部关系的量化分析,同时也包含对研究客体发展趋势的推断描述。也就是说,实证研究应当具备样本分析结果与真实情况相当接近的精确性、相信概率真实的可信度和可以延伸应用的共性。个案研究方法在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方面经常受到批评,虽然直观感觉、案件细节仍然重要,但一定程度上的定量数据收集、分析和判断已成为国计民生决策的重要依据。[15]25-30定量与定性的区别又是相对的,具体而言,定量研究在数据分析基础上进行归纳的同时,它仍然需要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原因,而这实际上需要个案的细节描述、比较分析来描述,没有定性研究,基于经验的定量研究难以提升;“演绎与归纳的相互补充,即使当我们主要依赖归纳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结论应通过演绎推理来确认和解译。”[15]130-133
教育法学独立性的消弭,很大程度上和其教育学、法学的交叉属性被隐匿相关联。学术进路和概念体系的差异,使得教育法学的双向误读在规范研究范式下似乎是个难以破解的困局,教育学界多年呼吁的“教育法学应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并未引起法学界相应的关注与回应。作为一个教育大国,教育法学的发展应当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司法大数据的裁判文书数据作为法治记录的官方发布,其受众范围由当事人扩及于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既有定分止争又有价值引领,基于此的教育法学实证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回避规范研究的“误读”。关注和回应实然教育法治实践的本土资源,发现实践中的教育法是新时代赋予教育法学的使命,更是教育法发展的历史机遇;而司法大数据为追寻实践中的教育法提供了绝佳的技术路径,使其以客观、独立的实然状态呈现自身的存在。
四、司法大数据的局限
司法大数据是一种资源,也是法实证研究的一种工具。它告知信息,但不解释信息;指导理解教育法治实践的同时,也可能会引起误解,这取决于其是否被正确认识和使用。
(一)由于技术因素和主观因素,司法大数据仍需进一步完善
一方面,文书数据的公开量、及时性仍有待提升,同时文书公开监督应进一步深化,保证上传文书数据的质量,同时法院内部系统之间有待进一步协调,确保统一的发布平台运行顺畅和良好的技术关联,文书公开的地区差异有待进一步消除。[23]另一方面,归类问题也增加了数据收集难度,例如教育行政管理诉讼的案由没有列入数据库,笔者对相关数据文书的收集基本是靠多次变换主题词反复搜索来完成,难免存在人为遗漏的情形。司法大数据的“大样本”数据到“全样本”数据尚有距离。
(二)司法大数据的全样本或者大样本缺乏对个案异质性的关注,对部分样本不够大的微观问题分析可能会出现偏差
正如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所有的数据案例都是有差异的,每个数据内部都隐藏着某些未被发掘的价值,其真正的价值就像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山,乍一看只能看到冰山的一角,但大部分都隐藏在表面之下。大数据的全样本和容错思维决定了其难以关注个案异质,难以对异质案例进行科学化归纳,结论的普适性甚或有失偏颇;实证研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归纳理论上的全样本数据而产生的一般性结论,带有某种程度上的风险性,数理统计回归分析专门手段的缺乏,难以对多个案例数据进行定量尺度的本质考察,形成的结论抑或会是狭隘的和特殊的,可能无法提升至一个普遍适用的水准,形成结论信度上的不足。同时,数据案例的异质性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观察同样异质的数据案例集合,实证研究在对司法大数据的案例数据定量分析的同时,会因迁就巨量、繁杂的数据而过于烦琐,更为细节的描述、机制的增加和过程的讨论,这实际上又需要个案研究、比较分析加以支持。这会使深度依赖数据案例的实证发现结论,尽管在细节方面很丰富,但在结论的把握上往往缺乏简洁的整体视角。
依次进行不进位加法和不退位减法口算测试、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口算测试.程序方法一致,下面以不进位加法和不退位减法口算测试程序为例进行说明.
(三)基于大数据相关关系的预测具有一定的或然性。
司法大数据相关关系的预测,是教育法学实证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数据案例是对法律实然状态的记录、分析和重组,司法大数据提供的是一种发现,不能准确地表现诉讼为何会发生,它只是将正在发生的这件诉讼呈现出来。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提醒的帮助已经足够大了,但作为应然法律投影的文书数据并不完善,据此做出的预测本身仍具有相当程度的或然性。因果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相关关系,应结合局部小样本精确量化或深度描述确定相关关系向因果关系转化。
五、余论
尽管教育法学的规范研究提出了诸多具有洞察力、生命力的问题,但较之于法学研究整体,长期单一的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制约了教育法学的发展,拉大了与社会期待间的距离。数据化时代,被隐匿的体现教育法固有特质的法律现象会在基于大数据的实证研究中逐渐显现,同时,基于司法大数据的教育法学实证研究,也使得教育法学和其他部门法学同处在发展的“弯道”。随着研究范式的进一步多样化、规范化,教育法学必将拥有更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1]龙洋,孙霄兵.对我国教育法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思考[J].教育学报,2011(6).
[2]祁占勇,陈鹏.中国教育法学研究热点的共词可视化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3).
[3]朱芒.高校校规的法律属性研究[J].中国法学,2018(4).
[4]陈柏峰.法律实证研究中的“经验”[J].法学,2013(4).
[5]褚宏启.教育法学的转折与重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6]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M].党国英,刘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7]谭晓玉.当前中国教育法学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J].教育研究,2004(3).
[8]劳凯声.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J].教育研究,2014(8).
[9]秦惠民.中国教育法学的产生发展背景与研究状态[J].中国教育法制评论,2008(6).
[10]湛中乐,苏宇.教育法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初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11]Bryan A. Garner.Black’s Law Dictionary[Z].Thomson West.10th ed.2014.
[12]http://kns.cnki.net/kns/Visualization/VisualCenter.aspx.2018-10-19.
[13]李林.共建中国的实证法学[C]//田禾,吕艳滨.实证法学研究(第一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4]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J].中国法学,2000(4).
[15]唐应茂.法律实证研究的受众问题[J].法学,2013(4).
[16]李扬.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实证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17]王工厂.教师劳动权诉讼救济实证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18]白建军.大数据助力法律监督[J].探索与争鸣,2015(2).
[19]左卫民.一场新的范式革命:解读中国法律实证研究[J].清华法学,2017(3).
[20]何挺.刑事司法实证研究:以数据及其运用为中心的探讨[J].中国法学,2016(4).
[21]白建军.案例是法治的细胞[J].法治论丛,2002(5).
[22]苏凯平.再访法实证研究概念与价值:以简单量化方法研究台湾地区减刑政策为例[J].台大法学论丛,2016(3).
[23]马超,于晓虹,何海波.大数据分析:中国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报告[J].中国法律评论,2016(4).
Discussionson Application of Judicial Big Data in Empirical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Jurisprudence
WANG Gongch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Zhengzhou Normal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044,China)
Abstract :Under a long-term, single, normative research mode, the interdisciplinary attribute of pedagogy has not been displayed,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pedagogy has been eliminated in the bidirectional misreading of law and pedagogy. With the arrival of Data Age, the inherent, independent nature hidden for normative research gradually emerged in empirical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jurisprudence. It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and opportunity of educational jurisprudence in the new era to pursue its own independent existence from the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Although the database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and the correlation prediction is limited, big data’s logical path, enormous, authoritative, objective, prompt data, and more operable and acceptable analytical method still make judicial big data, which is being constructed and perfected,provide a perfect practical path for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jurisprudence which has not really started yet.
Key words : educational jurisprudence;empirical study;research mode;judicial big data
收稿日期: 2019-03-20
基金项目: 2018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校生诉讼司法大数据的高校治理司法审查实证研究”(2018BFX017)
作者简介: 王工厂(1973—),男,河南太康人,博士,郑州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法学,教育法律实务。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09
中图分类号: D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 2019) 03-0050-0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标签:教育法学论文; 实证研究论文; 研究范式论文; 司法大数据论文; 郑州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