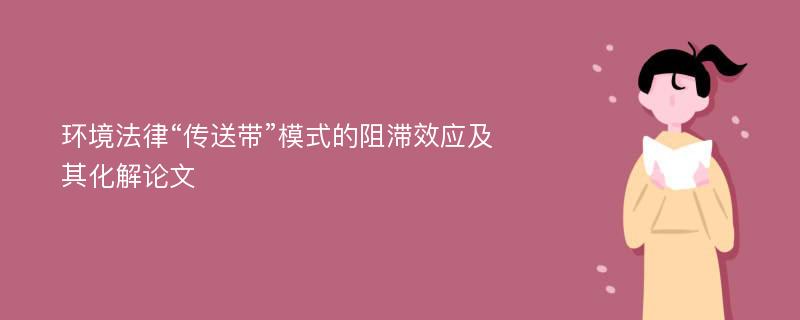
环境法律“传送带”模式的阻滞效应及其化解*
胡 苑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 环境法律及其实施具有高密度事前管控、涉多元正当利益衡平以及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等特性,传统的法律“传送带”模式将环境执法机关作为立法机关的附庸,导致了立法对环境执法的有效规范供给不足,法规范所传送的内容受限形成的环境执法僵化,以及立法内容抽离场域而不具有可实现性等阻滞效应。为应对“传送带”模式下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链接不畅、环境法治受限等问题,环境法规范模式需要从立法中心主义逐步向规制中心主义转型,即在环境事项上的权力配置逐步由立法机关主导转向规制机关主导,环境法律规则主要在行政阶段产生并由执法机关采用更有效的方式实施,以实现更加灵活和更具适应性的规则生成机制和规制执法机制,同时通过现有的司法体系和社会自我规制力量,为这一转型提供缓和性措施。
关键词: 环境法;传送带模式;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领域的立法具有问题应对和事件推动的特征,20世纪中叶后震惊世界的各国公害事件,成为现代环境立法兴起的导火索。公众常常因为特定的环境污染事件而进行请愿、发出主张和呼吁,从而成为国家环境立法的催化剂。各种已经发生的环境灾难,以及对未来即将引发灾难的悲观描述会造成强烈的集体恐慌和焦虑,而这种恐慌和焦虑最后只能通过“艰难的立法”来进行解决。① See Farber,Daniel A.,Politics and Procedure in Environmental Law,Journal of Law,Economics,&Organization,Vol.8,Issue 1(1992). 譬如前几年我国大城市秋冬季雾霾异常严重,人们对呼吸健康的焦虑情绪随着2015年初纪录片《穹顶之下》的传播达到了顶点,随后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迅速进行了修订并于次年实施。激烈的公众情绪往往会以特殊的方式影响环境立法的进程,但这一过程经常又是短暂的,当公众的激情消退并将关注点转移到其他领域之后,环境保护机构将不得不面临尴尬的处境,即必须将为数不少的模棱两可的立法转化为超级技术法规,并将这些法规适用于各类环境违法行为。② See Gauna,Eileen,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sfit: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Paradigm Paradox,Stanford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Vol.17,Issue 1(1998).
据汪劲教授统计,1979年至2012年中国制定的环境、资源、能源与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促进方面的法律有30多部,占同期国家全部法律的1/10,此外,我国还制定了相关行政法规60多部、部门规章600多部,并且发布了环境标准1000多部,但如此庞大的法律体系并未给环境法治提供完善的保障,环境立法“有数量无质量,既无大错也无大用”。③ 汪劲:《中国环境法治失灵的因素分析——析执政因素对我国环境法治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近几年中央发起的环保督察活动显示的情况,也证实了环境法律和现实的错位。譬如2017年原环保部督查组在进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时,两天内共检查734家企业,结果就发现604家企业存在环境污染问题。④ 《环保部督查组两天检查734家企业,超600家存环境问题》,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31/c_1121059183.htm,2019年2月3日访问。 在环境立法看似发达的表象下,存在着几乎可以表述为“环境违法为常态、环境守法为例外”的魔幻主义现实。
公众呼声催化立法的过程反映了传统的法律运作模式,也即法律“传送带”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理念是首先制定规范,然后才是执行规范。“传送带”意味着法律必须是由民选代议机关类的立法机构来进行制定,而行政机关只能像传送履带一样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代议机关制定的法律。法律“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理念体现了对执行机构权力的限制和警惕,因为早期行政法律的主要目标,在于克服警察国家的弊端和建立法治国家。⑤ 参见孙笑侠:《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构造》,《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为了防止行政权力对私人权利的随意侵害,行政法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演绎主要遵循控权性思路。我国在改革开放、寻求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正好需要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导致了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极大地吸收和同化了同时代的控权性行政法,韦德在其《行政法》一书中的描述详细地阐释了此种行政法治国之传送带的理念,“第一,任何事件都必须依法而行。将此原则适用于政府时,它要求每个政府当局必须能够证实自己所做的事是有法律授权的,几乎在一切场合这都意味着有限的授权。否则,它们的行为就是侵权行为;第二,政府必须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法治的实质是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但是议会授权常常是用很笼统的语言表述的。法治要求完全阻止政府滥用权力;第三,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完全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法官裁决;第四,法律必须平等地对待政府和公民”。⑥ [英]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由于环境法的内容主要是行政机关预防性的干涉行为人的环境容量利用和自然资源使用行为,其主要特点是基于许可下的管理规制,环境法律中的很大部分都属于行政法范畴。“在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中,环境法被视为行政法的一部分。”⑦ Michael G.Faure,Economic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Law:An Introduction,Public Economics,Vol.7,Issue 1(2001). 正因为如此,环境法体系也遵从了传统行政法律“传送带”模式,要求环保机构严格依法行政,然而环境法又有其自身的诸多特性,很难通过传送带模式实现。很多学者指出,由于环境法应对的问题复杂,所涉利益较广,环境法引发的新问题揭示了其与传统行政法理念和结构的诸多不适应,“行政法转变为利益代表模式与环境法的兴起同时发生”,⑧ 同前注②,Gauna文。 “可以说行政法的改变就是环境法引起的”。⑨ [美]理查德·拉撒路斯:《环境法的形成》,庄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页。 我国环境法律的“传送带”模式,使得环境立法内容有局限的同时环境执法进一步受限,从而影响了环境法的实施效果,导致了实践中的环境法治难题。
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使得法律在适用时有困难,对于故意传播艾滋病这种行为如何定性,不管是通过立法还是通过司法解释,都应该以明确的方式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进行规定。
二、“传送带”模式与环境法特性不兼容
行政法律“传送带”的核心约束性理念萌发于行政国家的形成早期,但在行政国家日益成熟的今天,这一法律结构性的基础原理是否仍然合理正遭受质疑。其实环境法的实施困境在诸如食品安全、药品管理等大量行政监管领域都已出现,只不过环境法作为一个单独且越来越重要的监管领域,其特性最为突出,从而显著地引起了行政法的演变。环境法的特性,使其明显和传统 “传送带”的控权性模式产生了内在的冲突。作为新兴领域,环境法秩序之良好实现所需的规范内容与实施路径,与传统行政监管事项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体现环境法律及其实施内涵的本质特性进行分析,是破解环境法“传送带”模式问题之所在的研究起点。
(一)环境执法是一种“无时不在场的监管”
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较,环境法具有极强的技术性特征,环境法在现实中的实施需要依赖于专业知识和技术规范。譬如,判定企业超标排污需要明确的排放标准,同时还要有专业性的环境监测数据;确定自然资源及生态破坏程度需要专业知识和勘查记录。这一特点也使得环境执法和传统的行政监管事项出现了差异。现代行政执法专家模式的倡导者认为执法机构需要自由裁量权,而不能刻板地遵循传统的“传送带”模式,因为“行政官员不是政治型的而是专家型的,由专家组成的执法机构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易于发现市场运行中的问题并提出和执行相应的治理规则,是行政机关拥有广泛权力的前提。现代社会行政管理所涉事项往往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立法者对于特定的事项经常缺乏专门知识,因而只能规定一般原则,而将具体问题留给行政机关裁量处置”。⑦ 周樨平:《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行政实施研究——以裁量权的建构为中心》,《现代法学》2015年第1期。 因此“传送带”概念存在着严重缺陷,环境立法往往不能充分规定环境执法所需的技术性问题,从而留下了大量模糊和宽泛空间,即便环境立法提供了详细的规定,环境执法机构也必须在执行时根据专业知识做出选择和判断,那种根据“传送带”理论推导的执法机关能够也必须严丝合缝地执行法律的判断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虚构而已。
然而环境法的事前行为与事后责任链条并不清晰。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加害人从制造损害到受害人发现损害中间有可能出现漫长的时间间隔与空间距离,加害者经常能够逃脱事后责任的承担。这是因为,环境损害要通过环境介质产生影响,其最先危害的是公共资源,譬如大量人口共用的空气、河流或者森林草场等资源,此种情况下共用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轻微的利益受损,但因无法主张权利,或者利益过于微小而不能或者不愿通过诉讼等方式实现责任请求主张。即便是受害人遭受了人身或者财产损害,因环境损害经常影响范围很广,每个受害者所造成的损害可能很小,以至于受害个体没有动力提起诉讼。此外,对于受害人而言,通常很难证明加害人活动与损害类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变得更加困难。② Landes,W.R.Posner,Tort Law as A Regulatory Regime for Catastrophic Personal Injuries,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13,Issue 3(1984). 如果损害在加害行为发生后很多年才出现,加害者很可能已搬迁、停业或者破产从而根本无法找到。这使得环境危害往往存在事后责任追究无力的问题,无法对行为人事前审慎作为产生足够约束。
会上,常务副总经理杨瑞生、副总经理刘江涛、马朝辉分别就集团公司2018年农资经营、房地产项目开发及资金运作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认真部署。
此外,环境危害行为人产生危害的频率和危害的严重性与一般行政管制对象也有所区别。任何对环境有危害的生产活动,只要生产进行,环境危害就必然发生,因为环境危害是生产活动的附随性后果,只不过在行为人遵守生产规范和排放标准时这种危害性可能会降低。与此同时,在企业生产阶段,环境危害行为人的事前注意义务其实对行为人自身有时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行为人本身对环境损害的造成并没有主观故意,有时也并不具备降低和控制危害的知识和信息储备,而很多常见的生产活动譬如化工品制造、金属冶炼、造纸和纺织等,均可能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环境危害事故。基于以上种种原因,环境领域的行政执法不是事后惩罚的低频监管模式,而是隐含“无时不在场”意义的高密度高强度监管模式。
(二)环境法涉及对多种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衡平
与此同时,环境事故容易引发社会关注成为热点,“当立法者的认知框架无法有效应对现代法律规制活动的知识挑战时,其不完备的信息能力将导致基于媒体话语的压力型立法。这类立法展现出有悖于理性立法的内在机理的决策特点”。⑩ 吴元元:《信息能力与压力型立法》,《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根据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其内容主要包含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这两大部分。社会压力会使得立法启动严刑峻法模式,在法律后果部分严加规定法律责任,以期通过威慑加快解决问题。我国2015年新实施的《环境保护法》被誉为“史上最严环保法”,以王灿发教授为首的新环保法实施效果评估课题组最新的评估报告指出:“新法两年的实施,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其实施不到位、作用发挥不理想的方面也严重存在。”①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效果评估报告(下)》,https://mp.weixin.qq.com/s/dR4ortczwkK6pk3L6VdGgQ,2019年2月6日访问。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威慑理论之所以有效,因其针对的主要是偶发性行为。然而,如前所述,环境法内含“无时不在场的监管”模式,此种高密度事前规制下威慑的彻底实现,其执法成本会高到不可想象。此外,威慑型环境执法引发的威慑过度,不仅直接执法成本高昂,还会引发间接执法成本,即第三方守法成本超过社会承受限度的问题。② 参见戴志勇、杨晓维:《间接执法成本、间接损害与选择性执法》,《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 环境规制要求政府通过行政执法预防损害发生,这个环节的产生本身是为了更有效率,但超过一定的威慑度之后,成本投入急增而效率改进不多,会导致威慑监管失灵。因此,环境执法改善的比较现实的核心未必就在执法环节本身,而很可能在于立法环节。
(三)环境法具有强专业性和技术性特征
为了“保护公众免受因高度工业化导致过度生产而产生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新社会监管将监管权力延伸至生产过程之中。之前由公司管理层控制的生产各环节,现在成为监管关注的对象”。⑩ [美]马克·艾伦·艾斯纳:《规制政治的转轨》,尹灿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环境执法的本质,是为了预防损害的发生从而需要“无时不在场的监管”。这就多少有一点类似于要求“为了通过预防来控制驾驶行为,执法人员必须与司机并驾齐驱;为了防止人们肆无忌惮地追赶公共汽车或以危险的方式烧烤,执法人员必须出现在公共汽车站周围和人们的后院中”。① Shavell S.,The Optimal Structure of Law Enforcemen,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36,Issue1(1993). 直到今天,现实的生活中,并没有这么做,对这些类型的行为,主要是靠行为人自身事前的谨慎注意义务和事后的法律责任追究来保障行为人的审慎作为。因为事前的注意义务并不繁重,事后的责任追究几率足以提醒行为人事前遵纪守法。这类危害性行为往往属于偶发类行为,故不需要太多的行政执法资源投入。
更进一步地看,在环境法律“传送带”模式下,各环保机构只能严格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即便执法机构实际上参与了细化执行标准类的准立法活动,这种活动也要限定在法律已有的框架内,而这可能会妨碍真正了解实情又具备专业知识的执法部门提出合理的问题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基于环境立法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背景储备,立法过程容易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制定空有愿景而事实上无法实施的法律。例如美国1970年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要求所有工作场所的环境有毒物质水平应保持在可行的最低水平。行政机关发现环境危害时往往需要大量支出才能略微降低健康安全风险。为了避免出现严重不良后果,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故意延迟启动了为多种有毒物质设定工作场所标准的程序。因此,尽管国会立法非常明确,但基于其现实的不可操作性,行政机关事实上利用其执法自由裁量权来大幅改变和架空了该立法。⑧ See Seidenfeld,M.,Civic Republican Justification for the Bureaucratic State,Harvard Law Review,Vol.105,Issue 7(1992). 面临环境领域专业性和技术性的挑战,强调法律优位的“传送带”模式往往并没有实现其法律权威性的目的,反而可能造成对立法和执法资源的浪费。
三、“传送带”模式给环境执法造成的困境
近年来,我国环境状况虽有所改善,但改善状况似乎与投入资源并不匹配。大规模的整治,本身便体现了环境执法面临诸多困难,在大规模治污过程中,还出现了不问违法与否的环保“一刀切”乱象。⑨ 《环保部部长:决不允许乱作为现象扰乱中央环保督察大局》,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wap/detail/sp/sp/shipin/cns/2018/03—17/news8470122.shtml,2019年2月5日访问。 此般现实,提醒我们应对我国环境法治进行根本认识,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环境立法以及立法的传导体系会决定环境执法模式,环境法治的实现,仍需要厘清症结性原因。
(一)立法“传送带”对环境执法的规范供给不足
“传送带”模式下,“人民代表机关通过立法将人民的意志传送给政府,政府通过执法治理社会,这是硬法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基本法治模式”。③ 姜明安:《完善软法机制,推进社会公共治理创新》,《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 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包含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行政执法监管无处不在,现有的行政法理论不仅未能将行政过程及其实践纳入其中,相反往往在远离具体行政程序的抽象层面上讨论,通常只是通过参考立法者的激励来解释监管后果,然而具体的监管决策实际上总是由行政机构而不是立法者作出的,只要将关注点转移到含有行政程序的现实世界,就会发现现有模式下监管寻租和执法失败的必然性。④ See Croley,Steven P.,Theories of Regulation:Incorporating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Columbia Law Review,Vol.98,Issue 1(1998). 环境法由于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其所涉法律问题经常是无涉价值的技术性问题,与发生的特定场域密切相关。比如20世纪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半数公害都发生在日本。其中著名的水俣病事件和痛痛病事件中所涉有毒物质汞和镉,在工业生产中并不罕见,而同期其他的工业先发国家并未出现此类大规模公害。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可能是日本“二战”后经济发展太过迅速而监管制度滞后,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日本人多地少的现实条件,导致工厂无法远离人群,从而导致公害发生。再如我国陕西凤翔县“血铅事件”造成615名儿童血铅超标,当地环保部门一方面认定东岭冶炼公司是造成这次儿童血铅超标的主要成因,另一方面又认定东岭冶炼公司废水、废气、固水淬渣排放符合国家标准。⑤ 参见陈钢、刘彤:《凤翔“血铅事件”调查》,《瞭望》2009年第33期。 如此逻辑怪异的结论,正好说明了环境问题往往是技术性问题,企业虽然达标排放,但体现国家立法的污染排放标准只是从总体范围确定环境污染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并不能保证不发生人体健康损害。“传送带”模式反映了立法阶段的抽象性和提炼性,从而导致环境规范过程失去具体场域的考虑,环境法的强专业性则进一步使得民意代表机关的立法与社会现状之间发生隔阂。
公众呼吁下的环境立法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终点,而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因为法律规制的对象不是物而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有学者认为博弈论是所有社会科学的物理学,笔者赞同这一观点。③ 参见丁利:《制度激励、博弈均衡与社会正义》,《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法律主体间的相互影响及其隐性约束,很多时候即便是参与人自身都不一定能够意识得到,实践中长期互动形成的微妙平衡并不如其表面那样简单而能轻易被一纸立法打破。弗里德曼也认为,一个法律制度并非主要是人类精心设计出来的,而是依靠人类超乎寻常的识别模式识别出来的。④ 参见[美]大卫·D.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杨欣欣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引言第3页。 法律中最有效的内容都来自人们长期生活中形成的规则,“综观各个国家的民事、商事乃至刑事法律,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都是来源于习惯”。⑤ 桑本谦:《法治及其社会资源——兼评苏力“本土资源”说》,《现代法学》2006年第1期。 因此,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实施良好的主要还是经过实践长期演化出来并经过检验的法律规则。
其中,结直肠肿瘤MDT团队也是国内最早开展的。尤其是结直肠肿瘤MDT团队中“结直肠癌肝转移外科和综合治疗”的项目荣获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2011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该团队主办10届上海国际大肠癌高峰论坛,牵头制定该领域国际指南。
“传送带”模式下的新兴领域立法恰好主要是一个设计过程而不是识别过程,现有的立法传统主要来源于归纳法下的现象整理和对策考量,未必契合真实场景下环境执法的本质规律。此外,我国环境立法容易造成现实普遍性违法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中国作为法治后发的国家,在法律制度的移植和借鉴上有诸多优势,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有丰富成熟的法治资源可供参考。一般情况下,如果所借鉴制度资源是反复出现的基于人性结构的规则,则借鉴具有较大可用性,民法中的罗马法资源就是这种典型例子。如果某项法律制度本身内含了效率和正义等具体场景下的平衡,以及需要一系列基础性条件和制度群条件的,环境法律制度就是这种典型例子,这样的借鉴可能就会面临表面上的合理和实质场景下的不合理,从而无法得到实施。
“传送带”模式一方面使得未必合理的立法在执行中不可置疑,另一方面也隔离了立法对真实世界规则演绎的借鉴。在“传送带”模式的要求下,环保机构的行为必须遵循法定指令,而不是自己行使判断力。一系列如行政问责、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率的打分考核机制使得执法机构必须确保自身行为不能偏离立法的内容。然而法律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现实中并没有哪一种法律能够完美地被创设出来,且自动依法治原则就能完美地被实施,忽略立法的静态型和实际法律实施的动态性只会造成现实环境领域普遍性违法。普遍性违法存在本身便预示着立法与现实的错配,从规则演进的长周期来看,环境问题尚属于人类面临的“新”问题,环境规制面临远比传统领域更加紧张的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冲突,加上立法的周期限制和程序制约,以及立法易受有组织的利益群体俘获等问题,传送带下环境领域立法的有效规范供给不足成为常见的问题。
(二)“传送带”模式导致的环境执法僵化
如前所述,环境法的本质涉及多种正当利益之间的衡平,这种衡平很难通过“传送带”模式下的立法实现。在此以环境法历史上两个环境侵害方式非常相似但处理模式完全不同的案例来予以说明。第一个案例是“坎贝尔诉希曼案”,被告希曼拥有一家砖窑,砖窑烧制砖块时燃烧释放的酸性气体导致原告土地上的植被和树木死亡。原告坎贝尔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对被告下达禁止令和赔偿判决,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请求。⑥ Campbell v.Seaman,63 N.Y.at 568. 第二个案例是经典的“布默诉大西洋水泥公司案”,被告美国大西洋水泥制造公司1962年在阿尔伯马县科曼斯镇附近经营一间大型水泥厂。该公司虽已安装了现代化除尘设备,但仍排放了大量的粉尘,对附近地区的布默等7户居民的日常经营(布墨拥有一家小型的修车厂)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布默等人于1967年向法院起诉,申请法院颁布禁止令,并要求被告就工厂产生的烟雾、灰尘和振动造成的财产损害进行赔偿。法院最后并没有颁发禁止令,只是判定被告应当向原被告支付一笔永久性的高额损害赔偿,即比独立第三方愿意购买原告拥有的这片土地所支付的价款更高的额度,以使得被告获得原告土地上的地役权,形成一个类似于缓冲区的区域。⑦ Boomer v.Atlantic Cement Co,26 N.Y.2d 219,257 N.E.2d 870,309 N.Y.S.2d 312,1970 N.Y. 这两个案件都是空气污染案件,都是被告对原告构成了侵权妨害,但前者法院颁发了禁止令使得砖窑关闭,而后者法院并没有适用禁止令,水泥厂通过支付赔偿后得以继续经营。事实如此相似的案件处理结果不同,其隐藏的背景在于第一个案件中砖窑关闭以后可以比较容易在其他地方重新选址开工,而第二个案件中,大西洋水泥制造公司的水泥厂雇佣了约400名员工,其资产价值超过整个城镇总资产价值的一半,原告的损失与关闭水泥厂所致损失之比相差悬殊,法院在谨慎比较之后,选择了衡平处理。
理论的提出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如果现实已经发生本质性变化,理论也应当与时俱进。就环境法律领域而言,需要破除“传送带”模式,由立法中心主义向规制中心主义改变。规制中心主义,意味着法律规则主要在行政阶段产生并由行政执法机构灵活实施。也就是说,立法需要放弃中心和前端的决定性地位,相应地在国家权力配置方面也逐步由立法机关主导转向规制机构主导,“行政所扮演的不再仅仅是一个‘传送带’的角色,也不再是对立法机关的萧规曹随和亦步亦趋……现代行政法学已经将控制的节点由行政过程的‘下游’位移到‘上中游’,已经将政策、政治和法律都作为自己的考察变量”。① 朱新力、宋华琳:《现代行政法学的建构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法律科学》2005年第5期。
即便以现在的观念来检视这两个案件,法院的处理虽貌似同案不同判,但究其细节还是相对具有合理性的。很难想象立法可以根据具体案件量身打造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规定。比如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0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这便是统一的禁止性立法规定,没有区分也不可能区分经营单位规模、所在地区的产业结构等具体的适用情形,这就导致了实质上面临多重正当利益冲突下的环境执法困难。尽管地方政府有法定的规章制定权,但其受限于法律的法定框架在先以及立法资源不足等问题,立法的限制会以传导方式使执法僵化,这种僵化继而会导致基层环境执法因缺乏地方支持而无法实施,“执法不严根植于国家法规与当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法律缺乏地方合法性,当地行为者拒绝执法”。⑧ Rooij B V.,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Law:Regular Enforcement and Political Campaigns,Development&Change,Vol.37,Issue 1(2010). 如果国家环保政策趋严,则会反过来出现不分具体情况的“严打”,比如2018年4月江苏省省级环保督察开始后,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政府发出告知书,要求当地化工园区内所有企业一律停产整治。⑨ 《新一轮环保风暴指向化工园区!撤销、关停、搬迁已经迫在眉睫!》,http://www.sohu.com/a/231037534_276522,2019年2月5日访问。 实践中种种执法乱相,或多或少与“传送带”上的立法受到立法固有的限制而无法反映利益相关方的合理诉求有关。
这几年,广州市以“好教育进行时”为抓手,推动各区基础教育提升质量、打造特色的做法,推动了广州杏坛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可谓“无边风景一时新”,此“一时”就是指“好教育进行时”,此举有以下几点特别值得点赞。
产业扶贫工作的扎实推进,需要结合地域产业扶贫实际,编制完善的发展规划方案,尤其是在贫困户受益机制上,借助于建档立卡,精细到户、精准到人,明确带动主体、实现帮扶资源的有效整合。地方要围绕精准扶贫实际,明确主要任务,开展规划评估,特别是协同各个产业部门,细化落实产业扶贫各项指标,提高透明度。
不似传统行政规制对象主要是伦理价值上比较容易判定为不正当利益型的行为,譬如行为人交通违章会影响自身和他人安全,再如行为人在食品中添加有害物质会导致食用者身体受损。环境危害行为虽然同样会造成环境受损并进一步产生人身和财产损害,表面上看也是负面的行为,但如前所述,其本质上是人类生产发展中的附随性行为,如果要求不产生任何环境危害,则主行为(生产发展行为)也需要被禁止。因此,环境领域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其是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如企业提供工作岗位并生产社会所需产品和周边居民要求良好生活环境的需求都是正当利益。既然环境法领域的利益冲突属于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其便不能通过简单禁止其中之一的方法来解决,而只能进行不同情况下的平衡取舍,“正当利益优位性选择的问题,表现形式是基于可行条件和问题的紧迫性的时空优先顺序的安排,并非对抗性的淘汰式选择,应当奉行‘统筹’、‘兼顾’和‘双赢’的衡平理念”。③ 李启家:《环境法领域利益冲突的识别与衡平》,《法学评论》2015年第6期。 另外,对企业的惩罚经常会产生意外牵连的效果,即“当公司感冒时,别人会打喷嚏”,在竞争不完全的世界中,惩罚的成本很可能最终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④ See Coffee,John C."No Soul to Damn:No Body to Kick":An Unscandalized Inquiry into the Problem of Corporate Punishment,Michigan Law Review,Vol.79,Issue 3(1981). 如果环境法律的制度选择在赋权与禁止之间并没有一定的规则,则“传送带”链条会失灵,因为具体场景下的衡平对环境法规范体系提出了极高的制度灵活性要求,简单禁止的模式能够通过立法制定并经执法传输,而不同情景下的衡平则难以通过“传送带”模式得以实现。譬如,水一直是最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之一,但因其一直处于流动状态,所以自然界中水的产权界定和分配一直是一个难题。“美国东部和西部各州均实施用水许可制度,但是东部和西部对何为合理使用的理解完全不同。美国东部各州的合理使用规则主要基于河岸所有权,即有权使用河水的人是靠近河道的土地所有人。美国西部各州的合理使用规则基于先占权之上,即用水优先权遵循先占原则——有权使用河水的人是那些首先将河水用来做有益用途的人。”⑤ 王慧:《水权交易的理论重塑与规则重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之所以形成不同的权利规则,是因为美国东部的水资源相对丰富,而西部气候干旱,美国历史上实行“河岸权”的州基本上都适用法院“个案判断”理论来灵活确定合理用水的标准。⑥ 参见王小军:《美国沿岸权制度研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4期;上注,王慧文。 这一例子恰好说明了环境法因需要进行利益衡平,故其规则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适,而立法囿于稳定性的需要,很难通过“传送带”体系为适应性执法提供资源。
(三)“传送带”模式导致环境立法内容失去执法场域性
为上述环境法的特性与环境法律“传送带”的模式局限,使得环境立法对环境执法的有效规范供给不足。中国政府一直在环境立法及环境机构设置上践行着相当积极的角色,从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伊始的环境法规初创,至今日之各项环境执法事务,无不打上政府正向努力之烙印。⑩ 参见郑少华、王慧:《中国环境法治四十年:法律文本、法律实施与未来走向》,《法学》2018年第11期。 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中国自上而下官僚科层机构的目标责任体系,已取代了环境法律的正式运作,或者是使得法律的实施成了第二位的目标。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中国“五年计划”中的约束性指标是中央核心关注事项,法律主要起到辅助性工具的作用,当法律规定与这些优位目标一致时可以得到实施,而当与目标不一致时,法律就被搁置一边。① See Wang A.The Search for Sustainable Legitimacy:Environmental Law and Bureaucracy in China,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Vol.37,Issue 2(2013). 我国早期GDP优先的目标导向和与之相随的环境执法软弱无力,以及近年来党政体系对生态文明的高度重视,进而涌现的一大批环境约谈、环境督察等偏运动式的环境执法,② 参见葛察忠、翁智雄、李红祥等:《环保督政约谈机制分析:以安阳市为例》,《中国环境管理》2015年第4期;郝亮、黄宝荣、苏利阳:《环保约谈对政策执行“中梗阻”的疏通机制研究:以临沂市为例》,《中国环境管理》2017年第1期。 更是这种观点的脚注。然而该“政府目标机制有用,环境法律无效”的论点存在自我矛盾之处,即在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已将主要环境生态指标纳入,并明确将其作为有约束力的指标的情况下,环境治理仍陷困局,可见问题的本质未必在于行政管理取代了法律实施。该论点对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作了机械性的分割,没有看到两者内在的广泛联系。我国环境法律实施不佳的深层次原因,更可能是环境立法未能向环境执法提供足够有效的法律制度供给。
要实现规制中心主义,需要立法机构给予执法机关充分的授权。譬如美国《行政程序法》早已规定了规制协商(regulatory negotiation)作为联邦行政机构规则制定程序的替代性方案,以使得法律规定更为切实有效,规制协商在环境规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适用。规制协商是一个“包括了规制机构、受规制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环保团体、消费者团体、州政府和当地州以下政府)在内的非正式协商程序,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们在拟定的规则上取得共识,随后拟定的规则接受传统的规制制定通知和评议程序”。⑤ [美]理查德·斯图尔特:《环境规制的新时代》,载王慧编译:《美国环境法的改革:规制效率与有效执行》,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4~55页。 又如法国环境立法“突破了以国家议会作为主要法律制定主体的约束”,并通过制定《综合环境政策与协商法》实现了“从集权式立法到协商型立法的转变”。⑥ 王树义、周迪:《论法国环境立法模式的新发展——以法国《综合环境政策与协商法》的制定为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 从欧盟层面上看,尽管“里斯本条约”要求加强欧盟议会的立法权,而现实却是广泛存在的授权模式,这些“新的授权模式的合法性不太可能通过‘传送带’理论得到保证,欧盟的主要立法都将民主合法性转移给行政机构和其他受托的规则制定者”。⑦ Gestel R V.Primacy of the European Legislature?Delegated Rule-Making and the Decline of the“Transmission Belt”Theory.Theory&Practice of Legislation,Vol.2,Issue 1(2014). 从环境立法中心主义走向规制中心主义在全球都已有实践,行政机构处于对压力反应过度的立法机关和反应滞后的法院这两端之间,只要明确了行政机构规制过程的透明度和参与性问题,基于行政机构的行动能力及其专业性,规制中心主义的行政国家才能实现体现包容性和适应性的规则生成目标。
设备运行自动化和无人值守机房是现代化工业生产的重要发展方向,而上机位监控软件是压风机组在线监控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实现对现场运行设备的远程集中监测与控制。上机位软件利用WINCC组态软件编程实现,其集成性、可编程性较好。通过调用专用模块,可方便实现所编制软件与PLC控制层的通信。上机位软件的主要功能包括:监控画面显示、运行参数控制、历史数据查询与汇总等,具体如下:
四、“传送带”模式阻滞效应之化解
如前所述,“传送带”模式下立法和执法链接不畅,可能会造成环境执法的阻滞效应,为此,需要考虑应对的解决路径。首要考虑的是改变传送带的立法模式,同时要改进执法策略,由于立法和执法改进未必能一蹴而就,还需要考虑发挥现有的机制提供其他缓和性措施。
(一)向规制中心主义的环境立法转型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主要国家,行政分支的作用都呈现强化趋势,政府在国家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我国在环境、工商和金融等领域设立了一系列社会性和经济性规制机构,“政府规制已经成为与宏观调控并列的一项重要政府职能。这意味着,我国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所有者政府’,但是没有转向‘守夜人’政府,而是走向了‘规制政府’”。⑧ 沈宏亮:《中国规制政府的崛起:一个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过程》,《经济学家》2011年第4期。 美国1929年有18个机构负责经济监管,1960年有49个,到了1976年就已增加到83个,随着监管机构的增长,政府对私人活动的管制程度和管制范围都在增加,把行政机关看成仅是立法指令之执行者的行政法理论引起了质疑。⑨ DeLong,James V.,Informal Rulemak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Law and Policy,Virginia Law Review,Vol.65,Issue 2(1979). 对此,美国的杰克逊大法官认为:“行政机构的崛起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法律趋势,其已经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第四个分支,破坏了原有的三分性法律理论;行政机构的活动被称为准立法、准执行或者准司法,‘准’说明了所有公认的分类都已破裂,这种说法不过是一个掩护而已,床铺上已经混乱无序,而我们只不过想用一个床单来掩盖使我们感到混乱和困惑的事实。”⑩ FTC v.Ruberoid Co.,343 U.S.470,487-88(1952)(Jackson,J.,dissenting). 虽然我国国家权力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的,“传送带”模式所强调的行政合法律性、可控性与我国权力结构在理论上具有高度契合性,但事实上我国长期大政府的治理传统,迭加环境法自身的特点,环境法领域立法权的不在场性和行政权的扩张性相对于外国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
熟练掌握几种常见离散型和连续型分布的相关函数命令,包括对应分布的随机数产生、分布函数、密度函数、分位数函数等命令;熟练掌握常用的特征数字的函数命令,例如均值、方差、中位数、协方差、相关系数、变异系数、峰度系数、偏度系数等;掌握常见的作图方法,包括绘制分布函数、密度函数、直方图等;能编写简单的程序来验证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能设计简单的蒙特卡洛试验,来估计感兴趣的数值。
“传送带”模式中的政府虽然可能是合法的,但其在现代社会是根本就不存在的。② See Bressman,L.S.,Beyond Accountability:Arbitrariness and Legitimacy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78,Issue 2(2003). 认为立法机关就能广泛代表民意的观点也未必正确,立法决策同样会被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俘获,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1977年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燃煤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是当时美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美国东部的煤炭含硫量很高,质量更好的低硫煤大都产自美国西部,东部煤炭生产企业和环境关注者结成联盟,其通过努力,在1977年美国《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中加入一条规定,要求全国煤炭生产企业安装硫煤洗涤器,相对于使用低硫煤,这是成本高很多的二氧化硫减排方法。该规定以增加电力消费者和西部煤炭生产企业额外支出为代价不当地保护了东部高硫煤的市场。③ See Ackerman,Bruce A.;Hassler,William T.,Beyond the New Deal:Coal and the Clean Air Act,Yale Law Journal,Vol.89,Issue 8(1980). 美国行政法著名学者斯图尔特也指出,超然意义上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公共利益最后可以拆分成为分散的个人和团体利益,立法过程不过是这些利益冲突之下形成的妥协,与之类比,“如果行政机关为所有受行政决定影响之利益提供了论坛,就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可以为所有人普遍接受的妥协,因此也就是对立法过程的一种复制。充分考虑所有受影响的利益后所作出的行政决定,就在微观意义上基于和立法一样的原则而获得了合法性。因此制定法无法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变得无足轻重了”。④ [美]理查德·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7~68页。 可见,环境立法中心主义走向规制中心主义本质上不存在合法性障碍。
因此,“传送带”模式实际是不完整的。行政执法机构会常规性地雇用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技术咨询,同时,该机构经常必须解决各种实际执法问题,所以积累了与法律实施具体情况有关的大量的经验,能够提供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所需的专业知识,而立法过程则往往是不同的利益团体进行争论和妥协,其在意的是赢得政策斗争,而不是实现技术上最为合理的方案。⑥ See McGarity,Thomas O.,Administrative Law as Blood Sport:Policy Erosion in a Highly Partisan Age,Duke Law Journal,Vol.61,Issue 8(2012). 有学者也在研究美国行政机构长期的执法历程后指出,经验证明了只有参与行业日常监管的机构,才能获得立法所需要解决问题的真实信息和专业认知,隔离立法和执法,并限制执法机构自由裁量权的发挥,只会妨碍良好政府的形成,因此特定监管领域的立法需要将行政执法部门纳入其中。行政执法机构的专业知识,能够防止立法机关制定不合理的或者过度激进的规则。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变得普遍的行政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已经证明了执法机关相对于立法机关的信息和技术能力优势,行政执法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强化,以及行政过程中的技术评估和法律实施选择,并没有出现“传送带”理论所担心的对立法机关立法主旨的不当偏离。⑦ 参见前注⑧,Seidenfeld文。 从环境法的专业技术性角度看,是否构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受到我国天然环境本底值、人口集聚度等各类因素的影响,不考虑具体实施条件会导致立法与现实冲突。环境执法监管属于社会型规制领域,其镶嵌于复杂动态约束的社会场域中,忽略需求层次、地区差异的立法和统一的高强度威慑型环境执法,可能形成双重错配,会进一步加大环境法律的实施难度。
(二)规制中心主义下的环境执法样态多样化
现代公共治理的语境下,行政行为不仅具有单方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而且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协商性和互动性的特征。⑧ 参见姜明安:《新时代中国行政法学的转型与使命》,《财经法学》2019年第1期。 环境法律“传送带”模式的松绑,可以为规制中心主义下的灵活性环境执法提供条件,实现从威慑型的命令控制式执法向多元治理型执法转型。如前所述,“传送带”下的立法因易受压力影响,立法机关难以获得更好解决问题的信息,加之受立法形式和过程的限制,其向执法机构的传导必然是一个单向度精简化以命令控制为内容的过程,而且为了保证特定监管领域的执法效果,立法往往选择加大惩罚力度的威慑模式。其问题是基于威慑理论衍生出来的令行禁止可能仅适用于简单型管制领域,严惩的立法结构会在复杂场景下失效。各国普遍出现了环境强制型监管向协商型规制转变,其核心原因还是在于环境问题是需要高密度监管兼有多重正当利益冲突在内的复杂性问题。与此同时,以环境风险为典型的风险社会使得事前规则制定失去了标准化和确定化的优势,现代环境问题还出现了主体多样化和污染分散化的特征,如农业面源污染和汽车尾气污染等,这些特点都使得法律传送带模式愈加不合理,并呼唤更加灵活的执法模式。
规制中心主义下的环境执法,因规制规则能根据执法机构面临的具体问题来制定,能够更加灵活和更有效解决问题,同时,因行政机构不是单中心而是多层级多区域的存在,从而可以围绕地方性问题为核心形成多中心治理结构。譬如美国联邦环保署在布朗纳任期下进行了多项改革,通过设立与被监管对象进行合作的管理计划,从而以不易被抵制的方式实现了对污染企业的设施监管;美国联邦环保署还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柔性执法的环境补充安排,只要执法对象主动支持特定的环保项目,或者能够超过法律规定减少其工厂的有害排放,就可以减少对其的罚金。⑨ 参见前注⑨,理查德书,第169页。 环境执法机构还灵活地使用经济激励制度,通过可交易的排污许可和环境税等制度,使得执法对象可以相应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法守法。⑩ See Stewart,R.Economic Incentiv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in R.Revesz,P.Sands,and R.Stewart,Environmental Law:The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ambridge:CUP(2000),pp.171~244. 此外,实践中还发展出更为灵活的包含利害关系人在内的互动网络管制方法(Network Regulatory Methods),以解决命令型管制的失灵。例如美国联邦环保署通过有毒物质排放清单计划,要求公开排放有毒空气污染物的信息,信息公开对企业的非正式压力致使有毒物质的排放急剧减少。① See Stewart,Richard B.,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78,Issue 2(2003). 不再受制于立法的威慑加码模式,行政机关可以选择更加有效的公私合作方式来进行执法,并通过试点等方法,探索和识别更有效的执法方式。
当然,规制中心主义下行政执法固然获得了灵活性,但也存在滥用的可能。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任意性,美国在行政机构放松管制的同时,通过司法审查保障利益相关人能进入行政规制商讨、公开和听证类协商程序。② Garland,Merrick B.,Deregulation and Judicial Review,Harvard Law Review,Vol.98,Issue 3(1985). 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等制度也很好地促进了行政监管的可靠性。③ 参见前注①,Stewart文。 还有学者提出基于信托理论中的委托、剩余控制和信托义务这三重框架来塑造新型行政法,行政机构作为信托受托人需要受到行政程序的约束,但不应过度以妨碍其履行信托责任。④ See Criddle,Evan J.,Fiduciary Found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Law,UCLA Law Review,Vol.54,Issue 1(2006);Mantel,Jessica,Procedural Safeguards for Agency Guidance:A Source of Legitimacy for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Vol.61,Issue 2(2009).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改革的试验,通过尊重人民参与管理的权利,也出现了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新兴的“参与模式”过渡。⑤ See Xixin,Wang;Yongle,Zhang,The Rise of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n China:Empirical Models,Theoretical Framework,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sian Law Review,Vol.13,Issue 1(2018). 更加理想的规制结构是所有合法利益都可以获得代表的代理结构。也是要求行政保持对利益集团和立法表达偏好的相对中立的代理结构,在这个概念下,行政机构不是偏好的发动方而是偏好的调解员。在环境治理的背景下,环保机构的使命是超越于环境保护者之上的风险经纪人,在规则制定的范围内管理和分散环境风险。⑥ 参见前注②,Gauna文。
(三)规制中心主义下的其他缓和性措施
立法和执法过程的改进是一个渐进缓慢型的过程,在“传送带”体系变革之前,有必要通过现有的制度体系发起缓和性措施,改进环境法律体系的实施。在现有的诸多制度着力点里,司法制度和社会自我规制制度客观上起到了改善环境法律“传送带”模式弊端的效果。“以法律防止损害无非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事前的警示限制,使人不从事致损行为,二是通过事后的惩处,使人们此后不再从事有害行为。与此相应,在法律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种防止损害发生的规则:事前规制规则与事后责任规则。”⑦ 刘水林:《风险社会大规模损害责任法的范式重构——从侵权赔偿到成本分担》,《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 在行政国家出现之前,司法决断早已存在,以期定分止争,维持秩序。行政国家出现之后,因行政执法效率更高且有事前预防性效用,因此环境领域大量问题的解决转为主要依赖事前预防的行政规制模式。然而事前规制模式和事后责任模式两者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无论法律制定得多么周详,……繁复庞杂的社会事实不可能与之天然吻合,在立法过程中被立法者浑然不觉的法律自身的漏洞……迟早会在司法过程——这个规则与事实的摩擦地带——暴露出来。”⑧ 桑本谦:《法律解释的困境》,《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适用事后责任规则的私人侵权诉讼,一方面可以视为私人借用法院这一公权机制补充执法;另一方面,行政执法是更直接的二元对立结构,而司法解决则更加具有过程性,司法过程中法官作为第三方可以仔细衡量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困境,这无疑也使得“传送带”模式下成文法的漏洞能够在司法过程中得到完善和修补。
针对私人环境诉讼易出现缺乏起诉动力的问题,由专业环保团体发起环境公益诉讼是常见的司法补足机制。⑨ Rossi,Jim,Participation Run Amok:The Costs of Mass Participation for Deliberative Agency Decisionmaking,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92,Issue 1,(1997). 我国立法已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不仅规定了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还于2017年通过修订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和行政两类环境公益诉讼。至“2018年9月,在已经受理的全部2041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为1836件,达到了受理案件总数的90%”。⑩ 江必新:《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发展及制度完善》,《法律适用》2019年第1期。 检察机关作为政府体系的内部成员,素来具有一定独立性,也不直接涉及政府经济管理事务,是比较好的规制参与方。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介入往往是行政执法出现障碍时比较好的替代性制度选择。
缓和性措施的另一大类,是发动社会自我规制之力量。“面对环境保护专业知识的复杂性和涉及领域的多元性,管制模式不再拘泥于国家的高权或中心地位,而是采取所谓的分散的脉络管制……其出发点仍是国家与其他主体对等之多中心结构。”① 张桐锐:《“合作国家”》,载翁岳生教授祝寿论文编辑委员会编:《当代公法新论(中)——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元照出版公司(台北)2002年版,第578页,转引自谭冰霖:《环境规制的反身法路向》,《中外法学》2016第6期。 社会自我规制又可以分为作为行政规制对象的企业之自我规制以及社会团体和公众之规制合作这两大类。时至今日,环境问题产生之初的具体场景与今天已经大不相同。“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企业在政府与公众的双重压力下,也开始从仅追求营利的法人逐渐演变成承担社会责任的法人。”② 郑少华:《论企业环境监督员的法律地位》,《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0期。 企业对环境利益的关注能够营造企业的正面声誉,预防环境危害的产生也能避免企业陷入受害人民事索赔、纯生态损害赔偿和行政处罚,与企业的长期经营具有正向相关的意义,这也构成了企业自我环境规制的动因和基础。绿色供应链、生态标签认证等管理标准便是较常见的基于管理型的企业自我规制。此外,企业环境监督员等新出现的制度也反映了企业自我规制之要求,企业环境监督员虽然受雇于企业,但其不进行业务性履职,主要负责监督内控企业生产,并向外部政府部门和公众进行环境报告。③ 参见上注,郑少华文。 该制度是企业自发进行自我规制的典型。
结合《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第八条及《人民警察法》第九条可以看出,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于继续盘问制度的适用标准是相对人有违法犯罪嫌疑,且当场不能确定其身份或排除嫌疑的。这样的标准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需要进一步进行探讨。如果采用主观标准,即存在赋予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自由裁量权过大,有可能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出现违反比例原则的情形;如果采用客观标准,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不可能就所有的客观情形作出周延全面的规定,有可能会导致执法的机械化以及放纵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后果。
社会团体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动参与也能极大改善环境规制。社会团体在现代社会分工细化与通信技术条件的支撑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个是专业性带来的强能力特征,另外一个是共同爱好、志愿带来的高凝聚力、行动力特征。这两个特征在环境法领域尤为重要,因环境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的一个重要区分点在于环境问题具有高度科学技术性的特征,这使得即便是我国经过激烈竞争选拔出的公务人员组成的现代政府,也未必有进行特定类型执法的足够资源。
数据统计应用SPSS21.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he Blocking Effect of"Transmission Belt"Mode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Its Resolution
Hu Yuan
Abstract: Environmental law and its implementation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like high-density of preexisting control,involving balance among multiple legitimate interests and high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and technicality.The traditional legal Transmission Belt Model regards the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agency as an appendage of the legislature,thus resulting in blocking effects such as the legislation's insufficient supply of effective rules on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the rigid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caused by the restriction on the content transmitted by legal rules,and the unenforceability of legal content due to isolation from the specific scenario.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poor link between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and limited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under the transmission belt mode,the model of environmental legal rules needs to be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legislative centralism to regulatory centralism,that is to say,the power on environmental affairs should b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allocation mode that the legislature plays a leading role to that the regulatory body plays a leading role.Environmental legal rules should be mainly generat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ge and implemented by the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a more effective way,so as to achieve a more flexible and adaptive rules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enforcement mechanism.Meanwhile,palliative measures should be provide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existing judicial system and social self-regulation forc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Law;Transmission Belt Model;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 DF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512(2019)05-0133-12
作者简介: 胡苑,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重大)“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重大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VSJ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姚 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