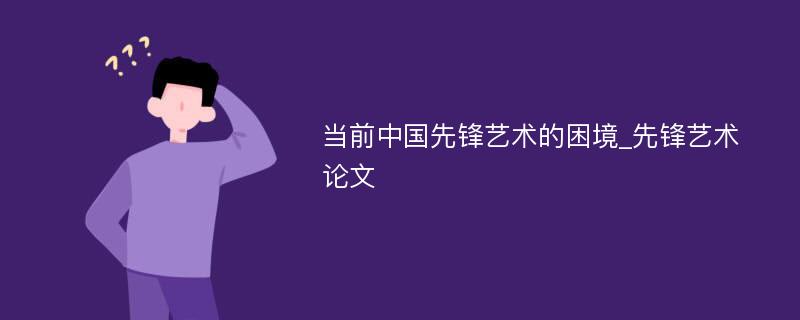
中国先锋艺术的当下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中国论文,困境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是大众文化全面占领中国的时代,是商品、消费、休闲等话语充斥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人们期待已久的告别苦难的“幸福”世界,向来以批判精神标榜于世的先锋艺术却陷入了一片温柔的泥沼……而面对西方的咄咄逼人的“后殖民”话语,中国的先锋艺术家们有逃离与反叛的希望吗?请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先生剖析——
从西到中的学术转向
新锐思想家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言人,他们的理论及思想最深层地反映着这个时代的脉动。毫无疑问,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术的确发生了很大的转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80年代可以称为“激进的西化路数”的话,那么90年代可以称为“保守的反西化路数”。80年代一部《河殇》以其否定黄色文明即黄河文明而要走向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为总体思路,引起了剧烈的文化论战。而90年代,150集的电视文化片《中华文明之光》则完全相反,旨在发现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灿烂光彩。同时国学热也已被众多学者认同,从国学丛书、大师丛书、民国丛书等多种丛书的出版中,都可看出国学在90年代拥有相当大的市场。而前不久出版的一本被商业炒作得很热的书《中国可以说不》,以及所谓“说不”系列,其中所表现的反西化、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路清晰可见。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这里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后殖民主义等一些语境问题。
在哲学思想方面,李泽厚和甘阳是从西学到反西学的典型的代表。在文化领域方面,80年代的西学路数和90年代中学路数可以发生在一个或几个批评家身上,如有的人昨天还在强调现代性、现代文化乃至后现代文化、后殖民文化,转眼又宣称“现代性”在中国应变成为“中华性”,从而走向反西化、反文化、反知识分子,而强调大众传媒、文化研究、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市民文化等等。昨天可能瞩目精英文化和现代理性,而明天却又走向世俗文化、市井文化和非理性。
当然这些学者的转向是个体的选择,但如果成为了一种现象之后,则具有了超越个体的特殊意义。可以认为,他们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知识谱系确实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是个体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世俗冲动取代了精神冲动,当然也有现实问题取代了抽象思辩,关注发展进程取代了空中楼阁的形而上学。在这种思想界、文化界的大转型面前,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中国泛化的情况下,如今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日益与中国文化中世俗化的东西互渗而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于是文学界的调侃文学、后新潮小说已成为消解中心话语以后的新中心;美术界政治波普、实验艺术、行为艺术方兴未艾;音乐界摇滚的强劲节奏正在以本能瓦解旋律的精神性;影视文化在广告传媒和文化经纪人的操纵下日益以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取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于是在倡导多元价值、多元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大众在多元与主体之间,将个体差异性推至极端甚至以个人的绝对差异性为由,割裂个人与他人的同一性,使当代中国实验艺术日益成为与他人的不沟通系统。
面对种种问题,先锋的眼光是否只看到了未来的目标,而丧失了“过程化”的生命和艺术的意义?可以说今日的先锋比任何一个后卫都要困惑,今日的先锋比任何一个非先锋所感受到的矛盾心理和冲突状态都多得多。因此,先锋的困惑是中国文艺的困惑。
诗人的死在诗人自己的眼中也许是崇高而伟大的,但在游戏者眼中却是无意义的,人们在悼念诗人的同时也抛弃了诗。
诗意的匮乏
90年代纯诗的贫困已经持续了七个年头,在诗人海子、戈麦相继自杀之后,诗人自杀成为90年代诗坛的事件,成为世纪末文化的一个沉重的寓言。在短短几年的“弹指一挥间”,诗人被“边缘化”了。创造的生命激情转化为“零度写作”,思想的魅力变成无深度的唠叨,深切的价值关怀置换成“金币写作”的策略(“稻粱谋”);精神品质成为超出当代人生存需要的奢侈品甚至无用品;语言浮肿,思想干瘪,诗思消逝,诗性世界沦为“散文”世界。也许,海子在90年代的门坎前自杀,正是他以“临终的慧眼”看到世纪末诗歌将在商业消费和技术理性的压榨下根叶飘零,濒于灭绝?
然而,这个世界的散文却火爆起来。
首先是新艺术散文家,如刘烨元、周佩红、黑孩等的出现。而后余秋雨、张承志、史铁生的文化散文成为文化界关注的中心。女性散文的作家群体包括张洁、唐敏、王英琦、斯妤、张抗抗、叶梦等,以其个性化、女性化、独白化的散文语言,使散文日益走向个人化。“新生代散文”则标明了散文新的发展取向,代表人物有曹明华、胡晓梦、老愚、骆爽、于君、冯秋子等。诗意失落于散文之中,然而散文真的能够符合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吗?真的能够成为这个文化匮乏时代的精英吗?
也许90年代的小说是最领风骚的,但它也是最为寂寞的。80年代长篇小说的年产量不超过100部,可到了1993年,就已经超过了300部,1994年接近400部,1995年为440部,1996年据说已达640部,然而处于生产“旺季”的小说却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一方面是由于小说的粗制滥造和过分的欲望化使读者感到其中精神的贫瘠,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快的生活节奏让人很难再读完厚本的虚构小说,此外,小说在形式上愈来愈玩“叙事魔方”而远离生活本身,因此,尽管小说出版年复一年日益增多,但读者却年复一年日益减少。虽然《大家》等刊物推出联网作家,甚至以重奖招徕读者,仍不能恢复小说在80年代那种一部风行而天下争阅的盛况,于是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已不可能再领昔日的风骚了。
“革命”的摇滚在甜腻腻的流行主义中逐渐丧失了它的立场。
不再先锋的摇滚乐
摇滚在90年代是文化先锋的代表。崔健是中国摇滚的第一代,他的音乐中包含着一种“革命的声音”。此后的“黑豹”、“眼镜蛇”、“唐朝”、“呼吸”乐队等,也将在中国摇滚音乐史上留下自己的一章。另有“1989乐队”、“指南针乐队”等,也曾在中国摇滚乐章中热闹过一阵子。然而,由于中国摇滚没有重视自己的革命性,反而过多地重视诸如出场费和媚俗的一面,加之很多歌手衣着古怪、言行粗鲁、吸烟酗酒,有的甚至性欲混乱,暴力吸毒,所以摇滚从重金属的精神革命到开始玩弄精神,再到彻底走向欲望化逐渐疲惫,在它惊天动地的喊叫声中,日益平面化地消失在它的千万歌迷之中。于是,出现了“黑鸭子歌唱组”、“四兄弟歌唱组”、“两兄弟歌唱组”等甜腻腻的流行歌曲。逐渐取代了摇滚的革命性。同时,在90年代中期,古典交响终于走出困境赢来了自己的听众。北京音乐厅场场爆满票价居高不下的演出和国外大型乐团的轮番轰炸可以见其一斑。各地的民乐热和民乐学习热也表明,在音乐上,大众的趣味正在日见分化,无论是古典的、西方的,还是古典中国的、现代西方的、当代或者后现代西方的,均可以获得自己的听众和自己的地盘。
但我们仍应注意,音乐的电脑化倾向、MIDI倾向乃至后现代无声音乐倾向的出现,使音乐越发走向形式化,丧失了批判功能,仅仅维持了一种争夺话语的功能。在世纪末,呼唤音乐的清洁化、纯洁化、精神性变得尤其可贵,其中民乐的正规化、音乐语言的纯净化将成为世纪末音乐必须关注的问题。
艺术家从热衷油画到热衷行为艺术,可以看到一种试验性的意向,一种玩世不恭中掺杂着愤世嫉俗,一种标新立异中的无可奈何。
美术的尴尬
美术在80年代一次次的先锋突围曾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然而90年代涌起的商品大潮将中国前卫艺术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即追求永恒之物之同时又必须把握当下机遇。有的人成功地进行了“话语转型”,终于登上了经济快车,有人还成功地为海外画商所“收编”,过起了锦衣玉食的日子。然而,仍有一批真正的前卫艺术家,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中将理想之火照亮被金币薰黄的大地。
这几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西风东渐”,美术界新生代或实验派们,确乎以东方式的智慧重组了“后”话语。无论是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殿堂的“后现代性”挪用,还是90年代艺术家的群体分化,无论是由《析世鉴》的高蹈还是“猪交配”的东西方文化冲突隐喻的粗陋(徐冰),无论是吕胜中具有傩文化基因的剪纸小红人,还是马六明、张洹等人的自虐“行为艺术”,都表征出当代中国美术所遭遇到的全面精神困惑和存在困境。后现代式的“挪用”、“拼接”、“平面”,在中国90年代美术的观念上、实践上、价值上造成了“实验化”和“反美学化”品质。于是,运用新技法、新材料、新方式表现个人话语和私人思想,展示自身“肉体知觉化、思想化”的存在境遇,强调“解构”策略、政治“POP”和艺术“游戏”,使当代艺坛在呈现个性化、边缘化势态的同时,也出现了后现代“耗尽”式的虚无感,一种玩世不恭中的深切的愤世嫉俗、一种标新(西方)立异(东方)中的“后殖民式”的无可奈何。我们必须提问:中国美术当代精神何在并何往?
当然,还有高兟、高强兄弟用装置艺术来强调这个苦难的世纪和预示人类希望的作品。高氏兄弟的《临界大十字架》系列“装置艺术”中,使十字架的意义由“本色”进入新的隐喻,《大十字架》是创作者对十字架进行的一次解构、整合与重构的实验。它已超出宗教的语境,切入现实存在与当代文化的语境,是对现代艺术堕落倾向的不满、反抗与超越,是从文化理想主义的高度对人类生存的异化状况作批判性的考察。“世纪末生活中的受难意识使我们产生了一种泛十字架倾向。生活、历史、艺术、理性、道德、权力、金钱、欲望、理想等等,都使我们想到十字架,仿佛我们自己的身体也被钉在一个无形的大十字架上”(高氏兄弟语)。不难看出,创作者在原初本色的物质十字架上,“装置”了圣经、地球仪、时钟,手枪、镀金数码、有机镜片、小灯泡、太极图等新的现成品时,在观念上也对“十字架”的意义进行了重组。这种物质的赘物附加增加了新的语境和空间序列。并以红色基调改造了黑色十字架的本体象征(死亡)模式,而成为警示(红灯闪烁)、生命(红色)、耻辱(红字)、拯救(红十字)的意义迭加,而又以倾倒的十字架在观念上突破了人与神的和好话语而再一轮强调了人将自己重新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世纪灾难的降临。
于是,十字架的意义经“装置”以后,呈现后退势态,由当代的希望——神人和解的象征后退为苦难的死亡装置,由这种装置所产生的人的缺席、神的缺席、在场的缺席,暗示的绝望、人神失和、苦难已成为“世界之夜”中的“人类的忧虑”。爱与死的十字架,又一次显现出“牺牲”隐喻性,在泛十字架情结中重新书写世纪末人类的命运,并在红色和各种“赘物”中指问或暗示了“真”。
后殖民话语使任何文化阐释都充盈着一种“阐释的焦虑”。然而,当我们东方人眼中出现的西方核心符码——“十字架”时,会怎样呢?是按照东方的语码重组呢?是将这西方符码移植为东方景观呢,还是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所指位移——泛化的能指呢?是以对抗的姿态使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东方对西方的误读和重组)成为“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呢,还是超越东西方“主义”而成为“人缺席”的时代审判和人类拯救的人类主义?这些问题至为复杂而又相当关键。
在我看来,近十几年的中国美术,不夸张地说成为了西方风格、形式、思潮、流派的东方实验地。中国现代艺术在相当程度上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翻版和摹仿。这一处境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将在国际艺坛永远处于挪用西方话语而最终难以超越的地位。这一“文化身份”和“价值认同”的夹缝,使一种无可奈何的次等文化情绪蔓延周遭,并通过艺术品转嫁给了观众和社会,使文化艺术中的后殖民问题进入人们痛苦思考的视域。
在艺术家强调游戏、苦难、希望、平面等多元价值观时,1996年出现了“周末艺术拍卖会”,于是艺术与经济,艺术与金钱的关系愈加紧密。拍卖市场的建立使中国艺术真正走向了市场,而市场也日益左右着中国的艺术家的创作,艺术和金钱就这样在90年代完美地结合起来。当然,像张大千、傅抱石的作品拍出了千万元以上的好价钱,这更使当代新潮或先锋艺术家怦然心动。但我们仍然要追问,在金钱与艺术之间,中国先锋艺术向何处去?
后现代语言转向导致文学批评日益脱离纯文学或纯审美,而走向价值平面的“后乌托邦”文学和意义滑动、错位的困境。
批评的语境
9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殖民主义思潮,无疑对这个曾经称为世界中心而今处于边缘的文化中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后现代主义的边缘化、零散化、非主体化与大众化色彩使精英文化意识,一元话语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遭到扬弃,而出现了多元文化共生的景观。后殖民主义使中国学者进一步意识到东方文化在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的同时,也成为西方文化被看的“他者”,并成为文化霸权当中的受支配话语。因此,如何在后现代与后殖民语境中为中国文化进行定位和为世纪末的中国文化争得自己的话语权力,成为了当今先锋批评家绕不开的问题。
就中国而言,学者们不满意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二元对立,而力求清理学术研究中长期的“非此即彼”思维模式,力求“一分为三”甚至走向多元多维看问题的非中心模式;或注重从地缘层面的世界与中国、北京与外地的“中心——边缘”冲突中走出来,倡导从中国看世界、从乡土看中国的文化交融与超越。无疑,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节点上,这一系列思索是相当重要的。
在90年代,整个文化批评出现了语言转向。批评观转型,表现为80年代的政治社会批评推进到文化批评。
与80年代文学批评相比,90年代的后现代批评更少建构而更多解构,更加强调政治波普化(pop)的价值取向,更注重玩世写实主义的文化策略。这一切表明,后现代语言转向导致文学批评日益脱离纯文学或纯审美,而走向价值平面的“后乌托邦”文学和意义滑动、错位的困境。因此汉语界和批评界必得思考,语言转向之后批评将向何处?是转向意识?文化?还是价值呢?
语言转向后,批评界大为活跃,其正面价值表现为:注重文学批评的思维层面、角度的开阔多元,即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社会政治批评,拓展到心理批评、原型批评、形式批评、解构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等新的批评层面;注重倾听语言,突出语言,淡化背景,进一步扩大阐释空间,促进了意义的增殖,注重语言表征出来的差异和语言本身的差异,强调语言冲突实质上是话语的冲突,人类构筑的语言“通天塔”的“语言乌托邦”思想在后现代日益为语言异性和多元性取代,因为强调这种差异并感受和玩味这种差异性使批评变得更为宽松、更能达成彼此的理解。
与其正面价值紧密相连的负面价值,如一枚铜币的两面:后现代文学的表征危机,显示出后现代文学语言是一种撕裂传统语言和逻辑的语言,当这种文化错位的多种话语碎片共存并进而拼凑成一张零碎无序的话语编织物时,语言的裂缝已再填平,从而误读成为后现代批评的正读;批评的“语言狂欢”表现为“语言自来水”效应,一些文学本文和批评文章,整篇都是一种“语言流”,读起来一泻千里,但不知所云,这主要是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肌体”过剩“骨架”萎缩,出现了话语膨胀(虚肿)而表征意义的危机。同时,还因整个理论框架的倾斜,在打破僵化体系时,只见废墟,而不见新体系的建立(只破不立),语言危机完全是人文精神和情怀的危机。
总体上说,90年代的先锋艺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力图挣脱这种困境。它在制造大众神话的同时,又在力求破除这种大众神话,它在为满足大众的欲望的最低纲领即世俗关怀的同时,什么时候又能走出这种平面化的低迷状态,开始指向最高纲领即人生的精神升华状态呢?这也许是文化艺术的中国式的“世纪末之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