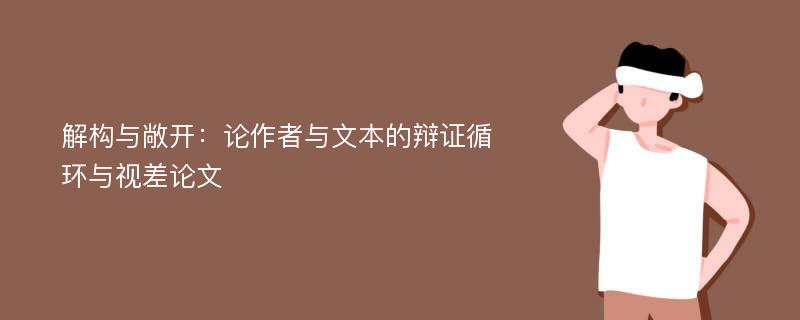
解构与敞开:论作者与文本的辩证循环与视差
唐解云1唐兴华2
(1.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2.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诠释学离不开探讨作者与文本的辩证关系,同时通过解构这种关系来达到辩证循环与视差的直观,敞开实践诠释学的问题域。作者与环境相协调时所面临的历史情境和心理要素等构成了文本的特有内涵。而文本一经形成,作者的对话经验以及历史理解便具有了为诠释者所解构的可能,同时带来读者的视差之见,并且在辩证法所表现出来的双重性、矛盾性以及发展性中多元敞开作者意图与文本意义之间的关系。通过在实践意义上的生命之流的考察,可以诉诸实践诠释学意义上的方法论与本体论的融合。
关键词: 作者与文本;诠释循环;读者视差;辩证法;生命之流
关于作者与文本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诠释学界探讨的重点。如何厘清它们的辩证关系是用好诠释学的“阿基米德之点"。文本意义是否表达作者意图?作者在创作文本时是否进行摘抄或模仿?文本是否是作者的死寂状态?……一系列话题围绕着作者与文本的辩证法而展开。殊不知,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诠释学走向辩证法是历史的必然。需要强调的是,“辩证法并不是那种能够使某个软弱东西成为强大东西的论证艺术和讲演艺术,而是那种能从事物本身出发增强反对意见的思考艺术。”[1]427辩证法通过返回到诠释学,辅助以现象学,形成了哲学诠释学的自我超越,并回归自身而给人带来不同视差。
一、解构与回归:作者意图与文本意义
受历史情境、心理状态或者人文氛围等因素的影响,作者意图不免会发生剧烈的、抑或微妙的变化。在创作文本的前后时间里,一定的时间距离必定会对作者的生命体验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文本一旦被作者创作出来便将作者的意图、生命体验等固化下来。“作者自身在被文字描述和记录的意义空间里得以形成;文本是作者降临的地方。”[2]153所以,作者是文本的“本质”,文本是作者主观意图的客观化物。必须强调的是,作者是能动的主体、实体。能动性应该成为文本存在的历史条件。作为诠释学的因素和规则,贝蒂提出“对象自主性原则",强调文本与作者意图的关联,以及作者所创造文本的内在性和独立自主性。文本可能独立于理解者之外,而非作者之外。不过在其客观化的过程中,作者正因为受时空、人文等因素的影响,会异化文本的部分内容,而这些部分内容构成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视差。文本被作者所创造出来,甚至通过艺术形式、行为方式等媒介固化下来。于是,作者离文本越来越远,文本却经历时间、地点的推移越来越固定,以至于读者反过来,会先入文本再求诸作者本身及其身后的故事,构成了“轻创造者而重创造物"之表象。这特别是在科技时代或者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是种文本的狂欢(同时表征为作者的孤寂和“死亡”),作者的存在受到文本的牵制甚至左右,此为一种异化状态。该类似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体创造之物反过来对抗、奴役主体的现象。(成为他者的)文本与作者的对立,正如机器与人的对立一样,人权与机器话语权之争在预测的未来不免让人惊心动魄。但是,由此异化过程,我们会发现文本惊人地演化、发展、充实及实现,使其已俨然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结构。譬如说“中国的古汉语到现代白话的演变,古汉语的文学体裁从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的小说,充分说明了虽然作者写作要受到语言的控制。但同样,作者也控制着语言。"[3]伴随着科学时代的理性表象,主观存在的人慢慢被异化为客观化物,甚至处于,抑或被束缚于虚拟的空间之内,正所谓“机器控制人而不是人控制机器"一样。
文本意义的偏向与否是诠释学所要研究的话题。同时,文本是否反映作者意图也很大程度地凸显其客观性和普遍性。首先,文本作为客观表达,存在于纸质结构中,既包括书写文本,又包括口传的固化物,如郭店楚简、曾氏家书、《圣经》、《荷马史诗》等;其次,文本也可以是艺术形式、美学造型,甚至自然现象等;最后,“作为行为方式,文本是动作及其构成的事件。"[4]经由人与环境互相协调的历史也可以成为文本,并且可以充当读者的“教科书”,历史的一系列因果链条可视为读者的“参考资料”。“不仅原始实在是本文,而且历史实在本身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本文。"[5]87而在诠释学境遇下的“文本",通常以语言性文本为重。当然,“文本就是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根据这个定义,由书写固定是文本本身的构成因素。"[6]148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不管是理论还是活动,诠释学都对语言的批评、理解、建构等方面尤为偏重。“在诠释学的语境中谈论‘文本',无论是诠释的理论研究还是具体的诠释活动,其主要对象无疑是语言性的文本,特别是书写文本。"[7]从充当“人—神"互动的信使赫尔墨斯的诠释技艺,到教会传统下的“唯独《圣经》"现象出现,到马丁·路德关注个体能动性的新教诠释学(倡导“《圣经》自解原则"),到沃尔夫“让哲学说德语”的努力,我们能够看到语言的强大力量及其背后诠释活动的空间维度。正缘于此,由于传递者和文本(承担)的负重程度的不同,言语性文本特别是书写文本的引导力量有时与作者的权威性相悖,或已“消灭了作者"。对于文本的保留,作为第三者的读者着重看待的是文本内容及其中的规则,并且转化为富有实证性和创造性的内容,预设出“合理性"。在大众化、时代化语境下,表现出读者对于文本塑造及理解的自由。简言之,作者意图与文本意义已经融贯了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而主客体之间的辩证法却不完全适用于作者与文本之间的辩证法。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由于“诠释循环"[8]①和“读者视差"现象而表现出双重性、矛盾性以及发展性等特点。为了说明这两种现象,我们需要回到阿多诺的《哲学的现实性》这个文本当中,去了解否定辩证法的主要内容。阿多诺试图对肇始于柏拉图的理性专制主义传统进行批判,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传统进行“规定了的否定"。该文本认为:就其原初意义而言,辩证法是反抗思想的同一性诉求的。否定辩证法意味着对所有本体论、同一性哲学的批判,以及对哲学概念和体系的打破,并且倡导哲学问题的多元敞开,同时返回自身予以否定。
We thank the Baoding Lightway Green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for providing experimental PV modules.
二、敞开与多元:双重性·矛盾性·发展性
作者与文本的双重性、矛盾性以及发展性的辩证关系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对话经验和历史理解。诚然,在诠释学意义方面,如何在进行诠释活动的时候灌输对这种否定辩证法的体验,是诠释学进路之要求。我们知道,理解过程就是再体验的过程,是影响历史流变的过程,这不仅是读者去体验作者的思想以及语言文本结构的过程,而且是诉诸一种对于生命、对于精神、对于信仰的客观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作者的主观精神与其文本的客观存在形成了不同角度的分割。作者往往是在历史的流变中去把握个体精神,领悟“为己之学",以可沟通自己和前人的体验情境为旨趣,并且突破地缘、业缘和血缘的限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遗传原理之所在。而诠释学循环所体现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就表现为:在时间距离以及经典条文的影响下,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是作为理解者对于文本的把握,都是在领悟中塑造自己的个体精神,以及体验某一事件的价值和效果。然而,对文本意义的理解的深浅程度,会造成理解与对话的不同通道,因而造成文本承接的负担,也会带有读者的视差之见。
大数据条件下,首先要做好的是数据库的基础建设。为此需要紧跟企业业务发展,扩充数据信息资源,实现各类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充分共享以及灵活机动地检索,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构建并完善重要数据的搜集渠道,健全结构化数据库,并且打破各部门各业务间的隔离和分化,增强数据的完整性和利用率,进而打造出智能化数据的分析平台,为实现数据的分析和挖掘以及连续、全面的审计提供技术支持。
“历史就必须为每个新时代重新书写。”[13]7“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轻重远近关系,受到“历史厚重感"给个体带来的生命体验的影响,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教会传统根深蒂固,一直到施莱尔马赫时期,诠释学语境是“作者中心论",并由“方法论"占主导;二,从伽达默尔到海德格尔,“读者中心论"占主流,并呈现的是一种“本体论"语境;三,利科尔提出“文本中心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前面两个时期所代表的诠释学方向的综合;四,到底是抄“近路"⑤,还是走“远道"⑥?无论哪种取向,都成为了相当一部分诠释学者在新时期面临选择的症候⑦。由此,在经历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相互争论、批判和建设,以及诠释学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转向后,我们可以看到诠释活动越来越倾向于让“理解"呈现在历史当中,并且以文本为中介寻求作者与读者的视域融合和情感共鸣。“理解的能力是我们作为主体个人的一个基本素质,它承担着我们个人与他人的共同生活,特别是它通过拥有语言和共同会话起着作用。”[13]3这就在一定意义上赋予了诠释学以人学特征,诉诸偏向于主体性的表达,其中,主体的生命体验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首先,作者与文本体现一种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伴随着读者、诠释者的视差之见。文本意义的解释到底是取决于作者意图,还是诠释者(读者)意图?还是在于其与其他文本的对照和融合?显然,诠释活动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在一定的历史场域中,对于诠释活动的不同取向,造成了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双重距离:作者创造文本时,将自己的意图、自己的情绪、自己的生命体验等融入了文本当中,使得诠释者对文本的理解不得不将作者考虑进去,这就是以作者意图理解文本。“作品的作者,当他运用语言时,语言的文义就由他的意图完全确定下来。"[9]78一般说来,不同作者有不同的文风,读者于是可以依据不同文风对不同作者进行粗略厘定。这样构成了不同作者与不同文本特殊语辞之间的距离,以及需通过文本还原作者的场合及历史的变迁。而传统解释学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把文本意义当作作者的意图,所以才认为读者可以完完全全地复制出文本的意义,从而走向了绝对主义,给了现代解释学以攻击的把柄。"[3]只有走向历史的深处,深入现实环境当中,才能还原诠释活动的原意,这就意味着实践诠释学的历史情境性。当读者进行文本诠释时,必须挖掘作者的时代背景和个性特点。通过对文本的语言与作者个性融合时,才能够表达出作者与文本的辩证循环。读者能够发现:在文本当中也能够敞开作者的实践特性和理论品格,因此,作者与文本应处在“内生共存”的关系场域当中。
其次,由于时代变迁、历史背景、意识形态、社会交往等因素的影响,作者与文本的关系呈现矛盾性,主要缘于诠释者(读者)的视差。“文本一旦问世,作者就死了"②,究竟思想定位与读者解读能否取代作者的存在呢?“严格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文本的主体或作者是让·雅克·卢梭。"[10]如果读者对文本的尊崇,仅是从作者背景、立场、意图出发,那么从作者与文本的关系中来看,作者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当读者从文本的客观性、内容、结构等方面去考虑诠释活动,而忽略作者等其他因素时,文本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当文本遇见文本,进行对照分析时,读者便作为作者与文本关系外的第三者存在而占据主导地位。只是视域问题:作者在阅读或者诠释自己作品时便成为了读者。这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偏差,而在阅读他者作品时又会陷入与自己作品内容结构、彼此意图相偏差的矛盾当中。比如立法者、法律条文与法官之间的关系正如前述:立法者一旦创造了法律条文,便在实质意义上与之脱离关系,剩下的只有法律文本的应用与诠释,立法者也必须遵循自己所创立的法律规则。法律条文随着被法官们的应用而赋予了层次不同的生命——伴随着实际情境的特殊性,法律文本的普遍适用性与法官们的主体运用性会产生一定矛盾。这是诠释学的处境,所以我们在理解作者与文本以及诠释者之间的关系时必须得注意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至于彼此的理解和对话,应放置在共同体内部进行讨论。
最后,作为主体及其主体实践的对象,作者与文本的关系体现出发展性,这不仅由于作者自身的成长、文本的适应和改造的需要,还受到读者(诠释者)的实证需要。正所谓“文本意义永远在途中”,文本意义的理解体现其发展性,然而若没有作者的创造以及读者(诠释者)的应用,文本则不可能存在和开放。作者为诠释者(读者)创造文本,因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鸣和偏差会影响文本的生成和发展。众所周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随着历史的发展,作者与文本之间、读者与文本之间进行着协调。作者与读者作为现实的个人具有个别性、具体性和变动性等特点。我们不难看出,作者与文本关系的发展具有时间上的、空间上的、思维上的渊薮。
在时间上,在理解和对话的过程中,读者对于作者的意图由于时间距离很难把握,即使在同一时代也会由于地缘、业缘等限制对作者创造作品时的意图捉摸不定。由于作者的历史变化,读者(诠释者)即使观其作品内容和结构也难以全面理解作者意图。作者总是在适应着历史变迁,也对自己的情绪、体验等进行改造,同时又回溯自己曾经创作的文本,陷入前理解和现理解的矛盾当中。彼此矛盾促使作者及其文本的成熟,也恰好是在人与环境的协调下,彰显了其中的实践意蕴。实践层面的“合格的行为选择"与理论层面的“爱智慧"所组成的“平行四边形"在作者与文本的发展进路中得到伸展。
“诠释循环"和“读者视差"的相互作用,使得作者与文本的关系由单纯转向复杂。作者在创作文本时融入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表达,也是历史表达。我们在理解作者及其文本时,依据不同方式、途径、设定等进行理解活动,效仿自然科学,意在为人文科学提供方法论。然而这就陷入了困境:自然科学式的生命体验往往直观化和个性化,不能从整体把握到更为细致的人物心理。而问题在于我们要在整体与个别的双向理解中确定诠释活动的方向或主题,使自己的生命体验可以像河流一样具有灵动性和可溯源性,并且呈现出一种社会性的特点。生命,从认识论意义上来说,不是一种被迫服从,不是一种义务,不是一种厄运,更不是一种欺骗行为,而是一种被综合的、获得承认的主体系统。它的“文本”是思想经验,它的“原理”是“一种认识工具”,它的“内容”是能被理解的社会历史,它的“追求”是获得自由和解放。因此,“有一种转喻的暴力,它贯穿并支配了海德格尔的阐释。”这种转喻也没有边缘和纽带,特别是其对于生命、生命体、整体与死亡的诠释而言。诚然,对生命的理解要在社会(交往)关系中进行,决不能脱离实践。这就是本文所关涉的本体论问题——诠释活动不仅要探讨“理解"自身,更要确定在实践层面上的本体地位,“……真正的理解活动在于:我们是这样重新获得一个历史过去的概念,以致它同时包括我们自己的概念在内……重构那些把文本的意义理解为对其回答的问题其实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提问。因为文本必须被理解为对某个真正提问的回答。"[1]507-508认识历史的意义或者说对生命之流的体验和融通之意蕴就在于此。
在思维上,作者与文本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作者和读者的价值判断、立场以及文本的效果因素上。施莱尔马赫曾说过“有世俗生活、误解,就有诠释学"。诠释活动如此,文本意义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作者和受众的俗世生活影响,也会从主观思维上产生批评、误解、理解等。由于每个读者有他所特定的“哈姆雷特",而文本意义依靠读者(诠释者)的理解和诠释才具有实质性内容。这样,文本意义在受作者意图的影响之外,还打上了读者理解的深刻烙印。作者在创作文本之时所带有的动因和价值观,以及文本受到受众的主观设定,都影响着彼此的价值判断。文本意义的开启受到能动主体的应用,在不同场合和阶段自有它的不同效果。前述“法律条文和法官"的例子也就在于此。不过,对于费尔巴哈式的“文本解释文本"、一些注疏传统④而言,作者与文本的关系只会越离越远,文本承接的负担也愈来愈大。正因如此,我们在进行诠释活动时,一定要注重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统一。
三、生命之流: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统一
①“诠释循环”是传统诠释学的难题,从“前理解”出发,指的是“整体只有通过对其各部分的理解而得到理解,反过来,对部分的理解又只有通过对其整体的理解才能完成。”转引自:李翔海.本体诠释学与西方当代诠释学[J].中国社会科学,1993,(4):133-146.
“主观与客观—作者与文本—否定之否定”体现出生命之流的力量,促使诠释活动向前推进。狄尔泰强调要回到“生命统一体”之中找寻诠释学的真谛,胡塞尔也提出“意识生命”的主体性预示。胡塞尔认为:“生命也是而且正是作为一切客观化物源泉的被先验还原的主体性”[1]322。“先入之见”、传统文化的张扬、“误解是理解的内在障碍"和“对话"等构成了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诠释学传统,到哈贝马斯的怀疑诠释学,聚焦于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所强调的是对意识形态进行鞭笞的社会批判理论,再到利科尔的文本诠释学,所强调的是“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统一"。诠释学不可避免地卷入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漩涡当中,如“读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以及“作者中心论”等。伽达默尔在对本体论诠释学的建构中,尤其是求诸关于人文社科领域中的真理时,反对在诠释活动中加入方法论因素。“由此导致的作为方法论思考产物的自然科学,与非方法论思考的人文科学之间的对立问题却令人费解。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问题,伽达默尔希望不借助自然科学来理解人类存在;另一方面,他却断言诠释学观念在一切人类活动中的普遍性,而这一论断无疑具有强烈的自然科学色彩。”[12]伽达默尔看到了科学主义泛滥下的人文关怀,进一步阐释了科学主义以及科技的局限性。由于观照了科学主义泛滥下的人文关怀,伽达默尔强调阐释科学主义以及科技的局限性。
按:患者冬季咳嗽,夏季自愈,呈现出“往来咳嗽”,能够看作是少阳证“往来寒热”的一种延伸,用西药治疗多不见疗效,用小柴胡汤治疗后,效果颇佳。
在空间上,文本意义的开启与其实用价值、效果历史相联系,凸显“含义—原意"并由应用性引路的作用链。不仅作者意图难以把握,读者意图的确定性,即“含义—原意"逐渐成为常识而体现的特性,因其多样性也存在不同之处。当作者作为读者(诠释者)阅读自己的文本时,由于自身生命体验、理解能力、语词驾驭能力的前后变化而意识到自己并不能完全理解先前自己的作品。毕竟“前理解"是确定的,作者也会不自觉地受到“前见"的束缚;而“现理解"又是不确定的、多元的,它可能与“前理解"趋同,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存异的——作者会意识到当时意图需要表达而未表达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在无意识状态时,在文本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东西。“读者、情境是不确定的,因而文本意义也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形成了文本的可塑空间。读者能拥有尽可能多的主观解释条件③,因而文本意义也在尽可能大的空间里漂浮。而在面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一系列理解和对话的需要时,也促使作者会针对文本“重建语境"。
②法国文论家罗兰·巴尔特在著名论文《作者之死》一文中的说法。
另一方面,后现代语境下的文本信息化又引起其客观而普遍的存在。文本可以是多元存在的,因而也受到读者、作者甚至语言自身的多元决定的影响。在作者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下,文本的诠释自然而然地带有主观多元的色彩。在这个意义上,文本已然与作者保持着流变的矛盾关系。无论在纸质结构中,还是在网络系统中,文本作为主观互动者的客观化物,保留了作者的思想,寄托了读者的情感,表征了历史的厚重和人物的鲜活性。但是,在这信息化时代,即使是最鲜活的文本,也不可能代表作者的原初全意。变迁的历史总会带来读者对于文本的相似、模仿等的视差之见,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发展性要求。“固然,文本解读的结果必然是一种作者视界与读者视界之间的‘视界融合',而不是读者放弃自己的视界或者让自己的视界覆盖文本作者的视界。"[14]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循环,升级为只有作者的线性运动过程。这里,读者根据对文本材料的模仿或者再创造,使自身主观化,成为正在或已完成了的模仿或者再创造物的作者。于是作者也就是读者,读者也就是作者,只是对于文本的历史审视和心理移情等方面有着效果、功能意义上的存异。这间接地体现出作者与文本的矛盾性,那就是文本可以作为读者的作者——体现了一种“作者的消弭"的话语权力。但是,我们应尽量避免由于文本特定化而带来诠释学上的极端主义。
亲虾到场后均放于3个培养池中,平均约7尾/m3,水位1.3m,每个培养池的水体为40m3,亲虾培养池覆盖遮光帘,即暗光培养,充气石每池40个平均布设于池内。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502诚哉斯言!为了克服这种极端主义以及将诠释学引入生命之流中,我们不妨“从文本到行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诠释学,体认其中的生命价值与历史意义。我们不能“制造马克思”,但是我们能“强调马克思”,特别是在实践诠释学的视域中得出生命之流的走向,以及主体性的诊断。俞吾金指出:“可以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意识形态学说称之为‘实践释义学’(die Hermeneutik der praxis)。”[16]336马克思用他鲜活的理论力量,及其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得来的社会经验,确证了实践诠释学的科学范式。从不同的角度,如作者角度、文本角度以及读者角度,都不能代替实践的中心地位。只有立足于实践,才能从真正意义上领悟生命的真谛,才能从作者和文本、作者与读者、读者与文本之间获得生存论意义上的历史诠释。随着马克思哲学的多元化研究,回到经典文本,加之融入自身的生命体验变得尤为关键,特别是在挣脱诠释循环的假象以及读者视差的局限等方面具有深刻意义。就这个现实性的、历史性的意义而言,实践诠释学直接为人们的理解之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力量。
注释:
为什么诠释学是生命之流?不管是作为理论研究的诠释学,还是作为主观活动的诠释学都离不开理解、意义等因素,这些都会融入作者或读者的生命体验,通过文字所固定着的生命表达去寻求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环境的协调关系。不管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科领域,不同的生命体验形成对诠释学的不同理解和意义—诠释主体的能动性、多样性景观形成诠释学的生命之流。“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11]427作者与文本的辩证法关系体现了诠释学的发展动态和内在要求。
现代社会开展“非遗”的生态化保护离不开科技创新。“非遗”的生态化传承保护要坚持与时俱进,与社会科技发展同步,要积极运用前沿的科学技术,维护“非遗”传承保护的条件,解决传承保护的短板,助推项目传承人文化层级的提升。
那么,作为作者生命体验的符号化的文本被固化下来后,是要依从作者意图,体现其原初性吗?还是要迎合读者(诠释者)的口味,发展其实证性?殊不知,其中的原初性和实证性的融合构成作者与文本的双重性。不仅作者具有自主性,文本也具有自主性,因此诠释者在理解之时所面临的自主选择也是双重性的。需要强调的是,“利科尔认为,文本的自主性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相对于作者的意图方面;二是相对于文本产生的文化境遇和一切社会学条件方面;三是相对于原始听众而言的意义方面。"[14]在主观因素的渗入与纯粹客观的存在之间,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立足于当下现实而继承经典,回归文本的经典之处汲取智慧。从哲学史角度,我们必须将文本意义化归生活,超越文本,并带着自己的审慎考量,“将现实加入文本"。这也是贝蒂所提出的“理解现实性原则",是一种视域融合:精神通过经验而整合到现实中来。
③读者的先入之见是理解的条件。
以小组为单位,按照老师下发的任务书(涵盖要完成的任务、制作要求、产品相关信息点、评分标准、学习反馈表),共同制作产品说明书。老师事前根据组员的情况布置相应产品给予制作(如女生较多的组,教师可选用化妆品、零食等学生感兴趣的物品;男生较多的组,教师可选用电器等物品布置任务。此任务也可以由学生自己设定),完成以后,组内进行修改,然后组与组之间派代表进行互改,并展示成果。最后每位同学完成学习反馈表,用于检查教学效果。
④一代大儒王阳明认为:“孟子以后的人物思想等不值得研究”强调读绝对经典。积累“注”、“疏”的东西,可能不好“排毒”,反而增加负担。
这时,肉仔停住了切肉刀,鼓着两只牛卵子大的眼睛直直盯住牛皮糖,不只是有点生气,而且对于这个体积比他小一倍的人居然敢向他挑战,大感意外。
⑤近路,本体论走向,而抛开认识论或者方法论。
⑥远道,从语言学出发,反思并进行理解。
⑦症候,即在整体视角下,意识形态(语言)所呈现的与实际“事件”相脱节的直接指向意识形态领域的“病症”。
参考文献: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利科.从文本到行动[M].夏小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左洁.作者·文本·读者[D].苏州大学,2007.
[4]汪堂家.文本、间距化与解释的可能性——对利科“文本”概念的批判性解释[J].学术界,2011(10):74-83.
[5]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7]潘德荣.文本理解、自我理解与自我塑造[J].中国社会科学,2014(7):50-65.
[8]李翔海.本体诠释学与西方当代诠释学[J].中国社会科学,1993(4):133-146.
[9]殷鼎.理解的命运[M].北京:三联书店,1988.
[10]王金福.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关系的几点意见[J].山东社会科学,2005(9):41-46.
[11]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成中英.作为知识和理解的科学——一个本体诠释学的诠释[J].吕晓钰,等译.学术月刊,2015(3):34-43.
[13]伽达默尔,德里达.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M].孙周兴,孙善春,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4]彭启福.文本诠释中的限度与超越——兼论马克思文本诠释的方法论问题[J].哲学研究,2007(2):18-24.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7]李翔海.本体诠释学与西方当代诠释学[J].中国社会科学,1993(4):133-146.
收稿日期: 2018-06-06
作者简介: 唐解云(1994-),男,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唐兴华(1993-),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B089. 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2( 2019) 03-01-07
(实习编辑: 郑 舒)
标签:作者与文本论文; 诠释循环论文; 读者视差论文; 辩证法论文; 生命之流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