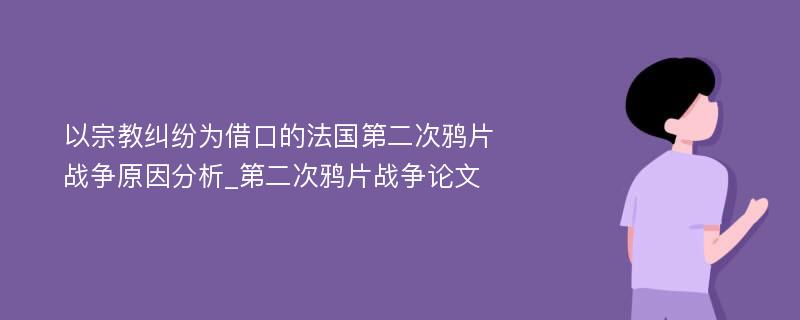
试析法国借口宗教纠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法国论文,纠纷论文,借口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为何?19世纪上半叶法中关系的特征——“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是探讨这一问题的突破口。法中关系和当时直接进行“商业交往”的英中关系大相径庭。英、法选择了不同的契机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系的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政治体系的运动除了国家、民族、地区间的政治交往,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各民族地区间进步人士的交往外,还包括欧洲基督教、天主教教士的传教活动。法国政府正是利用传教士的活动扩张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巩固国内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拿破仑三世充分利用国家政权干预经济,促使法国工业革命顺利完成,法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同时,帝国政府力改软弱无力的外交政策,积极活跃于国际争霸和殖民侵略的舞台。到1870年,法国已拥有殖民地面积达9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50万, 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殖民帝国,亚洲的中国也未能逃脱被法国侵略的厄运。1857年,法国以所谓的“宗教纠纷”——“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联合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
19世纪上半叶,法中关系主要表现为法国对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执著”追求,这决定了法国政府始终围绕传教利益的扩大,以加强对华的侵略势力。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清的是19世纪上半叶法中关系的主要特征——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由拉萼尼使团访华、耶稣会士活动、政府的支持、军界参与传教、租界状况等方面表现出来。
鸦片战争以前,法中关系十分疏淡。1840年鸦片战争后,法国政府开始注意中国。1841年曾派真盛意来华调查,企图乘机渔利。当法国政府看到英国侵华取得了巨大“收获”后,遂指派拉萼尼为专使,来华索要殖民特权。苏尔特政府指令拉萼尼:“为法国的航运和贸易获得与英国相同的利益。……只有通过法国和中华帝国之间签订一个通商和航运的友好条约,这个条约使中国接受我们的制约,如同它受到英国的制约那样。”(注:CH.麦朋,J.佛兰德,《上海法租界史》,巴黎 1929年版,7—8页。)《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使法国达到了这一目的。
但拉萼尼更进一步地向基佐外长呈报:“从商业贸易方面来看,英国人和美国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事情做。然而,从精神和文化方面来看,我认为该轮到法国和法国政府运筹决策和采取行动了。”(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316页。)即在政府命令之外,拉萼尼对天主教“弛禁”问题作出了贡献。与耆英交涉历经三个回合后,1846年春,道光帝终于颁布上谕:“谕军机大臣等,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均已依议行矣。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有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请所有康熙年间各省建立之天主教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而各省地方官,接谕旨后,如将实在学习天主教而并不为匪者,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假托天主教之名,籍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具照定例办理,仍照规定章程,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1964年版,2964页。)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清政府的同意,“弛禁”政策被打开了缺口。法国官方和舆论界公然赞赏拉萼尼取得的这一成果。在基佐看来,这一成果“不但会为你(拉萼尼)的使命增添光彩,而且也能为国王的统治及政府争得荣誉,教徒也将把这一切看作是法国的最光荣传统”(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449页。)。 1846年7月,拉萼尼被封为贵族。
耶稣会士重来中国传教的经过也说明法国官方人士对传教事业的重视。1841—1844年间,先后有三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他们均受到王后玛丽·阿梅利的支持。其中的一位传教士南格禄神父激动地说:“她(指王后)显得与其说是我们的保护神,还不如说是我们的母亲。”(注: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上海1914年版,43页。)1853年6月2日,翁毅阁神父(1851年4月—1854年8月任中国江南教区会长)回欧洲时,在法国作短暂停留期间,不仅介绍了中国江南教区的情况,并且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接见。
法国外交部和殖民官员也为传教士提供方便。从1833年起,法国外交部一直通过驻华外交官亲善地为神父们提供与西方通讯的便利。当拉萼尼使团刚到澳门,立即回答了罗伯济主教(驻澳门的一位法国耶稣会主教)的要求,表示将不辱使命,为传教事业斡旋。1849年11月10日,敏体尼(驻上海领事馆领事)致函法国驻华公使陆英伯爵:“全力保护天主教是我们执行的一项好政策,……我们已获得了很大影响。他们(天主教徒)将是我们商业的第一批主顾。”数月后,敏体尼又报告道:“公使先生,我对你重申,这些传教士是我们将来在这里取得重要地位和成就的工具。……我们的传教士必将为法国作出重要贡献。”(注: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上海1914年版,168—169页。)
法国军界也为传教事业尽责。1853年12月底,驻上海法租界的护卫舰“贾西义号”启航返法,舰长德柏拉在给母亲的信中记载了当时的心境。他说:“我离开了中国,好似一个还没完成任务的人,当我正对工作开始感兴趣时,被人剥夺了工作。……军舰虽不直接参加传教工作,但也能作出不少有益的事,给传教士帮些小忙。”史式徽(1866—1937年,法籍耶稣会士,文学博士,教会史教授)评介道:“小忙拯救了上海的天主教事业(指面对太平天国的压力),……奠定并实行了法国对教友们的保教权。”(注: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上海1914年版,280页。)
由此,上至王后、皇帝、外交部,下至领事、将领纷纷支持传教士们的传教活动。中国天主教教友人数从1800年的20万达到了1850年的32万。(注: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圣教杂志社民国27年版,283页。)
与此同时,法国对华贸易却遭冷落。1844年,在广州进出口的法国船只仅四艘,位于英、美、荷、比之后。上海法租界繁荣和发达程度与英租界相距甚远。1856年,上海法租界商人11人左右(法国人仅7—8人),英租界内,1844年就有50人,1850年增为1750人(注:张群《上海租界略史》,上海1931年版,29页。)。1851年8月14日, 上海各租界颁布第一个关于码头治安和海关税则的条例,道台和各国领事除敏体尼外均在条例上签了字。其中一项规定道:船只只能停靠在英租界前的河面。这意味着剥夺了法租界拥有接纳船只停靠的权利。可见在各租界中法国地位微薄。
法国官方殖民代表陆英、布尔布隆等均不注重贸易事务。陆英认为,一个领事不应参加商业交易,“我很佩服你的胆量(指敏体尼积极为贸易出力的行为),但不能同意这种行为”(注:CH.麦朋,J.佛兰德,《上海法租界史》,巴黎1929年版,41页。)。外交部尽管对敏体尼表示赞扬,但其有关贸易的报告却留在外交部的文件里无人查看。1853年3月3日,法国新公使布尔布隆从澳门写信给敏体尼,阐明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政策的理由。他说:“为了让您了解情况,我还是要告诉您,美国公使直到他离开为止曾再三向我保证,他打算严守中立。如英国确实要干涉的话,我看也纯粹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们在中国没有这类的利益。因此,中立政策对我们来说……显得重要。”(注:CH.麦朋,J.佛兰德,《上海法租界史》,巴黎1929年版,47页。) 法国所谓“中立”仅为外交的一种幌子,它曾积极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这却是法国忽视商业贸易的一种明证。
显而易见,法国在19世纪上半叶与中国外交关系的重心在于通过天主教进行殖民扩张,而非依靠贸易进行殖民侵略。
二
19世纪上半叶,法中关系主要以传教“事业”为主线索,法国为何受此利益驱动,并借口宗教纠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呢?
第一,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伸。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均利用天主教巩固国内统治,维护私有制,并将其作为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废除了天主教会所有经济特权,包括征收什一税和拥有土地的权利,土地收归国家,并将其拍卖,教会的地产落入资产者和富裕农民手中,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取得了硕果。教士从革命前的第一等级降为只领取国家薪金的教士,教会经济基础被彻底摧毁,成为完全从属于国家的组织。从此,教会往往成为某一政府为获得精神支柱、巩固政权而被利用的工具。1799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波拿巴认为光靠暴力统治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宗教的力量,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他着手进行教会改革,颁布法令:准许开放在大革命期间关闭的教堂,恢复礼拜日,他本人也常去做弥撒,以表示对教会的友好。为争取罗马教廷的支持,1801年7月,波拿巴力排干扰, 与罗马教皇签订了《教务协议》。协议规定:①天主教承认大革命原则,不再要求革命中已没收的教产和恢复教会的特权;②“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信仰的宗教”,而不是国教;③天主教必须完全服从国家,为国家服务,主教任职前必须宣誓效忠第一执政;④主教由第一执政任命,教皇授权,教士薪水由国家提供,教皇宣布不再以任何方式干扰教会财产的购置者(注:沈炼之《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12页。)。与此同时,波拿巴还宣布新教、犹太教与天主教具有平等地位,教士不再宣誓效忠宪法。波拿巴的宗教政策深得人心,消除了国内的宗教纠纷,彻底粉碎了反革命叛乱分子利用天主教,煽动广大教徒与政府斗争的阴谋,在国内迎来了和平、团结和统一,在国际上则缓和了天主教国家的敌对情绪,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另一方面,《拿破仑法典》确立的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使小农在大革命中获得的小块土地有了法律保障。加上新政权发展农业,发展小农经济的措施,小农的处境大为改观,加上宗教感情又得到保护,于是小农站到了波拿巴一边,在保卫法兰西民族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农民成了军队的主力。“农民是政权的强大支柱”在拿破仑三世那儿得以继承和发扬。
对外政策方面,波拿巴力主扩大传教事业。1802年,他曾几次致函巴黎总主教和教皇,陈述其看法,希望法国传教士既对传教事业有利,又对国家有利,并希望在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重新活跃起来,消除英国人在这方面的主导作用(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65页。)。拿皮仑一世于1806 年发布一道政令:派3名传教士到中国,并发给他们25000法郎旅费(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67页。)。
拿破仑三世仿效其伯父拿破仑一世的做法,甚至更为激进,以期获得教会及其影响下的农民的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还是第二共和国总统时,首先借助教育改革,实施拉拢教会的政策,他令部长法卢于1849年1月组建初级和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草拟有关法令。 该法令规定建立一个可由神职人员担任主要职务的公共教育委员会;神职人员可担任学校教师;承认宗教修会有开办私立学校的权利;“传教许可证”相当于小学教师执教许可证(注: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90页。)。维克多·雨果曾对此表示异议:“这一法令实际上是主张宗教、政府拥有控制教育的特权。”(注: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91页。)但是,国民议会中教权派首脑蒙塔朗贝尔等人的主张占了上风,认为“对于基督教的人民除了用刺刀外,还可用其他方法去恫吓他们。凡是遵守上帝法律的地方,上帝本人就在执行着警察的职务”。另外,“为了使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养成尊敬私有财产的习惯”,唯一的手段,就是“迫使他们信仰上帝,……信仰那个诅咒不信者永世为贼的上帝”(注:拉夫列茨基《梵蒂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年版,106页。)。法国政府的目的不言自明。
拿破仑三世还给予教会一系列政治、经济“优待”。红衣主教成为参议院议员,宗教界人士竟然可以参政。教士享有结社、报刊出版权,并有优厚物质待遇。宗教预算递增,1852年为3950万法郎,1859年增为4600万法郎。教育经费同期则从2300万减至2100万法郎。1852—1860年,教会所得捐赠是半个世纪总和的62%(注:沈炼之《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334页。)。教会学校从1850年的127所增加到1863年的3038所(注:沈炼之《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326页。)。
对罗马教廷甚为“关怀”是拿破仑三世的重要“工作”。1849年,他出兵占领罗马,帮助恢复了教皇政权,后将一个师的法军留驻当地,保护教廷,直到1870才撤走。1854—1856年,法国参加的克里米亚战争,其借口为“保卫圣地”,高举所谓“圣战”的旗帜,结果夺回了欧陆霸权。“十八年里,耶稣会成了法国的真正主人。他们增设了机构,发了财,扩大了影响”。因此,他们称赞“拿破仑三世在克里米亚战争时维护了宗教,以此重现昔日十字军东征的美好时光。克里米亚战争被看作是罗马远征的一个补充,受到全体神职人员的庆贺”(注: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93页。)。
法国波拿巴家族执掌的政府均热衷于将国内的天主教政策“输出”到被侵略的国家或地区,其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波拿巴曾如此向罗马主教表白:“我希望能给中国传教事业增加新的生力。……这与一般宗教利益无关,而是为了使中国的传教事业摆脱英国人的手掌,因为他们已着手这项事业了。”(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年版,232页。)对拉萼尼有人评介道:“他半公开地干预了传教事务,与其说是拉萼尼的宗教计划,不如说是他的政治计划。”(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334页。)拿破仑三世支持天主教会取得保教权, 同样“不是由于对宗教的热诚,而是出于体面和权力的欲望”(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234 页。)。
第二,为了争夺远东控教权,法国天主教会和政府力求扩大天主教在华的传教势力,以收政治、外交、经济之利。由欧洲某个强国担任保护远东天主教会的做法是教皇尼古拉五世开端,亚历山大六世确认的。亚历山大六世承认葡萄牙是在远东新发现地区享有天主教会保护权的唯一国家。葡萄牙丧失海外霸权,国势日衰,后起的英、美、法、德四国中,只有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加之法国对外贸易比较薄弱,因此就以大量派遣传教士的做法弥补不足。法国的情况正合教皇口味,教皇逐渐倾向法国。1838年,教皇格列高列十六以葡萄牙不能履行义务为由,取消其保护权。但里斯本对罗马这一决定提出了抗议。因为当时的东印度群岛宗主教德西瓦托莱自己兼任北京、南京、澳门三个葡萄牙教区的主教。所以,葡萄牙方面拒不接受1838年的诏书。法国一心想夺取这个位置。1851年,汇聚在上海的众多高级教士曾向法国外交部发出一份呼吁书:“部长先生,我们对这个国家是比较了解的。……只要法国允许她的代表(指传教士)以法国的名义讲话,并且是果断地和高声地讲话,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615页。)很明显,他们认为: “在北京能代替法国的均为传教士。”(注:H.高第《远东历史地理文集》,巴黎1914年版,194页。)保护和帮助天主教徒的只能是法国,正因为此“我们的教会开始重新昂起了长时期在暴虐下低垂的头,地方官也不再向他们征信仰税了”(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628页。)。事实上,《中法黄埔条约》后, 罗马教廷就明显倒向法国。1846年4月, 教廷命令在内蒙西湾子传教的法国教士孟振生去接管葡萄牙派任的赵主教所管的北京主教区,法国取得了远东控教权。
法国成为在华天主教会的保护者只是在罗马教廷面前有效,却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承认。1846年2月8日,清政府虽然颁布“上谕”准予国内天主教“免禁”和各省原建的天主堂由地方查明发还原主,但并没有请法兰西予以保护,而且在内地一律不准传教。以上这些,尤其是最后一条,使法国并未取得事实上的保教权。他们需要中国广大内陆地区全方位向传教事业开放。
第三,中国民众群起反抗传教士的强盗行径,使“给还旧址”的交涉持续了一二十年之久。其间,法国传教士制造了种种事端,他们在各地恣意讹诈,无视中国主权,动辄以武力相威胁。如咸丰元年四月,两江总督曾以松江府华亭县仓廒并非五口通商地区,系属内地为由,拒绝了法国领事敏体尼的索还。6月,法国却出动兵船一只停泊黄浦江, “其意在借兵要挟,开口便要给还松江府城内天主堂地基,如该道不允,即赴省见”(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本,160页。)。1851年12月,法国传教士顾铎德派驻定海城传教的天主教方安之,诱迫教民“屡将乡间各庄寺庙庵院献入教堂,踞占把持,各庄士民因屡被欺扰,群怀不平”,乃聚集村民,“逐出教徒,收回被占寺院”(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本,178—179页。)。在直隶一省,他们任意提出所谓旧址72处,强硬要求归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不提具体地址,只指示15个县府的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归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在旧址居住的大批居民,强占房屋和地产。山西绛州,传教士缺乏任何证据,即强令“归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然闯入总理衙门宣称:“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9页。)地方当局屈服于压力,传教士便占领了占地43亩的校址。据清政府文献载:“近年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不问民情有无窒碍,强令给还。甚至绅民有高华巨室,硬指为当年教堂,勒逼民间给还。且于体制有关之地及会馆、公所、庵堂,为阖神绅民所最尊敬者,皆任情索要,抵作教堂。光各省房屋,即寓当年教堂,而多历年所,或被教民卖出,民间辗转互卖,已历多人,其从重修理之项,所费不资,而教士分文不出,逼令让还”。而且,“因房屋有倾倒,反索修理之费。各种举动,百姓均怒目相视,俨若仇敌”(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108页。)。1860年以前,大多数民教纠纷往往都是因为传教士强占土地,索还旧址等事引起的。传教士仗势欺人,不能不激起民众的义愤和反抗。正如法国舰队水师总兵库旺·德斯布瓦所说:“中国的地主官太好说话了,……要求他们让出如此竞技场、玛大肋纳教堂之类的建筑和寺院,叫他们心甘情愿地把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区让给传教士。这是不合情理的。”(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595页。)
第四,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实说明,法国殖民政府通过教会在中国掠夺地产地租,从而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
法中关系在19世纪上半叶主要表现为“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但正如前述,法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借传教收政治、经济之利。这在基佐给拉萼尼的使华训令中,《中法黄埔条约》的内容里,以及许多史实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而法国与英美相比,其对华贸易极其薄弱。请看下表:
1871—1911年进口贸易价值中各国所占比重 (各国各期总计为100)
年份
教别国别1871-1873 1881-1883 1891-1893 1901-1803 1909-1911
天主教 法国
————0.6
基督教 英国 34.7 23.8 20.4 15.9 16.5
美国
0.5
3.7
4.5
8.5
7.1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65页)
以上情况正好与法国国情一致。19世纪中叶后,法国工业生产落后于英美的状况愈益明显。第二帝国时期,工业生产尚居世界第二位,第三共和国时期降为第四位,农业生产降到第九位或第十位(注:夏炎德《欧美经济史》,三联书店1991年版,452—456页。)。法国输往中国的商品,主要为时装、化妆品和葡萄酒之类,不大合中国的礼俗。因此,法国自拉萼尼使团来华后,均注重传教势力的扩大,企图借助教会将法国国内的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经济结构模式“移植”到中国,从而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并与英美匹敌。
近代中国的大地产,除官僚军阀的外,就是天主教会的。英美也借掠夺地产,侵犯中国主权,但数量远不及天主教会,并且很少有用于租佃剥削的记载,主要是建堂造屋,甲午战后还用来建工厂。不法传教士到底在中国占了多少地产,从局部史料看,可以有个眉目,但从全国范围来说,永远是个谜。但是“侵民利,发民财者,大多数皆是天主教徒”,他们“广置田宅,经营藩息,川至云贵,其中办事之人,皆理财能手,佃田租屋,概凭大道生财”(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375页。)。1899年, 天主教会在河北献县占地2184亩(注:《天主堂在献县等地的田产》,《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19世纪末年在江南占地约200万亩(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至于教会的租佃剥削,光绪年间,河北献县一份向教堂交租的清单就很可以说明问题。清单上载:“范顺祥种堂地十亩,打黑豆二石八斗,均分一石四斗,打红高梁四斗,均分二斗,……柴禾二吊,出册钱粮去一吊。”(注:《天主堂在献县等地的田产》,《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 这仅是半分成租,并不包括其它苛捐杂税。教会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也十分惊人。农民辛勤终岁,往往不足赡其家,教堂就发放高利贷,利率高达二到三分(注:《天主堂在献县等地的田产》,《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 )。不按期偿还,就服劳役或以土地抵押。天主教会还拥有武器,私设公堂,大搞教民村。绥西河套地区的各个天主教区,“筑墙自卫,俨然城堞”(注: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辑, 第41页。)。陕北靖边县成川、宁条梁地区教民村落“每处男女百数十名不等,皆以垦地为业,牛犁种子多自洋人发给,秋后按粮品分”(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年版,360页。)。这类教民实际上成为传教士的农奴。另外,天主教会利用霸占土地,建造房屋,进行房产租赁,以此谋利。镇江于1861年开埠,资格最老的天主教堂取得的房产最多,集中在天主堂街,都用来出租牟利。租户们因买卖清淡,要求教堂减低租赁费,聚集请愿并准备罢市者即达二三百人之多(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361页。)。可见, 教会拥有房产之多,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他们收取高额租费,却又拒纳赋税。如四川“彭县白鹿场之天主堂及其修院,占农田一万亩以上,除房屋面积,有九千余亩,岁收租谷,不纳田赋”(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374页。)。
再明显不过了,法国政府重视传教事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其侵略的国家或地区扩张政治、经济利益,中国反洋教斗争多半与天主教会的罪行有关,农村教案大多由天主教会的封建的超经济剥削引发的。难怪咸丰朝就有人说:法国“不以买卖为事,专在中国传教”(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本,128页。)。正因为此, 法国政府才充分利用天主教传教士在华的活动,竭力保护传教士在华的利益,急迫地要解决传教士进入内地的问题。而中国官府的禁令和中国民情的不容,成为其达到目的的巨大障碍。怎么办?“只有政治因素和恐惧感才能使中国人作出表示,只有在枪口的威胁下,他们才肯让步”。“只要出动四到五艘军舰,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迫使中国人接受我们的要求”(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655页。 )。法国遣使会主教安若望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备忘录道出了法国方面的计划,事实也正是如此。与清政府“和谈”未成,第二帝国的代表布尔布隆等与英国侵略者互相勾结,终以一年半前发生的“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拿破仑三世郑重地宣布:“打到中国去,为传教士讨还血债。”(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658页。)全权特使葛罗被派往中国,他率领法国远征队与英国共同行动,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局尽人皆知。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第13款规定:信教自由,“凡中国人原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距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1860年,《北京条约》不但给予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自由,且第六款规定:“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土,建造自便。”(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1964年版,1027页。)该文未曾载入法文本。英法等国以条约的形式实现了他们的殖民主义企图,法国正因为上述条约而拥有了事实上保教权。葡萄牙于1857年被迫宣布放弃澳门以外的护教权。众所周知,侵略国家还获得了其他政治经济权利。
1858年,法国又借口保护天主教出兵越南,1863年占领南圻,并向北圻进发。1873年10月6日, 法国南圻殖民者头子杜白蕾写信告诉顺化苏伊尔神父:“我们的目的是使越南政府和人民信奉天主教的文明,协助南国重新整顿财政和海、陆军的工作,最后平定那很久以来住有盗匪和叛乱分子的地方北圻。”(注: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三联书店1973年版,76页。)安邺率兵进入红河三角洲时,写信给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教:“主教,你是爱法国的,你对东京人事、地形比任何人都熟悉,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们一下,使我们征服越南的成果能够巩固下来,希望你为我们找到一些忠于我们国家的越南人,在我们统治下管理越南。”(注:《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268页。)战争的结果, 法国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变越南为保护国。当然,“传播法兰西文化”仅仅是借口,真实目的是“因为它(指北圻)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它,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注: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三联书店1973年版,71页。)。法国侵略越南,甚至中法战争的爆发与宗教因素都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法国与英国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为宗教因素而非经济因素。但法国侵略的最终目的仍在于经济政治利益。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经济性质的战争,它的发生为英法和中国两种社会历史进程相结合的产物。从此,中国被动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标签:第二次鸦片战争论文; 法国经济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传教士论文; 基督教论文; 拿破仑三世论文; 天主教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