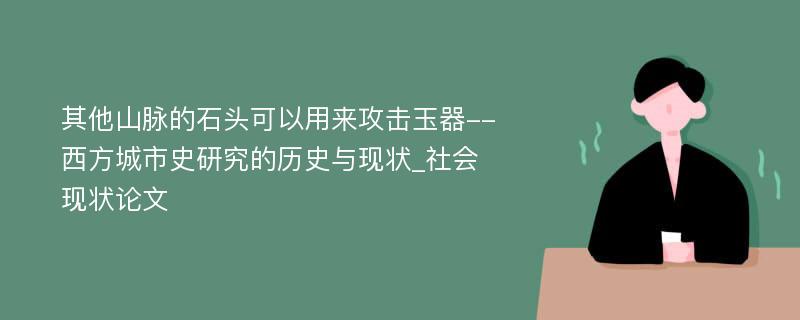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城市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以攻玉论文,他山之石论文,史研究论文,现状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7)03—0009—(05)
工业革命对近代世界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不仅在技术上突飞猛进,而且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比如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许多城市的人口以每10年40%到70%的速度增长,[1](P54) 到1900年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达全国人口的70%。[2](P425) 由于年轻人是这种流动的主体,传统家庭生活瓦解了、道德观念变化了。设施不佳、空前拥挤的城市本身成了许多新来居民的人间地狱。由于居住拥挤以及卫生环境条件恶劣,穷人区居民的健康水平下降,犯罪率也在呈上升趋势。[3](P627) 社会处于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激烈转型时期:个人如何生存?家庭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城市恶劣的卫生、交通状况如何解决?城市化对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又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最终又会带来哪些影响……一些重要的思想家都亲身经历这一变革,对此都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腾尼斯提出了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的概念,前者指小规模的、有内聚力的、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体,后者指由现代城市或国家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大社会”;迪尔凯姆在读书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那些失去了稳定社会规范引导的人们惶惑不安的心理状态;西美尔也论述城市社会对人们心态的影响[4](P412);马克思也一直关注城市问题,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更是经典的城市著作;韦伯则以更精确的历史分析方法考察了大量城市。城市问题促进了社会学研究快速发展,也是城市史研究兴起的社会背景。
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当代社会与过去社会之间的分界线是微妙的,不断变动的,而且是人为的……有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例如文化转移、不同社会之间的接触所引起的变化——对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研究主题。[5](P60~61) 可见,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或方法上的分野。因此,历史学家从由马克思、韦伯等思想家所首创的社会科学中汲取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变化理论,并把这些理论应用到城市史、家庭史这类直接反映当今现实问题的研究并不偶然。[6](P326) 这是城市史兴起的理论渊源,城市史与社会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也不例外,运用了大量的社会理论方法。美国汉学家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就“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①。而王笛新近出版的《街头文化》更是其中杰出的代表②。与此前的自上到下的对城市精英和城市管理、警察的研究不同,这个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从下到上的考察视角,即街头和丰富的街头文化贯穿全书。③
从学科本身来看,城市史属于新文化史的一个分支,是新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战以后的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又称“社会史”)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其中年鉴学派影响最大。到了19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取代“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为了区别以布克哈特、哈伊津哈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史,1989年亨特在《新文化史》[7] 中首次将这种史学流派称为“新文化史”。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新史学(政治史→社会史→新文化史)成为主流以后,传统史学并未寿终正寝,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与新史学相抗衡,只是大势已去而已。在新文化史家看来,“文化”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因素,文化既不是社会或经济的产物,但也不是脱离社会诸因素独立发展的,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因此,研究历史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新文化史家不追求“大历史”(自上而下看历史)的抱负,而是注重“小历史”(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意义,即历史研究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转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从过去注重对历史因果关系的探究转变到对事物和事件意义的探究。[8] 持久追求新话题的新文化史,④ 自然会把最能表达西方文明本质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
城市史研究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不仅研究城市的起源、嬗变,研究城市本身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城市与人、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设施、居民生活与礼俗的变迁,而且还要研究那些有关城市的理论。西方人关注城市,最早可追溯到希腊神话、史诗、哲人、地理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记述。苏格拉底曾说:“乡村的旷野和树木不能教会我任何东西,但是城市的居民却做到了。”[9](P31~32) 到了中世纪,“城市使人自由”又成了人人皆知的谚语。西方历史上自然也就充斥着大量有关城市的文献,但这些记述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
自20世纪早期以来,这一切都逐渐改变了。有关城市史的期刊与连续出版物出现了、城市史研究组织越来越系统化了、城市研究主题越来越明确了、理论与方法也越来越能反映出自身的本质特色。一言蔽之,科学的城市史已经真正建立起来了,城市研究空前繁荣。
史学杂志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的产物,是史学深入研究的必要条件,是史学持续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史学普及与专业化的标志。第一批史学专业杂志产生于19世纪后半期,以德国的《历史杂志》(1859[为创刊时间,下同])、法国的《历史杂志》(1876)、英国的《英国历史评论》(1886)、意大利的《历史杂志》(1888)和美国的《美国历史评论》(1895)为代表。随着近代文明在全球的扩延,创办史学杂志之风也蔓延到世界各地。稍后,随着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又产生了分科更细的史学杂志,如经济史、社会史、妇女史等专业杂志及地区史、国别史等区域和断代专业杂志。当然,城市史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最近几十年涌现出一大批这类杂志,比如《中欧城市史文献》(1963)、《现代都市史通报》(1970)、《都市史评论》(1972)、《都市史杂志》(1973)、《都市史年鉴》(1974)、《都市史、城市社会学、古迹保护杂志》(1974)、《历史上的城市》(1977)、《城市史》(1977)、《古老城市》(1978)、《都市:艺术、历史和城市人类文化学》(1979)、《都市史》(1992)、《规划史研究》(2002)、《规划史杂志》(2002)等一大批专业杂志。这些杂志设立专题以引导研究的方向、报道相关的史料与书目以便于学者的研究,在促进城市史研究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专业团体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陆续成立了一些城市史专业组织。成立于1919年的城市史协会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史研究中心,目的在于促进有关城市史、市镇史和地方史的研究。美国历史协会的城市史小组则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伴随着城市化浪潮,20世纪60年代以来又陆续建立了许多这类组织。城市事务协会的宗旨是促进有关城市生活、城市化消息的发布,支持高等学府、研究机构有关城市事务的发展,在促进城市事务专业化、学术化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位于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城市史中心成立于1985年,现已成为城市史方面跨学科研究、研究生教育重要的国际性中心。美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史协会的宗旨是促进美国规划史的教学、研究、出版和公共教育。伦敦大学和伦敦博物馆及其他机构一起于1988年成立大都市史中心,目的是以宏观和比较的方法促进对伦敦自出现以来的特性和历史的研究。在欧盟的支持下,“欧洲城市史协会”于1989年建立。国际规划史协会成立于1993年,目的是促进世界范围内的规划史研究。这些协会会员包含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史家、建筑史家、经济学家、规划学家、公共事务人员以及其他各领域的专家。它们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硕士、博士人才;为成员出版、举办会议、相互联系提供方便。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城市史研究。
韦伯、库朗士、皮朗等人的著作属于早期城市研究范畴,他们的论述虽然很重要,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激发人们对城市史研究的兴趣。柴尔德、汤因比、布罗代尔等人的城市研究有跨学科的性质,虽然对城市史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但不属于专业的城市史学家。除了这两类学者外,城市史研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作为一个学科的城市史首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那几年间出现于美国的,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韦德(Richard Wade)的著作促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施莱辛格反对特纳的边疆学说,代之以城市的方法解释美国历史,这标志着对城市史持久兴趣的开始。[10](P203) 在英国,布里格斯(Asa Briggs)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1963)是城市史研究中重要的一步。1961年、1966年在美国和英国召开的两次会议产生了城市史研究的两本重要著作,为城市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⑤
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危机引起了“新城市史”研究。⑥[6](P129) “新城市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前提:可以通过分析美国人口普查的各种表格及其相关的其他各种数据(特别是税收记录,城市姓名地址簿,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簿)来重建城市中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6](P251) 新城市史家是一群聚集在瑟恩斯罗姆(Stephen Thernstrom)周围的年轻的美国城市史家。这些新城市史家并不像孟福德、布里格斯、雅各布斯、迪奥斯等人一样关注“城市”现象的研究[11](P46),而是忙于研究社会流动、少数群体政治、市中心贫民地区等问题。[6](P27) 因为,研究城市问题不仅需要从经济的角度,而且需要把这作为一个社会变化进程来研究,研究移民同化、社会分层新形式、工作与休闲之间严峻对立等等问题。
与此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城市研究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勒费弗尔、哈维、卡斯特,他们把社会空间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12](P92),我们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该理论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下去考察城市问题,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13] 城市研究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作为一个历史学科,城市史总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不确定,处于困惑之中。英国城市史之父迪奥斯把城市史描述为一个“百纳主题”、一个“知识领域”,可见城市史不是可以用传统方法来定义的学科。[14](P1246) 首先,人们要关心城市是怎样产生、发展的。这是研究城市的内在观点,其重点在于描述、分析城市大小和形状的变化、城市人口和经济构成、人口组成部分的分布、商业设施和生产设施的分布、城市政治和城市政府的本质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要尽量评估城市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以外在观点来研究城市。关注的是城市这一文明现象是怎样广泛影响政治发展的,比如对美国革命或新政的影响;是怎样广泛地影响经济事件的,比如对工业化的影响……综合这两种方法则称之为社会生态学方法。[15](P3) 尽管研究城市史的方法越来越复杂,但城市史从没有彻底摆脱城市传记框架的约束。城市史研究压倒性的方式是以单个的城市中心作为研究焦点,从早期的经典研究比如斯提尔(Bayrd still)的《密尔沃基》(1948)到现代的系列丛书,都是如此。[14](P1247) 无论如何,人们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追述城市发展史的。
宏观上看,城市史学的发展与各个国家、地区城市发展进程是相适应的,城市发达的地区,城市史研究也非常发达。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家,从早期这些国家的城市就占据优势,因此也就难以把城市史从通常的政治史、行政史或者经济社会史的著作中区分开来,因为在这些地区,从本质上来看城市是分析民族、社会、文明诸问题最便利的单位。东欧、中国、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乡村经济占据优势,缺乏重要的工业中心,因而难以使城市史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另一类国家比如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的工业革命使乡村社会快速实现了城市化,自19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发展而带来的问题就为现代城市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4](P1247) 城市史研究兴起于英美自然是合情合理的。
总之,城市史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目前已出现了众多与这一领域相关的学科,如地方史、市镇史、建筑史、规划史、城市地理史等。广义上讲,上述学科都可以归入城市史这一范畴,因而城市史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学科性,它综合各门人文科学的优势,吸收不同的观念与方法,以独特的视角研究城市的历史、现状并审视未来。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伴随这一进程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这一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人类关怀的现实意义。⑦
收稿日期:2007—04—15
注释:
① 芝加哥大学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对《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的评论。转引自行龙:《也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景象》(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8页。
②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因其史料的丰富、方法的缜密、思想的深邃,对城市史研究有着重大的贡献,于2005年荣膺“美国城市史研究会最佳著作奖”。
③ 英国《中国季刊》评论语。见前揭书第399页。
④ 法国史家费雷的看法。见Francois Firet,“Beyond the Annale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5,NO.3(1983),p,405。
⑤ 这两本著作是汉德林(Oscar Handlin,1915~)和布尔查德(John Burchard)编辑的《历史学家和城市》(The Historian and the City,1966),迪奥斯(Jim H.Dyos)编辑的《城市史研究》(The Study of Urban History,1968)。见Martin Hewitt,“Urban Histor)”,in Kelly Boyd ed.,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 Historical Writing (Ⅱ),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1999,p.1246。迪奥斯所领导的雷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都市史研究群(Urbar History Group),以及1966年夏天所举办的国际都市史会议,都是重要的里程碑。他所编辑的大会论文集——《都市史研究》表现了他对都市史的展望。
⑥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城市史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比如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于1978年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城市史只字未提。
⑦ 孙逊:《都市文化研究卷首语》,刊《都市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注意以下数据,1992年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是77%,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85%;1992年占世界总人口的37%是城市人口,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增加到60%。可见今后一段时间发展中国家将面临着一系列城市化问题。参Conrad Philip Kottak,Mirror for Humanity: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McGraw-Hill,2005,p.10~11。
标签:社会现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