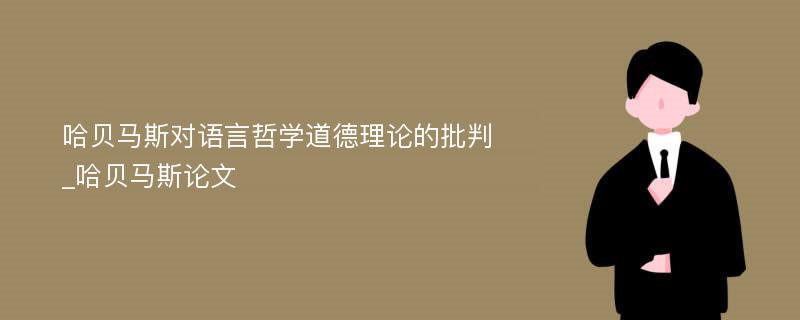
哈贝马斯对语言哲学道德理论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哲学论文,道德论文,理论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10)03-0018-08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对话伦理学”(die Diskursethik,discourse ethics),既源自语言哲学,又超出语言哲学。说它源自语言哲学,是因为对话伦理学本身就是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以后萌生而出的一种新的伦理样态,即有着深厚的语言哲学背景。说它超出语言哲学,乃是因为对话伦理学一改语言哲学把实践性道德问题排除在真理问题范围之外的做法,突破了语言哲学所囿于的经验主义的怀疑论框架。
而之所以说语言哲学在道德问题上难以迈出经验主义的怀疑论的框架,是因为固守经验主义传统的语言哲学在道德问题上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把规范性命题(或者价值命题、价值判断、评价性陈述、价值陈述)是否有真假性的问题与验证描述性命题(或者事实命题、事实判断、描述性陈述、事实陈述)的真假问题等而论之,以至于以摩尔(G.E.Moore)为代表的伦理直觉主义(intuitionism)、以史蒂文森(C.L.Stevenson)为代表的情感主义(emotivism)和以黑尔(Richard M.Hare)为代表的规定主义(prescriptivism)都基于各自的前提走向了道德怀疑主义,或者说,都对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哈贝马斯要从理论上论证或者捍卫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就势必要对伦理直觉主义、情感主义与规定主义各自的主张作出检视与批判。
一、对以摩尔为代表的“伦理直觉主义"的批判
众所周知,1903年摩尔《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一书的发表,标志着元伦理学(meta- ethics)的兴起。与传统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迥异的是,元伦理学并不致力于揭示隐藏于道德实践背后的一般的道德原则,并以这种方式来对人们解决实际道德问题的过程施加潜在的影响,而是试图解释道德话语的意义,处理道德命题的意义分析,探究道德事实与道德知识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追问道德判断的真实性或错误性。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揭示了“事实命题”(fact statement)和“价值命题”(value statement)的差异:前者是有关事态的描述,这类命题是依其与事态的实际相符与否来判定其真假值,而后者则是有关行为的评量,由于这类命题并不陈述事实,故而其真假值也就缺乏判断的标准。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或者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描述性陈述和评价性陈述、事实陈述和价值陈述)的区分,如果溯其端倪,无疑可追溯至休谟(David Hume)所做的“实然”和“应然”、“是”和“应当”的二分。在休谟看来,任何命题不外乎呈现为这样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是”或“不是”为系词的命题,另一种则是以“应当”或“不应当”为系词的命题,从前一种命题推不出后一种命题,换言之,从“是”推不出“应当”,① 这一著名的表述也被黑尔称之为“休谟法则”。② 基于此,休谟认为,传统的道德理论和现实世界的存在样态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混淆,因为,道德理论的“应然命题”(ought statements)绝不可化约为事实的“实然命题”(is statements),而这种将“应然”(“应当”)的层面化归为“实然”(“是”)的层面的做法也就势必会产生一种混淆,这种混淆用摩尔的话来说,就是“自然主义的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
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中首创了“自然主义的谬误”一词,并呈扬了“善”这一伦理学概念“不可分析”(unanalyzable)和“不可界定”(indefinable)的基本主张。所谓“‘善的’是一个单纯的概念,正象‘黄的’是一单纯的概念一样;正象决不能向一个事先不知道它的人,阐明什么是黄的一样,你不能向他阐明什么是善的”③。可以看出,以摩尔之见,“善”之所以不可分析、不可界定,乃是因为,“善”是一种最简单的属性(a simple property),是一种非自然的(non-natural)属性,或者说,是任何其他自然属性都无法取代的一种属性。虽然“善”与其他自然属性存在或此或彼的关系,但二者的分殊又无疑是根本性的和不可忽视的,倘若用其他的自然属性来取代善的属性,那就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
摩尔之所以批判自然主义谬误(或者自然主义),主要是因为:其一,自然主义无法为任何道德原则提供理由证明;其二,自然主义误导人们的思想,引诱人们接受错误的道德原则,从而完全违背伦理学的目的。摩尔的这一主张可以说既严厉地批判了以边沁(Jeremy Bentham)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从“趋乐避苦”的心理事实推导“功利原则”的做法,同时也成为英美分析性语言哲学的伦理学原则的出发点,其“自然主义谬误”批判在西方元伦理学领域也最早掀起了“是”与“应当”(或者“事实”与“价值”)的激烈争辩。
对于摩尔的论断,哈贝马斯作出了自己的评判。其认为,摩尔在论述评价性谓词(evaluative predicate)时,建构了一种非自然属性的理论,这种属性能够以理想的直觉(ideal intuitions)加以把握,或者能够通过“与把握事物属性的感觉方式相类似的”某种方式从理想的客体(ideal objects)那里读到。以这种方式,摩尔想表明,具有直觉意义的实质性规范陈述的真理(the truth of substantive normative statements)至少能够被间接证明。然而,摩尔的这种把典型的规范语句当作断言语句来加以表述的做法实际上把这种分析置于错误的轨道上。④ 另外,摩尔认为善的定义问题是全部伦理学的最根本的问题,且以往的伦理思想都试图给出“善”的定义,却又都陷入了自然主义的谬误之中。不过,摩尔虽指责人们在善的定义的问题上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可他自己在进行论证时却把非自然属性的“善”与自然属性的“黄”等同起来,亦即把规范性要求的陈述与真实性要求的陈述等同了起来。针对摩尔对两种根本不同的属性所作的混淆,哈贝马斯指出,“‘善的’(good)或‘正当的’(right)等诸如此类的措辞(expressions)不应与‘黄色的’或者‘白色的’等属性谓词(predicates of properties)相比较,而应与‘正确的’(true)等更高层级的谓词(higher-level predicates)相比较。”⑤
哈贝马斯从摩尔所举的“这张桌子是黄色的”和“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等例句出发,分析了道德判断和描述判断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指出,“(a)在既定的条件下,一个人应当说谎”这一命题可重新正确地表述为“(a′)在既定的条件下,说谎是正当的(或在道德的意义上是善的)”。以哈贝马斯之见,“很容易看出,句子(a′)中的谓词表述‘是正当的’(is right)或者‘是善的’(is good)较之于句子(b)‘这张桌子是黄色的’中的谓词表述‘是黄色的’(is right),起着完全不同的逻辑作用。”⑥ 一旦“善”这个价值谓词(value predicate)包含“道德上的善”(morally good)的含义,我们就能看出很明显的“不对称性”(asymmetry)。上述两个可比的命题也可重新表述为:(c)h是正当的(或者是命令的(commanded))和(d)p是真的(情况正是如此(it is the case))。
其中,h代表(a),p代表(b)。(c)和(d)这两种元语言学的重新表达(metalinguistic reformulatons)使得句子(a)和(b)所暗含的有效性要求变得清晰起来。通过(c)和(d)这两种句子形式,我们可以看出,谓词性质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the attribution of predicates)对解释内含于命题(c)和(d)中的有效性要求而言并不是正确的方式。如果我们想把正当性要求(claims to rightness)和真实性要求(claims to truth)加以比较,并不以一方同化另一方,那么,我们就必须澄清(clarify)p和h如何能够被奠基,认为(a)和(b)有效或无效的好的理由如何能够被提出(be adduced)。
在哈贝马斯看来,一言以蔽之,我们需要表明对道德命令证明而言,特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图尔明(S.E.Toulmin)清楚地看出了这一需要。哈贝马斯也赞同图尔明的看法,强调必须指明伦理学中的命令、告诫等道德义务论证的特殊性质。⑦ 对于上述问题,图尔明进一步指出了其症结之所在:“‘正当’(rightness)并非一种属性。当我问两个人哪种行为方式是正当的,我并不是问他们有关属性的问题——我想知道的是,是否存在选择这一而不是另一行为方式的理由。……这两个人在伦理学谓词情形中所需要的(或者他们都有的)相互矛盾的内容,就是他们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的理由。”⑧ 图尔明也清楚地看出,主观主义者对摩尔及其他伦理客观主义之弱点的回答只不过是同一个硬币的相反面。实际上,这两种阵营都是从这样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的,那就是,真理或者描述性命题的有效性规定着任何陈述得以被视为有效的意义。
基于此,哈贝马斯指出,一方面,“直觉主义者掌握道德真理的企图注定要失败,因为规范性命题(normative statement)既不能证实(verified),也不能证伪(falsified),换言之,不能以验证描述性命题的相同的方式来验证规范性命题。有鉴于此,可选择的做法就是对在实践问题上允许真理的观念加以全部拒绝(wholesale rejection)。”⑨ 另一方面,较之于直觉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当然不会否定这样一种语法上的事实,那就是建议人们就日常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一直保持争论,似乎这些争论能够基于正当的理由(good reasons)而被决定。但是,主观主义者却把规范与命令证明中的这种质朴的信任(naive trust)解释为源于日常道德直觉的错觉,显然又是错误的,故而,较之于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这样的认知主义者,道德怀疑主义者必须承担一项具有更高要求的任务,那就是他们必须解释我们的道德判断究竟是什么以及我们的道德情感究竟扮演什么样的作用。
二、对以史蒂文森为代表的“情感主义”的批判
摩尔直觉主义论证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直接促成了“情感主义”(emotivism)的出现。所谓情感主义,指的是持这样一种看法的学说:伦理学不过是个人情感的纯粹表达,道德判断不过是言说者个人情感、态度或者偏好的一种表达,或者说不过是情感宣泄程度不同的感叹句,比如“啊”、“哇”之类的感叹句,而道德判断与事实是截然二分的,事实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但道德判断仅仅是态度与情感的一种表达,根本就没有真假之分。同时,尽管人们仍然追求客观得到的标准,但任何这类追求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合理辩护。诸如,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认为,“从‘杀人是作恶的’这个陈述,我们不能推出任何关于未来经验的命题。可见,这种陈述不是可证实的,它没有理论意义,所有别的价值陈述也都是如此”。⑩ 石里克(Moritz Schlick)认为,价值只能建立在快乐的情感之上,道德判断无非是某种情感的一种反应。无独有偶,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也认为,伦理判断句除了表达感情、愿望外,并未说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它们纯粹是情感表达,并且因此就不归入真与假的范畴之下。”(11) 以哈贝马斯之见,情感主义这一分析的语言模式所认为的道德判断句不过是以第一人称句表达主观的偏好(preferences)、愿望(desires)和厌恶(aversions),或者是一个言说者试图使另外一个人以特定的方式而行动的命令。(12)
在语言哲学的伦理学传统中,最典型的情感主义伦理学的代表人物是史蒂文森。他的情感主义既发展了休谟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同时又深受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经验论与摩尔的分析哲学的影响,因而在方法上特别注重以对比人类日常语言中的道德话语与非道德话语之间的异同为其基本分析方法。较之于艾耶尔、卡尔纳普等情感主义者,史蒂文森情感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更强调判断或祈使句在语言中的功能是在因果关系意义上影响听者行为或情绪的观点,以及不像艾耶尔着重于我本人的感情与态度的表达,而是更强调以我的感受去影响你的情感与你的态度,强调价值术语的情感意义高于它们表达或暗示的任何事实信息。
在史蒂文森看来,一方面,道德语言的分析是伦理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因为,我们对道德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理解道德语言的问题,而道德语言和词汇,与其说是为了“劝导”,不如说是为了“表达”,同时,一个词汇情感上的意义(emotive meaning)就是该词汇的倾向(tendency);另一方面,道德生活中的伦理判断并非仅仅描述、记录或者揭示事实性的东西,而是主要表达人类的情感与态度。或者说,伦理判断的主要作用并非指出或者揭示某种事实,而是施加某种情感或态度的影响。作出伦理判断的主体不仅以判断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情感与态度,而且还以判断的方式把他们的情感和态度传递给听众,从而使听众与他们一起赞成或者不赞成某事物。而伦理判断之所以能够影响与改变人们的情感或态度,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情感意义起到了一种中介的作用。不过,“我们对别人的影响至多也只能达到‘粗略地趋近于’我们所期望的那个程度;我们不可能完全地达到我们所期望的影响别人的那种程度。”(13)
对于史蒂文森等情感主义者的这种分析的语言模式,哈贝马斯也给出了自己的评判。在他看来,“情感主义与命令主义的方法试图表明,规范性陈述之未明了的意义(unclear meaning)最终导源于经验性陈述或命令陈述的意义,或者是这两者的某种结合。”(14) 根据这种观点,规范性陈述的规范语义学内容,以规则的形式或者表达了主体的种种态度,或者表达了劝导的种种企图,或者兼而有之。也正是基于此,所以史蒂文森说,“这是善的”这一判断大致意味着“我赞成这个,因而如此做”(I approve of this;do as well)。通过这两个等值的判断,史蒂文森试图把握,表达言说者态度的道德判断的功能和道德判断被设计得可影响听者的态度的功能。(15)“很清楚,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基点在于单数第一人称或者说单主体那里。因此,情感主义仍在康德以来的意识哲学或主体哲学的视野范围内,而无从认识到规范存在的交互主体性特征。”(16)
三、对以黑尔为代表的“规定主义"的批判
无独有偶,在语言哲学伦理学传统中,规定主义者黑尔也如情感主义者史蒂文森一样把道德语言的分析视为伦理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也把日常语言作为伦理学研究的工作语言,不过,二者在理解与解释道德语言的性质和功能上却存在殊异,史蒂文森主张道德判断所表达的是判断者的一种情感或态度,而黑尔则认为道德判断所表达的是一种规定性。另外,黑尔较之于史蒂文森可以说更为深入地区分了“规定性”和“描述性”的语言(prescriptive and descriptive language),从而更加明确地分析了道德语言的性质。在黑尔看来,道德语言不是一种描述而是一种规定,或者说,道德语言的根本特征是“规定性”(prescriptivity),所谓“规定性”,指的是人们的日常道德语言中包含着道德原则指导、规定行为的根本特征。而规定性语言,就其要我们“做这个或做那个”的意义而言,乃是带有命令式的性质、祈使性语气的语言。而这两种规定性语言的命令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通常意义上的命令和规定,另一种是包含严格意义的价值性评判的表达语调,一种评价性的表示。(17) 可以说,黑尔特别强调道德语言的规定性,认为其高度体现了理性在道德判断中的地位与作用,倘若把道德判断归之为个人情感的纯粹表达,那就把这种判断变成了一种纯主观的东西了。
黑尔在《道德语言》(The language of morals)一书中强调,道德证明的形式即是从一个“道德大前提”(moral major premise)和一个“事实小前提”(factual minor premise),过渡至一个“道德结论”(moral conclusion)。诸如,在道德实践中,发现有人遭受不幸(小前提、事实),我必须去帮助他或她(结论、价值),其中在从“事实”到“价值”过渡的地方存在一个缺口,即隐含着一个大前提:我应该帮助不幸者。这个大前提当然也可以表现为其他三段论的结论。不过,在推理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将推理无限制地进行下去,而必须将推理的系列终结在某一行为原则上,而这一行为原则又是我们无法进一步加以论证的,如此,我们只好通过“选择”使自己为之承担责任。质言之,言说者所推荐的与所采用的规定,最终只能依凭言说者自己所任意采用的原则。正是在这一点上,黑尔的规定主义同情感主义一样,一旦遇到“终极原则”(ultimate principle)之类的问题,便认为判断不可能依靠论证,而只能诉诸“反判断”(counterassertion)。如此看来,黑尔的规定主义伦理学把行为者和说话者自身在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的时候所作出的“选择”,看作是我的道德价值批判行为的最高权威。如果说在事实性的问题上,真正的和正确的信念是独立于我的选择的话,那么,我们的价值判断则依据我们自己选择出来去强加于其上的那种标准。这显然是重复了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道德的主体同时又是立法者”的那种观点;只是这个道德主体通过讲出他规定的“法则”而成为“立法者”,他又通过讲出这个法规,而使之采取一种普遍性规定的形式。(18)
所以,不管是情感主义还是规定主义的伦理学,都一如存在主义者萨特(Jean Paul Sartre)那样,在用“情感”、“偏好”或者“选择”去说明价值评判时,都未在道德发展的历史中去探究“选择”的必要性的根源,而是把“选择”归结为道德概念本质本身。故而,他们实际上与萨特一样都从一个孤立的主体中心出发,都试图使自己的个人的道德性绝对化。(19)
哈贝马斯在批评黑尔的规定主义伦理学原则时,指出黑尔以综合命令(imperatives)和价值评判(evaluations)的方式,通过规范性的(“善”与“应当”)语句的分析,拓宽了命令主义的方法,并认为,黑尔所说的规范性语句中的中心性的语义学因素,“乃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言说者,规劝(recommend)或者规定(prescribe)听者从两种行为的可能性中作出某种选择。但是,由于这些规劝与规定最终以言说者任意接受的原则为基础,所以,这种类型的评价性语句(evaluative sentences)并不真的适合充当规范性语句分析的模式。”(20) 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黑尔的规定主义等于一种伦理决定主义(ethical decisionism)。在其理论中,证明实质性的规范句的基础是意向句(sentences of intention),也就是言说者借以表达其对原则的选择(最终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的语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选择是不容许证明的。”(21)
虽然在更狭义的意义上,黑尔的规定主义伦理学较之于情感主义和命令主义伦理学具有这样一个优点,那就是它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应该以理性来讨论道德问题。比如,黑尔这样强调道:“要在道德上成熟起来……就是要学会使用‘应当’语句,并认识到‘应当’一语句只有通过诉诸一种标准或一组原则才能得到检验,而我们正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决定而接受并创造我们自己的这些标准和这些原则的。”(22) 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所有这三种元伦理学的方法都得出了相同怀疑的结论。它们宣称,我们的道德词汇的意义,实际上在于表达某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如果以经验性语句、命令性语句或者意向性语句则能表达得更好一些。这些类型的语句,没有一类能够充当作出真实性要求或者任何需要论证的有效性要求的工具。就此而言,这即是对道德真理存在的信仰为何会被解释为一种幻觉,这种幻觉源自于日常生活的直觉性理解。一言以蔽之,非认知主义的方法一下子就剥夺了日常道德直觉领域的重要性。按照这些理论,人们只能以经验的术语来谈论道德问题。……它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经验性研究铺平道路,以及它们在这一前提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道德问题不容许有真理性以及规范理论意义上的伦理探究是无意义的。”(23)
四、对语言哲学道德理论批判的实质:清算道德怀疑主义
不难看出,不管是直觉主义、情感主义还是规定主义,实际上都仅仅局限于第一人称的话语之中,或者说仅仅停留于意识哲学的范围之内,都没有提出道德命题的有效性要求的条件问题,三者都只是把道德命题看作是采取更为合适的语言形式的意向性命题,又由于三者都忽视有效性要求的条件,不去研究道德命题的论证条件和具体形式,因而也就势必会陷入道德非认知主义之中,同时,这种道德非认知主义也必然会致使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怀疑主义的大行其道。
问题是,道德非认知主义、怀疑主义为何会盛行无碍?到底有没有克服、清算它们的有效路径?在哈贝马斯看来,伦理学领域之所以会充斥着道德非认知主义的迷雾,主要是因为有些人“还不相信行为规范在道德实践层面上能够得到证明”(24)。而“非认知主义立场主要依凭两个论据:其一,有关基本道德原则的争论通常达不到共识,其二,对规范性命题作真理性解释的所有企图都归于失败”(25)。这表明,非认知主义认为有关道德基本问题的争论一般都无法以正常的方式加以解决,争论各方也无法达成共识,另外,非认知主义还认为规范性命题不能要求被承认、被容许有真理性。在此,哈贝马斯无疑鞭辟入里地揭示了道德非认知主义的问题之症结,而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也长时间困扰着当今西方道德哲学界。
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麦金太尔(A.MacIntyre)对此也作了揭示,他把这种只有道德争论而无道德结论的现象称之为“道德语言的无序”,所谓“在我们居住的现实世界上,道德语言处于一种同样强烈的无序状态,正如我们描述的想象世界中的自然语言那样”(26)。在麦金太尔看来,道德语言无序的突出表现就是道德哲学方面的争执,而道德哲学争执中最令人瞩目的特点则是其“无终结性”(interminable character)。所谓“无终结性”,顾名思义,即意味着相互冲突的道德争论持续不断、没完没了,在此态势下,它们不可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或者说,当代西方文化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人们在道德上达成一致,当代所有的道德争论都不会产生出一个合理的结论,所有的道德分歧也都不会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而所有这一切无疑又意味着当代西方社会业已陷入了深深的道德危机之中。这种道德语言的无序如果进而言之,有两个核心表征:“一是概念五花八门(multifariousness),并且明显地不可通约(incommensruability);二是分歧双方若欲结束争论,就必须肯定地使用最终原则。”(27) 以麦金太尔之见,情感主义最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当代道德语言的无序状态,而克服这种无序状态的不二法门就是向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传统回归,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话语中找到共同一致的基点。
与麦金太尔向传统回归来克服道德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做法不同,哈贝马斯力主从当代西方道德文化资源的内部开显出普遍有效的原则与方法来驱散道德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迷雾。在哈贝马斯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指定(name)一个原则,它可以使道德论争原则上的一致成为可能,那么,第一个论据也就失去了其力量。如果我们放弃这样一个前提,即在与有效性要求相关联的程度上,规范性语句唯有在命题真实性(propositional truth)的意义上才能有效或无效,那么,第二个论据也就不能成立(fail)。”(28) 在此,哈贝马斯想表明的是,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理性的意义与必要性,以理性为基础来确立一种普遍化的道德原则,并通过合理化的论证来确立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就可以抑制直觉主义、情感主义对伦理学的侵蚀,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唯有以理性的方式探究道德规范的有效性要求,方能使之具有一种普遍性的超越形式。(29) 哈贝马斯对“普遍化原则”的探究即是在这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放弃把道德规范的有效性等同于命题的真实性的做法,放弃用反映论的模式来证明或证伪规范的有效性要求的做法,不把真实性要求看成是规范性陈述的唯一标准以及不以真实性取代规范性,就有可能消解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和命题的真实性二者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从而使我们的道德探究重新步入道德认知主义的轨道。而要明辨这一问题的实质,有必要回到前面所言的如何对待“是”与“应当”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去。事实上,也只有以新的方式处理“是”与“应当”的紧张关系,才能真正清算道德怀疑主义。
收稿日期:2009-03-02
注释:
① [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09-510页。
② 关于“应当”不能从“是”推出来,或者说道德不可能通过事实的科学来加以证明这一西方哲学特别是伦理学中的重要议题,也并非完全不存争议。根据汤姆·L·彼彻姆的研究,西方伦理学史上有关这方面的争论至少可分为五大基本派别:一是自然主义,它认为一切价值判断都可还原为事实判断;二是直觉主义,它在否定“应当”陈述能够从“是”陈述中推导出来的同时认为价值原则上是被直觉证明的,或不证自明地被人察知的;三是情感主义,在情感主义者看来,“我们的基本道德判断和原则,是以本身就缺乏任何事实信仰支持的态度为依据的——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方法合理地说服我们放弃它们,也没有方法提供对它们的最终确证”([美]汤姆·L·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道德哲学引论》,雷克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38页);四是规定主义,黑尔的规定主义伦理学“沿袭了休谟及其他非认知主义者区分事实和价值的观点。价值判断被看做是具有规约的或行为指导的功能……相反,事实论述不是行为指导,而只能作为对人类或自然现象的描述以及对它们原因的解释。所以根据规约主义(规定主义——引者注),这两个领域中的陈述表现出不可逾越的逻辑上的区别”(同上书,第539页);五是描述主义,福特(Philippa Foot)等人的描述主义一方面“不主张价值实际上就是事实。价值不能还原为事实,而事实也不能还原为价值”,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价值与事实在逻辑上是相联系的,所以,要把它们分成具有不同‘功能’的两种不同的类型是毫无意义的”(同上书,第548页)。
③ [英]摩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页。
④⑤⑥⑨ Jürgen 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01,P.52-53,P.53,P.S3,P.54.
⑦ 高宣扬:《哈伯玛新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416页。
⑧ Toulmin:An Examination of the Place of Reason in Eth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28.
⑩ [美]M·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杜任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0页。
(11) [英]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尹大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3页。
(12)(14) Jürgen 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01,P.54,P.54.
(13) 高宣扬:《哈伯玛斯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418页。
(15) Jürgen 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01,P.55.
(16) 龚群:《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5页。
(17) 高宣扬:《哈伯玛斯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418页。
(18)(19) 高宣扬:《哈伯玛斯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421、421页。
(20)(21)(23) Jürgen 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01,P.55,P.55,P.55-56.
(22) [英]黑尔:《道德语言》,万俊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88-189页。
(24)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25)(28) Jürgen 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01 ,P.56,P.56.
(26)(27) Alasdair MacIntyre:After 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Notre Dame,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1,P.2,P.34.
(29) 值得一提的是,黑尔也特别强调“理性”在伦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十分强调道德判断必须具有“可普遍化性”(universalizability),强调一个道德判断如果不具备可普遍化的能力,那么也就难以保持其自身的“规定性”(prescriptivity),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理性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应该说,黑尔的主张与哈贝马斯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二者的分殊也是非常明显的,黑尔的规定主义是建基于个体性的逻辑推理的前提(自我选择)之上的,从而缺乏一种互主体性的维度,而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则反之,即其建基于交互主体性的逻辑推理的前提(普遍对话)之上的。
标签:哈贝马斯论文; 语言哲学论文; 伦理学论文; 史蒂文森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语言描述论文; 语言表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