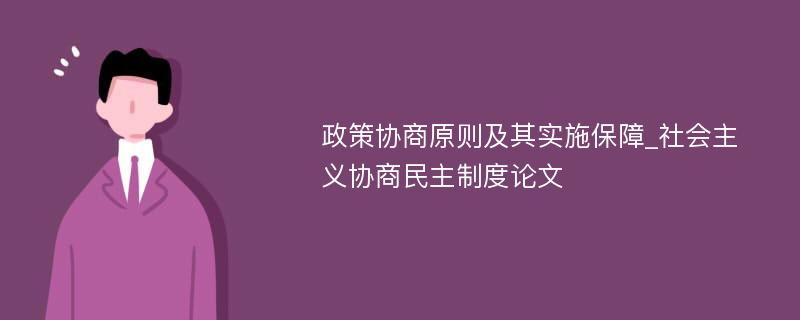
政策协商原则及实施保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则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公共决策所追求的两大目标。但现实的情况是,既不民主也不科学的决策不仅削弱政策执行力,损害决策部门的公信力,甚至会危及地方执政当局乃至整个政府的合法性。目前,较为通行的解决方案似乎是民主选举+代议政治+专家咨询。然而,选民与决策和管理的分离,专家咨询的有选择性和随意性等又降低了这种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所以到目前为止,能够改善这种方案的办法似乎就是引入协商政治了。 以协商性改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一思路得到了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的大力支持。简单地说,协商民主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①的过程。协商民主理论家不仅要求公民民主地选择政府领导人,而且,还要求公民广泛地参与决策过程。他们希望公共决策不仅要追求民主原则和体现多数人的利益,而且还要追求理性原则,考虑和协调社会各方观点和利益,努力使公共政策能够为社会各方所接受。 协商政治不仅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一条理想原则,而且也是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协商政治是在不同党派共同建国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从最初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层面的政治协商会议,到当今基层社会的民主恳谈,都是具体的实践形式。2013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并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那么,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哪些问题?坚持什么原则?本文试图在梳理协商民主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予以回答,并集中探讨政府公共政策决策中协商民主机制的建立问题,从协商主体、协商范围、协商程序、协商效力四个方面考察如何建立一个整合的、有效地、合法的政策协商体系。 协商民主的应用 “民主”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生活的价值。但民主作为一个正面词,其实是相对晚近的事情。达尔就指出,“直到20世纪以前,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声称非民主体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优越性”。②20世纪见证了民主理论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发展,但与民主的胜利相伴随的是对民主的激烈批评和对民主危机的深深忧虑。对民主的批评不外乎从两个向度展开:一个是批评当前主导的代议民主是对实质民主(substantive democracy)的阉割,以至于堕落为“选主政治”(electocracy);另一个是根本否认民主是一个可欲的东西,以决策和管理的专业性、科学性否定民主的道德正当性。 古希腊雅典的城邦民主是现代民主的历史先声。现代政治秉承了民主的原初含义,更渗透了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和公民权利理论,给民主套上了宪政和法治的辔头,让民主不至于肆虐泛滥而沦为“暴民政治”(mob rule)或“多数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现代民主要走出城邦范围的限制,使之在现代民族国家范围内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民主与代议制的结合就成为现代民主运作的实际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是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是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ism democracy),是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实际上,这三个概念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现代民主的本质,其指向都是同一种民主形式。一如任何理想和现实之间必然存在落差一样,民主的理想和民主的实践之间也总是存在差距,这就注定民主从理论落实到实践上时总会有各种局限与不足,需要面对各种批评,也会面临各种危机。在西方语境中,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段以来,民主实践遭遇了以下诸多困境:(1)民主政体下民众对政治人物和政治制度的信任和兴趣在下降,公民政治冷漠增强,公民政治参与度降低;(2)公民认为选举政治背后存在政治操作,利益集团和寡头政治难以克服;(3)公民之间的互动和信任存在问题,集体行动困境普遍存在,政治犬儒主义(political cynicism)广泛扩散。因此,如何调动和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培育公民的政治信任,改变公民“独自打保龄”的状况,从而“使民主运转起来”,成为西方民主国家解决“合法化危机”(legitimization crisis)的重要任务。 在上述背景下所兴起的协商民主不是对代议民主的替代和超越,而是对现代民主的深化和发展。协商民主理论家德雷泽克(John S.Dryzek)就明确表示,协商民主是自由宪政语境下的产物,协商的原则就是为了增进自由主义权利,而宪政自由主义也促进协商的开展③。协商民主从现实世界民主之不足这一向度来对现代民主提出批评,体现了对代议民主的深刻反思,是一种对民主的民主批评(a democratic critic toward democracy)。协商民主理论家希望以“协商性”补救代议民主之偏差,以公民参与协商提高公民的公共理性,以协商程序来保障人民主权,藉此重新提振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尽管对协商民主也有怀疑和批评的声音,但协商民主理论已在民主诸理论中蔚为大观,因此,德雷泽克把这种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热的现象称之为民主理论的“协商转向”(The deliberative turn in democracy theory)④。 协商民主调动公民积极参与政治,通过协商揭橥个人的真实偏好,通过理性对话和话语交谈来实现偏好转型(Transformation of preference),达致协商和偏好聚合(deliberation and aggregation)的结合。针对不同议题,协商民主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展开:(1)宏观层面,围绕国家的宪法制定、是继续保持国家统一还是准许分离主义得逞以及政体选择等根本问题,为达致社会团结、维护国家稳定而展开的政治协商;(2)中观层面,在政府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为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而进行的政策协商;(3)微观层面,也即在基层和社会层面,为打造良好的市民社会和基层社会秩序,围绕公民自治或社会治理问题而展开的社会协商。 中国协商民主理论的引介与发展几乎与国际保持同步,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中国语境中,协商民主理论被加入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话语(socialist democracy rhetoric)建构中,而且协商政治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实践也在三个层面展开:(1)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定、中国共产党与其它党派的共存合作等关系到国家基本政治制度选择的政治协商;(2)围绕政府以及各个部门的具体政策决策、方案选择、财政安排而展开的政策协商;(3)为实现社会和谐、基层稳定,围绕乡村自治和社会治理而开展的基层自治协商。改革开放以来,推进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一直是中国改革追求的重要目标。但囿于种种原因,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仍然面临繁复的问题,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将协商民主理论引入到政府公共决策中来,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通过多种形式和多种渠道展开政策协商就彰显出更加重要的价值。 政策协商的主体与范围 为协商民主辩护有不同的理由,或者认为其本身就是一种目的(ends),值得珍视;或者认为其是一种手段(means),体现为促进和提升其他价值和目的的工具性意义(instrumental reason)。无论是作为目的还是作为手段,协商同其他人类集体行动一样,都是有成本的,都涉及成本—收益计算(cost-benefit analysis)。因此,就必须考量协商的规模和程度问题,即要符合伊安·沙皮罗(Ian Shapiro)所谓的“最优协商”(optimal deliberation)⑤原则。 何为政策协商?简言之,就是多元行动主体为实现公共政策与民意的契合而本着积极参与、相互尊重、理性对话、平等协商的态度,围绕具体公共政策决策进行的商谈、对话、讨论,就公共议题的设置、公共政策的方向、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等公共政策涉及的诸多内容和环节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在进行政策协商时,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协商主体和协商范围,而协商主体和协商范围的确定又需要遵循相应的原则和机制。 所谓协商主体(deliberation subject)就是指参与协商的各方。一般而言,政策决策者、利益相关者、政策关切者、普通公民等是一般意义上政策协商的主要参与者,都属于政策协商的主体。政府决定做或者不做某项公共政策,可能具体涉及到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年龄层次的公民的利益和福祉,因此在政策协商时,协商主体的选择就对协商本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考虑到任何的政策协商过程都存在交易成本问题,因此,在具体的公共决策中的民主协商的主体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进行: 利益相关方原则(the interested parties)。在科恩(Joshua Cohen)看来,协商民主其实是一种合法性理论,协商结果的正当性来自于协商的参与者对协商议题是否有效表达了真实的想法和诉求⑥。政府决策的合法性主要取决于利益相关者对这一决策的认受程度。任何的政府决策都必定涉及相应的人群和范围,因此,受政府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和诉求必须得到表达和倾听。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绝非仅仅指政策直接涉及的人群,还需考虑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等多方面因素。在一般的政府决策中,往往存在两种极端情形:一是忽视受政策影响者的权益和利益诉求,只是从政府和部门利益出发,简单、粗暴、草率地推出一项政策,在政策执行受阻后,要么出动强力部门强行执行,要么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这些年这种情形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决策中常有发生,尤其是地方政府涉及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工程上马等方面的案例并不鲜见,新近中国股市调控政策也可算作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这种情形的后果是,要么引发激烈的官民矛盾,要么使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和严肃性大打折扣,减损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而为以后的政策执行带来巨大难度。另一种极端情形是,政府或部门为了缓解自身压力,把本不应该协商或参与的人群纳入到政策决策中来,形成人数上的优势以使得政策得以通过。这种情形损害了公共政策真正相关人的公民权利和利益,一些地方的危改拆迁政策出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⑦。开展政策协商的根本目的在于发现公民真实的利益诉求和意愿所在,提高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和科学性。必须明确的是,一方面公民的权利要保障,但另一方面,任何公共政策都带有强制性,既不能忽视公民权利,也不能罔顾政府决策的权威性,滥用民主机制。 民主性与专业性相结合原则(democracy and expertise)。在一个民主大行其道的时代,民意和民主的价值当然必须尊重。但有必要指出的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分工、行业分化不断加深,政府决策面临的复杂性也极其巨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呈现出高度的专业性。这就要求政府决策时需要将民主性和专业性相结合,政策协商一方面要考虑和尊重民众的声音——代表民众对自身利益和偏好的判断和表达;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专业知识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代表专业智识对社会复杂性和决策科学性的认知和理解,通过政策协商寻求民主参与和专业知识之间的均衡。之所以强调专家决策是因为:其一,从社会现实出发,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向前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趋势和要素,将人类社会带人极其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在前现代时期,一个统治者或许可能通过修身养德、清静无为而垂手而治,但在现代社会这几乎不可能;其二,从公民角度出发,现代世界民主的胜利实则是庶民的胜利,个体的声音是民主提倡的价值,也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但与此相伴的是,一直有另一种反思或批评的声音,即公民何以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当家做主?从古希腊苏格拉底之死到今天“阿罗不可能定理”,这些讨论都提出了对民主的怀疑,即民主可能会带来社会无政府主义(social anarchism)和精神无政府主义(intellectual anarchism),民主之结果可能是一种民主谬误(democratic fallacy),或者说民主非理性主义(democratic irrationalism)⑧。不管表述如何,这些都提醒人们,公民的政治参与需要学习、需要信息、需要技能;其三,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实际运行的政府决策模式基于某种寡头式的权力结构(oligarchic power structure),部分政治人物和知识精英或技术精英对政府决策起着实际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因此,民主的背后其实是福柯所批评的“隐藏的等级结构”(hidden hierarchies)⑨,这是人类公共政策制定无法回避的现实。政策协商必须考虑决策的复杂性,一方面要考虑和尊重民众的声音,但同时也要重视专业性知识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协商民主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它不是对公众的偏好进行简单地加总和聚合(calculation and aggregation),而是通过协商,在对话和协商中揭示公众的真正偏好,实现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数人利益和少数人权利的有效契合。在政策协商过程中,尊重民意,也尊重专业性知识,实现民意与专业性(democracy and expertise)、偏好与技术(preference and technical)的有效结合是制度和机制设计的关键。 代议性表达和参与性表达相结合原则(representative expression and participatory expression)。所谓代议性表达就是指公民的偏好、意愿、选择倾向由其所授权的代表或机构来表达;所谓参与性表达是指公民个体通过实际的个人参与投票、协商、议案等方式来亲自表达。任何大型的人类社会组织都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公共政策决策中的参与和效率问题。现代民主是近代以来为应对这一矛盾而发展出来的解决方案,是民主机制和代议机制的有机统一。但代议民主本身又必须面对民主性不足的批评,因为一直有批评认为代议民主本身背离了民主理想,是对民主的阉割和异化。“阿罗不可能定律”表明公众的偏好不能由简单的横向加总来发现和定义,所以,协商、对话、妥协和寻求共识才成为必需。协商民主实则是在代议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寻求一种新均衡。但是,协商民主须谨防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议而不决、商而无果。政策协商的最终结果是要决策,而任何协商又都有成本;协商主体的规模越大,越不容易达成共识。因此,在实际的政策协商中,协商主体选择的范围和规模必须按照成本和效益原则有所限制,才能实现公共决策的代议性表达和参与性表达的结合。此外,情感(emotion)和情绪(passions)历来是政治行为基本动力,在政策协商中,一些情绪协商参与者(passionate deliberation participants)会影响协商正常和理性的开展。而且,在协商过程中,也容易出现所谓的“意见领袖”,使协商被引导或偏转。例如,由于上位的民主政治和下位的社会自治之间以及公民精神的培养离一个健康、成熟、理性、妥协的政治文化氛围有较大差距,而现实政策又遗留和累积了诸多不足和矛盾,政策协商很容易造成“参与拥堵”和具体决策被“情绪参与者”(passionate participants)所绑架和左右的现象⑩。这种状况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尤其值得注意。 在回答了政策协商的主体选择问题之后,接下来需要确定的就是协商内容。并非所有的政府决策都适合或者必须进行政策协商。哪些协商政府应该开展、鼓励甚至要求公民付诸努力?这就涉及政策协商的范围问题。所谓协商范围(deliberation scope and scale)是指政策协商开展的内容与程度。毫无疑问,协商同其他商谈形式一样,既有可能产生好的结果和影响,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和负面影响。在关注协商如何开展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就是协商什么?必须明白的是,协商民主的兴起是民主的深化和发展,是政治文明的进步,但这并不能否认,在一定的社会语境、发展阶段、政策环境下,有些公共政策适合协商,而有些公共政策不适合协商。这也就是说,政策协商的事项范围必须要确定。一个一般性、原则性的回答是,“政府应该把有助于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协商形式最大化,而把改善人们生活无益的协商形式最小化”(11)。具体而言,政府的决策涉及国家安全、公众安全、保密性和时效性等公共决策时,一般不适用较大规模的政策协商。国家安全、公众安全和保密性这三个要素比较易于理解,而时效性可能需要特别说明。当政府政策面对的是转瞬即逝的时间窗口和机会窗口时,政府决策必须当机立断,以防延误时机。面对这样的事情,政策效率压倒了参与的要求。 涉及国家安全、公众安全和保密性的事项,必须按照法治的原则来规范。国家必须依照有关法律对何为涉及国家安全、公众安全的事项做出明文规定,对那些涉及保密性的公共政策也必须进行明确法律界定,以防止权力部门以国家安全、公众安全、保密性为借口,为决策不民主、不透明做掩护。对于涉及时效性的公共决策,决策部门也必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事后补充,履行相关程序和做出决策说明。此外,还有一些政策,涉及宗教、文化等相关敏感议题,在一个社会分化严重、民族矛盾潜伏、文化异质性高、地区差异性大的国家进行上述问题的决策时,是否引入政策协商机制也需要审慎考虑。因为议题选取或操作不当,就可能激化民族间、宗教间、不同文化间、不同地区间原本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反而不利于形成理性和彼此尊重的社会氛围,不利于达成妥协和共识,不利于促进政治和解。这样的结果与协商民主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协商范围还包含协商的程度,即协商到什么程度为止。协商民主的本意是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公民之间的理解,以达致一种共识性结论。但现实的情况是,协商的人群越大,达成一致性意见的可能性越小;协商的程度越深入,协商达致共识的可能性也越小。出于政策效率和成本考量,当协商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协商代表的参与性表达就需要让位于代议性表达,甚至让位于权威性决策机构的果断决策。 政策协商的程序与效力 在协商主体和协商范围确定之后,就必须考虑政策协商的程序。简言之,协商程序(deliberation schedule and process)是指协商按照什么样的日程安排、协商流程、协商步骤来进行。政策协商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形式也多种多样。在目前已有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协商日、陪协团、共识会议、民主恳谈会、听证会都是政策协商常见的方式。 协商日(deliberation day)是斯坦福大学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菲什金(James S.Fishkin)教授提出的一种协商方式,在该方式下,定期或不定期安排专门的一天用于政策协商,简称协商日。在协商日当天,协商各方围绕协商主题展开对话、讨论、沟通等(12)。陪协团(citizen jury)是指为制定一个决策,从公民中挑选出一些人组成一个团体或小组,该团体或小组成员倾听专家关于协商议题的讨论,向专家提出咨询之后,在本小组或团体成员之间进行协商、交谈、沟通,最后做出决定(13)。这种形式最早在北欧和美国较为普遍(14)。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是北欧的丹麦发展起来的一种协商形式,它召开一个持续几天的会议,让参与者自由选择对某个或某几个议题进行发言,然后就一些议题达成共识。与相对封闭的陪协团不同,共识会议的协商方式向公众公开和开放(15)。民主恳谈会和听证会在中国已经多有开展,毋庸赘述。 原则上讲,一般的公共政策涉及决策、实施、反馈、评估等环节,政策协商也应该贯穿这个过程的始终。不管政策协商选择什么方式,但就协商程序而言,必须从协商前、协商中、协商后三个阶段来进行协商民主程序建设。协商民主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公民对话、协商,发现和转化自己的真实偏好。任何一个政策的做出,都需要有相关的信息和知识,而政府部门和专家对决策所必须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与公民协商参与者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存在不对称。为了能够使普通公民协商参与者能够有效协商,必须对协商前相应的准备程序做出明确的规定。对政策协商的参与主体各方而言,要能够理性、积极地参与政策协商,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掌握相关信息和材料,这就要求政府在决策前向社会和公众公布和公开相关信息和材料,使得公众在协商前获得相关资讯,为有效协商做出知识和信息准备;同时,在协商进行前政府还要与社会公众进行互动,就协商参与者的选择、协商议程的设定、协商具体程序达成方案。具体协商过程需要有明确的流程和方案,协商过程要兼具规定性和灵活性,要借鉴国外经验和地方探索的成功案例。另外,在协商过程中,要采用情况说明、专家学者咨询、专题座谈等多种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具有操作性、可复制性、可预测性的协商程序。在协商后,要避免政府决策者只是把政策协商视为一个走过场的公关秀,要让协商中的民意、专家意见等落实和反映在决策结果上。最后,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要随时向社会公众、相关人士通报和公开政策执行进程和进展情况,就政策执行中的难度和问题及时向社会和公众反馈,使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能形成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和协商,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方案。 协商民主有三大初衷:其一在于通过公民协商来重新实现或更进一步体现人民主权,以重塑政治合法性;其二在于通过公民参与、协商、对话来重塑公共领域和公民身份,建设一个更加活跃的市民社会;其三在于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增强对政府的问责,以改善政府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和回应性(responsiveness)。政策协商要体现协商民主的价值,需要将协商的效力体现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结果和效果上,避免政策协商的过场化和表面化。所谓的协商效力(deliberation effectiveness)就是指协商与最后政策制定之间的关联度。有效的协商就是能够将协商结果反映到公共政策上。有效的协商既要防止政府决策走向专断和草率,又要避免政府决策走向民粹化,它需要专家的专业性知识、政府当机立断的决断力和民众真实有效的参与。现实中常见的情形是,由于政府与民众之间信任度不高,政府对民众持防范态度,遇事喜欢上纲上线、贴标签、戴帽子,于是本来可以协商解决的事情最后却以矛盾激化、事态升级而结束,极端情况甚至演变成政府与民众的严重对立;同时,由于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不高,因此,对政府具体政策执行的理解、支持和合作不够。为缓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减少政策执行难度,政府在政策协商时往往出于策略性和工具性考虑,政策协商在一些时候流于形式和过场,其效力极其有限。要真正发挥政策协商的功能,就需要珍视协商民主的价值,把协商和决策结合起来,同时要把事后问责与政策协商结合起来,避免商而无果、束之高阁的情况出现。总之,只有协商前、协商中、协商后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才能促进政策协商常态化、程序化和规范化。要真正体现政策协商的效力,根本点在于政策协商的制度化(16)。通过政策协商的问责制度去落实政府决策中的协商效力,发挥政策协商对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积极作用。 结语:中国政策协商空间 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在治理方面的重要差异表现在公共决策的包容性上,而公共决策的包容性主要体现为决策过程的开放性,其制度安排的主要形式就是“代议民主+协商民主”。 在西方民主国家语境中,协商民主建立在对代议民主或自由民主的反思和批评之上,算是古代雅典式直接民主的现代回响。有研究指出,协商政治与协商民主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一般来说,协商民主被从三个方面解释:第一,将协商民主作为政府形式;第二,将协商民主看作是决策形式;第三,将协商民主看作是治理形式(17)。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中国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都有着很大的空间。 中国的协商民主在国家制度层面、政府政策层面、基层社会治理层面都有开展。本文集中考察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原则和机制建设问题是基于如下判断: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如果进展良好,有助于推进中国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也有助于塑造现代公民,培育公民文化,实现基层社会的良善治理。 不过,反过来讲,中国政策协商的有序推行和良性发展也有赖于宏观层面的政治发展和微观层面的社会建设。有学者借鉴金耀基论述港英殖民时代香港政治所使用的术语“行政吸纳政治”来论述今天中国的行政与政治之间的关系(18),这种论述可能反映了今天中国的政治与行政之间关系的特征。然而,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行政确实可以吸纳一些政治问题,但恐怕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行政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其背后政治问题的解决。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和政策体系,有助于一个健康社会的成长;反过来,一个政府和政策体系要能够健康有序地运转,也需要有良好的公民文化和公共空间的支撑。 进一步而言,政策协商机制的建设与一个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回应性政府建设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只有一个真正的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回应性政府,才有可能建设起一套真实的、制度化的政策协商的民主机制,而政策协商民主机制的建设又是具体而微的落实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回应性政府的切实举措。 中国语境的协商民主与西方语境的协商民主自然存在差异,既不宜简单比附,也不宜互为否定。民主“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问题”(19)。民主通常也被看作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它从不完善、不成熟到较完善、较成熟,在不同的时段会有程度上的差异。 中国协商民主对于改进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密切联系群众”是有帮助的,不过,从完整的过程来看,没有选举民主作为制度保障,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的实现方式其实际效用也不敢高估。因为,协商民主需要有制度化的安排,包括选举制度的保障。如果没有选举民主这个“抓手”,协商民主就会呈现很大的随意性,而何时何事与何人协商以及协商结果如何有效等一系列问题就会成为问题。 ①俞可平主编:《协商民主译丛》,“总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②Robert A.Dahl,On Democra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44. ③④John S.Dryzek,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Liberals,Critics,Contest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8-16,p.1. ⑤(11)Ian Shapiro,Optimal Deliberation,in James S.Fishkin and Peter Laslett edited,Deba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3 p.121 p.121. ⑥See Joshua Cohen,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in Alan Hamlin and Philip Pettit edited,The Good Polity,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pp.17-34. ⑦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7-06/04/content_6193747.htm。 ⑧(14)See Gerry Mackie,Democracy Defend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chapter 1,A Long,Dark Shadow Over Democratic Politics,p.91. ⑨⑩Frank Fischer,Democracy & Expertise:Reorienting Policy Inqui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55 p.272. (12)Bruce Ackerman and James S.Fishkin,Deliberation Day,in James S.Fishkin and Peter Laslett edited,Deba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3,pp.7-30. (13)陪协团一词是仿照陪审团而翻译出来的,也许不一定精确,但尚未找到更好译法,故采用此译。 (15)See S.Joss,Evaluating Consensus Conference:Necessity or Luxury,in S.Joss and J.Durant edited,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The Role of Consensus Conference in Europe,London:Science Museum,1995 pp.89-108. (16)See Mark E.Warren,Institutionaliz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in Shawn W.Rosenberg edited,Deliberation,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Can The People Govern? New York:Palgrave M Avmillan,2007 pp.272-288. (17)参见陈家刚《协商政治与协商民主的内在关系》,《人民政协报》2012年10月17日。 (18)强世功:《“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香江边上的思考》,《读书》2007年第10期。 (19)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76页。标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公共政策过程论文; 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协商民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