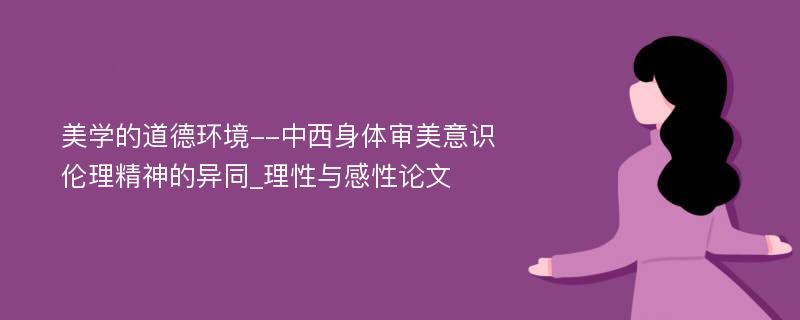
审美的道德之境——中西形体审美意识的伦理精神之同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体论文,中西论文,伦理论文,之境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所具有的自觉社会意识,使它在认识和实践的各个领域都无以逃避各种道德力量的辖制。人类形体审美意识及其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就具体体现伦理因素的普遍性、响应特定道德观念及其力量要求而言,中西形体审美意识还是有许多同异。
一
中西方人类经历着同样的生活过程,其各自形体审美意识中也常常反映出相似或相近的伦理精神,这首先就表现在它们都包含有“朴素为美”的道德理想。
中国人在形体审美方面力主“素以为绚”,强调真正美的人体在于归返内心、不饰粉黛的天然本色。如果说,这就是中国形体审美意识的基本伦理精神,则其中已然呈现了中国人对于形体美的总体追求意识,即培养和欣赏形体美不应执着于身体细节的感官享受,而要深入以朴素自然为核心的生活规范,通过对自然身体形式的感受来理性地领悟道德存在。“揽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润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1] 这种对形体美的把握,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求达到对道德极境的内心喜悦,“天然去雕饰”而臻于内在心灵的完善。对人的身体形象的观照由此转化为一种对内心道德的朴素要求。
同样,我们在西方世界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朴素为美”的形体审美理想。普洛丁说:“当你在反省自己或观照别人时见到了心灵的伟大,性情的正直,自处的纯洁,一副坚强面孔所特有的大丈夫气,一种镇静肃穆冲虚的心情所洋溢的尊严和谦逊,尤其是那种神圣的理性的光辉时”,“因为它们既然存在又显现出来,所以凡是见到它们的人,莫不说它们才是真正的实在。真正的实在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是美”[2]。依据这种形体审美中的道德自觉,西方人力图深入人的内心世界而发现道德“无色的光辉”,以为深入于这样的境界则无一不足、无一多余。所谓“天生的丽质,即使洗尽铅华,也无须腼腆”,就是涉入内在道德之境、体照朴素之光的形体之美。而对于认真寻求和感受形体美的人来说,最要紧莫过于领会“朴素为美”的道德理想,由此得到最高的和神圣的形体审美享受,在理性上切实体会到作为“美本身”的形体美之“朴素”理想“就是一切所依归,一切所仰望,一切因它而存在,而生活,而思维,因为它就是生命、理性和存在的原因”[3]。如此,则一个人“看见肉体美,就不该去追逐,但是如果知道这些肉体美只是镜花水月的幻象,就应该去追求那些幻象所反映的美本身”[4]。
其次,中西形体审美意识共同规定了物质身体形式与精神心灵的统一关系,强调形体美绝非单纯的肉体形象,还包含有重要的心灵因素。用鲍桑葵的话来总括这一观念的基本要求,即“人体如果不表现人的品质,又何以成其为人体呢”[5]?
《国语》讲过一个故事:“阳处父如卫,反,过宁,舍于逆旅宁嬴氏……(宁嬴氏)曰:‘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6] 这里,身体形式只是“情之华”,即某种外在感性形式,真正的形体美则是“言文相合”,即内在心灵与外在形貌完美统一。所谓“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便分明规定了心灵与身体外形的统一契合关系,单纯追求其中某一方面将产生形体审美意识的分裂。由此,在形体审美意识的伦理深层,中国人展现了特定的道德一统化意识:要求形体审美必须贯彻心灵与身体形式的统一契合,实际就是要求贯彻道德意识于形体美的欣赏和培养,以道德力量及其具体原则为最后的根源和本质。这一点,也恰是传统儒学道德观的明确表示。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已是相当明确的形体审美原则,所要求的是以道德的“善”(仁)支配身体的外在形式。所以,孔子“尽美矣,又尽善”的审美理想,即是音乐审美的主张,同时也灌注在中国人的形体审美活动中,成其为形体审美意识的根本理路。以这种伦理精神规范形体审美活动,则《世说新语·容止》篇中嵇康不但外形上“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心灵方面更是“高而徐行”,“岩岩若孤松之独立”[7],身体形式完善地统一着心灵内部的高拔之美。又于是,在艺术创造中,“貌虽端严,神必清古,自有威重俨然之色,使人见则肃然,有归仰之心”,而不能仅止“贵其姱丽之容”,以“取悦于众目”[8]。
西方形体审美意识也一定地坚持了这种心灵与形式统一的伦理本质。“心灵既然是一种神圣的东西,而且,是美的一部分,凡是它所能控制和统辖的一切东西,心灵都使之美乎其美,尽可能参与了美。”[9] 人体不但是物质的存在,也是精神的负荷,它是心灵所“能控制和统辖的”;心灵参与身体形式的培养、追寻形体美的心灵与肉体统一性,就是根本的选择。当心灵之美成形于一种完善道德之境,普照出令人神往的理性光辉;当心灵在冷静纯洁的理性中放射出智慧光彩,人对自身形体的欣赏便不是赤裸裸地实现感性的纯粹享乐,而是对心灵与肉体结合的感性对象的理性发现。至于实现了这种完美统一的人体形象,“非但康强健壮,经得起人生的打击;非但社会的成规和周围的冲突无法束缚他们,玷污他们;非但结构的节奏和姿态的自由表现出一切行为与动作的能力;而且他们的头、脸、整个形体,不是表达意志的坚强卓越,像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便是表达心灵的柔和与永恒的和平,像拉斐尔的作品;或者表达智慧的超越与精微玄妙,像雷奥那多的作品”[10]。
这种强调形体审美的心灵与肉体统一的伦理精神,在西方世界中确已成为一种普遍理性。当我们考虑到培根《论美》所说的:“如果美碰巧落在一个正直的人身上,它也一定会使他的德行放射出光辉,使他的罪过引起面孔上羞惭的红晕”[11],是根据形体美的物质存在和心灵精神统一而实现的某种道德意识升华与品质显现,其中包含了深刻的伦理自觉和道德优化理想;那么,再来理解博克所谓“谦虚是对不完善或有缺点的默认,它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可爱的品质,而且也确实加强其它可爱品质的效果”[12],就不难发现,他们其实都力图把人的内在修行与形式可爱的身体放在一起加以褒扬。内在品质的道德性之所以能和肉体物质性结合而构成身体形象的审美完整性,就在于它不仅“可爱”,而且足以强化身体外在形式的感性审美效应,突出身体之美的完整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形体审美的本质就是对人之为人的社会利益的肯定——人的身上统一着物质与精神的完整性、感性与理性的密切内容,所以从伦理精神立场体会形体的美,必然肯定人自身的社会存在价值。
二
如果说,伦理精神在中国形体审美意识中是一种道德理性的话,那么,它在西方世界则表现为一种知识理性。道德理性强调在形体审美中贯彻绝对至上的道德秩序和规范,知识理性则要求体会形体审美活动中的智力综合与平衡。
第一,中西形体审美意识之伦理精神的出发点不同。观照、追求和创造人的身体形式,西方人所坚守的伦理精神——无论是“朴素为美”道德意识,还是对心灵与肉体统一的探寻,根本地诞生于特定的宗教意识,是与“神人相合”的西方文化模式紧密贴合的。按照西方观念,神的美来自与神的身体相联系的理性和智慧并通过神的外形充分显现;人既与神一样具有复杂的感情、欲望和意志行为,必定分享了神的美,同神一样具有心灵与肉体统一的形体之美。质言之,在人的形体方面,心灵与肉体的统一性不是直接根据道德经验,而是通过理性的启悟和对神人一体的理解,通过发现神所具有的心灵与肉体统一之美而发现心灵与肉体统一的人体之美。这也是西方形体审美意识所内含的伦理精神出发点。也可以说,当西方人凭借知识理性领会到:所有品质或美德都从第一本质或美德(即神的本质与美德)产生,较下级的理智仿佛“受光”于一个发光物体并像一面明镜反射其上级的光辉,与神无间的人体也映照了神的美,与神同化为心灵(理性)和肉体(物质)的统一体;既然一切理性都是富有形式的,神的智慧便要求通过它的身体形式反映出灿烂的美,人也同样如此。
由此出发,西方人在形体审美中刻意体会这种心灵与肉体的统一性:它不单是一种道德意识,同时是理性的自觉和对人的内在智慧的积极欲求形式;身体之美不仅是一种形式美化,同时也是一种本质上与神的世界相统一的智慧光辉。因此,只有当人的身体不仅体现物质的形式,而且融合了崇高智慧的内在精神时,人的身体之美才真正达到了与神一体的境界。
中国形体审美意识的伦理精神,则以“纯粹伦理主义”为出发点。这种纯粹伦理主义的原则,体现为对一切事物的认识、选择都必须体合道德利益的要求。它不像西方人那样从理性自觉中返观神与人的默契,而是从感性自觉中发展神与人的天然差别并从中体会人的伦理性存在,所以它在另一条道路上选择了肉体与精神相统一的道德色彩。以“朴素为美”理想而言,其基本前提实际是追求物质满足的伦理意愿。《韩非子·五蠹》中说“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13],形体审美(“文绣”)的前提性要素是生活的物质满足(“饱糟糠”、“完短褐”),而在不具备基本生活条件情况下追求身体形式(包括“文绣”衣着),便违背了生活的道德原则、人之为人的社会利益。而由于生活的物质满足是一个无限追求的过程,因此对身体形象的审美追求就不应单纯以“文绣”即审美满足为前提,而必须服从不断追求完善的过程。这种形体审美的伦理意愿既表达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态度,也是其形体审美态度,它必然形成对物质生活“朴素为美”的身心自觉,并且规范中国人对形体美的普遍意识。
中国形体审美意识之于心灵与肉体统一境界的领会,也绝非出自宗教情感,而是一种“道德至上”的情感。中国文化历来强调从“义与利”、“力与德”关系上把握人生存在及其价值,讲究“义以为上”、“见利思义”。这种“道德至上”的文化观念,使中国人在追求自身价值时抑制了道德追求之外的东西,特别是个体价值,而强调回归与体合道德原则。它表现在形体审美意识中,就是强调心与肉、精神与物质的统一,并将之巩固为一种坚定的伦理精神。当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14] 时,实际表达了中国人的特定形体审美意识:心灵与肉体合成的人体形象之美,并不在于个体自我的存在价值,而在于所象征的那个绝对道德世界。从这种“道德至上”情感出发,中国人再把心灵存在与人体存在结合一起,加以理性的体察。总之,在中国,形体审美意识之伦理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纯粹伦理主义”意识或情感,它规定了中国形体审美意识发生、发展的途径和方向,从而在与西方形体审美意识的比较中见出了差异。
第二,西方形体审美意识之伦理精神主旨,是强调二元对立的统一,即心灵与肉体存在都有彼此的合理性,“既有美丽的肉体,又有高尚的灵魂”[15],在“二元”互为合作过程中把握它们的统一。尽管他们也曾有片面高扬理性和形体美之精神原型的观念。但在西方,形体审美意识中的绝对伦理情绪并未占据永久理论地位,心灵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和统一基本是被放在一个具有清醒理智水平的量器中来衡量的。“一切肉体活动的能力,我们都认为是有益的特征;体力必须能尽量发挥,做各种练习,在各个方面应用;骨骼必须具备适当的结构,四肢要有适当的比例,胸部要有适当的宽度,关节要相当柔软,肌肉要相当柔韧,才宜于奔驰、跳跃、负重、攻击、搏斗,不怕用劲,不怕疲劳”,同时又“不让一种性能占先而妨碍另外一种,要所有的性能都达到最高度,同时保持平衡与和谐:不能使这个力量的强大促成那个力量的衰弱,不能使身体为了求发展反而萎缩……加上心灵,就是意志、聪明与感情”[16]。这样,肉体与心灵的统一并不以牺牲肉体存在为必然前提,相反,肉体存在的独立性依旧相当明确。而为了保持肉体本身的独立性,避免精神(心灵)对肉体存在的漠视,就须将精神(心灵)价值放在一个适当位置上。这一切表明,在西方,肉体存在与精神存在的审美价值并非一定此高彼低,它们可以同样具有满足审美愉悦的功能;它们是对立的,必须达到相互融合才能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形体之美,但相互融合不是以心灵价值否定肉体的审美存在。其实,即便当普洛丁高扬心灵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时,他也并不是从纯粹道德立场看待形体美,而仍然从形体审美的情感快乐角度,从形体美本身的美感发展前途上,论证了心灵对于身体形象的巨大意义。
由于理性地觉悟到形体美之肉体与心灵、精神与物质的同等意义,西方人往往不做绝对努力来排斥肉体形象本身。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赞叹:“人的美,这首先是他身体的美”[17],从理论观念上明确肯定形体审美的物质基础。至于这种形体审美意识的伦理精神本质,则一定程度上联系着西方人自古而来的“美不是善”的审美理想:正因为美不是纯粹道德性质的,因而主善的心灵就不足以构成形体美的全部,它必然结合形体的肉体基础而达到审美的高度;正因为美不是善,所以形体美不等于心灵和道德的美,而是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二元对立中的统一。
既然形体审美绝不因为心灵存在而贬低肉体的现实性和审美价值,西方人在形体审美中便有理由热情欣赏肉体所焕发的美。这里不存在渎神的问题,只有敬人如敬神的自由。“这个女人的胸部:饱满的乳房,美妙无比,令人爱煞。如此的优美,简直非人间所有!”“你看另一个女人的臀部:多么神奇的起伏!软玉温香中,肌肉多么美妙!真要令人拜倒!”[18] 从罗丹这里,我们已完全可以了然西方人对肉质身体的感情,它甚至激励他们在现实生活和艺术活动中动情地分析人的肉体形态,把握人体的全部审美特征。在西方,对肉体感到强烈审美兴趣不仅正当,而且是一种文化积淀的自觉:肉体与心灵都是神圣的,其如神明也具有肉质身体一样无可指谪。
中国形体审美意识之伦理精神的主旨,则是强化心灵的道德觉悟、道德力量的一元性,以此否定纯粹肉体存在的独立性及其作为形体美独立元素的可能性。虽然中国人也讲肉体与心灵、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但肉体存在的必然性却被放在形体美外部,因而在本质上,心灵的道德价值才真正是绝对的,心灵之道德存在的一元性、心灵的道德指令才是形体审美的绝对根据。《论语·子罕》中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19],孔子一语道破中国人内心深处对于形体审美的强烈道德归属意识:“好德”是将心灵存在的道德意义绝对弘扬为审美的最高目的,“君子”追求“好德”,“小人”却单纯渴望肉体存在的审美愉悦;人既以“君子”为楷模,便应“好德”而非“好色”,以形体美的心灵价值为形体审美的唯一真实目的。这种以心灵存在价值追求为最高道德律令的意识,将肉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做了绝对道德划分:心灵高于肉体,精神主导物质。感性的形体审美对象被转化为一种道德存在得到臧否,心灵存在作为道德价值的肯定性象征获得理性肯定。于是,肉体存在的美丑性肯定着内在心灵道德品质的优劣,如《大戴礼记·四代》中所论,“盖人有可知者焉:貌色声众有美焉,必有美质在其中者矣;貌色声众有恶焉,必有恶质在其中者矣。”[20]
心灵道德的一元性价值最终克服了肉体存在的独立性,它作为中国人的伦理自觉,在追求灵肉一体中其实深藏了一种心灵存在的高超独拔。中国人也认识到,积德内满,文饰外物,美的内质必然要求显于文饰(孟子谓“充实而有光辉”),甚至《荀子·荣辱》篇中还提倡:“目好色,耳好音,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理者。”[21] 但这种表面的理论“体会”一来是对“文质彬彬”观念的感性认同,二来也并不与“好德”理性相冲突。因为“好德”所要求的心灵道德一元性价值自觉,在深层意义上已充分克制了对外在感性肉体的自由体味,文饰于外只是更加发扬道德光辉并使道德自觉心理再度昭显的特定手段而已。更何况,外在形体气貌的美化,实际也是表达圣人君子遵从礼教、显示礼仪等级的标志,《荀子·富国》中说“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所以“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22]。这样,对于中国人来说,内质与修文在形体审美上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在深层境界追求内在品质之美,在外显层次要求文饰其身,这在根本上不仅没有跳出以人格美为形体审美归宿的观念范围,而且是对人格美的极端追求。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在魏晋时代的人物品藻范畴中寻得证明。魏晋人物品藻时有“神鉴”之喻,既注重优秀人物外在形貌美化,《世说新语·容止》中说“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品藻》中又说“韩康伯虽无骨干,然亦肤立”[23],更注重考察形貌气度背后的人物心灵境界,所谓“怔神见貌”就是其形体审美的核心。他们以“神”指证人的内在品质之美,以“清”指证外在气度风范,而“清”既用以描绘人格内神体现于外在形象的风格,又用来传达人们对这种风格的审美体验,在自然、简约、素淡、奇俊、飘逸中见出内在心灵的崇高。这种尚“神”、尚“清”的人物品藻,本质上仍是以形写貌、以貌状神,是以精神、心灵为形貌核心和基源。贯穿于中国人整体观念中的形体审美意识,正处处体现了对“文质彬彬”的形象自觉。
不过,在中国这里,即便以形观神、以貌状神的自觉,也往往会受到压抑。而特别得到光大发扬的,是那种凝注于精神和心灵品质之“内美”的道德意识。此可谓“重神轻形”而突出“神”的绝对性。“道之为物,恍兮惚兮”,本来就没有确切“实体”形态而飘渺神圣,因而“大象无形”,人的实体感越弱,便越大越美。神在与形的冲突中走向对形的克服,“文灭质,博溺心”、“治其形,亡其神”一类命题常常成为中国形体审美意识及其具体活动的理论前提。它的道德意图非常明显,就是为了克制重形失神、追求形体外在美而失落对内在品质的崇仰敬畏。这种观念绝对归从于伦理精神的引导,在根本上也阻滞了中国人对身体形象的纯粹诗意构造和感官满足。对《韩非子·解世》中所写“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24] 的君子内质之美的追求,排除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普遍审美自觉与自由,归于心灵道德的一元世界。
第三,伦理精神在中西形体审美意识中发生效用的途径不一样:在西方,这种伦理精神促使形体审美活动走了一条由外向内、由身体形象透视心灵精神的理想化道路;在中国,它则引导人们踏上了一条由内向外、由心灵价值反观身体形象存在的理想化道路。
由内向外的审美道路反映在中国人“纯粹伦理主义”的形体审美意识中,突出了“重神轻形”、内美高于外美的理想,即:形体的美丽动人不是由审美感受直接确定,而是经由间接经验的道德觉悟获得震动;欣赏一个人的身体形象,首先是在道德层次捕捉其内在修性与高度,然后才由此及彼地欣赏其外在身体形式。儒家所谓心与色、气与声的必然统一,就是根据这一路线来确立的:“君子”之美植根于仁义礼智诸种心灵美德,由内心道德之美而生发出相应的色貌形象并赫然表现于五官四体。如《大戴礼记·文武官人》中所写,“心气华诞者,其声流散;心气顺信者,其声顺节;心气鄙戾者,其声嘶丑;心气宽柔者,其声温好”[25]。这其实还是以人格美来取替身体形象的客观欣赏价值。正因此,陶渊明《闲情赋》中那位旷世独秀的美女之美,并不在于其“瑰逸之令姿”、“倾城之艳色”,而在于“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芳”的高洁品质以及“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的淡远襟怀。后者恰是一种以道德价值为实质的内在之美,它主宰了这位美女的身体形象;“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的动态美人形象,通过对内的观察和一定的道德认识而被觉识、欣赏。
由内及外、注重心灵价值甚于直接感受外在身体形象的形体审美路线,也是最具实践理性的操作方法。如上所述,中国人直接将“容仪之美”对象化于仁德人格或道德模范。这其中所暴露的,是中国人永恒的形体审美理想和方式——具有美好品德的人的身体形象,也总是超越凡俗、有可仿效之处。反过来,一个人若想使自己的外在形貌赏心悦目,就须像道德人物那样或学习、修养仁道精神。《礼记·玉藻》就曾从头到脚为中国人设计了这样一种操作方案:抬脚沉重,举手恭敬,目不斜视,不露牙咧嘴,声音平静,头要端直,神气严肃,站立要体现出德行。由此实现的形体美(“君子之容”、“仁人之仪”),体现了内在心灵的气象——道德世界的纯洁品质由内及外地模塑了人的存在及其价值。显然,这种中国形体审美意识中的伦理精神,最彻底地实践了道德的改造和规范意义。既然形体美不但是心灵与肉体统一中的心灵一元化,而且由心灵制约肉体存在;既然形体审美要通过内在道德修养途径来展开,那么人的形体美当然在最终意义上归于内在道德价值的认识与学习,如《荀子·修身》中所说,“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26]。由内而外的形体审美路线一旦绝对化,变成了不变的理想原则,促使形体审美的一切都走向基本的道德模式,《荀子·非十二子》中说,“俨然、壮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广广然,昭昭然,是父兄之容也”,“俭然,辅然,端然,訾然,洞然,缀缀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27],人在这种家庭伦理规范基础上才将获得真正的美,形体美也必然归趋于这种家庭伦理原则。内在精神因素超越了外在形式的感性价值,因而所谓“气韵”便也可以直接转译为道德心灵、道德精神。由内向外的观照使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身体外在形象,而强调“容止动作发乎心气”。欣赏与评价一个人的形体美也必然根据人的内在的道德水平和自觉,此正如刘安在《汜论训》中云:“中有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28]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即使有美丽可观的外在形象,如果不同时具备一定水平的心灵品质、道德精神,也无法令世人认同和喜悦。所以,夏桀、商纣虽有硕长俊美的容貌,但其荒淫无度,外不足以存国,内不足以保身,在后人审美视野里终究没有太多魅力。同样,潘安虽是美男子,但他奔走权贵,失去了令人敬仰的魅力,也同时失去了身体形貌的欣赏价值。而当屈原意识到自己心目中的美人宓妃“厥美以骄傲”、“信美而无礼”,虽赞叹她的形容动作优雅可爱,到头来还是不得不“违弃而改求”。对内在品德、道德精神的关注,决定了对一个人形体的审美价值评判。这就充分反映了中国形体审美意识之伦理精神的效用途径。
反观西方所执行的却是一条由外及内的形体审美路线,即把对人的身体形象的审美过程提升到首位,而心灵境界水平则作为次一级原则,或者说主要通过直接感受身体外貌而深入内心的幽深底渊并升华出特殊的形体审美快乐。这条形体审美路线一方面基于对人自身审美感受过程的理解,即“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而不是一种涉及对象的感觉”,由此而把形体审美对象直接归于身体形式本身,“在观照那个站在我面前的强壮的、自豪的、自由的人体形状”时,它就“是把自己对象化了的自我,也就是说,和那个凭感官认识到的人体形状打成一片的自我”,“是我在我自身里面感觉到和体验到的那种人体形状,那种强壮的、自豪的、自由的自我”[29]。另一方面,则基于伦理精神在西方形体审美意识中的非绝对性,即不把道德力量绝对化到凌驾一切现实对象之上的地步。它使得西方人在形体审美中基本遵循了审美的直接感性途径,以人体感性存在为直接审美对象,主张“人体美在于四肢五官端正匀称,再加上鲜明的色泽”[30]。对内在道德精神的理性觉悟以及由此而生的道德感,并不直接影响形体的外在形式价值。塔索就指出:“美是自然的一种作品,因为美在于四肢五官具有一定比例,加上适当的身材和美好悦目的色泽,这些条件本身原来就是美的,也就会永远是美的。”[31] 形体审美的快感就来自对象的直接存在及其形式感,“美的外形很有灵效地引起某种程度的爱,就像冰或火很有灵效地产生冷或热的感觉一样”[32]。这种对身体形象的独立直观,一定地显现了审美的纯粹性,它在西方人那里还时常转化为对美的客观价值的确定信念——“人体美是一种客观的表现”,这种“客观性”就体现在它可以自由地、纯粹地凭借外在形式深入人的情感深境,像叔本华所言:“任何对象都不能像最美的人面和体态这样迅速地把我们带入纯粹的审美观照,一见就使我们立刻充满了一种不可言传的快感,使我们超脱了自己和一切烦恼的事情。”[33] 也因此,西方人敢于大胆地把审美视线直接投向身体形式的感性方面,并提出种种直接关涉身体形式的审美标准,“达到结婚年龄的姑娘,她的自然定性是孕育孩子和给孩子哺乳,如果骨盆不够宽大,胸脯不够丰满,她就不会显得美。但是骨盆太宽大,胸脯太丰满,也还是不美”[34]。
心灵存在及其在形体审美中的价值,通过对人体外在形式的观照而进一步获得更深一层的体会。于是,罗丹惊奇地发现了巴特农神殿里三位命运女神像背后的实质:透过美丽女神雕像的外观形式,发现“她们的姿态如此宁静,如此尊严,好像具有某种肉眼看不见的瑰伟的性质”,“无限的神秘高临在她们头上——那是无形的、永恒的‘理性’,整个自然要服从这个理性,这三位女神也就是这个理性的侍女”[35]。身体外部的审美特征决不轻易让位于心灵价值,而身体形式的美化则使欣赏者能凭借它而直窥精神的丰满、心灵的高尚。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在西方人那里,只有身体的外观形式才是唯一审美因素。它只是表明,心灵价值是经由身体外观传达出来并昭示于欣赏者面前,从审美角度对人的身体加以体会,已经可以反映或象征心灵的美、精神的威力。或者,人的身体外观形式的鉴赏、感受正是打开理解心灵之美大门的第一个关键,一旦正确而又毫不顾忌地感受到一个人身体外在的灿烂光辉,就能进一步通向对其心灵境界的审美判断,乃至在面对种种人的身体形象的审美悦乐中,像罗丹那样看到“妇女在她们的深刻的宗教性里类似花朵”,深切体会不同性别人体所寓示的种种不同心灵品质和精神存在。[36]
一旦身体外在形式的美被有效感受并因此而探入心灵的深境,捕捉到来自内在精神方面的美丽光彩,形体审美才算真正完成。这里,西方形体审美意识之伦理精神的非绝对性又一次得到证明:由外而内的形体审美过程,起步于以敏锐而热情的审美态度直观人的身体外在形式,包括对内在心灵之光的审美感受也一样保持了这个前提。因为这个缘故,西方人特别注重发现和培养能够直面人体的审美态度。在这方面,中西方也很不相同。中国人也注重心灵修养,但其归宿是养成归附、体合道德本质的仁德之心,而不是以审美态度本身为目的。西方人要求“净化”人的心灵世界,却不要求以道德情感来充塞内在灵魂的空间,而是力图通过对身体形象的直观来排除内心中有碍审美活动的一切杂质。“只有在清除了由于和肉体结合得太紧而从肉体传来的种种欲望,摆脱了其它情欲,洗净了因物质化而得来的杂质,还纯抱素之后,它才能抛掉一切从异己的自然得来的丑。”[37] 正因为对身体形式的审美感受是直观感性的,所以需要欣赏者具有能够敏感和观照身体形式的审美之心;正是为了更好地感受形体美,心灵才“须经历最艰巨的最剧烈的斗争”[38]
心灵的改造指向非道德的审美领域,这同样归功于那种由外向内的形体审美道路,显示了西方形体审美意识之伦理精神的超越性效用及其全面理性果实。而普洛丁的那句名言:“一切人都须先变成神圣的和美的,才能观照神和美”,则成了对此的特殊写照。
中西形体审美意识之伦理精神差异绝非偶然,其在效用途径方面所走的不同道路——由内及外和由外向内,充分反映了道德的绝对性和非绝对性的差异。而这其实也反映了中西方在形体审美意识方面理性觉悟的差别。
收稿日期:2006—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