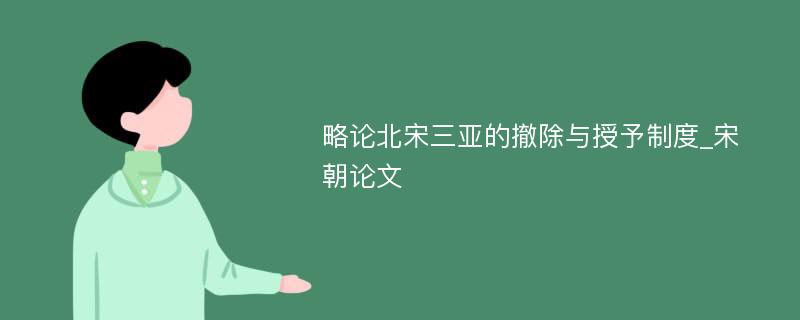
北宋三衙除授制度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4)02-0038-04
三衙,全名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是北宋禁、厢诸军常设之统帅机构。其帅,宋人称作“三帅”、“管军臣僚”,或简称“管军”,为武臣之极任。故三衙的除授,乃是北宋朝廷之重事,惟有皇帝和宰相、枢密使、侍从、台谏等朝廷高层方有权参预。
一、从权归枢密到宰相、枢密共议
按照北宋制度,枢密使“佐天子执兵政”,“委任尤重,本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势均中书,号称两府”[1](卷124),除授三衙自然是其职责所在。不过,正如宋太宗朝宰相吕蒙正对宋太宗所言:“臣备位宰相,可以进退百官。”[1](卷36)北宋宰相“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2](卷161),自然亦有权干预三衙的除授。因此,随着宰相、枢密使权力的消长,三衙的除授制度前后也就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以宋仁宗康定、庆历之际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在仁宗朝之前,三衙除授隶于枢密院,宰相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发挥太大作用。以宋太祖朝为例,赵普于枢密使任上即曾否定了宋太祖以符彦卿为管军的成议,《长编》卷4记载:“上欲使符彦卿典兵,枢密使赵普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屡谏,不听。宣已出,普复怀之请见,上迎谓曰:‘岂非符彦卿事耶?’对曰:‘非也。’因别以事奏,即罢,乃出彦卿宣进之。上曰:‘果然,宣何得在卿所?’普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未备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上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事遂中止。”当时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宰相对此事却难置一辞。个中原因,除赵普是宋太祖最亲信的开国元勋外,也与除授管军本属枢密使有关。
宋太宗朝也是如此,如雍熙北伐契丹期间,三衙的选派、军队的调动,“上(指宋太宗)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1](卷27)对此,曾经有人表示过不满,像知制诰田锡在奏章中即云:“岂有议边陲、发师旅,而宰相不与闻!若宰相非才,何不罢免?宰相可任,何不询谋?……伏乞陛下……事事与宰相商量,悔自前独断之明,行今后公共之理,则事无不允当,下无不尽忠矣。”[1](卷30)但宋太宗并没有采纳这些意见,淳化元年(990)十二月更进一步将“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1](卷31)著为定制,限制宰相不得与议包括任命管军将校在内的枢密院军政大事(即所谓的“机事”)。
真宗时,宰相开始参预枢密院重要军政的决策,如在澶渊之盟前夕,宋真宗就曾经对宰相毕士安、寇准表示:“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1](卷57)不过,直至仁宗朝宝元年间,仍然是“以中书制民,枢密主兵。故元昊反,边奏皆不关中书”[1](卷126)。对三衙的除授,宰相一般也不发表意见。
仁宗康定、庆历之际随着宋夏战争的爆发,情况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宰相逐渐取得了与枢密院共同除授三衙的权力。如在康定元年(1040)二月仁宗即采纳翰林学士丁度、知谏院富弼“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异,则天下无适从,非国体也。请军旅重务,二府得通议之”[1](卷126)的建议,专门下诏枢密院,规定边事并与宰相张士逊、章得象参议。庆历二年七月,知谏院张方平又将北宋在战争中屡遭败绩归咎于中书、枢密院分持文武二柄,认为:“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则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别文武为两途。为政多门,自古所患”,“宣(中书)、敕(枢密院)并行,议底细难一,事无责任,更相顾望”,强烈请求“特废枢密院”,或“并本院职事于中书”。[1](卷137)宋仁宗本人也有意于废枢密院,曾公开说:“军国之务,当悉归中书,枢密非古官。”至此,遂进一步命宰相吕夷简判枢密院事、章得象兼枢密使、枢密使晏殊则同平章事,宰相全面接管了枢密院的权力,三衙的除授权当然也不例外。
宰阳兼任枢密使,毕竟属于战时的临时性措施,不符合北宋以枢密使制约宰相军权的基本国策,因而在庆历五年(1045)宋夏双方达成了和议,西线战事趋于平静的时候,当年十月经宰相陈执中、贾昌朝的主动请求,宋廷下诏“罢宰臣兼枢密使”。
不过,宰相虽然不再兼任枢密使,但宰相对枢密院军政权力的必要分割却从此成为北宋朝野上下的共识,如宋仁宗在批准陈执中、贾昌朝请求的同时,即专门对枢密院下诏,要求:“凡军国机要,依旧同(宰相)商议施行。”[1](卷157)这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就是宰相正式从制度上分割了枢密院对三衙等中高级军官的任用权,据《长编》卷157庆历五年十一月记载:“枢密院请自今进退管军臣僚、极边长吏、路分兵马钤辖以上,并与宰臣同议,从之。”
正因为如此,自庆历年间开始,三衙除授不妥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时人批评宰相的一个问题,而不再仅仅归咎于枢密院。如庆历六年,当许怀德由殿前都虞候超迁马军副都指挥使时,对此心怀不满的殿前副都指挥使李昭亮即“诣两府叙陈”[1](卷159)。嘉祐五年(1060),宰相富弼因张茂实擢任马军副都指挥使而遭到弹劾的事例更为典型。张茂实,自幼生长于皇宫,关于他的身世,时人就有其为真宗之子的说法,在仁宗患病之际,以他出任三衙显然是不太适合的。因张茂实早年曾经与富弼共同出使过契丹,两人有一定的交往,所以很多人怀疑这是富弼之意。御史中丞韩绛遂上书弹劾富弼用人不当,史书记其言曰:“孜(张茂实后改名曰孜)不当典兵,而宰相富弼荐引之,请黜弼”[2](《张孜传》);“茂实出自宫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为殿帅(实为马军副都指挥使),盖尝同奉使,交结有自。”[3](卷上)此事后来虽然被证明纯属误会,“复用管军,乃中书、密院同议,人亦无间言”,[1](卷191)韩绛也引咎去职。但从此事中不难看出,宰相在三衙除授中发挥相当的作用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
在仁宗以后北宋各朝,三衙除授须经宰相、枢密院共议的制度被继续沿用,《宋史》卷162《职官志》云:“枢密院……及除都副承旨、三衙管军、三路沿边帅臣、太仆寺官,文臣换右职,仍同三省取旨。”具体的事例:如神宗朝熙宁四年(1071)五月,在是否填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的管军空缺时,即由宰相王安石和枢密使文彦博进行讨论,王安石还专门就管军的除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长编》记载:“安石曰:‘都虞候须以防御使为之,止是故事,初无义理。臣固尝论奏,以为但缘官阙遂例迁,或无功以选超授,皆无义理,不足以劝。’”[1](卷223)次年五月,在宰阳、枢密院共议高遵裕欲“带御器械”为日后作管军作铺垫时,王安石再次公开表态:“若除管军,自系朝廷拔擢。”[1](卷235)此处的“朝廷”,是宋代的一个专门用语,特指宋代最高国务机构宰相(元丰改制前为中书,改制后为三省)和枢密院,如南宋余应求上书中说:“三省、枢密,是之谓朝廷,陛下与谋议大事,出命之所也。”[4](卷23)文天祥也说:“三省、枢密院,谓之朝廷,天子所与谋大政,出大令之地也。”[5](卷3)
哲宗朝元祐五年(1090)十一月“三省(神宗元丰年间改中书为三省)、枢密院共议以张利一、张守约为军帅”[1](卷450);绍圣、元符间长期担任枢密使的曾布也曾多次谈到:“管军须三省同除”、“密院事稍大者,三省无不可照管。”[1](卷494、501)等等。
与此同时,这一制度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待三衙有缺后先由枢密院拟定初步人选,经宰相、枢密议定签字,提交皇帝予以审批的严密程序。以徽宗即位伊始补三个三衙之缺为例,据《长编》卷520记载,就是先诏“枢密院具曾任管军及堪充管军人姓名”,由枢密使曾布负责拟定王愍、苗履、刘安、张存、折可适、姚雄、姚古等七人的大名单,然后经宰相许将、蔡卞会同曾布等人于御前共议,待宰相等“众人皆曰然”之后,方从中遴选出王愍、苗履两人为新任三衙。
二、侍从、台谏参预三衙除授
不仅如此,所谓“大事必须集议,盖以朝廷示广大,不欲自狭,谋臣思共公,不敢自专,故举事多臧,众心皆服”[1](卷142)的原则在北宋深入人心,在三衙的除授过程中,为了更好地集思广益,避免执政大臣循私舞弊,也是队仁宗朝开始.包括侍从、台谏等在内的其他高级朝臣也可以发表意见。
侍从官方面,如庆历四年(1044)知制诰张方平就上书仁宗乞择人分总禁卫,认为:“今内则禁兵寝骄,极须弹压;外则边患不测,常资防备。李昭亮、王元恐未任专干心膂,除郭承祐好进多事,累被弹奏,不堪入典禁军外,乞于以次管军将校中择取一两人赴阙,分总禁卫。”并具体推荐“济州防御使向传范资性谨重,和而有守,典藩有政,常居课最;沂州防御使刘永年绰有武干,理戎严整,颇著风绩。此皆阀阅旧门,地连戚属”,[6](卷24)可以出任三衙。哲宗元祐八年(1093),曾经违背北宋不以枢密官属兼任管军的惯例而命枢密副使曹诵权管马军司,翰休学士范祖禹即上了著名的《论曹诵札子》表示异议,要求“特降指挥改正”[7](卷26)。
至于在北宋政治生活中极其活跃的御史、谏官等台谏官员,因“轩陛之下,庙堂之上,进退百官,行政教,出号令,明制度,纪赏罚,有不如法者”[8](卷13)皆得言之,所以对三衙除授的影响更大,甚至于往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认为不合适的人选有提出异议的权力。
以仁宗朝为例,如庆历五年(1045)郭承祐迁殿前都虞候,监察御吏包拯即上书反对:“按承祐累任无状,朝野佥知,物议喧然以为不可。”[1](卷157)庆历六年(1046)七月,当宋廷拟许怀德为马军副都指挥使,以御吏中丞张方平为代表的言事官们更是“上章论奏者相继”[1](卷159)。嘉祐五年至六年(1060-1061),先后两任御史中丞韩绛和赵概都对以张茂实任马军副都指挥使表示异议,最终促使其自请解兵权,出为知州。嘉祐六年(1061)九月,知雄州赵滋迁龙神卫都指挥使、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知谏院司马光连续进言“论赵滋为人刚愎,不可管军。”[1](卷195)等等。
三、皇帝行使决策权的多种方式
应该着重强调的是,正如真宗朝枢密使马知节对真宗所言:“当今兵柄,尽出陛下掌握,至于一命之士,皆由旨授。”[1](卷67)哲宗朝侍御史孙升也曾指出:“臣窃以管军之臣,乃人主爪牙,所以自卫,虽推择之议,当参详于执政,然除授之恩,必使归之人主。”[1](卷450)皇帝作为北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牢牢掌握着三衙除授的最高决策权。这种决策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皇帝越过宰相、枢密院的集议程序,直接以内降手诏,或者当面任命自己的亲信为三衙,这种情况在整个北宋始终存在。以太祖、真宗、英宗、仁宗、哲宗、徽宗六朝为例:
宋太祖朝张琼破格被提升为殿前都虞候,即是出于宋太祖的乾纲独断,“上谓殿前卫士如虎狼者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乃自内外马步军都头、寿州刺史擢殿前都虞侯、领嘉州刺吏”[1](卷2)。宋真宗宠信亲信夏守斌,遂不经宰相、枢密使,直接“遣中使问守斌:‘欲管军乎?为横行乎?’”[2](《夏守斌传》)
宋仁宗朝的情况相对复杂,迫于大臣、台谏们“乞罢内降诏书”的激烈反对,仁宗虽然不得不数度下诏表示“如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今后内降,无得辄受”,但“内降”仍然是相当频繁。仁宗还时常直接干预专门机构对官员的任免,在三衙除授上,尤其是如此,像李用和、李昭亮、郭承祐等外戚屡受台谏攻讦却能安居殿前副都指挥使等高位,关键显然就在于仁宗本人“用亲”的一己之私意,又如刘平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也是出于仁宗之意,《长编》卷115记载:“上(指仁宗)初擢(刘)平主四厢,谓左右曰:‘平,所谓诗书之将也。’”
宋英宗是一个“有性气,要改作”的君主,所谓“每有裁决,皆出群臣意表”,在用人方面就是往往断以己意。如以唐介任御史中丞,据他本人所说就是:“卿在先朝有直声,今出自朕选,非由左右言也。”[1](卷201)仅是因在藩邸时同杨遂有一面之识,英宗于是钦选其为步军都虞候,《长编》卷205记载:“初,绛州团练使杨遂为新城巡检,救濮王(英宗父)宫火,帝(英宗)识其面目。于是,侍卫司阙帅,帝首出遂姓名,擢登州团练使、步军都虞候。”
宋哲宗朝,皇帝更时常亲自除授三衙,然后批付或面谕宰相、枢密院正式任命。以元符元年(1098)正月决定除张整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为例,就是宋哲宗本人经当面亲自考察后批付二府除其为三衙的,完全撇开了三省宰相。其过程,据《长编》卷494记载:
“先是,泾原乞差近上兵官。曾布为上言:‘无人可差。泾原、熙河皆欲得王恩为总管,恩少壮,可驱策,兼颇得边人情,置之于此可惜。张整军政严明,可以管军,但恐以衰病。若召之一见,陛下自视其人才,可进则进,不可则却令归本任,似无所害。’上然之,遂召整。既对,论军政及职事,极有条理,上甚悦。翌日,谕二府曰:‘整殊不类武人,语言皆有条理。当时丰稷、韩忠彦皆拒而不授,何也?’整先除镇、定府钤辖,二师(为“帅”字之误)皆以为严酷失军情,不纳。布曰:‘臣不敢过称道之,然其军政严明,实有过人者。奏对果称旨,然管军须三省同除。’上曰:‘不须,待里面指挥。’即日批付二府除四厢。”
对此,正如枢密使曾布所谈到的:“上频收威柄,侍从、台谏多出中批或面谕,至整(指除张整为三衙)亦欲从中批出,三省无复差除,右使已阙数月矣。”[1](卷494)这与绍圣前大权归于高太后和旧党执政大臣,哲宗亲政后遂更为注重加强对用人权控制“频收威柄”的大背景有关。
徽宗则好用”御笔行事”,即不经中书省商议,不由中书舍人起草,不交门下省审覆,由皇帝在宫中决断,并亲笔书写,或由宫中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御笔行事,始于大观年间,史称:“御笔自此始,违者以大不恭论,由是权幸争请御笔,而缴驳之任废矣。”[2](《昊敏传》)三衙的除授亦如之,像高俅得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就完全出于徽宗乾纲独断。
二是皇帝在审批宰相、枢密院提交所拟定的三衙名单时,有时也向大臣提出为自己所属意而名单上未有的人选,供宰相、枢密院再度讨论,从而对大臣们的取舍施加影响。对名单中的不满意者,则直接予以驳回,令其重新拟定。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和六年(1091)先后两次除授三衙就是这方面较为典型的事例。
元祐五年十一月,为补三衙之阙,经宰相吕大防、许将等三省、枢密院诸执政大臣共议,“度越资级”,拟定以张守约、张利一两人应选。但在奏请审批时,垂帘听政代哲宗行使皇权的高太后虽未明确否定大臣们的提议,仍委婉地表示:“闻王文郁有边功,好作军职”,“姚兕亦闻忠实可用。”[1](卷450)待朝议结束之后,尽管吕大防等人继续坚持原议,另一宰相许将却改为迎合皇太后的意思,不在任命二张的诏书上签字,并上札子请另任王文郁为三衙。此事后来引发了一次牵涉到所有当时现任宰相和众多台谏官参预的政治事件,许将因此被罢相,而张利一为三衙的动议也最终被搁置。
元祐六年(1091),宰相、枢密院的拟议更是进一步被高太后、哲宗直接否决。该年四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有缺,宰相、枢密院进拟以雄州团练使王崇拯担任。在“同进画可”时,这一方案遭到了高太后和哲宗的否定,并驳斥众臣道:“崇拯有何劳能,闻说止是熟事,且须选有功劳之人。”[1](卷457)枢密院遂改拟曹诵,但也未获通过。
正是因为三衙的除授权牢牢掌握在皇帝之手,皇帝身边宦官等近臣,有时偶尔也能对三衙的除授发挥作用。如仁宗朝郭承祐得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就是得益于宦官的引荐,《长编》卷138记载:“卫州防御使、知澶州郭承祐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尝有中使过澶州,遽延入,问:‘管军阙补何人?’使者曰:‘闻朝廷方择才武。’承祐起,挽强自衒,左右皆笑,已而果有是命。”显然,中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收稿日期:2003-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