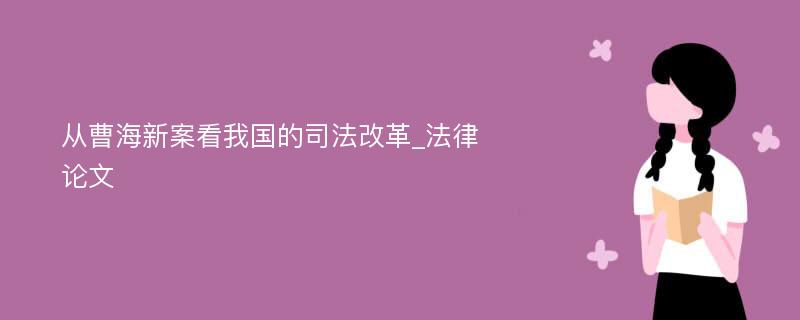
从曹海鑫案看中国的司法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法改革论文,曹海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看着手里这份由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8)第249 号刑事裁定书,心中沉甸甸的: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被我们的司法机关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了!案件留下了那么多的疑问,引发了那么多民众乃至文化界知名人士的质疑和不满,甚至还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参见《今日名流》1999年第3期,第4~12页)曹海鑫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很多,其中的实体方面更是牵扯到犯罪构成的要件、正当防卫的条件等复杂的刑法理论问题,证据方面也可以延伸出证据的可采性、关联性、证明力,证人的资格以及证言的效力,证明责任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曹海鑫的辩护律师提出的很多辩护理由都没有被法院采纳。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无法发表适当的评论,而想从本案所涉及到的法律程序问题入手,谈一下中国进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这是一个经历了较为完整的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被告人曹海鑫于1995年9月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拘留,同年10月被逮捕;1997年5月被一审判处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后,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的合议庭,没有对此案进行开庭审理,而是在秘密调查和评议后提交“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并于1998年9 月作出最后的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这份裁定书还声明:“本裁定即为核准被告人曹海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裁定”,也就是“终审裁定”; 同年9月25日,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了死刑执行命令,曹海鑫被执行死刑。表面上看,这些程序是符合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但是,这些程序符合公平、正义、合理等基本的价值要求吗?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句人所共知的司法谚语,阐明的是司法程序和过程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主要表现在:法官仅仅自己相信判决的公正性和正确性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让周围的人甚至广大社会公众相信他所作出的判决是公正的,说服案件当事人和任何关注案件的人士接受判决的结果,消除人们对其审判过程和判决结果上可能存在的合理怀疑。现代司法的这种理性协商和说服特点,可以从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法官的中立无偏、法庭向公众的平等开放、法庭上的举证和辩论、法院判决对裁判理由的详尽阐释等各方面表现出来。在一系列的司法理念之中,程序的公正性和裁判者的独立性是极为重要的。这两点如果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司法审判就会衍变成官方对公民的赤裸裸的报复,与权力滥用相伴随的暗箱操作就会肆无忌惮地吞噬一个又一个公民的自由乃至生命。因此,司法制度设计得科学与否,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管理技术问题,而与每一个公民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息息相关。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上诉的案件,组成合议庭后,由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司法实践中相当多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就以此为根据,拒绝对上诉案件开庭审理,而搞所谓的“调查讯问式”的审理,也就是变相的书面审理。在这种审理过程中,第二审合议庭几乎完全以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卷宗为根据,不论被告人是否对证据、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存有异议,都不再传唤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出庭作证,也不再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进行当庭调查,甚至连形式上的法庭审判也不再进行,公诉人、辩护人都不被允许出席法庭审判。事实上,第二审法院的法官在没有开庭、没有亲自直接接触案件证据材料的情况下,怎么能判定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呢?!法官的审理既然完全以第一审法院的审理情况为根据,而不具有丝毫的独立自主性,他们对案件证据的采纳、事实的认定甚至法律的适用又怎么可能突破一审法院的认识局限性呢?!因此毫不奇怪,第二审人民法院的裁决几乎99%都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要想对第一审法院所作的不公正判决申请上级法院加以改变,几乎难于上青天。可怕的是,我国很多死刑案件就是在这种第二审法院不开庭审理的情况下被作出生效裁决的,即使被告人所涉嫌的犯罪极为严重,但按照这样的法律程序和审级制度对其生命进行剥夺,也显得太随意了!
曹海鑫案暴露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死刑复核程序的名存实亡问题。本来,对死刑这一剥夺人的生命的极刑予以慎用属于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历朝都强调“德主刑辅”,一般除了乱世、暴君统治和战争时期以外,不会将生杀予夺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官僚,而是直接操纵在最高统治者皇帝手里。新中国成立以后,为贯彻“少杀”和“慎杀”的刑事政策,建立了颇具特色的死刑复核程序,以保证由最高司法机关对死刑的适用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但是,伴随着社会治安的恶化,大量死刑的复核权逐步被下放到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到目前为止,除了因犯有危害国家安全、贪污贿赂等少量罪行而被判处死刑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加以复核以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判处的其他大量死刑案件一律授权给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复核。过去,在各高级人民法院内部还曾实行过死刑复核机构与死刑审判机构的分离制度,不论是中级人民法院还是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死刑裁决,只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的范围,都要由高级人民法院设立的死刑复核机构进行单独复核。但到目前,高级人民法院对死刑案件的二审维持原判的裁定与本应独立存在的死刑复核程序已经完全合二为一了。也就是说,对于大量死刑案件来说,有权作出终审裁决的不是最高人民法院,而是高级人民法院;对这些死刑案件实行的是与一般案件无异的两审终审制。
当然,即使举行死刑复核程序,被告人也得不到多少公正的听审机会。因为我国目前的死刑复核程序实际是按照行政程序模式进行构建的:首先,裁判者在这种程序的开启方面属于典型的“不告而理”,当事人和检察机关都无权发动,而是由作出死刑裁决的法院直接主动移送拥有复核权的法院进行复核。其次,死刑复核尽管一般要由专门成立的法庭负责进行,但几乎从来不具有法庭审判的形式,因为控辩双方无权直接出席法庭,主持复核的法官也几乎从不听取检察官和辩护人的意见,而是仅凭原审法院移送来的案卷材料进行审查,即使讯问被告人,也难以听进去被告人的辩解。这样,死刑复核程序的存在就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它几乎完全丧失了纠正一审和二审判决错误的能力,也完全背离了当初建立这种程序时的初衷。我国目前一些不公正的死刑裁决很少能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得到发现和纠正,就是充分的证明。
曹海鑫案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有法院判决理由的阐述问题。本来,法院作出的不论是有罪判决还是无罪判决,都应当对其理由进行详细的说明。尤其要说明为什么采纳某一证据和意见,而对另一些证据和意见拒绝采纳;要详尽地解决自己的推理、判断过程和思路。可惜的是,我国目前的判决书一般篇幅都过短,对判决理由的解释必然不够详尽、具体。而且,目前的判决书尽管也对控辩双方的争议点进行了列举,但对法官究竟如何认识并解决这种分歧点的,则解释不够。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要点,尽管也简要地进行了说明,但往往不去具体分析这些意见究竟为什么成立或者不成立,而是笼统得出“辩护理由不成立”的结论。这就很难使辩护人信服判决书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更有甚者,有的两级人民法院所作的完全相反的裁决结论,却都建立在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实认定基础上。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第一审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无罪判决,第二审法院作出了有罪判决,但两家法院在对案件证据的采纳、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方面的描述中,几乎采用了完全一致的内容。这种在判决理由阐述方面的欠缺,导致我国法院的判决极易流于随意化和非理性化,也难以令当事人甚至公众产生信服。
最后,当然还有法院和法官的独立审判问题。目前影响法院和法官独立审判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从外部来看,地方各级法院的财政管理和预算几乎完全操纵在地方各级政府手里,法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受制于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其电力、水、土地、通讯、基建以及法官们的日常生活事项也都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要法院完全独立于地方各种势力的影响和干预,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从内部来看,法院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按照司法的特点进行构建,而经常进行所谓的“上下沟通”,上下级之间的请示和批示几乎成为司法实践的惯例,在同一法院内部又存在着行政与司法职能混同的问题,作为司法行政管理者的院长、庭长,往往直接干预甚至决定案件的审理结果,更何况还存在着一个保证这种行政干预具有合法化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这就使法官在审判方面几乎不可能具有独立自主权。此外,影响法官独立审判的问题还有:法官的身份独立问题、法官的司法伦理规范的遵守问题、法院独立与新闻自由的关系问题、法院独立与人大领导的关系问题,等等。
从曹海鑫案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我国进行大规模的司法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问题,而仅仅是采用教化的方式继续搞形式上的整顿运动,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满会进而危及党和政府的威信,危及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伦理基础,甚至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一个日益走向民主、法治的国家来说,与其让民众在政府门前静坐抗议甚至与官僚们发生冲突,不如让他们走进法院,与被控诉者进行理性、平等、冷静的争辩。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堡垒的司法,应当担当其化解社会冲突、解决利益争端、树立政府威信的使命。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司法公正、独立、公开、透明的基础上。
标签:法律论文; 法官论文; 高级人民法院论文; 法制论文; 司法程序论文; 司法改革论文; 法院论文; 死刑复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