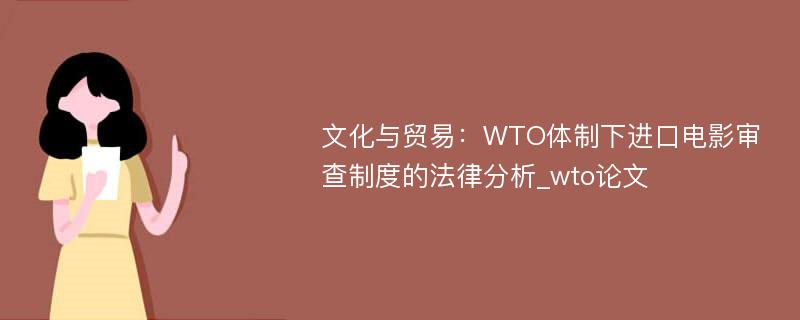
文化与贸易:WTO体制下进口电影审查制度的法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体制论文,制度论文,法律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13)02-0032-08
2010年1月19日,“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通过了修改后的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上诉机构认为中国对进口电影的经营权实行垄断管理违反了中国《入世议定书》第5条的贸易权承诺。诚然,电影作为产品,应当遵循自由贸易游戏规则,参与市场竞争。但电影所传达的文化价值极易在自由贸易中形成文化普同,对主权国家造成文化侵蚀。对进口电影进行内容审查是防止这一趋势的有效手段。然而,WTO贸易规则中是否对进口电影审查制度有着特殊的规定?主权国家尤其是中国从该案件中又当获得哪些启示?本文试图以WTO体制下文化与贸易的争议为切入点,对进口电影的审查制度作一分析。
一、电影的双重属性
1.电影的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
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各国政府所重视。一方面,其文化内涵所体现的创意、创新性,包含了各国不同的价值理念,其内容影响着观赏者的情感、认知甚至是非判断。①正因如此,电影产品又被称为“精神产品”。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强调电影产品的“文化属性”。他们普遍认为,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文化霸权”正逐渐趋向“文化普同”,弱化了文化的多样性并对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威胁。②如果对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实行完全的市场主导,则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应该允许适当的政府干预。因此,文化产品和服务不应该受制于贸易规则,或者至少应适用特殊的贸易规则。③另一方面,电影产业发达的国家更强调电影的“经济属性”。以美国为例,美国坚决主张电影产品应以市场为主导,全面适用WTO的贸易规则。早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美国代表即不惜以整个视听部门破局的风险为代价,坚决反对欧盟提出的文化特别待遇及例外条款,甚至一度放弃了此回合的视听部门谈判。④正由于美国的强硬态度,使得欧盟的文化保护政策未能如愿。虽然电影的“文化属性”不言自明,但是在世界经济强国的经贸博弈中,电影产品的经济导向趋于上风。现今的WTO规则中,GATT条文里,唯有第4条关于“放映限额”是国民待遇的一个例外规定;GATS条文里,没有任何关于文化例外和文化特殊性待遇的条款。具体到电影产品,也未能享有特殊例外或特殊待遇的法律地位,只是各个成员方尚无市场开放的压力。
2.电影的货物属性与服务属性
电影产业以其高投资、高风险的特质,决定了其必须以产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分散风险,收回成本。一部电影的获益链条一般为:影院首映→付费频道→录像带和DV→免费电视频道播出→二轮免费电视频道播出。不难看出,电影虽以胶卷、碟片的产品形式进入市场,但其真正的商业价值却体现在“服务”,并非电影产品本身的销售所带来的收益。在对海外电影进行进口审查的过程中,将电影产品定性为服务还是货物尤为重要。
在WTO现有规则中,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法律制度同时起步,彼此独立。“以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为表现形式的不歧视原则在GATT中的结构是一种‘平行式’(horizontal obligation)的法律体制,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作为GATT中的两个普遍原则,其地位是平等的;而在GATS中,不歧视原则是一种‘立体式’(vertical obligation)的法律体制,最惠国待遇原则仍是普遍原则,国民待遇不再是普遍原则而只是具体承诺。”⑤由此,一项文化产品归类为货物还是服务,其享受的待遇迥然不同。在WTO的先决案件中,已有相关产品因其实质所反映的“服务性”而引发了其到底受制于GATT还是GATS的激烈争论。
其一,在“美国诉加拿大期刊进口措施案”中,加拿大据其9958号关税令的规定,将期刊分为受加拿大政府资助的期刊、商业期刊和国际商业期刊,不同版本期刊要按照所登载广告总价的80%缴纳货物税。加拿大认为,期刊中的广告虽然以产品形式表现于外,但实质为“服务”,其征税措施应当属于GATS的调整范围。同时,由于加拿大并未在GATS项下就广告服务作出任何承诺,虽然本案有适用GATT规定的可能,但就服务部门的减让事项应当以GATS为准,为避免两大贸易法律体系的相互冲突,故应排除GATT的适用。⑥相反,美国强烈主张加拿大的上述措施违反了GATT第3条的国民待遇原则。对此,上诉机构认为,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国际公约应以不损害公约中所明确订立的任何义务方式”的解释原则, GATT与GATS条文中都没有对两个法律体系的位阶作出任何安排,因此在WTO协议中, GATT和GATS处于同等地位,并没有优先适用哪个法律体系的问题。同时,广告虽具有服务属性,但其作为期刊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文字内容共同结合为一项不可分割的有形货物,即期刊本身,故上诉机构否定了加拿大的主张,肯定GATT的规则依然适用。⑦
其二,在“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中,中国据其《电影管理条例》的规定,对进口电影的经营权实行垄断管理。进口电影的进口权和发行权由中影和华夏两家公司专享,同时,进口电影的进口与发行条件由中影集团统一规定。与此相比,国产电影的发行渠道则较为广泛,包括中影和华夏在内的电影制片方、各级地方电影发行公司均可通过市场竞争发行国产影片。⑧美国认为,中国对进口电影进口主体的限制规定违反了中国《入世议定书》第5条的贸易权承诺,对进口电影和国产电影在发行权上所实行的差别待遇违反了GATT第3条国民待遇的规定。中国主张,电影是以荧幕播放为形式的有声连续画面,核心在于画面“内容”,电影(如胶片和母带)作为其传播介质,只是服务的附属品。而且中国在GATS中已经做出了影院放映电影的相关承诺,电影进口一词在中国有关法规文本中的含义为“服务”,其影响电影进口措施应排除 GATT的适用。⑨然而,上诉机构认为,电影所展现的“内容”同货物本身并无实质性区别,两者之间的义务并不相互排斥,即使影片的“货物”形态与影映的“服务”形式同是进口,也无法证明该争议措施不会造成歧视待遇,同时,上诉机构认为这种歧视很难避免。⑩
综上,因电影的文化属性,考虑到保护各国本土文化及广受商业电影影响的“濒危小众电影”,GATT第4条纳入“放映限额”的规定,以回应美国电影大举攻占欧洲及各国市场的现象,同时也为保护本国文化信仰免受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11)但该授权性规定仅仅局限在电影产品影映的时间比例上,并未站在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高度赋予各成员方更广泛的管理措施。
又因电影的货物和服务属性,引发了各成员方对文化产品管理措施的广泛争论。通过上述两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意见的分析,不难发现,WTO对包含有“服务属性”的电影产品除“放映限额”外,并不存在对具有“服务属性”的电影产品给予特殊待遇的条款。(12)WTO体制中是以有形抑或无形的一种“形式化”标准来区分货物和服务,虽然中国在论证中指出了电影与一般货物相比存在特殊性,并试图将其归入服务之中,但是在现行解释之下,这种主张却不能得到支持。就中国而言,法律规定以国有独资企业执行进口电影的内容审查相悖于其贸易权承诺。依据WTO规则的适用和解释,包含有货物与服务双重性的电影产品与其他货物和服务没有实质区别,已固定在某种有形载体(比如胶片)中的电影固然与其他货物相比存在特殊性,但其只是“特殊的货物”,并不会因此变为服务。一旦WTO成员做出了具体的货物贸易承诺,无论该产品具有多大的服务性权重,都要受制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相关承诺的严格解释。因而各成员不能以文化性和服务性为由对电影产品采取或维持贸易限制措施。
二、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适用
当WTO成员的国内管理措施同其贸易权承诺相冲突时,GATT项下的公共道德例外条款可为该措施提供合理抗辩。尤其在电影产品的内容审查中,电影所体现的多样性价值理念易对各国公共道德造成潜在不利影响。然而,WTO规则在为各成员方的国内管理提供自主性的同时,也设置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引用公共道德条款必须同时满足以下要件:(1)必要性原则;(2)公共道德的动态解释原则;(3)非歧视性原则。
必要性原则是要成功援引公共道德例外条款首先需要满足的条件,也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优先考察的原则。从WTO先决案件来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认为“动态解释原则”和“非歧视性原则”的运用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13)如“非歧视性原则”的适用范围要求为“本协定”,但却没有清晰地界定该协定的适用空间,“本协定”是专指GATTl994还是包含附件1A的所有贸易协定,甚至于囊括所有WTO成员的相关“入世”承诺;同样,“动态解释原则”创设于“安提瓜诉美国影响跨境提供赌博和博彩服务措施案”(以下简称“美国博彩案”),该案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认为,公共道德的含义应当“以现代整个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为视角进行解读,公共道德的内容可以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内容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当前的社会、文化、种族道德等”。(14)实际上,这一开放性解释是建立在深刻认识到WTO成员各方在社会理念、价值和制度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基础之上,同时也为实现WTO协议的最大化接受而预留了出口。(15)肯定地说,上述问题均为案件的审理增加了难度和不确定性。由此,依照先前案件的做法,专家组采取一种“回避”的策略,即先假定第20条可以援引,然后直接审查必要性是否满足,遵循由易入难的分析层次。应当说,“必要性”满足与否是能够成功援引GATT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关键。在“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中,专家组引用了一系列DSB的在先案例,认为“必要”一词不仅仅局限于“有助于”和“必不可少”,(16)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所保护价值的重要性;(2)对贸易的限制程度;(3)可能的替代措施。
在“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中,中方为证明对海外进口电影经营只限于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经营的正当性,将限制贸易权与保护公共道德联结在一起。中方提出的抗辩路径是:中国需对公共道德进行保护→进口电影对一国的公共道德有潜在的不利影响→保护公共道德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对海外电影产品进行内容审查以避免带有法律禁止内容并损害公共道德的文化产品进入中国境内→由政府指定或批准的企业(一般为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企业)进行内容审查比由政府或私营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来审查更为可靠和有效→因此中国规定只能由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企业来进口文化产品(同时实施内容审查)→对文化产品的进口贸易权进行限制是为保护公共道德所必需的措施,并且该措施也符合“非歧视性原则”的要求→因此,争议措施具有合法性。专家组认为,该限制措施在维护公共道德方面确有重要性,同时也认可该措施“有助于”中国相关政策目标的实现。然而,在关键的贸易限制程度和可替代措施方面,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否定了中国的主张,其认为美国所提出的由政府从事内容审查作为排除外资企业贸易权的替代措施虽然给中国带来不合理的负担,但却有利于合理降低贸易限制,同时该替代措施是“合理可用”的。因而中国现行的由国有企业承担进口电影内容审查的措施并非为“保护公共道德所必需”。(17)
当然,即便中国成功通过了“必要性原则”的考察,并符合了“动态解释原则”的检验,仍需满足该内容审查措施自身的“非歧视性”论证。在“美国博彩案”中,上诉机构认为,一项措施一旦具有表面上的歧视性,则极有可能在情况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18)由此可见,上诉机构的“形式化”标准与严格解释不仅限于对文化产业归类的阐释,而且贯穿于对各项原则解析的始终。在“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中,中国对进口电影明显的“内外有别”的审查措施很难通过“非歧视原则”的考量,也难以运用GATT公共道德例外条款免责。
综上,在WTO体制下对海外电影进口的内容审查,就中国而言,既无特殊规定也无可适用例外条款的可能,仅能依照一般产品履行相关贸易权承诺。中国无法以电影的“文化性”和“服务性”为理由采取或维持现行的贸易限制措施。虽然案件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但其背后却凸显了相关文化政策在WTO体制下所面临的困境。首先,WTO本身致力于推广贸易自由化,只要各成员方在相关领域作出具体贸易承诺或对视听部门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作出承诺,便要严格遵守并受到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严格解释”的限制。虽然一些例外条款的设计缓和了国内管制(包括文化产品的进口管制)同贸易自由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诸如“公共道德”等例外条款的适用十分严苛。其次,电影产品的文化和服务属性未被纳入GATT的特殊考虑之内亦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GATT成立之初深受经济学中“比较利益”思想的影响,构建者认为唯有在政府和他人干涉最少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生产者才会以最适当的数量生产货物,并以市场认为最有利的方式进行交易和运作。(19)同时,GATT条文在1947年订立时,电影并未兴盛(电影系20世纪初期的产物),当然在创始初期并未慎重考虑具有双重属性的电影产品是否例外于自由贸易的议题。(20)
如今,电影产品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发生彻底的改变,不仅仅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亦被视为普及各国文化、教诲大众的媒介工具,中国业已认识到电影产业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2011年12月15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电影促进法意见稿》)中明文规定,电影应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主义为方向,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不难看出,中国在促进电影产业发展时是将电影的“文化性”置于首位。而当国家的文化性导向同WTO体制的经济性导向发生冲突时,中国应当采取哪些更加灵活的贸易管理措施,既可与WTO现有的规则保持一致,又能在国际、国内层面上实现市场开放和保护国内电影文化多样性的平衡,值得深入思考。
三、中国电影贸易措施的完善建议
现今,“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已经尘埃落定。可以说,该案体现了争端解决机构确立和传承的WTO普世的“贸易自由化”理念,当各成员方对文化产品采用较强的管理措施同 WTO规则产生强摩擦时,必将受到WTO的否定评价。透过该案,成员方在文化产品领域中,应如何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缓解摩擦,在WTO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另辟蹊径实现“管制”目的,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1.国内法层面——“弱管制”替代措施
中国的进口电影内容审查制度,究其规则本质,是通过国家行政手段的强制干预以达到保护国内电影健全发展,塑造文化多样性的目的。国家通过对电影内容审查权的垄断直接控制了进口电影的引进和发行时间,此类管制措施以较强的行政手段缓解了进口电影对国内电影产业造成的强烈竞争压力,间接地降低了外国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排斥了外国电影的市场竞争者。不言自明,此类“强管制”手段不但明显与WTO规则相悖,也带有计划经济的历史遗迹。保护本土电影的文化多样、实现文化兴国,是全球各国的共同目标和期待。中国在试图达成上述目标时应当优先选择与WTO义务相融合或冲突较少的措施。
我们不妨借鉴西方国家对电影采用的“弱管制”措施。称之为弱管制,是因为此类措施并不限制外国影片在本国的映演,不降低进口影片的市场占有率,其目的仅在于奖励、扶持本国电影的制作与发行,避免本国电影市场在自由贸易规则下被外国电影所掠食,同时保障了消费者选择观影的自由。一些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弱管制”措施主要包括:电影制作与销售的补贴、电影制作的低息贷款、奖励公私企业投资电影产业、税收减免优惠以及电影人才培育等。其中,补贴的方式是WTO规则允许的“柔和”手段。现今,在服务贸易领域,由于相关补贴问题尚未达成具体规则,WTO成员尽可在文化服务领域采取税收减免或贷款优惠政策以曲线救国(21);同样,GATT项下的“特定类型补贴的例外条款”也为各成员方在文化产品领域实行相关补贴措施提供了空间。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对电影产业的制作与发行采取补贴的政策。例如法国对电影的制作、发行所设计的“自动补贴模式”,只要该作品合乎“法国制作”的本国电影,即可依照电影的收益获得补贴。同时,法国要求电影公司必须将获得补贴的部分金额投入到下一部电影的制作中。法国用于电影产业的补贴预算一年即达到1.86亿欧元,其中半数以上用在本土电影的制作上。因此形成了良性循环,振兴了本国电影产业。(22)在税收优惠方面,欧盟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允许服务于本国电影产业的公司,其亏损项不记录在会计年度报表中,可与过去或未来的会计年度中分别提列;对于盈利的部分,有些国家特别承认该部分可免征税费,只要该公司继续将其盈余投入到电影的制作、新技术的研发以及新人员的培训等即可。(23)目前,在《电影促进法意见稿》条文中,中国已经决定采取诸如专项基金、税收优惠等“弱管制”措施以促进电影的繁荣发展,但该征求意见稿并未出台,同时相关配套法律规定也未颁布。可以说,在WTO规则下,“弱管制”措施替代“强管制”措施已经成为发展各国电影产业、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趋势。
2.国际法层面——WTO与《文化多样性公约》的程序关联
如前所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为在WTO体制下应当给予文化产品以特殊待遇,但由于美国的持续反对,该努力多次受挫。以欧盟为代表的WTO成员转而在WTO体制外寻求解决。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明确指出:“世界经济贸易之整合,尤其是通讯、媒体市场之整合,对文化多样性及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威胁。”(24)2001年,由于WTO成员方的相关努力无果,文化多样性议题迟迟无法获得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文化政策会议,与会国共同发表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年10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大会最终以148国赞成、2国反对的悬殊差异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公约在肯定文化产品作为“货物”所应具有的市场价值外,更明确承认了其文化和服务属性,强调了文化产品对传承各缔约国思想意识和展示各国风貌的重要性。同时,公约进一步确定了各成员在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有权依据自身的特殊国情,在本国境内采取适当政策措施以达到上述目的。中国是《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原始缔约国,依据该公约的规定,中国政府有权利根据本国电影产业的客观情况,维持以国有企业承担对进口电影进行内容审查的规定。那么,《文化多样性公约》同WTO规则之间是否存有一定的程序连接,使得该公约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存有解释和适用WTO法律规则的余地?
依据《争端解决程序谅解》(以下简称DSU),非WTO协定(包括《文化多样性公约》)同 WTO各项协定的程序连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法律的适用。依据DSU第1条和第11条规定,争端解决机构(包括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必须依据争议所涉及的WTO“适用协定”来处理贸易争端。非WTO协定、一般国际法原则不能独立构成确定争端方权利义务的适用法,但它们能够为解释WTO规则提供指导。其二,法律规则的解释。依据DSU第31条第2款的规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适用WTO规则时,应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解释国际条约应当考虑该相关国际法规则是否适用于各当事方之间”的习惯规则来阐明协定的内容。由上,《文化多样性公约》作为非WTO协定仅具有解释WTO规则的地位。在WTO的先前案例中,以“美国、加拿大、阿根廷诉欧盟转基因案”为例,欧盟曾援引《卡塔赫纳生物安全协定书》,寻求以WTO以外的国际法规则作为其维系转基因国内管理措施的正当性解释。该案专家组认为,依据国际条约的“习惯解释”规则,美国并非该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方,因此并不能要求专家组将其原则和规则考虑在内。不难理解,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排除上述公约作为解释WTO规则的原因来自“当事方之间关系的缺失”,即美国并非上述公约的缔约国。同时,争端解决机构也认为WTO的各项“适用协定”在争端解决的适用时是一个整体,彼此不产生任何歧义,而《文化多样性公约》所赋予的成员国权利同WTO成员的贸易自由化义务相排斥。不难推测,专家组在“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中回避讨论《文化多样性公约》在该案的适用与解释问题自在情理之中。
现今,世界各国对文化产品越发重视,《文化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在短短的4年间即达到99个,影响力越来越大。为解决两者在文化产品态度上的根本冲突,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若干完善WTO有关文化产品贸易规则的建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即是“程序连接法”。所谓程序连接法,是指通过某些“法律条文”或其他程序设计,将“贸易自由化”的普世规则与“文化多样性”的特殊规则实现程序连接,本质上为两者的冲突矛盾架构有效的桥梁,使得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相关案件时有必要考虑保护各成员的文化多样性。(25)具体包括:
其一,程序设计。通过部长大会决定的方式,在相关WTO协议中增加和《文化多样性公约》相联系的程序性条款,规定在自由贸易与保护文化多样性相冲突的情况下,解释WTO规则时,争端解决机构应考虑《文化多样性公约》。(26)依据WTO以往的实践,成员方可依据WTO协定第9条,以集体决策的形式将形成的“相关决定”纳入决议。如在多哈回合谈判中,该届会议原本未涵盖“民俗保护”及“生物多样性”等事项,但囿于各成员方的强烈要求,最终在《TRIPS协定与公共卫生宣言》中将上述问题纳入其中。(27)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文化多样性同生物多样性两者具有密切关系,既然WTO总理事会已经将生物多样性同贸易自由问题纳入谈判并形成决议,那么在文化多样性同贸易自由的互动中,应不难在总理事会或部长级会议中针对“文化多样性”问题形成相关决议。倘若在新一轮谈判中形成该决议,那么成员方再涉及文化争议案件时,可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项的规定,对条约进行上下文解释时应一并考虑“嗣后实践”(subsequent practice),并将该嗣后实践形成的部长会议或总理事会决议中所规定的文化多样性问题视为相关WTO涵盖协定义务的参考文件。
其二,法律条文。在WTO新一轮多边谈判中,将上述文化保护要素直接或间接的理念根植于WTO规则之中,允许WTO成员在其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中专门提及《文化多样性公约》,在相关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栏目中明确声明与《文化多样性公约》相一致的限制等。采用联系方法可以将《文化多样性公约》中的文化保护要素直接或间接合并在WTO法中。(28)由此,即便争端一方并非《文化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相关当事方仍可援引该公约实现促进和保护本土文化多样性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经贸的发展中,虽然大多数国家力主推进文化的多样性,力促形成文化的特殊性条款,但各国的国情及相关利益仍存有差异,一些贸易大国如中国和欧盟,应首先努力协调各自主张,力求统一立场,方可在后续WTO谈判中有的放矢,推动上述方案的形成。
注释:
①韩立余:《文化产品、版权保护和贸易规则》,《政法论坛》,2008年第3期。
②(24)Word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Our Creative Diversity,UNESCO,1996,p.64,p.104.
③Jan Wouters & Bart De Meester,The UNESCO Conven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WTO Law:A Case Study in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42(1),2008,p.205.
④Clinton Says Emerging Uruguay Round Pact Is in U.S.Interest Despite Shortcomings,Int'l Trade Daily(BNA),at D5(Dec.16,1993).转引自Lisa L.Garrett,Commerce Versus Culture:The Battl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over Audiovisual Trade Polices,19 N.C.J.Int' l L.& Com.Reg.552,1994,pp.553—554.
⑤John.H.Jackson,Construction a Constitution for Services in Trade.The World Economy.Vol.11(2).1988.
⑥⑦Canada-Certain Measures Concerning Periodicals,WT/DS31/AB/R,para.5.14,5.17.
⑧⑨⑩(17)China-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rtain 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WT/DS363/AB/R,para.10,para.22,para.195,p.374.
(11)Frederick Scott Gait,The Lift,Death and Rebirth of the“Culture Exception”i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Culture Protection and Intervention in the Face of American Pop Culture’s Hegemony.3 Wash.U.Global Stud.L.Rev.909,912,2004.
(12)Tania Voon,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18.
(13)(14)United States 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WT/DS285.paras.6.468-6.469.
(15)刘瑛:《GATT第20条(a)项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研究——以“中美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为视角》,《法商研究》,2010年第4期。
(16)Korea-Various Measures on Beef,WT/DS161,para.156.
(18)彭岳:《贸易与道德:中美文化产品争端的法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9)Mirela Keuschnigg,“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Physica-Verlag Heidelberg,1998.
(20)Michael Braun,Leigh Parker,“Trade in Culture:Consumable Product or Cherished Articulation of a Nation’s Soul?”,International & Policy,1993,pp.155-191.
(21)石静霞:《新一轮服务贸易谈判若干问题》,《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2)(23)Emmaunel Coca,Patrik Messerlin,The French Audiovisual Policy:Impact and Compatibility with Trade Negotiations,Hambur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3),p.11,p.13.
(25)陈卫东、石静霞:《WTO体制下文化政策措施的困境与出路》,《法商研究》,2010年第4期。
(26)薛狄、那力:《国际文化贸易的价值冲突和法律选择》,《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27)徐挥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障及促进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之潜在冲突与调和》,《政大法学评论》,2008年10月第99期。
(28)陈儒丹:《“非WTO协议”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适用》,《法学》,2009年第2期。
标签:wto论文; 文化多样性论文; gatt论文; 法律论文; 文化属性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服务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