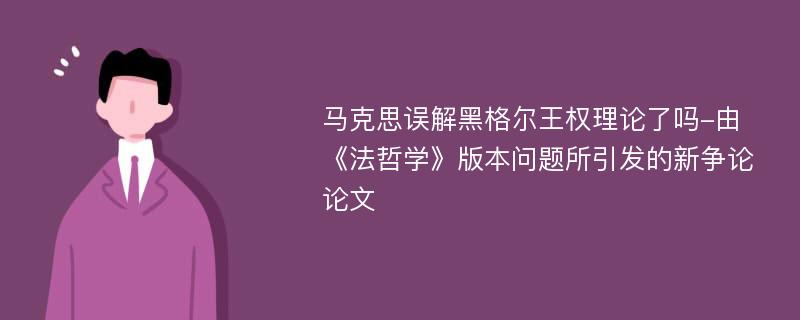
马克思误解黑格尔王权理论了吗? ——由《法哲学》版本问题所引发的新争论
梁燕晓
(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084)
摘 要: 王权理论,长期以来都是解读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绊脚石,也是黑格尔招致诋毁的源头,不过,随着法哲学讲义等新文献的陆续出版,西方学界开始研究《法哲学》版本问题,并重新思考黑格尔王权的复杂形象。这一新的研究趋势,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早期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王权理论的两大核心逻辑:王权的专断任性和王权的逻辑泛神论前提。将甘斯版《法哲学》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献对比,表明前一种批判是马克思“有意”忽视《法哲学》“补充(Zusatz)”部分而造成的部分误读;后一种批判,则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只是在《资本论》时期作了进一步的“深化”。总的来看,由于甘斯版《法哲学》内在的解释张力和自身当时相关文献背景知识的缺失,所以,在面对黑格尔王权学说时,马克思选择了与之进行一场痛击其形而上学基础而“有意”忽视其双面形象的错位的思想交锋。
关键词: 马克思;黑格尔;王权;《法哲学》版本
自1820年《法哲学原理》(以下简称《法哲学》)公开出版以来,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理论便饱受争议,其王权学说更是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一方面,黑格尔笔下的王权因其所具有的“自然出身论”“王位世袭”以及 “无限的主观决断”等特征,长期以来一直被诸多批评者视作黑格尔思想保守性的明证。鉴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曾表达过与之类似的观点,因此他自然也被划归在这一阵营之中。近年来,国内学界逐渐开始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即青年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合理地”理解和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虽然一些学者从黑格尔的角度指出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官僚制和立法权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注] 参见韩立新.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J].河北学刊,2009,29(1): 14-24;汪行福.黑格尔的官僚制理论与马克思的批判[J].教学与研究,2018(6): 24-33;李淑梅.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代议制因素的批判[J].江西社会科学,2014,34(2): 18-25. 但是对于王权学说却鲜有问津,这似乎预示着马克思对黑格尔王权学说的批判已成为板上钉钉的铁案。
另一方面,从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法哲学讲义等新文献的陆续出版,伊尔廷(Karl-Heinz Ilting)等西方学者开始区分“出版物中的黑格尔”与“课堂笔记中的黑格尔”,认为1820年公开出版的《法哲学》并不代表黑格尔真实的政治哲学思想,其王权学说也并非是为专制的普鲁士国家辩护,而是提倡立宪意义上的“虚君”。这一理论动态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因为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马克思便可能批判了一个“假黑格尔”、一个“假王权”。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本文将围绕《法哲学》版本差异视野下王权的诸争论展开,试图解答马克思是否真的误解了黑格尔的王权理论这一问题。
(2) 基坑与斜拱桩基承台边缘净距L对基坑围护桩变形的影响规律为: 随着边缘净距逐渐增大,基坑围护桩的水平位移逐渐减小且趋于稳定,当边缘净距达到25 m(此时L/H=1.25)时,即边缘净距超过一倍基坑开挖深度时,大水平推力斜拱桩基对基坑围护桩的变形影响比较小; 随着边缘净距逐渐增大,围护桩水平位移最大值出现的位置深度hL逐渐增大,斜拱桩基产生的水平推力对基坑围护桩水平位移的影响深度也逐渐减小,当边缘净距达到25 m时,影响深度基本为0。
一、马克思批判视野之外的《法哲学》版本问题
诚如伍德(Allen Wood)所言,海姆(Rudolf Haym)对把黑格尔解释为普鲁士保守主义辩护士的传统负有主要责任。[注] Allen W. Wood. Hegel’s Ethical Though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57-258. 尽管马克思于1843年便写作了严厉声讨黑格尔王权理论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但是由于该手稿命途多舛,直到1927年才真正问世,因此在思想史上塑造黑格尔保守形象的关键人物不是马克思,而是海姆。1857年,海姆在《黑格尔和他的时代》中将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与推行反动政策的普鲁士相联系,并断定它实质上是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国家威权主义哲学,之后此评价在思想史上保持着长久的影响力。
不过,在如何评价黑格尔王权学说的问题上,伊尔廷却发现海姆的观点十分“别致”。海姆一方面高度赞扬君主所体现的主观性原则,另一方面非常惋惜君主没有贯彻这一原则,反而倒退回到了普遍性和实体性原则,也就是说,黑格尔的君主并不是国家这一建筑物的地基或拱顶,而仅仅是最高处的十字架,其全部的意义仅在于说“是”和御笔圈点。[注] 此处暂且不讨论海姆并未像通常的批评者那样将君主的无限主观性等同于君主专制这一问题,只凸出海姆眼中黑格尔王权形象的两面性。 可见,在海姆看来,《法哲学》中君主的形象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极其复杂的。无独有偶,伊尔廷发现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在《黑格尔和国家》中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即黑格尔的君主,从体系的角度看是所有国家活动的来源,但从实践的角度看仅仅是空洞的形式上的意愿。[注] K.-H.Ilting. Einleitung zur “Rechtsphilosophie” von 1820 und Hegels 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 [A]//K.-H.Ilting. G.W.F.Hegel: 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 1818-1831, Band 1.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iedrich Frommann Verlag[M]. 1973: 25-26.
[9]威廉·华兹华斯[英],黄杲炘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6-27页.
因此,这里有必要谈一下《法哲学》的结构和版本问题。[注] 参见Anmerkung der Redaktion zu Band 7[A]//G.W.F.Hegel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7: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M]. 1970: 524-531和邓安庆.黑格尔《法哲学》版本考[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2(6): 55-63. 目前通行的中译本《法哲学》[注]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每一节主要由正文、附释和补充三部分构成。不过,在1820年最初出版的《法哲学》(以下简称“原版《法哲学》”)中,每一节实际上仅仅包含正文和附释两个部分,其中附释是对正文的进一步阐发。黑格尔去世(1831年)后,他的学生甘斯(Eduard Gans)于1833年编辑了新版的《法哲学》(以下简称“甘斯版《法哲学》”),与原版《法哲学》相比,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增加了补充部分。所谓的“补充”,是甘斯从黑格尔的亲手札记和学生听课笔记中选取摘录的。原来,原版《法哲学》出版后,黑格尔每次上法哲学课程时,除了照本宣科以外,仍会对书中的内容进行随手“笺注”和课堂口头“补充”。由于黑格尔的手写“笺注”大多数是一些不连贯的单词,因此甘斯主要选用了两份记录在学生笔记[注] 这两份笔记主要是指霍陀(H.G.Hotho)记录1822-1823年讲座的笔记和格雷斯海姆(K.G.von Griesheim)记录1824-1825年讲座的笔记。 中的口头补充。
甘斯所遴选的“补充”在随后的《法哲学》博兰德(Bolland)版(1902年)、格洛克纳(Glockner)版(1931年)和理论著作(Theorie-Werkausgabe)版(1970年)中都得到了保留。不过,批评也接踵而至,虽然甘斯一再保证 “补充”中所包含的东西都来自黑格尔所给予的材料,但是后人仍然质疑他所遴选的“补充”材料的不完整性与任意性。为此,《法哲学》的拉松(Lasson)版(1912年)将“补充”整体移到了书后的附录中,豪夫迈斯特(Hoffmeister)版(1955年)和历史考证(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版(2009年)则直接删除了“补充”。这场旷日持久的围绕 “补充”问题的文献争论,在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伊尔廷版(1973-1974年)《法哲学》中得到了初步解决,因为伊尔廷将黑格尔1818-1831年间的几个重要的法哲学讲义按照历史顺序排列出版。至此,人们可以相对较为全面地了解黑格尔法哲学的发展脉络,并客观地审视《法哲学》的印刷版与黑格尔“口头补充”版之间的差异。
通过文献的比较,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马克思“厚”行政权、立法权的补充而“薄”王权的补充的倾向,尤其忽视了伊尔廷所强调的有关王权的那几处关键性补充。而这样的一种 “明显偏心”的做法,显然不能被简单地推脱为马克思的无意之举,试想,连海姆这种极其严厉的批评者都注意到了补充中黑格尔王权的多面性或歧义性,马克思对此却只字未提。不得不说,这是马克思留给后来研究者的一道“哥德巴赫猜想”。
推进农业发展区域化布局。积极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区域布局规划,完善涉农优惠扶持政策,重点支持绿色果蔬、苗木花卉、食用菌、良种繁育等产业发展,做优葡萄、冬枣、莲藕等特色农产品,推动优质小麦、谷子等大宗粮食作物种子化发展,鼓励种植优质花生、油用牡丹和油菜等油料作物。
其一,拒斥形而上学与逻辑学,立足经验进行建构。伍德宣称,对于今人而言,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是死的,只有其社会政治思想才是活的。[注] [英]艾伦·伍德.黑格尔的伦理思想[M].黄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7-9. 霍耐特认为,虽然20世纪后半叶以来,黑格尔的法哲学获得了强劲复兴,但是始终无法与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所代表的康德传统相抗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逻辑学的论证方式,“《逻辑学》是关于精神的本体论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往往是令人费解的”。[注] [德]霍耐特.不确定性之痛[M].王晓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8. 为此,在《不确定性之痛》和《自由的权利》中,霍耐特抛弃了“普遍——特殊——单一”的概念逻辑,直接采用“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具体自由”的思想史模式来解读《法哲学》的抽象法、道德和伦理,努力使其“再现实化”。
位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腹地的通辽市,享有“内蒙古粮仓”的美誉。2013年,通辽以国家实施“节水增粮行动”为契机,按照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以实施“8511521113”工程统揽全市农村牧区工作,大力发展节水高效农业,建设3个十万亩连片节水增粮高产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区,既节约了地下水资源,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升级,又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实施“节水增粮行动”起到示范作用。
依据上述的法哲学版本史可见,海姆等人所指摘的王权的矛盾性,实质上体现了黑格尔在正式出版物与课堂口头表达之间的思想张力。那么,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王权理论时,是否注意到了正文与补充之间的区别,是否认识到了王权的多维度形象呢?
二、马克思的王权批判与《法哲学》讲义之间的思想张力
为何马克思有意忽略《法哲学》王权部分的“补充”呢?既然无法从文献的角度给出解释,那么我们便尝试从马克思王权批判的思想理路进入。考虑到上文中提到的《法哲学》版本问题,我们会依次阐释“正文和附释”中黑格尔的王权论证逻辑、马克思对“正文和附释”中王权的批判逻辑和“补充”中黑格尔的王权辩护逻辑,进而比较三种逻辑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审视第三种逻辑能否形成对第二种逻辑的解构。
与菲尔默(Robert Filmer)等人通过神权来论证君权的做法不同,黑格尔更多地诉诸理念(概念)的展开逻辑。首先,就宏观层面的立宪君主制而言,它是依据理念发展的结果,“国家成长为君主立宪制乃是现代的成就,在现代世界,实体性的理念获得了无限的形式”。[注]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87. 并且,不同于近代基于制衡原则的三权分立制度,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制依据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单一性”原则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王权,其中,王权是最后决断的主观性权力,是其他一切权力的归宿和开端。其次,就微观层面的王权而言,黑格尔使用经验论证和概念逻辑论证相结合的方式来阐明它的合理性。第一,国家必须拥有统一的主权。国家的对外主权表现在,相对于他国而言,它具有独立自主性;对内主权表现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各种职能和权力形成一个有机体,而非病态的孤立原子。第二,主权在君。主权作为国家的主观性,作为国家的人格,“只有作为一个人,作为君主才是现实的”。[注]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96. 也就是说,主权必须落实到一个具体的自然肉身之上,由现实中的君主来代表。第三,君主凭自然出身决定。现实中代表主权的“X君主”是通过直接自然的肉体出生被先天选定的,其概念依据在于“意志的纯自我规定(简单概念本身)直接转变为‘这个’和自然定在,而没有特殊内容(行动中的目的)作为中介”。[注]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01. 第四,君主世袭而非选举。黑格尔从效果论的角度谈到,世袭制“能避免御座周围的派系倾轧和国家权力的削弱与破坏”,而选举制则会使“国家权力仰仗私人意志的恩赐”,进而削弱国家主权,瓦解甚至摧毁国家的存在。[注]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03-304.
面对“正文和附释”中黑格尔对王权的论证,马克思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反驳。一方面,马克思揪住黑格尔“逻辑泛神论”的小辫子不放,认为君主立宪制乃至整个法哲学不过是逻辑学的注脚与补充,这是一种主语与谓语、现实与观念的颠倒。同时,黑格尔在论证“君主的自然出身”时出现了逻辑跳跃,由自我规定的理性直接过渡为自然规定性,从而省略了其逻辑学所固有的“中介”环节,用“普遍性——单一性”的二元逻辑代替“普遍性——特殊性——单一性”的三元逻辑,这明显与逻辑学的体系不相容。另一方面,抛开黑格尔的概念论证,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王权本质上代表的是偶然性与任性。国家需要统一的主权和主权要由一个具体的个人来代表,对于这两点,马克思并不反对,“有谁曾经怀疑过国家是通过各个人来行动的呢?”[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4. 但是,作为国家这一统一体的代表的“某一个体”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君主,也可能是某一人民。另外,即使退一步,暂时承认“主权在君”这一前提,马克思也不赞同君主的产生机制——由自然出身而非选举来决定,更别提其所附带的长子继承制。“黑格尔证明,君主一定是肉体出生的,这一点谁也没有怀疑过;但他没有证明,出生造就君主”,[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4. 如果诉诸出身来为王权及其继承制辩护,那么就等同于将君王下降到牲畜的层面,将国王的最高政治使命定位为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生殖活动。此外,像赦免权、决断政务而不承担责任之类的权力,在马克思眼中,也无不体现了君王的任性。可见,逻辑泛神论与君主的专断任性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王权学说的两大核心逻辑。
通过回顾思想史,伊尔廷从黑格尔的批评者那里发现了王权的“非专制”维度,不过,这只是他为黑格尔正名的第一步。接着,伊尔廷又从文献的角度指出,海姆和罗森茨威格提及王权“橡皮图章”形象的文本都出自《法哲学》的“补充”(Zusatz)部分,而“补充”背后所涉及的正是《法哲学》的版本问题。事实上,《法哲学》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版本,且诸版本之间关于“王权”的说法存在着足以做出截然不同解读的差异性,而海姆等人正是因为忽视了版本问题才无法理解黑格尔王权学说的内在冲突。
至此,本文已展示了“补充”中的王权辩护逻辑与马克思的王权批判逻辑之间的内在张力。笔者认为,马克思应该看到了“补充”与“正文”中王权形象的差异性,但是鉴于当时相关背景知识的匮乏且为了保持批判逻辑的连贯性,马克思策略性地选择了忽略该部分内容。
针对用户烟气轮机内壁催化剂结垢导致烟气轮机效率下降的问题,渤海装备以新型高效弯扭复合型叶片、高效扩压器设计、动叶过渡衬环、静叶衬环采防结垢等新技术为切入点,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烟气轮机效率从78%提升至82%,一年可为用户累计多创效1000多万元;非计划停车清垢周期由1个月延长至1年以上,设备的检修周期由1年延长至3~4年,全面满足了客户对烟气轮机产品“安稳长满优”的综合要求。
在一个组织完善的国家中,问题仅在于作形式上决断的顶峰和对抗激情的自然堡垒。因此要求君主具有客观特质是不正确的。君主只用说一声“是”,并御笔一点。其实,顶峰应该是这样的,即他品质的特殊性格不是有意义的东西。[注]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02.
可见,在“补充”中,黑格尔的王权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君主并没有无限的决断权,反而受到内阁专家、国家法律制度的限制,“说是”与“签字”成为他的生活日常,俨然一位橡皮图章意义上的有限君主。诺尔斯(Dudley Knowles)[注] Dudley Knowles. Hegel and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329-330. 用硬阅读(hard reading)和软阅读(soft reading)来对应 “正文”和“补充”,他指出通过“硬阅读”得到的君主形象类似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姆三世,他是一个可疑和反复无常的改革反对派;而通过“软阅读”得到的君主形象类似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对于国家仅具有象征意义。因此,“补充”中的君主是非任性、非专断的,其特殊个性是不足为虑的,而这样一位 “虚君”即使是由出生决定并世袭继承下去,也不给国家带来危害。不过,这一王权形象恰恰与马克思所批判的“专断任性”逻辑相违背,如若将其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中,那么必然会削弱马克思的批判力度,甚至违背其批判方向。在此情况下,马克思有理由舍弃于己不利的“补充”。
尽管已经阐明了“补充”与“正文”之间王权形象的差异性,但是尚不清楚黑格尔究竟为何要做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述。伊尔廷诉诸当时的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在完成1818-1819学年冬季学期的法哲学课程后,黑格尔从1819年3月便开始加工整理《法哲学》一书,并计划于9月份将其出版。然而,随着激进学生桑德(Carl Sand)刺杀俄国沙皇的代理人兼作家科策布(Kotzebue)事件的持续发酵,普鲁士的政治气候由改革转向了复辟,9月份当局通过了卡尔斯巴德决议,决定在大学里实行严格的政治控制,可随时解雇政治上不被欢迎的教师,并加强对出版物的预先审查。有鉴于此,黑格尔推迟了当年的出版计划,并对书稿进行了大幅修改。[注] K.-H.Ilting. Einleitung zur “Rechtsphilosophie” von 1820 und Hegels 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 [A]//K.-H.Ilting. G.W.F.Hegel: 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1818-1831, Band 1.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iedrich Frommann Verlag[M]. 1973: 43-68. 通过仔细对比1818/1819年法哲学讲义和1820年出版的《法哲学》,伊尔廷发现讲义中的王权是仅仅宣誓意义上的国家首脑,其地位甚至被消减为“政治无效性”。[注] K.-H.Ilting. Hegel’s Concept of the State and Marx’s Early Critique [A]//Pelczynski.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93-113. 可见,在1820年《法哲学》之前或之后的讲义中,王权仅仅是一种象征,而之所以在正式出版物中它被赋予无限决断权,依照伊尔廷的解释,恐怕是黑格尔的明哲保身之举。
要判断人工智能创作有无自然人作者介入,首先需要了解自然人干预人工智能的方式。虽然人工智能创作过程是完全自动的,人工智能程序一旦开始运行人就无法介入其中,但人工干预对于人工智能创作并非无关紧要。人工智能业界的一句戏言“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工干预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的影响程度。一般来说,自然人对人工智能创作的人工干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那么,“补充”中的王权形象能否构成对马克思上述批判的“反批判”呢?能否构成马克思“遗漏”这一部分内容的理由呢?事实上,伊尔廷等人经常加以引用的是279节和280节的“补充”,现将其要点摘录如下:
三、现代语境下如何理解马克思对王权形而上学前提的批判
王权的专断任性和王权的逻辑泛神论前提,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王权理论的两大核心逻辑。诚然,前一种经验批判已被前文证明是马克思有意的误解;但是,后一种逻辑批判尚未得到应有的说明。诚如韦伯所言,近代是一个祛魅的时代。启蒙所高扬的人的主体性,促使一切超验的存在物抑或本体论保证都从这个世界退场隐匿。在此境况下,如何安置黑格尔王权的形而上学前提——“理念”“概念”等呢?现代学者大致有三种选择路径。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几乎逐字逐句地摘抄了《法哲学》第261—313节的相关内容。鉴于该手稿创作于1843年,且其中出现了大量的“补充”,因此马克思当时所阅读的应该是甘斯版《法哲学》。 然而,通过比较甘斯版《法哲学》中原有的“补充”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摘录的“补充”之间的差异性,笔者发现马克思选择性地忽略了王权部分的补充。具体而言,王权部分(第275-286节)共有12小节,甘斯版《法哲学》中7个小节(第275、276、277、279、280、281、282节)含有“补充”,而马克思仅仅摘录了第276节“补充”中的一句话,“各个环节的这种理想性正像有机体的生命一样”[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8. 。与之相反,行政权和立法权部分的情形却大为不同:行政权部分(第287-297节)共有11节,甘斯版《法哲学》中2个小节(第290、297节)含有“补充”,马克思对此皆有提及,并详细摘录了297节的补充;立法权部分(第298-313节)共有16节,甘斯版《法哲学》中7个小节(第298、299、300、301、302、306、309节)含有“补充”,马克思对除第300节以外的其余6个小节的“补充”都进行了摘录。
比较困难的是把这个“我要这样”作为人来领会。这不等于说君主可以为所欲为,毋宁说他是受咨议的具体内容的束缚的。当国家制度巩固的时候,他除了签署之外,更没有别的事可做。[注]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00.
其二,深化逻辑学的系统性解读。布鲁克斯(Thom Brooks)[注] Thom Brooks.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A systematic read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等人是这一路径的代表性人物。由于黑格尔在《法哲学》序言中提及,“关于思辨认识的本性,我在我的《逻辑学》中已予详尽阐述;所以在本纲要中我仅仅对进展和方法随时略加说明”,[注]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 因此布鲁克斯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法哲学》,我们要做的不是抛弃《逻辑学》,反而是更加系统地利用它。为此,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战争、法律、家庭、道德、惩罚、财产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证明在缺失系统逻辑方法的指导下,这些问题根本得不到真正澄清。
其三,重构“精神”概念的内核,将其转化为近代的主体。泰勒认为,随着现代文明在工业化、技术化和理性化方向上的发展,“没有人相信他(即黑格尔,引者注)的核心本体论命题,即宇宙是由其本质为理性必然性的某个精神设定的”,而他的学生青年黑格尔派,则顺应时代潮流完成了“从精神向人的转变”。[注] [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M].张国清,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826,839. 伊尔廷则将“精神”具体理解为“人类的自我意识”,认为《法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自由意识的现象学,它阐明了“人类自由的自我意识如何可以把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等制度理解为人类自由的条件”。[注] Karl-Heinz Ilting. Die Dialektik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A]//Paolo Becchi, Hansgeorg Hoppe. Karl-Heinz Ilting: Aufsätze über Hegel[M]. Frankfurt am Main: Humanities Online. 2006: 114.
在笔者看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马克思接近于第一条路径,即直接拒斥黑格尔神秘的逻辑。在逻辑泛神论的指责中,马克思借鉴费尔巴哈主谓颠倒的逻辑,认为不是观念规定人而是人规定观念,王权的合法性依据也并不在于神秘的理念。《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接近于第二和第三条路径,即重新审视黑格尔的逻辑学所蕴含的方法性原则,并将其归纳为革命辩证法,同时,将神秘的“概念主体”阐释为“人类实践活动”,抑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运动”。当黑格尔被视为“死狗”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却公开宣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认为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其合理内核体现在“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2.
可见,黑格尔王权理论(或者说法哲学)的形而上学前提,被马克思细分为两个部分:概念的神秘主体和概念所揭示的方法。《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马克思对两者都持否定态度,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因逻辑主体的神秘性而直接放弃了对逻辑方法的探寻。拒斥超验主体,这是近代哲学的核心特征,马克思哲学也不例外。不过,此后的马克思逐渐意识到逻辑辩证法在方法论层面的优越性,并利用它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将逻辑主体置换为人类主体。因此,在马克思对王权形而上学前提的批判中存在着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四、结 语
《法哲学》版本问题的出现,为解读黑格尔的王权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为客观审视马克思对黑格尔王权理论的批判创造了新的条件。对于经验层面的王权权力,马克思严厉地批评了“正文”中体现的专断任性,而忽视了“补充”中呈现的“虚君”维度;对于王权神秘的形而上学基础,马克思直到《资本论》时期也还在批判这种错误的主谓颠倒,不过,此时他已经进一步创造性地转换了其形而上学的主体,并吸收了其中合理的方法论原则。总的来看,由于甘斯版《法哲学》内在的解释张力和自身当时相关文献背景知识的不足,马克思在面对黑格尔王权学说时,选择了与之进行一场痛击其形而上学基础而“有意”忽视其双面形象的错位的思想交锋!
本文通过问卷方式获取数据,最终得到697个样本。样本筛选标准:一是根据GEM对新创企业的界定标准,选择成立时间在42个月内的企业;二是剔除了没有创新投入的样本;三是剔除了缺失量大的样本。
当然,从文本研究的角度指出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王权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并不意味着是对马克思的贬低,反而是对马克思哲学真精神的一种坚持。因为一方面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存在发展变化阶段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恰恰处于这一关键的转型期;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历史地思”,[注] 何中华.历史地思:马克思哲学新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即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看待某个问题,审视某个人的行为方式与立场,而这一学术视角,不仅要求能用来批判马克思理论对手的学说,而且也要求可以用来审视马克思自身的理论。
Did Marx Misunderstand Hegel’s Theory of Monarchy: A New Argument Arising from the Issue of the Version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LIANG Yanxia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monarchy has long been a stumbling block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origin of Hegel’s defamation. However, with the successive publication of new documents such as Lectures on Philosophy of Right , Western scholars began to study the issue of the version of Philosophy of Right and rethink the complex image of Hegel’s monarchy. Drawing on this research approach,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two core logics of early Marx’s critique of royal power: its arbitrariness and its “logical pantheistic mysticism”. A comparison of Gans’ editorial Philosophy of Right andCritique of Hegel ’s Doctrine of the State shows that the former criticism is the misreading of Marx’s “intentional” neglect of the “Zusatz” in Philosophy of Right while the latter is always adhered to by Marx and is further “deepened” during the “Capital ” period. In general, due to the inherent interpretation tension of Gans’ version of Philosophy of Right and his lack of knowledge of relevant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in the face of Hegel’s theory of royal power, Marx chose to engage in a dislocational confrontation, crushing its metaphysical basis and “intentionally” ignoring its double-sided image.
Key words: Marx; Hegel; monarchy; version of Philosophy of Right
作者简介: 梁燕晓,清华大学哲学系与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生。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806210408)、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黑格尔的自由理论研究”(20151080425)
DOI: 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9.02.011
(责任编辑: 黄谷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