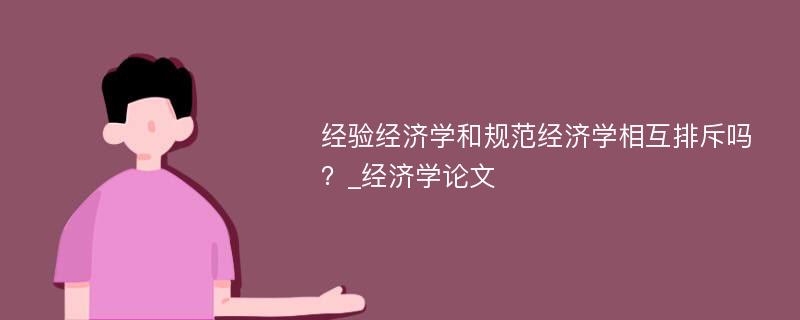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相互排斥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实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对立起来,是我国经济学界当前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作者区分了评价性事实判断与描述性事实判断,并由此证伪了上述观点的理论渊源——“休谟命题”。在此基础上,作者讨论了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关系,得出了二者是协调与互补的结论。针对我国经济学的现状,作者认为应构建二者协调互补的大经济学框架。
关键词:实证经济学 规范经济学 对应与排斥 协调与互补
一、导言
依据“是——应该是”二分法原则,经济学被区分为两大分支,即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Senior,N.W.,1827)。实证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现象“是什么(What it is)”的知识体系,而规范经济学则是关于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What it should be)”的知识体系。形成这两大知识体系的主要研究方法就分别是实证法(Positive method)与规范法(Normative method)。由于对科学的本质属性、经济学研究中是否能够摆脱价值判断,以及对实证法与规范法两种方法范式及其间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差异,经济学者们分化到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两面旗帜下(本文分别称之为实证经济学者和规范经济学者,下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者都可以截然区分为这两类,实际情形复杂得多。)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及它们的研究方法俨然相互对立、排互排斥,对立与排斥似乎成了这两大经济学分支及它们的研究方法范式间关系的本质特征。
本文将从认识论及证伪休谟命题等角度深入剖析,最终形成以下结论:视对立与排斥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及它们的研究方法间关系的本质特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协调与互补才是其本质特征。
二、休谟命题的证伪
大卫·休谟(Hume,D.)在《论人的本质》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问题“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此命题在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之间做了一刀切的逻辑区分,这就是休谟命题(Hume proposition),又被喻作“休谟的铡刀”。休谟的“铡刀”也使经济学者们为经济学当中是否涉及价值判断而争吵不休,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成了区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说,“是什么”乃是对客观事物的状况及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的事实性陈述,也就是事实判断;而“应该是什么”则是价值主体(即人)对价值客观(即客观事物及其间的关系)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的需要的一种评价性陈述,即对价值主本与价值客体间的价值关系的陈述,也就是价值判断。当然,价值判断并不是一定都采用“应该是……”这种形式的陈述。可见,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基础,而价值判断是在事实判断基础上加入了一种新的因素,即人的主观需要、人的理念与价值观。由此来看,既然价值判断包含了事实判断所不具有的新因素,自然由事实判断是无法推论出价值判断的,即人们不能从“是什么”中推论出“应该是什么”,如我们不可能从“小A偷东西”这一事实判断中推论出“小A偷东西是可耻的”这一价值判断。至此,休谟命题在一般社会领域中似乎是成立的。而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它“是什么”就指导人类“应该怎么做”,规定着自然事物“应该是什么”,且人类在面对自身以外的自然界时,其价值判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人类应该遵循客观规律,这才是符合人类福祉的”。这样一来,在自然科学领域可以说休谟命题是不成立的,或休谟命题不存在(由于面对自然界时人类价值判断的高度一致性使得在自然科学领域价值判断似乎“消失”了,不存在)。
但是,依据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价值判断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依存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实践,存在着“真”“假”之分(“真”的就是符合特定情境中的价值关系,但并不一定是合理的)因而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价值判断本身是可以被检验和证伪的。虽然在面对人类自身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时,面对自然界时的人类价值判断的那种高度一致性不复存在,每个人会从各自不同的情境出发作出多种多样的是非好坏及应该与否的价值判断,但这并不妨碍对价值判断的验证。当某一价值判断通过了检验(这已是实证研究了),则可以形成一个关于这一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的确实存在的事实性陈述。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是一个关于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即一个关于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间的价值关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如经验证了的“小B认为小A偷东西是可耻的”、“大多数人认为小A偷东西是可耻的”、“大家都认为小A偷东西是可耻的”等陈述,尽管“小A偷东西是可耻的”这一价值判断是小B或大多数人或大家作出的,但这三种陈述都是关于这一价值判断的事实性陈述,而不再是一个价值判断了,即存在“小B认为或大多数人认为或大家认为小A偷东西是可耻的”这一事实。再如,当我说“效率应当优先于公平”时,我在作价值判断,而当我说“某经济学者认为效率应当优先于公平”时,我是在作一事实判断。而上述这些关于价值判断确实存在与否的事实判断也是可检验、可证伪的。进行关涉价值判断的经济问题研究时,首先需要进行的就是检验这一类事实判断。这样一来,休谟命题就不再适用了,也就是说,“人们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此处的“是”就是指关于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我们不妨称之为评价性事实判断(Appraising fact judgments),而把另一不含任何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称之为描述性事实判断或纯粹事实判断(descriptive fact judgments or pure fact judgments)。如从“大家认为偷东西是可耻的”及“小A偷东西”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事实判断中推论出“小A偷东西是可耻的”这一价值判断。这里所推出的价值判断的普遍意义就会小些直至最小。也就是说,价值判断的存在方式是多层次的,既有普遍意义最小的以某个社会成员为载体的价值判断,也有多层次的普遍意义较大的以某一社会成员群体为载体的价值判断,这一群体可以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社会成员直至全人类。随着载体范围的扩展,价值判断也就越具普遍意义。因此,在研究关涉价值判断的经济问题时,首先就需确定经济学者所要采用的价值判断的普遍意义有多大,因为,尽管较合理的价值判断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少数人意愿服从于多数人的意愿”的民主制度虽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坏处最少的制度。
因此,休谟命题看来只有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纯粹事实判断(亦即描述性事实判断)上才可能是成立的。但是,单个的纯粹事实判断是毫无研究意义的,只有把它们联结在一起运用思维的力量归纳推导出某些具有较普遍意义的事实性陈述(亦即所谓规律性认识)时才有意义。此时这种不含价值判断的规律性认识具有自然律性质,与自然律一样否定了休谟命题。当然,由于这种规律性认识主要是一种统计规律性认识,难免会存在个别甚至较多的反例,其对休谟命题的否定力度不如自然律及关于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那样强大。
从以上论述来看,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即休谟命题基本上是不成立的,或者说,休谟逆命题基本上是成立的,即“人们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此处的“是”包括评价性事实判断和描述性事实判断(即纯粹事实判断)两个方面,由此二“是”共同推论出“应该是”。
三、对实证经济学者观点的分析
先让我们来看看实证经济学者的观点。且不论经济现象与问题中或显或隐的包含着价值判断的那些评价性事实判断,仅就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纯粹或描述性经济事实判断而言,实证经济学者运用实证法作用于这些纯粹经济事实判断建立起实证经济学,若只到此为止,那么经济学除了是一堆尚未被证伪的具有一定统计规律性的假设的集合外,对经济实践没有什么意义。要使经济学达到认识论的目的,势必尚需以这些被实证检验了的假设为前提去进行规范研究,从而建立规范经济学,并将包括经济政策建议在内的规范经济研究成果用来指导经济实践的进行,以推动经济的良性发展。这才是经济学的最终目的之所在,是经济学研究的巨大魅力之所在,也是包括实证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得以发展的动力之所在。事实,当实证经济学者指出了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途径等时,他已经是在进行规范研究了,虽然他不建议应该采取其中哪一条途径。因为这些可能途径的提出一定是基于和决定于某些前提假设条件,由这些前提假设条件规范演绎而来,研究者潜意识中的价值判断也极可能无形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只要实证经济学者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他实际上就在规定着未来政策等的选择范围与方向,含有强烈的规范成分。这并不奇怪,当实证经济学者孜孜不倦地对大量经济学假设命题进行经验求证时,他们的潜意识里就是渴求赋予这些假设命题的普遍意义。
当然,有人会指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实证经济学者所运用的实证法本身已并非纯粹的经验归纳,其中包含了演绎法的运用,即从归纳出的假设命题出发进行演绎以求得可供观察的结果,然后将该演绎所得的结果与实证经验相比较以检验所求证的假设命题。如果将演绎视作规范法的核心的话,那么,实证法中包含有规范法的因素。实证经济学对此的忽视则可能起因于他们对规范法所作的数学式的公理性假设演绎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但总之可见,对于以纯粹经济事实判断为基础进行的实证经济学研究来说,无论是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方法的采用,还是形成的实证研究成果等均或多或少带有价值判断和规范的成分。
无疑,经济现象与问题中更多的是关涉价值判断的现象与问题,这也就是众多的实证经济学课题都或显或隐地包容判价值判断的原因之所在(尽管实证经济学者对此可能视而不见)。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价值判断是可检验、可证伪的,存在“真”“假”之分,并不是纯粹主观、不可检验的。价值判断带有经验特征,具有历史性,具有多层次性的特点。此时,实证经济学的意义就更为凸现出来,那就是对那些可能或已经作为规范经济学规范演绎出来的价值判断进行验证,以确定其“真”“假”及其统计规律性有多强,从而有效防止一些规范经济学者以所谓“先验的、内省的”为借口来武断地赋予其个人或某一社会成员群休的价值判断以普遍意义,并以此为规范研究的起点。只有当被实证经济学研究所验证具有较高的统计规律性的价值判断被规范经济学研究所运用,然后以规范研究成果付诸经济实践,并以实践经验来检验和发展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如此无限延续下来才会形成一个经济实践和经济学互动发展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具有较高统计规律性的价值判断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以其为指导来推进的经济实践是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谋福利的,当然,这还赖于实证经济学研究和规范经济学研究工作本身的质量。
其实,上述对价值判断的实证研究成果主要是通过对该价值判断的确实存在与否的事实判断,即评价性事实判断进行验证来取得的,而不是直接针对价值判断进行验证。这样,休谟逆命题的奇迹就发生了,由“是”推论出了“应该是”。这里的“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实证经济学验证了的关于纯粹经济事实判断(亦即描述性经济事实判断)的带有自然规律特性的“是”,二是经实证经济学验证了的关于经济学中所涉及的价值判断的评价性事实判断这个“是”。此二“是”构成了实证经济学,由此二“是”就可以推论出“应该是”的经济学,即规范经济学。但是,由于实证经济学者否定了第二个“是”的客观存在,只研究第一个“是”,而“应该是”往往是将前二个“是”综合在一起推论得出,所以他们只好侧身于规范经济学之外了。
四、对规范经济学者观点的分析
以上我们讨论了实证经济学对价值判断及规范经济学之依赖及其对规范经济学之重要意义,这已经足以驳斥规范经济学者的观点了。规范经济学者认为,他们所赖以规范演绎的是一些先验的、内省的价值判断等前提假设,也就是说,其前提是不可检验、也无需检验的,并企图凭此建立起一套类似于由公理性假设演绎而成的数学体系那样“科学”的经济学体系。依据唯物史观,不存在任何所谓先验的、内省的价值判断,连人本身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更何况其思想,其价值判断。虽然规范研究成果是演绎而来,具有必然性,但其演绎的前提应是经过实证检验的,并且还要通过将规范研究成果付诸经济实践,以实践经验来检验和修正。也就是说,规范法只是从一定的前提出发进行演绎的方法,其前提之真假及规律性则是必须经过检验的,而不存在天生公理性、无需检验的前提。数学式的公理性假设演绎法只是规范法的一种特例,并不适于经济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规范演绎的前提的价值判断等假设是否具有充分的统计规律性,对于规范研究成果及由之指导进行的经济实践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此外,在传统的规范经济学者看来,实证经济学是不科学的,因为经验归纳的结论是或然的,由特称陈述到达全称陈述是不可靠的,孰不知任何理论只要是具有可证伪性且尚未被证伪就可以认为是科学的。况且据现代科学中的统计规律性和相对真理观,即使被个例证伪的理论也不失其科学性(故有实证研究是为理论寻找其适用的边界一说)。所以,传统的规范经济学者在否定了实证法的科学性及其作用之时,也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沼,因此他们只好为自己的规范研究寻找一些所谓先验的、内省的、不言自明的前提。这种把规范法作数学式的公理性假设演绎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也使他们只得如此。而事实上他们所赖以规范演绎的前提无不带有经验特征,他们规范演绎的方向也受经验的影响,他们规范研究的成果最终还要受实践经验的检验,对于这一些,他们只好视而不见。可见,规范经济学者既否定了上述第一个“是”的客观存在,又否定了第二个“是”的科学性,所以他们只好把经验的东西带上“先验、内省”的帽子,借助于数学式的公理性假设演绎法来建立“应该是”的经济学。
行文至此,笼罩在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实证法与规范法之间的对立与排斥的迷雾已经廊清,那种将它们相互对立排斥起来的观点看法,其实是不堪一击的。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那道“休谟鸿沟”被填平了,一个大经济学框架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协调互补、合二为一、一以贯之,实证法与规范法相得益彰、共放异彩。而这一大经济学框架的哲学基础就是唯物辩证的认识论和唯物史观。这一大经济学框架还有一个重要的实践基础,那就是,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与政府这看不见与看得见的两只“手”共同操作的混合经济,在此经济体制下,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与政府失败(government failure)并存。
五、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学者形成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的有关观点出发去进行规范研究的传统,有趣的是,这一传统倒颇有几分类似于西方规范经济学者作数学式的公理性假设演绎法理解的规范法传统。这在东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相映成趣,但是,其成因则是根本不同的。自然,我们也不重视甚至完全忽视实证研究,如我国经济学者曾赖以进行规范研究的两个重要前提,即“人人是大公无私的,中央计划部门是完全信息的”这两个假设,就是未经实证研究检验的明证。当然,这受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规范性及当时的研究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在由上往下运作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尚未构成严重危机。但在今天,我国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领域呈现出众多的非成型、非规范态和极具特殊性的纷繁复杂的现象与问题,这些现象与问题涉及到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的各个领域,且带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初创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特征。显然,这些现象与问题是无法纳入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理论框架进行解释和解决的。由于市场经济的共性,我们可以充分引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但若想成功地把这些基于与我国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上的成熟态的市场经济理论框架直接套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上显然是一场白日梦。这就要求我国经济学者一方面要完整地把握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注意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另一方面要在扬其长、避期短地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大力强调实证研究精神。“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需要自己河里的石头,他山之石虽可攻玉,但不可能摸着他人河里的石头过自己的河,河情不一样。因此,唯有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进行认真老实的、全方位的实证研究,运用已有的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进行大胆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才能创立起能概括我国这些非成型、非规范态、极具特殊性的经济现象与问题的范畴、概念和理论模式,藉此建立能合理解释、预测和指导我国经济实践的经济学框架,并藉此搭起一座通向经济学国际交流的桥梁。
前面我们已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经济学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规范经济。我国正处于初创市场经济时期,应在一开始就规范我国的市场经济,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此时,规范经济研究也十分重要。但这些规范研究的方法范式不是我国传统的规范法,而是与实证法协调互补、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规范法、规范研究的前提假设都应当是经过实证检验的。在我们这么一个曾有过份强调精神力量传统的国度里,对价值判断等规范之前提更应注重实证检验。况且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原有的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价值体系正在消解,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体系正在孕育、催生之中。此外,对于那些带有自然规律特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我们也缺乏认识。在此情形下,若缺乏实证研究想当然地凭旧的或新的理念化的价值体系等为依据来进行规范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实践,则势必因滞后或超前等而导致经济实践的失败。
其实,实证研究的精神本质在中国有着“亲密的兄弟”,那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此等等,只是国人口里说得多了,手头就做得少了,以至这些成了口号式的套话甚至被当成陈词滥调,这同我国曾长期缺与实证研究相配套的学术自由的环境氛围有重大干系。现在我们要向西方学习实证研究方法,固然要把握其引入数理统计学之后发展起来的严密精美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把握其实证精神,也就是要重新恢复诸如实事求是等实证法之中国“兄弟”。这种务实精神体现在经济学研究当中,就是实证经济研究与规范经济研究携手并进,互为基础,协调互补,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