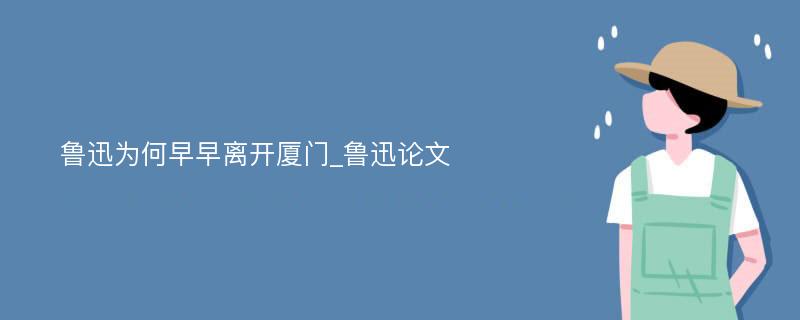
鲁迅为何提前离开厦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厦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6年8月下旬,亦即“三·一八”惨案发生近半年后,鲁迅离京南下, 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教。同行的还有许广平,但她不是和鲁迅一道赴厦门,而是同抵上海后,再分乘另一只船去广州。这次南下,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生活是一次重大转折。
对于这次南下,人们一直说是“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鲁迅随时有遭逮捕的危险,与此同时南方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也引起鲁迅的向往,为避风头,也为了奔赴革命,鲁迅即决定“战略转移”。许多年后,鲁迅自己对这次南下是这样说的:
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西滢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①
对于鲁迅的说法,很少人加以深究,更无人质疑。几十年后,朱正在其撰写的《鲁迅传略》中,针对鲁迅的解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撤职”的事,是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批准的。但是经平政院裁决,于1926年初即撤销了这个撤职令,恢复了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要逮捕”的事,当是指“三一八”惨案之后报纸上流传的那个50人的名单。当时鲁迅确是面临着遭到通缉的威胁,但是这个威胁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段祺瑞在3月18日制造了惨案,4月间就被推翻下台了,“下通缉令之权,则已非段章诸公所有,他们万一不慎,倒可以为先前的被缉者所缉了”。接着是奉军大举入关,形势也险恶,鲁迅不得不到医院暂避。但到5月初,空气也基本缓和,他也回到了家中。鲁迅离开北京前往厦门,是8月下旬的事,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至少在这20天之前,他就已经在从容布置动身的事了。他多次出席友人的饯别宴会,出席女师大的送别会,并在女师大的毁校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十分精彩的演说,走的那天,到车站送行的友人有十多人。可见不能说鲁迅是在遇到危险的情况下仓皇出走的。至于说是因为南方的革命运动正在走向高潮,所以南下,这说法也未必确切。福建省的地理位置显然是在南边了,但就政治地理来说,当时却和北京一样属于北洋军阀的统治区域,不过比北京更加闭塞。要是真因南方革命才来,那为什么不一直跑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去,而要到这个当时颇为寂静的孤岛一般的厦门来呢?
朱正的结论是:
上述的这些解释至少是不完全的。鲁迅离开北京,也许有避开政治环境险恶的北京的意思,也许有靠近革命正在起来的南方的意思,也许还有若干种其他的考虑。不论怎样说,现有材料表明,在所有各种原因之中,他和许广平的关系确实是原因之一。
朱正对鲁迅的质疑,语气十分委婉,说鲁迅的解释“并不十分错”,只是“不太确切”,“是不完全”。但他意见十分明确,就是:鲁迅的南下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和许广平的关系”。
为了支持自己的看法,朱正费了不少笔墨,引证许多材料,说明鲁迅早在动身南下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和许广平的关系就急剧升温并发生质变。鲁、许二人为了关系顺利发展,商量并达成共识,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离开北京,在一个新天地里一起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北京,鲁迅有一个“家”,那里不但有年迈的母亲,更有由母亲做主为他娶下的“妻子”朱安;而鲁迅还因为自己的身份、位置,不能不考虑社会影响和世俗之见。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朱正的论述,因为那都是曾经存在的事实。我在这里重申一下朱正的看法,只是为了强调鲁迅的南下主要是为了许广平,明乎此,才可能正确分析和把握鲁迅提前离开厦门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鲁迅离京南下是为了和许广平结合,那他为什么不和许广平一道都去广州或厦门,干脆开始就在一起岂不更好?这样问似乎合情,于理方面却嫌简单,没有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上面已经说到,因为种种原因,鲁迅不能不顾及社会影响和世俗之见,如同赴厦门或广州,其效果和同在北京发展关系能有多大区别?事实上,即便这样同时出发到上海再分赴两地,已有流言说他们是“双宿双飞”。因此,开始二人不去一处,而是分赴两地,空出一段缓冲时间,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再结合在一起,实在是出于鲁、许的精心计划和缜密思考。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实际问题是,即没有人邀请鲁、许二人同时到一个地方去。那时郭沫若等创造社“诸君子”正在广州,中山大学没有想到聘请鲁迅。鲁迅到厦门,是应时任厦门大学文科学长的林语堂之聘。林语堂素有“绅士派”之称,对周围的事反应迟钝,不太关心。不但在北京时没有看出鲁迅与许广平有什么特殊往来,就是一年多之后鲁迅许广平双双从广州到上海,事情已经十分明朗,他还毫无觉察,依然好像蒙在鼓里。这当然也和鲁、许“保密工作”做得好有关。否则,林语堂知道鲁、许之间的关系,说不定会邀请他们同赴厦门,那还真能省去二人后来的许多麻烦。至于鲁、许二人当时愿不愿和敢不敢,那又当别论。总之,鲁迅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教,合同期为两年,是最初就定下来的。
对于鲁迅初定到厦门工作两年,许广平后来也有过说明。她说:在离开北京之前,“我们约好:希望在比较清明的情境之下,分头苦干两年,一方面为人,一方面自己也稍可支持,不至于饿着肚皮战斗,减低了锐气。”② 又说:“我们在北京将别的时候,曾经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③ 鲁迅自己也几次说到他打算在厦门大学的任期。1926年6月17日,即动身前两个月, 在给李秉中的信中就说到“时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在到达厦门之后给李小峰的信中也说到:“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④。但最后的结果却是:鲁迅在厦门逗留不足半年(实际仅一学期,时间是4个月又12天)即提前去了广州。给人的印象真有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对于鲁迅的提前离开厦门,当时以及后来人们从不同角度做出了一些不同解释。
有人认为,鲁迅提前离开厦门,和厦大的“胡适派”及“现代评论派”有关,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从北京来的一伙人当中……自己内部闹开了”⑤,“被排斥,所以走掉的。”⑥ 这说法其实是不确的。的确当时厦门大学有些人或追随胡适,或追随陈源等人,他们也时不时给鲁迅一点不愉快。用鲁迅的话说是,他们“常常寻上门来”,给鲁迅一些“小刺戟”。⑦ 但是,对于在北京就已经和陈源等“正人君子”打过几回恶仗的鲁迅,还真没有怎样把他们当回事。鲁迅当时就说:“他们想攻倒我,一时也很难,我在这里到年底或明年,看我自己高兴。”⑧ 又说:“至于我下半年那里去,那是不成问题的。上海,北京,我都不去,倘无别处可走,就仍在这里混半年。现在去留,专在我自己,外界的鬼祟,一时还攻我不倒。”⑨ 由此可见,“胡适派”也好,“现代评论派”也罢,对鲁迅都不够形成多大威胁,不可能成为促使鲁迅提前离开厦门的原因。
又有人认为,鲁迅提前离开厦门,和厦门大学校方人事方面的矛盾有关,具体说就是鲁迅与厦门大学的教务长兼大学秘书并兼理科主任的刘树杞不合。的确,鲁迅到厦大后,刘树杞连着给鲁迅许多不快,诸如连着改换鲁迅的住处,以及索回国学院的房子等。数十年后,当时在厦门大学文学院主事的林语堂甚至还说:“鲁迅真受过刘树杞的气……刘獐头鼠目,但实在能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单说鲁迅吃他的亏。刘那时大概是兼总务,三易鲁迅的住房,最后一次,派他住在理学院的地窖。这回真使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这样鲁迅自然是在厦门大学呆不下去了,他到广州大学去。刘驱鲁迅,学生听见鲁迅要走,起而驱刘,激起大风潮。”⑩ 不过,以鲁迅的心胸和境界,实在不会太计较刘的作为,更不至对刘采取“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的政策。就在刘树杞索回国学院用房时,鲁迅还心平气和地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理科诸公之攻击国学院,这几天也已经开始了,因国学院房屋未造,借用生物学院院屋,所以他们的第一着是讨还房子。此事和我毫不相关,就含笑而旁观之,看一大堆泥人儿搬在露天之下,风吹雨打,倒也有趣。”(11) 可见刘树杞虽然有几分可恶,但在鲁迅眼里,还真算不上怎样一个人物。试想鲁迅在北京,对于号称“老虎总长”的顶头上司章士钊的打击迫害都未放在眼里,敢捋虎须,甚至上告到平政院讨公道,一个小小的刘树杞搞点小动作,鲁迅会在乎他,能因他而打乱自己的行动计划提前离开厦门吗?
由是一些人把眼光转到整个厦大校方,而不是只看到一个刘树杞。他们说,鲁迅的离去,主要是对厦门大学总的情况不满,是对校方黑暗腐败的失望。的确,鲁迅到厦门后不久,即发现厦大的实际情况不如自己的想象,基本条件差不说,学校负责人也不像是要真心办好教育。对此,陈梦韶在他著的《鲁迅在厦门》一书中还专门设一节分析鲁迅离开厦门的原因,其中说:
他(鲁迅)到厦大来,本想为学校做一点事的。但是一到厦大后,看见学校当局,并无真心要提倡学术研究,心里就有些怀疑了。他看见:第一,学校把教授当作“变戏法者”看待,对教授尊重不够。……使鲁迅先生到校一个月后,就有“人亦何苦因为别人计,而自轻自贱至此哉”的反感!第二,国学院只装门面,不务实际。学校当局把国学院教授当雇工看待,拿多少钱,该做多少工。天天希望他们“从速做许多工作,登表许多成绩,像养牛之每日挤牛奶一般”(《两地书·五八》)。但只是为了装门面,并无诚意为学术,为鼓励著作。……第三,减少国学院预算,没有决心办好学术研究事业。厦门大学于9月开办国学院,11月校长就要变更计划,减少国学院预算。鲁迅先生为此事,去和校长谈话,“即提出强硬之抗议,以去留为孤注”(同上,八一)。校长虽然答应取消前议,可是“维持预算之说,十之九不久又会取消”(同上),鲁迅先生当时已能够看出来了。
总之,有这样的学校当局,有“倚靠权势”“胡作非为”的文科主任的“襄理”,有“陈源之流”“弥漫厦大”的“现代评论派”等,这就使鲁迅先生感觉得“此地空气恶劣,当然不愿久居”(同上,七三)。兼之学校当局对办学无真热情,无计划性,视教授为知识贩卖者,要其尽速交出成货,而却不重视其成绩。学校当局在国学院成立典礼时的演说,措辞何等堂皇,说整顿国学,要看做是最重要的事。而今竟然“空雷无雨”,“行不顾言”。预算任意缩减,教授所研究的成绩,不依原定计划出版,没有发展国学院前途的决心。这又使鲁迅先生觉得“即使无啖饭处,厦门也决不住下去的了”(同上,七五)。
应该说,陈梦韶的这段分析是切合实际,比较具体中肯的;其中,还引了一些鲁迅的原话,从而加强了分析的可信性。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鲁迅提前离开厦门就是感到那里条件环境太差,让他无法继续待下去。因为鲁迅到厦门后不久,就发现厦门的空气很龌龊,不宜久居,更不是理想的工作和生活之地。但他也并未觉得厦门比较其他地方就特别不好,一刻也不能停留。他在到厦门后不久给川岛的信中曾说:“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 ”(12) 明乎此理的鲁迅,也决不会认为别的地方(小沟)就一定比厦门干净,从而急急舍此求之于他。对于厦大办学不认真,鲁迅来校不久也是看清楚了的,当时也对川岛说过:“厦大的当局,只是为了要报账,想拉几个人做幌子,并非真心要办好学校,‘发扬国学’。”(13) 然而他还是动员川岛来厦门——尽管告诉川岛“勿作长久之计”。并告诉川岛说自己也还可以“在这里混半年”,而不是说一刻也呆不下去。因此,说鲁迅对厦大不满和失望是促使他提前离开厦门的主要原因,多少有些夸大。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本文一开始所说并被朱正一再论证的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肯定鲁迅之所以提前离开厦门,就是因为许广平,简单说,就是为了尽早与许广平在一起。
其实,就在鲁迅即将离厦时,有人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说鲁迅是为了“月亮”而去广州。偏偏有些好心人不肯正视这点,想方设法为鲁迅辩解,其中最突出者就是鲁迅的同乡、学生和朋友川岛。他在三十年后写的《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还说:
——所谓“月亮”,是指景宋夫人,她和鲁迅先生于1926年8月26 同车离京赴沪的。又于9月1日,同天分登开往厦门和广州的轮船离沪的。我在北京,在上海时,都听到关于他们俩的谣言,说他们俩同车赴沪,又同船赴厦,大有双宿双飞之态。谣言总多少有点影子;三分事实,七分假造,才会使人听了可以相信。在我一到厦门时,就为这事问过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只是笑了一笑说:“你看着好了。”话虽不得要领,平时鲁迅先生对我也并不隐瞒,比如每礼拜里的信来信往,我是晓得的。既有三分事实,就有发展扩大的可能。可是鲁迅先生的要离开厦大,绝不是为了“月亮”;真的“月亮”还可以由东而西的绕行地球,难道象征的“月亮”就不能从广州而厦门吗?假使厦门大学可以留住鲁迅先生的话,他们俩原打算分头埋首苦干两年再说的。——所以说鲁迅先生为了景宋夫人要离开厦门去广东的话,也只是企图来缓和当时的紧张空气的。
川岛这样说,显然是出于对鲁迅的拥戴和尊重,其情可感。但是,即便是从当时鲁迅回答他的话,已可以看出一点端倪:说“你看着好了”,明摆着不是否认,甚至可以理解为默认。便是川岛,当时又何尝没有一点感觉。文中说“三分事实”,说鲁迅的回答“不得要领”,就不是完全糊涂。只不过还是有些书呆子气,再加上主观上的好意,本来看到了事实,却还要绕开走,不免让人觉得是在为鲁迅AI写作“此地无银三百两”。
说鲁迅是为了急于和许广平在一起而提前离开厦门,其实是很自然也很好理解的事。
鲁迅和许广平由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如果从“女师大事件”算起到双双离京南下,时间为一年多不足两年。此时的许广平刚从大学结业,正是青春年华,热情高涨;而鲁迅,虽已步入中年,各方面都很成熟,但因家庭婚姻不幸福,感情生活久处压抑状态,现在遇上许广平,有如打开了减压阀,其感情怎能不喷涌而出。应该说,他们离京南下时,正处在热恋之中。论感情,他们当然希望生活在一处,但现实条件又让他们不能不分开。可以说,这分是为了合,是不得已的分;一旦能合,他们肯定想早一天合在一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完全把握他们当时的想法和感情,但从他们二人留下的文字,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地难舍难分。譬如他们在分手时还彼此相约短时间内不写信,至少是船未抵岸、生活未安顿好之前不通信。但是,就在他们刚分手不久,甚至船还没有启碇,只不过二人各乘一船,思念之情就紧紧纠缠着双方的心。许广平在船上四天,就陆续写了9段文字, 把它们汇成一信,踏上广州后即寄给鲁迅。信中说:“总是蓦地一件事压上心头,十分不自在,我因想,此别以后的日子,不知怎么样?”她甚至直率地对鲁迅说:“临行之预约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14) 而且,就在她乘坐的轮船经过厦门时,她就急切地打听从厦门到广州的走法,并写寄给鲁迅“借供异日参考”。由此可见,在许广平来说,离京前同意和鲁迅分开两年,那是出于理智,一旦真正分开,感情上就觉得难以忍受。
其实,鲁迅又何尝不是如此。鲁迅年龄比许广平大许多,各方面较之成熟,思虑也就多些。他没有和许广平那样在船上就沉不住气,但一到厦门不等安排好生活就立即给许广平写信,尽管他知道此时的许广平还在船上,还没有抵达广州。此后,他几乎每天到邮政代办所去看是否有广州来信,有时不等收到对方来信就连珠炮般地写信。在厦门期间,他和许广平之间通信数量之多,频率之快,可谓空前,他对许广平的思恋之情,由此可见。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鲁迅对两年之约,也很快感到太长。就在他刚到厦门学校还未开学时,他就向许广平倾诉:“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15) 有意思的是,许广平接读鲁迅的信后,不知是未明其意还是明知故问,竟然问鲁迅:“你为什么希望‘合同的年限早满’呢?你是感觉着诸多不惯,又不懂话,起居饮食不便么?如果的确对身子不好,甚至有妨健康,则不如失约,辞去的好。”(16) 这颇有点像天真少女玩纯情游戏。面对许广平的追问,鲁迅不得不表白:“我之愿‘合同早满’者,就是愿意年月过得快,快到民国十七年,可惜到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了。”但鲁迅还是放不下他的“沉稳”,不肯直说是因为思念许广平,只把话说到九成而不是十成明白。不过他还是接着又说:“其实此地对于我的身体,仿佛倒好,能吃能睡,便是证据,也许肥胖一点了吧。不过总有些无聊,有些不满足,仿佛缺了什么似的……(17) 这“不满足”,这“仿佛缺了什么似的……”所指为何,不用说许广平应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就是对于外人,又还用得着费辞加以解释吗?
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许广平或鲁迅,说嫌“合同时间”太长,说希望尽快相见,都不只是纯粹的感情表达,而是真有愿望,真有打算。他们都在寻找机会,伺候机会,一旦机会来到,他们就勇敢行动,即使要废除合同也在所不顾。
客观形势的变化令人难料。也许真是吉人天助,这机会不久就逐渐走来,那就是广州中山大学因办学需要聘请一些教师,这为鲁迅提供了去广州和许广平相聚的可能。
原来1926年春中山大学请郭沫若来校任教后,创造社几位主要人物陆续来到广州,中山大学一时名声大振。但不久郭沫若参加北伐,一些随郭沫若来的教授也相继而去,中山大学为了继续聘请一些新型学者,由是把目光转向鲁迅。这时间,是在1926年秋季,也就是鲁迅刚抵厦门后不久。长期以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研究者都说中山大学决定请鲁迅,“是由中共广东区委员会提出,经过与当时任中大委员会委员长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斗争以后决定的”(18)。不可否认,当时左派势力为了争取鲁迅到校任教,付出了很大努力,起了促进作用。但当时掌权的国民党确实想争取一些带有进步色彩的文化人来校任教,也是事实,即以当时和鲁迅同时被考虑的在厦大的还有林语堂、沈兼士和孙伏园等,并非鲁迅一人,就是证明。
中山大学邀请鲁迅并非一开始就说是聘任,而是后来才态度明确,其间有一个过程。对此,过去一些研究者未予注意,或者看得不够仔细。即如朱正的《鲁迅传略》,其中说到“10月16日,鲁迅就已经收到中山大学朱家骅的邀请电报”,(19) 虽未明说就是聘请,但从上下文看,给人的印象是中山大学这时就正式聘请鲁迅了。而实际情况是,中山大学朱家骅邀请鲁迅、林语堂、沈兼士等人赴广州,是因学校改制(委员制),请他们一行人去“指导一切”,这就像现在说的学术访问、教学交流。当然,访问交流后有人会被留下聘用,那又当别论,但至少此时(10月16日电邀)不是正式聘请。然而,这对于鲁迅毕竟是一个可能提前结束签约离开厦门的机会。现在没有资料证明中山大学朱家骅在发出电邀之前是否已和鲁迅取得过联系并征求了鲁迅的意见,仅从《两地书》看,只能说是许广平在广州知道郭沫若离开中山大学后出现空缺,希望鲁迅前来填补。许广平写信第一次说到此事是1926年10月7日,亦即鲁迅到厦门刚1个月,可见她是多么希望冲破原先两年之约的急切心情。许广平在信中说:
厦大情形,闻之令人气短,后将何以为计,念念。广州办学,似乎还不致如此,你也有熟人如顾先生等,倘现时地位不好住,可愿意来此间一试否?郭沫若做政治部长去了。广大改名中山大学,校长是戴季陶。(20)10月18日,许广平又写信说:
中山大学停一学期,再整理开学,文科主任的郭,做官去了,将来什么人来此教授,现尚未定。你如有意来粤就事,则你在这里的熟人颇不少,现在正是可以设法的时候。(21)10月22日,她还继续写信动员,说:
中山大学(旧广大)全行停学改办,委员长是戴季陶,副顾孟余,此外是徐谦,朱家骅,丁维汾。我不明白内中的情形,所以改办后能否有希望,现时也不敢说,但倘有人邀你的话,我想你也不妨试一试,从新建造,未必不佳。我看你在那里实在勉强。(22)
其实,就在许广平写第二封信(10月18日)的前两天(10月16日),鲁迅已收到中山大学朱家骅的邀请电报,只不过当时信息传递不那么发达,许广平并不知道,所以还在动员鲁迅来粤。而当她得知中山大学已电邀鲁迅,而鲁迅对是否去粤还在犹豫时,就在10月23日又写信说:
这里既电邀你,你何妨来看一看呢。广大(中大)现系从新开始,自然比较的有希望,教员大抵新聘,学生也加甄别,开学在下学期,现在是着手筹备。我想,如果再有电邀,你可以来筹备几天,再回厦门教完这半年,待这里开学时再来。广州情形虽云复杂,但思想言论,较为自由,“现代”派这里是立不住的,所以正不妨来一下。否则,下半年到那去呢?上海虽则可去,北京也可去,但又何必独不赴广东?这未免太傻气了。(21)接着又于10月27日写信说:
……我当日即复一快信(按:指10月23日信),是告诉你不妨来助中大一臂之力。现在我又陆续听说,这回的改组,确是意在革新,旧派已在那里抱怨,当局还决计多聘新教授,关于这一层,我希望你们来,否则,郭沫若做官去了,你们又不来,这里急不暇择,文科真不知道会请些什么人物。(24)
许广平这样连着写信给鲁迅,动员鲁迅前来广州,可以看出她希望和鲁迅相聚的急切心情。其实,鲁迅对去广州又何尝表现不热心,只不过他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他认为中山大学只是请他去“指示一切”,没有明确发出聘请。他曾说:“我以为中山大学既然需我们商议,应该帮点忙,而且厦大也太过于闭关自守,此后还应该与他大学往还。”(25) 那只是从学术交流的方面而言。而另一封信中,他即说到聘任问题,他就十分认真了,他说:“现在伏园已有信来(按:此时伏园已在广州),并未有非我即去不可之概”。(26) 在另一封信中又说:“(伏园)给我两封信,关于我的事,一字不提。今天看见中大的考试委员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他也在内,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27) 这说明,鲁迅觉得中山大学只是请他去走走看看,提些意见,交流交流,这固然好,但不是正式发出聘请,加上当时林语堂对去广州表现也不够积极,所以他就只能说“我的行止,当看以后的情形再定。”(28) 除此之外,鲁迅对去广州还有一方面考虑,就是正好此时对许广平发生一点误会,影响了他去广州的积极性和决心。过去人们对此一直未予足够注意,或者竟是完全忽略。因此有必要在这里补上一笔。
原来许广平在广州的工作一直不十分顺手,劳累不说,还常遇一些操心麻烦事。此时正好有一位在北京时就认识的革命者李春涛来到广州,和许广平重遇。李本来在北京当教授,这次是以代表身份来广州开会。李便邀许广平去汕头,表示“无论教书,做妇女工作,做报纸宣传工作(他)都可以想办法。”(29) 许广平即萌发了去汕头的想法。据许广平后来说:
当时,想去汕头,是为了走向革命,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同时,也为了离厦门近一些,与鲁迅呼应较便。但对在厦门的鲁迅解释得不够详细,便引起他的牢骚来了:“我想H.M.不如不管我怎样,而到自己觉得相宜的地方去,否则,也许因此去做很迁就,非意所愿的事务,比现在的事情还无聊。”在写完这封信的深夜,又添了几句:“我想H.M.正要为社会做事,为了我的牢骚而不安,实在不好,想到这里,忽然静下来了,没有什么牢骚了。”(见《两地书》第八十一)这里越是说没有什么,正表明有什么,因此我考虑:同是工作,要自己去闯,可能也多少干一些事,但是社会这样的复杂,而我又过于单纯,单纯到有时使鲁迅很不放心,事情摆在面前,恐怕独自干工作是困难的了。既然如此,就在鲁迅眼前做事也是一样的。这样的想法一决定,就不去汕头了。以后也没有改变这决定。(30)
这段话中,许广平引了鲁迅给她信中说的话,也许是她忘记,其实鲁迅在此之前的一封信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他列出对去广州的三点疑虑,前两点有些空泛,第3点就分明地说:“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在厦门何异。”(31) 这“一个朋友”显然指的是许广平,而这语气也其实是牢骚十足,甚至比许广平上引的话更甚。好在他们二人的关系已非一般,所以误会很快消弭,警报立即解除,但鲁迅仍不放心,没忘记在后一封信中正面明确提出:“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这里,就中大教授职。但我极希望H.M.也在同地,至少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些有益于人的工作。”(32) 这话看似有些多余,因为此时许广平已蹋下心来,决心留在广州和鲁迅在一起,一刻也不分离。但仔细品味鲁迅这段话,其中分明有对许广平的深爱,更有误会后感到的歉意,因而其内容又极为丰富,包蕴着深长意味。
对于鲁迅提前离开厦门,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高长虹事件”,它从另一个方面促使了鲁迅下决心。这一点是高长虹始料未及,也是许多研究者没有往这方面想的。(33) 这里没有必要过多叙述“高长虹事件”本身, 只需指出高长虹因为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而辱骂鲁迅,使鲁迅极为气愤。开始鲁迅没想到高长虹是因为追求许广平而不得,见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大发醋意,说自己是太阳,许广平是月亮,骂鲁迅是黑夜。当鲁迅知道实情时,反而感到有必要光明正大地接近许广平,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对许广平的爱。他在厦门就给许广平写信,说:“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闻者相似,且说长虹之攻击我,乃为此。用这样的手段,想来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的不甚竞争,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现在就偏出来做点事,而且索性在广州,住得更近点,看他们卑劣诸公其奈我何?然而这也是将计就计,其实是即使并无他们的闲话,也还是到广州的。”(34) 另一处则说得更加明白,即1927年1月11日致许广平信中说:“那流言,是直到去年11月, 从韦漱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沈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地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35) 而且,就在这封信中,他更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是的,“我可以爱”,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话语啊!五四运动高潮时,鲁迅曾称赞一名要求真爱的青年是“人之子”,喊出了震撼人灵魂的声音:“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36) 现在,鲁迅自己发出的也正就是这真正的“人”的声音。
就这样,鲁迅为了尽早和他的所爱——许广平在一起,决定不再在厦门“混”下去,尽快离开,越快越好。1927年1月16日,即鲁迅在厦门生活工作了整整4个月又12天后,毅然提前离开了厦门。是的,厦门大学工作条件生活环境恶劣,人事关系复杂,等等都是鲁迅提前离开厦门的原因,这也正如鲁迅说他去广州是想“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并“同创造社联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37) 又说要教些书、写点文章继续搞文艺运动一样,都是真实的,但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地看到,种种原因,种种目的,都绕不开一个起主导作用(激化作用)的因素,就是希望尽快和许广平在一起。这是鲁迅作为普通人内心深处的主观愿望和情感需要,我们不但不应回避,相反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在本文结束前,作者还想说一句的是,探讨鲁迅为何提前离开厦门,对研究鲁迅可能并无多大补益,但对鲁迅研究或许并非全无意义。许多年来,人们都在说“鲁迅是人不是神”,又说应该摆脱泛政治化的视角去观察鲁迅、研究鲁迅。这无疑是对的,本文的立论就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方法上更是从具体材料入手,对纷繁的史料做出仔细的梳理和分析,从而确立自己的结论。至于具体论述是否有当,就需要请学者朋友多加指教了。
2006—3—21 于北京北太平庄蜗庐
注释:
① 《自传》,《鲁迅全集》第8卷第4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年们》。
③ 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
④ 鲁迅:《厦门通信·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4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 见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
⑥ 见陈梦韶:《鲁迅在厦门·七》。
⑦ 《两地书·五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 《两地书·六十》,《鲁迅全集》第11卷第1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⑨ 《两地书·六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1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⑩ 林语堂:《忆鲁迅》,载《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自传附记》。
(11) 《两地书·六○》,《鲁迅全集》第11卷第1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 《致川岛信(1926年10月23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5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 川岛:《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
(14) 《两地书·三七》,《鲁迅全集》第11卷第108—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 《两地书·四一》,《鲁迅全集》第11卷第1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 《两地书·四七》,《鲁迅全集》第11卷第1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 《两地书·四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1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正式出版时,后一句改成“总有些无聊,有些不高兴,好像不能安居乐业似的。”
(18)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36页。这一说法十分普遍。
(19) 朱正:《鲁迅传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4页。
(20) 《两地书·五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1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1) 《两地书·五九》,《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2) 《两地书·六一》,《鲁迅全集》第11卷第177—1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3) 《两地书·六三》,《鲁迅全集》第11卷第1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 《两地书·六五》,《鲁迅全集》第11卷第1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5) 《两地书·五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 《两地书·六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1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7) 《两地书·六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1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8) 《两地书·六九》,《鲁迅全集》第11卷第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9) (30)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68、69页。
(31) 《两地书·七三》,《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 《两地书·八三》,《鲁迅全集》第11卷第225—2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3) 不是不知道“高长虹事件”,而是没有人说到它从反面对鲁迅提前离开厦门所起的作用。
(34) 《两地书·一○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263—2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5) 《两地书·一一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2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6) 《热风·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3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7) 《两地书·六九》,《鲁迅全集》第11卷第1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标签:鲁迅论文; 许广平论文; 大学教育论文; 厦门大学论文; 厦门生活论文; 读书论文; 广州中山大学论文; 月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