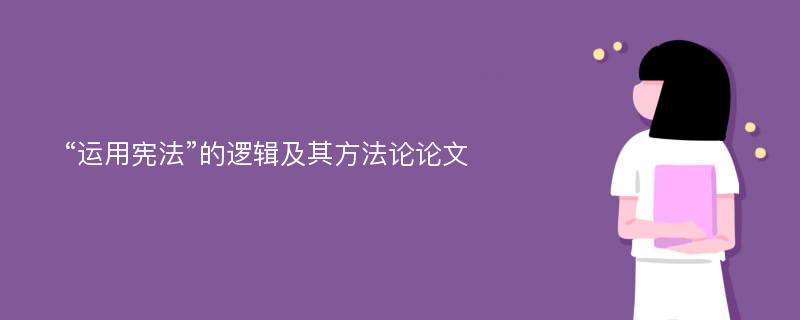
“运用宪法”的逻辑及其方法论 *
范进学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030)
【内容摘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运用宪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与宪法思想的重要内容,具有深刻的划时代意义与强烈的现实价值,它将我国宪法实施这一实践问题从理论逻辑还原为实践逻辑;运用宪法的实践逻辑,注重的是如何运用,即方法论问题。它包括立法机关如何“运用宪法”,也包括执法机关如何“运用宪法”以及司法机关如何运用宪法等等。“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是党中央对我国立法机关提出的立法要求,以此为标准,在我国宪法实践与立法实践中存在两种具体方法模式:一是 “根据宪法”模式;二是 “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模式。作为事实上担负着“运用宪法”的重要使命的裁判者法院,在我国现有宪法制度设计下,运用“非解释性宪法适用”方法,通过引用或援引宪法规范或宪法原则作为裁判的依据。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专门机构,在进行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必然遇到对宪法条文的理解与解释,只有通过宪法解释,才能作出合宪性的判断,对合乎宪法的规范性文件予以维护,对与宪法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予以改变、撤销或废止。
【关 键 词】 运用宪法 宪法实施 宪法解释 合宪性审查
“运用宪法”是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宪法实施提出的重大举措,该《决定》明确指出:“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1]P50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运用宪法”的宪法实施这一思想反复强调过,2018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带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2]2018年12月4日,习近平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再次要求:“要在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3]。由此观之,“运用宪法”思想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关于宪法实施战略的最新深化与表达,它其实是对十七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来的“用法”思想①的进一步具体化与升华的结晶。如何科学理解与认识“运用宪法”的逻辑?如何将“运用宪法”这一重大宪法实施思想落实到立法、执法及司法等法治实践各个环节,将是今后宪法实施的重要使命与根本转向。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探究,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运用宪法:宪法实施从理论逻辑到实践逻辑的展开
在我国,一般理论学说将宪法实施等同于“法律实施”,认为宪法本身规定的内容,其原则性、概括性比较强,不易具体实施,它需要转化为具体的法律,通过法律规范将宪法规定的内容具体化,从而加以实施。这种通过法律实施宪法的观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友渔就提出过,他认为:宪法实施是通过制定法律以贯彻实施宪法。[4]周叶中也曾明确主张:宪法实施是“将宪法文字上的、抽象的权利义务关系,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生动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进而将体现在宪法规范中的人民意志转化为人们的行为(包括积极的作为和消极的不作为)”。[5]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也采取了相同的观点,认为“所谓宪法实施,是指宪法在国家现实生活中的贯彻落实,是使宪法规范的内容转化为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行为。法律实施是宪法实施的重要环节,就国家机关而言,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制定法律,将宪法原则和规定予以具体化,行政机关依据法律作出行政行为,司法机关依据法律作出裁判,如果其行为违反了法律,可以通过法律机制予以纠正并追究法律责任,使之严格依法行使职权。就社会组织和个人而言,如果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得到实施,便意味着通过法律得到具体化的宪法实质上也得到了实施”。[6]P296即使部门法学界,也有学者主张宪法实施需要法律才能实施的观点,如民法学家王利明教授就指出:“在我国,由于宪法规范不具有可司法性,无法直接适用于案件裁判,所以,有必要通过部门法将宪法的原则、规范予以具体化,这也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同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虽然规定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其规定大多抽象原则,难以直接适用于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活事实。”[7]这种将宪法实施转化为法律实施的理论逻辑就在于法律是对宪法的具体化与精细化,凡是宪法上所确定的内容,只要全部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法律规则,然后加以法律的实施,那么宪法自然而然的得以实施。按照这种宪法实施的理念与思路,宪法文本与宪法规范则无需运用,运用的只有法律。因此,长期以来,在我国立法、执法与司法等法治实践中,基本不强调如何运用宪法,在司法实践中甚或排斥宪法的运用。②因此,即使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学法守法用法”的要求,但其中的“用法”之“法”,往往被理解为“法律”而不是“宪法”,虽然理论层面可将“用法”之“法”解释为包括了“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但这里的“法”并没有明确指向 “宪法”。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在于长期以来人们一般不把宪法当作可以“运用”的法律看待,所谓“用法”,实际上一直被理解为“运用法律”。
[译文2]Observing abnormal behavior in an animal can be suggestive of a particular disease problem or poor management practice.
自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用法”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的要求之后,在理论层面才将“用法”之“法”明确确定为“宪法”与“法律”,即不仅强调“运用法律”,而且突出强调了“运用宪法”。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运用宪法”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与宪法思想的重要内容,它具有深刻的划时代意义与强烈的现实价值,它是将我国宪法实施这一实践问题从理论逻辑还原为实践逻辑,即宪法实施本质上是运用宪法的实践问题,而不是纯粹一种理论问题,理论逻辑再周全、再严密,也离不开宪法的运用,宪法作为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它“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8]P141作为公民的行为规范,宪法需具有可操作性;作为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宪法需具有适用性。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而提出“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要求。无论是宪法的可操作性与实践上的适用性,都必须要求人们能够“运用宪法”,理论上无论怎样阐释宪法实施的重要性都不过分,但是若是仅仅停留于法学理论上的论证,而忽视了法治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宪法实施仍是空中楼阁,难以从天上落地人间。因此,运用宪法是宪法实施从理论逻辑到实践逻辑的真正展开,这对于宪法实施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宪法实施只有从宪法理论逻辑走向宪法实践逻辑,才能发挥宪法作为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应有价值。
然而,毋庸讳言,“运用宪法”的思想迄今在宪法治理实践中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司法界存在着普遍排斥宪法在司法中的运用就是最好的诠释与佐证,因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健全“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在我国法治实践中并未确立起来。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于2018年2月与12月又两次再三强调“运用宪法”的思想,他不仅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运用宪法”、做“用法”的模范,而且号召要在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以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可见,“运用宪法”思想已经不简单地作为宪法实施的倡导性口号宣示,而且成为全党、全社会应当开展宪法实施的实践性宣言书。
除了引进部分优秀的校外课程资源,我们更应该充分利用校内的教学、科研人员优势,建设好自己的网络课程资源。但目前校内的网络课程存在明显不足,主要有:l.由于资金投入不足,部分课程录制质量不高,后期制作落后;2.由于重视程度不足,对网课的宣传推广不够;3.课程表现形式单一,对学生吸引力弱;4.课程设计不够完善,没有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学习者无法真正实现学习内容、学习过程、学习评价的自主性;5.常常仅对本校学生开放,等等。
图4~7为完整试样和预制裂纹试样在三点弯曲试验中,试样变形破裂过程微震和电荷感应信号的监测结果。图中的(a,b,c,d)分别为试样变形破裂过程的时间-力曲线、位移-力曲线、时间-微震和时间-电荷感应信号曲线,(c)图中上、中、下三图分别为电荷传感器1、2、3接收到的电荷感应信号,(d)图中上、中、下三图分别为垂向振动速度传感器和两水平向振动速度传感器接收到的微震信号。
建立健全运用宪法制度强调的是宪法在整个中国法治实践中的运用,不仅体现在立法环节,也体现在执法与司法环节。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宪法规范只有确实发挥其引导、规制、指引、保障的功能,宪法的权威与尊严才能真正树立起来,宪法实施才能真正落地。运用宪法的实践逻辑,注重的是如何运用,即方法论问题。它包括立法机关如何“运用宪法”,也包括执法机关如何“运用宪法”以及司法机关如何“运用宪法”等等,只有解决了如何运用的方法论问题,才能使运用宪法的法治实践真正展开。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从20世纪90年代起步,到2002年,共建成各类园区48座.2003年以后,园区建设步入发展阶段,从2003至2005年,共建成各类园区85座,超过了以前13年的总量.2006年,我国园区建设井喷,一年建成各类园区107座,2007年以后,园区建设步入快速发展通道,2008年至2012年,共建成各类园区1 122座,年均增速42.2%,见图3[1].
二、“根据宪法”与“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立法机关运用宪法的两种方法
法治实践的宪法运用首先体现在立法环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立法须先行,要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始终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牛鼻子”,《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9]P442“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是党中央针对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应有之义,而判断一部法律是否优良的标准可能很多,但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标准,则是通过司法审查或宪法审查机制,以是否符合“宪法精神”为标准来评断立法或规范性文件是否良善。如果按照是否符合宪法精神作为判断标准,那么在我国宪法实践与立法实践中存在两种具体方法模式:一是 “根据宪法”模式;二是 “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模式。
(一)“根据宪法”方法模式
上述第一种情形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法律,其立法内容几乎都是现行《宪法》序言或具体条款所规定的内容,都能够直接在宪法条款中找到出处或来源。如《反分裂国家法》是根据宪法序言第9自然段“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制定的。《预算法》是根据宪法第89条关于国务院行使“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的规定制定的;《社会保险法》是根据宪法第45条关于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制定的;《劳动法》是根据宪法第42条关于“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第43条关于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而制定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根据宪法第45条、第49条“禁止虐待老人”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是根据宪法第八条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制定的;《文物保护法》根据宪法第22条关于“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制定的;等等;几乎所有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法律,其规定的内容均在《宪法》文本中找到具体出处与来源。因此,从上述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法律考察,所谓“根据宪法”立法,无非就是根据宪法文本的相应内容而制定。
随着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辅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的专责机构之后,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会渐进展开。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合宪性审查机构,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增加了“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其中“开展宪法解释”将是该委员会的核心工作。笔者认为,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专门机构,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必然遇到对宪法条文的理解与解释,这时,只有通过宪法解释,才能作出合宪性的判断,对合乎宪法的规范性文件予以维护,对与宪法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予以改变、撤销或废止。
在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笔者共考察了240部现行法律,其中84部法律的第1条均写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内容,占全部法律数量的35%;另外156部法律未写“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占全部法律数量的65%。
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山东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齐鲁大地处处焕发勃勃生机。
直接写入“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与未直接写入“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其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在宪法文本中直接找到相应的条款作依据或来源、出处,凡是未写入“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其规制的内容一般不会直接在宪法文本中直接找到,如《产品质量法》是“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是“为了加强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规范进出口商品检验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进出口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顺利发展,制定本法”;《电力法》是“为了保障和促进电力事业的发展,维护电力投资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电力安全运行,制定本法”,《港口法》“是为了加强港口管理,维护港口的安全与经营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港口的建设与发展,制定本法”;《食品安全法》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等等。关于产品质量责任、进出口商品检验行为、电力事业、港口管理等各项具体内容,《宪法》的确皆未有相应规定,因而这些法律就不会写入“根据宪法”而制定字样。其实,所有未写入“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其规制的内容均在《宪法》文本中找不出具体的相应规定。由此可推知,凡是宪法文本中没有直接对应的相关内容的,一般不直接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1)直接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共计80部法律;其中,《缔结条约程序法》、《戒严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继承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本法。
(2)根据宪法和××法,制定本法。如《高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第一条都规定:“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驻外外交人员法》第1条规定:“根据宪法和公务员法,制定本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条规定:根据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则。《科学技术普及法》第1条 规定: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法。
(3)直接根据宪法第××条具体内容,制定本法。如《兵役法》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五条‘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和其他有关条款的规定,制定本法。”
“根据宪法”,首先需明确何谓“根据”。依照《古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根据是指“依据”、“出处”、“来源”之义。[10]P1576 “根据宪法”之含义就是所立之法的内容是“依据”宪法,或者是来源于宪法,或者在宪法文本中找到“出处”。从我国现行宪法文本考察, 宪法文本出现“根据”一词共计17次,但只有第89条第1款针对国务院行使的职权才白纸黑字出现了“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的立法要求,至于对全国人大以及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宪法文本则未明确出现这种“根据宪法”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字眼。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全国人大或地方立法机关可以不“根据宪法”制定法律规范性文件呢?从宪法文本语言中无论如何是解读不出这样的含义的,毕竟在现行宪法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中明确提出了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的宪法要求。对于这种宪法要求,我们可否作以下理解,即一切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而“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就是与“根据宪法”同义?换言之,所有国家机关当然包括一切立法机关,其活动都必须“根据宪法”,即有宪法上的依据或来源或出处,否则违背了宪法序言的这一要求。如果这一解读是正确的,那么所有立法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不会因宪法条款中没有写上“根据宪法”就可以自行其是。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指出:在西方法治国家或立宪国家,几乎所有重要法律都不作“根据宪法”之类的规定,如民事法典包括 《法国民法典》、《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日本民法典》、《日本商法典》、《日本民事诉讼法》、《日本破产 法》、《美国统一买卖法》、《美国统一商法典》、《德国民法典》、《德国民事诉讼法》;刑事法典包括《美国刑法典》、《美国模范刑法典》、《法国刑法典》、《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德国刑法典》、《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意大利刑法典》、《日本刑法典》、《日本刑事诉讼法》。[11]然而,这些国家都有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机制,他们通过特定的司法审查机构和程序,对违反宪法的所有法律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以保障所有法律符合宪法精神。因此,宪法条款中是否明确写上“根据宪法”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确不能免除立法机关“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的宪法义务。因为我国现行宪制也确立了宪法审查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宪性审查制度,该机制由2018年宪法修正案所确立的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专责机构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具体实施,从而保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12]的要求。其中“违宪”指的就是所有规范性文件都有可能“违宪”,一旦违宪,就可以通过备案审查制度,依法撤销和纠正。因此,既然所有规范性文件皆有“违宪”的可能,就必须要求所有立法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应当“根据宪法”,以便“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③
不过,也有的法律虽然“根据宪法”制定的,但宪法文本中似乎找不到明确的规定,如《海关关衔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加强海关队伍建设,增强海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感、荣誉感和组织纪律性,有利于海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根据宪法,制定本条例。”再比如:《人民警察警衔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加强人民警察队伍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增强人民警察的责任心、荣誉感和组织纪律性,有利于人民警察的指挥、管理和执行职务,根据宪法,制定本条例”。上述两部法律都涉及国家行政工作人员的执法与管理行为,但具体到海关工作人员与警察职务行为,《宪法》文本中未具体规定相应内容,因而它们所“根据”宪法具体哪一个条款或内容制定的,并不明显。类似这种情形的法律,应当无需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另外156部法律没有直接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如《产品品质量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电力法》、《港口法》、《企业所得税法》、《食品安全法》、《民用航空法》、《环境影响评价法》、《车辆购置税法》、《耕地占用税法》、《节约能源法》、《广告法》、《船舶吨税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防沙治沙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公共图书馆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环境保护税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等等。
在条款中载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84部法律中,又细分三种情况:
当然,也有例外,如《国籍法》虽然没有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但显然该法律是应当写入的,因为《宪法》第33条明确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公民”,国籍是现代社会中某一自然人作为一个特定国家成员法律上的资格或身份,它反映一个人同某一特定国家固定的法律关系;[13]P210具有一国之国籍,才能成为一国之公民,从而承担公民义务,享受公民权利,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唯一条件,因此,国籍问题必须通过具体法律加以规定,而《国籍法》则是直接根据该条款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应当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也同样没有写入。现行《宪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两部基本法就是针对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直接根据第31条之规定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再比如《婚姻法》,正如该法第1条规定:“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而《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我国《婚姻法》就是直接根据第49条制定的。总之,类似上述法律,其基本内容或规定的制度均在《宪法》条款中找到出处或依据,完全可以应当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法律,但事实上却未明确写入。
抑制EGFR表达后,鼻咽癌SUNE-1细胞株增殖细胞数、迁移细胞数目及侵袭细胞明显减少(P<0.05),见表2。
从图1可以看到,所得镀层均匀、光亮,测得其显微硬度为(93.6 ± 3.3) HV,平均光泽为421 ± 66。
通过以上考察与分析,笔者认为存在着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一部法律是否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并非像有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写入这八个字的就是“立法者的一种自我限权”,[14]P246因为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作为国家立法权的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何以在有的法律中写入,而有的法律则未写入?如果是自我限权,最佳的选择应当是所有的法律皆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从而始终保持相同的姿态。因而,写入与否并非是基于自我限权,而主要是依据宪法文本中有无相应的内容。
第二,一部法律是否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也并非像有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中国现阶段制定基本的法律时,在首条写进‘根据宪法’的内容,为的是在宪法的至上性时常被人忽略、忘记或经常遭遇挑战的情况下强调宪 法的根本法地位和至上性”。[11]事实上,法律写不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字眼,并非是宣扬或强调宪法的至上性,因为无论是否写入,都不会影响宪法的至上性地位。
第三,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均存在同样的情形,即有的法律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有的则不写。如由全国人大制定的《预算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事诉讼法》等皆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而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企业所得税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婚姻法》、《国籍法》、《合同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多部法律却未写入;同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中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而同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大量法律中却没有写入。可见,并非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就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就不写或少些写“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语际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着重探讨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下如何理解和实施第二语言的言语行为。它常常定义为“研究非母语的第二语言操作者在使用和习得第二语言行为时的模式”[1]。也就是说,语际语用学重点研究的是外语/二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
第四,本来在宪法文本中能够找到出处与来源的法律,在立法时应当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却事实上未写入;有的在宪法文本中找不到出处或依据的,却在立法中写入。但是,符合这两种情况的法律数量不多,均属例外情况。因此,不影响笔者所得出的结论的成立,即是否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所依据的标准主要是看宪法文本中是否有相应的内容,而不是依据其他标准。有学者指出:“凡是大型的、基本的、与宪法关系较密切的法律,其本身都做了内容为‘根据宪法’的规定,只有不多的一些小型的、非基本的、与宪法关系较远的法律,没有规定‘根据宪法’的内容”[11];事实是,宪法本来就是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的法律,自然基本制度的内容均可在宪法中找到,它们自然与宪法关系密切,所以皆在法律中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而那些小型的、非基本的制度不会在宪法作出规定,自然就在宪法文本中找不到出处,从而无需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因而,这一标准能够解释那些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法律何以写入以及那些未写入的法律何以未写的基本原因所在。
因此,只要依据是否在宪法文本中找到出处与来源来解释“根据宪法”之基本内涵,就能够把握立法机关如何运用宪法的方法问题;质言之,只要在宪法文本中能够直接找到所立之法的出处或来源,那么制定的法律就必须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若不能找到直接出处或来源,那么法律就无需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因而,据此笔者建议,像《国籍法》、《婚姻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法律,其规制的基本制度和内容都可以在宪法文本中找到出处,那么就应当写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像《海关关衔条例》、《人民警察警衔条例》所规制的内容在《宪法》文本中找不到相应的出处的,就无需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当然,除了宪法第89条规定“根据宪法”制定行政法规作为国务院的宪法义务外,并没有明确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义务,但不论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只要是对宪法规定的制度或内容的具体法律化,就应当写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以此表明立法依据的正当性与妥当性;韩大元教授指出:“根据”实际上表明法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宪法是正当性的表达,以宪法为依据意味着获得民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15]如果所制定的法律,并非是直接对宪法制度或内容的规制,则无需写入,只要遵循“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宪法原则即可。
(二)“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方法模式
“符合宪法精神”是对我国立法活动的总体要求。何谓“宪法精神”? 宪法精神就是保权与限权精神,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限制国家政府一切公权力滥用,体现民主、共和、宽容、平等、自由、法治和人权精神。[16]P71。韩大元教授也指出:“宪法精神就是人们对宪法的意识、思维与心理状态,体现国家的根基与‘元气’。宪法精神以‘人的尊严’作为宪法制度存在的基本哲学,以人为出发点,回到人本身,捍卫着人的神圣性与不可代替性,体现自由、民主、法治、宽容与和平等价值”。[15]宪法精神凝结于宪法文本之中,约束着一切国家机关之所有行为,通过宪法精神,发挥宪法的价值引导、规范调整与共识凝聚的基本功能,宪法精神在立法活动中的体现,就是要求所有立法都遵守“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宪法义务,以塑造立法的合宪性基础。
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如何才能做到“符合宪法精神”?符合宪法精神的方式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根据宪法”,另一种是“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根据宪法”由于是直接依据宪法的基本内容,因此,只要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所有规范性文件,毫无疑问是符合宪法精神的。然而,“根据宪法”立法却不是一切立法机关普遍的宪法义务,它只是我国宪法对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即国务院的单独要求,对其他所有的享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没有像对待国务院一样特别强调“根据宪法”进行立法。
同时,还有学者基于审判权的本质,认为“事实上,只要承认法院在解决个案争议中适用法律的权力( 也就是审判权),就不可能禁止其解释法律,如果宪法规范有可能在法律适用中发挥作用,则解释宪法条款是不可避免、不可禁止的。这是客观上、事实上不可能被禁止,而不是谁有权禁止的问题”。[24]进而认为“考虑到宪法条文的特性,通常情况下,仅有‘援引’条文的工作是不够的,而必须对被引之条文进行理解,方能把握其含义”;“不论我们将法官对宪法文本的具体操作方式称之为‘理解宪法’、‘分析宪法’、‘开展宪法’、‘援引宪法’还是‘贯彻宪法’,这都只是用语上的差别,其本质都是对宪法的解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充分重视并认真对待。马克思曾说过:“法律是普遍的。应当根据法律来确定的案件是个别的。……法官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根据他在认真考察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32]P180法官在运用法律解决个案纠纷时,根据他对法律条款的理解来解释法律,这正是司法过程的本质。法国比较法学家达维徳指出:“颁布法律或条例是权力机关的事。可是法律的实际效用决定于实施的方式。法律的实施以解释过程为前提”。[33]P109的确,只要存在法官,就存在着法律的解释。问题是,并非所有的法律条款都需要解释,解释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存在着词义不明的情形,如《立法法》第45条就列举了两种解释的情形:一是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是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倘若制定的法律没有出现上述两种情形,自然就无需解释。换言之,凡是条款明确、含义清楚的就直接可以适用而无需解释。若把仅仅援引而无需进行解释的条款不加区分地一律视为“宪法解释”的观点无疑是一叶障目,作为我国宪制架构下的法院,必须恪守职权法定的法治原则与我国宪法根本制度,在自身缺乏解释宪法的宪定职权的前提下,在裁判过程中若遇到需要解释的情形,将不得自行解释,而是中止裁判,把需要解释的宪法条款依照程序或规定提请有解释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解释。⑤若允许或默许法院在裁判过程中解释宪法,则实际上赋予了普通法院法官解释宪法的权力,那将会改变我国现有的宪法架构,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
一般说来,“根据宪法”方式包含着“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原则,即凡是“根据宪法”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不会同宪法相抵触,但“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原则却未必包含着“根据宪法”,虽然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在宪法文本中找不到直接依据或出处,无法直接在规范性文件中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但并非表明立法机关就可以不根据宪法进行立法,而是遵循“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义务,其所立之法合乎宪法原则或宪法精神。宪法原则是宪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准则,是宪法规则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宪法原则在我国宪法中体现为党的领导、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法治等;而宪法精神之精髓在于保障人权、约束公权。所有立法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除了“根据宪法”制定外,更重要的是必须遵循宪法原则,符合宪法精神。正因为所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都必须首先合乎宪法精神,才有了党内法规关于“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的规范性要求。[9]P443由此可见,“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并非仅是对立法者依宪立法的形式要求,而是内含着立法者应当根据宪法原则与精神进行立法的价值判断,毕竟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17]P26。在一个宪法至上的法秩序中,确立所有法律都必须与宪法相一致,显然是一个合理的方法论原则。
三、非解释性适用:司法机关运用宪法的方法
作为案件裁判者的法院,事实上担负着“运用宪法”的重要使命。按照我国宪法序言的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作为国家机关的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则必须以宪法为裁判活动准则,履行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事实上,真正“运用宪法”的主体,最终是司法机关,只有司法者把宪法作为法源、并在疑难案件中将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宪法才能成为活的宪法。应当说,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在应当“运用宪法”的认识上已经获得广泛共识,目前学界存在争论的问题是法院如何运用宪法?是纯粹的“适用”宪法,还是可以“解释”宪法?抑或通过合宪性解释方法即“按照宪法的精神对法律的内涵进行的解释”[18]间接发挥宪法的作用?
笔者主张,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在我国现有宪法制度设计下,没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它只能“适用”宪法,详言之,司法者运用宪法是把宪法原则、宪法规范作为裁判的法源,在法律层面穷尽了一切手段之后仍无法找到解决案件的办法时,可以寻求引用或援引宪法规范或宪法原则作为裁判依据,这种司法运用宪法的方法,笔者把它定性为“非解释性宪法适用”,即法院或法官在援引宪法条款时,仅仅援引那些字义清楚、明白无异议,并具有公理性,不必作字词含义的解释。换言之,法官审理普通案件时,或为了增强判决结论的说服力,或为了补充法律之漏洞,直接援引宪法条文,而不作解释。[19]人民法院在“运用宪法”时为何不能解释宪法?因为我国宪法把“解释宪法”的职权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该常委会才可依据宪法上的职权对宪法进行解释,这就决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宪法”的权力的专属性和排他性,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外,其他任何机关都不得行使“解释宪法”的权力,即使“隐含”的宪法解释权也有违立宪,如果其他机关譬如法院拥有了“隐含”的宪法解释权,就意味着法院事实上同样具有了宪法解释的权力,这与宪法典的设计是相冲突的,也违背宪法典的立宪原意。[20]P15所以,在我国目前宪法解释制度性结构下,法院只有采取对宪法不作任何解释的司法适用,才能与我国宪制相契合。
不过,也有部分年轻宪法学者出于运用宪法的强烈意识与时代责任感,试图将宪法适用的制度性结构问题转化为法律解释方法即合宪性解释问题寻求运用宪法的可能路径。[21]例如张翔教授就指出:在法官没有宪法解释权的前提下,宪法依然有对司法发生影响的空间,即在普通的法律案件审理中,如果法官负有对法律作“合宪性解释”的义务,有将宪法的精神藉由法律解释贯彻于法体系中的义务,则在普通法律案件中,就有作宪法层面分析的可能。[18]黄卉教授甚至乐观地指出:“通过体系解释、尤其目的解释,完全有理由突破目前的通说,转而认定在现有宪法框架下人民法院是有权解释宪法,从而铺平了法官进行合宪性解释的道路”。[22]这样就为我国宪法进入司法适用领域、发挥宪法对司法的某种影响,找到了某种路径。这种学术努力与学术贡献值得充分肯定。然而,在笔者看来,合宪性解释虽被视为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但毕竟像德国慕尼黑大学斯特凡·科里奥特教授所指出的:“合宪性解释就是对法律——而非对宪法——的解释”,他认为合宪性解释的概念仅适用于“法律”(Gesetz),而不包括国家的其他法律行为。如果认真审视,我们可以发现,合宪性解释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解释方法,也不是目的解释的一种类型。它毋宁是要求,对法律解释的多种可能结果进行相互比较,并排除其中与宪法和宪法的基础决定不符的部分。[23]当然,科里奥特教授的观点在国内并非没有争议,有学者就明确指出:“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必然包含了对宪法的解释,我们不能掩耳盗铃地否认宪法解释曾经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出现过。”[24]其中涉及的核心在于:合宪性解释是否必然触及到宪法概念的解释?依照常理,在若干个法律解释结果中,判断哪一个法律解释结果合乎宪法精神,必然触及对宪法精神的理解与把握,根据“理解”而作出最终解释结果的取舍。问题在于,理解是否等同于解释?加达默尔曾指出:“理解总是解释,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他甚至说:“一切理解都是解释”;[25]P395,496倘若理解就是解释,那么合宪性解释必然触及对宪法的解释;然而,理解与解释虽然是诠释学的一对核心范畴,但二者并非相互直接包含或等同。《现代汉语词典》对“理解”的解释是:“懂;了解”;对“解释”的解释是:“说明含义、原因、理由等”。[26]P704洪汉鼎先生指出:“理解与解释不同,理解是解释的基础和前提,解释则是理解的发展和说明。”[27]P66理解就是理解,并非总是解释,狄尔泰就把“理解”看作人以心灵力量的整体去认识自己及自己所创造的精神世界的能力;施莱尔马赫把理解视为是一种推理过程,即用已知比较未知,从已知推出未知。[28]P145赫什则认为理解在于原原本本地构造文本的意义,而解释则是解释者对文本的意义所作的阐释,渗杂有解释者附加的成分。[29]可见,理解是对文本精神、意义的内心认同与领会,了然于心;解释是对文本语词、含义的书面文字的说明与阐释。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在理解基础上才能解释,因而可以说没有理解就没有解释;然而,解释则是对不明确的含义或意义的说明或创造,理解“在于原原本本地构造文本的意义”。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或比较与选择性方法,其要求是:依字义及脉络关系可能的多数解释中,应优先选择符合宪法原则,因此得以维持的规范解释。在具体化宪法原则时,法官应尊重立法者对具体化的优先权。[30]P221在合宪性解释中,由于不触及宪法原则或精神的具体化解释,法官仅仅依其内心的“理解”或领会作为选择性解释结果的取舍标准,因而“合宪性解释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并不是宪法解释,当然也就不是依据宪法裁判具体个案,但却依然是在具体案件中对宪法所确立的价值的贯彻,这个贯彻所凭借的就是法律解释的方法”。[18]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多少体现出宪法规范在整个国家法秩序中的最高位阶性与权威性,使我国宪法能够发挥其价值指引的应有功能。
另外,有学者基于我国宪法在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归纳出了三种宪法解释方法意义上的“解释性适用”的情形,这就是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31]P104然而,仔细审视之后,上述三种所谓的宪法解释,其实均可归为宪法“理解”而非宪法“解释”,皆属于“非解释性宪法适用”的范畴。譬如:在“张嘉华案”中,法院指出:“公民的合法的所有财产不受侵犯,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公民享有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学者认为这种将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解析为“占有、使用、处分、收益”之权利,就是对宪法上的“财产”一词所作的文义解释。[31]109笔者认为,这并非为宪法上的“财产”一词进行解释,法院引用的两段话是分开的,前一句是宪法规定,后一句是从《民法通则》第71条摘录的一句话,即“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物权法》第39条也规定: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是法官将私有财产“理解”为“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没有针对宪法上的“财产”概念进行解释。这种形似“解释”,实则“理解”。另外,学者将法院认为的举报权视为对宪法第41条关于公民控告权、检举权的文义解释,实际也是一种理解,因为汉语中的“举报”之意就是“检举报告”。[26]P73再比如,将法院判决书中关于“我国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婚姻法》《刑法》等多个法律规定了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而且法律规定完整的赡养义务不仅包括物质供养,还包括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的一段话解释为宪法体系解释方法,并认为是将宪法义务的含义解析为物质供养、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三个层次。其实这三个赡养的层次并非是法院的解释,而是对2012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规定的援引。④另外,学者针对人民法院在“吉林科龙优质种(肉)牛繁育有限公司与九台市西营城街道办事处杨家岗村村民委员会合同纠纷案”中的裁判说理部分认为是对《宪法》第10条“征收征用”条款中的“土地征收”、“土地征用”概念进行了解释[31]P126-129。事实上,法院的裁判说理部分看似对上述两个概念的解释,实则仍是立法者的解释,譬如裁判书引用了王兆国在关于宪法修正案第十条修改说明中关于“征收”与“征用”的差异,这种引用中的解释仍是立法者的解释,而非法院法官的解释;裁判书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引用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8条关于对“公共利益需要”的列举式规定,同样是立法者对“公共利益”的解释。诸如此类的裁判书中所涉猎的有关宪法条款的引用,皆属于法院对相关条款的理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宪法解释。
1.2.1 不同因素对甜菜苷类色素提取率的影响 色素提取工艺流程:新鲜原料→去除外层果皮→将果皮打碎→加入溶剂浸泡并搅拌→离心分纯→过滤→真空浓缩→色素溶液。
如果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或规范性文件在宪法文本中缺乏相应的制度或内容而没有直接写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那么其体现宪法精神的方式就是遵循“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宪法义务与宪法原则。作为立法机关立法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合乎宪法精神的宪法义务则是“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既是一项宪法义务,也是一项宪法原则。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立法法》第3条明确规定了“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第100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可见,在立法过程中遵循“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原则还是一项宪法义务。因此,无论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还是行使部门或地方立法权的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过程中都必须遵循宪法原则,其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均须符合宪法精神。
据介绍,水稻作为单子叶植物生物学研究的模式植物,在基因组与功能基因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与同为模式植物的拟南芥相比,水稻需要较大的室外大田或温室,而且其较长的生长周期和对自然环境的高度依赖性,也制约了其生物学基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水稻逆境抗性、水稻病原菌互作等方面。
鉴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宪法制度构架中,法院运用宪法的主要方式就是“非解释性适用”;至于借助合宪性解释方法,以体现宪法规范在整个国家法秩序中的价值引导与权利保障功能,应当提倡而非禁止,从而使法律的解释合乎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保证解释法律的合宪法性。
从理论逻辑到实践逻辑、从宣言性倡导到建立健全运用宪法制度,这是中国宪法实施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它标志着中国宪法实施不再仅仅停留于口号式的宣扬,而是落实于运用宪法制度的构建与方法意义上的具体适用上,从而将会消除那种关于“宪法无用论”的错误观念。这种宪法实施的实质性进步,事实上突破了法律实施就是宪法实施或宪法实施等于法律实施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它意识到了宪法实施与法律实施的根本差异并非在于内容上的实施与否,而是功能与对象上的差异。换言之,法律实施得再好,也不等于宪法实施得好,因为宪法实施的功能在于保障一切规范性法律文件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从而实现凡是与宪法相违背的抽象性文件予以撤销或废止、进而保障公民免遭国家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立法性权利侵害之目的。
四、解释性适用:合宪性审查机关运用宪法的方法
既然“根据宪法”制定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那么在立法实践中,立法机关尤其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国家立法权时,是如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其遵循怎样的规律?笔者对此结合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进行初步的实证考察。
鉴于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并未在第五次宪法修改案之后作出相应修正,因而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机构不只是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即法制工作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是我国法规备案审查的主要承担者⑥,它对报送备案的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对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司法解释有权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予以撤销、纠正,因此备案审查制度是一种融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机构。
无论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作为合宪性审查机构,在运用宪法时,其方法与司法机关运用宪法的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对宪法相关条款的解释性适用。我国的合宪性审查不是由普通法院或专门机构如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进行的司法审查,而是采取由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对法律的合宪法性进行立法审查模式。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审查、研究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的,首先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其次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及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反馈;再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向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研究意见,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最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经审查、研究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在后两个阶段,均涉及对宪法相关条款的解释:第一,审查机构向制定机关提出意见,涉及对相关宪法条款的理解与解释;第二,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涉及对相关宪法条款的理解与解释。合宪性审查必须对宪法相应条款的含义的解释,以判断规范性文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譬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提到将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问题,⑦就需要合宪性审查机构对宪法第37条关于“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条款作出解释,从而说明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制定了《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是何以与宪法相抵触,以便从根本上废止收容教育制度。
结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运用宪法”思想,实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与宪法思想的重要内容,具有深刻的划时代意义与强烈的现实价值,它将我国宪法实施这一实践问题从理论逻辑还原为实践逻辑,即宪法实施本质上是运用宪法的实践问题从理论逻辑到实践逻辑、从宣言性倡导到建立健全运用宪法制度,这是中国宪法实施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建立健全运用宪法制度强调的是宪法在整个中国法治实践中的运用,不仅体现在立法环节,也体现在执法与司法环节。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宪法规范只有确实发挥其引导、规制、指引、保障的功能,宪法的权威与尊严才能真正树立起来,宪法实施才能真正落地。运用宪法的实践逻辑,注重的是如何运用,即方法论问题。它包括立法机关如何“运用宪法”,也包括执法机关如何“运用宪法”以及司法机关如何“运用宪法”等等,只有解决了如何运用的方法论问题,才能使运用宪法的法治实践真正展开。“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是党中央针对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若以此作为判断标准,那么在我国宪法实践与立法实践中存在两种具体方法模式:一是 “根据宪法”模式;二是 “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模式。作为事实上担负着“运用宪法”的重要使命的裁判者法院,在我国现有宪法制度设计下,没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它只能“适用”宪法,即司法者运用宪法是把宪法原则、宪法规范作为裁判的法源,在法律层面穷尽了一切手段之后仍无法找到解决案件的办法时,可以寻求引用或援引宪法规范或宪法原则作为裁判的依据,这种司法运用宪法的方法为“非解释性宪法适用”,即法院或法官在援引宪法条款时,仅仅援引那些字义清楚、明白而无异议,并具有公理性,不必作字词含义的解释。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专门机构,在进行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必然遇到对宪法条文的理解与解释,这时,只有通过宪法解释,才能作出合宪性的判断,对合乎宪法的规范性文件予以维护,对与宪法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予以改变、撤销或废止。
唐末诗评家张为在其诗评专著《诗人主客图》中,将马戴列为“清奇雅正”的“升堂”弟子。[20]马戴诗中所呈现的典雅、清奇之美与其人生态度是不可分的,他在创作羁旅诗歌时,多处提到其向往归隐的倾向,对隐逸生活的羡慕,这是源于释道因素对其的影响,与老子提倡“淡泊”的思想也是分不开的。
注释:
①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这是党中央首次提出“用法”理念;此后在制定实施的“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皆强调“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2011年3月28日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所作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的思想;2012年3月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快形成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同样提出:“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首次将“尊法”放在首位,提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八字诀。
② 如195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批复》、1986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1986 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询问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 用法律规范行文件的批复》,在列举的“可以引用”的法源目录里没有列上宪法;2016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明确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2009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 律文件的规定》第4条规定:“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 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该规定未将“宪法”纳入民事裁判文书可以引用的法源之列,从而使法官不能直接援引宪法裁判民事案件,客观上导致我国“宪法规范”不能直接作为法官处理纠纷的依据。2005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判决书援引法律等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判决书中一般不得直接引宪法”。
③ 现行《宪法》第5条第2款。
④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第十二条 赡养人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护理。”
⑤ 即使在那些设立了宪法法院的国家,普通法院如对一项法律的合宪性发生疑问,只能中止诉讼程序而将问题提交宪法法院(参见勒内.达维徳:《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二)普法与执法存在脱节,缺乏有效融合。“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要求,要“将普法贯穿于执法全过程,渗透于执法各环节”。根据调研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单位较为重视责任制的落实,结合各自实际开展了许多形式内容丰富的普法工作,值得肯定。但应该注意到,各级各部门对“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要求认识仍有欠缺,存在单纯为了普法而普法的现象,执法与普法存在脱节,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⑥ 备案审查制度是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宪法性制度。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监督法的规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应当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报送备案的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对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司法解释有权予以撤销、纠正,因此备案审查制度是一种融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机构。
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2018年12月24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习近平.更加注重发挥宪法重要作用 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N].人民日报,2018—02—26(2).
[3] 习近平.弘扬宪法精神 树立宪法权威 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N].人民日报,2018—12—05(1).
[4] 张友渔.进一步研究新宪法,实施新宪法[J].中国法学,1984,1.
[5] 周叶中.宪法实施: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J].法学,1987 , 5 .
[6] 《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1.
[7] 王利明.何谓根据宪法制定民法?[J].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1(创刊号).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9] 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编.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汇编(上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10] 古汉语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11] 童之伟.立法“依据宪法”无可非议[J].中国法学 ,2007, 1.
[1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3] 蔡定剑.宪法精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4] 马岭.宪法原理解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15] 韩大元.民法典编纂要体现宪法精神[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6.
[16] 范进学.中国宪法实施与宪法方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17] 梁启超.政论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4.
[18] 张翔.两种宪法案件: 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J].中国法学,2008,3.
[19] 范进学.非解释性宪法适用论[J].苏州大学学报,2016,5.
[20] 范进学.认真对待宪法解释[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21] 张翔.两种宪法案件: 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J].中国法学,2008,3.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J].法学研究,2016,6.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 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J].中国法学,2014,6.王光辉.论法院合宪性解释的可能与问题[J].四川大学学报.2014,5.杜强强.论合宪性解释的法律对话功能———以工伤认定为中心[J].法商研究,2018,1.
[22] 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J].中国法学, 2014, 1 .
[23] [德]斯特凡·科里奥特.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正当的解释规则抑或对立法者的不当监护?[J].田伟 译.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3.
[24] 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J].中国法学,2014,6.
[25]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6]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7]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8] 殷鼎.理解的命运[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9] 彭漪涟.逻辑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30]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1] 余军等.中国宪法司法适用之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The Logic and Methodology of “Applying the Constitution ”
Fan Jin -xue
(KoGuan Law School,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plicitly put forward the ideas of “Apply Constitu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rule of law ideology and constitutional thought of XiJinPing’s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profou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and strong practical value, it will b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Country the practice problems from theoretical logic to practice logic; the practical logic of applying Constitution, we pay attention to how to apply it, that is, methodology. It includes how the legislature applies the constitution, How law enforcement applies the constitution, how the judiciary applies the constitution, and so on. To make every piece of legislation conform to the spirit of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legislative requirement put forwar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legislature of our Country. On that basis, there are two specific methods in China′s constitutional practice and legislative practice: one is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The second is the mode of “no conflict with the Constitution”. As a judge with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applying the constitution”, the court applies the method of “non-interpretative appl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under the design of China’s existing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takes constitutional norms or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as the basis of judgment by quoting or invoking them. As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constitutionality review, in the process of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inevitably encounte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t is only through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o mak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judgment, the constitutional regulatory documents shall be maintained, in conflict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normative documents amended, revoked or cancelled.
【Key words 】applying the constitut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constitutional review
【中图分类号】 DF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6274( 2019) 04— 016— 12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项目“加强宪法实施、教育和监督研究”(项目批准号18JZ036)、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宪法解释制度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7AFX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范进学(1963-),男,山东临朐人,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法理学。
(责任编辑:孙培福)
标签:运用宪法论文; 宪法实施论文; 宪法解释论文; 合宪性审查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