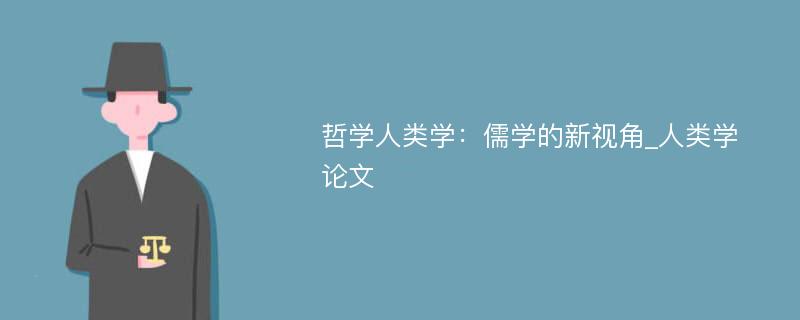
哲学人类学:儒学研究的一个新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儒学论文,哲学论文,新视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孔孟之道中,所有的人类,都可以在“性”上统一。“性”是全部儒学的中心命题——“尽其在我”的逻辑根据。
“性”是什么?它至少有三重涵义。
它可以指“性能”,即生物本能。老子把这一生物本能概括为简洁的“食”“色”二字,说:“食,色,性也。”《荀子·性恶篇》所全面描述的“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这种种人性中的弱点和阴暗面,都是从这一“性能”引申而推论出来的。
它又可以指普遍存在的具体性格,为所谓“清”与“浊”,“刚”与“柔”,“智”与“愚”等相对应的概念。它一般被概括为“气性”、“才性”、“气质之性”以至“百人百性”等。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就是从这一基础上抽象出来的。
“性”在孔、孟这里,却是一个特殊的范畴,超越于前两种涵义。孟子说:“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四肢之于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认为,对老子等对生物本能的归纳或演绎而出的种种现象,并不能称之为“性”,而是有着更为根本的东西。对此,张载说得更清楚。《正蒙·诚明篇》中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不以“气”——性格、“质”——性能这二者之“性”为真正的“性”,这是儒家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是“君子”的标志。但更重要的,是“善反之”,须去现象之后寻求和获得的“天地之性”——这才是那最根本的东西。
这一“天地之性”,它不在任何别的地方,而存在于一般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之中,成为命中之“命”。对一般生命说来,它是超越具体生命的绝对的普遍,是使生命真正成为生命的东西,即生命的本体,以《中庸》来说,即“天命之谓性”,以《诗经·大雅·先民》来说,即“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一“天地之性”,只有在人的生命中才能存在。
因此,到哪里去寻找对这一生命秘密的觉慧——这一问题唯一的答案在此,就是人的自身。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所倡的即以自身的具体而微的生命来觉解以至显现出宇宙的真正生命。这就是《易·上系》中所谓“显诸仁”的意蕴,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一儒家人性论的最后答案的根据所在。
从这一基础出发,因各种偶然情况的存在,使人类有千差万别,“习相远”拉开了人类形成不同的距离。那末,爱智慧因而必须传播智慧的思想者,就有责任成为教师,去偶然中宣讲必然和坚持必然,让人们在“学而时习之”中获取智慧;让人们在“克已复礼为仁”的自觉自律中完美、完善;更进而使人们都作为主体而哲学化,已立立人,已达达人,搏施济众成为圣人——“大而化之之谓圣”,以自己所完成的伟大去实现对人的文化。
儒学从此而去规定的理想人格,谓之“诚”。“诚”,是对真实无妄的一种概括。为什么要把真实概括为“诚”呢?朱熹解释了,他说:“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圣人之所以圣者,无他焉,以其独能全此而已。”这是以此岸为场,以生人为点必有的哲学概括。“诚”中包孕着的是以此岸生人为唯一的至情。孔、孟均以对生命的肯定为基本的哲学立场。而对生命的肯定,勿庸赘言,又首先是生命真实的肯定。但真实地肯定了生命,还是不够的。《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存在是真实无妄的。能体证到这一存在真实,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但唯有所有生命中的特殊生命——人类,才会自觉地去觉悟这一存在真实,亦在这一觉悟中去获得应有的真实存在,以期达到“纯粹至善”。因此,周敦颐在《通书》中能说:
圣,诚而已矣。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
儒学世界与儒教王国极不相同,在有的地方和时候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在儒学世界中,宇宙以运动表现出真实无妄;运动,就是真实无妄的根据。各个具体的宇宙生命,因而也是真实无妄的存在。但这是远远不足的。只有人对“各正性命”的发现,寄希望于各自体证以至自觉地实践生命的应有内容,生命才可能真正真实地存在,也即纯粹至善地存在。
生命的这一运动历程,表现为矛盾的普遍展开。周敦颐于《通书》中又曾说过:
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享”,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阴”与“阳”,不过是“矛盾”抽象的再具体。生命,就在这矛盾的无间歇中继续存在。有悟于这一生命本体,回归于这一生命本体,就是“性”的全部,即“性”的体——“元”,“性”的正确路向——“享”,“性”的价值——“利”,“性”的定位——“贞”。生命的一切,都只能完成于生命之中。
但这并不是每种生命都能具有的觉悟,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人类的意识。这个意识之源在“仁”,即一个个体在现实交往关系中与另一个个体发生关联的地方,这种意识总是成为活生生的时候——两个个体相遇,实质上意味着存在者与自己相遇;某一个体与另一个体的体验是存在者的自我体验。这一段几乎类似于热恋的蜜语,所说的却是热恋及其他相关的一切的哲学:在生命中才能体验生命。而又只有人类,才能在生命中体验到生命。
这一意识之极,亦在“仁”:在生命中实现生命。而只有人类,才能在生命中实现生命。所以,这一极至,就必然地为《中庸》所谓:
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这也即张载《西铭》所谓: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至此,似可以说,在这一系列中运作的“性”,远非兽性,亦非神性,它,只能是人类理性。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基本的儒学,在本质意义上说来,它不过是存在者关于自身的一种意识而已。
二
人是一个能够自我质疑的存在,因而人的问题只有人自己才能回答。虽然不少人类学家都肯定着远在古希腊哲学、历史学中就已有人类学的存在,每一个民族中也都蕴涵着一种人类学,但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明确的事实——人类学,作为文艺复兴之后的一门综合性的现代科学,其产生毕竟是晚近的事;它是经历了漫长的形成时期之后而独立的。
而且,在产生之初的人类学,一个不短的时期内曾仅仅是生物学发展中的一个副产物。它以人类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其变化规律,人体发育中有关体质的各种问题,各人种的形成及分布等等,为研究对象。在1596年奥·卡斯曼(O·Casmann)首先以《人类学》题名他的著作之后,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还是相当沉寂的。在人类的存在获得强有力的生物学证明的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考古学的突出进展,一些古人类骨骼化石在世界不同地区的被发现,人们注意到人类和猿类尤其是其中的类人猿的关系。从人类的来源这个问题开始,一系列与人类相联系的问题,即人的自然史作为一个重大的课题进入研究领域。这时的人类学,诚如托皮那(Topinard)1876年在其《人类学》中所说:“人类学是博物学的一个分科,为研究人及人种的学问。”
当已被注意到了的人类之间的文化差异,被用身体的差异来解释陷入窘境之时,人类学的研究由体质而推广到文化——人的一切文化表现,就注定了是必然的。特别是现代世界的剧变和随之而来的文化震荡,使人类在长时期中形成的时空顺序、整体意识以至感应能力都陷入混乱以至危机之时,“正如形而上学和信仰对现代人来说已不再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一样,世界本身对现代人来说也失去了本身自明的性质。对世界的神秘和可疑性的意识,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这样盛行;另一方面,或许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地要求人们面对今天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采取一种明确的态度。知识和信仰已不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必需了。形而上学的欲望和怀疑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对立,是今天人们精神生活中一种巨大的分裂;第二种分裂就是一方面生活不安定和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需作出明确的实际决定之间的矛盾。”(〔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译本第25页)
这种混乱与危机,归结为一点,就是人对自我发生了困惑。几乎是一种讽刺,在人类学日益科学化的时候,关于人的本质和起源的观念却变得比任何时候更有争议、更不确定和更不相同——人对于人自己来说,却整个地、完全地成了“疑问”。
对二十世纪以来如此深刻的“自疑”来说,哪里是最好的提问场所和答疑的宝藏所在呢?毫无疑问,仍然只有人类学才是。没有庄体的客体,不仅难于想象,而即使存在那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现在,终于遇到了一个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存在——人,我们应该作出什么?这取决于我们对“我们”的诠释,从这里才有可能获得我们所面临的世界与我们的承受限度之间关系的重新确定。怀着这样的兴趣和激情,于是,喧宾夺主,文化人类学在本世纪蓬勃地发展起来,亦出现了其它学科望尘莫及的众多分支,以至于可以在现有的众多学科中都可以划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部分。人们的现实,被命名为一种文化现实;人们之间的一切差异,都被归结为文化产生、发展中的差异。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斯·舍勒创立了哲学人类学。继后,生物学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文化人类学分支不断涌现。这些学科虽各从不同的视点出发,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即对人“还原”,寻找人类文化先验的“根”,以从此而重绘人与世界关系的蓝图,去超越危机的现实中的现实危机。——人类学研究的突飞猛进,因此当然就成为一种必然。
舍勒的哲学人类学,从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所考察过的人类的外在特征和文化成就这里出发,但它认为这仅是对人类的表面认识,它认为更重要的、在这一切之上的、构成人类与其它一切现存生物相对照的基本的本体论结构,才是它的研究对象。它认为人对人自身的这一认识将严重地影响到人的存在。如用舍勒的话来说,哲学人类学作为一种人类学,它对人提出的特殊问题是:
为什么那些成百上千适应能力差的物种都灭绝了,而人这个适应性如此之差的物种为什么却没有灭绝?这种病态的、落后的、忍受着苦难的动物,其基本状态就是胆战心惊地作茧自缚,自我保护它的适应性极差、极易受损害的器官。而这个几乎已被宣判了死刑的存在,却得以钻进“人性的原则”亦借此进入文明和文化中以自救。这一切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马克斯。·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李们杰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899年版。以后引自同书者,不再一一注出。)
哲学人类学一般地说来它是对十九世纪带有分裂世界倾向的实证主义的抗议,它表现出一种一般的哲学不再能满足的哲学需要:证明“神的存在”的哲学已经过去,一种证明“人的存在”的哲学开始来临。它以一种对人类学的哲学整合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从其具体形式着眼,哲学人类学则表现为对人类学的一次否定。
近代人本主义从根本上拒绝了“上帝造人”的神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以及历史学的一系列证明。在这一系列证明中,更强有力的一个证明就是人类学的证明。而从哲学人类学看来,这正是使人的地位和价值受到极大贬低的一个主要根源所在。面对着生物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显赫的研究成果,哲学人类学提出了一个反命题:人的不可理解性和人的本质的不可规定性。因此,以至有人可以说出:“哲学人类学的代表是在砍他们自己坐着的那根树枝。”舍勒的哲学人类学认为。所有关于人的不论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抑或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失误,即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关于人的观念——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结构的说明:关于人同整个自然界的关系,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的起源,人受其推动和用以推动的力量,人在世界上的生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开端这些种种的一个完整的答案。而这个答案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仅是哲学的基础,而且是全部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的基础。以寻求这一答案为使命的一种科学,就是哲学人类学。舍勒认为:“哲学形而上学的终极目标,是认识绝对地存在着的存在。”而当“存在者展现在人身上”时,在此规定下的人类学理论,应对人类绝对地存在着的存在进行探讨,建构“人而上学”,它的的最低目的是:“在各门不同的科学业已取得的有关人的单项知识大量宝藏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观照的新形式。”
其实,舍勒所梦想的这个“人而上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是早已建立了的。它,就是中国儒学的核心——孔孟之道。
如果把中国春秋时代发生过的“礼坏乐崩”不仅只理解为一种单一社会制度的衰灭和崩溃,而也认识到这也是一种已经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根本性对立的冲突的种种表现,把它理解为远古以来长期形成的时空顺序、整体意识和由此而来的古人的感应能力所陷入的混乱以至危机,那么孔子思想中的若干方面是不难说明的。给孔子和儒学定性,在结论上的分歧可以多至无可穷尽,而在方法上却可以说是极为近似的: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把各自不同时代的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现实预设为孔子的自觉。这尤为集中地表现在近现代以来的儒学研究中。以西周——春秋的社会性质作为孔子评价的唯一参照,曾是很长时间内孔子研究的不二法门。殊不知,孔子虽自信于“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然而西周——春秋以至后来所划分出、所认定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若干阶段的性质,却是孔子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他不可能自觉他所处的社会将在以后的历史学中获得的地位,更不可能预想到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对照中产生的对西周以来中国文化的评价。他所知道的,也仅仅只是一种人的自我困惑。在中国,这次困惑是空前的,而且,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在二十世纪以来这一次放大了的“礼坏乐崩”中,有了哲学人类学的产生。哲学人类学表现出一种对现有人类学研究的否定,表现出一种对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对人的本质的现成证明的拒绝。这些研究和证明,也恰是历史未来得及给孔子和孟子提供的。于是,孔孟之道和哲学人类学之间,虽相距二千多年的时间跨度,却有了一种共同的逻辑:寻找人类文化先验的“根”之所在。只是当时的孔孟是藉此去规划人与世界关系的应有蓝图而不是“重绘”而已,其间的共同目的都是否定危机的现实中的现实危机。
孔孟之道中的“性”,它不是别的,它正是一个“构成人类与其它一切现存生物相对照的基本本体论结构”,而且它甚至是一个人类与自身中的生物性相对照的基本本体论结构。它说明着人同整个自然界的关系,它是人的形而上学的起源,是人受其推动和用以推动的力量,也就是人在世界上的生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开端。它虽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观照的古典形式,但它毕竟是一个统一的关于人的观念,是一个曾有过的完整的答案,是一个关于人的绝对地存在着的存在的说明。
全部儒学就从此才得以视宇宙为有情,赋自然以生命,构架起人中有天,天中有人的思维模式。全部儒学之“得以钻进‘人性的原则’,并借此进入文明和文化中以自救”作为一种文化生命的存在,亦因此才是可能的。
三
相距着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与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它们都共同认定:人的清晰而确立的自我形象是人类社会生活稳定和健全的基础。它们都从此出发去寻找人的这个理想的自我形象,而在人的问题上脱离与神学及自然科学的联系。其间虽有自觉与否的区别,但却是在历史的两极上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并且提问的立场也是相同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舍勒也是从“人之异于禽兽者也几希”这里出发的。舍勒断然拒绝了两种似乎是冲突着的观点。第一种是声称理智的选择为人所独具而为动物所没有的观点,舍勒认为这种观点“正是在我认为不存在本质区别的地方申明本质区别的存在”;第二种是舍勒所谓“达尔文学派和拉马克学派的一切进化论者”拒绝承认人与动物之间有一个终极的区别的观点。他于是在自然科学之上建立了一个生命的等级图式,从这个图式来规定人的特殊的宇宙地位。
在这个图式中,舍勒认为植物是仅有外向的感觉欲求的存在,这种感觉欲求仅是一种无对象的喜悦和无对象的痛苦。植物的营养、生长和繁殖,都只存在于“感觉欲求”的模糊统一中。而处于生存的第二级上的一般动物,之取得了“灵魂”的形式,是由于它们具备了“本能”行为,从而产生出了“合习惯的”行为与“理智的”行为:即“以同类过去的行为为基础”的行为,一个“突发的,解决一个能动地规定的任务,不依赖之前已作过的次数”的行为。
舍勒认为,使人所以为人的是“一个与所有生命相对立的原则”。因此,人可以处在生命的最高等级的层次,人集存在的“生命的所有本质阶段于一身,并且至少就本质范围而言,在他身上整个自然达到了它的存在最高的统一”。但人却不是一种更为发达的生物。虽然,植物性只相当于人的睡眠状态,而与一般动物相比,“作为智力及联想记忆最发达的可塑的哺乳动物类型,人的本能极不发达。”因此,“使人之为人的东西,甚至是一个与所有生命相对立的原则,人们绝不能用‘自然的生命进行’来解释这个使人之为人的原则。”
那么,这个使人之为人的东西,在舍勒眼中是什么呢?他说,这是“事物本身最高的原因”。这个原因,即与所有生命相对立的原则,早在希腊人那里曾用“理性”来概括过。但舍勒认为,它不够全面;应当用一个既能包含理性概念,又能包容对元现象或本质形态的观照,还能包容如善、爱、悔、畏等其等级不确定的情感和意志所产生的行动的词来概括。舍勒认为,这个词就是“精神”(Geist)。 舍勒亦由此而给人定义,他认为:“那个精神在其中,在有限的存在范围内显现的行为中心,我们要名之以人本身(Person),以严格区别于一切功能性的‘生命’中心。”“存在者展现在人身上”,“而精神本身最终就是这个存在者本身的一个定语。”“精神”成为人的纯粹的存在,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原始的存在领域。
在舍勒之前,已有过一系列的“人”的定义。从正面的明确特征来给“人”定义的,有“制造工具的动物”、“政治动物”、“万物存在的尺度”、“符号的动物”等等。这些定义在正面的、明确的方面有了某种获得之余,难免会在负面带来一定的亏损和欠缺。于是,又有了从负面的隐喻来暗示“人”的特征的若干定义,如“裸猿”、“会笑的动物”、“唯一会许诺的动物”等等俱是。这些定义从负面显示出相当的机智,但给正面的说明的,是蒙上了模糊的面纱之处远多于可作补充之处。因此,两者都让“人”自身总是不能释然。理所当然地,人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古希腊的“理性”定义这里来,认为这个定义在内涵上或外延上都还未被上述正负两种定义所超越。只有舍勒认为“它,不够全面”,而试图用“精神”这个词来取代之。
可与这一系列“人”的定义相映的是,在中国先秦也有过一幅灿烂的“人论”图景:
墨子在《兼爱》中,从各种身份的人的“自爱自利”着眼论述了“不可不劝爱人”的必要;于《尚同》中,又从“一人一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这一“交相非”的现实出发,肯定了“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的合理性。在墨子眼中,人是一种需要与满足之间的政治被动者。《节葬》、《非乐》等篇,其对人的视点都从此出。在法家的著名代表韩非那里,这一点被揭发出了更深刻的物质原因。他有一个著名的举例,曰:“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畴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他由这一简单事实而结论曰:“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主客之间乃至一切人际之间的关系在实质上无非利害关系。“兼相爱”是不可能的,“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人是一种需要与满足之间的经济动物。韩非的政治理论、历史理论及人口学观点,都以此为核心。
在这第一次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震荡中,“人”对于人自己来说第一次完全地成为“疑问”的时候,因对“人”的困惑而愤疾于人性,各执一偏,以至最后荀子之把“人”归结于“性恶”,都是可以理解的。第一个深切地感受到且提出对“人”的困惑的孔子,却没有把目光停留在现象上,而深入了更本质的东西,说“性相近,习相远”,需要与满足间的种种现象是结果,只有“性”才是唯一的原因和本体,使人成为人的原则,人的纯粹存在。
对“性”曾有着不同路向的诠释:
道家是不反对“性”的存在的,但另是一种理解。道家的开创者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性的存在,就是为了否定人的一切特殊的存在。在道家这里,人的一切需要都成为多余,满足就是不需要,墨子和韩非的人论无可立足。这是道家全部人论的出发点。
老子也是不反对“性”的存在的,但他把“性”的内容仅归结为“食”与“色”,说“食、色,性也。”现象就是纯粹的存在,无所谓结果与原因。墨子、韩非以至荀子的人论,在此都有了哲学根据。
孔子的“性”定义,当然不能这样地诠释。如果它是“习”的对立面,是准备用以否定人的一切特殊的存在,那么何必倡导对文化的“学而时习之”呢?而如果它仅有生物性本能的内容,那么何必又由此而去劝勉“欲仁仁至”和“克己复礼”呢?“性”在孔子这里,它既包括“对元现象或本质形态的观照”,它还包括“确定等级的尚待说明的情感和意志所产生的行动”。“性”的这一哲学内容,唯有孟子正确地诠释了:《孟子·告子上》载孟子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性善”,这如同水流的归宿一样,是人性的元现象或本质形态,
种种“不善”于其毫无责任。《孟子·公孙丑上》又载孟子说: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孟子这里所谓“四端”,也是“确定等级的尚待说明的情感和意志所产生的行动”。
“性”、“性善”、“四端”,在孔、孟眼中也是“使人之成为人的东西”,如果舍勒允许的话,可以把他的定义作如是说而丝毫无损:
那个“性”在其中,在有限的存在范围内显现的行为中心,我们要名之以人本身,以严格区别于一切功能性的“生命”中心。
标签:人类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孔子论文; 人论论文; 国学论文; 舍勒论文; 中庸论文; 儒家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