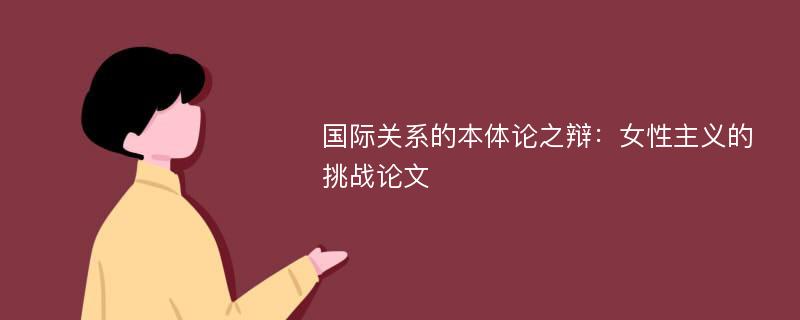
国际关系的本体论之辩:女性主义的挑战*
苏云婷 赵 薇
内容提要 | 本体论是国际关系知识产生的根源,是对国际关系本质的回答。基于对国际关系本质的不同认知,国际关系学界开始了“第四次论战”,理念主义对物质主义发起了本体论挑战。作为理念主义本体论的认同者,女性主义并不止步于在国际关系中引入观念和关系因素,而是致力于以社会性别为核心本体,改变国际关系的男性认同特征,进而发展出建基于社会性别的截然不同于主流学派的国际关系知识。
关 键 词 | 本体论 物质主义 理念主义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Feminism)研究视角和方法介入国际关系催生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早期的女性主义致力于拓展国际关系的研究主题,发现或添加女性议题,改变国际关系的性别盲区(gender blind)特征。然而女性主义者很快发现,这种做法充其量是对原有的研究框架做细枝末节的修补,并不能真正改变国际关系的男性霸权主义特征。① 吴小英:《当知识遭遇性别— —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1 期。 建基于男性经验和男性认同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不可能真正包容女性主义经验与思维方式。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知识确立的关键在于,对主流方法论特别是本体论进行彻底颠覆和改造。本体论思考由此进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
首先,就是其比较“另类”的焦段。正如你纠结的一样,是选35mm还是50mm?这是很多摄影爱好者甚至是职业摄影师的苦恼,如果你也在犹豫,那么这支40mm镜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折中选择。既没有35mm那样的小广角形变,又没有50mm镜头那么太过刻板的视角,取两者的优势满足更多拍摄场景需要。
一、论战背后:国际关系本体论问题的显现
方法论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国际关系亦不例外。“国际关系理论是由方法论的论争界定的”。② J. Ann Tickner, Gendering a Discipline: Some Feminist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30 (4), 2005, p.2186. 方法论演变促动范式转换,推动国际关系研究主题的深化与变动。“通过向说明关于社会现实的有效知识如何产生提供原则,每一种方法论都与一种特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相联系。”③ Caroline Ramazanoğlu and Janet Holland, Feminist Methodology: Challenges and Choices, SAGE Publications, 2002,p.11. 广义上的方法论(methodology)是由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和分析方法(method)构成的系统。它涵盖决定事物的本源,认识事物的角度,获得知识的途径,搭建研究议程,确定分析工具和手段。在方法论体系中,本体论始终处于首要地位。
本体论用以说明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和逻辑起点。国际关系学的本体论关注:国际关系是由什么质料构成的?国际关系的本质究竟为何?它是客观实在还是人们观念的结果?国际关系表象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国际关系的事实背后隐藏着什么意义?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形成本体论,其后引发出:人类如何获得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认知?这些认知如何得到理论和实践的确证?进而形成特定的认识论和具体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本体论在方法论体系中带有决定意义,本体论决定方法论的取舍① 袁正清:《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需要本体论的观照——来自建构主义理论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 期。 ,是造成学术分异、流派林立的根本性原因。只有对本体论的基本假定予以足够的关注,才能确当地理解各学派之要义。
②换言之,国际关系学派的不通约本质上是由本体差异造成的。国际关系本体论揭示出世界的本质与本源,界定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分析单元、单元的性质及其变化。
⑦ Charlotte Wu, Gender as a Category of Analysis: Reconciling Feminist Theory with Feminist Methodology, Graduat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10, 2013.
④ Charlotte Wu, Gender as a Category of Analysis: Reconciling Feminist Theory with Feminist Methodology, Graduat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10, 2013.
在本体论问题上,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学科成立初期,研究范畴界定、研究议题筛选和研究框架搭建的背后已经隐藏着本体论问题,是研究者的“无意识”、“潜意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开始“从具体问题转向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问题”,
⑤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84 页。 物质主义本体论、实证主义认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开始受到挑战。到90 年代,本体论不仅成为国际关系明确的研究对象,而且赋予了国际关系流派分野以哲学意蕴。本体论上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的分殊,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的“第四次论战”——本体论之辩。随着社会因素进入国际关系,并逐渐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研究群体,开辟出一条截然不同于正统理论的研究路径,国际关系学科就此出现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两种不可通约的本体论。
由现实主义界定的国际关系学科,运用从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习得的本体论进行理论建构,意欲发现国家国际行为的规律和法则。在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者看来,国际关系是独立于人类观念的客观存在,不受人类观念、行为的影响。人们只能发现、遵循其具有客观实在意义的规律性。国际关系理念无非就是对客观现实的描述而已,只有还原程度的差别,而无任何社会意义。批判理论则认为,国际关系绝非独立于人类社会的物质事实,而是行为体互动所形成的社会事实,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社会实在具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和集体意义的性质”。⑥ 袁正清:《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需要本体论的观照——来自建构主义理论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 期。 国际关系研究不能仅停留于对国际关系作出描述,还要对行为体的行为动机和意图进行解读,为其行为后果提供合理性解释。如果国际关系只是客观的、无从改变的不完美世界,那么搭建所谓不同的路径去获得对这个“客观现实”的认识岂非徒劳。
③ [美]布鲁克·A·艾克里,[ 瑞典 ] 玛丽娅·斯特恩,[ 新西兰 ] 杰奎·特鲁:《国际关系女性主义方法论》,金铭译,中译出版社,2016 年,第 5 页。 它“不仅与什么应该被认识或什么算作知识(count as knowledge)相关,而且关乎如何对待知识”。
国际关系的物质主义本体论立场,在传统现实主义那里表现为对国家、国家利益和权力等实在性的判断;新现实主义对国际物质结构的强调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立场。
女性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不仅是社会化的,而且是性别化的。以社会性别为核心分析范畴,使女性主义发展出截然不同于主流学派的国际关系知识。在本体论上,主流学派以物质界定秩序,认为国际关系是国家间实力分配的结果,作为秩序要素的国际制度则是实力分配的反映;女性主义则认为,国际关系是国家在社会交往中建构的,是国家间共有观念的体现。在认识论上,主流学派多以理性国家为中心,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解释秩序;边缘理论则认为,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多样性的,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必须充分考虑主体经验的多样性、差异性。在分析方法上,主流学派通常采用自然科学、经济学等分析方法,而边缘理论更倾向于社会学、解释学等分析方法。恰恰是方法论尤其是本体论的格格不入,成为女性主义长期徘徊在国际关系学科边缘并遭到主流学派强烈抵制的重要原因。对于身处边缘、被压迫的群体而言,他们最想探寻的绝非单纯的真相,而是如何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就此而论,女性主义与批判理论在本体论上绝非全然一致,它对主流学派的批判也最为决绝且彻底。
二、客观实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建构主义承认国际关系具有某种客观性,但同时强调,国际关系不是由行为体之间物质力量的分配决定的,而是由行为体间的共有观念(collective ideas)造就的。建构主义被认为着眼于认同、规范、理解、观念和主体信仰等,而不是现实主义所关注的物质、外在这些主导国际关系的生物逻辑。③ Javier Lezaun, Limit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Social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 (3), 2002. 在建构主义看来,现实主义强调的物质结构之中,实质上潜藏着社会关系。规范构成了行为体的利益、身份,创造出预期,并对什么才是恰当的行为作出规定。只有在与观念结构互动的情况下,物质结构才能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反过来,国际关系一经产生,又不断建构着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因此,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行为体与国际结构形成了互构性关系。结构与行为之间的互动是规范变革的首要驱动力(primary driving force)。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主流学派,力图为国际关系搭建更为坚实的科学根基。现实主义关注物质能力,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政治的基础亦是物质的。
①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2003. “具有决定意义的事物是独立于我们思想和经验之外的。”
② Benjamin Frankel, Restating the Realist Case: An Introduction,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s,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xiii. 这构成了现实主义学派的全部哲学基石。新自由主义虽然认识到了观念、规则等被现实主义忽略的要素对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但同时又认为,它们的作用是以制度、机构、国家等实体为载体的,因而在本质上也物质的。无论在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权力都被视为国际关系的基础性变量,被用于形成并维持国家间先定的关系。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以及国际制度都是永久的、稳定的实体存在,国际关系不过是行为体之间权力关系的表现,而权力的来源是物质性力量。作为行为体追求权力的结果,国际关系在本质上必然也是物质的。在实践中,国际关系由国家建构、破坏或维护,通过一系列有形的国际法、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来调节;国家以确定的政府、领土、公民等形式存在;国家的对外行为常常为利益和权力所驱动。这些为国际关系的物质主义本体提供了直觉基础。
③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 页。
传统贸易结算中买卖双方直接通过银行进行结算,跨境电商的交易中第三方支付机构成为结算双方的中介,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目前《国际结算》课程的教学跟不上实际业务的发展,亟须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与时俱进,适应快速发展的国际贸易。
作为批判理论阵营的一员,女性主义认同理念的本体论意义,赞同将社会因素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分析范畴。是否存在独立的有别于主流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本体论?这是女性主义经常面临的质疑。对该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着女性主义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边缘地位是由女性从属于主流性别本体的境遇决定的。在主流学派眼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或是子虚乌有,或是国际关系衍生出的次领域。对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而言,最好的状态不过仅仅获得了“国际关系预选赛”的参赛资格。面对主流学派的诘难,女性主义认为,这恰恰反映出国际关系的社会建构程度远远超越其他批判理论的指控。由于缺乏对本体论的性别拷问,批判理论的批判显然并未切中主流学派的要害。
西研究区闪锌矿矿石结构为他形晶粒状、他形粒状。构造为裂隙充填,形成不规则网脉状。伴有硅化、黄铁矿化、黄铜矿化,矿化呈脉状沿构造节理或裂隙分布,显示矿床成因类型为热液充填型。
传统现实主义力图在人性之中寻求对国际关系的科学解释。它认为,均势是国家间权力角逐的最终形式,并在客观上体现为国家间的秩序状态。人的需要决定着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行为,人类追求权力的本性是导致由人组成的国家无休止地追求权力的根本原因。而权力欲是人类的生物本能,具有生物特性。布拉德利 •塞耶(Bradley hayer)指出,现实主义的人性观与“生物进化论”Evolutionary Theory)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生物进化论”为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① Bradley Thayer, Bringing in Darwin: Evolutionary Theory,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2000.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观念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清晰可见,秩序表达的就是强者的利益。“生物进化论”为权势均衡秩序提供了有形的生物学基础。
建构主义以现实主义批判者、对立面的身份①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5, 2003. 。作为理念主义的代表,建构主义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尽管内部流派众多,但作为同一学术阵营的建构主义拥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观念:“概念先于观察;实证性事实的意义取决于组织事实的概念”,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②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 :《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86 页。 并主张以“变革本体论”(transformational ontology)取代“立场本体论”(positional ontology)。引入“变化”这一分析范畴,并以此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固有特征。建构主义描绘世界转变的过程,赋予观念现象以本体地位。建构主义认为:第一,全球政治是由国家所持有的主体间共有观念、规范、价值引导的,作为一种观念结构,主体间的共有观念限制并影响着国家的行为;第二,观念结构对行为体的作用不仅是调节性的,更是建构性的,它导致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不断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和利益——我是谁?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能够扮演何种角色?第三,观念结构与行为体相互建构、相互决定。观念结构规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反过来,结构又是在行为体实践过程中产生、再生并改变的。概言之,建构主义将国际关系事实视为主体间性的、社会的现实,而非现实主义所谓客观的物质现实。
本文提出一种抗盲检测直扩隐蔽信号设计方法,提出基于数据分级的大信号掩盖技术,给出了波形参数设计方案,并对大信号掩盖下的机密信号解调BER的理论值进行推导.最后仿真验证了所提方案可实现机密信号的抗盲检测.同时在保证机密信号抗盲检测能力的情况下,解调损失可控制在接受范围内.未来工作将分析初始相位、扩频码等参数对信号抗截获的影响.
② Dale C.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2000. “新现实主义具有清晰的本体论,其中国家、权势均衡、霍布斯式的追求权力的男人,以及国家组织的契约基础,被假定为与国际关系永远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③ Robert W. Cox, The Way Ahead: Toward A New Ontology of World Order, Richard Wyn Jones ed.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1, p.46. 它“重点研究国家,把国家化约为其物质力量的维度,并同样地将国际关系结构化约为均势,把均势视为物质力量的结构……且倾向于不重视国际关系中的规范和制度方面”。④ [加]罗伯特·W. 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国际关系:超越国际关系理论》, [ 美 ] 罗伯特·O. 基欧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205 页。 在对国际关系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新现实主义试图抛开传统现实主义的“人性论”,转而寻求更为“科学的”体系原因。然而,生物学的基础并未完全从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中剔除出去,它将传统现实主义倡导的物质主义本体论进一步发扬。新现实主义假定了一个类似于自然界生物进化的场景,“零和博弈”导致了国家对“死亡”的恐惧,只有通过彼此竞争才能战胜这种恐惧。在这一假定中,物种间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制度变迁均由自然选择逻辑主导。对权力结构和人类生物本性的双重依赖,使得新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本体论立场更加明确。新现实主义力图糅合经验和理性,从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面展示国际关系的物质性。它认为,追求权力是人性的必然结果;国家具有特定的利益,利益是国家外部行为的根本动力;国际体系由国家间的权力关系构成,对国家行为实施有效控制,国家体系的无政府性状是恒定的、不可变的。上述三个层次本质上都是物质的、不变的,由此产生的国际关系也必定是物质的、恒定的。
以制度为核心范畴的新自由主义,也持物质主义本体论。新自由主义以国际制度为研究起点,对现实主义的冲突性国际关系观构成了挑战。但是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又与现实主义保持了一致。因此,新自由主义并未摆脱物质主义的本体论立场。尽管强调制度具有独立解释国际关系变化的作用,也认识到制度是在行为体互动中建构的,但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对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是以物质力量分配为基础的。制度约束了行为体的行为,是介于潜在的权力分配与其结果之间的解释性变量。规范、观念因素被新自由主义者赋予了有限的因果作用。由此可以断定,在新自由制度主义那里,物质力量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制度无非是行为体追求利益的补充因素,其作用在于将秩序稳固化、持久化。
自2008年开始,宁夏每年对全区农民用水户组织和基层水利管理人员进行培训,重点是农民用水户协会负责人及骨干。2008—2013年共举办培训班52期,合计201天,共有7 340多人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相关人员掌握了水费的计算方法,为让农民用上放心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技能。
三、社会建构:理念主义本体论
新现实主义是物质主义本体论的集大成者。新现实主义假定,优胜劣汰的国际政治法则是超越时空的普遍的客观存在,它由先定的结构现实驱动。
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是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基本特征。物质主义本体论认为,无论自然世界还是社会世界都是客观实在的,社会世界不过是自然世界及其规律在人类社会的映射。国际关系客观存在,自然产生,且能被经验证明,它先于且外在于人类的观念。
建构主义所谓的建构不仅仅是一个隐喻(metaphor)。通过社会互动,行为体并非单纯创造了观念、理解或认同,而且也制造了事实、客体以及空间。行为体形成的“什么是应当追求的”、“什么是应当避免的”等观念,决定着国家的真正利益。国际关系、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不过是制度、文化、观念建构的结果,而不是主流学派所说的不可改变。如果国际关系是无可改变的客观实在,无论人类做怎样的努力都无法使之发生丝毫改变,世界不可能变得更美好、更符合人类的伦理价值诉求,这岂非学术的悲哀?人类的悲哀?建构主义认为,主流学派对国家行为的后果作出因果解释,但更为重要的是回答“国家和国际关系是什么?怎么样?”建构主义不仅致力于研究规范本身,而且也关注由规范导出的因果机制。在它看来,国际结构是行为体社会互动的结果;国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行为体;国家认同、共有观念是通过复杂的、相互交织的实践建构起来的,因而是不稳定的、变动的;所谓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客观的、先定的,国际关系之所以会呈现出冲突性的无政府状态,根本上是由国家之间的敌意导致的。国家不是孤立的、单子式的,而是由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观念塑造着国家之间的互动,而社会关系结构建构了行为体的互动规则。因此,只有透过行为体的彼此互动,无政府状态才能获得意义。因而,无政府并不具有确定性含义,也不具有唯一逻辑。通过其社会活动,行为体完全可以改变赋予无政府状态不同的文化和逻辑,将自己从现实主义所谓冲突性的无政府文化中解放出来。
⑤ J. Ann Tickner,Gendering a Discipline: Some Feminist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30 (4), 2005. 而且,制度本身是由组织、机制等实体形式表现的。从本质到形式,制度都具有了物质性特征。
建构主义对传统学派,特别是对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本质所进行的批判,拓展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视野,将研究的注意力从物质结构转向观念结构、社会关系层面。当下,对于规范是国际关系的影响因素这一问题,学者们不再存有争议。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在一定意义上,规范在本体论上是真实的,他们更关心的是规范如何、何时以及因何产生和演变。① Annika Björkdahl, Nor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m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5 (1), 2002. 与此同时,建构主义不仅强调了行为体关于国际社会的理念和知识,而且也关注了其中的物质因素。“探求国际关系知识和权力如何互构,带来知识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互利双赢,确立了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的一席之地。”② Javier Lezaun, Limit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Social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 (3), 2002. 在本体论上,建构主义更接近于反思主义立场,而在认识论上,却很大程度上分享了理性主义视角。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成为一个建构主义者与同时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并不是先验矛盾的。”③ Javier Lezaun, Limiting the Social: Consructivism and Social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 (3), 2002. 对客观秩序和结构观念的认同,以及试图搭建沟通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桥梁,糅合理性主义认识论和反思主义本体论,寻求“调和立场”的努力,使建构主义最终未能在批判现实主义上走得更远。
采用陈从瑾[12]等人的方法,向3.9 mL DPPH溶液(25.6 mg·L-1)中分别加入0.1mL稀释后的荷叶发酵上清液,抗坏血酸作为阳性对照,反应总体积为4.0 mL。在常温、避光条件下反应30 min后,测定其在517 nm处的吸光值A1。每个浓度重复3次,其中抗坏血酸作为阳性对照,蒸馏水做空白对照。DPPH清除率按下式计算。
四、社会性别:女性主义本体论的挑战
建构主义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视角研究国际关系的做法,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女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分享了共同的本体论基石:把政治事实理解为社会建构,赋予观念解释性地位。不过,女性主义的立场绝非仅限于此。女性主义与以理念为本体的建构主义并不能整合到同一本体论名下。对社会关系、变化过程的关注,使女性主义不同于主流学派,而对社会关系中性别要素的倚重又使其与建构主义区别开来。女性主义认为,社会性别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一种没有涵盖社会关系,建基于无政府世界中单子式国家的本体论不可能为人们理解国家关系提供充分的支撑。同样,一种虽然倡导社会关系本体却未能凸显并建基于社会性别的本体论,也不能呈现国际关系的真实图景。与建构主义不同的是,女性主义没有止步于简单的文本批判,而是力图发展出更为详尽、系统的研究计划,强调只有将社会性别引入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之中,才能彻底突破主流本体论的偏狭,形成更为真实、全面、公正的国际关系理论。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百分之百的回答。我通常在拍摄时关闭合焦提示音,但如果有人喜欢在拍摄过程中打开提示音,又不会干扰其他人,那么我认为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社会性别绝非出于学术研究的便宜由学者创设的一个术语,而是人类社会现实的真实呈现。社会性别不仅应该成为分析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且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的构成性(constitutive)因素④ J. Ann Tickner, Gendering a Discipline: Some Feminist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30 (4), 2005. 。社会性别不仅是一种分析工具,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伦理工具。它不仅意图描述、解释国际关系既成的事实,也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结构、制度,以构建一个更加正义且美好的世界。运用社会性别范畴,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的核心假定进行了挑战,并且解构了由主流学派创立、界定的基本范畴。以社会性别为本体论的系统研究正悄然改变着由男性主导、以男性认同为基本特征的国际关系学。
女性主义与主流学派分歧的根本在于二者本体论的差异。女性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依托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传统中深嵌着性别化本① Gillian Youngs,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alations and Gender Mainstream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5, 2008. 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这一性别化本体是用以界定国际关系的特质之一。男人是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主体,而作为男人“他者”的女人则是客体。通过社会实践与意识形态再造,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的观念成为社会化的产物。体。”② [美]伊丽莎白·菩露格:《作为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斗争:改变在家工作的性别规则》, [ 美 ] 温都尔卡·库芭科娃、尼古拉斯·奥鲁夫、保罗·科维特:《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肖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151 页 ;R. Charli Carpenter, Stirring Gender into the Mainstream: Constructivism,Feminism and the Uses of IR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 2003. 这是国际关系学未明言却隐含的本体。在主流学派所谓客观、性别中立的国际关系背后隐藏着被性别化的社会建构。换言之,“女性和性别无论对于国际关系的日常实践还是国际关系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它们却在主流学派的讨论和检视中缺席了。”③ Seema Narain,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 of J. Ann Tickner, Indian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Vol.21 (2), 2014. 主流学者认为,女性主义者假定性别关系与国际关系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主张通过在国际关系议程中添加妇女和妇女问题,以改变世界秩序的冲突性特征,因而是“性别本质主义”的。实际上,这是对女性主义的曲解。女性主义者认为,男人和女人的行为特征是由社会实践、社会结构建构的,是观念意义的,与二者的生物特征并无多大关联,不存在所谓男性或女性的本质属性。所谓“男人进攻,女人和平”只是社会共有的观念,而不是性别的本质。
主流学派“建立在国家间关系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它将国家视为行动于自利国际环境中的统一理性行为体,而女性主义理论却是社会学的,它源自社会关系尤其是性别关系的本体论,这种关系始于嵌入整个社会等级结构之中的个人层面”④ J. Ann Tickner, Feminist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eace Review, March 2004. ,这导致二者对性别和权力问题有不同的认知。在性别认同问题上,主流学派认为,性别对于国际关系而言是无关紧要的、边缘化的,性别身份处于权力政治之外;女性主义则认为,身份特别是性别身份应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议题,国际关系是由具有性别身份的人、性别化的社会实践活动造就的。在权力概念上,主流学派认为,权力是国家的一种物质特性,只有量的变化;女性主义则认为,权力是一种社会建构,而性别则是权力的符码。特别是物质主义以物质本质界定国际关系,把国际关系简单地理解为国家之间的权力较量,其中包含着以力量为基本特征的男性气质认同。这种男性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并最终导致了其对权力的尊崇。就本体论而言,女性主义总体上趋向于理念主义,强调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情境下妇女经验予以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经验对于知识、性别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建构具有基础性地位。主流学派之所以呈现出男性特征,国际关系之所以被权力政治所主导,其根本症结在于,国际关系是建基于男性经验的,主流学派是以男性视角和理性选择模式建构的,女性及其经验完全被排除在外。
本体论分歧导致了女性主义与主流学派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主流学派致力于解释国家行为及其后果,女性主义则由“解放目标”驱动——研究在国家、国际机制、国际结构中被漠视、抹杀、剔除的女性及其经验,并力图改变这一状况。只有根植于个体生活的理论才能起到解放的作用。女性主义以边缘化的、长期被忽略的个人日常生活为研究起点,采用自下而上的路径,将妇女的日常生活经验与国家,以至全球层面的政治、经济权力的构成与运作联系起来,关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对性别不平等关系的影响,以及性别不平等如何支撑这些结构等问题。女性主义者力求展示并证明社会性别是国际关系一个无所不在的本质特征(a pervasive feature),① J. Ann Tickner, Gendering a Discipline: Some Feminist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30 (4), 2005. 它对于揭示国际关系事实所蕴含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至关重要。世界政治中弥漫着性政治。只有将女性经验作为理论原点才能达成更为真实的知识。② Aram Ziai, Post-Positivist Metatheory And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arison Of Neo-Gramscian, Feminist And Post-Structuralist Approaches, Hamburg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 Vol.5, 2010. 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社会性别就是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所有层次政治安排的实践的结果。
本体论分歧进一步导致女性主义采用了根本不同于主流学派的认识论,并据此形成了独特的分析方法,进而形成了女性主义独特的方法论。方法论的标准是多元的,存在着国际关系研究的女性主义路径”(feminist way)。不仅对于何为事实的本质或知识的客体,女性主义与主流学派存在根本的分歧,就连什么是知识这个问题上二者也有不同的认知。女性主义知识的建构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an ongoing process)。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更倾向于使用视角(perspective)而不是方法论意指正在进行的女性主义研究计划。这一研究计划的目标是“在女性不同的经验基础上重新思考传统知识”③ Seema Narain,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 of J. Ann Tickner , Indian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Vol.21 (2), 2014. 。女性主义知识就是要建立对传统学科的女性主义批判,并搭建起全新的学科框架。国际关系研究的题材不再是单纯的客观实在,“写作、分析与调查工作再也不是什么科学实证项目,而是一种文化实践”,是处于特定情境中的研究者讲述的故事。④ [英]玛丽西亚·扎尔维斯基:《分心的反思:国际关系领域女性主义知识的生产、叙述与拒绝》,[ 美 ] 布鲁克·A·艾克里,[ 瑞典 ] 玛丽娅·斯特恩,[ 新西兰 ] 杰奎·特鲁:《国际关系女性主义方法论》,金铭译,中译出版社,2016 年,第39 页。 通过倾听女性并理解与其生活经历紧密相关的主体间意义,女性主义研究成为一个强调社会内化意义存在广泛差异的辩证过程。女性主义寻求理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性别等级制,及其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决定性影响,并致力于改变这种性别等级制。显然,女性主义视角的引入为国际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课题,也拓展了人们的研究思路。
结 语
女性主义本体论聚焦社会性别,力图发现国际关系中的性别关系及其社会建构成因,运用性别分析方法形成对主流学派的全面挑战。首先,它解构了主流学派的立论基础,在物质本体之外,添加了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性别要素;其次,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范围,弥补了主流视角的偏狭;再次,它不囿于对主流本体的理论挑战,还形成了对实践中主流本体性别特征和性别认同的有力批判;最后,它致力于以社会性别本体建构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形成完全的、自主的女性主义理论。
2) 局部现浇混凝土的墩柱,混凝土的黏结作用效果明显,墩柱的抗侧力及耗能能力明显提升,加入耗能钢筋后,墩柱的性能再次提升.带耗能钢筋的局部现浇墩柱性能明显优于其他3个墩柱,后期应深入研究,使其在实际工程中可以得到应用.
今天,女性主义学派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仍处于边缘地位,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旅程(an unfinished journey)。女性主义的声音不仅没有引起主流学派的足够重视,反而因其自身理论建构能力的不足而遭受诸多质疑。未来,凸显社会关系因素特别是社会性别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社会性别为核心范畴,构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本体论,进而形成独特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出有别于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开拓出别样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知识,应当成为女性主义从批判主流走向知识系统建构的有效路径。
宝宝是父母的心头肉,时时牵挂、疼爱有加。宝宝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或者小伤小病,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恨不得病生在自己身上。有时一场疾病之后,宝宝瘦了,父母也累坏了。许多宝宝大病一场之后,连性格也发生了转变。
作者简介 | 苏云婷(1 9 7 5- ),大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赵薇(1994-),大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大连 116028)
* 本文系2012年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全球治理结构:当代国际机制的生成机理研究” (2012M510817)、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公共应急管理:一种女性主义视角”(201508210028)、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女性主义世界秩序理论研究”(10YJCGJW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编:俞 平)
标签:本体论论文; 物质主义论文; 理念主义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大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