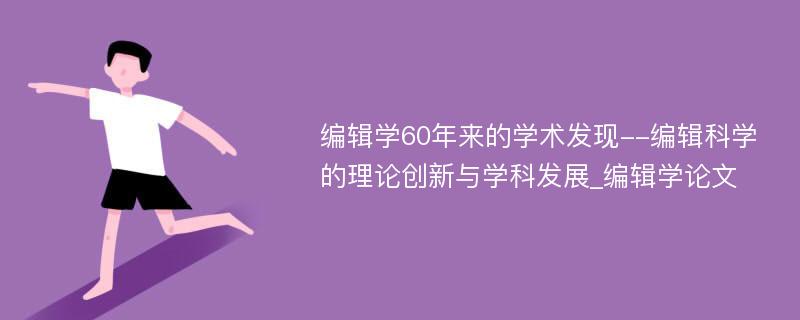
编辑学研究60年的学术发现——编辑学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论文,学科论文,学术论文,理论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 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0)01-0108-07
富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研究,从历史上第一本《编辑学》著作出版,至今已整整60年了。但随着中国的社会革命、共和国建立、抗美援朝战争、经济建设的发展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翻天覆地的演变和30年的改革开放,直到1980年代,编辑学研究才得到长足发展并日益成熟。美国的《克利弗兰旗帜日报》曾在1990年12月针对当时中国的编辑学研究盛况报道:“我想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近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编辑学。”[1]此时,中国的编辑学研究已同日本、韩国等一些国际出版界人士联手协作,共襄编辑出版等媒介产业。在这曲折漫长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编辑学研究都发现了什么呢?这里仅从编辑学学术理论方面的一些研究发现,说明编辑学已经发展成长为一门不可轻视、不可替代的社会人文科学。
一、发现了编辑学的专业普遍性与媒介贯通性
世界上编辑学研究的第一本书,出自1949年中国的广州,一个常开现代风气之先的城市。是广州自由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当时广东国民大学新闻学系的一套丛书,其中一本是李次民教授著的《编辑学》。既然是新闻学系的丛书之一,这本书为什么不带“新闻”二字,而独标“编辑学”三字作为书名呢?我请李玉莲博士从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复印了此书。研究发现:1)本书共22章,虽然用19章的篇幅大量讲述新闻纸的编辑知识和方法,但同时又特设3个专章,分别讲述杂志编辑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方法,以及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特征和艺术方法。其内容显然突破了新闻纸编辑的范围;2)这本《编辑学》的“目录”之前,加了当时5个新闻学家与教育学家的5篇序言,认为该书虽出自新闻编辑实践,但其学理专攻编辑,与单纯的新闻学著作有所不同。罗香林序中讲,李教授“著编辑学二十二章,不先著新闻学,而殷殷以编辑学为务者,以报章良否,其先决条件系乎主编者学养与编辑艺术也。……而专为此门著作,则以次民此书为创举”。鲁豫东序中讲:“我一向把编辑工作看做一种组织的艺术。一张报纸的销路好不好,读者也许一时还无法探听出来;可是它的版面好看不好看?内容充实不充实?读者可就不难加以分辨。从而,这就首先得归咎于编辑工作做得好不好?——再伸言之,就办报纸,或者编其他书刊,也都如此,没有什么例外。”“尤其是编辑学,能够像李先生这本书那样,广泛地从新闻学、新闻纸,一直说到杂志,精细地包括了全般的编辑理论和技术,并加以透彻地阐释的,据我所知,这似乎还是第一本。”[2]9这里引述的序言已公然表明,编辑活动远非是局限于新闻业之内的一种辅助性职业,而是贯通于报纸、杂志,乃至“其他书刊”的文化事业!作者李次民教授还在自序中引述革命的新闻学工作者萨空了在《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中的话:“编辑新闻,决不是任何知识分子都能胜任的。”[2]11从而说明,报纸编辑家不仅要有新闻家的学问,还要有编辑家特有的学问,包括普遍通用于书刊等各种不同媒介的编辑学的理论知识、经验方法和智慧技能。这本书第一次发现了“编辑活动”存在于报纸之外的书刊等其他媒体,有一定的普遍性。
1954年,苏联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К.И.倍林斯基的“ПРОΓРАММА ПО КУРСУ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5年请倍林斯基教授来华讲授“书刊编辑课程”,并将他的这个教学大纲翻译成中文,于1956年8月出版。该书封面注明:“供国立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专业用”。“大纲”名称КУРСУ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Я,本意是编辑教程课程或学程,这里直接翻译为“编辑学”,成了一个学科术语,带有专门的学问、学术、学理等含义。不过“大纲”内容中,确有地方谈到,这是“以出版社的经验为基础的一门科学”,是关于“书籍和杂志的主要创造过程的一套原理”。《大纲》还特别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编辑活动”,并将俄苏历史上经典作家的“编辑活动”与其政治活动、科学活动等同等看待。还研究了“俄罗斯古典文学家们的编辑活动经验及其对苏联编辑人员的教养意义。”《大纲》的“第二部分”即“书刊编辑总论”,概括地研究了俄国的编辑出版史,列举了许多经典著作的编辑范例,并论述了“编辑职业的产生与苏维埃新型编辑事业的发展”。大纲的“第三部分”是“书刊编辑分论”。分别讲述政治书籍、通俗科学书籍、技术书籍、工业书籍、农业书籍、教材、工具书、学术书籍、文艺书籍等8大类书籍的编辑方法和具体编辑业务。①
应该说,编辑学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把报纸、期刊、图书3种传统的纸质印刷媒体贯通起来,显示出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普遍性。同时,也与古代图书的编辑出版历史连接起来,致使这个新兴的编辑学表现出其多种媒体的空间延展特性和时间传承特性。正是人类在其文化史中长期不断地从事编辑活动,逐渐积累起创造各种传播媒介的实践经验,才孕育成我们称之谓“编辑学”的科学理论的雏形。不过,正如李次民的《编辑学》尚未摆脱报业社团新闻学的蛋壳一样,倍林斯基的《书刊编辑学大纲》也未脱出版社机构内部的职业编辑的窠臼。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的新闻学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摆脱传统的报纸新闻学的狭小框架,拓展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并与美利坚国内国际政治、复杂社会环境、实验心理学、实用教育学、信息的传播与控制技术等现代学科结合起来。于1949年伊利亚诺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威尔伯·施拉姆主编的《大众传播学》。在充沛的学术基金和自由学术研究的氛围下,“传播学”研究广泛推进,迅速发展;学派林立但又协同合作,很快成为一门世界性显学。而中国的编辑学研究只能在阶级斗争之缝隙中零星地进行。唯日本和德国,二战以后因其文化深受美国军政统治之束缚,曾在1946-1948年间发动过争取媒介“编辑权”的运动,后来,出版商们得到了一定的出版主权。日本、德国都制定了一些保护自己出版权的法规,但对编辑的文化内容创新这个学理问题未能深入研究。日本在1969年成立了“出版学会”,专门研究出版物的编辑、印刷、复制和经营销售问题。对编辑学的理论研究虽然进展不大,但也公认编辑活动是贯通于各种新老媒体中的对文化内容的分类整合与编次排序,显示出版物的科学思想水准、文化整体倾向与编辑灌注于不同媒体的社会政治态度。这正好也是编辑学的专业普遍性之所在。
编辑学贯通于各种传播媒体的专业普遍性,是不是被公认,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过去,人们没有潜心研究编辑学,就认识不到早已存在于各种出版物中的编辑学理的普遍性。反而往往认为,编辑活动是一种潜隐性的、附属性的、被雇佣的文字加工修饰等琐事,编辑者不过是为人作嫁的丫头仆人。至多不过是隐匿于某一出版媒体的谋生性职业活动。像抄书匠、校对工、看门人做的那种糊口生活一样,根本提不到什么“学”与“理”的层面。旧时代的编辑人,不过是一种文化仆役,是识字、抄字、改错字的仆人而已。到了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传统出版业与新兴的电子媒介业发展迅猛,编辑学研究之风大兴。这时,中国编辑学的研究中心转到了北京。编辑有学无学之辩,不仅新闻界、出版界、科技界在讨论,教育界也在讨论。这种盛况直接导致了中央领导同志对教育部复函,同意在几所重点大学试办编辑学专业。此时这个专业已与30年前仅仅在新闻系设置的课程大不相同。它不再是新闻学的一部分,也不仅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而是相对独立的编辑学专业,普通的编辑学学科。尽管它的学科体系还不成熟、不完整,暂时还不得不设置在新闻系、中文系或其他系科,但其发展势头很猛,科技编辑学、文艺编辑学、影视编辑学、新闻编辑学、各种软件编辑学与普通的理论编辑学也相继问世。如几本不同的《编辑学概论》《编辑学基本原理与方法》《编辑学通论》以及《编辑学原理论》等几十种著作纷纷出版,深入而广泛地研究编辑学的学理与贯通于各种新老媒介中的编辑方法、专业技能。在近30年的历程中,中国设置编辑学与出版学等学科的大学已达80多所。有些大学还培养了不少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在同西方传播学的交流过程中,作为普通编辑学的专业发展与学科建设,显然越来越成熟。目前,中国编辑学会正在组织编写一部《普通编辑学》著作,力求科学地论述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的理论创新成果。编辑学的专业普遍性、通适性及其在各种传播媒介中的贯通性、横断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和认知。
二、发现了编辑活动的主体和主体性
有关编辑活动的研究,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因为中国的文字发明很早。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并形成体系,用以系统地记载复杂的事物、史实和思想感情,至少有5 000年的文明史可资证明。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册典是世人已知的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化媒体,距今已有3 000多年历史。甲骨文献中就有关于编辑活动的记载。甲骨版面的编辑规范和艺术水平令世人惊奇、敬佩。②古代所谓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应该都是当时各种传播媒体的一些储藏方式。春秋时代有些诸侯国的史官、巫师还能查阅、讲述或诵读。到春秋时期,老子、孔子等诸子用文字载体著书立说,重新整理编纂三代遗存的典籍,特别是老子的《道》《德》二经和孔子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或称“大六艺”),形成一种媒体结构系统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民族建立大国体制的主流文化传统。秦相吕不韦,聚养学士,编纂并校雠《吕氏春秋》,是一桩巨大的系统编书工程,也是一次较大的媒体创构活动。汉朝设置专门编校图书的国家机构,任命刘向、刘歆等负责搜集整理古书,研究各家学派的经典版本与诸子百家著作,并校雠抄录行世。造成庞大的经、史、子、集等图书结构。经过唐宋大规模编辑丛书、类书、教材、工具书,使用抄写与刻版印刷技术广为传播,中国的编辑活动开始形成一种文化职业活动,直至明清时期,编书业依然繁盛。其规模之大,令世界惊讶。但是编辑活动的主体,众多的编修官、校雠者、抄书人、刻印工,却被位高权重的封建帝王隐压在显赫的钦定书籍背后,至多署上领衔编修官的姓名。至于寺院僧道编译抄写刻印的佛经道藏类图书与儒家书院学者抄写刊印的经史子集一类书籍,由于多为后学讲解研究之用,才署上藏书家、纂集家或编辑者之名,乃至署上地方乡绅出资者或书商的姓名,以显其文化传播之功德。自从孔子编“六经”,托述古圣先王之所作,自标“述而不作”,到后来人们看出书籍这类媒介不仅原创作者有“作意”,而且编述者还增入自己的“编意”,显示出编者的认识态度和思想倾向。但在中国相当长的封建专制时代,作者也是不被重视的,许多书籍没有作者署名,或托名古人创作。唐宋以后,文人自编或亲朋好友代编诗文集与传记之风兴起,刊刻出版者看到书市有利可图,才渐渐将作者或编者署名于书前或书后,广而告之读者,以期多售获利。明清出现的民间坊刻书籍则多为供大众阅读的小说稗史、戏曲唱本、小型历书之类,主要为出版商控制,并不看重编辑者的地位。
随着近代报刊媒体的出现,出版的商业化得到空前发展。新的出版机构往往以巨商大贾为老板,出版商几乎决定了一切出版物的命运。编辑完全成为老板的雇佣,谈不上什么编辑活动的主体。出版商将古代经典的神圣光环销蚀殆尽。
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虽多通过兴建教堂礼拜仪式传播“圣经”,也大力兴办“英华书院”之类教会机构,编书、编报、编刊,广泛发行于众,编者往往以“代圣立言”的牧师或教徒身份从事编辑出版活动。一点也不改变《圣经》神创,或者神与人签订媒介“契约”的观念。不论签订的是《旧约》还是《新约》,其实都是人写、人编,供人阅读的媒介物。但就是不把编辑传播的主体标出姓名。
19世纪的书、报、刊,已署上作者姓名,以支付稿酬取得版权之法,推出“名人”效应,借以做广告,牟取商业利益。但仍将编辑人隐伏于出版物之后,以剥夺编辑权之法节省掉这一精神劳动成本。旧式的出版机构,常以局、社、会、馆、所等名称,把编辑校雠工作放在印刷厂内作为印务的一个工序看待,支付编校、抄手、印工一类的微薄工资。编辑者并无人权或人格地位可言,更不要说独立的“编辑主体”了。
20世纪中期以来,经过60年的编辑学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编辑学”成为支撑包括传统出版业和现代广电影视网络屏幕多种媒介产业的一门科学,在深刻而广泛的学术研究与专业讨论中,真正发现了编辑活动的主体,——具有独立人格而又不仅是附属职业的媒介建构主体。他们的专业资格是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和编审,如同大学里的教师资格称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一样,也如同作家记者那样,分为初、中、高等不同级别的专业资质与人格地位。在出版物与影视作品的版权记录中,正正经经地署上了编辑者的姓名与职称,以示其在媒体构造与传播中所担负的社会文化责任。“编辑工作者”能够自豪地对社会公众说“我是编辑”了,不再只是单单“为人作嫁”的文仆,一生注定的“无名”之辈。俨然也成了一种缔造文化的主人。特别是“编审”这种名称本身就意味着“编辑审定”者的主体地位和人格价值。
编辑学研究,不仅发现了几千年来未被人们发现或被旧制度掩盖隐匿下来的编辑主体,而且发现了编辑的主体性。编辑的主体性,指的不仅是编辑与其缔结构造而成的文化媒介客体相对而言的主客关系,而且更深刻地指明编辑主体与其对象主体,包括原创、编剧、导演、演出、歌唱、放送者等主体和阅读、观赏、聆听、评论等主体之间的交互传承与创新关系。编辑的主体性,更主要的是指编辑在与其他主体的协作互动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交互主体性。这种交互主体性与其个性之间是差异的对立与和谐的统一,呈现于编辑主体之间的整体性。主体性主要通过个性与个性的精神交往和互动创意,协同进入到创造性的文化实践,从而积极综合多方面的力量和元素,缔结构成统一主体性的整个活动“场”。③编辑主体性的发现,使得编辑活动主体从此不必再隐匿于媒介客体之中,编辑主体也不再深深地被隐匿于作者主体或读者主体之中。编辑的社会人格本性与社会权益也不应再潜隐藏匿于上帝圣胞或父母膝下去讨求生活,而成为独立于世的社会文化人之一格。在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正蓬勃生存着的独立编辑机构、编辑专业和编辑人,正是编辑主体性的新生态的呈现和证明。
三、发现了编辑活动的“主体间性”特征,找到了编辑科学的学理
60年来的编辑学研究发现,编辑主体在架构文化媒介的活动中,其主体性往往并不表现为单一的、孤立的个体独创性,而是与创作主体、复制主体、阅读主体等交互启发、协力推动的组合性创构。其创构的成果,也是具有共生性和交互性的媒介。无论是东方的唯物辩证法还是西方的唯物辩证法,无论是古代的共处相生哲理还是现代的间相交互哲理,都能逻辑地证明,编辑主体在其从事的创构文化媒介活动中,都充溢着、发散着一种被称为“主体间性”或“交互协同性”的差异互补或矛盾统一的文化哲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吸收全世界各种优秀的哲学传统之精华酿造而成的科学哲理。它的现代哲理形态、概念术语和新创的关键词,是其基本原理和核心精神的科学发展的表现。东方的实践论、矛盾论、科学发展观与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哲理的现代发展。西方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论,文本交互与文本对话论,以及传播媒介多声部交响论等,也是马克思主义哲理的现代发展。并且在各自不同的“语境”下,在不同的叙述形式与逻辑论证中,两种语言思维得以相互对译,实现意识交流,逐步取得共识和理解。这是具有国际人本意义的理性共识与感性“通觉”。“编辑学”的学术研究发现并认识了这一点,无疑就找到了人们所从事的编辑活动的科学学理。因为它告诉我们:人作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在其编辑、阅读、创作等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一方面既充满着个性创造精神,同时又洋溢着互性、联动精神,整个看来,就是一个协作过程。无论是在生产、交往、生活活动中,还是在信息传播、知识启蒙与智能创新等文化活动中。主体的个性与互性都是共同存在,交相发生与协同发展的。所以中国学者历来把编辑之学视为“通力协作之学”(陈望道语)。编辑主体创造媒介的过程,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作者主体、阅读主体交互创造于一个共通的时空场境之中。那是一个搜集、审核多种文化元件,设计特定的媒介蓝图,并把许多稿件加以琢磨,组合安装成一种媒介结构整体的综合性创造,其结果就是流传于某个时空中的媒介载体。如古代孔子编的“六经”,中世纪中国形成的“四库”等。编辑构造的成果是媒介结构整体,而不仅是一种种的“文本”,一期期的报刊,一档档的节目,一盘盘的电影拷贝,一张张的影视光碟,或一屏屏的网络视频、音频等,而是一连串的媒体结构。只有整体结构及其涵蕴的思想意识、历史内容与理想信念等才是人文相化的共同的文化本质,才是社会的软实力。因此,人们创造媒介,实质上就是创造性的缔结构造人类共创共享的媒介成果或文化力量。西方世界常用framing一词来表述这种创构文化媒介的编辑活动。港台有人用“框架”、“架构”、“构造”、“组织”、“结构”等词汇来译解这种编辑行为。用于诸如“新闻架构”、“故事框架”、“理论建构”、“媒介构造”等等。我曾用中国古代现成的“缔构”一词,突出“缔结”和“构造”的意思,说明编辑的创造性,主要不在于独自的原始创造,或元件性的创造,而在于综合组织、装配构成整体结构的创造。就像缔造一支军队,形成战斗力量一样,又像构建一栋大厦一样,造成一个空间,形成一种实用功能。这样似乎更符合编辑创构媒介的本质特性,例如把电影媒介所需要的诸多元素,如人物、故事、画面、色彩、音响、歌舞等等镜头,通过蒙太奇等各种剪接方法,构成一部完整的艺术影片。甚至将许多影片分类排序,组织构成一场大型的电影节。突出的是缔结和构造。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在2006年出版的《传播与社会学刊》卷首的“编辑方针”说到:“西方传播学累积的实证资料已经不少,相对欠缺的反而是理论建构、深度分析和有创意的整合。”例如报纸的“新闻价值”就是通过编辑和记者等新闻主体“组织新闻资讯,制作新闻报道,构成报纸版面,掌握社会议题与舆论话语的架构向度”。因而强调我们的编辑学要突破地区性研究、行业性研究、分支的个案研究或类型性研究和“量化”分析的方法,关注“质化”的本体论研究方法,达到一种合乎逻辑的学理高度,以期获取一定的媒介架构效果。在推动一门科学发展的同时,也发展了这门科学,使编辑学提升到普遍通用于各种新老传播媒体的基础理论学科的高度。
四、发现了编辑活动早于出版活动、大于出版活动
2006年春天,中国编辑学会的老会长刘杲同志在《中国编辑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编辑活动的范围大于出版活动的范围,编辑活动的发生早于出版活动的发生。”这是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中的一个重大发现。其重要意义在于:这个观点不再把编辑学研究辖置于出版业范围之内,也不再把编辑学研究截断于出版业之后。而是把编辑学研究置身于文字、图像、音乐等符号文化的产生、发展与未来的全部历史过程之中。使编辑学研究与整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媒介技术学等贯通起来、链接起来,向着作为一种基础学科——普通编辑学的理论方向挺进。这对编辑学学理和方法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把编辑学提升到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高度,促进了编辑学理论体系及其整个学科体系的建构。这个讲话曾被《中国出版》和《河南大学学报》全文刊登并被作者收集在他的第三部编辑出版学著作《出版笔记》一书中。尽管出版界一些人囿于当前出版社体制内的职业编辑观对这一普通编辑学的大编辑观持有不同看法,但随着编辑活动在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从出版职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越来越走向广泛开放的文化产业,走向各种文化客体的对象化观照,走向传媒系统的集团式建构和世界文化市场的辽阔蓝海,编辑学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就与时俱进。到了2008年5月,新一届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凤同志又继而提出“大编辑、大媒介、大文化”的口号,意谓:大编辑构建大媒体,大媒体传播大文化,大文化铸就大编辑的旋转式连环上升的学说观点或传媒思想理念。2009年中国编辑学会第14届学术年会以“编辑与文化”为中心议题,讨论了中国编辑如何担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当代先进文化力量如何铸就新型编辑人才的重大课题。研讨会上,学理与方术并驾,编辑与文化齐驱。而关键是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介该如何又好又快又多地建构。以当前网络数字化技术编辑为例,无论是网络新闻界面的编辑、网络期刊的编辑,还是网络维基百科的编辑,多种多样的网络视频、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的编辑,不仅呈现出无量讯息的“云技术”调控趋势,而且促进编辑者、创作者、阅读者、传播者、使用者更多主体角色的快速转换与高度的互补互动特征。当然传统的文本出版业仍然会被预留下自己的发展空间。但虚拟的赛博空间总是要同真正的现实世界相结合,共同进入未来的文化胜境——统一的世界文化活动场。
五、发现了编辑建构的“媒介间性”特征
60年来的中国编辑学研究,不仅发现了编辑主体是在同创作主体、阅读主体乃至出版商主体的多向交互过程中创构媒介的,而且以编辑活动为中心创构出来的媒介载体是多种多样的,相互补充、相互推动的。不仅是手工刻、写,机械印刷的传统版媒介有互补互动的特征,而且以光电动力数字技术操控的影视、网络、手机荧屏媒介也同样具有互补互动的特征。传统的甲骨、金石、竹木简牍和纸质印刷媒体与现代的光电映像视频屏幕媒介之间,更广泛地存在着互补互动的规律性特征。我们的许多编辑学研究论文都或深或广地论述过这个特征,并视之为媒介发展的一条定律。西方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曾从历史上分析过各种传媒的演变,提出要从媒介的互补互动性方面去理解和支持文化媒介的发展。欧洲现代哲学社会学和传播学家也曾在他们的研究中创造了Intersubjectivity与Intertextuaility两个术语,并成为学术性的关键词。我们的翻译者将这两个关键词分别译为“主体间性”与“文本间性”,猛然看起来,甚为生涩,慢慢才咀嚼出它的意味,说的不过就是人们创造精神文化的媒介载体时,不是单一主题独创的,而是众多主体交互参与共同协作创造的。他们创造出来的多种多样的媒介成果,例如一本书与一本书之间、一种报纸与一种报纸之间、一种期刊与一种期刊之间,都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互相传承、互相交流、相互推动、协同发展的间谍性与兼有性特性。汉语译为“文本间性”并不十分贴切,带有不少“文字版本”难以包容、难以涵盖的缺憾。因而有人译为“互文性”,即不同文本中交互兼容的对话性、互参性。这是翻译界的问题,我们且不多讲。只说我们编辑学研究的既是创构大媒介(包括出版物、影视物、网络与手机荧屏显示物等)、传播大文化的课题,就理应创造一个新的学术术语“媒介间性”或“媒体交互性”,其英文形式可以相应的书写为Intermediality,并作为普通编辑学的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我们对“媒介”这个麦克卢汉式的命题的理解,及其规律性的阐发。由此导致出我们对于编辑学的认识已经达到的高度。
编辑活动是以编辑为中心枢纽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活动。由编辑主体创意策划并协同创作、阅读等构造媒介的过程,如同启动出版、影视、网络等传媒业殿堂的旋转门,迎接着著作主体和阅读主体不断地进进出出,转换生成各种文化媒介。造成人文相化、共创共享的媒介结构空间,即文化传承与交互传播的公共空间。
作者、编者与读者众多主体的文化交互,叠加累积着媒介载体,增生提升着媒介价值,缔结构造着层出不穷的媒介载体。在不断解构老媒介、缔构新媒介的交互过程中,新媒介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吸收着并消化着老媒介中“味道鲜美的肉”,形成日新又日新的文化内容。在“逝者如斯”的人文传播历史中,图书、报纸、期刊诸版本,广播节目、电影银幕、电视、网络频道与手机荧屏等各种媒介载体,无不突出显示着应该称之为“媒体间性”的多重交互性特征。于是,我们不得不新创一个英文形式的关键词Intermediality,以使中国的编辑学研究与国际上科学哲理层面的学术研究接轨,能从更高的科学理论视角考察和认识目前世界面临文化媒介产业的理念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现代化进程,推动各国和国际的文化大繁荣。
六、发现了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链及其与新闻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技术控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初步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编辑媒介学学科体系
编辑媒介学的原来提法是“编辑出版学”,最早由苏联专家К.И.倍林斯基在1954年提出的“编辑出版专业”翻译而来。那时,电子媒介尚未形成世界性传播媒体,出版媒体还独立称霸于世。所以1987年由伍杰主持编辑出版的《编辑教学丛书》中,第一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叶再生先生撰写了一本《编辑出版学概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后来,我国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设置相关的专业学科目录时,采用了“编辑出版学”这个名称。但在长期的特别是最近20年对编辑学的深入研究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编辑学与出版学是一个传统的、基础的学科链条,是编辑学所专注的科学思想文化内容与出版学所专注的媒介复制技术、市场营销模式紧密邻接的两个相互推动、协同发展的学科群。在编辑学学科之下,有图书编辑学、报纸编辑学、期刊编辑学、辞书编辑学、影视编辑学、音乐编辑学、美术编辑学、网络编辑学等等,还有编辑思维学、新闻编辑学、科技编辑学、文艺编辑学、档案编辑学以及校雠学、版本学、目录学、插图学等等。在出版学学科之下,则有手抄出版学、刊刻出版学、印刷出版学、出版营销学、出版市场学、出版计量统计学乃至出版核算、纸张开本、印刷工艺、发行广告之学等等。两个学科之下又各有一个分支的专业学科群。
编辑出版学发展到现在,已远远突破了传统的出版媒体。现代新型的光电传播媒体,近20年间层出不穷,传媒介质已由原来的天然物质经过人工或机械加工而成的版面、纸面等,演变为完全由高科技手段创造生成的银幕映像,磁带、光盘、网络声频、视频及其屏幕等纯然人造物所取代。现代的电子激光编辑排版技术也取代了手工划版铅盘排字,成为全新的数字化程序操作。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链,在实践中已演变为更多更大的编辑传播媒介学。这个学科同既有的新闻学、传播学、教育学等一级学科相比,已足构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在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编辑媒介学也足以构成一门训练现代人的基本素质和文化教养的一门基础性学科。事实上,现在的小学生已在教师指导下,学习编辑墙报、黑板报和纸质小报并排演文娱节目、绘制图片集等等初级的编辑技能了。中学生、大学生一般也学习并掌握了一定的编辑知识和媒介传播技能,办报纸、广播、编节目,乃至在网络上编刊物、作图像或发表论文、传播新闻、音乐视频,参与维基百科的编创和阅读等等。编辑学的知识技能和文化智慧常常是他们喜欢学习的内容之一。如同学习语言媒介、文字媒介一样,编辑媒介学也是人们毕生需要不断学习、提高、加强、精益求精的一种学问,尤其是在今天的数字化网络时代,其先进者,则应当被专门培养教育成编辑媒介学的专业高端人才,以便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媒介文化软实力。
注释:
①倍林斯基:《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②参见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修订版)》,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
③参见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修订版)》,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
标签:编辑学论文; 网络新闻论文; 新闻专业论文; 媒介策划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论文; 文化论文; 主体性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