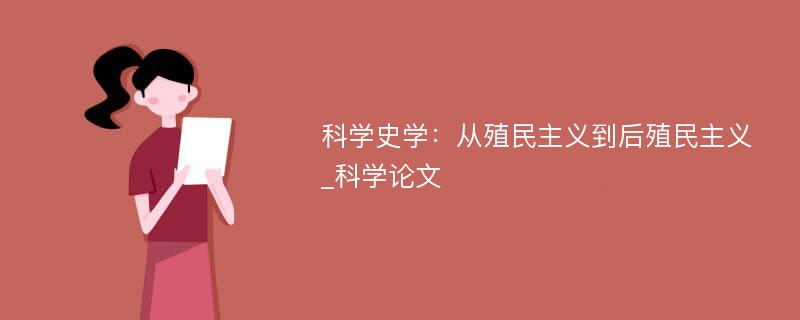
科学编史学: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史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3)01-0022-07
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看,西方科学史应分为两个时期。①第一时期,从9世纪到16世纪,在欧洲与中东围绕着地中海地理空间所进行的科学培育时期,通常称为“古典科学”时期。这是近代世界科学的直接先驱。与这一时期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各种传统科学,如中国、日本、印度这些地方的传统知识,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现代西方科学的诞生与发展同样作出过贡献。第二个时期就是“近现代科学”时期,从16世纪至今,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建立,导致了各式各样研究领域出现,它们都带有各自某些独特的研究主线、论题、目标与争论,并上升为独具西方特色的哲学。这一时期,科学被符号化为这样的名字,如伽利略、培根、牛顿,还有那一时代的伟大哲学家,如笛卡尔、康德与孔德。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的是西方科学向边缘地带的传播,作为西方帝国通过地理扩张带到其开拓地的礼物之一,构成“文明使者”话语的组成部分。二战后,这种传播论带上了“全球化”的特征,即科学研究及其机构被全球化了,它研究的主题几乎都由大规模的工业化、财政手段与“大科学技术”(如核与粒子物理学、天文学、分子生物学等)所引导。科学知识围绕着全球化在拓展,对日常生活与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何从方法论视角思考第二时期的科学传播史,构成了本文讨论的主题。
一、科学的殖民主义传播模型
直到20世纪中期,科学史与殖民主义史分属于不同领域。帝国主义的历史是政治史、军事征服史、管理与贸易史。受英美传统分析哲学的影响,自西方科学哲学诞生以来,只关注科学活动的产品,特别是科学理论,关注一般的科学方法的问题,如证实与解释的本性等。科学哲学的一般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概念分析,时常伴随着在形式语言、符号逻辑中的方法与理论的重构。与此相应,科学史大部分是认知史,关注科学理论本身的逻辑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帝国的终结”与去殖民化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把科学视为反思的对象,探索欧洲殖民主义强权如何利用科学去达到经济上的优势与政治上的控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对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史传统,科学史家日益表现出政治与知识上的不满,转向了科学的社会史研究。②人们开始考察科学的传播与欧洲殖民地扩张的关系史,科学史家巴萨拉(Basalla,1967)、麦克洛德(MacLeod,1987)与阿达斯(Michael Adas, 1989)确立了殖民地场所中西方技科学(Technoscience)传播、适应与运用的理论基础,把西方科学置于欧洲成功扩张以及随后的全球殖民化的中心。其中最为著名的工作当数美国历史学家乔治·巴萨拉(GeorgeBasalla)的经典论文《西方科学的传播》,这是科学知识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说明,它描述了近代科学如何进入非欧洲世界的途径。巴萨拉模型的三条曲线,暗示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科学发展,在本质上追随着一个包括三个相继阶段的进步模型,这个模型被视为西方科学价值的地方性传播范式。第一阶段是一个“科学探险”过程(由具有科学素质的旅行家进行),它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产生出依赖于宗主国的“殖民地科学”;第二阶段是一个青春期,随着西方探险的地理大发现,一系列西方科学被传播进入殖民地或边缘国家;第三阶段是跟随而来的成熟期,在这个阶段,殖民地国家或地区完成了自己的“7项任务”,包括“克服”地方性的“哲学与宗教信念”(如五四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等)后,西方科学逐渐取代了地方性知识,科学传播的各种“独立”机构(如本地人主持的各种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与管理机构)相继确立,输入欧洲技术,相应的欧洲意义上的“科学的”社会模式最终得以形成。科学联系着国家,一种科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与国家的自主性的内在关联涌现出来:一个独立的国家必须有其自己的科学,但其语言要适合于西方世界的探索性范式,西方世界的“科学殖民化”就此形成。巴萨拉的理论反映出一种科学的殖民主义扩张史:随着科学的向外传播,“‘文明的使命’所做的不过就是:让‘母亲之国’在其传播所到之处不断诞生出相同的婴儿”③。
巴萨拉的“三阶段模型”深深地根植于罗斯托的(W.W.Rostow)经济增长的阶段理论。在1960年,罗斯托在其《非共产主义宣言》中描述了经济增长的五阶段论,这是一部关于现代化理论的经典。罗斯托强调科学技术在达到“从传统社会起飞”目标的过程中的重要性。7年以后,巴萨拉扩展了这种传播论,提供了西方科学与机构从中心到边缘传播时的各阶段的细节。关于现代性的巴萨拉/罗斯托路径,假设了具有欧洲特征的科学/经济发展的模型为非西方世界提供了范式,“前科学”的非西方世界如今正在经历西方数百年以来的发展道路,而非西方国家的哲学、宗教信念、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组织则是传播的可能阻抗。施特(Schott)把巴萨拉/罗斯托模式归咎于广泛共享的认知标准、世界大同主义和合作关系的制度化。“对自然不变性和知识正当性的信念穿越世界各地,连同参与者的世界性定位,创造了非西方文化吸收欧洲传统的可能性。”④
从巴萨拉的三阶段模式来看,知识的空间性或科学的地方性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他看来“知识空间绝不是特殊的,而是完全普遍的”。结果,“几乎所有坚持数学与科学知识全球化及其应用的普遍性的作者,很容易忽视大量的其他工作,而正是这些工作在创造与维系一种情境空间,在其中科学的‘应用’才得以进行”。换言之,按照旧的哲学范式,“空间的重要性被消解了”⑤。因此,科学史家在整体上对科学与空间的复杂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兴趣。
隐藏在巴萨拉三阶段模型背后的是萨顿式的实证主义科学编史学。萨顿认为以同样的方式,科学揭示出自然的统一性,科学史揭示出科学的统一性,因此,科学史提供了人类统一性的证据,因为科学史对人类来说是本质的。在科学的年代,这允许人类在宇宙的进化中能够更好地理解自身的情境。这是一种线性的、实证主义的科学与进步的观念。⑥
巴萨拉模型表面上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仿佛阐释了一个国家的科学与社会发展的捷径,而这在欧洲却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对于殖民地世界的“新欧洲化”来说,巴萨拉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他假定在科学传播与国家发展之间具有一种清晰的联系:在所有国家中,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是基于现代科学,随后才逐渐具备了欧洲文化、法律、经济、技术的“优势”。如澳大利亚与美国,虽然与欧洲的距离遥远,但其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与种族方面比欧洲的邻居(如土耳其、埃及)更欧洲化,伴随的是它们的土著文化及其传统几乎被完全摧毁。巴萨拉的模式反映出“中心—边缘”关系的社会学与现代化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巴萨拉科学传播的简单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招致广泛的批评。“事实上,这种模型具有某种启发价值,但缺少解释力,因为它表现出某种起源上的错误推论,在其中,一种思想的存在被认为是其现实的存在的一种充分解释。”⑦这暗示着这种解释是单向的与线性的,它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帝国主义策略,依据某种政治力量来解释和论证传播。这种研究忽视了殖民地科学得以出现、发展和流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情境,仅强调传播的认知维度,即坚持现代科学之所以起源于欧洲,是由于其拥有高于其他知识形式的所谓内在优点,使它能够直线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这里,科学仿佛在真空中传播,忽视了其被接受的各种情境条件。事实上,西方科学传播所至,是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一些是殖民地,一些是半殖民地,还有一些是非殖民地国家;一些是“新兴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另外一些国家则具有数千年的属于自身的科学与文化传统,如中国与埃及。无论西方科学进入的是何种地区与国度,只有适应地方性知识、文化与社会与经济条件才能得以生存。“对许多读者来说,巴什拉模型的历史话语太接近于美国的经验”,事实上,地方性“不是被动地接受西方方法和知识,而是根据它们与自然知识、宗教和其他因素的关系来选择性地吸收它们”⑧。
二、田野科学实践
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科学哲学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巴萨拉的科学帝国主义无疑是基于传统的实证科学的观念。为研究科学的全球史⑨,我们必须扩展科学的范畴及其界线。
随着皮克林《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1992年)一书的出版,科学史开始关注科学中的田野实践(field practices in sciences),进入了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研究阶段。它们不再集中关注科学理论、科研机构或实验室,不再仅仅关注纯粹理论知识的生产、循环与运用,而是更多地关注科学中行动者的异质性、建构知识场所的多样性与科学行动者之间谈判的复杂性。这样,科学的建构者、使用者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界线不再清晰了。知识生产的场所呈现为多样化,跳出了专家知识的堡垒:考察外行群体、社会运动、媒体与大众文化;考察在一个学科发展中的政治、机构与经济力量的影响。这样,对科学的研究就处于一种“多场所”的常人方法论纲领之中。
受“科学实践研究”的影响,科学史家开始把科学置于拥有具体时空的地方性场所之中,探讨文化相遇情境中的科学实践及知识建构,强调田野科学在科学史上的重要性,追踪在日常社会与公众生活中的知识建构,这种研究的结果呈现出科学并非是欧洲白人的专利。这就把科学史扩展到后殖民研究阶段,科学编史学发生了研究视角与内容上的重要变化。如受实证主义的影响,科学史家传统上更加关注实验中的精英文化,关注精确科学,如物理学与化学,几乎没有为田野知识留下任何空间。而一旦我们把科学视为一种实践,就打开了田野知识的科学家族,如动物行为学、农艺学、森林学、地理学、地质学、自然史、植物学、动物学、公共健康等。不像实验室,自然场所不是科学精英独占的空间,而是公众空间,其界线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界定。它们中间生活着非常不同的人群,从事着非常不同的事情。某些是永久居民,某些是匆匆过客,他们狩猎或捕鱼、搜寻食物、探险、野营、旅行、创作小说与诗歌、绘画。虽然处于田野中的成员是异质性的,追求着时常相互矛盾的不同目的,但他们都在以复杂的方式共同建构着田野知识,建构过程远比实验室科学复杂。知识建构不仅出现于欧洲宗主国,同样出现于非欧洲世界。参与知识建构过程之中的人时常包括本土人,他们带有自身的视角、传统与技能。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史,必须转换研究视角,把科学置于全球性的视野之中,更多地关注特殊的时空中交往行动的细节,对它们进行深描。这会使历史学家关注科学探索的多维度的地方性情境,消除帝国主义在宏大科学叙事的历史舞台上的绝对中心地位。熟悉殖民地生活方式的学者们注意到:“他者的”或“不精确的”科学,包括社会与自然史、生命科学,都是殖民地生活的日常伴随物。如果我们提倡一种在全球性舞台上的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观点,将会把科学实践的范畴扩展到完全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建构的路径,它研究文本与对象、建构者与材料、建构途径与空间之间的不同关系。
在这种后殖民主义的科学编史学中,科学史家力图超越固定的中心—边缘的说法,认为每一地方性都有成为中心的可能,都充当信息循环的一个节点。与这种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是对交往或接触行动的兴趣,它们超越了地方性,使知识保持着跨地域的流动。当前科学史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丰富的内容,包括对旅行者、传教士、本土的观察者与助手的关注,关注这些中介者所占据的空间特征以及这些中介者在联结而成的一个行动者网络中的流动。科学要成功,就必须旅行,必须依赖于中介者使它流动到别处,以网络形式跨越了帝国、民族与地域。非西方世界的人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着自己既有的文化传统和不断变化着的历史观念。借助于历史深描,在全球化框架中重新思考更为遥远的各种地方性知识及其历史,意味着科学史家需要把科学理解为一种交往或接触形式,意味着要以这种形式去把握异质性的运动、转译与传播的过程,继而创造出一种西方历史与非西方历史的相对平等的有效对话空间。
三、科学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相遇模型
20世纪90年代后,巴萨拉的科学殖民主义模型已经受到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理论⑩的挑战,科学史家开始用“相遇”的多元视角取代了线性的“传播模式”。“文化相遇”的编史学倡导后殖民主义的多元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偏爱一种非线性的、多视角的历史深描,关注历史中的机遇性交流实践,重新解释非西方文化及其自然知识的遗产。对科学的帝国主义统治与殖民地管理的传统关注已经让位于对帝国/殖民相遇情境中的文化与知识的关注,重新思考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更为复杂的双边关系。这种研究挑战了欧洲中心的编史学,提出了研究现代世界的新视角。科学现在不再被分为西方与非西方,强调在不同地区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思考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全球化条件。当前文化相遇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考察作为一种竞争、文化汇流的复杂的知识相遇过程,探讨多元中心(有些在欧洲,有些在其他地方)与不同边缘之间的物质、知识与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多方向的流动。在其中,“殖民地科学”(colonial science)获得了新含义,它不仅指在殖民地时代欧洲之外的地方所建构的科学(巴萨拉意义上的),而且还包括利用殖民地知识资源在欧洲所进行的研究,还包括在贸易区域所进行的科学。这样,科学就被视为是自然系统知识的缩写,研究的焦点是植物学、动物学等田野科学,如施尔宾格(Schiebinger)研究了殖民地的生物勘察(bioprospecting)(11),表明在由欧洲的航海与征服所激发的全球化相遇过程中,殖民主义本身包含着众多的不同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欧洲科学像本土的非欧洲科学一样,同时都发生了改变。(12)
自16世纪起,科学就开始介入帝国主义的征服与殖民化过程,然而这种权力必须与地方性知识体系进行协调才能运作,这种协调是帝国主义殖民事业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位宇宙学家在给到新世界旅行者的指令中解释的那样:“你应该寻求有关(本土)实践的科学信息,或他们所理解的有关世界的创造性知识,他们那种关于天体运动与构成的知识。”(13)巴萨拉模型认为,原始数据出现在殖民地,后继的信息积累、组织与分析却是发生在宗主国。但他忽视了这样一种事实,即远离宗主国的机构与群体时常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在广阔的地域中收集信息,同样在分类、评估、鉴定与概念化这些信息。这些地方性活动因此值得科学史家认真对待。在殖民地中的博物学家不仅在与欧洲的科学机构对话,同样也进行着相互间的对话。因此,联系着殖民地的科学网络是广泛与强大的;科学交流的网络因此是“多中心化的”,带有“多层次的权力与相互作用”。科学知识的建构时常依赖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以及殖民地之间的复杂的交流。美籍华裔学者范发迪(Fa-ti Fan)用一个术语“文化相遇带”(cultural borderland)表示这些交流得以发生的空间。在一个文化相遇带中,不同背景的历史行动者相互间作用着,进行着谈判与交易。这些相遇的过程与结果可能从征服、冲突、摩擦、合作到混合、杂揉。“一个文化接触区就是每时每刻这些行动得以发生的空间。”(14)这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符号空间。
首先,“文化接触带”会使人们去追踪实际的相遇过程,直接关注在日常生活场所中发生的文化实践,它不仅包括理论,而且还包括物质文化。其次,它强调在文化相遇情境中的灵活性与机遇性。再次,它强调“边缘”的存在,边缘的人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着自己的历史观念,就像他们的文化一样,是不断发展与变化着的。这种科学编史学考察本土的行动者的类型、旅行过程与相互联系的历史,依据本土行动者自己的术语尝试重新定义传统的地方性知识。需要“深描历史”,在全球化框架中重新思考各地方性知识及其历史。
利用“文化相遇带”的方法论,范发迪研究了清末英国博物学家在中国的日常科学实践。(15)这种路径完全不同于中国科学的传统编史学,传统上人们关注于中国知识与“西方科学”的对立,并把中国科学史置于西欧全球化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情境之中。范发迪的研究一开始就超越了严格的文化界线,如中国—欧洲、东方—西方,追踪在文化相遇带处的知识的循环、翻译与建构,在这里,身份与文化范畴时常是际遇性的。其次,他把博物学看成是理解科学帝国主义的重要场所,这不仅是因为它对自然史的研究是关键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权力谈判与知识翻译的场所。因此,在微观政治层次上,博物学使得研究者能在日常实践中观察科学帝国主义的活动。再次,他注意到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各式各样的历史行动者,如在中国的英国博物学家包括商人、外交官、医生、军事官员、园艺家、旅行家与顾问官员。自然史的研究则会关注博物学家与他们雇用的本地人之间不断的沟通与谈判。最后,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科学文化与物质实践时,就会发现交流谈判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是复杂的、动态的与地方性的。在中国,博物学实践关系中的权力分布不一定会偏爱英国博物学家,他们身处其完全不熟悉的场所,他们对田野工作的场所控制显得更为薄弱,会碰到更多的麻烦,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被西方列强完全殖民化,英国博物学家在中国的探险并不会得到英帝国主义的直接保护。这样,博物学家与中国雇员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与工作关系是其田野研究成功的关键。如在他们的经济植物学的探险实施中,对中国本地人的信任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控制着贸易物品,他们知道哪里有何种动植物,知道从何处获得它们。因此,中国人在知识生产的网络中占据着相对关键的环节。这里。后殖民科学史中时常会碰到的权力的“反对称性问题”凸显。
在后殖民的语境中,科学史家还认识到欧洲探险家在海外所获得的知识至少包括某些地方性知识。在许多情况中,帝国勘察在整体上依赖于其与地方性知识的协调。在清朝的中国广东,英国博物学家从其中国伙伴(主要是园丁、商人与手工工人)那里获得广东的动植物。欧洲人还要雇用本地工匠去绘制这些物种的图形。由于几乎所有物种都不能够在跨海的长时间旅行中存活下来,于是这些图表就成为关键的科学信息。广东的英国的博物学家选择出他们想要的动植物,然后指导工匠进行图形绘制;中国的工匠则提供了精确描绘各种物种所必需的工匠的知识、技能与观察能力。基于绘画中的动植物,英国博物学家利用西方科学的范式进行描述并分类。在这种交易中,就科学的可信性与等级来说,英国博物学家与中国工匠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英国博物学家具有更多的科学话语权。然而,英国博物学家并不会固守宗主国的科学权威,他们时常要认真对待广东地区的植物与动物群落知识。中国的工匠,此时扮演着科学中的“不可见的技工”角色。中国传统的工匠一直是从中国输出的绘画的生成者,其风格是中国流派的绘画与欧洲“实证主义”(复合视线、光与阴影等)的混合。输出的绘画是中国工匠与欧洲消费者之间合作的产物,它被创造以适应欧洲的市场。有趣的是,这些绘画在欧洲被视为中国风格的绘画,而在中国本身却被认为欧洲风格的绘画。这是一种全球接触的产品。这些自然史的绘画构成了科学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风格、思想、美学、物质文化、植物与动物知识的广泛交流。因此,绘画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相遇的实践场所,在其中,欧洲的与中国的艺术与科学之间实现相互融合。自然史就体现在艺术、科学与商业的接触带之中,中国工匠与欧洲博物学家都参与到自然史中知识与物质文化的建构之中。所有这些构成了自然史的有机部分。交流以多重的形式出现,发生在未能预期的地方(如输出的艺术与科学的可视表征、在田野中的民间知识与在园艺学中的风格与技能)。在田野的情境知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博物学家与本地人,以及不同知识传统之间的复杂的谈判过程及相伴的产品。它们形成了一种知识与文化实践的异质性组合的关键成分,它们置身于知识与文化实践的全球化循环的丰富情境之中。因此,我们不应该再保留诸如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这种有问题的绝对二分,它们应是历史行动者的边界文化产品与权力谈判的产物。当然,这并不否认科学与知识传统之间的全球性等级,不同社会之间总存在这种等级。但在“特殊的场所”中,知识生产的机构与智力等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机遇是情境化的,随着特殊的情境而发生变化。
“文化相遇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首先,对于科学史和自然史,我们不仅需要来自于欧洲帝国的视角,而且需要来自于殖民地生活的视角。情境化的两个方向的互动——在非欧洲文化中去解读欧洲资源与在欧洲文化中去解读非西方资源——是富有成效的,正是在欧洲人与非欧洲人、西方科学与非西方科学的多元化的相互介入的过程中,殖民地科学得以出现与发展。我们不应把地方性知识视为是对欧洲的反映或阻抗,而应把其视作建构殖民地独立史的组成部分。殖民地相遇的交织经历,提醒人们欧洲人所写的殖民史事实上时常是有关欧洲在海外的历史,它必须依据地方性叙事者熟悉的术语来重写。
其次,我们需要对知识与权力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地方性空间”成为重构历史的一种合法“中心”。科学在被意识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之前,首先应该是一种地方性的显现。在殖民地科学与地方性文化的关系中,我们发现在实践中的科学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活动,表现为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之间及其历史的异质性知识融合。异质性的地方知识在对自然界的探索中得以产生与编撰,在与欧洲科学相遇的过程中,也改造着欧洲知识,因而是更具整体性的全球科学史的组成部分。这样的过程与事实,赋予地方性知识与方法以探索和应答自然界的合法性。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相遇与交流的“传统叙事空间”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展现。这是一个行动者的实践世界,不是一个柏拉图式的观念世界。这是情境空间中的实践,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是一种“自我—他人—物”体系的重构,一种经验在科学中得以构成的“现象场”的重构。(16)这种重构强调的是在欧洲科学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其穿越的是多元化的矛盾空间,在穿越过程中,双方都获得了全新意义上的重构。
再次,坚持人类对自然界的理解的多元性,认可在较为复杂的世界中建构不同文化和谐相处的可能性。把地方性价值系统引入科学,会使人们逐渐意识到地方性知识在保持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资源有效管理上的重要性。对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已经确立了科学与地方性知识的对话的必要性,促成了两种系统的力量与视角的结合。承认地方性思维模式的智力地位与持续的有效性,也反映出了一种日益增强的国际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授权出版了大量有关知识、文化与发展问题的报告,所有这些报告都反对传统的文化同化政策:“一种文化上具有独特性的人民失去了其身份。这些身份表现为其语言运用,其社会与政治的机构,还有其传统、艺术形式、实践与文化价值,被限制了。今天的挑战……是发展出一种场所,它能够确保发展是综合的与相容的。这意味着尊重价值体系、尊重土著人所拥有的有关他们社会与环境的传统知识,尊重他们文化得以生存的机构。”(17)在这种对地方性知识的重新评估中,科学史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这种评估并不是抽象的争论,而是基于地方性知识实践的案例研究,这种自然主义的途径行将打开一个平等的比较空间。
结束语
在后殖民的语境中,历史—情境化地思考西、方科学,使非西方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比较成为可能。这种比较无须去反思非西方世界为什么没有接触欧洲,并按后者所期望它们那样行动(李约瑟);也不会把地方性科学化为简单的接收史,这种把历史限制在单向性叙事的做法(巴萨拉),是在线性术语中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西方科学与非西方知识体系之间的比较时常充满着不愉快,认为这些不愉快源自不同文化之间的界线,事实上,这些不愉快背后隐藏着的是人们的一种信念,即只有西方文化提供了一种对自然的无私利的、并在文化上中立的说明,因为只存在一种客观实在,科学也只能提出一种可信的方法去描述与解释这种实在。为把近代科学理解为一种合理与进步的思想与机构的传播,这种实证论观为科学史学家永恒化了一个清楚的议程:寻求欧洲启蒙精神传播的地方性“踪迹”,各种殖民地科学组合成了西方科学的“车轮辐条”。科学史就是一种不断克服“迷信”与“无知”的历史,在高级的科学解释面前,宗教与信念退却。
然而,殖民地的相遇从来不是单向的,因为每一个社会都会产生有关自然的知识,这种知识承载其文化传统,勾画出其地方性的自然的真实结构与过程。西方社会也不例外,它所承载的诸如自然律、原子论与进化论,就反映出其政治、社会与文化传统,如法律、个人主义与进步论。当研究“科学实践”的大门打开后,科学史家的焦点转向了文化意义或合法性权力如何体现在科学与技术的文化与政治建构中,重构不同的行动者如何在交流中共同建构出一种全球意义上的新科学。历史学家注意到宗主国(metropole)与殖民地(colony)之间,并非简单的“中心”控制“边缘”,而是互相影响、彼此作用,同时重审了帝国脉络中文化与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经验的案例研究能够成功地整合科学内容与历史动态的情境,经由这样一种关键场所,人们能够看到特殊性与普遍性是如何相互渗透,人们能够超越“地方性”被动接受现代科学的传统科学编史学。我们需要研究技术史与殖民地科学史之间不断变化着的复杂的互动关系。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关注不同精英人物与文化相互间的交流,如今人们意识到殖民地中田野知识的相互交流,更突出地表明了不同思想是如何在欧洲与非欧洲之间流动的。基于这些理由,这类纲领必须强调用自己的术语表达出来的地方性知识在科学知识扩展中的作用。这样,后殖民主义研究就为科学史提供了一个新“剧场”,成为研究世界史、科学史、全球资本运动史、环境变化史的学者共同会集之处。
注释:
①参考了Michel Paty,Comparative History of Modem Science and the Context of Dependency,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 1999,4.184-186对西方科学的三分期讨论。
②相关的主要研究见Science and Empires:Historical Studies about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European Expansion edited by Patrick Petitjean,Catherine Jami and Anne Marie Moulin.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1,Colonialism and Science:Saint Domingue in the Old Regime by James E.McClellan III.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③Roy MacLeod,“Introduction”,Nature and Empire:Science and the Colonial Enterprise,Osiris,Vol.15,p.6.
④Schott,Thomas (1993),“World Science:Globaliza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Participation,” 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8:198.
⑤Steven Shapin,The Mind Is Its Own Place’Sci.Context,1990,4:209.
⑥(美)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⑦Roy MacLeod,“Introduction”,Nature and Empire:Science and the Colonial Enterprise,Osiris,Vol.15,3.
⑧Paolo Palladino and Michael Worboys,Science and Imperialism,Isis,Vol.84,No.I,Mar.,1993,99.
⑨Global Histories of Science.Isis,No.1,March 2010.
⑩Fa-ti Fan,Science in Cultural Borderlands,East Asian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7)1:213-231.
(11)指研究由生物有机体所提供的,可能具有医学与商业价值的物质。
(12)Londa Schiebinger,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Press,2004.
(13)引自Global Knowledge on the Move,Nell Safier,Isis,2010,135.
(14)Fa-ti Fan,Science in Cultural Borderlands,East Asian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2007) 1:215.
(15)(美国)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M].袁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6)希拉·贾撒诺夫,科学技术论手册[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17)UNESCO,Our Creative Diversity: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Unesco Publishing,1995,pp.70-71.
标签:科学论文; 巴萨拉论文; 全球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后殖民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英国殖民地论文; 科学史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殖民地历史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博物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