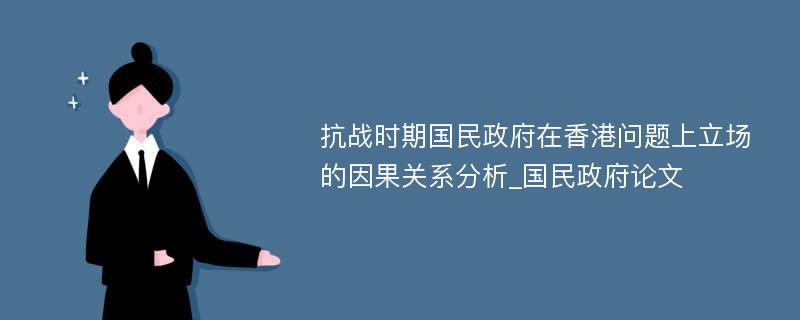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所持立场之因果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国民政府论文,探析论文,所持论文,因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方明珠——香港“在我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国耻的创伤”①。十九世纪中后期三个不平等条约使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如今根据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联合公报》,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沧桑变化的香港这段耻辱的历史终将在1997年6月30日划上句号而掀开新的一页。
不过,在香港主权归属问题上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了一定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意识。本着“把事情的本来面目还给了历史”②这一宗旨,本文欲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所持立场之前因后果试作一简析,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国民政府时期,迫于中国人民反英斗争,英国政府曾于1927年交回汉、浔租界地,1929年交回镇江租界地,1930年交回厦门和威海卫租界地,可是惟独不肯放弃香港这块王冠殖民地。为此,就香港主权归属问题,中英两国政府间发生正面交锋,国民政府当局屡向英方交涉要求收归,但未遂愿。至抗战爆发后,随着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对此要求更为迫切且态度益趋强硬。这是为什么呢?
1939年9月二次大战爆发后,到1940年局势更为动荡,“欧战方殷,日趋扩大,英、德相持,美、日敌视”③。是年夏,法国败降,英伦三岛被困,德国称霸欧洲,并向拉美渗透;日本在亚洲也积极向外扩张;特别是德、意、日三轴心国结成军事联盟,意欲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翌年,在欧洲,德国一方面加紧对苏发动军事进攻的准备,实施包围;一方面又对英国继续大规模轰炸,并向大西洋发展其潜艇战争。在亚洲,日本则蓄谋实施其“南进”战略,致使太平洋上风紧云急,阴霾密布,日美矛盾日趋尖锐。局势的演变使英、美不得不慎审其战略方针,1941年3月两国制定了“ABC-1”计划,确定了以欧洲为两国主要战场及“先欧后亚”战略决策。为了保证该政策的实施,他们期望帮助中国,支持中国打下去,“使之成为不断缠住日本和消耗日本力量的地方”。为此他们不得不作出一些“高姿态”,给中国一些甜头,于是就开始了两国与中国之间订立“平等新约”的交涉。是年4月初步磋商,7月继美国之后,英方向中方表示:待远东之和平恢复时,愿与中国商讨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④既然如此,国民政府斯时乃考虑到收回香港主权问题,不过因尚未摸清英国态度,故对赴任不久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发去训令,要他“研究并试探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当然不是要他直接进行谈判,“只是指出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日寇在太平洋、南洋、缅甸横行无阻,美国在珍珠港受到袭击,以致太平洋舰队不能活动。而英国经营多年远东头等军港的新加坡守军八万余人不到二十天被日本攻垮了,不到半年工夫日本把英美打得狼狈不堪,而中国是一个军备很弱的国,却抗日抗了四年多。”⑥这个现实使英、美不能不再次审度中国的战略地位,得出结论:“支持中国就是保护我们本身的安全和利益,是我们盟国的事业成功所不可少的条件。”⑦他们要利用中国广大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以及坚持数年抗日斗争的经验,支持中国“继续参战”以拖住日本,“使它不能任意在太平洋作恶”,来保证其“先欧后亚”总战略的顺利实施。为此他们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之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重要成员,在形式上通过《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使中国跻身于四大国行列。由于蒋介石“擎着抗战的旗帜,使全国人民无法不支持他,盟邦不得不支持他。”⑧“英、美把蒋介石看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⑨经罗斯福提议,蒋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英国授予他‘大十字勋章’”⑩……种种荣誉和溢美之词骤至,与太平洋战争前乃有天壤之别,这些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来说不能不滋生一种陶醉感和满足欲。不过面对现实,他们也清楚,对英、美来说,“如果蒋的装备低劣和给养不足的部队在战场上支持不下去的话,那么击败日本将需要丧失更多的船只和生命,就更不必说财力上的消耗了。”(11)又何况太平洋战争前近五年中,“因为中国一直在对日抗战,在亚洲遏制了日本侵略者,使英国人占了不少便宜”(12);再说为争取最后胜利还需中国付出多大代价和牺牲?这些或于国家、民族,或于蒋介石个人私念都形成不平衡的心理。一种要求偿还旧债和平起平坐、等价交换的心态,势必促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与英国屡次交锋乃至冲突。
毋庸讳言,一定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意识也是促使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争取香港主权回归而坚持正义立场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回溯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国从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当始自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则是最早侵入中国且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这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而强占香港的殖民帝国,故而中国人民与其宿怨甚深。到抗战时期,“在珍珠港事件以前,英国对远东的态度和行动,就已经引起人们的怀疑。英国的政策总是把英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不直接涉及英国利益的情况下,他们总是避免得罪强国,那怕这个强国是侵略者。”(13)乃致到1942年11月,“英国人基本上没有给予中国援助,连一架飞机都没有给过。”(14)而“所谓贷款,只不过是一个姿态,……并没有真正实施的打算。”(15)所以中国的“老百姓都认为,中国要摆脱外国侵略,争得自由,不能指望英、法等国来发善心,做好事。”(16)有着反抗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尊严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无时不在想着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复失地”,而蒋介石等人“同样怀有这样的夙愿。”(17)这里我们仅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而言,应该说还是基本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多次明确地提出收回香港主权的要求。主要表现在:①在与英政府交涉及签订《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的全过程中;②在开罗会议期间;③关于对香港日军受降权谁属问题的交涉。
关于《中英新约》的初步磋商早在1941年4月即已开始,已如上述。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在美、英远东战略中的地位顿趋重要,中、苏、美、英诸国结成盟邦。“而中国与英美等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不仅于《大西洋宪章》和《二十六国联合宣言》精神不符,而且由于中国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不平等条约已失去实际意义,因此,中国再次向美、英两国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18)对此,美、英两国政府于1942年10月9日分别通知中国政府,声明愿即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次日,蒋介石将此宣布于众。10月30日,英驻华大使薛穆向中国外交部递送了《中英条约草案》。自此直到翌年1月11日签约,谈判交涉历经两个多月。中方的立场是“只接受在平等基础上的盟国之间的谈判”,否则“宁可不谈”。谈判代表宋子文、吴国桢等人秉承蒋介石指示“要么‘一刀切’,不留尾巴;要么就不谈”(19)的原则,坚持捍卫主权、领土完整的立场,折冲樽俎于强权之中,进行了艰辛曲折的谈判交涉。最终在其他方面取得了较满意的结果,但在香港问题上却“触礁”了。中方坚决要求收回九龙新界。早在1942年7月,蒋介石即要求外交部研究如何收回九龙问题,谈判开始后的11月23日外交部提出了要求归还九龙的谈判草案。宋子文在对英方所提草案的修正案中,更具体建议在草案第五条中加入如下内容:“英王陛下认为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签订之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即废止,并同意该专条所给予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之一切权利,应予停止。”第六条还指出:英方在九龙租界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他官有资产及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并相互谅解。……”(20)蒋氏在此方案上亲自批示,强调英方要宣布愿意归还九龙租界地。对于中国政府的正当要求,英国政府采取蛮横和耍赖的态度,声称“我们提出的废约只是废除治外法权”,九龙新界问题“与废除治外法权无关”;甚至认为“九龙新界是英国扩大的领土,这与租界是两回事”,饬令薛穆“通知中国政府九龙新界不在讨论之列”。(21)这种强盗逻辑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不满。在谈判中,“中国一直力图说服英国终止它对九龙的租借权,并以此为签署条约的条件”,“否则中国舆论是不会满意的。”(22)宋子文在谈判中寸步不让,每次都重复坚决要求收回九龙的立场,并以此作为签约的先决条件,强调“条约如果不包括收复香港,委员长是不会同意签字的。”(23)而“吴国桢则具体地阐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的民族感情,并且从法律角度力争收回九龙。他说香港和九龙都是由不平等条约引起的问题,既然谈判废约,当然要涉及九龙。不归还九龙,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就不完全,中国政府亦无法向人民交待。”(24)蒋介石甚至提出“以后用我们自己的军队收复它”(25)的意见。中国这种坚决、强硬的立场几使谈判成为僵局,原定于1943年元旦签约的计划未得实现,英国谈判代表薛穆为此“面带忧色,郁郁不乐,颇为沮丧”。(26)虽然最终由于顾维钧这位外交耆宿从中转寰,更由于英国的狡狯谲诈,以“盟国之间会产生意见分歧,从而损害盟国的团结”等为由,采取延宕之策,推至胜利后再行讨论。同时“美国一直在敦促中国尽力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如中英谈判破袭,会影响美国”(27)而对华施加压力,最后蒋介石同意签约,但认为须声明随时再次提出九龙问题的权利,并要加上“中国民众自然对英国拒绝讨论九龙问题感到不满”这句话。(28)签约的当天,宋子文即交给薛穆一份关于九龙问题的正式保留意见:“关于交还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政府不以现时进行谈判为宜,本代表认为憾事。1898年6月9日许予英国租借九龙条约之早日终止,实为中国国民素所企望,而本日签订条约之意义,为开两国邦交之新纪元,中国政府以为项该条约能于此时终止,则新纪元之精神当更为显著,因此之故,本代表通知阁下,中国政府保留日后重行提请讨论此问题之权。”(29)虽然此问题被搁置了,但蒋氏“对香港问题仍然萦绕于怀。条约是缔结了,可是香港问题排除在外,使他不悦。”(30)后来宋子文“也曾数度提出过这一问题,也为未能在自己任内实现香港的回归而遗憾。”(31)
由于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主权归属问题上的龃龉并未因《中英平等新约》签订而消除,故而双方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再次交锋。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的大国首脑会议,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对此他大吹大擂,回国后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宣扬“开罗宣言反映了人民对‘轴心’国斗争的解放精神,反映了正义原则和反殖民主义的胜利。”(32)基于这种认识,他利用会议的机会,再次阐明中国政府关于收归香港主权问题的立场。据随蒋氏参加开罗会议,时任蒋侍从室中将高参杜建时的回忆,会上“蒋介石还提出战后拒绝英国军舰驶入中国港口,取消英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收回租借地。罗斯福支持了蒋的意见。罗斯福接着问蒋:‘你对香港如何打算?’蒋尚未答复,丘却大声疾呼:‘请大家注意,香港是英国领土。’蒋介石回敬说:‘英国以暴力入侵中国,与清廷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概不承认,战后随时可以收回香港’”。(33)又据杜文所载,在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及其高级幕僚出席的三国军事首长举行的第一次联席参谋会议上,蒋氏再次申言:“中国为独立自由而战,香港原是中国领土,在不平等条约下为英国霸占,英国人曾被日本从这块土地上赶走,今天要以无数的中国生命,收复这块地方,香港必须归还中国。”(34)而当英国参谋总长布鲁克将缅甸与香港相比较时,“蒋介石反驳,不能拿香港和缅甸相比,香港原是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收回,中国不是帝国主义者,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英国哑口无言。”(35)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评论蒋介石其他方面的功过是非,仅就上述几段关于香港问题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言论,当应得出在此问题上蒋介石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坚持了反对殖民主义、捍卫民族利益正义立场之结论的。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战争的结局日趋明朗,而英国原先困危窘难局面亦渐消除,它在远东的力量有所恢复,随即背弃战后讨论九龙问题的诺言,欲以武力抢占香港,以图重温旧日殖民帝国之美梦。为达到目的,它以所谓“香港是在英国手中失陷,由于事关英国国家荣誉,故应由英军收回并恢复其战前状态”(36)为借口,在日本投降后,派兵迳往香港受降。此举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愤懑和反对。本来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颁布的第一号受降令:“在中国境内(除满洲外)、台湾以及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37)香港理应归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受降。为此,蒋介石申言:“在并未承认香港是英国领土的中国而言,乃是不能许可英国擅自在中国战区内接受日军投降的。”(38)同时又派遣一特使赴港,通知当时在港筹组临时行政组织的前港英政府辅政司金逊:中国军队即将到港,应由中国军队司令官接受驻港日军投降。(39)还于8月21日令陆军第二方面军接受广东地区日军投降事宜,其中由集结在广西苍梧的第13军接收东莞、九龙、香港。但在美国改变原先态度而偏袒英方情况下,英国大耍无赖手段,对香港进行武力“收复”。最后“中国乃不得不在失掉对香港主权立场的范围内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40)蒋介石于8月22日电达麦克阿瑟:“可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授予英军司令官以接受日军投降的权限。”同时还进一步表示,一方面要尽力避免与英国在香港发生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打算以武力来抵制英国人在中国战区之内所采取的行动。(41)为此蒋介石召见薛穆,明示可以英国所派之哈考特少将代表他接受驻港日军的投降,并让薛穆通知其政府:“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42)此一强硬立场使得英国不得不作出一定让步,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即哈考特不仅仅代表英国政府,而且同时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日本人的投降书上签字。(43)应当承认,国民政府在此问题上最终由于多种原因而妥协了,“但这种妥协是有条件的、有限的。在涉及主权问题时,态度仍是强硬的。正是这种强硬妥协的结果,才使哈考特以双重身份在受降书上签字。”(44)
此外,促使国民政府在此问题上持强硬立场还另有他因,其中“罗斯福总统的态度也鼓励了中国,他不止一次表明,他完全赞同委员长关于收复失地的愿望。罗斯福本人还曾敦促过丘吉尔把香港还给中国。”(45)1943年6月,赴美治病的宋美龄为辞行再访白宫时,与罗斯福详商了战后远东和平与善后等问题,“美国人在首先注意到重庆反对传统的殖民主义大国方针的同时,支持了重庆的这一立场。罗斯福……向宋美龄保证说,满洲和台湾应该归还中国;香港在中国享有主权的情况下,将成为‘自由港’”。(46)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又曾与史迪威谈到,他认为“必须在香港升起中国的旗帜”(47);在会议上,他又“敦促过丘吉尔把香港归还中国,并且说,那里的居民90%以上都是中国人,加之又十分靠近广州。”(48)及至战争后期,在为克里米亚会议准备阶段,罗斯福还“希望会议能作出安排,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政府。”(49)由于自恃有美国的支持,对于本身与美国关系亲近和密切程度甚于英国的国民政府来说,从心理上当然显得理直气壮,遂鼓足勇气要与英国理论一番,屡屡交锋。殊不知美国这样做是从其战后的战略计划考虑的,它是“想破坏欧洲殖民主义在亚洲阵地”(50),以达其称霸全球之目的。故而在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下一着棋则是“尔后蒋介石必须作出‘巨大的姿态’,并宣布香港成为‘自由港’”(51),从而为其“门户开放”的传统政策再增新内容,此乃其真正目的。难怪宋子文曾这样说过:“首相和总统都是政治家,他们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搪塞起来,八面玲珑。那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否则他们不会有今天。”(52)此语不谬。正因如此,又加上“英国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情绪,他们是一个狡猾的民族”(53),一方面说得冠冕堂皇,另一方面则强调“英国立国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获得殖民地”(54),更何况香港这块王冠殖民地,怎肯轻言放弃?这就决定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争取香港主权回归的努力难以奏效。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鸦片战争以来,英帝就是中国人民的老对手,但屡次交锋总是以中国之败绩而告终,此中除了历代政府颟顸腐败、屈辱妥协和英国的船坚炮利、武力威胁之缘故外,还应看到“英国人的外交手腕历来诡计多端。同它合作,其他国家休想得到多少好处。英国人看来能说会道言辞动人,但……他们将顽固地坚持其传统政策。”(55)而“英国的传统政策,一贯是以损人利己作为核心”。(56)当太平洋战争初期英国在远东属地相继失陷,其殖民统治岌岌可危时,为维持远东局面,它要“尽一切可能使中国继续参战”以拖住日本,于是就对华“有意表示友好,建议缔结新约”;而当中方提出归还九龙问题时,它就以种种借口来推托和拖延,致使《中英新约》未能涉及香港问题。可是到战争后期轴心国的败局呈明显趋势,英国在远东局面相对稳定时,它即初步做好战后抢占香港的战备工作。而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它又妄称“香港是在英国手中失陷……应由英军收复并恢复战前状态”,强行抢占香港。为逃避履行对华所作的“战后讨论九龙问题”诺言,以“当时的局势刚刚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时期,不愿发生新的纠纷,造成亚洲新的不安”为托词而食言自肥。这个老奸巨滑、诡谲善变的老牌殖民主义者,为着自身的利益,对华一再施之蒙骗、耍弄和欺侮、讹诈的手段,这对于本身内部矛盾重重、弊端种种的国民政府来说,自然是无法与之匹敌的了。
所以,虽然战时在罗斯福支持下,“中国形式上、法理上都取得了平等的地位,在名义上已是四大国之一,但却受到不平等的甚至歧视性的待遇,同众多的二、三流国家一样,被英美摒于大国交往圈之外,中国常处在被支配、被摆布的地位。”(57)中国跻身于四大国行列乃是服从于西方国家战时和战后战略目标的,正如1943年罗斯福对英国蒙巴顿勋爵所言,“把中国当作大国就可以在战后一个时期制止侵略。有了五亿中国人作为盟友,这在今后二十五年或五十年是非常有用的,即使目前中国还不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军事和海军的支援。由于它的战略地位,一个友好的中国还可以成为抵制苏联可能在亚洲进行扩张的缓冲地带。”(58)中国在其全盘棋局中乃一小卒罢了。故而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华盛顿会议和魁北克会议(前半段)皆剥夺了中国合理的出席权;而发表“四强宣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却唯缺中国外长参加。尤为甚者是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居然撇开当事国——中国,由苏、美、英三国迳自作出损害中国主权的协议。尤其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所实施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致使国统区出现政治上腐败反动,经济上垄断却掠,军事上溃退如泻的局面,这种自杀政策只能是削弱自身国力。而英国正瞅准了这些,才耍赖与高压相结合,使其拒不归还香港主权的阴谋得逞。
正因为中国是弱国,另一帝国主义大国——美国则玩弄两面派手法助英欺华,一方面抚慰中国,表示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却又支持英国,除前述在中英新约谈判中因香港问题争持不下时,美对华施加了压力外,又如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霍贝克曾表态:“尽管美国人民同情中国,希望香港回归中国,但美国政府是站在英国一边的。”(59)同样,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对中国保证支持的同时又保证不改变英国在远东殖民地的状态。(60)再如继罗斯福后任总统的杜鲁门则在香港日军受降问题上公然偏袒英国,他致电蒋介石:“英国在香港的主权是没有问题的。倘为投降仪式而发生麻烦,似乎将抵偿不了其恶劣影响。”并让麦克阿瑟修改命令,饬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61)可见美、英两国沆瀣一气,欺侮中国。
争取收回香港主权的努力和斗争有始无终的另一重要缘由,乃因战后反苏反共的共同目标将国民政府绑在了美、英的战车上。日本的投降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但也意味着美、英同苏结盟关系的终止。原曾是战时的盟友,而今成为两大对立营垒的擎旗者。早在1945年1月,罗斯福就曾说过,随着战争胜利的即将到来,“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更多地意识到胜利者之间的意见分歧。”(62)杜鲁门更于1947年3月提出了遏制苏联、独霸全球的“杜鲁门主义”。而国民政府在反苏反共旗帜下,一直唯美国之马首是瞻。在与苏、英关系权衡中,不要说在战后,即使在战时虽然对英国有所怨尤、争执,但却与对苏关系有本质不同,它认为在“对苏关系中需要英国的影响”(63),正是出于“在今后对付苏联时,与英国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64)考虑,故在中英新约谈判的最后才会出现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让步。尤其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正与英国为驻港日军受降权谁属问题争持不下时,国民政府竟因得悉苏军于8月22日占领东北全境消息后,深恐中共军队在苏军护持下进兵东北而影响其战后进行反共内战方针的实施,遂决定“自须集中力量防备苏俄势力之深入”,而“避免因香港问题分散了国家的力量和国民对外注意力”(65),于是将头一天部署的准备进兵香港受降的军事计划弃之不顾,而于当天作出让步:英军司令官可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为了反苏反共这第一目标而可置民族权益于不顾的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为争取香港主权的回归所作之努力和斗争,终因上述诸般缘由而未得结果。
历史已过去半个世纪,世界和中国均发生了巨变。令人欣慰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争取香港主权回归愿望的实现指日可待,无论英国当局还将打出怎样的牌,玩弄何种花招,五星红旗终将于1997年7月1日起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
注释:
① 《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录》,[台]蔡国桢发展有限公司出版。
② 刘大年:《七十年与四十年——<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吴玉章致李根源信》,(1940年9月26日),《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④ 《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第606页,正中书局,1983年版。
⑤(17)(45)(48) 《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14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⑥⑧⑨ 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1945年春),《吴玉章致李根源信》,(1940年9月26日),《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⑦(11)(49) [美]威廉·李海:《我在现场——罗斯福、杜鲁门回忆录》第211、337页,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⑩(32)(46)(47)(50)(51) [苏]B.沃隆佐夫:《蒋介石评传》第174,198,197,197,19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1年版。
(12)(13)(14)(15)(16)(22)(23)(25)(26)(27)(28)(30)(52)(53)(55)(63)(64) 《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349,8,108,8,10,169,16,176,173,175,178,18-19,316-317,15,230,178,172页。
(18)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1卷,第22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19) FO371/31657,F6761/828/10,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FO为英国外交部档案,现藏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
(20) 宋子文呈蒋介石(1942年11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三)
(21) F7822/828/10,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Dec.5,1942。
(24) FO371/35679,F123/1/10,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9)(61) 关国煊:《由<中英平等新约>到<中(共)英联合声明>》,[台]《传记文学》第64卷第3期。
(31)(57) 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359、36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3)(34)(35) 杜建时:《忆开罗会议》,[港]《镜报》1984年5月号。
(36) FO371/46751,F4008/1007/10。
(37) [英]《1942-1946年的远东》第7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38)(40)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
(39) 柯林斯:《汇丰百年史》。
(41) Federal Archives,Suitland,Haryland box 8,meeting 7924Aug.1945。
(42)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7日)。
(43) Colonial Office 129,591/18:Foreign Office to Seymour,30 Aug 1945。
(44) 高岱:《战后香港归属之争述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4年第2期。
(54) FO371/35689,F3563/10/10,The Future of Asia,May 16,1943。
(56) 《关于英国切断西南交通问题》,《群众》杂志第5卷第1期社论,1940年7月25日出版。
(58) 转引自解力夫:《抗日战争实录》(下)第80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9) FO371/35740,F3561/1,Halifax to Eden,July 13,1943。
(60) FO371/46751,F5066/1147/10,Minutes,Aug.231,1945。
(62) 《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动力》第107页。
(65) 金达凯:《香港前途问题的瞻顾》。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香港论文; 历史论文; 远东论文; 蒋介石论文; 宋子文论文; 九龙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