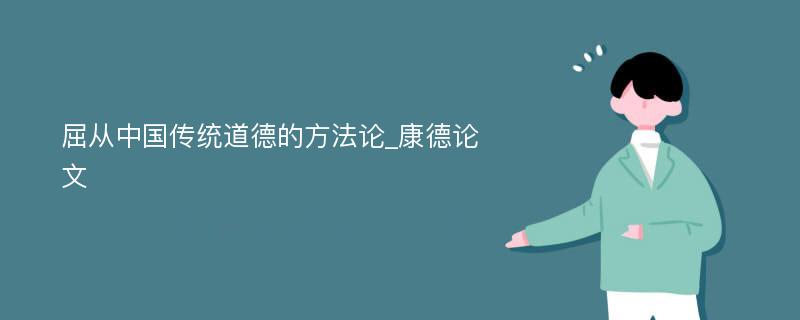
中国传统道德扬弃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中国传统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精神,国民心性问题将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之一。这就使得对于传统道德的分析提取、批判继承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传统道德怎样批判、怎样继承?继承什么、批判什么?若缺少冷静、清醒、合理的方法论指导,即使有不能偏颇的信念,但一遇到实际问题,仍往往会违背初衷,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之两极端。不解决对传统道德批判的方法论问题,在理论上就难以对传统道德合理梳理分析,在实践上就难以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传统道德,故名思义,首先是传统的、历史的、既往的道德,然而,传统道德不仅仅在于它的这种时间特征,更重要的在于它那传统时代特有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内容特征。本文是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道德价值体系的意义上使用传统道德这一概念并进而探讨对传统道德扬弃的方法论的。
一、舍弃内容 继承形式
中华民族道德是发展着的。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道德发展的一个环节,它是生长在传统时代的民族精神。这里隐含两层涵义:a、 传统道德生长于传统时代,在根本上是传统时代的产物,因而,随着传统时代的消失,它在整体上就必然失去存在的依据;b、 传统时代及其道德是中华民族及其道德发展的中介,传统道德是传统时代的民族精神,它曾孕育了若干代人,维系了中华民族,因而,在传统道德之中总是包含着某些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普遍文明财富,这些必须被发扬光大。扬弃或批判与发扬光大这是一体两面的事。
人们往往习惯地认为,传统道德中包含了珍贵的道德财富,应当通过具体分析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故对传统道德的继承是具体内容的继承。然而这似乎公允合理的看法恰恰是值得怀疑的。第一,传统道德内容纷繁复杂,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根本上又从属于传统时代的基本道德价值体系,即使是那些劳动人民的美德也难免带有传统时代及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的烙印;第二,除非割断一切规定与联系,否则,就不可能有绝对善的东西,即使我们今天看来可以值得光大的某些东西,一旦在传统时代、传统价值体系内考察,很可能事实上是统治者的婢女,带有恶的性质;第三,传统道德的内容又是有层次的,当透过现象进入更深层次时,传统道德内容又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成为心理构建形式的,最深层次的道德恰恰不是内容的而是稳定的内形式的(关于此内形式后文将专门阐释)。因此,笔者以为,对传统道德的扬弃或批判继承首先不是内容的,而是形式的,是舍弃内容,继承形式(我们并非完全否定通常意义上所主张的对传统道德应当具体分析其成分的做法,只是认为这种做法必须首先打破其体系、舍弃其根本内容方可能是合理的,这正是我们与“抽象继承说”的重大区别之一)。
众所周知,道德作为人类自我提升的方式,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都要从社会存在中汲取生命养料,故,其内容总是具体的。说道德内容总是具体的,这不仅指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内容,还指即使在同一历史阶段或基本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对善恶有不同的具体规定。不仅如此,甚至那些维系人们社会交往、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具有全人类因素的道德要求,那些貌似超越利益对立而适用于不同利益集团的道德要求,一旦到现实生活中被赋予现实内容后,也会表现出明确的阶级内容、尖锐的利益对立(譬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同的“仁”、“义”规定赋予它不同的善恶标准与价值取向。革命者可以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下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为正义、进步事业,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同样,那些统治者及其鹰犬,那些法西斯分子也可以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下,为维护落后腐朽的政治统治及其社会秩序而拼命)。道德的内容总是具体的,并随时代、阶级、利益集团的变化而具有极大的差异甚至根本的对立。在存着利益对立的社会,没有普适、超阶级的道德要求,道德内容是具体的,故也是暂时、变动的。正由于此,恩格斯才深刻揭示:在道德领域里,“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才高度肯定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的思想。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对那些奢谈空洞抽象的爱、人性等资产阶级思想家予以无情批评。
道德的内容是具体的,故尔它总是暂时的、流动的、易逝的。然而,暂时、流动、易逝中总是存在着永恒、稳定,在这千变万化的具体内容背后隐藏着人类精神的灵魂,这就是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对人生的严肃态度,就是对人之为人的追求。这种追求、责任、义务、态度在社会历史中可以有多种表现样式与具体内容,甚至有可能以幼稚、愚昧、悲剧乃至恶的方式存在,但它们却是对人之存在意义深刻内蕴的昭示,是人类文明宝库的瑰宝。这恰恰正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人类世世代代值得光大的。
康德的道德哲学思想对我们似乎是颇有启发的。康德以自由意志、实践理性、绝对命令等道德思想著称。康德以为自由意志是人的质的规定性,人应当不作任何计较为义务而义务。康德的旨趣是抓住人的崇高性、道德的圣洁性,人作为自由意志存在,对社会具有责任与义务,这种责任与义务如此神圣犹如是上帝的律令一样,他抓住了崇高的义务与责任这一道德的核心。人首先应当具有崇高的义务与责任感,然后才谈得上在具体时空条件下具体履行义务、责任的问题,离开前者,后者就失去原则与灵魂,成为水月镜花。康德的这种思想有点类似于孟子讲男女之“礼”(男女有“礼”应避讳,但对溺水之兄嫂又当救之),令人感悟。黑格尔在评价康德的义务论思想时认为,康德将义务与自由意志相统一,提出义务与理性应符合一致,这是康德思想的卓越之处,同时,他又不满足于康德为义务而义务这一形式的同一,要求进一步探究这义务究竟是什么,探究义务的具体内容,因为,“善作为普遍物是抽象的,而作为抽象的东西就无法实现,为了能够实现,善还必须得到特殊化的规定。”在笔者看来,黑格尔对康德义务论思想的这个评价虽是合理的,但却不是完整的。关于义务的大致线条应当是:在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中形成的道德要求凝结为义务——义务由于社会物质生活过程本身的力量,以及在世代流传中积淀为民族精神而获得神圣性与崇高性,人们应当拥有崇高与神圣的义务与责任感——义务的履行形式是多样的,即虽然原则是抽象的,但实践形态则是具体多样的。康德抓住了或者说体悟到了义务的神圣性,却没有合理揭示这种神圣性的来源;抓住了人之为人应当有崇高的义务与责任感,却没有进一步明确揭示义务实践内容的具体多样性。不过,关于义务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没有康德就没有黑格尔,甚至康德比黑格尔更深刻、更重要。没有崇高的社会义务、责任心,就不可能有善的道德实践,也无须对义务作进一步具体内容规定。黑格尔的思想是以康德义务论为前提并对其作了进一步深化。对于人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要有崇高的社会责任心与义务心,这是人的善的性质的确定性。至于履行义务的个体实践形态问题,当然也很重要,但这更多的是善的实践能力问题。道德并不能事先告知人们在个人场景中究竟该怎么做,道德是生活的智慧而不是机械的教条。
康德义务论思想中对义务的解释是唯心的,但他所包含的价值与意义却是深刻的:人应当不作得失计较担负起对人类与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人应当有崇高的责任感与义务心,这种思想尽管如黑格尔所说是形式的同一,但却相当深入地接触或者说揭示了道德的核心,揭示了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本质与核心。这种对人类与社会的责任与义务,这种对人生价值的严肃态度,是人类在世代自我提升过程中逐渐从丰富表象、具体内容中提炼、升华而成的稳定的精神结构,这种精神结构由于它与物质生活联系环节的复杂性、历史的久远性、心理的积淀性,似乎是远离现实、形式的,但恰恰是具有丰富内容、本质的,它是扬弃了具体存在内容杂多性、关于事物本质普遍性的内形式。在这里,形式是深刻、普遍、稳定的,内容却是表象、具体、变易的。
这里有必要对内形式作进一步阐释。严格地讲,形式有内、外之分,外形式是事物存在的表象,它丰富多样同时又变易不定,与事物的质没有必然的内在一致性。内形式则是事物存在的结构性要素整合方式,用康德术语表达就是“范型”。道德作为实践理性,则是人类在物质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提升的方式。如果说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本内容的实践是人存在的基础及其本质力量的确证,那么,道德则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精神规定。道德的进步过程,是在社会物质生活方式进步基础上人的精神解放、获得自由之过程,是主体性的文化——心理构建之过程,道德的内容确实是具体的、历史的,但它们却时过境迁、流逝承转,世代积淀留存为人的主体能力与心理结构。道德在世代的历史过程中,意识演化为无意识,理性深沉为感性,内容嬗变为形式:人之为人具有神圣的使命与崇高职责。这种职责最抽象、最缺少具体规定性,但却使人无时无刻不感到做人的资格、尊严、自豪,无时不刻不感到它的神圣与令人敬畏,无论何时何地作为人履行这种义务、职责是无条件、至上的。正是这种义务、职责,人们虽然往往难以言说,但却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它的存在,并从中寻找生命存在的意义,虽然这种义务、责任极其抽象,但它却成为人们近乎本能的行为范型。这种义务、责任是最抽象的但却又是最充实的,它是形式的但恰恰同时又是最富有内容的,它是内容的灵魂。这种内形式,是人类文明的最深刻、最珍贵财富。今日世界其实并不缺少义务与责任,缺少的正是义务、责任的灵魂;今日世界人们对义务、责任的规定、解释可以说到了难以再具体的地步,——任何人都可以在义务、责任之神圣名义之下为所欲为,但缺少的恰恰是对人类存在、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这一最简单、最抽象、最普遍的无尚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内容是杂多,(内)形式是纯粹。
继承形式、舍弃内容,就是说要继承传统道德中世世代代流传积淀而成的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义务感,对生命价值的严肃态度,要有博大胸怀、高尚情操、优美灵魂。传统道德的任何具体内容都有具体时空限制,都是相对有限的,此处为善很可能彼处为恶,而传统道德中所隐含的那种崇高责任与义务感,那种对生命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孜孜追求,以及它所体现出的博大胸怀、优美灵魂、高尚情操,则是人们应当永远光大的。对生命存在意义与价值的严肃认真态度,对人类、社会、人民的神圣义务与责任感,这是道德具有永恒魅力、放射耀眼光环之所在。
继承(内)形式、舍弃内容,就是把握了传统道德乃至人类道德的灵魂,就为对传统道德内容的进一步具体分析、具体继承奠定了价值基础与合理前提(这也是我们与通常“抽象继承说”在方法论上的原则区别之一)。
二、破除体系 继承内核
舍弃内容、继承形式,关键的是在高扬对人类、社会、人民的义务与责任,严肃人生价值、生活态度基础之上,打碎传统价值体系,发掘传统道德中的合理颗粒,诠释创新,赋予新的内容与含义。
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是传统道德的最本质内容。首先,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是对传统时代社会存在方式、道德关系的最深刻、最完整的把握与揭示。犹如黑格尔的庞大哲学体系表达了黑格尔对存在、世界、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完整认识一样,任何一种道德价值体系总是以体系这一完整的方式表达了它对那一时代及其道德关系的认识,表达了它的基本道德价值指向与要求。就传统中国道德而言,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之上、以血亲家庭关系为核心而构建的纲常伦理道德体系,传统道德的价值指向与规范要求均纳入血缘家族纲常关系体系之内。正是这种血缘家族纲常关系体系一方面决定了传统道德的基本特质,另一方面决定了它与现代道德的原则区别。建立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传统道德体系没有也不可能引导国人向现代道德体系转化(李约瑟所要解开的中国古代灿烂科技文明与近代以来科技落后原因之谜,可能离不开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其次,传统道德体系决定了传统道德成份的价值性质。传统道德中的任何具体道德成份最终总是被纳入这种纲常体系内并从这体系中获得自己存在的具体规定,即使是那些在今日看来带有全人类因素的道德要求,孤立地看似乎具有普遍性品性,但是在传统时代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之下,它们也不可避免地被传统价值体系所规定,并成为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给这些具有全人类因素的道德要求带上了沉重的桎梏、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另一方面又要使它们往往沦为统治者的奴仆(以“忠”、“孝”为例,平心而论,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没有“忠”、“孝”,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孝敬长辈,这是人类得以延续发展的基本美德。尽管在传统时代于传统道德之下我国历史上曾涌现了相当多的志士仁人,留下了令后人仰慕的精忠报国、谦敬孝亲的情操品行,但是从根本上说,“忠”、“孝”仍未跳出血缘家族纲常伦理之巢穴,甚至相反还进一步强化了这纲常伦理体系的社会功能,成为奴役人民百姓的工具)。任何价值体系中的具体组成部分,它所揭示的道德关系与伦理要求,就其本身而言,总是局部的,其善恶性质甚至会向对立面转化。传统时代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决定了传统时代一切道德因素的基本价值特质。
价值体系是道德性质的依据,特定时代的价值体系服务于特定时代及其存在方式。虽然传统时代中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道德要求,这些道德要求甚至可能互相矛盾对立,但是,它们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作为血缘宗法存在关系的反映,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总是不可避免地受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制约。在传统道德体系之中,确实存在具有某种普遍、永恒价值的颗粒,但要使这些颗粒重新放射光芒,必须首先打碎加于其上的枷锁,破除其赖以获得善恶性质的价值依据。
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不是体系的,而是某些成份的。由于这些成份在传统时代的传统道德体系中有特定内容,因而这些成份就不能被今人简单拿来,它们必须被诠释。诠释就是批判,就是创造,就是在新的道德体系之下,赋予其新的内容与含义。简单地说,就是接过范畴、要求、命题,重新赋义(在这个意义上,以往人们所说的“抽象继承”也并非一无所是)。这种诠释是道德批判与继承的统一,是价值要求连续与中断的统一,是情感的一贯与升华的统一。诠释本身是件极其艰巨的工作,它可能是渐进的也可能是急骤的,但不管如何,它决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的,决不是蹈古人之履而是拓今人之路的。
韦伯对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兴起中作用的研究,虽然在许多地方可以值得进一步讨论,但他所揭示的新教伦理运动对传统宗教的某种新的阐释事实上为资本主义精神生长寻得了一块产床的基本思想则是中肯合理的。宗教的禁欲主义、天职经过新的阐释摆脱了它那消极无为性,获得了开拓创造性,禁欲主义精神事实上成为封建宗教道德向近代资本主义道德转换的中介、桥梁。恰如韦伯借用约翰·卫斯理的语言所表达的: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运动由“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经济人”取代了“朝圣者”。西季威克曾站在功利主义立场对既有道德要求及其体系似乎表现出了明显的维护,但仔细品味他的真实思想,他想表达的实则是对既有道德要求的批判取代应避免社会的失范、动荡,其中就包含着通过诠释而实现这种过渡、在连续中实现中断的合理成分。道德的发展同历史的发展一样,均是中断中的延续,延续中的中断。诠释是道德发展方式之一,道德发展不唯是诠释的。
破除体系、继承内核,就是在对传统道德质的否定基础上,具体分析其中有关成份,具体继承。借用傅伟勋先生的术语,就是在搞清“实谓”、“意谓”、“蕴谓”基础上,确立其“当谓”、“必谓”。没有这样一种对质的真正否定,没有这样一种剔除与诠释,对传统道德的继承批判就难免虚无主义或盲目照搬。值得指出的是,对传统道德某些内容的诠释性的创造工作,应当建立在破除其道德价值体系基础之上,如果这种诠释发生在传统价值体系尚未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之时,那么,它虽能起到批判继承作用,但这种批判继承的总体上仍未超出传统改良的范围。宗教改革运动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价值批判与构建的命运均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无论是舍弃内容、继承形式,还是破除体系、继承内核,都有一个立足点问题,都有一个价值依据问题。没有一个合理的立足点与价值依据,对传统道德的扬弃就难以实现。
三、立足现实 中西合璧
对中国传统道德扬弃的前提是存在一种作为扬弃依据和如阿基米德所说的那个支点,人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是,或者从现代西方价值体系或者是从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寻求这个支点。笔者以为这两种思维方式均不可取。它们存在两大基本缺憾:a、陷入“体”、 “用”之分的僵化思维模式;b、以理论而不是实践作为最终依据, 因而总是不牢靠的。
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扬弃,事实上存在着双重任务:传统道德现代化,外来文化本土化。这双重任务的交织使得对扬弃的支点的寻找必须跳出简单的“体”、“用”之分思维模式,不能简单地说以“西学”或“中学”作为指导这种扬弃的价值支点之“体”。对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应当寻求坚实的价值批判支点。
在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面对社会动荡不已、列强入侵、西方文化冲击,一些人首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近代中国价值体系构建方式。虽然这只是主张在原有价值体系框架内的非根本性的改良,但是应当承认,相对于“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极端守旧思想毕竟是个进步,为认真学习研究西方价值思想开了一丝门户,同时亦为保留传统优秀价值观念提供了某种前提,这是近代中国为解决传统观念近代化、外来观念本土化问题而作出的一种有意义尝试。然而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因为这种“体”、“用”模式是要将西方的某些价值观念嫁接到中国传统礼教价值体系之上,而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交流、整合决非简单嫁接之事,这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它涉及不同文化形式、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交流、整合需要极强极深刻的理性能力;另一方面,在当时它又与民族救亡图存直接连在一起,民族传统、民族精神上升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又使得上述价值批判、交流变得极为复杂(这样一些复杂的矛盾就必然在人们思想深处引发出所谓“体”、“用”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体”、“用”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敏感十分复杂的问题,若对“体”缺乏一种科学的把握,很可能成为或者是固守原有价值体系、或者是全盘照搬外来价值体系的代名词。就理论上说,近代的“体”、“用”之分价值批判模式存在两个致命缺陷:a、不了解在不同民族文化价值碰撞背后, 隐藏着代表两种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价值体系的尖锐冲突,而这两种价值体系又由于各自的历史内涵注定了彼此不能简单融合、嫁接;b、 以传统儒学礼教为价值体系之母体,吸取某些外来价值观念,一是这些价值观念在这母体中必然被扭曲,一是既有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将会保持不变。自鸦片战争以后,“体”、“用”之争一直不断:“中学”为体抑或“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抑或“西学”为用?其实质是或者将西方的某些价值观念嫁接于传统礼教价值体系之上,或者是以外来价值体系取代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其实,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这种“体”、“用”之分的提出问题的方法就不合理,东、西学不是简单的“体”、“用”之关系。
西方外来道德价值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对传统道德扬弃的价值依据,即“西学”不能为“体”。对此最值得认真考虑的反对意见有二:a、 西方社会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向后现代化发展的社会,现代化的这种发展走向是不可抗拒的,故对于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的中国来说,应当以代表了现代化发展方向的西方道德价值体系为价值批判座标; b、作为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之上的西方道德价值体系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是不同层次的,有质的区别,应当以前者为支点批判扬弃后者。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详细讨论非本文所能容纳,在此只择其要言之。第一,西方价值体系与价值观点这是虽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西方价值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庞杂的复杂问题,有待从诸多主义中甄别选择、剔除提炼。西方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一样,都是人类自我提升的产物,拥有某种全人类性的因素,但是这种全人类性因素决不是其体系,而只是其中某些要素。体系由于是那个民族在那个时代对社会存在的总体把握,因而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事实上迄今也尚无国人明确是原封不动、点点滴滴照搬西方价值体系的,人们提出更多的是诸如民主、自由、平等这样一些具体价值要求,但这里同样存在着打破体系、取其内核的问题。第二,就经济发展历史形态看,西方发达国家确实处于先进地位,基于现代大工业基础之上的价值体系的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内核也确实比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体系中的宗法、血缘、等级等价值内核优越合理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矗立其上的社会价值体系自身就是值得我们照搬的。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与社会形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并非如此一一简单对等,另一方面,与这种比较先进的经济发展形态相适应的积极价值要求又是与其它那些消极、颓废乃至靡烂的价值要求混杂一起。至于说西方价值体系的个体本位、对个性的解放,虽优越于血缘宗法整体本位、对个性的压抑、吞噬,但在历史过程中看,前者仍然是发展的中介,仍然是要被扬弃的,何况它内孕着人们已普遍注意到的不可避免的消极性。第三,更重要的是西方价值体系是西方那种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民族个性特色,是西方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因而这就直接引发出两个问题,一是民族情感问题,一是合理的、全人类文明价值财富存在的民族个性问题。以西方价值体系为价值判断依据,即使姑且不论理性上是否合理,在情感上,由于它缺少东方民族历史与文化之根,故就必然带来民族心理、民族情感、民族精神上的深层问题。即使是那些包孕在西方价值体系中的合理价值要求,也有个中华民族具体存在方式问题。这就恰如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学说也不能照搬中国,必须与中国历史、文化、现实相结合,变为活的存在才能为中华民族接受一样。即使是人们孜孜不倦执著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精神,仍然存在一个在不同民族中不同表现形式的问题(打个不恰当比方,犹如房子都须有墙与顶,但不同民族的生存环境、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因素则使不同民族的房子结构有不同的风格一样)。
“西学”不能为“体”,“中学”亦不可。这里关键的是对“中学”本身的理解。若是传统道德,则本身就是要被扬弃的。唯一值得考虑的是当代中国道德价值体系。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确实建立了一系列道德行为原则规范,初步孕育出一种新的价值原则及其体系,这种价值原则及其体系也确实塑造出一大批令人仰慕的新人。不过,中肯地说,这种原则及其价值体系经历几十年实践,尤其是近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能够凝聚人心的社会价值体系,应当是既立足于市场经济实践又有理想前导性的。我们曾经拥有的道德价值体系也在这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经受锤炼。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暂时失范、混乱现象,软、硬分离两张皮状况,均严肃地表明居于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的道德价值体系正处于一个新的发育、生长阶段,它正认真地从生活、实践中寻找自己存在的依据及其生动内容。
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价值体系,其自身并非是存在的终极理由,它们自身必须从活生生的生活中获得存在的辩护,生活存在本身才是一切价值批判的最终依据。因而,对中国传统道德扬弃的终极依据就只能是当代生活实践,即,若一定要说有“体”的话,此“体”在根本上就不是理论、观念的,只能是生活、实践的,这就是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体”,相对于此,一切思想观念均是“用”。既然如此,对传统道德扬弃的价值支点、依据就只能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这不是说对传统道德的扬弃不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而是说,用以指导我们思想、行动的理论、价值尺度必须在实践中经受进一步检验、丰富与发展,在变革社会人生的现实实践中,使社会人生及其指导价值体系均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发展。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所给予我们的最珍贵财富之一。这样,对传统道德的扬弃,实质上就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批判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积极思想财富的主动价值构建过程。
立足现实,突破“体”“用”之分的思维框框,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立足现实、中西合璧构建当代中国的道德价值体系。中国的道德传统更多立足血缘家庭整体,关注于身心性命,探究存在的价值,西方的道德传统则更多的是立足个体权利与自由,关注社会伦理,而这两者都以各自的方式发展了人类发展着的道德的某一方面,两者在当今社会都存在着彼此交融统一的任务。这样一种实现二者辩证统一的道德应当是当代人类道德发展的最高类型。
对传统道德的扬弃过程是一个主动价值批判与构建过程,而非自发过程。这里尤其要注意防止几种思想倾向:
a、以为对传统道德的扬弃,主要是理论上的批判、学者的工作。 其实,新的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的确立是新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确立的最终依据。两种道德价值体系之间的批判、取代,根本上是两种物质生活方式之间的批判、取代,新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形成与确立,不纯粹是理论上的批判、建树,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批判建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时代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最深刻内容,也是当代中国扬弃传统道德构建完整新价值体系的最深刻经济与历史依据。当代对传统道德的扬弃、新价值体系构建过程中出现的暂时迷惘、混乱乃至失误,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对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洞悉,一方面更需要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其运行秩序。改革的倒退与停滞都是没有出路的。
b、以为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就能自发地否定传统道德,建立起完整的新价值体系。其实,市场经济建设只是为对传统道德扬弃提供了现实物质前提,但是,第一,恰如笔者曾指出的市场精神不等于伦理精神,市场经济自身并非是善恶判断的可靠依据;第二,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的道德价值选择,必须通过从事现实活动的人的积极严肃的人格批判、积极崇高价值目标的设定来实现,必须在科学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指导下的自觉价值批判来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放任形成的价值观往往是腐朽没落的,这已为我国近年来的实践所证明。
c、以为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个体主体地位及其积极性与创造性, 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恰恰缺少的是对个体精神的弘扬,因此,应当大力弘扬个体精神。确实中国传统道德中缺失个体精神,甚至存在压抑乃至吞噬个体的极端,市场经济也确实要求一定的个体积极性与创造性,呼吁一定的个体精神,但是,个体精神并非绝对就是善的,个体精神具有二重性,因此,对个体精神的弘扬应当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应当警惕由于对个体精神的弘扬而导致的对传统道德的极端否定,麦金太尔对西方近代以来伦理发展倾向的批判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应当警惕在对传统道德批判的同时毁灭我们世代流传下来的珍贵德性精神。
批判就是继承,扬弃就是发展,批判、扬弃的方法就是发展的方法。传统道德是不能被置之不理的,在传统道德中作为民族精神而存在的神圣社会责任、义务、使命意识,严肃的人生价值追求,正是当代中华民族发展的价值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