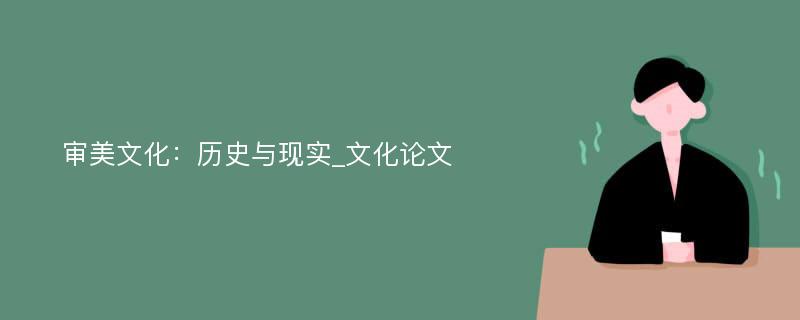
审美文化:历史与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审美文化”概念的历史,应当追述到席勒在1793-95期间撰写的《美育书简》[1]。在这部著作中,席勒首次提出了“审美文化”概念。产生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是现代性启蒙运动在欧洲的深入发展。启蒙运动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以新兴学科独立为标志的现代文化的分化,另一方面导致了在欲望原则和理性原则的双重压抑下的现代人性的分裂和创伤。文化的分化使审美文化的确立成为可能,而现代人性的分裂和创伤又需要审美文化成为一种统一的机制和医疗手段。席勒正是在这两个前提下提出“审美文化”概念的。
文化分化是文化现代性的基本标志之一。美学学科的独立和系统化是现代文化分化的重要事件。从鲍姆加通命名“美学”并且确立美学学科体系,到康德在其哲学系统中明确划分认识、伦理和艺术(知情意),不仅使美学从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独立出来,获得独立性和系统性,而且使艺术摆脱长期以来作为宗教和政治附庸的地位,获得了以自身为根据的自律性。康德给艺术确立的自律原则是,审美的无利害感,形式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如果说学科分化是现代文化的标志,那么,艺术自律性的实现,则是现代文化非宗教化,即世俗化的标志。文化的分化无疑适应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知识和财富的无限积累)的需要。但是,文化的分化是以人的感性与理性统一体的分裂为基础的。因此,在文化的分化中包含了现代文化对人性统一体的创伤。这种创伤表现在两个方面:由于感性与理性的分裂,现代人一方面重新成为失去理性统一法则,完成听任于感性欲望冲动的原始人,另一方面又成为被剥夺了感性需要的完全受控于理性原则的野蛮人。
席勒的思想,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继承了康德的艺术自律原则。但与康德强调知情意三分不同,席勒坚持这三者的统一。他认为,理想的人(完整的人)是知情意完美结合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包含着三种协调的基本冲动,即以自然原则为基础的感性冲动,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的形式冲动和以审美原则为基础的游戏冲动。这三种冲动,形成三种文化状态:自然状态、道德状态、审美状态。席勒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承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在道德状态中人的自然(本性)被理性法则支配。这两种状态都是人性受强制。审美状态是自然状态和道德状态的结合,一方面它消除了自然的偶然性,另一方面它消除了道德的强制性。在审美状态中,人达到感性和理性、形式与自由的统一。因此,只有通过审美状态,人才有可能成为完整自由的人,同时,也只有完整自由的人,才能真正进入审美状态。
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席勒提出了“审美文化”概念。根据席勒,审美文化是与道德文化、政治文化相对的一种文化。这三种文化分别以审美状态、道德状态和政治状态为基础。席勒认为,现代社会发展使人性分裂和伤残,文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使人在纯自然状态生活中也服从于形式,即使远离美的王国的时候也成为审美的。而这正是审美文化的职能。因为审美文化使一切事物服从美的法则,在其中,自然和理性的法则都不能约束人的选择,并且审美文化把给与外在事物的形式赋予内在生命。明确讲,在审美文化中,人以美的形象(活的形象)为感受对象,并且以自由想象的关系与之游戏,因此,人一方面摆脱了对自然物的实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摆脱了道德或政治原则的强制性,进入想象力对形式的自由游戏。所以,席勒一方面把审美文化作为实现人类理想文化的基本途径,同时又把审美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境界。在《书简》最后一封信(第27封信)中,席勒直接提出了“审美王国”的理想,这是“审美文化”观念的扩展,实际上是试图用审美文化统治、同化道德文化和政治文化。
席勒坚持的核心是现代文化启蒙的社会理想:人性的完整和自由。但是,他所奉行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使他的理想找不到现实的基础。审美文化能否最后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席勒也没有把握。在《书简》结尾,他自问:但是美的国家是否如其显现的一样真正存在呢?他的回答是,作为一种需要,它存在于每个优美的心灵中;作为一种成就,它只存在于少数精英的圈子中。可以说,席勒的审美文化是理想的精英文化,他把这种精英文化作为对社会大众作自由启蒙的基本途径。
在席勒之后,18世纪中期,英国文化学派的中坚人物,马修·阿尔诺德发展了这种文化的精英主义立场。他在于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一书中,明确主张,随着现代机械文明的发展,技术的提高和物质的丰裕,带来的是社会文化的堕落和无政府状态。边沁主义的享乐原则支配了文化观念,结果是“工人阶级也开始获得和使用随心所欲的英国式人权”。与席勒一样,他认为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完善人性。他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文明完全是机械化的,外在化的,把人带向无止境的更多的欲求之中,因此,文化完善人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就更加重要。阿尔诺德直接把文化定义为“文化就是通过学习迄今为止人们所想到的和所说出的、最美好的东西而实现自身的完善的活动”。在这个定义下,他给文化做出了这些规定:愉悦的、明丽的、非功利的,以完善为目标,对于人的心灵是内在的,并且具有普遍的社会性。他特别强调文学的文化价值。因为文学比其他文化形式更具有心灵性和精神性[2]。阿尔诺德也与席勒一样,认为这种理想文化的实现,只是少数文化精英的使命。他认为,这些文化精英是尚未被机械文明毒化的剩余者。他们不是以特定的阶级精神,而是以普遍的人类精神为文化的基本取向。
很明显,阿尔诺德的文化观是席勒审美文化观的继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稍后的斯宾塞把阿尔诺德所主张的文化称为“审美文化”[3]。但是,两人各有侧重。席勒倡导审美文化,主要在于反对资本主义道德文化和政治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和伤害;阿尔诺德倡导美的文化(审美文化)主要在于反对现代机械文明对人性和文化的侵袭。进入20世纪以后,F.R.立维斯发展了阿尔诺德的反机械文明的文化思想,把它用于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在他和D.汤普森合著的《文化与环境》一书中,立维斯尖锐地指出了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机械性文化,其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模式,破坏了人与自然、民间性和内在性之间的联系,“它损害的是一个有机社会的健康机体以及这个社会体现的生动的文化”。在阿尔诺德的路线下,立维斯也主张用精英主义的审美文化来抗拒机械文明的大众文化[4]。
从席勒到立维斯,都坚持审美文化的理想原则和精英意识。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这种审美文化观,根据在于文化分化之后的艺术的自律性。如果艺术的自律性根本就不成立,或者说,即使在理想的文化环境中,艺术的自律性可以成立,但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中,这种自律性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破坏,那么,以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为基础的审美文化观还能否成立?明确讲,在现代历史发展中,审美文化能否实现,在现实中的审美文化又是否符合席勒诸人的理想观念?
在这里,我们就要涉及到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这种文化批判理论仍然以文化与机械文明的对立为理论前提。但是,从其理论先驱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2)到中坚人物阿多诺的《审美理论》(1969),文化批判理论都坚持马克思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是两个观念,一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整体观,即把文化看作社会意识形态的整体表现;二是经济决定论,即从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历史展开来阐释文化的发展。马克思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韦伯的“理性化”,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等系列概念,揭示了文化从作为人的自我解放力量到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意识形态的退化演变。用阿多诺的观念来讲,文化的否定性功能被生产的商业和技术体制所整合了——文化变成了异化现实的肯定的意识形态。
与席勒、阿尔诺德诸人的文化理想主义的乐观意识相反,文化批判理论是悲观的。这种悲观意识基于这样的认识,即文化艺术的自律性必须以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个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为基础。但是,正如卢卡奇一开始就指出,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个性一方面被商品生产赋予前所未有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被商品生产所建立起来的物化所取消(《历史与阶级意识》)。阿多诺更明确地指出,“个人独立的过程是商品交换社会的一种功能,终止于个人被一体化所毁灭。”(《否定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商品生产需要个人的独立,但是普遍交换必然取消人的个性价值,使之物化为商品。在这个普遍的物化历史中,是不可能期望文化艺术的自律存在的。在《审美原理》中,阿多诺一开始就指出,“随着社会越来越非人化,艺术就日益失去它的自律性。艺术这些曾经充满人性理想的基本成分已经丧失了它们的力量。”[5]
对于文化批判理论,艺术自律性的根本丧失,是现代文化状态的主要根源。阿多诺诸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揭示大众文化的非文化(工业化)实质的。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的实质不在于它的内容平庸或趣味低俗,而在于它的工业化生产模式。“文化工业”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启蒙辩证法》(1947)的定稿中,它代替了初稿中使用的“大众文化”概念。在他逝世前撰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阿多诺解释说,之所以用“文化工业”来代替“大众文化”,就是为了纠正和杜绝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即大众文化是从“大众”中自发产生的一种“流行文化”。正相反,大众文化是根据市场需要,以标准化和制度化模式生产出来的文化工业产品[6]。简而言之,“文化工业”概念揭示了大众文化是被技术-经济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整合的变化,在根本意义上,它是非自律的文化。
文化工业的整合力量对于现代文化具有整体意义和普遍意义,在它整合流行性的大众文化的时候,它也整合了非流行的精英(先锋)文化。就艺术而言,在现代文化运动中,无论高雅艺术还是通俗艺术,都被整合在现代生产运动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起支配作用的是普遍交换原则,准确讲,是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统治。在普遍交换原则的支配下,康德为艺术确立的自律原则(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逻辑中。阿多诺认为,当流行艺术直接认同文化工业的价值原则,以媚俗的姿态进入大众市场的时候,严肃(先锋)艺术坚持自律原则不过是一个假象。事实是,严肃艺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变成了它取得商业优势的特殊策略,通过这个特殊策略,严肃艺术把自身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商品:它以无目的性否定商品利益原则的目的性,但同时,它的无目的性又是对商品交换原则在终极意义上的无目的性的肯定。也就是说,它以否定的形式肯定了商品的绝对性。所以,文化工业填平了精英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的鸿沟,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不是对某种特殊文化的指认,而是对工业化的现代文化整体的指认。它指认了现代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即现代文化丧失了它对现实的超越的、否定的功能。
阿多诺认为,文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不仅要使自身适应人的需要,而且同时总是要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物化关系提出抗议,从而恢复人的荣耀。一旦文化完全被同化和整合在物化关系中,人类生存的内在性就瓦解了。文化工业型的文化产物,不仅在附属的意义上也是商品,而且彻头彻尾只是商品[7]。在文化工业的时代,席勒和阿尔诺德所理想的审美文化丧失了人类理想的价值——文化工业把它变成了文化商品。今天,不是缺少席勒所呼吁的对美的形象的需要,而是这种需要已经变成了日常的消费欲望;也不是缺少阿尔诺德所要求的愉悦精美的文化产品,而是这些产品以现代技术才能创造的辉煌景观充斥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席勒和阿尔诺德都相信审美文化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和完善,因为席勒认为形象是人的自由的作品,阿尔诺德则认为真正的美的艺术是深入心灵的。但是,现实却是,生活的审美化,同时就意味着文化艺术的商业化和人的内在性的消解,而自由也随之泛滥为无限制的消费-享乐欲望。可以说,审美文化的现实展开,不仅没有实现席勒向往的人性的完整和阿尔诺德所追求的对机械文明侵袭文化的抗拒,相反,是人性的日益分裂和畸形,是机械文明对文化的全面整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反对以康德美学为基础的审美文化观念。他认为,审美文化,即生活和文化的审美化,是双重的自我异化:一方面,审美文化的无目的性(无利害感)原则的实现,不过是自我从现实生活(政治和经济)的边缘化和异化;另一方面,这种无目的性的自我异化又进一步肯定了现实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审美文化对于以工业革命为核心的进步文化是一种否定,但是,这种否定是抽象的否定,它必然要转向它的否定对象。在文化工业时代,艺术不可能在它所反抗的现实世界之外占据一个优越地位。“艺术的反抗因此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同化于它所反抗的对象。”为了在这种悖论中保持艺术的抗拒力量,艺术所坚持努力的不是对现实的审美化虚构,而是对现实的反审美的陈述。所谓反审美的陈述,即征用死亡意象,采用碎片话语。现代艺术先天地倾心死亡。阿多诺说,在今天,如果艺术是可能的,它就必须走到文化的边缘,介入野蛮领域。艺术的基本职能是保护生命,抵抗死亡;但是当它履行职责的时候,它不得不与死亡联盟。“只要追寻艺术的可能性,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希望在死亡中,这是必然的代价。”[8]
在中国,审美文化概念的真正引入,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于金亚娜等学者对前苏联美学的译介,尽管席勒美学的译介远早于此。这一概念之所以如此迟缓地进入中国美学界的视野,原因在于:其一,此概念即使在西方美学界,也不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概念。特别是战后,随着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影响,审美文化逐渐由一个肯定性概念变成了一个否定性概念,并且作为过时的审美主义的乌托邦观念被置于批判和拒斥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概念。其二,在80年代后期以前,文化,尤其是“作为问题性的现代文化”,还没有进入中国美学界的意识,它当时关注的是“美的本质”等超现实的形而上学问题。只有到了80年代后期,由于国内现代化运动深入展开,更由于进一步与海外世界沟通,文化的现实问题的压力所逼,中国美学界才真正开始有了“文化”意识。“如果文化成为我们的理论问题,只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问题。”[9]
前苏联美学具有两个理论基础,一个是由康德开始而由黑格尔完成的德国理想(浪漫)主义美学,一个是革命化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美学。而这两个美学理论都是前20世纪的文化理论,它们的政治性揉合决定了前苏联美学具有革命浪漫主义和审美乌托邦的双重色彩(见前苏联《简明美学辞典》中译本“审美文化”辞条)。带着这种双重色彩,在前苏联美学体系中,审美文化概念并不具有对20世纪,特别是战后文化、艺术的具体意识和针对性。中国美学界对审美文化概念的初步使用,无疑深受前苏联美学的影响。其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想主义地使用审美文化概念,把审美文化作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文化乌托邦;二是泛化地使用审美文化概念,把这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概念泛化为一个泛指所有人类审美-艺术活动的概念。
审美文化经历了从理想到现实(观念到生活)的历史演变。要正确地使用这个概念,首先必须对其历史演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当代文化现实的清晰认识。泛化地使用审美文化概念,将导致这个概念的抽象化,最终成为一个无意义(无独特内涵)的概念;理想主义地使用审美文化概念,将使这个概念的所指成为纯粹的经典文本观念,而不能触及当代文化的现实。特别要指出的是,理想主义的审美文化观念,基于启蒙文化的精英主义立场,必然排斥大众文化。这种排斥,忽视了审美文化的大众文化演变。但是,这种排斥的现实效果却是适得其反的。它产生两个背反的结果。其一,它的精英意识为大众文化的文化操纵提供了理论口实——它实际上为大众文化的明星体制作美学辩护;其二,它的审美主义的乌托邦使大众文化的唯美主义运动变成关于人性理想的堂皇叙事。文化批判理论揭示了这一事实,即席勒和阿尔诺德寄予厚望的自主的“精英”本身变成了被动的“大众”:大众传媒操纵的对象。文化工业的虚幻性就在于在大众中维持“精英”的幻象。理想主义的审美文化观念,由于它以“精英”作为基本话语,必然强化而不是削弱这种幻象。
在历史与现实结合考察中,对审美文化应当确立这样的基本认识:一、承认审美文化的现实性,即审美文化是当代文化生活的现实;二、同时承认审美文化的非理想性演变,即生活的审美文化是对审美文化理想的否定性展现。因此,在当代文化艺术研究中,坚持审美文化概念和否定性地(批判性地)使用这个概念,是真正积极的文化立场。这种立场的积极性在于,它同时反对审美主义的乌托邦和文化虚无主义——它在对人类生命的真实关怀中建设人类生命的意义,它是对当代文化的批判性重建。
注释:
[1]席勒《美育书简》,英文版(Thoemmes Press,1954),第10、21、23信。
[2][9]见安帝欧·米尔勒《当代文化理论》,英文版(UCL Press,1994)第22-23、4页。
[3][4]见滕守尧:《大众文化不等于审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5][8]阿多诺《审美理论》,英文版(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第1、357页。
[6][7]《新德国评论》(New German Critique)第6期(1975)。
标签:文化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美学论文; 文化工业论文; 阿多诺论文; 席勒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人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