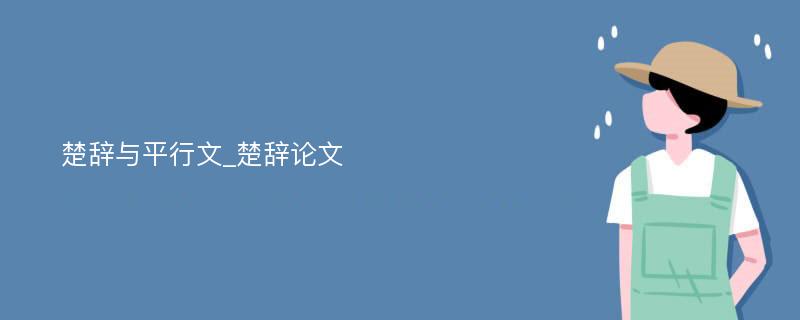
楚辞与骈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骈文论文,楚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1)04-0063-05
一、骈文与赋体文学的关系
骈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类,只有在汉民族语言的特定基础上,才能产生出这样的文学体裁。它或有韵或无韵,与中国古代的韵文、散文构成复杂的交叉关系。
骈文作为体式的边缘性源于其内涵的驳杂。李兆洛《骈体文钞》包括31个子类,大凡铭刻、颂扬、哀诔、诏书、书论、碑志、连珠、笺牍、杂文等等,除诗赋外,只要是以骈对为主,即全归入“骈文”之中。孙梅的《四六丛话》虽有所精简和变化,也仍有19类。可见无论是实用性的还是审美性的文章,都有可能成为骈文,其入选的标尺便是骈对句法的运用。那么这里的“骈文”,更多地指向一种语言艺术的运用方式,其体类的含义非常轻淡,因此不会与骚、赋、表、启等文体构成一种纯粹的并列关系,而往往是互容交叉的了。
要将骈文与上述其他文体截然分开,是十分困难的,但它与骚、赋的区别却不但可行,而且必要。以往有不少研究骈文的学者,把骈对的赋也视为“骈文”,这很容易加剧文体分类的混淆。笔者认为,部分地运用骈对的句式,只能说是一种修辞手法,与正规、纯粹的骈体文是有区别的。这不仅表现为骈句数量的多寡,而且还表现为一种创作时的骈对意识,以及这种创作意识在那一时代的普及程度。从文学史的事实看,骈文的成熟期是在西晋时期。只有到了此时,当审美意识前所未有地普及到全社会的时候,当作家群体在创作中表现出对语言形式美的刻意追求的时候,骈文才真正得到了它适宜的文化沃壤,迅速地成长并成熟起来。而此前尤其是汉末以来的辞赋虽然较多地使用了骈对的句式,但毕竟尚未达到两晋南北朝骈文的那种程度和意识。况且作为文体的辞赋与骈文,尽管彼此的联系非常紧密,却各有其不同的源流和文体特征,尤为重要的是,它们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时段中发生并成熟的。早在骈文形成之前,辞赋便已定型而且成为笼罩文坛达数百年的主流文体。因此,两者的出现有先后之分,它们构成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从晋代开始的一些赋作,如陆机《文赋》、江淹《别赋》等作品,往往虽以“赋”名而全用骈句,与骈文毫无二致,对于这些作品便只能尊重作者的命名,以“赋”称者视为骈赋而归入赋类,不以“赋”称则可纳入骈文。这种分法虽然不是很科学,但却比较易于操作,否则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所谓丽辞,也就是对偶。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论对偶,首先肯定对偶是自然形成的,然后便是追溯对偶的缘起,从《尚书》、《易经》、《诗经》、《左传》、《庄子》等先秦典籍一直到汉魏的辞赋。文体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是先在一切与之相关的文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骈文也是如此。然而在这众多的文体因素中,对骈文影响最大、造成骈对句法在汉魏六朝大行其道,并直接促成骈体文成熟的是辞赋文学。惟其如此,许多骈文研究著作都把辞赋纳入其考察的范围,如刘麟生《中国骈文史》、金钜香《骈文概论》、姜书阁《骈文史论》、台湾张仁青《骈文学》等。
近人容肇祖指出:“自然汉赋未必是真实伟大的东西,但是这种体裁,曾经消耗几百年的天才们的智力,并且后来这种铺叙排比的体制,侵入散文里,成为一种骈文,发生的影响更大,差不多可以说,足足影响了二十多年的文人。”[1]台湾学者简宗梧也说:“当辞赋体式逐渐成为写作文章公式的时候,也正是赋体从大量排比以‘图写声貌’转化为珠连偶对以‘据事类义’的阶段,所以六朝骈文之兴,也正是文章辞赋化的结果。”[2]赋体作为汉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其地位是其它任何文学体类所无法比拟的。两汉文人才力的高下、创作的成就,都必须通过赋体的形式来得以展现,所以才有那么多天才的作家为此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以致杰出如张衡,为了作《二京赋》,竟然“精思附会,十年乃成”(《后汉书·张衡传》)。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五、七言诗逐渐兴起,但因其篇幅的短小,还不足以施展并显示作者的才力,故在文人的心目中仍然不可与辞赋同日而语。萧统《文选》中的赋作占全书篇幅的1/3,便反映了当时文人看看辞赋的文体价值观。辞赋文学地位之重要、笼罩文坛时间之长久,使它对数百年间的其它文体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巨大影响,其中自然也包括后起的骈体文。
赋体文学的主要内容是描绘外物、抒写情志,表现形式的主要特征是铺陈和叙写。这种功能和表现上的特点很容易导向排比和对偶句法的运用;同时汉代的赋在句法上继承了“楚辞”的传统,先天地带有骈偶化的倾向。汉赋因其主流的地位,将这种骈对的句法和观念推向它种文类,使汉代尤其是东汉的各体文章日益骈化,甚至连《汉书》这样的历史著作也未能避免其影响。而随着汉末赋作骈对风气的进一步兴盛,如《归田赋》一类篇幅较小、以抒情为主要内容的骈体赋陆续出现,各种文章受其熏染而更加注重对偶的运用,经过魏晋文人有意识的努力与实践,到西晋便成就了体制规范的骈文。所以说骈文定型和成熟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各种文章在赋体文学的影响下日益骈偶化的过程,骈文的成立,确乎是“文章辞赋化的结果”。辞赋是汉魏作家精力之所萃,是他们显示学识才力的主要文体,故赋体的创作除了状物言志外,还有扬名传世之目的,这就造成了此类作品特别注重辞藻的华丽和典故的频繁使用。因此,辞赋文学不仅在对偶这一关键性的因素上成就了骈文,而且在藻绘、用典等方面也对骈文有一定的影响。
二 楚辞句式形成骈偶的独特功能
汉魏赋体文学之所以多用骈对句法和华丽的词藻,以致对骈文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与楚骚的血缘关系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它句法的骈对特征主要是继承“楚辞”而来的。换言之,是“楚辞”特殊的语言组构方式造成了汉魏赋体的骈偶化,并进而影响到骈文的产生,汉魏赋体则只是充当了“楚辞”发展到骈文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把楚辞直接当作骈文的先声。如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云:“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自赋而下,始专为骈体,其列于赋之前者,将以骚启俪也。”近人徐嘉瑞也说:“六朝文人的骈文,是远接《楚辞》一派,由汉赋蜕变下来的。”[3]《四六丛话》论文,依次为《选》、骚、赋,然后才是其它文体。孙氏以骚为骈体之先声,而骚对骈文的启迪则是通过“赋”这一中介来实现的。姜书阁也赞成此说,他认为:“不但汉、魏六朝的骈文和赋从《楚辞》的骚赋来,即唐代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维、柳宗元、李商隐这些骈体文名家的名作,也是上继汉、魏、六朝,而渊源于楚辞的。”[4]
按照孙梅的看法,楚辞与后代赋作和骈文的承传关系均一一对应,如由《离骚》到《幽通赋》、《思玄赋》,由《国殇》、《礼魂》到《马汧督诔》、《祭古冢文》,由《天问》到《经通天台表》、《追答刘沼书》、《辨命论》、《劳生论》等等。用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来说明楚辞与后来赋及骈文的承传,显然十分勉强,因为楚辞之所以能通过赋体文学影响到骈文的生成与发展,并不是由某一篇或几篇作品的特点所决定,而是由楚辞总体的文体特征所决定的。
人们谈及楚辞作为“俪体之先声”对骈文的开启作用,一般都会列举出楚辞中各种类型的对偶句,例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类型:
1)《离骚》、《九章》型: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离骚》)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涉江》)
心*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哀郢》)
2)《九歌》型: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湘君》)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
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河伯》)
当然,人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楚辞中的对偶句进行分类:当句对如“屈心而抑志兮”(《离骚》)、“荪桡兮兰旌”(《湘君》),双声对如“忳郁邑余侘傺兮”(《离骚》),叠韵对如“聊逍遥以相羊”(《离骚》),重言对如“风飒飒兮木萧萧”(《山鬼》),四句中二、四句为对者如“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四句中二、三句为对者如“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等等。
楚辞中的对偶句数量之多、所占比例之大,确实是先秦其它文献所无法比拟的,然而考察楚辞对骈文的影响,无论列出多少对偶句都只能说明某种现象,而类拟的对偶句,在先秦的其它典籍中也可以找到。其实,楚辞之所以多骈对的句子,并导致后来赋体的骈化和骈体文的产生,是由它特定的语言组构方式所决定的。那么楚辞句式结构上的这种本质特点是什么呢?这便是以“兮”字为核心和枢纽的对偶式组构方式。楚辞的句式主要有《离骚》型如“○○○○○○兮,○○○○○○”和《九歌》型如“○○○兮○○○,○○○兮○○○”两种,前者“兮”字处于两句之间,后者“兮”字处于一句之中,但不管怎样,“兮”字都占据着句子中心的位置。在这两种句式中,“兮”字不仅是语音的中心,也是结构的枢纽,它规定了楚骚句子内部和两句之间的对应关系及基本节奏,同时也规定了楚骚句子必须以两两相对的偶句形式出现,否则就会破坏结构的平衡。当然,这两种句式也有相当的灵活性,“兮”字前后的字数即使不完全相等,也可以通过诵读时语音缓急的调节来达到平衡,但汉民族看重平衡与和谐的审美心理趋向,却诱使作家更多地去选择“兮”字前后字数的相等。这种字数的相等便给骈对句法提供了一个基本前提和实现空间,并从心理上进一步迫使作家在实义语言的搭配上更侧重其意义和结构的对称性,特别是当“兮”字前后两部分在意义上构成一种并列关系时更是如此。骈对的句法也就在这样一个不经意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楚辞对偶句式之所以普遍,根源就在于楚骚以“兮”字为中心的句式结构,也在于这种结构对创作、修辞心理的一种潜在规定性。
洪迈《容斋续笔》卷三云:“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烝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枻’、‘斫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阁序》,一篇皆然。”楚辞中的对偶句,除了《离骚》型的六字对句(“兮”字不算)之外,以所谓的“当句对”为最多。“当句对”在《九歌》中极为常见,因为“兮”字在一句之中,具备了产生这种对偶句的机能,洪迈所举的例子,便都是《九歌》的成句,只不过省略了“兮”字而已。值得指出的是,《离骚》型的句式因长度的缘故,不能不在“句腰”安排一个虚词或者意义较虚的词,以维持节奏的稳定,如“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句中的两个“而”字即为句腰,它们分别在两个分句中充当枢纽的作用,与《九歌》可型中的“兮”字有同样的功能,故这种句式也很容易产生“当句对”的对偶类型。
有些论者为了更详细地说明楚骚对骈文的启迪,到《楚辞》全书各篇中去搜罗例句,包括《招魂》、《渔父》和《天问》。其实这些作品中极少偶句,即使能找出少量类似的句子,也不足以证明骈文与它们的密切联系。楚骚的骈对特征,最集中而典型地表现在上述两种句式之中。正是因为这两种“兮”字句型独特的语言组构方式,使其具备了产生偶句的基础和条件,并将这种骈对基因传给它的嫡子——赋体文学,从而促成各体文章的骈偶化,进而逐渐在西晋形成了规范的骈体文。
三 由楚辞到赋再到骈文的演进
四言句和六言句是赋体文学和骈文最基本、最常用的两种句式,骈文发展到唐代,“四六”竟成了它的异名,可见这两种句式在骈文中的重要地位。人们常说古代文学的“风骚传统”,其实骈文在形式上也与这一传统密切相关。如果说骈体的四言句是从《诗经》继承而来,那么其六言句的来源则是“楚辞”。客观地说,楚辞不但给后起的赋体和骈文提供了骈偶化的基因与范本,而且还给它们提供了一种具体的骈对组构资源,那就是六言句。试看下面的例句:
屈原《离骚》:“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相如《上林赋》:“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渊淤之浦。”
班固《两都赋》:“仰悟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
张衡《归田赋》:“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
曹植《洛神赋》:“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
陆机《辨亡论》:“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
丘迟《与陈伯之书》:“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
庾信《哀江南赋序》:“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
王勃《滕王阁序》:“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这些例句皆出自从楚辞向骈文演进过程中各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其中的六言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句中必有一个虚字,如“而”、“之”、“以”等等,而这正是楚辞句式的重要特征。这种六言句因其虚字的存在而多了一层迭宕,在成熟的骈文中,它与较少使用虚字的四言句搭配,便形成了一种顿挫抑扬、虚实相间的特殊韵味。
就楚辞发展到正规的骈文之路向而言,是由楚辞到赋、到赋的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作文章、最后形成骈文;就其实现的方式而言,则是楚骚句式在赋体文学中“兮”字逐渐弱化乃至消失,形成以六言为主要句式的文体赋并日益骈偶化,然后为各体文章所利用和借鉴,最终形成骈文。这一过程从西汉初期开始,到西晋为止,长达六百余年,大体上可分成三个阶段来叙述。
第一阶段是西汉时期。汉初贾谊《吊屈原赋》诸作和淮南小山、庄忌等人的骚体作品,基本上是对屈原辞作的沿袭,形式方面并无大的变化。西汉中期司马相如《大人赋》、《长门赋》、《哀秦二世赋》依然保持着楚骚的形貌,《子虚》、《上林》等大赋则语辞诡滥,颇多对偶之句,对赋体尚骈的风气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此后王褒《洞箫赋》骚、散相间,俪语多而齐整;扬雄诸赋,或骚体或散体,多摹仿相如而偶句更甚。此时期无论是骚体赋还是散体的大赋,虽然对偶句较楚辞有所增加,但都是出于铺陈排比的需要,并非有意识的追求。
第二阶段是东汉时期。两汉之际班彪的《北征赋》虽为骚体,但其中有的句子“兮”字已经消失,作品虽无太多的骈偶,但也有“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这样相当工整的对句,可以说这篇作品揭示了楚骚句式是怎样演变成六言骈体句的线索。尔后冯衍的《显志赋》虽通篇为骚体,但大半为对偶句。这两篇赋作揭开了赋体文学骈对化的序幕,为骈体赋和骈体文的出现开辟了道路。此后无论是傅毅《舞赋》、班固《幽通》等小赋,还是《两都》、《二京》等大赋,对偶句的运用都非常普遍,到了汉代后期张衡的《归田赋》,几乎全篇为对偶句,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骈体赋了。此时期是赋体文学和各类文章日益骈偶化的时期,运用对偶的句法从事各体文章的写作,已逐渐成为一种为文人普遍认可的时代风气。
第三阶段是魏晋时期。汉末自由开张的文学氛围促进了抒情文学的发展,也强化了汉末以来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关注,骈偶化的赋作越来越多,曹植的赋作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例如他的《洛神赋》主要由对偶句构成,其中四言对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六言对如“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错综对如“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骚句对如“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兮若流风之回雪”等等,对偶精工,形式多样,充分体现了赋家运用骈偶句法的圆熟技巧。建安七子、曹丕等诸多著名文人的赋和其他文章,也大抵是这样的风习。到了西晋,注重对偶的风气越发浓重,傅玄、张华、左思、潘岳、陆机、陆云等一大批文人,无不将骈对的方式运用于他们的辞赋与各类文章的创作之中。例如陆机的《文赋》、《豪士赋》、《感时赋》等不少的赋作,基本上都是以六言为主,辅以少量四言,无“兮”字,篇中的对偶句十分普遍,像“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赋》)之类工整而优美的六言偶句,在他的赋作中随处可见。除傅玄和陆云喜用骚体外,西晋赋家大多采用不带“兮”字的六言句和四言句来作赋,而且多是骈偶的对句。从《离骚》“○○○○○○兮,○○○○○○”句型脱胎而来的六言句,经由汉魏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彪、班固、张衡、曹植等文人的运用与改造,日益骈偶化,终于在西晋蔚为大观,并与承《诗经》而来的四言句紧密融合,形成了“骈文”这一影响中国文坛极为久远的独特文体。
西晋是一个作家作品数量骤增的时代,也是一个注重文学形式之美的时代,陆机等文坛主流文人各体皆精,当辞赋骈偶化发展到极致并成为时代风气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将这种写法移植到其它各类文章的创作上。其结果便是当时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以骈偶的句式为主体,追求骈偶成为整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的意识和倾向。例如陆机《豪士赋序》中的一段:
且夫政由宁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起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见百姓之谋己,则申宫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惧万民之不服,则严刑峻制,以贾伤心之怨。
各种错综复杂的四六对和长对运用得熟练自如,已经是成熟而规范的骈文了。事实上,两晋南北朝有不少“赋序”皆为典范的骈文,从中似不难窥见赋与骈文之间的联系。正是在如此浓厚的骈偶意识弥漫于整个时代的情况下,大批规范的骈文涌现出来,如李密《陈情表》、陆机《辨亡论》、《与赵王伦荐戴渊疏》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发展到南朝,则追求俪语的风气更甚,遂使骈文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楚骚“兮”字句通过赋体文学这一中间环节促成了骈体文的产生,同时,在西晋以后成熟的骈文中,楚骚句式依然是构成篇章的语句材料。倒如孔稚珪《北山移文》:“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唐人卢照邻《悲今日》:“已濡首兮将死,尚摇尾兮求活。”唐人吕温《药师如来绣像赞》:“地万里兮天一极,往无由兮来不得。”等等,兹不赘列。相对骈体赋,骈文中的楚骚句使用得不是那么普遍,这是因为骈文多为序、启、表、赞等带有较强应用性的文类,而并非纯粹的抒情作品。这些用于骈文中的楚骚句式,往往本身就是对仗工整的偶句,且比构成骈文最常见的四、六言句有更强的咏叹色彩和错落流利的韵致,所以在骈文中不仅能增加句式变化,有效地冲淡因句式过于整齐所带来的弊病,而且还可以增强抒情性骈文的表达效果。
[收稿日期]2001-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