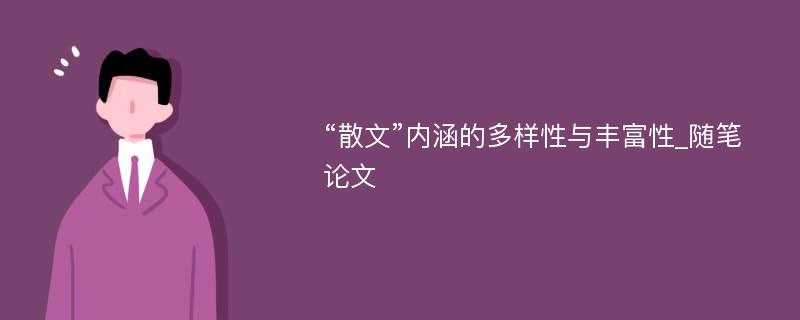
“随笔”文类内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丰富性论文,多样性论文,内涵论文,随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位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都会对于文类的划分,感到一种困惑和无奈,因为这一问题的探讨,常常使自己一不小心就会置身于悖论的境地。英国随笔家本森在《随笔作家的艺术》一文中就抱怨说:“为文学命名,为文学的表现形式分门别类,实在是一件纠缠不清的、令人扑朔迷离的事情,仅仅为了方便才不得已而为之。”(注:本森:《随笔作家的艺术》,《伦敦的叫卖声》,刘炳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第1版,第273页。)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文类的划分和设置,是人们对文学的性质和形式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并做出界定和阐释文类的标准和规则。只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被设定的文类的内涵和外延却常常处在动态的变化过程。有鉴于此,歌德做出“历史性文类”和“理论性文类”的划分意见(注:歌德语,参见Tzvetan Todorov《The origin of Genres》。转引自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8月第1版,272页。),这是极富有创见性的理论。任何一种文类的规则总结和边界设定,都有可能在其后遇到来自文类的内部或外部出现的“例外”力量对于这一理论概括的反抗和瓦解,小说,戏剧是如此,随笔也不例外。因此,随笔文类理论的建构应该是开放式的,要有一定自由度和包容性。
“随笔”,作为一种“历史性文类”在中国古代确实出现比较早,但作为一种文类的名称始于宋代。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自序云:“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此后,人们一般都认定洪迈所厘定的界说。清嘉道年间陆以湉作的《〈冷庐杂识〉序》就有一段涉及“随笔”定义的文字:“暇惟观书以悦志,偶有得即书之,兼及平昔所闻见,随笔漫录,不沿体例。”这就是说随笔内容是观书、阅世之所得,随笔的文字是随着思路率性而作,随笔的文体是不受传统规矩的约束。此正是随笔创作的“活力”之所在。同样在当代,人们还是对这一传统的定义颇为认同,张中行以为“随笔”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容,要“有情有识”;二是结构,“笔随着思路走”;三是语言,以“清灵”为好。(注:张中行:《我的随笔观》,《写真集》,作家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245页。)汪曾祺也认为:“随笔大都有点感触,有点议论,‘夹叙夹议’,但是有些事是不好议论的,有的议论也只能用曲笔。‘随笔’的特点还在一个‘随’字,随意、随便。想到就写,意尽就收,轻轻松松,坦坦荡荡。”(注:汪曾棋:《〈塔上随笔〉序》,《塔上随笔》,群众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1版。)那么,作为当今通行的辞书权威工具《辞海》也是这样诠释“随笔”的:“散文的一种。随手写来,不拘一格的文字。中国宋代以后,凡杂记见闻也用此名。‘五四’以来,随笔十分流行,形式多样,短小活泼。优秀随笔以借事抒情,夹叙夹议,意味隽永为其特色。”
在国外,人们对随笔的传统看法又是怎样呢?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指出:“杂文体裁在一五八○年得名于法国散文家蒙田。但在这以前,古希腊作家忒俄弗雷斯托斯(Theophrastus)与普鲁塔克,古罗马作家西塞罗与塞内加就开始从事杂文创作了。”(注: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101页。此处将"Essay"(随笔)译成杂文。)然而,在蒙田之前的古代西方随笔家并没有留下有关于论述“随笔”的文字。但是他们的随笔创作却无不时时提醒人们去理解他们对“随笔”的独特贡献。尤其是普鲁塔克,他撰写的《道德论丛》,常常为了要说服别人,而求助于实例、例证乃至逸闻,因而形成了“轶事”文体,这对后来的蒙田和培根影响很大。这也就是说,在普鲁塔克的时代,西方古代随笔的文体特点基本成形。在内容上,是杂俎,包罗万象,而以谈论伦理修养为多;在形式上大都采用苏格拉底式宣讲,柏拉图式对话或辩驳的方式,有些则是家庭聚会中的非正式谈话,颇有后世“席间漫谈”或“炉边闲话”的风味。而作为“历史性文类”的古代西方随笔,还是得到后来继承者的发扬光大。16世纪法国思想家蒙田,虽然他创造了"Essai"这名称,并成为近现代随笔的鼻祖。但他的随笔创造并不是空穴来风,相反他从普鲁塔克、塞内加那里,不仅获得生活的哲理和处世的智慧,而且从他们创造的随笔文体得到极大的启迪。P·博克曾称蒙田“杂谈”式的随笔文体,是“希腊议论文的一种复兴,常常用来谈道德问题,文章短小灵便,笔调生动、幽默,给读者一种亲切感,就像在聆听作者的娓娓之谈”(注:P·博克:《蒙田》,孙乃修译,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122页。)。到了后来,西方一些随笔论者也一直没能走出古代随笔所确立的规范。1775年,英国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在其编纂出版的《英语词典》中采用了蒙田的说法:“随笔是表达人们内心思想的一种松散的未经仔细推敲的短文,它既不完善,又不规则。”这就强调了随笔信笔写来,意到笔随,不大考虑结构上的精心结撰的结果。像这类观点,在西方学界还是代表着较为普遍的看法。英国学者W·E威廉斯(W·E·Williams)在"A Book of English Essays"一书中认为“英国的'Essay'花色繁多,但几乎没有规则”,但却给"Essay"下了一个定义:“Essay是一般比较短小的不以叙事为目的之非韵文。”这个随笔定义,强调承袭西方以议论为主的伦理随笔的文体特点,因而它其实就是对古代西方随笔文体认可的一种解说而已。在当今学界中,以译介英国随笔著称的刘炳善,在总结英国随笔文体特点的基础上,他认为随笔的形式非常灵活,变化多端,要想给它下一个确切、固定、圆满的定义是很困难的。但是,给它划个大致的范畴也还是可以做到的。首先,在文学的总范围内,先把诗歌、小说、戏剧放在一边。然后,在散文的大范围内,再把纯理性的议论文(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的科学论文、文论、批评论著等)、纯叙事文(正而八经的历史、传记、自传,大部头的回忆录等)、纯抒情文(像屠格涅夫、泰戈尔或纪伯伦那样的散文诗等)当作三个极端,让它们“三足鼎立”。于是再来看看这“三角地带”中间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散文小品。那么,不管是偏于发发议论而夹杂着抒发作者个人之情的,或者是偏于个人抒情而又发发议论的,或者是偏于叙事而又夹杂着一点议论和抒情的,还有那些文采动人、富有个人风趣的短评(又不管是社会评论、文学评论、艺术评论)——这些议论、叙事、抒情浑然杂糅,并且富于个性色彩、运用漫谈方式、轻松笔调所写出的种种散文小品,统统都可以叫做“随笔”。(注:刘炳善:《英国随笔简论》,《随笔译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9页。)
在日本,“随笔”作为“历史性文类”,早在平安中期就已产生,这是以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的诞生为标志。除此之外,鸭长明的《方丈记》(1212)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1324-1331),也是日本古代著名的随笔著作。但作为“理论性文类”,“随笔”一词来源于中国,最早出现在文坛上是室町时代(1392-1576),但是直至近代大正时期(1912-1925)才明确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18世纪时期,日本学者石原正明在《年年随笔》里这样诠释“随笔”:“随笔是将所见所闻的事,所言所思的事,郑重正言的事,随心所至而述下,故有把极熟识的事写错,并没有骨骼且显稚拙,成为很不堂皇的作品,然因其无修饰之故,能见作者的才华与气量,实为很有兴味的作品。”(注:石原正明语,转引自林林《漫谈日本随笔文学》,《散文世界》,1989年第6期。)可见,这个随笔定义,带有中国传统随笔定义的明显烙印。正因为如此,厨川白村在论西方"Essay"时,他不愿将"Essay"等同于日本传统意义上的“随笔”,指出“有人译Essay为‘随笔’,但也不对。德川时代的随笔一流,大概是博雅先生的札记,或者玄学家的研究断片那样的东西,不过现今的学徒所谓Arbeit之小者罢了”(注: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Essay》,《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64页。)。日本传统随笔的形式,与中国传统随笔的形式差不了多少,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传统的随笔并不都是“博雅先生的札记”或“玄学家的研究断片”,不少佳作尤其注重捕捉个人的情思和感兴,记录个人的见闻和体验,以情趣的赏玩为见长,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中国晚明的小品。在现代中国,有些专门从事日本随笔的译家,也颇为看重日本随笔的这一特色。周作人就曾称自己“大概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注:周作人:《明治文学之追忆》,《立春以前》,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69页。)。谢六逸在发表他翻译日本随笔家志贺直哉的随笔《雪之日》时,在译者《引言》中说:“日本的著作家虽然不少皇皇大作,但终未能掩盖这些小品文字的价值。它们如睡莲的滴露,如窗隙里吹进来的一线春风,是可爱的珠矶。再就文学理论上说,最能表现作家的真率感情的,也非这些小品文莫属了。”(注:谢六逸:《〈雪之日〉引言》,《大江》创刊号,1928年11月25日。)由引可见,即使是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对日本传统随笔独特韵味的赏玩并未减弱,因而他们所持的仍然是传统的审美标准。
通过对古代中外文学史所赋予“随笔”学理内涵的考察,何谓“随笔”这个问题的探究也就趋于明朗化。因此,综合中外传统意义上“随笔”内涵起码有这几个方面:1、题材不拘,内容多样。《辞海》中所说的“中国宋代以后,凡杂记见闻也用此名”,因而大量笔记类作品也冠以“随笔”名称,可见随笔的适用之广。2、笔随思路,率性而作。这里强调了随笔家心态的自由和开放。3、夹叙夹议,笔调灵活。可以有议论,有记叙,有抒情,有描写,有引证,有对话,营造出一个开阔舒展、情理兼备的论理系统,呈现出知识之美,智慧之美,思想之美,情趣之美。”
然而,由于随笔本身的灵活多样,人们对它的理解存在着歧异和不确定性因素。尤其是在广义散文的范畴之内,随笔与笔记、小品、杂文等都是这一大家族的成员,长相酷似,难分你我。柯灵说:“随笔与散文、杂文为兄弟行,胸襟放大,神形潇洒。”(注:柯灵:《随笔与闲话》,《新现象随笔——当代名家最新随笔精华》,韩小蕙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24页。)鲁迅在致书商李小峰的信中就曾将在该书局出版的《鲁迅杂感选集》,称之为“随笔集”(注:鲁迅致李小峰信,1933年3月25日,《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5页。)。周作人《再谈俳文》称:“英法曰Essay,日本曰随笔,中国曰小品文皆可也。”(注:周作人:《再谈俳文》,《文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37年5月14日。)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对散文、随笔、小品、甚至杂文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理不清楚。汪曾祺坦率地说:“我实在分不清散文、随笔、小品的区别。”(注:汪曾祺:《〈塔上随笔〉序》,《塔上随笔》,群众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著名学者季羡林也有同样的困惑,他说:“我还想就‘随笔’这个词儿说几句话。这个词儿法文原文是Essai。这一下子就会让人联想到英文的Essay,从形式上来看就能知道,这本是一个词儿。德文则把法文的Essai和英文Essay的兼收并蓄。统统纳入德文的词汇中。这在法、英、德三国文学中是一种体裁的名称;而在中国则是散文、随笔、小品等不同的名称。其间差别何在呢?我没有读‘文学概论’一类的书,不知专家们如何下定义。有时书上和杂志上居然也把三者分列。个中道理,我区分不出来。”(注:季羡林:《〈蒙田随笔全集〉序》,《蒙田随笔全集》,潘丽珍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那么,随笔、笔记、小品、杂文果真都是理不清楚的一团乱麻吗?笔者以为,从“历史文类”来看,随笔作品在中西方可以说是“古已有之”,尽管它在历史的演进中,其面貌发生了变异;然而就“理论文类”来说,随笔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又具有相对稳定的内涵和外延。因此,区分散文、随笔、笔记、小品、杂文的工作,还必须把它们放在中国现代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和辨识。按照“五四”后学界接受的西方文类的四分法,即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该“散文”概念就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广义散文的指称,它自然包括随笔、笔记、小品、杂文、报告文学、传记等。
随笔与笔记。笔记是中国古代富有特色的一种文体,它肇始于魏晋,而宋明以后最为繁富。《辞源》诠释有二,一是“古称散文为笔,与‘辞赋’等韵文相对,也称笔记”,这其实是指大散文的概念;二是“随笔记录的短文”,指的是宋代宋祁著有笔记,始以笔记名书。南宋以来,凡杂记见闻者,常以笔记为名。也有异其名为笔谈、笔录、随笔者。实际上,笔记与随笔都是在北宋和南宋才出现的文体名称,而且古人对二者常常并无严格的区别,凡“杂记见闻”者既可以称“随笔”,也可以称“笔记”。据褚斌杰介绍,中国古代笔记文大致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小说故事类,野史见闻类、丛考杂辨类、杂录丛谈类。这四类内容是相当庞杂的,除了小说故事类不好划归随笔外,其余均属于中国古代随笔的范畴之内。所以,随笔与笔记在概念上有重叠之处,但二者的外延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吕叔湘在编选《笔记文选读》时,他选择了以“随笔之体”作为选录的标准,他说:“搜神志异传奇小说之类不录,证经考史与诗话文评之类也不录。前者不收,倒没有什么破除迷信的意思,只是觉得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都可另作一选,并且已有更胜任的人做过。后者不取,是因为内容未必能为青年所欣赏,文字也大率板滞寡趣。所以结果所选的,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记一时之谐谑,或叙一地之风土,多半是和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似乎也有几分统一性。随笔之文似乎也本来以此类为正体。”(注:吕叔湘:《〈笔记文选读〉序》,《笔记文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7月新1版。)这种随笔之体的笔记,其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可写,随笔写去,是属于“质胜”之文,风格较为朴质而自然。因而,吕叔湘在选录笔记文时,难免以今人理解的“随笔”眼光来辑录,即笔记文中要带有思想或情趣的文章方可入选。记得王瑶在谈到“五四”散文深受外来的影响,尤其是英国随笔的影响时,曾这么说:“随笔、笔记一类文字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它的性质本与英国的随笔相近。”(注:王瑶:《“五四”时期散文的发展及其特点》,《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41页。)这说明了中国古代随笔、笔记类作品,与当今受西方影响而形成的现代随笔观念有其相通之处,只不过我们要如何以现代随笔观念去重新梳理和甄别。
随笔与小品文。小品,是明代文人把自己平常随意挥写的“独抒性灵”之作的称谓。这一名称是借用佛家用语,《世说新语·文学》有一句“殷中军读小品”,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可见“小品”是与“大品”相对而言,晚明文人也是在“篇幅短小”这个意义上使用它。《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也曾在这层意思上诠释:“散文品种之一。‘小品’一词在中国始于晋代,称佛经译本中的简本为‘小品’,详本为‘大品’。后遂以‘小品’统称那些抒写自由、篇幅简短的杂记随笔文字。”(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1084页。)但这种诠释还不够全面和准确。晚明文人把“文”分为“小品”和“大品”,在于把那些谈天说地、抒写性灵、言近旨远、形式活泼的小品文,从文以载道的重负中摆脱出来,而使之获得独立的文学价值。李鼎如以为《明文致》一书的编选,是“于朝家典重之言,巨公宏大之作,概所多遗。噫!此仅案头自娱,且姑撮一代之秀耳”(《〈明文致〉序》)。这说明了晚明文人已明确地把小品文和“巨公宏大之作”相区别开来,认为小品文是“案头自娱”的一类文章。这一观点在叶襄圣为卫泳辑录《冰雪携》作的序文里也有类似的表述:
卫子永叔爰自万历以后,迄于启祯之末,为文凡若干卷,自郊庙大章与夫朝廷述作,照碑版而辉四裔者,姑一切勿论。特取其言尤小者。遴数百篇以行于世。涂酌义专,又无訾于挂漏之病。曰:“吾识其小者,其大者固将有待尔。譬诸观溟海者,苦无津涯,而临清流则易以浏览;陟乔岳者,弥望无极,而视拳石或足以寄畅。卫子之志,亦犹是也。
这里,叶襄圣把小品看成是“郊庙大章”和“朝廷述作”那种庄严正大的大制作相对的文类,是“易以浏览”的“清流”和“足以寄畅”的“拳石”。因此,晚明小品的出现,本身就带有瓦解、反抗正宗“大品”地位的色彩和效用。而小品虽以“小”自居,但它讲究“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丽典新声,络绎奔会”(注:陈继儒:《媚幽阁文娱序》,《媚幽阁文娱》,郑元勋辑,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所以是“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注:郑超宗语,转引自唐显悦《媚幽阁文娱序》,郑元勋辑,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晚明“小品”颠覆“大品”的社会功用,追求独抒性灵、任意挥洒的自由心态,以及以“清”、“真”、“韵”为特色的笔墨旨趣,都令不少的“五四”知识者倾心折服、追慕不已。因此,到了现代中国,原本传统意义上的只指涉“笔记”的“随笔”概念扩充了它的内涵,也可用来包含像晚明一类的小品文。
由于小品文的精神特质与西方的"Essay"之文有相类似之处,所以有的“五四”知识者虽主张译成“随笔”,但也有不少人主张译成“小品文”。李素伯就说:“有人译作‘随笔’,英语中的Familiar essay译作絮语散文,但就性质、内容和写作的态度上,似乎以小品文三字为最能体现这一类体裁的文字。”(注:李素伯:《什么是小品文》,《小品文研究》,新中国书局1932年。)另一位学者方重更是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小品文就是英文里的Essay。”(注:方重:《英国小品文的演进与艺术》,《英国诗文研究集》,商务印书馆1939年4月初版,第46页。)但是并不是对这种译法,没有人提出过疑义。梁遇春曾称:“把Essay这字译做‘小品’,自然不甚妥当。但是Essay这字含义非常复杂,在中国文学里,带有Essay色彩的东西又很少,要求找个确当的字眼来翻,真不容易。只好暂译做‘小品’。”(注:梁遇春:《〈英国小品文选〉序》,《英国小品文选》,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初版。)这其中,以朱湘的反对意见尤其值得人们注意:
有一种最重要的“文章”:“爱琐”文。这便是普通称为“小品文”的那种文章;不过我个人不满意于“小品文”这个名称,因为孟坦(Montaigne),在西方文学内是正式的写这种文章的第一人,他有许多Essays在篇幅上一毫不小,有的甚至大到数万字的篇幅,至于在品格上,他的Essays的整体是伟大的,更是公认的事实。他,以及西方的另一个伟大的“爱琐”文作家蓝姆(Lamb),都是喜欢说琐碎话的。至于培根(Bacon),他的Essays,在文笔上,自然没有那种母亲式的琐碎,不过,在题材上,它们岂不也有一种父亲式的琐碎么?(注:朱湘:《文学谈话(七)·分类》,《朱湘散文》上集,蒲花塘、晓菲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251页。)
朱湘将“Essay”译成中文谐音字“爱琐”,又寓指“Essay”文作者喜欢说琐碎话,并拒斥“小品文”译法,这真是一箭三雕。朱湘的眼光较为犀利,他看出了“Essay”被译成“小品文”背后所存在的缝隙和人们普遍存在着对“Essay”误读的现象。因为晚明文人所创作的小品文以篇幅短小而见长,而西方的“Essay”就没有这条禁规,如蒙田《雷蒙·塞邦赞》,就长达十几万字。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朱湘认为西方“Essay”既有“母亲式的琐碎”,但也有“父亲式的琐碎”。也就是说西方随笔虽有娓语闲话的风格,但伟大的随笔家,他必定以思想的深刻博大和理性的批判精神而见长,是“父亲式的琐碎”。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用随笔概念可以涵盖小品文的指涉范畴,但反过来小品文就不好概括当今随笔所包容的复杂内容。
随笔与杂文。“杂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刘宋范晔的《后汉书·文苑传》中,而后梁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还有撰写“杂文”论,但他所认定的“杂文”,是指传统的“正体”文章即诗、赋、铭、赞、颂之类以外的无法归类的杂体文章,如“答问”、“七”体、“连珠”,以及“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等等。后来的苏轼在《答谢民师书》和王安石的《上人书》里,也以“杂文”来泛称传统正体文章以外的众多的一时无法归类的文章。这些有限的古代文论资源告诉人们:在中国,杂文是“古已有之”,杂文是非正体的杂体文。这种把杂文视为非正体的杂体文观念,到了现代中国仍还存在。鲁迅在晚年也曾说过:“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页。)而周作人在建国前对“杂文”的看法,基本上是持非正体的杂体文的观点。他说“所写的文章里边并无什么重要的意思,只是随时想到的话,写了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体制,依照《古文辞类纂》来分,应当归到那一类里才好,把剪好的几篇文章拿来审查,只觉得性质夹杂得很,所以姑且称之曰杂文”。他强调指出“杂文者非正式之古文,其特色在于文章不必正宗,意思不必正统,总以合于情理为准”,“杂文的特性是杂,所以发挥这杂乃是他的正当的路”(注:周作人:《杂文的路》,《读书》第1卷第1期,1945年。)。
而使“杂文”赋予现代意义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在从事“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鲁迅强调杂文在当时社会形势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页。)因此,《辞海》中关于“杂文”词条的撰写者,就倾向把“杂文”的诠释定位在其战斗性的传统上,认为杂文是“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以短小、活泼、锋利为其特点”,“‘五四’以后,杂文在鲁迅等作家手里发展成为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件或社会倾向的文艺性论文,颇具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论战性;艺术上,行文感情饱满,议论形象鲜明,有较强的震撼力”。由于人们带着这种杂文观念,穿行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生与死、血与火之中,这就使人们对于杂文就是“匕首”和“投枪”的结论深信不疑。因而,当20世纪末文坛刮起一股“随笔”创作热潮时,有的学者试图在杂文与随笔之间作个这样的区别和诠释:
杂文,是政治性比较强、社会性比较强的那种评议性的散文,属于硬性题材,作为原“议论散文”之一种,应予独立;随笔,包括随想、知识小品、科普小品、学者随笔、文化随笔、生活随笔等,是软性题材的评议性论文,作为原“议论散文”之另一种,也应独立。我个人觉得,杂文、随笔原是一类的,因为它们没有严格的界限,只存在题材上的软硬。杂文讲究讽刺,随笔注重幽默,二者都很讲究文采,这两种文体应合在一起予以独立。(注:刘锡庆语,见安裴智《辨误排疑看散文—刘锡庆教授访谈录》,《太原日报》1995年5月16日。)
笔者以为以题材的“软”、“硬”为标准,作为随笔与杂文的本质区别,这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也是不符合随笔和杂文的历史与现实,是误读的结果。原因有二,其一,杂文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非正体的杂体文”的观念,这就意味着不一定都要“政治性”很强、有“战斗性”的文章才能称之为杂文,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杂文创作也不是非得篇篇强调他的“肉搏”和“讽刺”。随笔固然有表现“软性”题材的一面,但往往在“硬性”题材上的作用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和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大英百科全书》就指出:“随着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敏锐的政治先觉者的出现,随笔成为宗教和社会批评的极端重要的武器。由于它灵活、简捷、对时事暗含一语双关的讽喻性,因此成为哲学改革者的一种思想工具。”(注:转引自张梦阳《〈大英百科全书〉关于散文的诠释》,《散文世界》,1985年1、2期。)世界随笔史上能成就为伟大的随笔家,诸如蒙田、培根、斯威夫特、尼采、厨川白村、鲁迅等等,也往往在“硬性”题材上显示出其思想的精深与博大。其二,鲁迅赋予的现代杂文观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渊源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后接受西方"Essay"影响而建立起来的现代随笔观念。厨川白村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鹤见祐辅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以及长谷川如是闲的随笔作品,都是鲁迅平常酷爱读的一类文章。尤其是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中一再表达这样一个观念,“建立在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根柢上的近代的文艺,在那一面,是纯然的文明批评,也是社会批评”(注:厨川白村:《出了象牙塔之塔·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92页。)。鲁迅的现代杂文观念就是建立在“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基础之上的。这说明了鲁迅的现代杂文观念,其实是在对现代文艺观念包括现代随笔观念的解读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因此,我们不能将杂文仅仅规范为只能所谓反映“硬性”的题材或定位在“战斗性的文体”。杂文研究专家姚春树先生就不同意这样一种偏狭的观点。他在充分考察、梳理古今“杂文”界说的基础上,重新厘定现代“杂文”的概念:“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对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注:姚春树:《中国杂文从古典向现代的嬗变》,《中外杂文散文综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8页。)显然,无论从概念的内涵还是外延来看,这一见解无疑是比较科学和准确的,因为它抓住了杂文体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且揭示出杂文固有的本质特征和美学品格。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现代的随笔与杂文“长相”极为酷似,确实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血缘关系。而我们既然否定了以题材的“软”、“硬”作为划分标准和依据,那么它们之间是否能够划上等号呢?笔者以为二者之间虽有重叠之处,但并不可以等同。朱光潜曾说:“‘小品文’向来没有定义,有人说它相当于西方的Essay。这个字的原义是‘尝试’,或许较恰当的译名是‘试笔’。凡是一时兴到,偶书所见的文字都可以叫做‘试笔’。这一类文字在西方有时是发挥思想,有时是抒写情趣,也有时是叙述故事。”(注:朱光潜:《论小品文——一封给〈天地人〉编辑者徐先生的公开信》,《孟实文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朱光潜在这里按随笔的表现功能,将西方的随笔分为议论随笔、抒情随笔、记叙随笔等三种类型,这一点对于我们区分随笔与杂文是富有启发的。尽管西方随笔源头以议论性随笔为主,但朱光潜将随笔分为三种类型还是比较符合随笔后来发展的客观情况。比如,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塞内加、普鲁塔克到文艺复兴的蒙田、培根都创作以议论性为主的伦理随笔,这种随笔文体通常被称为“杂谈”或“杂论”。但随笔在英伦三岛上后来的发展和壮大,随笔被应用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广泛。17、18世纪随着报业的崛起,随笔也被用来描写人物,并产生极好的社会效果。英国随笔的集大成者兰姆,他撰写的《伊利亚随笔》,其叙述和抒情成分都很浓厚,而议论所占的比重不大,常常是片言居要,起到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因此,从艺术的表现功能来看,只有随笔中的议论性“随笔”才能同狭义概念的“杂文”(即指以议论为特征的杂文,而非广义的“杂体文”)划上等号。鲁迅曾称:“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注: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3页。)英国的随笔是多种类型的,既有议论型,也有记叙型和抒情型。鲁迅所说的“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实际上就是指议论型的随笔。因而,鲁迅将杂文中即议论型的随笔说成近似于“英国的Essay”,这就显得鲁迅说这话时的审慎和有分寸。无疑,鲁迅这样的区分是准确和有价值的。
以上,我们就随笔与笔记、小品文、杂文作了一番的区别和鉴定工作,谈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关于这一点,笔者很赞同叶廷芳所认为的“随笔小于散文(或者说它是散文里的一种),而大于一般的小品文,它可以包括某些杂文和政论”(注:叶廷芳:《〈外国名家随笔金库〉序言》,《外国名家随笔金库》(上),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毋庸讳言,在目前随笔研究相对滞后的情况下,笔者所谈的这些想法只能是相对而言,不可能有绝对化的标准。因为作为构成这些文类的理论要素是极不稳定和活跃,它们本身常常出现互相串门的现象,再加上我们的前辈也常常在这个问题上缠夹不清。因此,对它们的清理和研究,不可能一下子就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非常成熟的界说。在此仅作抛砖引玉,期待方家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标签:随笔论文; 小品文论文; 散文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辞海论文; 鲁迅论文; 杂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