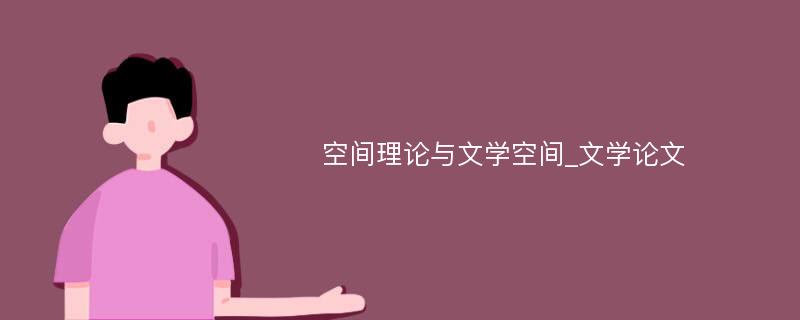
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论文,理论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末叶,学界多多少少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而此一转向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最是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学者们开始刮目相待人文生活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给予社会关系和社会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空间反思的成果最终导致建筑、城市设计、地理学以及文化研究诸学科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日俱增呈现相互交叉渗透趋势。对于现代都市空间经验这一从稳定一统向多元流动特征的变迁,文学的理解事实上不可能无动于衷。就小说中的城市空间而言,19世纪的模式被认为是叙述和描写,20世纪一方面都市生活的时间节律明显加快,一方面空间的经验也变得支离破碎。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回忆已无形式可言,乔伊斯和弗吉尼亚·沃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则使完整的叙述不复可能。那么,近年大有成为显学之势的空间理论对于文学又意味着什么?本文将就此作一探讨。
索雅与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是近年后现代学术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此概念由来于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雅(Edward Soja)1996年出版的《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Third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一书。爱德华·索雅出生在纽约布朗克斯(Bronx)区,据他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文化多元性表现得再明显不过的城区,他10岁时便活像个街头地理学家。什么是第三空间?索雅承认他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第三空间这一概念,是有意识尝试用灵活的术语来尽可能把握观念、事件、表象以及意义的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在更大的语境上看,20世纪后半叶对空间的思考大体呈两种向度。空间既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索雅提出的第三空间正是重新估价这一二元论的产物,据索雅自己的解释,这一理论把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均包括在内的同时,又超越了前两种空间,而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向一切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敞开了大门。
上承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Lefebvre)1974年出版的名著《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索雅分析了他所说的三种“空间认识论”。“第一空间认识论”最是悠久,索雅指出此一思维方式主宰空间知识已达数个世纪,它的认识对象主要是列斐伏尔所说感知的、物质的空间,可以采用观察、实验等经验手段,来作直接把握。我们的家庭、建筑、邻里、村落、城市、地区、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和全球地理政治等等,便是此一空间认识论的考察对象。第一空间认识论偏重于客观性和物质性,力求建立关于空间的形式科学,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与环境的地理学,因此作为一种经验文本在两个层面上被人阅读:一是空间分析的原始方法,就对象进行集中的准确的描绘,一是移师外围,主要在社会、心理和生物物理过程中来阐释空间。
比较来看,“第二空间认识论”要晚近得多,可视为第一空间认识论的封闭和强制客观性质的反动。简言之是用艺术对抗科学,用精神对抗物质,用主体对抗客体。索雅认为,它假定知识的生产主要是通过话语建构的空间再现完成,故注意力是集中在构想的空间而不是感知的空间。第二空间形式从构想的或者说想象的地理学中获取观念,进而将观念投射向经验世界。精神既然有如此十足魅力,阐释事实上便更多成为反思的、主体的、内省的、哲学、个性化的活动。所以第二空间是哲学家、艺术家和个性化的建筑家一显身手的好地方,不仅如此,这里还是倾情展开论辩的好地方,空间的本质是什么?它是绝对的呢,还是相对的呢,还是关系的?是抽象的呢,还是具体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呢,还是一种物质现实?思想起来都叫人颇费猜测。但索雅也承认两种空间认识论的界限有时候并不那么一目了然。他引列斐伏尔的话说,它们有时候仿佛是全副武装,打算决一死战,有时候却又一方包含而且促进着另外一方。而近年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等等思想和方法的融合,则是推波助澜,促使两种空间融合。第一空间分析家更多地求诸观念,反之第二空间的分析家们,也非常乐于倘佯在物质空间的形式之间。
“第三空间认识论”由是观之,它既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认识论的解构又是对它们的重构,用索雅本人的话来说即是,“它源于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是我所说的他者化—第三化的又一个例子。这样的第三化不仅是为了批判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思维方式,还是为了通过注入新的可能性来使它们掌握空间知识的手段恢复活力,这些可能性是传统的空间科学未能认识到的”(Soja 81)。作为“他者化”—“第三化”的又一个例子,很显然第三空间不仅仅是种批判和否定,诚如“解构”一语本身的肯定和建构意味已为大多数人肯定,“第三空间”认识论在质疑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在向先者注入传统空间科学未能认识到新的可能性,来使它们把握空间知识的手段重新恢复青春活力。为此索雅强调在第三空间里,一切都汇聚在一起: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等等,不一而足。如此而来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任何将第三空间分割成专门别类的知识和学科的做法,都将是损害了它的解构和建构锋芒,换言之,损害了它的无穷的开放性。故此无论是第三空间本身还是第三空间认识论,都将永远保持开放的姿态。
第三空间与《阿莱夫》
《第三空间》中,索雅辟专节就他的第三空间和博尔赫斯的“阿莱夫”作了比较。第三空间既不同于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又包容两者,进而超越两者。据素雅观之,就活像博尔赫斯同名小说中那个貌不起眼,却是包罗万象的“阿莱夫”(Aleph)。真可谓芥子须弥,极天际地。“阿莱夫”是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1945年写的一部短篇小说。Aleph是希伯来字母中第一个字母,神秘哲学家们认为它意为“要学会说真话”,在小说中,则活生生是个涵括万象的微观世界。小说开篇作者便引了两段文字作为题记,其一出自《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啊,上帝,即便我困在坚果壳里/我仍以为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国王。”其二出自霍布斯《利维坦》第四章第四十六节:“他们会教导我们说,永恒是目前的静止,也就是哲学学派所说的时间凝固;但他们或任何别人对此并不理解,正如不理解无限广阔的地方是空间的凝固一样。”索雅称他在重读了《空间的生产》后,再一次为《阿莱夫》这篇小说所倾倒。的确,博尔赫斯作品文体干净利落,文字精炼,构思奇特,结构精巧,小说情节常在东方异国情调的背景中展开,荒诞离奇且充满幻想,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正可与索雅的第三空间相类比。
关于阿莱夫,索雅引博尔赫斯自己的话说,永恒是关于时间的,阿莱夫是关于空间的。在永恒中,所有的时间,包括过去、现在、将来都共时存在。而对于阿莱夫,则全部宇宙空间原封不动见于一个直径一英寸许的光闪闪的小球里。他大段援引了小说里的有关文字:
我合上眼睛,过一会又睁开。我看到了阿莱夫。
现在我来到我故事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中心;我作为作家的绝望心情从这里开始。任何语言都是符号的字母表,运用语言时要以交谈者共有的过去经历为前提;我的羞惭的记忆力简直无法包括那个无限的阿莱夫,我又如何向别人传达呢?神秘主义者遇到相似的困难时便大量运用象征:想表明神道时,波斯人说的是众鸟之鸟;阿拉努斯·德·英苏利斯说的是一个圆球,球心在所有的地方,圆周则任何地方都不在;以西结说的是一个有四张脸的天使,同时面对东西南北。(我想起这些难以理解的相似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们同阿莱夫有关。)也许神道不会禁止我发现一个相当的景象,但是这篇故事会遭到文学和虚构的污染。此外,中心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综述一个无限的总体,即使综述其中一部分,是办不到的。在那了不起的时刻,我看到几百万愉快的或者骇人的场面;最使我吃惊的是,所有场面在同一个地点,没有重叠,也不透明,我眼睛看到的事是同时发生的:我记叙下来的却有先后顺序,因为语言有先后顺序。总之,我记住了一部分。
我看见阶梯下方靠右一点的地方有一个闪色的小圆球,亮得使人不敢逼视。起初我认为它在旋转;随后我明白,球里包含的使人眼花燎乱的场面造成旋转的幻觉。
阿莱夫的直径大约为两三公分,但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体积没有按比例缩小。每一件事物(比如说镜子玻璃)都是无穷的事物,因为我从宇宙的任何角度都清楚地看到。我看到浩瀚的海洋、黎明和黄昏,看到美洲的人群、一座黑金字塔中心一张银光闪闪的蜘蛛网,看到一个残破的迷宫(那是伦敦),看到无数眼睛像照镜子似的近看着我,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镜子,但没有一面能反映出我,我在索莱尔街一幢房子的后院看到三十年前在弗赖本顿街一幢房子的前厅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细砖地,我看到一串串的葡萄、白雪、烟叶、金属矿脉、蒸汽,看到隆起的赤道沙漠和每一颗沙粒……我看到曾是美好的贝亚特丽丝的怵目的遗骸,看到我自己暗红的血的循环,我看到爱的关联和死的变化,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之中看到世界,在世界中再一次看到阿莱夫,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我看到我的脸和脏腑,看到你的脸,我觉得眩晕,我哭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名字屡屡被人们盗用、但无人正视的秘密的、假设的东西:难以理解的宇宙。(qtd.in Soja 55-56)
博尔赫斯写到这里,自称他感到无限崇敬、无限悲哀。索雅则发现将《阿莱夫》的意义与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生产的理论联系起来,可以从根本上打破空间知识旧的樊篱,增强他所要说的第三空间的彻底开放性:一切皆见于第三空间,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它,其间万象无一不是清清楚楚,然第三空间又神秘莫测,从来没有人彻底看清它、理解它,它是一个“无以想象的宇宙”。故此,任何人想运用语词和文本来把握这个无所不包的空间,将终归徒劳。盖语言和文字都在时间里流出,此种叙事形式和讲述历史的方式,永远只能触及第三空间“阿莱夫”般共时态状的皮毛。索雅认为这里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与博尔赫斯描述阿莱夫是异曲同工的,一样不断提到语言、文本、话语、地理和历史编纂等等,实是无能为力完全把握人类的空间性的,或如《阿莱夫》篇首引的《利维坦》所言,无限广阔的地方:无限广阔的空间!
这个无限广阔的空间果真是言所不能言吗?我们的语言肯定未必如此不堪信任。索雅指出,同博尔赫斯的“阿莱夫”相似,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其所涉空间亦是形形色色,足以叫人眼花缭乱。他引述了米歇尔·迪尔在“后现代血统”中按字母顺序给出的各式各类空间形式,指出作者是将列斐伏尔视为批判性后现代主义的先祖。(注:See Michael Dear,"Postmodern Bloodlines."Space and Social Theory:Geographic Interpretations of Postmodernity.Ed.Georges Benko and Ulf Strohmayer (Cambridge:Blackwell,1996).)这些空间形式加上索雅自己添加上去的,大体有绝对空间、抽象空间、适宜空间、构造空间、建筑空间、行为空间、身体空间、资本主义空间、构想空间、具体空间、矛盾空间、文化空间等六十余种。这众声喧哗的不同空间何以和谐统一起来?索雅认为博尔赫斯的“阿莱夫”提供的沉思冥想模式诚然可佳,但是有折衷主义倾向,而如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所言,他的政治与理论工程是旨在探索走向不同的社会生活和不同生产方式的空间,因此它跨越了科学与乌托邦、真实与理想、构想与实际之间的鸿沟,探索既是“可能”又是“不可能”的辩证关系,并最终超越上述种两元对立,所以,列斐伏尔是始终关注着现实,与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过程密不可分。简言之,社会空间的社会生产,这就是列斐伏尔,也是博尔赫斯,给予“第三空间”的最大启示。
重读文学空间
空间作为社会空间的社会生产,这对于文学的理解意味着什么?现任教于英国达勒姆大学地理系的麦克·克朗(Mike Crang)在199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中,以“文学景观”为题专门讨论了文学中的空间含义。克朗属于近年开始崭露头角的文化地理学新锐,他指出,过去20多年里地理学家开始日益关注各式各类的文学作品,视之为探讨景观意义的不同模式。文学诸如小说、诗歌、戏剧、传奇等等,故此是各显神通,在展示它们如何理解和阐述空间现象。比如首先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描写,就是地理学的另一个丰富多彩的资料库。关于文学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克朗指出:
文本并不是单纯反映外部世界。指望文学如何“准确”地和怎样的应和着世界,是将人引入歧途。这样一种天真的方法错过了文学景观大多数有用的和有趣的成分。文学景观最好是看作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而不是视文学为孤立的镜子,反映或者歪曲外部世界。同样,不仅仅是针对某种客观的地理知识,提供了某种情感的呼应。相反文学提供观照世界的方式,显示一系列趣味的、经验的和知识的景观。称此种观点是主观论,实是错失要领。文学是一种社会产品——它的观念流通过程,委实也是一种社会的指意过程。(57)
这如列斐伏尔空间是为社会所生产同时也生产了社会的理论所示,文学故此同样是一种社会媒介,一个特定时代不同人众的意识形态和信仰,由此组构了文本同时也为文本所组构。文本组构了作者想说、能说,甚而感到不得不说的言语,同时又组构了言说的方式。所以文本是环环相扣,交织在它们或者是认肯或者是有意颠覆的文化惯例之中。而有鉴于文本必须有读者的阅读参入方可实现其身,故就意义的传达、流通和更新而言,读者的在场将和作者的写作行为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克朗因此强调文学不是举起一面镜子来观照世界,而是一张纷繁复杂的意义之网。任何一种个别的叙述,都难分难解牵擎到其他的叙述空间。这些空间未必一定要是文学空间,像官方文牍、学术著作,甚至宣传广告,都可罗列其中。文本就这样组成了一张观念和观念之间的大网,就在这大网之中,它确立了自己观照世界的方式。“现实主义”即为这样一种连接方式,但是它既不是准绳,也不意味排斥其他方式。而就其写实的意识形态来说,现实主义毋宁说是都市空间的产物。我们的空间经验当然不止是都市一种。对此克朗说,地理学的空间的文学方法,每一种都提供了理解一种景观的特定视域,每一种都吸收了其他方法,每一种都设定了它的读者群体,每一种都有它的修辞风格而求勾勒出令人信服的图景。文学和地理学当然有所不同。文学可以虚造想象地点,一如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忒休斯公爵所言,诗人的眼镜滴溜溜狂放地一转,可以从天上看到地上,赋形予压根就不存在的东西,可以给予子虚乌有一个居所和一个名字。但是谁又能否认文学在我们地理想象的形构中,确确实实出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呢?克朗指出,哈代不遗余力描写威塞克斯的乡情民俗,俚语方言,可谓展示了一种生动有机的地域文化身份。他毋宁说是在叙写一曲挽歌,哀悼那一种行将消逝的乡野景观和乡野生活方式。苔丝一家被迫离乡背井的凄惨命运写出了社会动荡和乡村贫困化的过程。而新贵德伯维尔家族则又活灵活现勾画出了社会分化中的一个层面。《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景观描写由此揭示了金钱的力量如何向乡村空间渗透,它再明显不过体现在阿列克斯对苔丝的控制上面。可怜的苔丝在这股焕若命运无远弗届的社会力量面前,根本就是一只束手待毙的无助的小鸟。这样来看,文学对于地理学的意义不在于作家就一个地点作何描述,而在于文学本身的肌理显示社会如何为空间所结构。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哈代了解了威塞克斯,哈代小说中的威塞克斯,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比较历史之中的那个威塞克斯,没有疑问是更具有“哲学”意味的。
但考究文学与地理学的空间联系关系并不是将一张地图重叠到另一张地图上面。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在文学文本的内部来探究特定的空间分野,这些分野可以同时见于情节、人物以及作家自传等等多种方面。克朗称进而可在文本里构建一种家园感(sense of home),由此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帝国主义和现代社会的地理知识。例如旅行故事中,典型的地理学结构就是设定一个家园,不论是失落的家园也好,回归的家园也好。他读出许多文本的空间故事,都在呼应这个行旅主题,主人公先是出走他乡,饱受磨难,历经种种奇遇,最后又回到家乡。甚至《吉尔伽美什》这样出自中东文明的人类最古老的史诗之一,都已经在丝毫不爽的展示这一模式。荷马的《奥德赛》亦然。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尤其将这个故事叙述得凄惨。其他如童话、骑士故事、民谣以及数百种小说的情节,包括流浪汉小说和更为晚近的旅行见闻,都可以见出类似的结构。
那么这结构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又是什么?克朗在这里看中的是性别政治的地理学。家园是给人以归属和安全的空间,但同时也是一种囚禁。为了证明自身的价值,男性主人公于是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进入一个男性的冒险空间,就像《奥德赛》里奥德修斯不得不离开家园,先是围攻特洛亚整整十年,然后又是历经整整十年回归故土。这缺场家园的二十年里他被认为是历经考验证明了自己的文化身份,特别是十年回乡途中,他是凭借典型的男人的智谋狡计,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妖媚女人。回到故国,则发现他的妻子帕内罗珀抵御浪荡子们求婚和儿子要求继位,已经是几无招架之功,乃不得不重施权威,再次确立家长地位。另比较特洛亚题材的五部史诗,《奥德赛》是唯一一部主人公平安到家的作品,便也足以发人深思。其他如《俄瑞斯忒斯》,阿伽门农回到家里,迎接他的是妻子与其情夫的合力血腥谋杀。回乡由此展示出更为凶险的意义层面,表明家园中的男权同样可以脆弱以至于如此不堪一击。克朗指出,假如细读文学作品中这一家园的空间结构,可以发现,起点几乎无一例外是家园的失落。回家的旅程则如是围绕一个本原的失落点组构起来。有多不胜数的故事暗示还乡远不是没有疑问的主题,家园既经失落,即便重得,也不复可能是它原来的模样了。所以,在这一结构中构建的“家园”空间,可视为一种追根溯源的虚构,一种追缅失落之本原的怀旧情绪。这又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文学描写可以揭示空间如何组构,以及空间如何为社会行为所界定。文学中空间的意义,由是观之,较之地点和场景的意义远要微妙复杂得多。
文学中的空间一大部分是城市的空间,克朗指出小说描写城市早有悠久的传统,但城市不光是都市生活的资料库,不光是故事和情节于中展开的一个场景,不论它叙写得怎样绘声绘色。城市景观同样也表现了社会和生活的信念。为此他举的例子是雨果的《悲惨世界》。他指出,雨果围绕巴黎来构建小说的中心情节,那些穷人居住的窄街小巷就构成了一种黑暗的想象性空间,那是城市未知部分的一种神秘地理。克朗指出小说是采取了居高临下的全景式视角,可是这视角依然是无法企达关于城市的全部知识,城市依然显得晦暗阴森,凶兆密布一如迷宫。而另一方面,与这穷人的陋巷空间针锋相对的,是官方和国家的空间。这里克朗发现雨果是有意识针对这些穷街陋巷描写了那些今日巴黎引以为豪的通衢大道。大道通向迷宫般的窄街小巷,成为军队和警察镇压穷人的通衢。故此,一边是开放的、正规的国家控制的地理空间,一边是晦暗的狭窄的贫民的空间,两者适成对照。小说因此可以被读作利用空间描写来寓示一种知识地理学,揭示国家怎样应对潜在的市民暴动,所以,它也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地理学。克朗认为这一说法并不过分,例如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首当其冲被摧毁的东西之一,就是街灯。因为正是街灯,让警察看见穷人们在干什么。这样来看,巴黎的街灯便是权力的眼睛,勾画出了监视和控制的公共地理学。这里光明和黑暗的象征意义,和我们对这个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解,又是多么不同。
如果我们以19世纪的巴黎作为起点,克朗说,那么我们可以发觉都市生活的情感经验在历经怎样的变化。工业化的核心概念即是现代性。城市的现代化导致它无边扩张,结果是城市的空间大到无以认知。说明这一点,只消将旧时的村庄的概念同今日的城市作一比较。他指出,早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就有社会学家西美尔等人将村落与城市比较,指出村落的社群里人与人直接交往,对彼此的工作、历史和性格都十分熟悉,他们的世界相对来说是可以预知的。反之现代城市则是陌生人的世界,人与人互不相识,互不相知,乡村的宁静平和为都市的喧嚣骚动所取代。而在文学中,波德莱尔的19世纪中叶巴黎的“闲荡者”(flaneur)形象,就是很典型的现代城市的见证人。这个“闲荡者”别无所事,所好就是在街头转悠,将都市的喧嚣骚动当作风景来细细品赏。他的目光在新空间里如林的新商品上一一扫将过去,看着街上车水马龙,物欲交换川流不息,心里不由得就感到几分满足。所谓的新空间,指的是19世纪巴黎触目皆是的拱廊街和百货商店。克朗提醒这个“闲荡者”的性别:他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公共场所对于资产阶级妇女来说,看来并不是个可以慵懒闲逛的好去处。这个男性的闲荡者由此和左拉小说里的妇女们形成鲜明对照。左拉笔下的女人也为琳琅满目的商品痴迷不已,但是她们逛商场不逛大街。商场这个封闭的空间比较流连市井街道,克朗认为,它成为文学的中心场景标志了都市空间从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的转移。它不仅是建筑和经济的移位,同样也是城市经验的移位。
文学在克朗看来是参与了这一空间经验的转移。“闲荡者”于波德莱尔和福楼拜这样的作家都具有浓重的自传性质。文体风格对于城市描写的影响,也大有不同。是以文学作品不应被看成仅仅是反映或描述了城市,仅仅是种资料库。事实上以往大多数地理学家读文学作品,基本也就是奉行以上读解理念,将作品视为被动的社会科学的现成资料,指望它们可以提供清澈透明的信息。但小说家肯定不是地理学家,克朗指出,我们相反应当细细考察城市如何建构在小说之中,诚如前面雨果的例子所示,以求确认现代性不光是流于字面的描写,而本身就成为城市描写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故此,波德莱尔的诗作不光是巴黎写景,相反其文本自身似乎也参入了这“闲荡者”的诡异行踪,一路游荡过无数人等,可是永远也无以把握整个城市。因为都市的空间经验,根本就不会容忍这样一种居高临下的把握模式。
由此可见,文学与空间理论的关系不复是先者再现后者,文学自身不可能置身局外,指点江山,反之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本身成为多元开放的空间经验的一个有机部分。要之,文学与空间就不是互不相干的两种知识秩序,所谓先者高扬想象,后者注重事实,相反毋宁说它们都是文本铸造的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凸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意味深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