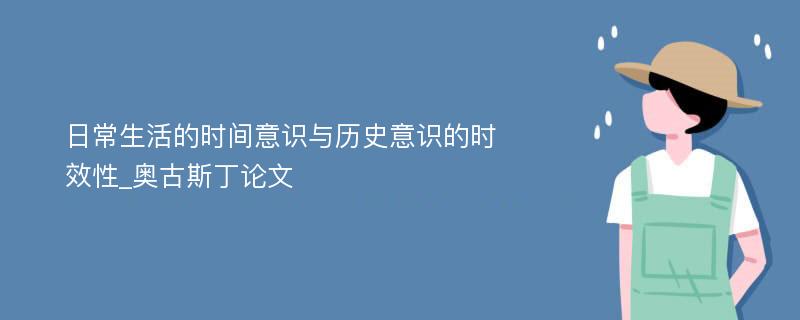
日常生活的时间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时间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时间性论文,日常生活论文,时间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只承认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科学。这门科学主张历史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下进行实践的人们的连续建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一方面表现为特定的为现实的人们所继承的物质生产方式内容,另一面它又表现为处于流变之中的“暂时性”。这个暂时性作为历史的根本特征并不是作为本体论的时间而出现的,而是和历史辩证法下的人的实践特征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这一原因,它只是到工业文明之后才为我们所把握。
工业文明之前,人们受制于“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的狭隘的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的时间意识构成人们历史意识的基础,表现为主体活动的事件的连续性直接构成人们历史意识的经验内容。而时间具有不可还原的本体论特征,如果说流动性与永恒性相对,那么作为个体人生体验的时间性就在于对永远不能企及的永恒性的连续追逐。因此,作为永恒的造物主对个体具有绝对的权威,永恒成为基督教的唯一时间:物体只能在时间中运动,上帝是时间本身。由此,人们的活动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整个人生也是如此,人生不过是人类整个历史的一部分,则整个人类史又何尝不如此。(注: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6页。 )这是宿命论(决定论)的基础。
但是,正是奥古斯丁所忏悔的时间问题第一次清晰而正确地表达了日常生活的时间意识与人类历史意识的时间性的关系,也揭示了个体与历史之间的矛盾性质。他指出:说时间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类是不确当的。或许说:时间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三类,比较确当。这三类存在于我们心中,别处找不到;过去的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的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的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注: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7页。 )由于个人拥有的只是当下感觉,所以作为圣徒的奥古斯丁最终将永恒给予了上帝。但是,作为人的奥古斯丁与作为基督教圣徒的奥古斯丁并没有因为这样就获得了自己的统一性,人“能根据已经存在而能看见的预言将来”这一自然模式的因果性与上帝给予时间这一非自然模式的时间观念严重冲突着。为了解决这一冲突,他只能说人所能够看见的只不过是上帝已经安排好了的。
如伽达默尔所言,奥古斯丁“不是真正使‘时间’、而是使作为意识的时间意识成为主题,并使‘时间’的存在空间返回到在毁灭与聚集,畏惧、希望和懊悔之间的生命张力。”也就是说,他就将日常生活的时间意识导入历史。当然,这绝不是说作为人的奥古斯丁已经具有了真正的历史观念。
事实上,真正的历史观念是作为近代科学和近代哲学的产物而内在地和工业文明联系着的。近代科学的发展使人第一次意识到人对自然的支配能力,也真正开始了摆脱自然必然性而趋于人类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近代哲学以其自然科学模式重新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意识。它首先证明了思维只不过是一种“意志的活动、理智的活动、想象的活动和感官的活动”,而上帝本身只不过是“具有上帝观念的我们自己的存在”的思维结果。(注: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0—171页。)因此,当笛卡尔宣称:“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构造出世界来”时,他事实上已经肯定了时间也只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属性,“神”在历史之中的作为只不过是“运动的根本原因”。由此,神被赶出了历史。进一步,斯宾诺莎指认“神即自然”时,运动的绝对性与必然性使我们能够第一次直面自己的历史——人类史。
但是受制于牛顿物理学之自然星空,人类可能拥有的只是“一部服从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因此,历史运动的最高点即是那个“社会的合目的性”——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人类历史也就终结了。(注: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近代哲学所能够获得的历史意识,也只能使历史从天体回环运动的自然本体论模式中解放出来,形成明确的线性史观和决定论史观。因此,在康德那里,同时留下一个问题:工业使得人类看到自己的力量,但人们却现实地被更高的“自然”历史所围困。黑格尔看到了这一点,他开始用超越牛顿物理学的眼光来看持时间和历史。他将当下的完成看作是历史的终结点,从而也是“时间的收成”(伽达默尔语)。他指出:法国大革命真正是世界历史的,它实现的自由原则证明了“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观念”的发展。“哲学所关系的只是‘观念’在‘世界历史’的明镜中照射出来的光辉”。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证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只有这一种认识才能够使“精神”和“世界历史”同现实相调和——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在每天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因此,在他之后历史的终结问题成为历史性的最为重要的命题,也成为历史性争论的核心问题。但是进一步,基于自然必然性的历史的死亡或终结,也就意味着人的历史的真正开始。黑格尔肯定了人通过劳动而收获历史的可能,但是他不愿意将这一收获看作是“暂时的”,所以,他无法从本体论的时间中走出来,而将历史又重新拉回到永恒的循环中。
真正使历史从本体论的时间中解放出来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历史科学并不是自然史,而是人类史,它从一开始就和人类的实践特征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历史观中,时间是作为人类实践的表现而存在的。在前工业文明之中,中国人用“一袋烟工夫”或“一里路光景”来表达时间意识,这和工业文明之中“时间即是金钱”是同构的,但是二者却充分表现出不同实践水平之上人类历史展开形式的差异。事实上,工业文明之后,自然是必然地退隐和消失的。虽然我们可以从生态学的角度来批判导致“自然之死”的工业文明,但不能否定的是,工业文明使人类真正驾驭自己的历史成为可能。更进一步,这也加剧了人类历史的复杂性,在摆脱自然的物役性之后,人类则受制于历史的似自然性。
在这个似自然性牢笼之中,奥古斯丁的问题在20世纪的海德格尔那里再一次形而上学地再现出来。海德格尔对时间的讨论仍然是从本体论进行的,不过在他那里,本体论只是更为深层的提问方式,他要将这种提问方式来塑造当下的真理。因此,当他说时间的基本现象是将来时,他所肯定的也只是当下的暂时性。所以他强调历史之谜就在于:何谓历史性地存在。(注:海德格尔:《时间概念》,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97年版。)在他看来,人类作为人的日常在世方式(当下性)之“烦”——作为与外物发生关系的烦忙和作为与他人发生关系的烦神——的“境域”的“时间性”有三个环节:曾在、将来和当下。而时间本身不是一个现成摆在那里、均匀地流逝着的存在者,而是不断涌现,不断出现,不断“到时”。这样他就将奥古斯丁的“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三维模式代之以“本真的”时间性,而“烦的结构的源始统一存在于时间性”,由此他认为当下存在者的创造过程平息了他的生存悲剧(技术理性之下此在的荒谬性),而以此在的历史性消解了似自然性牢笼的合理性,而以与流俗解释的斗争使此在的人的存在获得意义。(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二篇第五章。)
如果将海德格尔直接解释为马克思主义者,恐怕也会遭到他本人的反对。但是,他对此在历史性的分析,以及由此展开对存在的历史的意义探讨,从存在的历史的本质来思新时代人的无家可归的状态,这种方式确实超越了绝大多数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进一步讨论这一主题时,他就站得更高,在历史意义上肯定了马克思历史观点的优越性,而扫荡了胡塞尔、萨特等人在历史领域的浅见。(注:《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83页。)他真正地使历史意识与日常生活时间意识、 从而也使之与自然科学的时间模式区分开来,成为真正地属于历史的东西。
回到马克思,臣服于生产方式的既定性牢笼的日常生活的时间意识并不是真正的历史性,历史性作为时间,它是生产方式运动的形式,只要人类实践活动尚未停息,历史就不能真正完成。因此,关于历史的终结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话,在所谓知识经济条件下关于终极未来的产品设计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想象。
标签:奥古斯丁论文;
